明人对书院的态度.docx
《明人对书院的态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人对书院的态度.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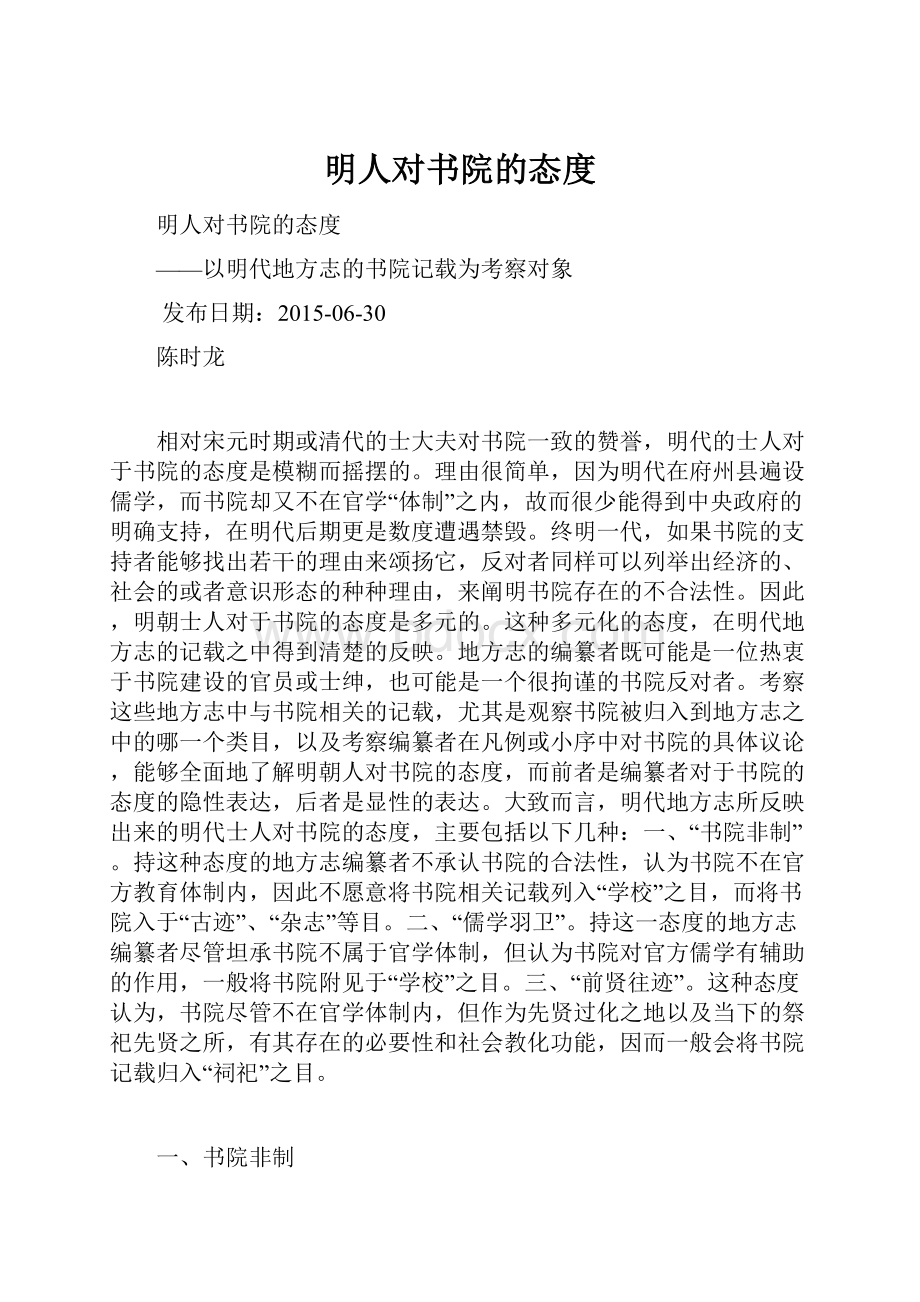
明人对书院的态度
明人对书院的态度
——以明代地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
发布日期:
2015-06-30
陈时龙
相对宋元时期或清代的士大夫对书院一致的赞誉,明代的士人对于书院的态度是模糊而摇摆的。
理由很简单,因为明代在府州县遍设儒学,而书院却又不在官学“体制”之内,故而很少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明确支持,在明代后期更是数度遭遇禁毁。
终明一代,如果书院的支持者能够找出若干的理由来颂扬它,反对者同样可以列举出经济的、社会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种种理由,来阐明书院存在的不合法性。
因此,明朝士人对于书院的态度是多元的。
这种多元化的态度,在明代地方志的记载之中得到清楚的反映。
地方志的编纂者既可能是一位热衷于书院建设的官员或士绅,也可能是一个很拘谨的书院反对者。
考察这些地方志中与书院相关的记载,尤其是观察书院被归入到地方志之中的哪一个类目,以及考察编纂者在凡例或小序中对书院的具体议论,能够全面地了解明朝人对书院的态度,而前者是编纂者对于书院的态度的隐性表达,后者是显性的表达。
大致而言,明代地方志所反映出来的明代士人对书院的态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书院非制”。
持这种态度的地方志编纂者不承认书院的合法性,认为书院不在官方教育体制内,因此不愿意将书院相关记载列入“学校”之目,而将书院入于“古迹”、“杂志”等目。
二、“儒学羽卫”。
持这一态度的地方志编纂者尽管坦承书院不属于官学体制,但认为书院对官方儒学有辅助的作用,一般将书院附见于“学校”之目。
三、“前贤往迹”。
这种态度认为,书院尽管不在官学体制内,但作为先贤过化之地以及当下的祭祀先贤之所,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教化功能,因而一般会将书院记载归入“祠祀”之目。
一、书院非制
明朝初年,朱元璋命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使地方学校的规模与系统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修《明史》称:
“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
”[①]在朝廷遍设官学的背景下,元代以来逐渐官学化的书院开始面临生存困境。
明人郑岳(1468-1539)说:
“宋元时书院领于官,赐额割田,主以直学山长。
迨我朝定制归于学,而书院废。
”[②]地方志记载表明,明初有不少书院转变成了地方儒学,书院学田也变成了儒学的学田。
李国钧先生列举了杭州西湖书院、丹徒淮海书院、桂林宣城书院、徽州紫阳书院、东光兴贤书院等在明初都改为地方官学或社学的例子[③]。
类似例子还不少。
例如,广东惠州府丰湖书院,最早创于宋代宝祐年间(1253-1258),元代设山长,至明洪武初年乃“即之为县学,遂废”[④]。
福建建安县屏山书院在明初“改为建安县学”[⑤]。
江西乐安县鳌峰书院在元代有学田六百六十亩,“至明代罢官制归儒学,遂为学田”[⑥]。
浙江淳安县石峡书院创自宋代,明初“田入于官,士养于学,而书院遂废”[⑦]。
更有不少书院直接被拆毁作为他用。
例如余姚的高节书院始建于宋淳熙七年,“洪武中有千户刘巧住者,取其废材营三山所演武厅,遂就湮废”[⑧]。
显然,由于战争破坏及教育体制的调整,书院的发展在明朝初年陷于低谷期。
这个沉寂阶段大约持续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
即便是书院史研究者经常谈到洪武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朱元璋命设尼山、洙泗书院之事,也值得讨论。
《明太祖实录》记载:
“立尼山、洙泗二书院,各设山长一人。
”[⑨]然而,尼山、洙泗书院的创建,实际上却晚至永乐年间才得以完成,而山长之设更因“官制并无山长职衔”而从未实现[⑩]。
实际上,书院既不在体制之内,又不复有山长之设,兴废较前代更无常。
成化年间任河南按察副使的胡谧在成化十六年(1480)撰成的《伊洛书院记》中说:
“国家既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专宪臣以董之。
……然诸旧遗书院以不隶于官,如同文、嵩阳、颍谷三书院,皆荡然靡存。
”[⑪]《福清县志续略》记载龙江书院时说:
“洪武初,书院不复置官,日渐颓废。
”[⑫]显然,地方志编纂者充分认识到,体制的改变,是书院颓废的重要缘由。
清人杨廷望在历叙宋元时代书院的辉煌之后说:
“至明,而书院之旧者日以湮没,后虽有建立,亦寻即倾圮,不复如前制之详矣!
”[⑬]
朱元璋建立起了一整套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的系统的官学教育体制,并以它为基础进行科举选拔与官员任用,从而使宋代以来的书院被排斥到教育体制之外。
他的继承者们基本遵循这一祖制,多位皇帝都曾经明确表示书院“非制”。
弘治年间,吏部郎中周木上疏言:
“苏州常熟县故有学道书院,祀孔门高弟言偃,后废为公廨,乞仍旧修建。
”礼部的覆奏表示赞同,说:
“孔门弟子惟偃,生于南方,而北学于中国,南方学者得其英华,盖自偃始,宜如木所奏行之,或得并免偃后裔徭役,以慰其乡人景仰先哲之心,亦清朝之盛事也。
”明孝宗却最终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本朝无书院之制,且偃已通祀於学校,不宜重劳民”,重建学道书院的事情被搁置下来[⑭]。
嘉靖十七年,御史游居敬弹劾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请“仍禁约故兵部尚书王守仁及若水所著书,并毁门人所创书院,戒在学生徒毋远出从游,致妨本业”。
疏下吏部,吏部的回覆虽为湛若水本人辩护,但承认说:
“惟书院名额似乖典制,相应毁改。
”于是,明世宗下谕:
“书院不奉明旨私自创建,令有司改毁,自今再有私创者,廵按御史参奏”[⑮]。
从世宗批复看,是同意吏部“书院名额似乖典制”的说法。
也大概是从游居敬的弹劾起,重申了民间讲学之所不得以书院名的禁令,可以改称精舍。
耿定向在万历毁书院时说:
“书院名扁,非敕旨不得擅称,盖申自嘉靖初年,因甘泉为游台长居敬者所刺,部议改为精舍。
”[⑯]因此,地方官员创办书院,多向上级请示,以示不敢私创,有些甚至要向皇帝请示。
例如,宣德间大理卿胡槩奏命巡抚江南,向皇帝上奏说:
“访知嘉兴府洪武中旧有陆贽祠,湖州府有胡瑗书院,苏州府有范仲淹祠、魏了翁书院,今皆颓毁,欲从宜修整,未敢专擅。
”皇帝谕行在工部尚书吴中说:
“崇祀先贤,盖以表励后进,如不劳民,宜从所请。
”[⑰]虽然同意修建,但只是为崇祀先儒,而且还有“如不劳民”的条件,较宋元时书院之纷纷鼎建赐额,不可同日而语。
宋元时代频繁的书院赐额情形,对明代为教学、讲学而设的书院而言几乎绝迹。
《明实录》所记载的书院赐额的例子,大部分是赐给宗室及大臣用以储藏御赐图书或翰墨的书院。
唯一例外是成化间兵部右侍郎李敏(1425-1491)向皇帝上奏请求在家乡河南襄城县南的紫云山麓建书院,“愿籍之於官,以为社学”,得到了成化帝“紫云书院”的赐额[⑱]。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天启五年巡盐御史李缉敬疏请表彰河南张信民的正学会所为正学书院,至十月即“奉旨表正学会所为正学书院”[⑲],不过也没有赐额。
作为明代一朝典制汇编的《明会典》,在学校一门下,也仅设“儒学”、“社学”二目,清楚地表明书院不在学校体制之内[⑳]。
吕坤在其《实政录》中即说:
“官衙、吏舍、仓库、祀典、庙貌、坛壝、学校、桥梁、公馆,凡有损坏,不妨设处兴修……至于书院、阁亭、楼台、庙宇不关民义,切戒兴作,违者查究。
”[21]可见,在吕坤看来,非但书院不在学校之内,且属“不关民义”之物。
地方志中的书院记载,也反映部分明代士人认为“书院非制”的态度。
在一些明朝士人看来,明代的官学教育体制已然非常完善,因此不再需要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南直隶望江县学生员龙子甲受知县罗希益聘请主修《望江县志》,其卷二《学校》末论曰:
“汉兴,历四世始立太学;宋兴,历五世始立府州道学;我明兴,太学预兴于未登极之前,郡县学兴于登极之二年,社学兴于登极之八年,盖可谓轶汉宋,俪商周矣。
”[22]教育体制既如此完善,则书院便成了多余。
黄佐(1490-1566)在嘉靖《广西通志》中说:
“书院之建,何为者也?
肇自唐人禁中,以储书籍。
宋人踵之,以祀乡先生而施教焉。
既有学校庠序,则吾以为赘也。
”[23]黄佐并不完全反对创建书院,接下来他的话题一转,大谈书院对于相对偏僻的广东地区的重要性。
然而,黄佐之语却表明,府州县既然遍设学校,书院是否多余,其实一直是人们可以讨论的一个话题。
而且,明代从国子监到地方儒学、社学的学校体系,“仿三代庠序学校之雅意”[24],而随地而设的书院尽管自唐宋以来已然流行,在一些明代士人看来却是悖离古制,相应有一种书院“非古”的议论。
曾总督两广军务并在广西梧州创建岭表书院的陶谐(1474-1546)就曾经表示说:
“书院非古也。
”[25]万历《广东通志》的编纂者说:
“里塾废社学,兴书院,非古。
”[26]释如一在《福清县志续略》中也说:
“书院非古制也。
”[27]
然而,认定“书院非制”,并不代表官方对书院的态度是完全排斥的。
明朝景泰年间朝廷编纂《寰宇通志》,书院与学校并列,是该志三十八门之一。
天顺五年(1461)编成的《大明一统志》,以南北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分区,以府、州为单位,下设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祠庙、陵墓、古迹、名宦、流寓、人物、古迹、列女、仙释等二十门。
因此,士人们往往会从《大明一统志》所设的“书院”之目寻找书院的合法性。
嘉靖《广平府志》的编纂者陈棐(1535进士)就说:
“圣祖于即位之先,即立国子学;洪武二年,诏天下立府州县学,八年诏立社学;……嗣亦崇重书院,故《一统志》于前代书院,首登载之。
”[28]万历己未(1619),杜应芳倡修《四川通志》,于凡例中说:
“统志例有书院一款。
万历初,裁革书院,易以他名。
今散见于学校宫室内,以待兴复云。
”[29]只是因为万历初毁书院的政治压力,地方志才将书院散见于其他目内。
二、作为“前圣古迹”的书院
明代是官修志书发达的年代,大量地方志是在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的指导下进行的。
因此,书院记载归入何种门类,一方面取决于地方志编纂者的态度,另一方面却也受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的影响。
修志凡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既然正式的官方教育体系不再有书院的栖身之所,曾经广泛存在的宋元书院又当如何在地方志中体现?
永乐十年(1412),朝廷颁布《修志凡例》十六则;永乐十六年(1418),再颁《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则[30];前后两次颁行《修志凡例》,由十七门增至二十门,基本上只是条目分合,差异不大。
永乐十六年《修志凡例》规定了官方对书院记载的标准处理办法:
书院不归入“学校”,而归入“古迹”。
按照这一凡例,地方志下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乡镇、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仙释、杂志、诗文等二十门。
其中,“学校”门不录书院相关内容。
“学校”的门类下所应载的内容包括:
“叙其建置之由,续修理者何人,廨舍、堂斋、书籍、碑记并收录。
学官、科贡、人才并详收录,有碑记者亦录”。
唯有“古迹”一门,有涉及书院者。
永乐十六年《修志凡例》载:
“古迹。
凡前代城垒、公廨、驿铺、山寨、仓场库务,古有而今无或改移他处者,基址亦收录之。
……亭馆、台榭、楼阁、书院之类,或存或废,有碑记者亦备录于后。
”[31]永乐年间所定的《纂修志书凡例》对此后的地方志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统年间,清丰教谕吴骥受命编纂《大名府志》,在《凡例》中说:
“永乐十六年礼部颁降《志书凡例》,已有定式,故今之所囗囗囗遵其次序囗。
”[32]句中虽有模糊不清处,大概能知道《大名府志》应是遵从永乐十六年礼部颁降的修志凡例的。
成化《湖州府志》亦在凡例中说:
“志书悉以礼部所颁式为准。
”[33]
受永乐《纂修志书凡例》的影响,把书院作为“古迹”加以记载的例子,在明代地方志中比较常见。
弘治《保定郡志》自称“体仿《永阳志》”,并行列了数十个门类,书院记载在卷二十二的“古迹”门下。
[34]弘治《句容县志》,则将书院相关记载归入卷五地理类之下的“先贤遗迹”门[35]。
当然,书院记载归入“古迹”门,最著名的当数康海(1475-1540)的正德《武功县志》。
康海是明正德年间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方志理论家,“简派志家”的代表。
康海认为,永乐《纂修志书凡例》分目过细,而方志应叙次雅洁,类目不宜过繁,一般设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等门[36]。
正德十四年(1519)修成的《武功县志》七篇,基本上采取这样的体例[37]。
《四库全书总目》称:
“是志仅七篇,曰地理,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赋,曰官师,曰人物,曰选举。
凡山川、城郭、古迹、宅墓,皆括于地理;官署、学校、津梁、市集,则归于建置;祠庙、寺观,则总以祠祀;户口、物产则附于田赋;艺文则用《吴郡志》例,散附各条之下,以除冗滥。
” [38]其中涉及武功县绿野书院的记载便是出现在地理篇的古迹之下,文曰:
“绿野亭今在县南郭东外,为宋儒张子子厚寓所。
张子与武功簿张山甫厚,故武功弟子因从子厚游,亭此讲学焉。
弘治八年(1495)冬,户部尚书沁水李瀚(叔渊)时以御史巡按至,诸生以白,御史乃谋于提学副使今少傅吏部尚书杨公一清。
杨公以知县(宋)学通有良治,能用其民,一以责学通。
踰年乃成,改曰绿野书院,择师授徒。
……今去改建才二十三年矣,其废坏已十四五矣。
”[39]康海本人在弘治年间曾被陕西提学杨一清拔入正学书院肄习,正德间亦曾与吕柟等人讲学于云槐精舍,对书院有一定的感情。
绿野书院乃宋儒张载讲学处,又经杨一清檄建,康海对其历史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三原学者王恕记载说,杨一清“于西安在城修复正学书院,武功修复横渠书院”,[40]则当时已名为书院无疑。
饶是如此,康海并未将绿野书院视为学校而置于“建置·学校”,反而是放在“地理·古迹”之中。
虽然康海不满于永乐《纂修志书凡例》之复杂,并将古迹搁在地理篇下,但将书院记载置于“古迹”之中的做法,却又无疑是受到了永乐《凡例》的影响。
相反的是,成化《湖州府志》的修纂者张渊虽然自称“志书悉以礼部所颁式为准”,却将书院记载附见于学校[41]。
可见,编纂者在内容安排上,其个人对事物的态度是决定性的,而作为形式的体例是可以灵活变动的。
《武功县志》作为明代的名志,其对于书院相关记载的编排,直接影响到其它一些地方志。
嘉靖二十四年(1545),叶联芳修《沙县志》,卷五“学校”下设“庙学”、“教谕”、“训导”、“廪”、“增附”、“吏”、“乡饮酒”、“书籍”、“射圃”、“社学”、“乡社”、“木铎”诸目,几乎涉及所有教育或教化机构及其设施,唯独不载书院,但卷二“疆里”的“古迹”之目下,却明确注明“古书院、堂斋轩台亭宅附”,记载了豫章、了斋、风岗等三所书院。
显然,在叶联芳看来,书院既然不在官学体制之内,如豫章书院“今为豫章祠”,而另两所书院不复存在,就都应该视作为“古迹”。
[42]这种编排,与《武功县志》将书院记载置于“地理·古迹”之下的作法极为相似,而更远的源头则自然还是永乐的《纂修志书凡例》。
终明一代,将书院记载归入“古迹”的做法一直存在。
嘉靖《昆山县志》列“学校”之目,附载社学,而书院记载乃在卷二“古迹”——“石湖书院,在县治东南,宋范文穆公读书处,今为巡抚行台,邑人犹以书院称之。
”[43]嘉靖二十三年(1544)修纂的《永丰县志》在其凡例中说:
“书院久废,书于古迹。
”[44]隆庆《保定府志》、万历《安丘县志》也都将书院记载置于古迹志下。
[45]然而,随着明代中期以后书院建设的复兴,开始活跃的书院还能称作“古迹”吗?
嘉靖二十七年(1548)刊刻的《霸州志》,虽然将当时由按察副使周复俊创建并且尚存的文明书院列入卷四学校志之下的“书院”之目,但是,已然不存的书院如益津书院则收入卷一舆地志的“古迹”之目[46]。
这种区别对待,不仅秉守了明初以来将书院置于“古迹”的传统,又很好地兼顾了现实。
然而,同一事物分处两个门类下,对于地方志的体例却又是一种破坏,而且不便人们查阅。
因此,将书院记载按其尚存与否分置“古迹”与“学校”两个门类下的体例,并不为更多的地方志所接受。
与将书院收录到“古迹”中相近的做法,是将书院收入到“祠祀”或坛庙。
这种做法的前提,是肯定书院是先贤的遗迹:
它虽然不再有教育的功能,但却有宣扬教化的作用。
“非制”的书院得以保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书院通常是祭祀先儒的场所。
明人王鏊(1450-1524)在正德《姑苏志》中说:
“(苏州府)书院凡六,设官主教事者四,学道、文学、和靖、甫里。
子孙奉祠事者二,文正,鹤山。
今唯文正、鹤山存,而鹤山又为巡抚行台,乃以后屋为祭所云。
”[47]从《姑苏志》的叙述可见,当初“设官主教”的书院到明代都不复存在,幸存的只是“子孙奉祠”的文正书院和鹤山书院。
作为祭祀先儒的场所,书院的存在有其必要性。
李东阳在《重建文定书院记》说:
“宋之初,学校未立,故(书院)盛行于时,今虽建学置师遍于天下,无俟乎其他。
而前贤往迹风教之所关,亦不用废。
”[48]嘉靖《徽州府志》的编纂者汪尚宁曾说,书院之建有“三善”,可以“申大儒之祀,复名宦之迹,敦讲学之会”[49],把书院的祭祀功能排在首位。
隆庆五年(1571),广东太平府学训导甘东阳增补《太平府志》,感慨书院与先贤的关系,说:
“唐人禁中以储书籍,宋人踵之以祀先哲,此名贤之寓道德之光而士之观望操弧修德胥此焉籍也。
太平书院有二,而所寓者则翁公万达、胡公世宁也。
二公道术之正,事业之隆,脍炙人口,非独太平感之,虽天下莫不仰之也。
士业于此,登其堂宇,想其风韵,而身心道法咸则象之,虽不及人,不为忧也,岂独诵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哉!
”[50]在甘东阳看来,书院之存,就像寺观佛像之于信徒,有“象教”的功能。
释如一在其所纂《福清县志续略》中说:
“书院非古制也。
非古而举之,义也。
肇自唐人禁中,以储书籍,宋人踵之,以祀乡先哲而施教焉。
或者以为赘,然而名贤之寓,道德余光,亦何可泯哉!
”[51]对于一个不太重视书院的地方志编撰者来说,既然不少书院在明代只是作为先贤的祭祀场所而存在,他就更愿意只描写书院的现状,将书院归入“祠庙”、“祠祀”、“坛祠”、“庙祀”加以记载。
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十三“文事一”之下有“学校”之目,附“社学”,但没有书院方面的记载。
对书院的记载,出现在《重修毗陵志》卷二十七“祠庙”之中:
“东城先生苏文忠公祠,在郡城顾塘桥北……元至大间改建东城书院,至正末毁为民居”;“龟山先生杨文靖公祠,本旧书堂,在怀德门内十余步……元改创龟山书院,设山长一员主之……国朝成化五年广西佥事郡人郑观乃即今地创建祠屋四楹,中塑先生像,以二周配。
”[52]显然,《重修毗陵志》的编纂者深知这些祠庙作为书院的历史,但还是把它们归入“祠庙”之类。
隆庆五年(1571)张德夫初修、万历二十六年(1598)江盈科增修的《长洲县志》,其书院记载不见于卷四“学宫”,然其卷十一“坛祠”下有“横渠祠”,记载说:
“国初知府李亨嘉为九世孙工部郎孙避奏建横渠书院于乐圃。
……宋濂有记。
……嘉靖年间,十四世孙罗雄守哲令子庠生应基捐赀鼎建书院于家,呈请督学耿定向移檄有司照文正等祠例承祀。
”[53]具有“书院”之名的“横渠祠”,在万历《长洲县志》中并没有作为“横渠书院”来记载,而更强调其祭祀功能。
苏民望修、萧时中纂修的万历《永安县志》,其卷二“建置志”下有“疆域”、“学署”、“典籍”、“社学”、“武署”、“属署”、“庙坛”诸目,但“四贤书院”的记载既却不在“学署”,而以“祀吾延平杨、罗、李、朱四先贤”之故载入“庙坛”。
[54]
有些地方志不将书院归入“古迹”门,但处理方式亦与之相近,如将书院归入“院宇”或“宫室”之下。
正德《颍州志》卷二公署所附学校部分没有书院的记载,而关于西湖书院的记载则安排在卷一宫室之下。
[55]万历《池州府志》也没有将书院记载放在卷二建置下的“学校附社学”目,而置于“院宇”目。
[56]将书院归为“古迹”,或归为“宫宇”,只是将书院视为过往的一物质存在,而将书院归入“坛庙”或“祠祀”,则部分肯定了其教化的功能,但却都不认可书院在现实世界中还能起教育的作用。
然而,像万历《乐安县志》那样将书院归入“杂志”的做法则很少见。
万历《乐安县志》没有将书院安排在卷九“学校附社学”的部分,而是将书院放到全志最末的卷二十“杂志”之中。
编纂者在《杂志·叙》中说:
“志犹史也。
史之纪事也核,而其为文也精。
志则惟其事不惟其文,故存古传疑,殊条琐撰,无弗载焉。
夫灾祥以备监戒,信矣;寺观之设,虽非其正,有其举之,莫或废也。
妖□之事,君子不道。
宇宙大矣,何所不有。
八景终焉,则县之大概也。
志杂志。
”卷二十“杂志”收录明诚书院的史事[57]。
将书院载入“杂志”,在明代地方志中绝不多见。
按地方志的编纂惯例,杂志所载一般为异端或琐碎之事,所谓“事有无所系属,各志不及载者”[58],或“其他诡奇之迹、琐屑之言难以类系者” [59],其作用则“所以外异端、吊往古者”[60]。
万历《乐安县志》作者蒋奇镈大概是视明诚书院为琐碎之事。
民国《续修广饶县志》载:
“蒋奇镈,字乘埜,……少颖异,善书,工词赋,万历乙卯(1615)以第二人登乡荐……手辑《邑志》二十卷。
邑令孟楠为板行于世。
初愚谷太仆(李舜臣)病沈令清旧志之芜陋,因弃取进退之,其谨严典确,识者以比康对山之武功志。
奇镈因以为书。
今太仆志已不可考见,赖奇镈采列而并註所出,犹得窥先正义法,故为书益重。
同时有张四维、张孔教、陈菃、张孔思者,实左右其事。
”[61]编纂者或许在不经意中,将事迹偏少的“书院”等同于寺观、灾祥、景观之类可有可无的“殊条琐撰”!
三、作为“儒学羽卫”的书院
然而,书院果真是完全多余的吗?
在一些明朝士人眼中,事情远非如此。
他们认为,书院实际上是儒学的羽卫。
在官学日益衰败的明代中后期,书院作为官方儒学的必要补充的观点越来越突出。
正德年间,正德《南康府志》的编纂者就说,书院是先儒建来“以待天下有志之士”之所,“非学校外一宫墙也”[62]。
嘉靖《常德府志》的编纂者说:
“儒学之外,又有社学以为基本,书院以为羽卫。
”[63]黄佐在嘉靖《广东通志·凡例》中称:
“书院以辅学校之所不及,故皆详书之。
”[64]至晚明万历年间,书院作为儒学的必要补充的说法,进一步为人所接受。
万历《郧阳府志》的编纂者说:
“社学则儒学之基本,书院则儒学之羽卫。
”[65]章潢(1527-1608)在《新修南昌府志》中认为,社学、书院于儒学是有助益的:
“豫章宿称文献,广厉学宫,以开儒术,又有社学、书院相与翼而明之。
”[66]晚明安福人王时槐(1522-1605)认为,无论是士子赖以获得生员身份的官学,还是士子从事质疑辨惑的“山林授徒之所”(其实指书院),都是学校,是学校的不同呈现形式。
他在万历《吉安府志·学校志》的小序中说:
“今诸州县皆有学,社学所以翼之也,书院又所以翼之也。
士生吉郡,非挟策游郡国学校,则退而质疑辨惑于山林授徒之所,其犹有党庠术序之遗也乎。
”[67]万历四十三年(1615),北直录的饶阳知县万献策在《儒学学田记》一文中谈论说:
“天下郡邑,有书院以造士,有学田以养士,两者未可觭軽云。
”[68]崇祯《大城县志》的编纂者则称:
“名贤书院,亦所以羽翼夫学校者也,仿郡志悉附焉。
”[69]
那么,书院从何种意义上构成官办儒学的羽卫呢?
对此,嘉靖三十三年(1554)编纂《湘阴县志》的知县张灯在创建该县仰高书院时的一番议论,可以回答。
他说:
“郡县有学,学有斋舍,书院可已乎?
但今之斋舍存学宫者多隘陋难容,加之为县令者不时加修葺,或鞠为茂草往往有之,其可以为藏息之所乎?
今于县治之西建立书院,定名仰高,殆有取于宋人名亭之意耳。
盖兹地密迩岳麓者,为紫阳南轩讲道之地,后学之所当景式者也。
果能朝夕触目警心,期以进德修业为事,则异日经纶懋囗,必有奇伟之士应时而出者。
兹院之建于湘邑,宁无小补邪?
”[70]张灯认为,由于州、县儒学的斋舍多“隘陋难容”,书院的创建为士子提供了一个“进德修业”的场所。
隆庆元年(1567),陆柬修《宝庆府志》,在卷三《地理考·建置》下设“公署、行署、藩封、学校”诸目,“学校”之下则有“学田、社学、书院附”。
陆柬在其自撰的《东山书院记》中说:
“迨国朝道化旁敷,乃彬彬焉,得与上国齿。
盖教有人,学有地,其明效可证睹矣,此书院不可无作也。
”[71]在陆柬看来,书院建设是“学有地”的重要保证。
由于明代官学一般没有斋舍供生员肄业,能够提供斋舍、号房的书院便成了儒学必要的补充。
随着明代中期以后官学的进一步废弛,作为士子藏修之地的书院则进一步得到建设。
万历《忻州志》引嘉靖年间县志编纂者党承志(1511进士)的话说:
“典阙而宜举者,书院是也;……书院群居讲习,丽泽资焉。
”[72]正是从为生员提供优游藏修之地的意义言,书院构成府州县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