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启功百年诞辰.docx
《纪念启功百年诞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纪念启功百年诞辰.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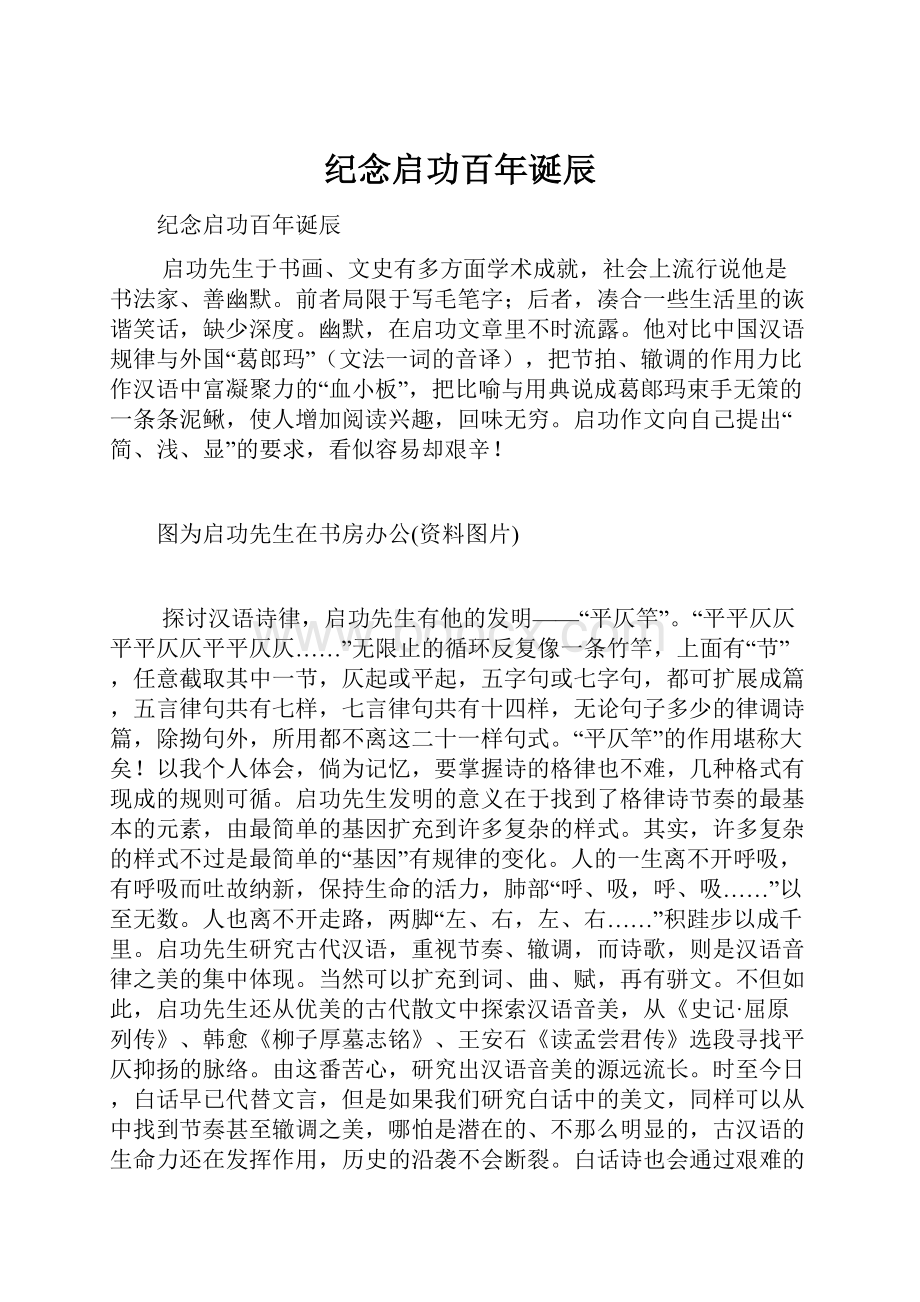
纪念启功百年诞辰
纪念启功百年诞辰
启功先生于书画、文史有多方面学术成就,社会上流行说他是书法家、善幽默。
前者局限于写毛笔字;后者,凑合一些生活里的诙谐笑话,缺少深度。
幽默,在启功文章里不时流露。
他对比中国汉语规律与外国“葛郎玛”(文法一词的音译),把节拍、辙调的作用力比作汉语中富凝聚力的“血小板”,把比喻与用典说成葛郞玛束手无策的一条条泥鳅,使人增加阅读兴趣,回味无穷。
启功作文向自己提出“简、浅、显”的要求,看似容易却艰辛!
图为启功先生在书房办公(资料图片)
探讨汉语诗律,启功先生有他的发明——“平仄竿”。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无限止的循环反复像一条竹竿,上面有“节”,任意截取其中一节,仄起或平起,五字句或七字句,都可扩展成篇,五言律句共有七样,七言律句共有十四样,无论句子多少的律调诗篇,除拗句外,所用都不离这二十一样句式。
“平仄竿”的作用堪称大矣!
以我个人体会,倘为记忆,要掌握诗的格律也不难,几种格式有现成的规则可循。
启功先生发明的意义在于找到了格律诗节奏的最基本的元素,由最简单的基因扩充到许多复杂的样式。
其实,许多复杂的样式不过是最简单的“基因”有规律的变化。
人的一生离不开呼吸,有呼吸而吐故纳新,保持生命的活力,肺部“呼、吸,呼、吸……”以至无数。
人也离不开走路,两脚“左、右,左、右……”积跬步以成千里。
启功先生研究古代汉语,重视节奏、辙调,而诗歌,则是汉语音律之美的集中体现。
当然可以扩充到词、曲、赋,再有骈文。
不但如此,启功先生还从优美的古代散文中探索汉语音美,从《史记·屈原列传》、韩愈《柳子厚墓志铭》、王安石《读孟尝君传》选段寻找平仄抑扬的脉络。
由这番苦心,研究出汉语音美的源远流长。
时至今日,白话早已代替文言,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白话中的美文,同样可以从中找到节奏甚至辙调之美,哪怕是潜在的、不那么明显的,古汉语的生命力还在发挥作用,历史的沿袭不会断裂。
白话诗也会通过艰难的历程吸取传统汉语的美感逐步走向成熟。
从汉语传统的立场看,这应是一条必然的途径,当然决不排除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当代语言的融入等多方面因素。
我至今记得启功先生有一次跟我说,他写白话文的时候,心中默默地有文言作底。
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文言的根底深,懂得文言与白话相异又相通。
有了“文言作底”,写的虽是白话,读起来也会是优美的,单说“文言简练”不足以说明问题。
启功先生对汉语中一字即一词,一字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形容词的现象作了深入的阐释与发挥。
“平仄竿”发现了汉诗的音韵规律,而对汉字的字形规律,启功先生也作了十分精密的研究。
他仔细察看古代帖子中笔画轨道的方向角度、笔与笔之间的距离关系,字中各笔的聚散疏密。
他确认赵孟頫说的“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是真实不移的道理。
用笔与结字究竟何者更重要,古今见解各有侧重,我曾写《传统与“一画”》与学界共同商讨。
在启功先生那里,更看重结字的重要性。
画一个方块,从上而下,从左至右都分作五、三、五的比例,交叉的中心在一个“三”的正方形,任何一个字的聚处便在这正方形了。
启功先生画出“大”“戈”“江”“口”“一”“米”等字为例证,称这一发现为“黄金律”“黄金率”,x:
y=5:
8(0.382:
0.618)。
楷字的中宫,本来属于“模糊数学”的范畴,如此精确的计算,为前人所无,称得上新发现。
在西方,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比率将音乐与数学联系,如今启功先生将写字放在数学的精确度上了。
至于说到怎样才能写好字,发挥书法的艺术性,便不能因此而简单化。
我曾将个人意见面陈先生。
先生讲述了“国”字的例子,“玉”在“口”中,偏左偏上便觉美观,否则效果不佳。
他说这可能与人的心脏偏左上侧有关,又说“黄金律”的中宫实应在左上部。
由此我想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知觉经验的由来等相关的问题。
我以为从这里获得的教益应当大于结字“黄金律”的具体数据。
书法倘与“数”联系,也还要从“模糊数学”得到启示。
再如先生的“一生师笔不师刀”的观念,几乎称得上是学习书法的法门。
无论碑、帖,都用刀刻复制,只有“透过刀锋看笔锋”才能体会到原作的真貌。
但我也曾问过启功先生,刀锋既是客观存在,是否也算一种趣味?
这种趣味是否值得融入书法,如何融入?
这又是一个学术问题了。
但至少刻意仿效刀锋是不可取的吧!
启功先生研究学问,重视实证,并且善凭直觉。
倘问上面说到的“平仄竿”从何而来,从先生著作里找不到,全靠读书多,想得多,触发偶然的“顿悟”。
有些灵感,他在与人交谈中获得。
他坐在火车上听车轮行进的节奏,向一位心理学家请教,启发了对格律诗的节奏感的理解,抓住这个理解不放,于是写出了有识见的文章。
《上大学》是一篇回忆教学历史的文章,教学相长,教师都是亲密的朋友,切磋琢磨,谦虚又自信,许多真知在良好的氛围中孕育成长。
历史上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先例,今天的情况怎样,我因缺少直接体验,只好不谈了。
鉴定书画,是启功先生一大贡献。
“观千剑而后识器”。
他有过从事书画鉴定的良师,还因为他本身从事书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平生见过数以十万计的书画作品,看艺术风格善于领悟,看纸墨图章熟稔在胸。
再是看旁证也十分重要,要有广博的多方面的文化知识,这就显示出博学的力量。
书画鉴定如果单会看笔迹,照启功先生说,公安部门的专职人员也能做到。
这句话一言道破了鉴定的学术性质。
比如对《旧题张旭草书四帖》作者的否定,对陆机《平复帖》的九行八十六字释出全文中出现的三个人名作了考证,都是综合素养的成果。
启功先生从长期书画鉴定中总结出“七忌”,实事求是,破除迷信,包括反对“挟贵”、“挟长”极其可贵。
启功谈书画鉴定,还十分注意一些“民间”鉴定家的经验和贡献,并向他们请益,虽然他们名气不大,但是有真才实学。
这样的事件也正好体现了没有“挟贵”、“挟长”的难得品质,显示出书生本色。
那启贤:
我与启功先生的交往
自撰墓志铭(启功)
中学生,副教授。
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
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
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
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
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
身与名,一齐臭。
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百年诞辰,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
启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爱党爱国的民主人士。
他尊师重教,为人师表,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
我是1942年与先生相识,并拜为书画老师的,至今已70周年。
1941年夏末,启功先生的书法展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
我渴望见到他,是在参观了先生的书法展之后。
当时我正在《书法精论》(193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丁文隽先生(1905—1989)门下学习书法。
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一走进展室,就见到挂满了启功先生精心创作的书法作品:
有中堂、条幅、楹联、扇面,还有没装裱的作品;有榜书、草书、行草、行楷,还有临摹晋唐的名人名帖,可谓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这是我第一次观看个人书法展,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我接连参观两次,一是为了加深印象,二是想见到作者,但事与愿违,一直没能见到启先生。
1942年暑假,我们十多位男女同学,有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有国立艺专的,正在爱新觉罗·溥松窗先生(1913—1991)家中学画,突然有人喊:
“启先生来了!
”接着有人开门,有人让座,溥先生也放下手中的画笔,站起身来欢迎,并让启先生宽衣。
我见来人,中等身材,身穿白夏布长衫,黑色圆口布鞋,手拿一折扇。
圆圆的脸,戴着一副黑边圆形眼镜,满面笑容地进来了。
宁静的画室顿时活跃起来。
屋里的十多个人,只有我一人是第一次见到启先生,于是溥先生给我引见,说这是启功老师。
我上前深深地给我仰慕已久的老师鞠了一躬,叫声:
“启老师好。
”先生和颜悦色地问起我的姓名、年龄、在何学校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
从此,我与先生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之情。
此后,凡是同学们到溥先生家学画时,启先生都赶来为大家评评作业,答疑解惑。
两位老师的密切往来,不仅是因为住得近,同在辅仁大学任教,还因同为满清皇族的爱新觉罗家族。
溥先生是清惇亲王的孙子,曾祖父是道光皇帝;启先生的先祖是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亲王,其后人逐渐分离出王府,靠科举考取官职,曾祖父溥良中进士入翰林,祖父毓隆也是翰林。
从家族的辈分讲,启先生比溥先生小两辈,按年龄,启先生还长一岁。
成年后,两人同为“松风画会”的成员,该会由溥雪斋(伒)先生组建于1928年,成员都是当时满族的名画家,如溥心畲(儒)、关松房、祁井西、惠孝同、溥松窗(佺)、启功、溥佐等人。
可见,溥先生和启先生亲如兄弟。
我们这些在溥先生家中学画的同学们,实际上是在二位老师的共同悉心教导、传承之下学习的。
溥先生把每个同学的作业批改后,即忙于创作;启先生是以口述讲评为主,很少动手创作,但有时也给同学画个册页,写个扇面等。
我每次来不仅呈上画稿,同时把临写的碑、帖都拿来请二位老师赐教。
启先生见我临写《张猛龙碑》,很高兴,给我讲临碑的方法,得知我在丁文隽先生家中学书法,还要我向丁先生问好。
在二位老师的精心教导下,经过三年多勤学苦练,我的山水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
1945年夏,我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
入学后,到溥先生家去得少了,见启先生的机会也少了。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我没能来得及向几位老师告别就离开了北平,到解放区正定去了。
这一别就是整整30年。
“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工作,即开始寻访启功先生。
我已听说了先生这些年的不幸遭遇:
1956年,自幼抚育先生成人,相依为命的慈母和未出嫁的姑姑相继病逝;1958年,在北京画院协助工作的启功先生被补划为“右派”,剥夺了执教资格,停发工薪;1966年,在“文革”中受到批判;1975年,夫人章宝琛病逝,先生无子无女,孤身一人寄居在内弟章宝珩家,同年大病,险些丧命……年逾古稀的启先生能够承受住如此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着实令人慨叹!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978年秋,我住在西直门招待所,距启先生居住的小乘巷很近。
一天晚饭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先生住地,来开门的正是章宝珩先生。
只见院子不大,满地落叶,北房三间是章先生住的,两间平顶南房是启先生住的,正如先生自述的“宿舍两间,各方一丈”。
我推门进入,见外间除在墙角支着一张木板床,堆有杂物外,没有任何东西。
里屋挂一白布帘。
挑开门帘,只见启先生半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室内一桌二椅,靠墙是一大书柜。
我见先生起来,立即上前敬礼、问好,紧紧握住先生的手。
先生对我的突然到来,一时目瞪口呆。
当我坐下之后,才慢慢向先生汇报了我这30年的简要情况,并约定过几天再来看望先生。
这一年的秋、冬是我到启先生家次数最多的时期。
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刚刚得到彻底平反,很少外出,客人很少,我的工作也不忙,一般吃过晚饭就没事了。
每次见面,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
经过多次交谈,我深感先生还是那么大度开朗,从不讲不愉快的事,也没有不满情绪,有时还爱讲些笑话。
我问他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要不要请人照顾?
先生说:
“这样很好!
”当我问起还作画吗?
先生说:
“不画了。
”还说:
“我要有条件,真想把过去的画都收回来!
”以此表明对自己的画是不满意的。
谈到书法时,他说:
“我在‘文革’中替造反派抄了不少大字报,还受过表扬,说我抄得又快又好。
所以,有些人说我的字是抄大字报练出来的。
”我听后哭笑不得。
在谈到书法创作时,启先生还对我讲述了他的“三不写”:
一是没有出处的诗词不写;二是个人自作的不写;三是称谓不当的不写。
并举例说:
“台湾来人要我写‘国父孙中山像’,我就没写。
因为只有国民党才称孙中山为‘国父’,我不是国民党。
”我说是不应该写。
天气渐冷,启先生住的小屋生起个小煤球炉,还挺暖和的。
我多次遇上先生吃晚饭,每次都是由章先生送来一小盘菜、一小碗米饭。
启先生把菜放到炉盘上,边吃边烤火。
我总提醒先生要注意安全,防止煤气中毒。
有一天饭后,来了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进门来就对启先生说:
“教我们这孩子写字吧!
”先生回答说:
“你们先教孩子学文化吧!
没有文化学什么书法!
”二位见屋里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只好走了。
走后,先生对我说:
“学书法不是练杂技,越小越好。
”
和启先生交谈,主题总离不开书法。
有一次先生讲到“书体”时说: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甲骨、金文、大小篆、隶和楷、行、草各个书体,这是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演变来的。
不能说篆、隶优于楷、行、草,书体本身没有优劣之分。
”当然在笔法、结体、章法上各有不同,各有特色,各有各的美。
我知道先生从不写篆隶,所以,在谈到作为一位书法家要不要做到“各体皆精”时产生了分歧。
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先生却认为:
“为了画鸡还要先画蛋,画蝴蝶先要画蛹吗?
”我坚持说:
“书法家还是应该兼攻各体,这样才能博采众长。
”先生又说:
“唱京剧的青衣还要会唱花脸吗?
”这个问题没有再争论下去。
在谈到临写碑帖时,先生讲解“通过刀锋看笔锋”的观碑法,这是他多年临碑的经验之谈,即要透过碑刻的表面刀痕看出原来笔迹的真面目。
讲到这里,先生还记得我临写过《张猛龙碑》,我俩一致认为这是北碑中的神品。
我说,“从先生的书法艺术中,可以看出深得此碑字体的修长秀丽之美”,学书者不可不学。
在深入探讨刀锋和笔锋时,我也讲:
“不能把碑刻中的方笔都看成是刀锋,用毛笔同样可以写出有棱有角的方笔。
如果把北碑和汉隶中的方笔都写成圆笔,也就不能称之为北碑和汉隶了。
”先生没有反对我的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与启先生的密切接触,以及广泛深入、无拘无束的交谈,我受益匪浅,深深感悟到先生的人生理念、崇高的道德品质、渊博的学识、在书法艺术上的深层次探索,以及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无愧为令人崇敬的永世师表。
遗憾的是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如此机遇了。
1982年,启功先生时逢古稀,离开了蛰居20多年的小乘巷,搬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
这栋位于北区的6号小红楼,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楼,设备简陋,二层分东西两侧,启先生住西侧。
每天下午,窗外树影摇曳,先生戏曰:
“浮光掠影楼”,自寓主人的学识浅薄。
此后,启功先生的生活起居、备课、创作书画、接待客人、辅导学生,都没有离开这栋红楼。
此时,高等院校的教育步入正轨,压在先生肩上的教学担子也越加繁重。
学校成立学术委员会时,他被选为学术委员;开设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班,任导师,后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校外活动也与日俱增,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84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换届,先生由第一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二届主席。
来访的、索要书画作品的客人络绎不绝。
启先生为了讲学和文化交流,还接连去香港,出国赴日本、韩国、新加坡。
他经常是夜以继日地劳累,加之年事已高,体弱、失眠,有时彻夜不能入睡。
有一次,我上午11点去启先生家中,只见屋内坐满客人,待客人走后,我见桌上早餐没动,想要把牛奶加热请先生用。
先生说:
“我不想吃。
”又说:
“昨夜没睡。
”我见先生疲惫不堪,只好扶他去休息。
不久,我再次去看望先生,只见门外贴有一信函,是学校写的,并盖有红色公章,内容是函告:
“为了保证启功先生的工作、休息,每日上午不会客。
”我看后为之叫好。
如果说过去我见启先生挥毫、创作书画的机会少,自搬到红楼以后,机会就多了起来。
经常,启先生半天也放不下笔,有的客人张口就要四五件,先生是有求必应。
有一次,下午写到天快黑了,写了十多件。
为了让先生休息一会,我自荐来替他盖章。
先生却说:
“不忙,我自己来。
”这使我联想到:
先生每创作一幅作品,从选纸、裁纸、选笔、调墨,到最后用印,都是自己动手,十分认真,从不要他人代劳。
例如用印,要根据每件作品的落款位置、选定用印的大小,用一方还是两方。
凡用两方的,上必为阴文,下为阳文;上为名章,下为字。
用印的位置、距离、清晰度等都恰到好处,一丝不苟。
一件作品完成后,还要反复检查,没有任何瑕疵,最后才出手。
这种真诚的创作精神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
这些对我无疑是最好的身教。
有一次我遇上启先生代人鉴定书法长卷,约有四五米。
展开后,只露出一段文字,没露作者署名。
先生便肯定地说:
“好!
”并毫不迟疑地说出作者姓名,随后再展出作者署名。
如此计有清代名家姚鼐等十多人的题跋,没有一个错的。
我们几个围观者,无不为之惊叹,一致称赞先生在鉴定古文物中的一双慧眼。
我经常去看望启先生,主要是感到他年龄日高,身边无人照顾,想帮助他做些事,先生也从不把我当客人。
有一次我上楼,见先生下楼外出,我见无人无车来接,就搀扶先生下楼,走出校门。
我要给先生拦出租车,先生执意不肯,直奔公交车站,我只好把先生送上了车。
在这之前,我曾听说先生为了挤公交车,曾摔得鼻青脸肿。
自启先生搬进红楼,我只有一次向先生求教、请他审阅我的书画作品。
那是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准备在北京、广州等地举办个人书画展,大部分作品拟请先生审定。
我带去几十件书画,先生兴致勃勃地一件件仔细认真地看起来。
见我的国画山水大多数取材于祖国的名山、胜地,尤以黄山、桂林为多,先生高兴地说:
“你的画有了很大变化,很好!
”当我一再请先生提出意见时,他只是对个别作品的着色等讲了点意见。
当审查书法作品时,先生只是说:
“好!
”当看到篆书、隶书后,还加了一句:
“我写不了。
”我说:
“您太客气了。
”一再请先生提些具体意见。
先生讲了他写行草书的经验,说:
“写行草讲究连贯,在落笔和收笔时,最好不要一个字一落一收,而是藏在下一个字的中间,这样看起来字与字笔笔相连,笔断意连。
”最后,先生欣然命笔为我题写了展名“那启贤书画展”,还为我的书画集题写了书名《那启贤书画选集》。
在和启先生闲谈中,我曾说到市场上有很多他的书法赝品,10元一件。
先生说:
“人家要吃饭嘛,你能不让人写?
”当说到如何鉴别真伪时,先生说:
“写的最不好的就是我的。
”我还问过先生:
“听说拟请您担任书法博士生导师?
”先生回答说:
“我不行,我不用‘搏’,一碰就倒了。
”随后,先生又反问我:
“你说字写得什么样子就是博士呢?
”我无言以对。
还有一次我对先生说:
“现在有人大量收集和收藏一些书法家的作品呢!
”先生说:
“有些人的作品,在作者死后升值,有的也不一定能升值。
”
公元2001年,当我听说国务院聘请启功先生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后,说:
“您现在是部级待遇了,应配专车了。
”先生笑着说:
“我不急。
”
2001年11月,原辅仁大学美术系学生、我的师姐拟在炎黄艺术馆举办画展,由我代请年已八十有九的启先生主持开幕式,先生高兴地同意去。
当我说我用车来接先生时,先生说:
“不必!
我现在有车了。
”第二天上午,我在展厅门口接先生时,见他乘坐了一辆新的奥迪车。
在以后的3年里,我也患了和启先生同样的眼疾——“眼底黄斑变性”,先生说:
“我们同病相怜。
”由于忙于治病,视力也在不断衰退,我很少去看望先生了,直到最后在巨大的遗像前和先生告别。
人去文章在 道德流水长
——启功先生诞辰百年研讨会侧记
晚年启功
启功先生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圆润秀劲、端庄妩媚的书法,看上去让人如沐春风。
直到辞世六七年后的今天,他的书法在艺术品拍卖中依然屡受追捧,价格不断走高。
事实上,启功先生的主业是文史,他一生研究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教授古典文学、古代汉语。
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是“穿衣服”一般的家常事。
今年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近日,十余位启功先生的生前友好、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他们的追忆中,启功先生的人品、文章、性情,如涓涓流水,静静流淌。
人无完人,启功例外
“我心中的佛就是启功。
”中国书协副主席、文物出版社原社长苏士澍先生说,启功先生为国家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先生常写的对联“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他把学问都琢磨透了,用最浅显的语言让大家明白。
诗词格律的规律复杂难记,先生用竹节法讲得一清二楚。
在文物鉴定方面,除了真伪,先生还提出了“模糊度”的概念,就是看够不够那个时代。
先生拟定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师范”,意为“所学足为后辈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紧扣“师范”二字,平易晓畅,却又内蕴深刻。
如果先生活着,肯定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说得明白有味。
先生待人以诚、平和、有恒心。
大家都知道启功先生从不打假,说要给人留口饭吃,其宽厚大度可见一斑。
书法家佟韦曾经说过,人无完人,但是启功先生例外。
启功先生内侄章景怀照顾他生活多年。
他说,启功先生学问好、道德好、人缘好,家里永远是高朋满座,有大学问家,也有社会的闲杂人等。
在外出差,他的屋子永远是最热闹的。
还有一个纪录,可以说前无古人——他无偿赠送的书法、绘画作品起码有几百幅。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赵仁珪插话,古代评价人了不起,常说“道德文章”。
景怀说的人缘好,用一个比较古雅的词就是性情。
资深收藏家孙永学说,有人请启功先生帮忙看藏品,一些画属于赝品,先生只是很委婉地说,不好说。
过一段再问,他说我忘了。
这是他很智慧的地方。
他说人家把积蓄一生的钱财还有精力搭在上面了,眼力不够收藏错了东西,本来就挺伤心的,再往伤口上撒盐不好。
学问高深的人,只能得到尊重;品格好,就有人追随你。
学深似海还无波
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启功先生的中国文联图书审读员张铁英说,启先生的学问特别全面。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说谁谁能背十三经,启先生说我就能背《尔雅》,躺床上就背起来了,那可是最早的一部词典啊!
他20多岁就能用古文写漂亮的文章,还能写很纯熟的律诗,后来写成打油诗那类,是要创新,而且立刻就出彩了。
黄庭坚某幅书帖,徐邦达都解释不了,启功先生很轻松就读下来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最早一版《红楼梦》,到处找人注释,俞平伯说:
“找元白(启功先生字元白)。
”沙孟海先生曾和启功先生盘过道,他说一样,启功先生补充一样,沙先生特别佩服,自己的文集和书学院都指定启先生题字。
启功先生说老舍把北京话给弄歪了,他用的基本上是下层的北京土话,不是北京的雅言。
《启功全集》编委、北师大出版社编辑李强说,现在很多人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间隔着一道鸿沟,我理解启功先生是一个桥墩式的人物,把我们丢失的传统文化传递到21世纪。
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也曾说过:
启功先生“最令人心折赞叹的研究成果产生于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与敏锐准确的艺术鉴赏眼光的完美结合”。
滴水之恩涌泉报
北师大原校长办公室主任、《启功全集》出版委员会主任侯刚跟先生接触了30多年,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不忘恩师。
1988年,他看到学校里有些农村来的孩子学习、生活有困难,就想用作品换钱来帮助他们。
先生有个习惯,不把自己的字当回事。
不论尊卑,但有所请,不忍拂意,欣然从命,接受电视台访谈时还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
结果他写的时候经常有人来,说先生这是给我的吧,就拿走了。
最后到校招待所找一间房,有一次写着就晕倒了。
3年的时间,从300多幅里挑出来100幅字、10幅画,去香港筹集了163万元,起名“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全部交学校管理。
“励耘”二字,便源自启功先生恩师陈垣的“励耘书屋”。
这后面有一段故事。
启功先生是满族人,始祖是雍正帝第五子、和亲王弘昼。
少年时家道衰落,在族人的帮助下,拜博通画史、书画鉴赏的贾羲民和画技熟谙的吴镜汀学习。
18岁时,从戴姜福先生学习古典文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
21岁时,被傅增湘先生介绍给陈垣先生,涉足学术流变与考证之学。
陈垣先生认为他的作品“写作俱佳”,先后推荐他任辅仁中学国文老师、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两次都因没有文凭,不久就被辞退。
26岁那年,陈垣先生又举荐他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
启功先生常说:
“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的恩惠之恩,是再造我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
”
王大山先生为此次筹款帮了大忙,启功先生给他画了一张红竹子,说我这一辈子都要感谢王大山,因为他帮助我完成了对老师的心愿。
后来大山生病,从深圳回北京,先生知道了亲自到机场去接,令侯刚至今想起来还感动哽咽:
先生对朋友、对于他有恩的人,那是永远不忘。
“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
”
赵仁珪说,启功先生一向认为书法再怎么发展也不能脱离实际的用途,让人能看懂是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