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的.docx
《妇女的.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妇女的.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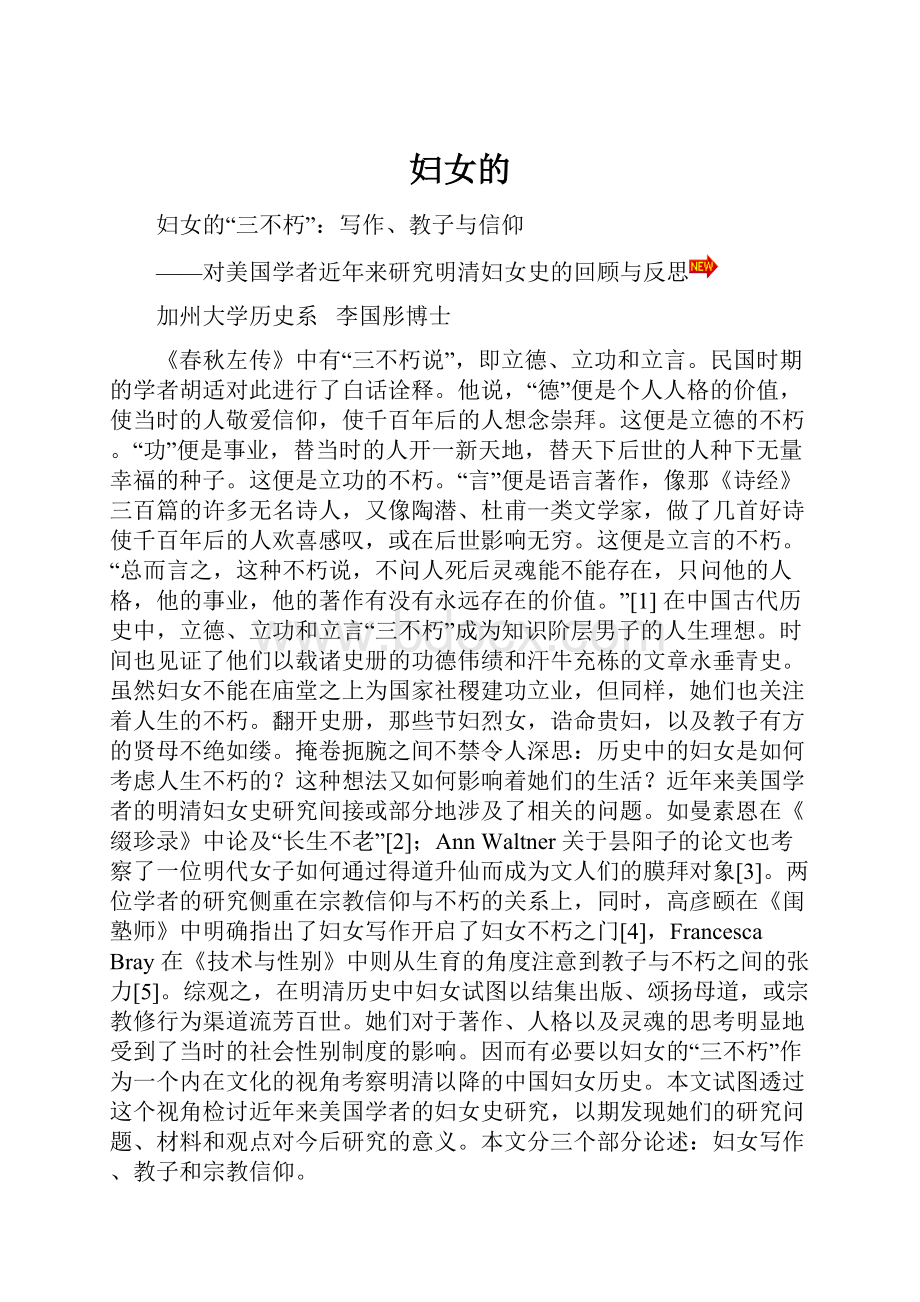
妇女的
妇女的“三不朽”:
写作、教子与信仰
——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明清妇女史的回顾与反思
加州大学历史系 李国彤博士
《春秋左传》中有“三不朽说”,即立德、立功和立言。
民国时期的学者胡适对此进行了白话诠释。
他说,“德”便是个人人格的价值,使当时的人敬爱信仰,使千百年后的人想念崇拜。
这便是立德的不朽。
“功”便是事业,替当时的人开一新天地,替天下后世的人种下无量幸福的种子。
这便是立功的不朽。
“言”便是语言著作,像那《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又像陶潜、杜甫一类文学家,做了几首好诗使千百年后的人欢喜感叹,或在后世影响无穷。
这便是立言的不朽。
“总而言之,这种不朽说,不问人死后灵魂能不能存在,只问他的人格,他的事业,他的著作有没有永远存在的价值。
”[1]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成为知识阶层男子的人生理想。
时间也见证了他们以载诸史册的功德伟绩和汗牛充栋的文章永垂青史。
虽然妇女不能在庙堂之上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但同样,她们也关注着人生的不朽。
翻开史册,那些节妇烈女,诰命贵妇,以及教子有方的贤母不绝如缕。
掩卷扼腕之间不禁令人深思:
历史中的妇女是如何考虑人生不朽的?
这种想法又如何影响着她们的生活?
近年来美国学者的明清妇女史研究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相关的问题。
如曼素恩在《缀珍录》中论及“长生不老”[2];AnnWaltner关于昙阳子的论文也考察了一位明代女子如何通过得道升仙而成为文人们的膜拜对象[3]。
两位学者的研究侧重在宗教信仰与不朽的关系上,同时,高彦颐在《闺塾师》中明确指出了妇女写作开启了妇女不朽之门[4],FrancescaBray在《技术与性别》中则从生育的角度注意到教子与不朽之间的张力[5]。
综观之,在明清历史中妇女试图以结集出版、颂扬母道,或宗教修行为渠道流芳百世。
她们对于著作、人格以及灵魂的思考明显地受到了当时的社会性别制度的影响。
因而有必要以妇女的“三不朽”作为一个内在文化的视角考察明清以降的中国妇女历史。
本文试图透过这个视角检讨近年来美国学者的妇女史研究,以期发现她们的研究问题、材料和观点对今后研究的意义。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述:
妇女写作、教子和宗教信仰。
妇女写作:
彤管与箴管并陈
明清妇女写作和结集出版之盛况已经成了学界不争的事实。
值此盛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也尘嚣四起。
有人针对妇女出版作品评论道:
“从来妇言不出阃,即使闺中有此韵事,亦仅可于琴瑟在御时,作赏鉴之资,胡可刊版流传,夸耀于世乎?
”[6]对此女作家并未示弱,给予了响亮的回击。
清代女作家吴琪在〈《红蕉集》序〉中直言:
“若斯编者,可以传矣。
然则古今女子之不朽,又何必不以诗哉?
夫抱贞静之姿者,尽不乏批风款月;具挑达之行者,或不解赋草题花。
彼有大节或渝,而藉口一字不逾阃外,其视集中诸夫人,相去为何如也。
”[7]吴琪批评了妇女作品出版有碍妇德的说法,并将诗歌创作提升到妇女不朽的高度。
顾若璞(1592-约1681)在自序《卧月轩集》时指出:
“尝读诗知妇人之职,惟酒食是议耳,其敢弄笔墨以与文士争长乎?
然物有不平则鸣,自古在昔,如班(昭)、左(芬)诸淑媛,颇著文章自娱,则彤管与箴管并陈,或亦非分外事也。
”[8]清代女作家顾静婉在自序《钞韵轩诗稿》时也表示了相同的感受:
“困顿无聊之境,借以自娱外,每嘱存稿,余颇以为非;窃恐率尔涂鸦,反资谈柄焉。
……余闭门课子,绣倦炊闲,偶检旧笥,得昔年咏句约百首,并近作,挑灯手录,原知篇不成篇,句不成句,岂曰鸣其不平,鸣其不幸耶?
”[9]她们视写作为宣泄心中不平的管道。
有的女作家甚而把此道当作医病的办法。
“每于疾时愁处,无可寄怀,便信口一吟,觉郁郁舒而忧尽释也。
”[10]
女作家所接受的教育包括诗书声韵之教和内则箴规之教两方面。
无论是在写给亲友的书信中,还是在诗集的序跋中,她们都极力表白自己深明女训,诗词创作并没有妨碍其妇德,只不过是对造物的不平、生活的不幸的一种宣泄罢了。
诗书之教是明清文人家庭中重要的教女内容。
文人们重视妇女的母教角色,寄望于她们能教子以书香继世。
但他们又不愿意女子在诗书上过多地花费精力,于是想尽办法干预她们,使得女作家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女作家对于结集出版的困惑也源自女教中的双重观念。
一方面,她们受女训观念束缚,觉得“内言不出阃外”,为恪守女子之道就只能将自己一生的心血之作付之一炬;另一方面,诗书之教和文学创作启蒙并又赋予了她们历史使命感,在咏史怀古的创作中,历代女杰就像一面面旗帜召唤着她们。
虽不能像昭君那样出塞和亲平息边塞干戈,也不能像班昭兰台续表修国史,她们仍希望其著作能汇入历史长河。
她们在序跋中虽然表示了在创作和出版中受到女教的困惑,但是她们最终决定出版作品之举则表明她们没有向女训的束缚屈服。
不管其文集如何以“绣馀”、“红馀”、“焚馀”命名,她们还是将“妇言”推出了阃外,并坦言等待采王风者将其作品纳入彤史。
对于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与结集出版,也有来自圈内人的一些负面评论。
如女作家方孟式(1582-1639)在给妹妹方维仪(1585-1668)的信中谈及著名女诗人徐媛(1560-1620)的诗作,评说道:
“偶尔识字,堆积龌龊,信手成篇。
天下原无才人,遂从而称之。
始知吴人好名而无学,不独男子然也。
”[11]清代女作家王贞仪(1768-1797)也在书信中指出:
“大抵今人之弊,最患急于求名,唯恐人不及知。
而未定之稿,出以示人,求片言于大老名公以为荣。
在彼固不自知,而一经有识者哑然置之。
夫所以哑然置之者,以物之不足当一赞叹,且遽因其人之乞求,遂柔声媚态以贡谀也。
”她明确地表示不会出版自己的诗作,“唯守内言不出之训,以存女子之道耳”。
[12]这里道出的某些女作家好名、出示诗稿求序为荣的现象,与内则女训确有明显冲突。
既然“诗文不是女子分内之事,内言不出又是女子之道”;那么,出版诗稿的妇女又求的是什么呢?
名载史册本身并不简单地意谓着不朽。
毕竟还有美名远扬和遗臭万年之别。
女作家对其作品是否有损其妇德甚感焦虑。
这一点在盛清时期尤为明显。
曼素恩注意到妇言与妇德之间的张力,并从明清鼎革的角度考察之。
她指出:
“高彦颐以娴熟的笔法记载了妇女诗作所传递出的妇女文学天地与晚明文学氛围的相似性。
但在盛清背景下,妇女的诗词创作变了调。
它崭露头脚,变得更有争议,惹得一些男文人对女作家评头论足。
”[13]其中以章学诚(1738-1801)为代表。
章氏高度赞扬妇女的经学研究,认为她们为传承家学和复兴经学传统做了贡献。
但他批评道:
“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者,转因诗而败礼。
礼防决,而人心风俗不可复言矣。
”[14]男文人对于妇女写作的焦虑确实影响了妇女自身对于写作的观念。
曼素恩引用女诗人恽珠(1771-1833)为例,认为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中以“德正言顺”作为她的编辑准则与章氏言论不出左右。
恽珠拒收名妓的诗作,不为风月之词所动。
由此可见,妇德已经成为妇女写作的关注点。
那么,才女们又是如何缓解妇言与妇德之间的张力的呢?
参酌以往研究,本文将从传播、语汇和主题三方面讨论这个问题。
高彦颐在《闺塾师》中充分肯定了明清妇女的著作并指出,“文学创作见证了女作家的个人主体存在,并开启了通向不朽之门。
”[15]进而又探求其文学表述的传播方式。
清代女诗人沈善宝在自序《名媛诗话》时曾指出,“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
……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
”[16]高彦颐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多个范畴,如家庭圈,亲属圈和公众圈。
女作家要么单独出版个人诗文集,要么将作品附于家人的集子里,要么同好之间相邀联袂结集出版。
从妇女不朽的角度来看传播过程,结集出版是妇女写作中的一个关键元素。
王献吉在序《焚馀草》时道出“焚稿”与结集出版之间的内幕:
(孺人)俯仰三四十年间,荣华雕落,奄忽变迁,触物兴情,惊离吊往,无不于诗焉发之。
孺人亦雅不以屑意,成辄弃去,所存无几何。
一日谓不肖曰:
妇道无文,我且付之祖龙。
余曰:
是不然,《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删《诗》者采而辑之,列之《国风》,以为化始。
[17]
当王凤娴在犹豫她的诗稿存留时,并没有竟自焚稿,而是征求兄弟的意见。
王献吉以《诗》三百为例驳斥了“妇道无文”的教训,王凤娴也就释然地将诗稿付梓流传后世。
王凤娴兄弟王献吉之见识非同一般。
他认为妇言一经付梓就成为后世史家有案可稽的材料。
正是这种历史保存意识使得妇女作品结集出版合乎情理、有规可循。
如果王凤娴焚了诗稿,她的作品就像历史中绝大多数妇女作品一样寂然无声。
换言之,出版历史性地保存了妇女的声音。
许多女作家认识到出版的重要性,只是刻意地用“焚馀”或“绣馀”命名文集,或在序跋中以妇德的表白来包装遮掩其走出阃外之妇言。
除了文学创作,妇女的箴管之作--女教书在明清两代传播亦广。
其中以《闺阁女四书》最负盛名。
它包括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氏姐妹的《女论语》、明代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和明末山东琅琊王相之母的《女范捷录》。
但是女教书的广泛传播并不意谓着其中内容的有效传递。
KatherineCarlitz在研究中指出,书籍本身具有其生命力,编纂人、资助人和出版商的动机跟读者的意图一样参差不齐并影响着书籍的制作。
装帧和木版插图使儒家节孝观念与浪漫爱情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那些女教书更趋愉乐化。
[18]她仔细地检视了明代贞诚堂版的《绘图列女传》,发现其中的插图和坊间流行的《古本戏曲丛刊》的插图没什么区别。
造成此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插图的作者既画女教书又画坊间香艳小说,他们并没有根据文本的内容而刻意调整插图的内容。
于是,在《绘图列女传》里出现了图文不符,甚至有伤大雅的画面。
她认为晚明社会中出资印书与印书赚钱的现象使得财富和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异化。
妇女本身及妇德圣像成了商品。
LisaRaphals在《分烛》一书中也用一章的篇幅考察了不同版本的《绘图列女传》的变化。
[19]她认为画面中妇女的位置、姿态以及男女人物的高度比例反映了插图工匠的妇女观。
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出版过程中,各种因素潜在地影响着妇言和妇德的传播,即便是宣讲妇德的箴管著作在商品化中也可能发生异化。
传播之外,考虑妇德和妇言之间张力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女作家用以表达思想的语汇。
我们注意到,很多闺秀运用男文人的语汇表述自己的想法。
清人陈宏谋(1696-1771)评价道:
“夫世之妇女,守其一知半解,或习闻片词只义,往往笃信固守,奉以终身,且转相述,交相劝戒。
”[20]如,一位明代闺秀在评《牡丹亭》时引用《孟子》关于“情”的论述[21]来发表她个人关于无情非有才的观点。
高彦颐针对这一现象指出,男子与妇女对于“情”的诠释话语有所不同。
男子的话语浸透着哲学术语,反映了理学与佛道的融合;而妇女的话语则侧重于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情感。
[22]在高彦颐的书中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个例子说明妇女用男子的语汇表达了歧义。
寡妇秦淑殉夫时以名教之言“好女不侍二夫”自表其志,而她的个人经历则表明她的殉死“是发乎情感,出于夫妇间的私誓。
”[23]妇女使用男子语汇或名教教条是出于有意无意间的附会。
学者的研究提醒我们在使用妇女著作时要仔细审视其中某些语汇的歧义,避免误读文本。
闺秀们不仅使用男子的语汇,而且时常对身边事表现出“男子般的焦虑”。
高彦颐在书中特别指出女诗人顾若璞的作品以训导为目的,明显地表述了她对男子中心家庭的肯定。
[24]“男子般的焦虑”也影响了女作家的创作主题。
曼素恩认为恽珠决意在诗集中摒除名妓的作品反映了她处在妻子的位置上对风月闺词“应有的鄙夷”。
在某种程度上,恽珠这种“妻子应有的鄙夷”遥相呼应了章学诚对妇女诗词的批评。
曼素恩分析指出闺秀之所以要把名妓在士人文化中边缘化是为了提升她们自己作为有修养的已婚妇女的角色。
[25]在文学创作中,闺秀青睐教子主题并着意颂扬母亲角色。
藉此,闺秀得以与名妓划清界限从而保全妇德。
对十七世纪妇女写作的研究,从妇女在社会组织和自我认同中崛起的角度,注意到形式多样的妇女社团的发展。
女作家藉以传播作品并表达自我认同感。
相对而言,对十八世纪妇女写作的研究则更关注妇女的道德观念和生命角色。
曼素恩认为研究对象在明清社会政治鼎革中的变化使然。
对此本文的观点是,高彦颐在研究中或多或少地以女性主义理论的视角入手;而曼素恩则更多地联系到盛清的社会背景。
很显然,她们二位都注意到妇女写作开启了妇女不朽之门,但又都没有深入发掘下去。
本文建议以“妇女不朽”为内在视角进一步发掘女作家的创作初衷,从而可以顺藤摸瓜地对其内心世界给予理解之同情,而不是止步于用理论之石扣击表象的阶段。
在思考妇女写作与追求不朽间的关系时,特别应注意到妇女写作不仅是她们的自娱消遣,还是她们汇入史册的一个渠道。
她们理解由于时人关于妇女文学的批评,其作品付梓会有损妇德,但闺秀们为了能彤管留声仍竭力平衡这种张力。
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换着语汇和主题,压抑个性或女性声音,以免影响其清高的形象。
她们关于教子主题的热衷也令我们注意到妇女写作与颂扬母道之间的关联。
教子:
母不取其慈,取其教
明代以前的女教书对母仪、母教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
如唐代《女孝经》专列〈母仪章〉,指出:
“夫为人母者,明其礼也。
和之以恩爱,示之以严毅。
动而合礼,言必有经。
”著者引《诗经》“教诲尔子,式谷似之”,来解释母仪之道。
唐代《女论语》中不列〈母仪章〉,但在〈训男女章〉中言及母教: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
年已长成,教之有序。
训诲之权,亦在于母。
”明清两代的女教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母教传统。
明仁孝文皇后徐氏在《内训•母仪章》开宗明义曰:
“孔子曰:
‘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理者也。
’是故无专制之义。
所以为教不出闺门,以训其子者也。
教之者,导之以德义,养之以廉逊,率之以勤俭,本之以慈爱,临之以严格,以立其身,以成其德。
慈爱不至于姑息,严恪不至于伤恩。
伤恩则离,姑息则纵,而教不行矣。
”在〈慈幼章〉里又强调了“慈”与“教”二者之关系:
“故慈者非违理之谓也,必也尽教训之道乎。
”[26]由此可见,教训之道在母仪中的重要位置。
明代刘氏的《女范捷录•母仪篇》不像《内训》引据圣人经典而述,著者从一般生理常识着眼,指出:
“父天母地,天施地生,骨气像父,性气像母。
上古贤明之女有娠,胎教之方必慎。
故母仪先于父训,慈教严于义方。
”刘氏认为母亲对子女身心的影响更为重要。
清人冯树森撰《四言闺鉴》时,也列举了古代贤母的范例,并将其归纳为“教子心法,作母指归”。
所谓“教子心法”就是用榜样的力量感化妇女,激励她们见贤思齐。
母道在明清研究中不是冷门。
一些学者从教子与妇女生育的角度考察这一主题。
他们注意到妇女通过为人母,特别是教子达到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换。
FrancescoBray在《技术与性别》一书中以三章的篇幅讨论了“母道的意义”。
[27]她指出过分强调母亲角色中的自然因素的说法欠妥。
从生理角度看,母亲的生育是自然天性与社会行为的结合。
从社会角度看,母亲可以通过理智的胎教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正如前引刘氏所教诲的“胎教之方必慎”。
母亲在母子纽带中有两个贡献:
一是母亲在怀胎和哺乳过程中对孩子的生理塑造;一是母亲在教子过程中向孩子传授社会准则和道德价值观。
更甚之,明清时期一些母亲执书课子,成为传道授业之师。
[28]
Bray清楚地揭示了文人关于母道的建构。
在文人笔下,母道的意义不再是怀胎生产和哺育之恩,转而变成了适当的道德教育。
母亲的社会性要求妇女具备道德纯正修养高尚的素质,同时其生理性则要求妇女身体健壮兼能专注胎教。
这些观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明清时期及以降的母道提供了重要的基石。
Bray强调她关于母亲之社会性的观点主要基于中华帝国晚期的情况。
她认为在宋元时期对母亲角色的评价发生了变化,母亲的学识比德行更重要了。
她指出:
“孟母三迁的故事更多地颂扬了其德行而不是学识;但宋元时期一些著名文人在传记中经常念及得功于母教。
”[29]对此,LisaRaphals持不同见解。
Raphals在研究吕坤(1536-1618)《闺范》的基础上指出了明代中期母亲的学识不像以前那么重要。
明中期以后女教书重视母仪的趋势在吕坤《闺范》中反映最明显。
《闺范》“善行”部分,分为“女子之道”、“妇人之道”、“母道”等。
吕坤明确地阐述了“妇道”、“母仪”与“女道”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妇道母仪,始于女德。
未有女无良而妇淑者也,故首女道。
”女道是妇道与母仪的基础,教养女道是以妇德和母仪为期望目标。
那么,吕坤期望的母仪又是什么呢?
他在“母道”中讲到: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
”可见他重视母仪的核心是“母教”。
他在“母道”之中,又分列了〈礼母〉、〈正母〉、〈仁母〉、〈公母〉、〈廉母〉、〈严母〉、〈智母〉等项。
[30]其母道的分类中进一步佐证吕坤的母教原则:
即重视教训作用。
Raphals把《闺范》与刘向《列女传》相比较,指出《列女传》中仁智和辩通两项被淡化了。
一半以上的颂扬母亲学识的故事在《闺范》中被改头换面。
于是,她认为明代士大夫关于家庭与礼制的焦虑渗透到《闺范》步步为营的布防中。
[31]
对吕坤《闺范》的研究中,JoannaF.Handlin的观点可以帮我们重新审视Raphals和Bray之间关于母道转型的分歧。
Handlin有针对性地考察了《闺范》的读者层,指出吕坤着眼于教导百姓而非上层妇女。
[32]吕坤的身后知音陈宏谋在十八世纪强调:
“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而岂独遗于女子也?
”陈氏对村姑里妇也关爱有加:
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
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
或者疑女子知书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笔墨工文词者,有时反为女德之累。
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纵不能经史贯通,间亦粗知文义。
即至村姑里妇,未尽识字,而一门之内,父兄子弟,为之陈述故事,讲说遗文,亦必有心领神会,随事感发之处。
一家如此,推而一乡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
[33]
由此可见明清士大夫对于在中下层妇女中进行社会宣教之高度重视。
面对政局纷乱、礼崩乐坏之社会万象,士大夫以心目中的理想观念为支柱,力挽危局。
在此背景下,吕坤面向中下层妇女的宣教更侧重于德行而不是学识。
曼素恩在《缀珍录》中关于盛清时期“承慈训”“承母教”现象的明晰阐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不断建构着的母亲之社会性的意义。
她深入地揭示了盛清社会中存在着的对那些饱读诗书且又极具影响力的母亲的焦虑。
这些妇女受业于满腹经纶的父亲,又将娘家的“家学”传给儿子,以“母师”之尊严顶立门户。
曼素恩指出,这种微妙的母子关系成了有清一代瓷器画匠们喜爱的题材。
不过,画匠们试图解除“母师”带给人们的不安,他们把儿子画成幼童,把母亲以年轻丽人的形象展现出来。
[34]据曼素恩的观点,母亲的学识在盛清依然受到闺秀和文人的推崇。
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有二:
一是母道的意义与时俱进,不是固定不变的。
二是不同阶层或群体的母道要求有所不同。
宋代以来科举考试与家庭文化之间不断强化的纽带影响了母道的语境。
社会和家庭期待着母亲培养出孝子或金榜题名的学士。
作为回报,母亲也会相应地得到诰封或是永不磨灭的传记、墓表。
所谓“母以子贵”的现象。
孝子不仅能传承香火,而且还可以让母亲的英名流芳百世。
翻阅名人文集中的妇女传记及墓表时,我们常常发现作者提及“受某某孝子请托”。
子嗣的出人头地或奔走请托使母亲的德行得以载入史册。
明代文人归有光(1597-1571)笔下的郭老妇人就极具代表性。
郭孺人始归陈氏,丈夫日游庠舍,不能治生产,几无以自赡。
郭孺人的娘家田肥美,岁收多,于是她捐嫁时衣被财物,买田庐。
“每岁之冬,即往收获。
苦寒迨春,而面尝皲瘃。
”辛勤二十余年,家用可以给。
而夫君以年赀贡入太学,后当了州县官,儿子也取了进士。
归有光赞曰:
“为妇以至于今,其勤劳如此。
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仅已登岸,而操舟者没焉。
”归有光形象地把郭孺人对夫家所做贡献比为操舟者,丈夫儿子都能以功名显于世,而独此最尽力的妇人却劳而无功。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郭老妇人也有一个心愿,她表示一生尽瘁于夫家,“但得片石,求能文者志吾墓足矣”。
[35]老妇人一生鞠躬尽瘁,但求身后留名。
归有光听了郭孺人的心愿后,评价道:
“孺人以女子,有志于名后世,夫岂为区区之名,即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没没者。
”至此,归有光将其相夫教子的事迹归于她有不甘于平庸的志向,即志在通过墓碑名留后世。
盛清时期的一位士人曾痛切地评论这种妇女“有志于名后世”的现象:
郑母守贞三十年,有子成立……盖棺以后,其子阳丰述其状而号泣。
吾乡诸君子哀其志,为诗歌以扬厉之,凌霜劲节没有馀芬。
郑母之遇其亦可幸者乎。
名教二字闺阁同之。
[36]
“然或不幸不遇肖子,复不获当代巨公为之传,信荒山僻野之间湮没者,何可胜道。
”妇女与男子同样珍视名誉,然而她们的身后之名却如此脆弱地寄托在儿子的请托和号泣上。
她们对于身后之名的牵挂类似于女作家对其著作流传的渴望。
母亲因教子有道以德行名载于史册或墓表,同样地,女作家则以其著作流芳百世。
母道与妇女不朽的联系使得它在明清历史中更加复杂化。
我们可以进一步在明清宗教信仰的环境中考察士大夫高扬母亲社会角色,压抑生理角色的背景。
宗教信仰:
超凡脱俗,得道升仙
儒家文人并不排斥宗教经典,认为“读书于经史正课之暇,佛经中如华严、法华,力之俱足以增长智慧”。
他们对年长妇女在家中潜心学佛,以解西方之旨亦持肯定态度。
但又强调,“女人不得供养尼姑在家,此辈两舌是非,多致离间骨肉。
子孙有不守此训者,即为不孝。
”[37]然而,文人对出家女子的态度颇耐人寻味。
唐宋以来文人笔记时常记载妓女悟道出家的美谈,明清两代亦然。
在文人眼中,妓女、女尼、女冠同属家庭以外的妇女角色,她们都不受妇女家庭角色的限制,超越了世俗人伦规范。
女尼、女冠越规僭礼的行为及其宗教影响力对妇女的家庭角色有相当之影响。
文献记载,妇女入寺敬香看戏,生出种种事端。
如“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仔、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驰禁。
”[38]再如“张观准知河南某府,俗妇女好看庙戏,禁之不革。
张伺某庙演戏时,出不意往坐其大门,使役堵其后门,命男子尽出,因令役谓诸妇女曰:
‘汝辈来此,定是喜僧人耳,命一僧负一妇女而出。
’绅民哗然。
”[39]从官吏竭力禁止妇女入寺的记载,可以想见当时妇女参与宗教活动的程度。
对妇女宗教信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妇女宗教信仰与儒教政权焦虑之间的张力;家庭角色的责任与宗教话语对妇女不朽之诠释间的冲突;妇女的宗教体验与儒家文人冠以妇德再表现间的误解。
对盛清妇女宗教信仰的研究揭示了妇女的宗教修行与妇女切身的焦虑相关。
她们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与儒学礼教背道而驰。
曼素恩在研究中提及“长江中下游流传的民间故事透露出妇女设法逃避生育带给她们的不洁并祈求长生不老的愿望”。
进而,她指出,“妇女的宗教信仰与妇女对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和升仙成佛的焦虑紧紧相连。
”她还从生命角色的角度去考察妇女的行为,并指出在老年阶段,妇女往往皈依宗教,膜拜观音菩萨和道教娘娘祈求她们心目中的长生。
关于妇女宗教信仰与儒教政权焦虑之间的张力,曼素恩分析指出:
“虔诚的宗教信仰冲破了内闱的墙,向幽禁妇女的儒家礼教发出了挑战。
”尼姑道姑上门联络妇女,在家里讲经做法。
士人视之为洪水猛兽,把“三姑六婆”归之为罪恶渊薮。
[40]尽管妇女的宗教信仰属于私人行为,但它仍在政权的视野之内,难逃遭受打击的厄运。
清前期地方官吏曾针对民间信仰展开一系列清扫。
此间,寺庙中的女香客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
其中黄六鸿(1633-1693)在他著名的《福惠全书》中特别提到:
大户人家的妇女把外出当作消闲。
打扮得珠光宝气的,频繁地出入寺庙和一些公共场所。
她们以烧香敬佛为名,却在幽廊暗室行狎昵不轨之实。
地方官吏认为妇女外出敬香扰乱了社会秩序,应该坚决予以禁止。
甚而,任何协从人等一律严惩不怠。
RichardVonGlahn在他的名篇《财富的魅力:
江南社会史中的五通神》中对民间妇女的宗教信仰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41]他在分析陆粲《庚巳编》中的五通故事时,注意到五通“性极好淫”。
作者运用了性政治(sexualpolitics)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