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跃辉访谈录无尽与无数《文学青年》甫跃辉专号.docx
《甫跃辉访谈录无尽与无数《文学青年》甫跃辉专号.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甫跃辉访谈录无尽与无数《文学青年》甫跃辉专号.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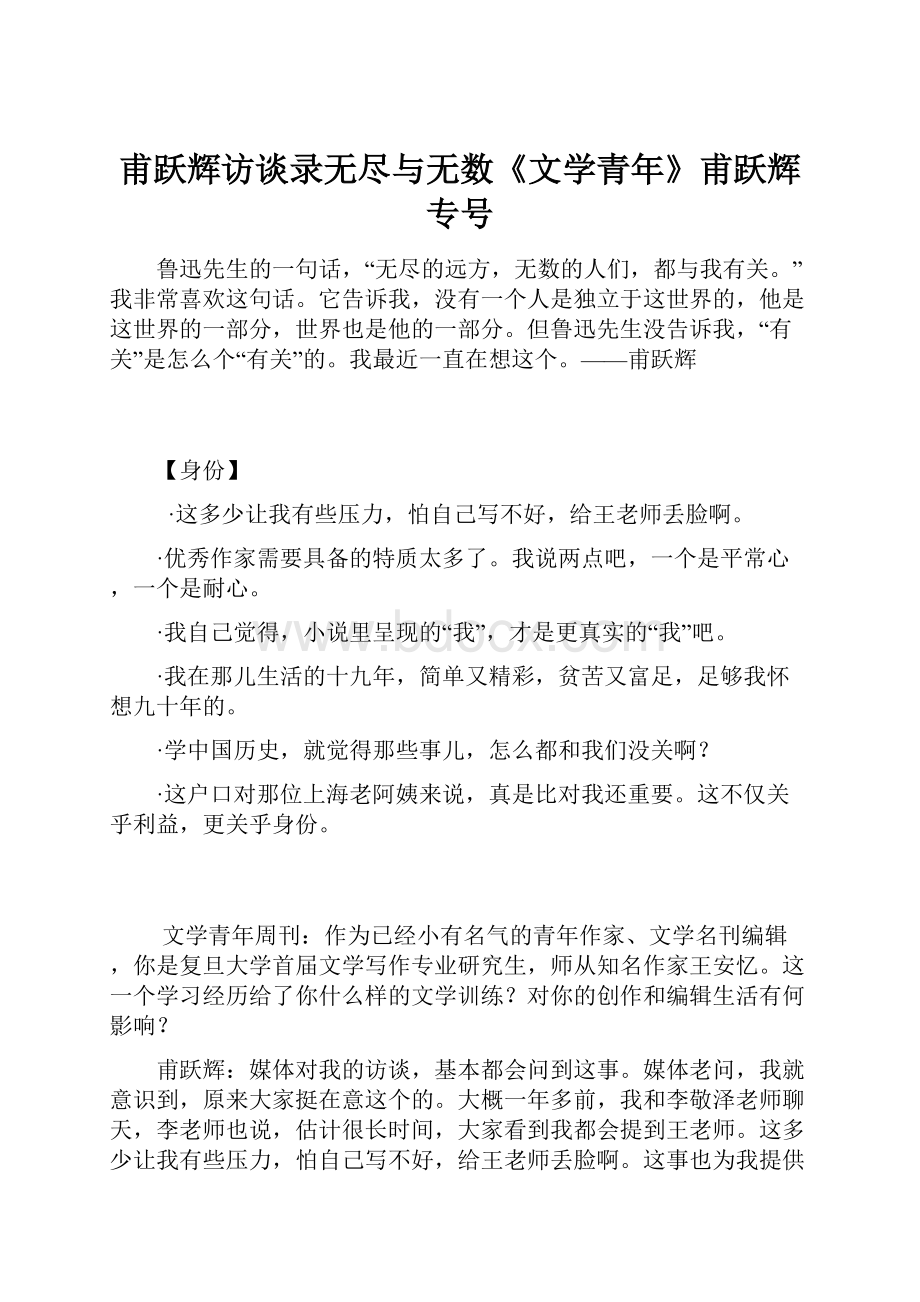
甫跃辉访谈录无尽与无数《文学青年》甫跃辉专号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它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是独立于这世界的,他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他的一部分。
但鲁迅先生没告诉我,“有关”是怎么个“有关”的。
我最近一直在想这个。
——甫跃辉
【身份】
·这多少让我有些压力,怕自己写不好,给王老师丢脸啊。
·优秀作家需要具备的特质太多了。
我说两点吧,一个是平常心,一个是耐心。
·我自己觉得,小说里呈现的“我”,才是更真实的“我”吧。
·我在那儿生活的十九年,简单又精彩,贫苦又富足,足够我怀想九十年的。
·学中国历史,就觉得那些事儿,怎么都和我们没关啊?
·这户口对那位上海老阿姨来说,真是比对我还重要。
这不仅关乎利益,更关乎身份。
文学青年周刊:
作为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文学名刊编辑,你是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师从知名作家王安忆。
这一个学习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文学训练?
对你的创作和编辑生活有何影响?
甫跃辉:
媒体对我的访谈,基本都会问到这事。
媒体老问,我就意识到,原来大家挺在意这个的。
大概一年多前,我和李敬泽老师聊天,李老师也说,估计很长时间,大家看到我都会提到王老师。
这多少让我有些压力,怕自己写不好,给王老师丢脸啊。
这事也为我提供了一些隐形的方便,比如,有些跟王老师关系不错的长辈见到我,就会对我格外照顾一些吧。
去年和中国作协去台湾,回来后,台湾朋友跟我说,接待我们的吕正惠老师知道我是王老师的学生,就说应该对我好一些。
哈哈,他们本来对我就挺好了。
另外,对我做编辑也有好处,有些长辈因为王老师的缘故,会比较愿意把稿子给我吧。
这段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则是,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更认真了。
我是2005年底开始写小说的,陆续发表了一些东西。
正式跟王安忆老师读书是2008年,我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
王老师对我的写作提出过很多批评和建议,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我很感激她,但我每次见到她都很紧张,从未开口对她表达过感激。
在此谢谢王老师!
文学青年周刊:
很多人认为,你是一个成长很顺利的作家,你有你独特的故乡经验和异乡生活,有端端正正的科班出身,受到过很好的教育和扶持,你的写作也很刻苦,走的是很正的纯文学的路。
大概很多青年作家会羡慕你。
作家之路本身是很残酷的,大多数写作者和作家都成为时代的炮灰,被传播和认可并留下来的总是极少数。
你如何看待一个作家的长材之路?
有经验可循吗?
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甫跃辉:
我自己现在也没“成材”啊,所以没什么“经验”可谈。
写作确实太残酷了。
有个事儿给我很大的触动:
研究生期间,我在《收获》杂志实习,恰逢《收获》要做五十周年作品精选。
我就去翻看这五十年的杂志目录,让我吃惊的是,很多作家很多作品,我压根就没听说过。
这可是《收获》啊,中国最顶级的文学刊物了,而我是中文系的学生,平时读当代文学不少。
这才多少年,很多人很多作品就已经不为人知了。
所以,发表啊,出版啊,很多时候真的不能太当回事儿。
唐朝三百年,我们熟知的文人和作品又有多少呢?
我们现在那么多作家作品,绝大多数肯定都是炮灰。
没准儿,我也是炮灰。
但炮灰不炮灰,不是我有必要去考虑的。
我想写,写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优秀作家需要具备的特质太多了。
我说两点吧,一个是平常心,一个是耐心。
平常心包括很多,比如刚才说的,别老觉得自己牛逼,别太把发表出版当回事儿;比如不能老觉得自己是个作家,老端着,其实就是个普通人,也不用特意去“体验生活”,因为自己是普通人,每天都在生活。
还有就是耐心,这个太重要了。
不少刚起步的写作者很着急把一个东西写完,着急发表,着急出版,这样肯定不行啊。
文学青年周刊:
从坊间传闻及与你的交往中,感觉你开朗,好酒,而作家通常有孤独的一年,你是个内心保有阴郁甚至变态(这一特征在你作品的人物中有体现)的人吗?
你的性格与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关系?
甫跃辉:
很多时候是吧。
在复旦读本科时,我就认识青年评论家金理了,经常一块儿吃饭喝酒,他知道我写小说,但我从来没给他看过。
认识很久了,有一次他跟我说,让我把小说发给他看看,看后他跟我说,我的小说和我这人不大像。
原话我记不住了,意思大概是这个。
我自己觉得,小说里呈现的“我”,才是更真实的“我”吧。
说到性格,我原来也完全不是现在这性格。
大三以前,我非常非常内向。
去年我回老家,参加高中同学聚会,聊了没多久,他们就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开朗了啊?
你以前都不跟女生说话的。
怎么会有如此大转变呢?
这跟我大三时候在《萌芽》杂志的实习有关。
那是学校分配的小实习。
我在《萌芽》待了两个多月,跟办公室的同事们说过的话大概不到十句。
写实习鉴定时,带我的周佩红老师说,你以后这样可不行,得跟人交流啊。
其实,我也想跟人交流,可实在是紧张,觉得说什么都是错的。
那两个多月,我过得太痛苦了。
读研究生时,经张业松老师推荐,我得以到《收获》实习。
我就想,反正他们又不认识我,那我就从此变个人好了。
就很主动地跟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交流。
慢慢地,我的性格就变了。
但不管外在的性格怎么变,内在的那个自己并没变吧。
因为这样一个内向的内在自我,我才会在小说里比较重视人物的内心,有些小说甚至写得也比较阴郁。
喝酒跟性格也一样,我研究生前喝酒很少的,这一两年喝得多。
这不是好事,以后还是得节制。
不然,小说没写出来,先成酒鬼了。
文学青年周刊:
和许多作家一样,你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带有明显的成长小说特点。
人人或多或少在创作中曾穿上过青少年时期的衣服。
你来自云南,那是一片美丽而富有生命气息而相对纯净的土地,说说你的故乡经验吧,它们给了你什么文学上的滋养?
甫跃辉:
我是个特别喜欢回忆的人,对画面有非常好的记忆力--当然,得是我感兴趣的画面。
我常常会跟朋友说起故乡的事儿,一个个画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太鲜活了,而我的表达太苍白。
不记得在哪儿看到的了,南京师范大学的何平老师说,我有一个“强大的故乡”。
也不是那儿特别美--我老家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施甸并不是有名的风景区。
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我只好跟人说,就是腾冲旁边的一个县。
我在那儿生活的十九年,简单又精彩,贫苦又富足,足够我怀想九十年的。
我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不少,比如2013年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刻舟记》。
但我没有直接说这是云南,这是保山,这是施甸。
直接说出名字和虚构一个名字是很不一样的。
2014年,我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一个短篇《母亲的旗帜》,第一次在小说中直接用了老家的地名松山。
对,著名的松山战役就发生在保山。
文学青年周刊:
很多作家写作,以及作品,都存在一个外来者和异乡人的身份。
你自云南乡村进入中国内地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上海,这个城市和你原来的故土,分别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甫跃辉:
人会本能地把自己和自己所待的地方当成中心吧。
小时候,我还以为保山就是世界的中心呢。
有一阵子,我看天气预报都看北京的,以为北京什么天气,保山就什么天气。
长大了才知道,对整个中国来说,保山实实在在是“边城”。
保山的历史,影响到中国的很少。
学中国历史,就觉得那些事儿,怎么都和我们没关啊?
上海呢,又是中国特别中心的地方。
保山和上海,这反差就太大了。
从我上海的视角去看保山,从保山的视角来看上海,都是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不少写作者都想通过写作找到归属感,能够让内心安稳。
我现在这样子,离开保山了,不大可能再回去长期生活了,算是新上海人,但对上海也不熟悉,没有本土上海人对上海的那种感情。
两边不靠,很难在某个确定的地方找到归属感,也就没有安全感。
或许只有写作,才能让我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文学青年周刊:
关于乡土经验的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作家,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以及莫言、苏童、马原等,都写出了各自非常成功的作品,甚至形成了各自的文学场。
近二十余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的人流向城市,城市的器物与习惯蔓延至乡村,传统和风俗日益退却。
你如何看待乡土小说--假设这一类型存在的合理性--在当下和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甫跃辉: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乡土小说在其间占据了怎样巨大的空间。
有人甚至说,中国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的城市小说。
这么说当然比较离谱。
假如用写的什么地方来区分小说管用,所谓城市小说,就是写到城市的小说而已。
没那么玄乎。
城市也不是非得像纽约那样才叫城市。
上海是城市,昆明是城市,我老家保山市的市区也是城市。
不管写的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只要能写出城市里生活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就是城市小说。
生活在城市--不管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里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的。
从外在的物质状况来说,每个城市都有商店啊酒吧啊KTV啊酒店啊,这些场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城市人的性格。
同样的,山林、野地、田亩、江河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乡村人的性格。
这也是所谓“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这样的分类方法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吧。
当下,中国城乡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他们的生活、心态等等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先说个城市的事儿,我租住在上海的一栋筒子楼里。
那儿住的,要么是外地人,要么是生活相对贫苦的上海人。
有一次,一位江西过来打工的中年女人和我聊到她小孩上学的事儿,问我有没有上海户口,我说有,又说,不过这也没什么的,没准儿过几年户籍制度就取消了。
这时候,一旁洗衣服的上海老阿姨不答应了,说上海户口怎么能取消呢?
取消了还得了……我想,这户口对那位上海老阿姨来说,真是比对我还重要。
这不仅关乎利益,更关乎身份。
再说农村的一件小事。
我老家农村,这几年很多人家都在盖新房子,钢筋混泥土的那种,有点儿像上海的别墅。
盖了房子要请客吃饭啊,两年前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吃饭时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张卫生纸。
这是从未有过的。
这证明大家日子过得好了,开始像“城里人”一样讲卫生了。
甫跃辉:
我非常感谢李老师对我的鼓励。
那句话是2012年评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的时候,李老师开玩笑说的。
差不多可以说,正是李老师这句话,让我得了这个奖。
他这句话不止让我吃惊,也让其他评委老师很吃惊。
我认识的一位评委老师见到我,开玩笑说,小甫你是不是贿赂过李敬泽啊?
我说我都不认识李老师啊。
在这次评奖后,我才跟李老师建立起联系。
过了几个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给我出短篇小说集《动物园》,我脑袋一热,就给李老师发了条短信,问能不能给我这本书写个序,李老师一口就答应了。
我当时身在东莞,把这事儿跟塞壬一说,塞壬说你真是太过分了,她认识李老师那么多年,都不敢提这种要求!
又过了几个月,李老师真把序写好了。
在序里,李老师又提到了这句话。
很长时间,大家都拿这话开玩笑。
几天前,在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上见到毕飞宇老师,毕老师还说,别人得奖也就得了,我得奖还得了个标签。
我真正写到“性”的小说并不多,到现在,主要就那么三四篇吧,中篇《亲爱的》、《弯曲的影子》,短篇《坼裂》和《普通话》。
《动物园》里也有,很少。
两性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把这个写好了,是非常牛的事儿。
我以后肯定还会有不少篇目写到这个。
希望我能真的做到你说的“狠”。
我现在写得还不算“狠”,仅仅是尽量真切而已。
写作的时候,最大的禁锢不是外面给的,而是我们自己给的。
当内心自由了,才能坦然地写作。
不管写性,还是写别的,写作都需要来自内心的勇气。
文学青年周刊:
这两年你一口气出了五本书,短篇小说集有《少年游》、《动物园》、《散佚的族谱》,中篇集有《鱼王》,长篇小说《刻舟记》。
刚刚,又在台湾出了短篇小说集《狐狸序曲》,这已经是第六本了。
据我观察,被人谈得较多的是你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尤其是其中顾零洲系列的几篇。
如此立体的写作,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创作精力和动机?
你本人有更为看重的体例和作品吗?
甫跃辉:
我现在写作的时间太不规律的。
基本是晚上写,写得很慢。
很多人对我的印象都是特别勤快,写得特别多。
但我真是挺懒的,写得也不多。
比如今年吧,我到现在就写了三个短篇一个中篇,加起来就四万字。
那个中篇还没修改。
大概是我刚写作那几年写得多,积攒了不少东西,有的朋友就觉得我写得快写得多吧。
我写短篇比较多。
我平时也很喜欢读短篇。
这也有个私心,因为写长篇是个大工程,一旦失手,很划不来。
所以,写长篇得慎重。
文学青年周刊:
你较近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是一部风格和作品背景差异较大的书。
最有辨识度的,我认为同样是“动物园”系列,紧张而细腻,为2010-2012年间的作品;《晚宴》结束了你对顾零洲这个人物的塑造,时间回溯到2009年前的创作,题材以乡土和城乡结合部为主,有《旧城》、《老街》等,最后一篇《苏州夜》是单纯的都市生活,写一个初次招妓的年轻人。
你也说过,希望作多种尝试。
那么到目前为止,是否有自己确立或希望成为的风格?
甫跃辉:
每个重要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吧。
我当然也想确立属于自己的风格。
但不能为了确立而确立,那样太刻意。
我试图写各种各样的东西,但这些东西终究是我写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儿,再怎么七十二变,终究还是那个猴子。
我现在仍然没有找到,或者说建立起那个属于自己的具有强大辨识度的风格。
因为我还没能穷尽自己。
我相信,在穷尽自己的路上,所为的风格,会自然形成的。
文学青年周刊:
就我所见,“动物园/顾零洲”系列是你的作品中被谈论最多的。
你如何看这一系列?
它们似乎也体现了你一些希望建筑属于自己的文学场域的野心,不少作家都有这样的成功经验,比如高密之于莫言,枫杨树村之于苏童。
甫跃辉:
我在《动物园》后记里有一段话:
“曾经有记者采访我,说很多作家都会为自己的写作找一个‘根据地’,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鲁迅有鲁镇,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苏童有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
现在的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作家还在不断建构这样的‘根据地’。
我是不是也要给自己弄一块呢?
我说,不,坚决不!
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太多太多了,我再增加一块,无非是鹦鹉学舌,多我这一块儿少我这一块儿区别也大不到哪儿去。
”
“顾零洲系列”没按照地名来统一,而是按照人名来统一。
当然,这也新不到哪儿--文学之所以求“新”,是因为时代“新”了。
要和时代相呼应,所以也就要求文学“新”。
很多人都干过这样的事儿,比如高晓声就写过“陈奂生”系列。
我只是觉得,这对我来说,琢磨一个人,比琢磨一个地方更有意思一些。
我挺重视“顾零洲”系列,到现在一共写了六篇,还有几篇计划要写。
《小说选刊》选载这系列中的《坼裂》一篇时,我在创作谈里说过,在我的所有小说中,“顾零洲”是和我本人是最像的。
我写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写我自己,那些明亮的和黑暗的东西,在他身上有,在我身上也有。
当然,他又不是我。
很多很多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儿,在我身上都没发生过。
但如果我和他处在完全的情境中,难保那些事儿不发生,而且,我敢肯定,我也将和他一样在内心里挣扎、推让、不舍。
这就是“虚构与纪实”的微妙吧。
文学青年周刊:
你的小说集《鱼王》包括三个中篇小说,写的是三种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寓言故事。
前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也有代表作叫做《鱼王》,同样也是寓言性质的短篇小说集。
越往现代走,普通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衰弱得很厉害,而在过去,甚至人类的早期,动物与人的关系十分密切,敌人般的豺狼虎豹,伴侣般的马和狗,互为依存的禽类,鱼与渔民……这些经验随着现代化,人类的进与动物的退,在迅速消亡。
你是如何把握住这一层已然不明朗的关系,并且采取了寓言般超脱的方式?
想传达什么?
甫跃辉:
不记得是哪位朋友跟我说的了,说我写了很多以动物作为篇名的小说。
他这么一说,我回头看看,还真是。
除开你刚说的这三篇,还有《雀跃》、《红马》、《巨象》、《饲鼠》、《鬼雀》、《红鲤》等,还有些篇名没带动物的名字,实际也写到了动物的,比如《动物园》、《三条命》、《初岁》等。
这跟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有关吧,农村有很多动物,我小时候养过不少,包括兔子、老鼠、鸟、鱼等。
我们写作,一般来说都专注于人。
但人其实只是世间万物之一,单单看到人,这世界就太小了。
写动物,就是想看到更广大的世界,看看我们和这世界有怎样的关系。
文学青年周刊:
就我对你的阅读感受,特别深刻且十分喜欢的,是你对事物的铺陈,春笋般四处生长的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举个例子,“一列火车正朝大桥驶近。
是从身后来的,汽笛尖利地响起,头顶的铁桥颤动着,有小小的水珠落下,声音越来越近,四周的黑暗也颤动着。
他紧紧抱着包,紧紧压迫着心口。
他的心正应和着铁桥的颤动而颤动着--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只在大水里泅渡的墨黑的小老鼠--火车到了,铁桥被猛地一震,就要垮塌,不知哪儿来的力量,他伸出一只手,撑住铁桥。
”这是你在一篇小说中队一小段场景的描写。
现在的青年作家可能缺乏这种经验、想象和耐性;同样的,你的小说中有许多类似意识流的漫想。
我相信,这是文学的一种魅力,它捕捉细节,甚至制造感知。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写作特征?
下面也将要谈到,可能也是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有人认为你的作品过于繁复、啰嗦。
甫跃辉:
这可能跟我的记忆方式有关吧。
前面说过,我会记住很多很多画面。
写作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也全是画面,这些画面都是没发生过的,但它们在一瞬间就生成了,跟真实发生过的几无二致。
我有强大的、用文字把这些画面描述出来的欲望,包括画面里的一丝风,一根草,一只虫子。
有时候,觉得自己的描述太苍白,没有我脑海里的画面那么精彩,就会用很多文字尽力去表达。
这大概就是有时候会显得啰嗦的缘故吧。
嗯,应该用最简洁的文字,传达出最复杂的意味。
要说灵感来源,大多还是来自生活吧,并非书本。
确实,我的写作至今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
我觉得,繁复和啰嗦也不全是坏事,看用在什么地方吧。
最好是,该啰嗦的地方得啰嗦,该简洁的地方能简洁。
大多数人活一辈子,都这么简单肤浅。
希望有一天,我能深刻地写出这种“大多数人的简单和肤浅”。
文学青年周刊:
2013年底,在上海召开了你的第一个文学研讨会,我通读了纪要,感觉对你的作品中的优点、特质及问题,都有深刻的剖析。
批评家程永新评论你的创作,他说,一部好的小说其实有的时候是通过修改产生的,但这一点在你那里体现还不够。
这是程老师的看法。
当然,我读过的一些你的作品,里面有比较明显的修改痕迹,因为你标注了修改时间。
这也是一种创作习惯。
你的写作,是习惯一气呵成呢,还是更多的会不断修改打磨?
谈谈你的写作习惯、创作和润色的灵感来源。
甫跃辉:
多数都会经过大量的修改。
比如我那小长篇《刻舟记》,我刚写作不久的2006年完成的初稿,到2012年出版,六年时间,修改了六次,每一次都有详细的时间记录。
还有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普通话》,我在校样上还做了大量的修改。
程永新老师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过我短篇,《朝着雪山去》和《秋天的刀子》,每一篇也都经过大量修改。
程老师和我的责编廖增湖老师都特别认真,他们一次次跟我聊怎么改可以让小说更好一些。
我比较笨,总不能一次领会,但笨归笨,几次改下来,仍然受益匪浅。
真得好好感谢他们。
平均下来,我的每篇小说都会修改三四次吧。
印象中只有一篇例外,就是201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骤风》,那是个六千来字的短篇,我写了三个小时,写完回头看了一遍,几乎一字未动。
要说灵感来源,大多还是来自生活吧,并非书本。
平时就会很注意生活的细节,经常会觉得,哦,这个可以写进小说啊。
这也是写作的人让人厌烦的地方,不能让生活成为自然的生活,偏要让生活成为虚构的小说。
文学青年周刊:
你的写作中有没有体现出某种核心的价值?
这一点也是程永新提出来的,他认为你的小说中缺乏一个核心价值。
甫跃辉:
确实,我的写作至今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
这个世界每天那么多事发生,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天空、大地、植物、动物、人类,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是这理所当然的世界的一份子,每天活得理所当然。
可有时候我真是觉得恐怖啊,感觉这世界全不对。
什么都不对。
我自己也是不对的,每一件事都不对。
这样的情形,我哪里去找一个核心价值?
之所以写作,或许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核心价值”吧。
但我现在还没找到。
等哪天我找到了,并能够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或许我的写作就具有某些永恒的品质了。
文学青年周刊:
张新颖教授据说是你发表的首个作品的推荐人,他对你的关心自不待言,而他也指出过你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你的语言特别繁复,以至于啰嗦。
我觉得这点觉得很有意思。
啰嗦是不是写作的障碍,可能不大好说,比如我熟悉的几位作家,蒋一谈、赵志明,说话都是比较绕的,赵志明讲故事也很繁复。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个“繁复”或者“啰嗦”的特征?
甫跃辉:
我一直很感激张老师,我的处女作《少年游》是由他推荐发表在《山花》杂志上的。
而且,当时我并不知道老师能够帮学生推荐发表作品,我只是把小说发给他看看,问他这样的作品是不是达到发表水平了,他就回邮件说,帮我推荐出去了。
我觉得,繁复和啰嗦也不全是坏事,看用在什么地方吧。
最好是,该啰嗦的地方得啰嗦,该简洁的地方能简洁。
郑板桥说,删繁就简三秋树,但这世界不能总是秋天,也得有枝繁叶茂的夏天。
不然岂不是太单调了点儿?
文学青年周刊:
陈思和教授对你的创作作过长篇评述,其中大部分是肯定和鼓励的,最后谈到对你的一个不满足是“不够深刻”。
对社会感受不够深刻,反映在作品里。
你对这一个“不够深刻”怎么看?
甫跃辉:
我没想到我的研讨会陈老师能来,来了还说了那么多。
谢谢陈老师。
陈老师说得对,我现在的作品是不够深刻。
现在怎么可能就深刻呢?
我觉得我还在练习阶段呢。
不止写作这样,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这样,“不够深刻”。
我时常觉得,我只是活在这个世界的表面。
我并未能够真正地了解这个世界,也并未能够真正地了解自己。
活得太简单肤浅,写得太简单肤浅。
也有可能,我活了一辈子写了一辈子,还是这么简单肤浅。
那只能说,这简单肤浅也是真实只一种吧。
大多数人活一辈子,都这么简单肤浅。
希望有一天,我能深刻地写出这种“大多数人的简单和肤浅”。
我想,“深刻”还跟作品的体量有关吧。
中短篇要写得“深刻”,太难了。
鲁迅先生这样的毕竟太少。
对写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大概不是看别人,而是审视自己吧。
在任何领域,圈子的形成都是很正常的。
哪怕在村里,每户人家也会形成一个交往的圈子。
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非常喜欢这句话。
它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是独立于这世界的,他是这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是他的一部分。
随随便便就是“作家”,那“作家”就太贱了。
文学青年周刊:
八十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作家,是否普遍面临一种“不够深刻”的问题?
我们的学生时代没有经历过重大的社会变革,即便有,比如八九十年代之交,对我们而言,也是感受不深。
当我们开始写作,面对的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物极度接近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接触的是类似摇滚乐的表面抵抗,以及无处不在的解构,我们更多地关注“我”与个体,人性偶尔写到,人生或家族的长河却很少涉足。
如何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刻起来,尤其,体现在我们的创作上,去获得那种真切的“罪与罚”式的深刻?
甫跃辉:
我想,“深刻”还跟作品的体量有关吧。
中短篇要写得“深刻”,太难了。
鲁迅先生这样的毕竟太少。
更多作家的“深刻”还是靠长篇体现的。
比如你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我的感觉,他的短篇也不“深刻”。
他的那些长篇,才真正让他的作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肌理深处。
我和我的同辈作家们,目前多半写的还是中短篇,相对来说,长篇还比较少。
有分量的长篇更是少之又少。
怎么深刻起来?
这个还是交给时间吧。
文学青年周刊:
今年的《收获》杂志以两期的规模,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这是《收获》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收获》以“先锋小说专号”后时隔近三十年再次推出集体推出青年作家。
八十年代的那次,余华、苏童、格非、马原、孙甘露等当时的青年作家集体亮相文坛,如今来看,当时的眼光不可谓不犀利。
这次青年作家专号推出了一批作家,包括你。
身处其中,你如何看待这一批青年作家的集体亮相,你们这些作家是否集中了这个时期最优秀的青年作家,将取得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等前辈那般成就?
你如何看待这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情况和特征?
甫跃辉:
头两年《收获》也推出过青年专号的。
只是媒体没这么关注吧。
这个谁知道呢?
写作是个漫长的、淘汰率非常高的事儿。
兴许现在正写得热闹的这一波年轻写作者,过个几年,大部分都不写了;兴许不少还没开始写作的同龄人,会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