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文学人物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docx
《从古典文学人物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古典文学人物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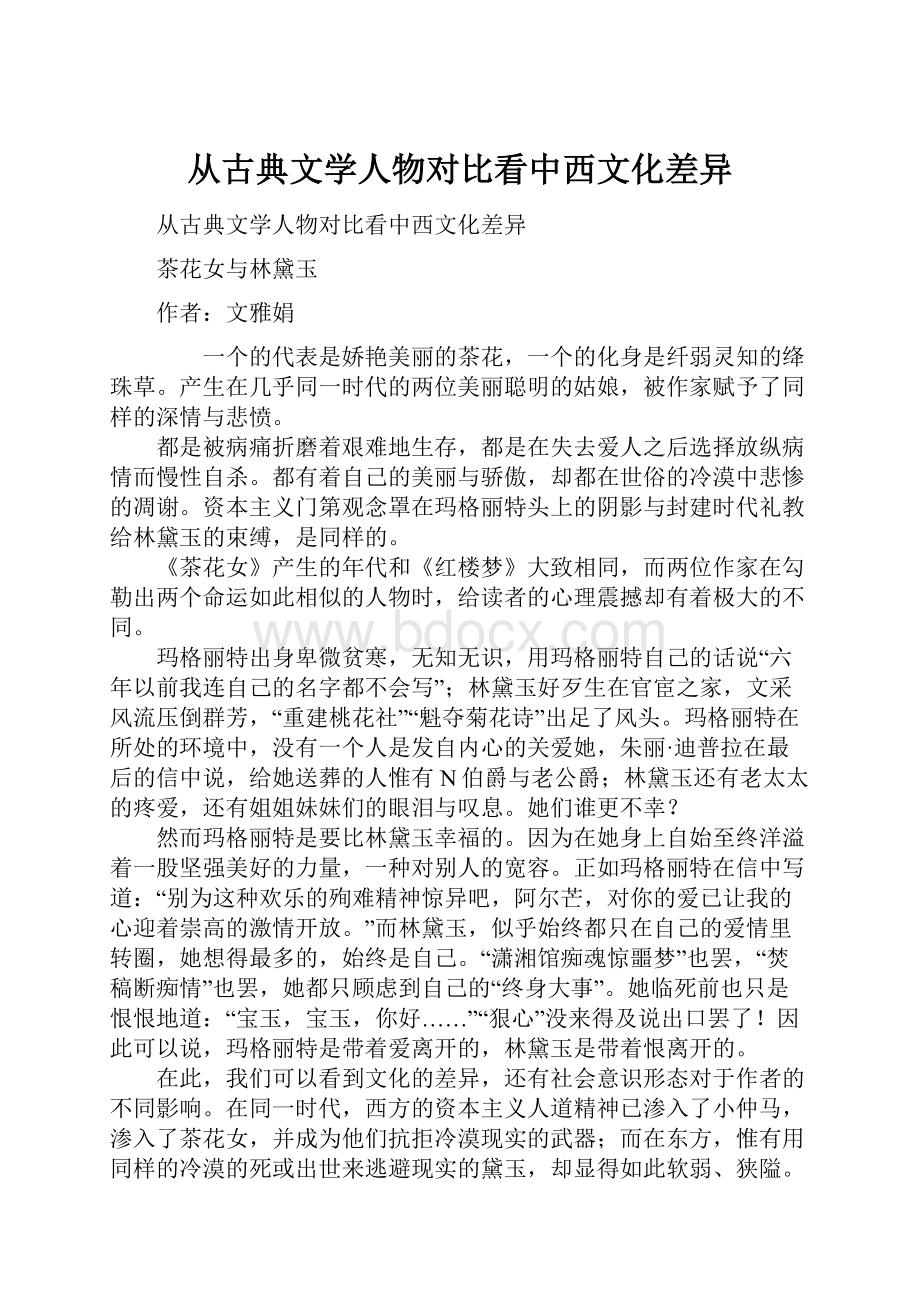
从古典文学人物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
从古典文学人物对比看中西文化差异
茶花女与林黛玉
作者:
文雅娟
一个的代表是娇艳美丽的茶花,一个的化身是纤弱灵知的绛珠草。
产生在几乎同一时代的两位美丽聪明的姑娘,被作家赋予了同样的深情与悲愤。
都是被病痛折磨着艰难地生存,都是在失去爱人之后选择放纵病情而慢性自杀。
都有着自己的美丽与骄傲,却都在世俗的冷漠中悲惨的凋谢。
资本主义门第观念罩在玛格丽特头上的阴影与封建时代礼教给林黛玉的束缚,是同样的。
《茶花女》产生的年代和《红楼梦》大致相同,而两位作家在勾勒出两个命运如此相似的人物时,给读者的心理震撼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玛格丽特出身卑微贫寒,无知无识,用玛格丽特自己的话说“六年以前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林黛玉好歹生在官宦之家,文采风流压倒群芳,“重建桃花社”“魁夺菊花诗”出足了风头。
玛格丽特在所处的环境中,没有一个人是发自内心的关爱她,朱丽·迪普拉在最后的信中说,给她送葬的人惟有N伯爵与老公爵;林黛玉还有老太太的疼爱,还有姐姐妹妹们的眼泪与叹息。
她们谁更不幸?
然而玛格丽特是要比林黛玉幸福的。
因为在她身上自始至终洋溢着一股坚强美好的力量,一种对别人的宽容。
正如玛格丽特在信中写道:
“别为这种欢乐的殉难精神惊异吧,阿尔芒,对你的爱已让我的心迎着崇高的激情开放。
”而林黛玉,似乎始终都只在自己的爱情里转圈,她想得最多的,始终是自己。
“潇湘馆痴魂惊噩梦”也罢,“焚稿断痴情”也罢,她都只顾虑到自己的“终身大事”。
她临死前也只是恨恨地道:
“宝玉,宝玉,你好……”“狠心”没来得及说出口罢了!
因此可以说,玛格丽特是带着爱离开的,林黛玉是带着恨离开的。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差异,还有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作者的不同影响。
在同一时代,西方的资本主义人道精神已渗入了小仲马,渗入了茶花女,并成为他们抗拒冷漠现实的武器;而在东方,惟有用同样的冷漠的死或出世来逃避现实的黛玉,却显得如此软弱、狭隘。
比较中外古典作品,无一例外地发现:
西方作品中的主人公始终有着昂扬的精神,如简·爱、凯瑟琳、郝思嘉;而东方则渗入了太多的虚无玄幻,如《源氏物语》、《镜花缘》里的人物。
茶花女与林黛玉是根植在不同文化沃土上的奇葩,而她们的形象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应不仅是在文学上,还应在民族精神与社会意识上。
伍子胥与哈姆雷特的复仇之路
复仇,是人类几乎各民族都盛行过的历史和文化现象。
这种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成为各民族文学的宠儿,我们在人类文学宝库中可见人们以各种纷然杂呈的方式演绎着这个近乎永恒的主题。
在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要以史传为载体。
[1]有“史家之绝唱”之称的《史记》,无疑成为这种复仇文学的一个经典,它为我们展现了无数个悲惨壮烈、可歌可泣的复仇故事。
西方国家则从神话传说到古希腊罗马悲剧时代便开始了对复仇主题的演绎,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复仇主题已经发展成一种相对系统化的文学主题。
这时候在英国产生了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复仇悲剧。
《哈姆雷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复仇悲剧家族中的一员,同时也是最具艺术魅力的一员。
本文选取《史记》中独具魅力的伍子胥复仇故事与哈姆雷特的复仇故事相较而论,试图从两个同是为父报仇却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经典故事中分辨中西方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并试图阐释此间差异形成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伍子胥与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过程中复仇主体的行为表现与复仇主体在整个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中寻找其差异的表征。
我们先看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伍子胥复仇过程的描述:
遭奸佞,父兄被杀;图雪耻,亡走异国;过昭关,越险赴吴;存大志,助阖闾立;谋国事,数请伐楚;得良机,引兵入郢;鞭王尸,终雪大耻。
从文本里我们可以发现,伍子胥在得知父亲遭奸佞所害之时起,就已心存复仇之志,决意弃小义雪大耻,借他国之力报父兄之仇。
“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後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
二子到,则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
往而令仇不得报耳。
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
”他在兄长被执后即与楚使者弓矢相向,既而亡走异国,相机复仇。
去楚之际向至交申包胥表明复仇之志,曰“我必覆楚。
”此后,文章极力表现伍子胥在吴国的军事行为,他与吴国国君共谋征伐之事,戮力伐楚,此间无任何犹疑。
吴兵入郢之时,面对申包胥对他鞭平王尸这种行为的责难——“此其无天道之极乎”,子胥曰:
“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3]史记索引对此的解释是:
子胥言志在复仇,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报,岂论理乎!
譬如人行,前途尚远,而日势已莫,其在颠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责吾顺理乎!
[4]执意复仇的伍子胥,抛开伦理的束缚,“倒行逆施”,可谓矢志不渝、心坚意决至极。
《史记·伍子胥列传》的写作,主要是根据《左传》。
伍子胥的父兄被害以及伍子胥引吴兵入郢的事件在《左传》中描述得相当精彩。
[5]司马迁在改写《左传》这段文字时,着重加了两点。
其一,增加了伍子胥逃往吴国时,一路历经磨难、备尝艰辛的情节。
伍子胥先至宋,再奔于郑,又适昭关,昭关欲执之,“伍子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赖一渔父渡之,“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
[6]伍子胥为了复仇,疾病、乞食、九死一生,命运可谓悲惨。
司马迁在描述这个过程中极力体现的伍子胥为复仇忍受的苦难和艰辛,无疑为塑造伍子胥含辛茹苦、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形象添了重要一笔。
其二,“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7]这段精彩文字,也是司马迁后加的。
这种掘尸鞭之三百的复仇可谓是“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怨毒确是怨毒,但在这种残忍之致、怨毒之极的复仇行为中不难感受到复仇主体在长期心挂大仇,今朝得报的无比痛快、酣畅至极的心情。
在此,司马迁舍弃了吴兵入郢“以班处宫”的残酷暴行[8],把历代统治者所标榜的“君讨臣,谁敢仇之?
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将谁仇”的谬论撕得粉碎,着力表现复仇主体舍伦理之义报血亲大仇的快意淋漓。
7
从以上分析可见,《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述伍子胥的整个复仇过程,从父兄遭难之时复仇之志产生,到亡走异国借力复仇,最后引吴入郢,鞭平王尸达到复仇目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矢志不渝、心坚意决,为复仇含辛茹苦、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形象。
在整个复仇过程中,伍子胥没有任何犹豫和疑虑,从始至终,他只有一个坚定的意念即是为父兄报仇,在复仇之前他忍受苦难,使用一切手段,借吴国之力伐楚,最后,复仇成功,他肆意享受折磨仇人的快感,鞭平王尸,雪大耻,报夙仇,这个结果也正是他一开始就想见的,此间复仇主体虽有激烈情感的波动,但其精神世界却是稳定的,并未因外界的风云变换而改变复仇心志。
与此不同,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似乎已把充满鲜血与死亡的动态复仇行为抛在脑后,而在冥思之中另辟蹊径。
《哈姆莱特》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像《史记·伍子胥列传》那样的动态复仇行为,而是主人公哈姆雷特静态的思考。
哈姆莱特在剧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与行动的矛盾中徘徊。
而且,这个矛盾也不是简单的复仇与否的问题。
首先,《哈姆雷特》中关于复仇的方式、手段及其目的的思考,不是一种简单直白的方式,而是更加复杂。
如果说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叙说的伍子胥复仇行为过程是一个直线延伸的轨迹,那么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一剧中演绎的就是一段蜿蜒曲折的矛盾发展历程。
相较于伍子胥在父兄遭难之际便已萌生的复仇之志而言,哈姆雷特的复仇之志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
父死母嫁的突变使他震惊和悲伤,他只是感到这一切太不正常了:
虽然王后和国王告知他“从生活踏进永久的宁静”“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他的母亲竟在父亲去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嫁人了,而且她嫁的竟然是与老哈姆雷特相比简直有“天神与丑怪”之别的父亲的弟弟;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哈姆雷特推断:
“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
”[9]这个阶段的哈姆雷特是忧伤的、悲观的,他的精神世界遭到轰毁,那曾经存在于他的幻想中的理想家园变得“荒芜不治”。
他厌世绝望:
“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
”[10]他想到了死,但并没有准备复仇;他没有找到复仇的依据,只是理想被击碎了。
直到值班哨兵告诉哈姆雷特,已故国王的鬼魂一连几个晚上在城堡出现,他决定亲自观察,终于看见父亲的鬼魂,听到父王被害真相:
“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戴着王冠呢”[11],这时,他开始酝酿复仇的计划了。
哈姆雷特的复仇计划的最终形成是经过反复思考的。
自从见到父亲的亡魂,为父复仇的念头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但是,这位丹麦王子在思索复仇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单纯地考虑杀仇凶雪父耻。
按照一般的逻辑,在装疯试探、演戏证实后,哈姆雷特应该立即举剑复仇,杀死奸王,而且他是有机会这么做的。
但是哈姆雷特却一再犹豫,放弃复仇良机:
面对惊慌忏悔的克劳狄斯,哈姆雷特认为如果此时结果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的”,“这简直是以怨报德”,因而放弃了这抽剑一击的极好机会。
[12]哈姆雷特将复仇同解救丹麦这所“牢狱”的责任结合起来,审慎地思索更适合的时机、更准确的途径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为了更切实、更有效地复仇,借助雪报这一非同一般的仇怨来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哈姆雷特处于思想的囹圄中痛苦不能自拔,他在痛苦的思索中意识到使命的艰巨复杂性,“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
然而哈姆雷特这种思索并未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究竟怎么复仇,在未能等到理想实现最佳时机的情况下,他就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中,不得不采取了远非上策的手段,借与雷欧狄斯比武之机揭露了克劳狄斯的罪恶阴谋,并杀死了仇凶。
此时,哈姆雷特并不是整个复仇行动的策划者和驱动者,他只是在新的阴谋败露时,顺应各种偶然因素造就的必然之势,让那彷徨已久的复仇之剑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个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没有完全实现复仇的正义目标,没有也不能解决他思虑的任何问题。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从乍逢巨变到除掉仇人的漫长过程中,尽情展示了复仇主体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使一个多思的哲人式的王子跃然台上。
在此,莎翁使行动的复仇悲剧变成了人的复仇悲剧,这种悲剧不再以罪行、灾难等外部的矛盾和冲突为重点,而是以人的内部的矛盾斗争为中心,揭示一个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的人怎样探索自我和外在两个世界。
在这样的复仇悲剧中,事件本身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是作为事件施动者的人。
《史记·伍子胥列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复仇主体含辛茹苦、隐忍以就功名的复仇准备过程以及复仇成功时快意鞭尸的一个烈丈夫形象,我们从这个烈丈夫身上感受到的是那种忍辱负重、不屈抗争的复仇精神内蕴。
《哈姆莱特》让人记住的却是丹麦王子在“牢狱”中沉思的身影。
从这种意义上说来,哈姆莱特是这部剧的中心,复仇行动只是映衬他的一种手段。
在此,独具匠心的莎翁拭去了复仇之剑上的斑斑血迹,将它改造成探索人性和世界的利器。
我们也可以在复仇主体对人、对生命、对宇宙的思考中更多地体会到深层的人性底蕴。
中西方两个经典复仇故事体现的复仇观念,是中西方整个复仇主题系统整体性价值取向突出的表现。
这两个复仇经典故事中所昭示的中西方复仇文学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
首先,西方较为偏重复仇行使时主体精神世界的冲突;中国则较为关注复仇事件本身的结局,包括关注复仇者自身在复仇成功后的命运。
两者一重人性揭示,一重伦理实现。
《哈姆雷特》中极力展示的是王子在复仇过程中静态的思考与行动的矛盾,复仇主体作为自己的精神主宰的人探索自我和外在两个世界的过程。
而《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更多的是关注复仇事件本身的发展状态,伍子胥在复仇过程中的行动,司马迁浓墨重彩地描述伍子胥复仇之路上的艰辛并特意展示复仇的结局——伍子胥掘平王墓鞭尸三百,终报父兄之仇。
此外,伍子胥在复仇成功后又遭吴国奸佞所害,自刎而亡的命运也在司马迁笔下以大篇幅的笔墨展示。
其次,西方写复仇,注重个体性格成熟的过程、人格的变化与完善;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少了必要的心灵冲突与过程描叙,而让最为痛快淋漓的仇凶毁灭的结局尽快地充分展露,以期大快人心。
哈姆雷特最初在剧中出现的时候只是一个受过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的单纯的大学生,而在经历为父复仇的整个过程中,通过一段痛苦的思索,对个人与世界进行探索的精神洗礼中逐渐成熟,他对世界的认识也从一种理想化的状态转到了现实和残酷中,并对这种班驳的现实有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试图借复仇之机改变现实的荒乱黑暗。
《史记·伍子胥列传》在复仇主体心理冲突方面则几乎无所涉及。
按一般逻辑,伍子胥经历如此震撼的家变,复仇之路上经历甚多艰辛,心理上肯定有个变化过程,史记索引中也曾提到伍子胥“志在复仇,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但文中却没有关于伍子胥心理痛苦的文字。
而复仇结局——掘墓鞭尸在历史上给人的审美感受确实是达到了大快人心的效果,同时也由子报父仇的的成功结局实现了伦理目标。
其三,西方复仇之作常引发人们对个体与命运抗争的悲壮感,让人反思深省;中国复仇之作更多的激发善必胜恶的愉悦感。
哈姆雷特的整个复仇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是与丹麦黑暗现实、与悲剧命运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抗争的过程,这种抗争的失败无疑带有强烈的悲剧色彩,使人面对这种结局时产生强烈的悲壮感,并随着悲剧的复仇主体对生命、对世界、对宇宙的思考而陷入反思。
伍子胥的复仇,抛开其中的君臣礼仪不说,掘墓鞭尸的结局以复仇主体在此间的痛快淋漓、彻底雪耻而言,势必使人产生恶人得诛、善人大仇终报的愉悦感。
相较而论,西方的复仇每每牵动着震撼人心的重大悲剧主题,也往往涉及了对人灵魂的拷问,很少驻足于伦理上的具体个别的是是非非、善恶美丑。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西方复仇文学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实际上是由中西方文化习俗、文学传统等诸般差异作用的结果。
复仇在上古氏族社会即已有之,上古时代的复仇是以血族复仇的形态出现的,其在“死后有灵”的神秘观念支配下,认为横死者要求本氏族成员为自身讨还血债;借助氏族成员的义务,“以血还血”的信念强固了氏族群体意识,并在这种意识支配下建构了复仇伦理。
[14]在中国,到了周秦极其以后的宗法社会,复仇继续流行,这时候作为原始人血族复仇的直接延续,复仇演变为为家族,家庭成员雪恨,即血亲复仇。
古代中国血缘宗法制度根深蒂固,一族之人按照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彼此负有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为亲人复仇即是其中之一,这种责任与义务一旦发生,就是必须履行的,不可推卸的,[15]这种观念造就了现实中血亲复仇的持久与普遍受推重,而这又离不开先秦儒家学说中对复仇的肯定。
以孝悌为本的儒家思想对血亲复仇给予充分的肯定。
《孟子·尽心下》: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
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也。
”汉初的儒家经义对复仇也作了具体的解释。
《礼记·曲礼》:
“父之仇也,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孔颖达疏:
“父是子之天,彼杀己之父,是杀己之天,故必报杀之,不可与共处于天下也。
天在上,故曰戴。
”此外,在《周礼》等儒家经义中也散见许多对复仇的肯定言论。
可见,早期儒家学说中对复仇的态度是一致的,它鼓励提倡人们血亲复仇。
复仇是受害主受到侵害后迫不得已进行的极端性报复方式,复仇的实施,往往企图从肉体上毁灭仇主,复仇主体所期待达到的,与执法所得结果并无大异。
在礼崩乐坏,正常社会秩序被打破的情形下,复仇又每每作为对善被无情毁灭的一种正义抗争。
对此,儒家学说中没有正面的论述,但孔子以直报怨的观点却是对这种正义抗争的的一种支持。
[16]此外,先秦儒家将复仇从原始心态和个体冲动中提纯升华,赋予了复仇以正义庄严的伦理内核与肯定性的道德评价。
儒家对血亲复仇的这种无条件的肯定,对古代复仇文学、复仇文化价值观的建构是决定性的。
古代中国复仇文学的总体倾向是以“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表现模式,演绎善对恶的正义讨伐,而复仇者在复仇行为过程中的心坚意决、无所顾忌也往往得到“一面倒”式的褒举同情。
这种对复仇主体“一面倒”式的褒举以及复仇主体的心坚意决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中就已深植其根。
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咏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讴歌的就是两个复仇神话故事。
《山海经·北山经》、《述异记》等载炎帝的少女名叫女娃,溺死在东海,死后化作精卫鸟,经常衔西山的树枝小石投入东海,想填平它,其名字又叫冤禽、志鸟;刑天与天帝争作主神,头被砍掉,他就以乳头为目,以肚脐为嘴,手操斧盾挥舞而战。
这两则神话中的复仇主体,都不因身死体残而罢休,而是执著地完成未竟的复仇事业。
可以想见,复仇的过程展示已说明了其占据复仇主体的整个追求目标,而且体现了对复仇不惜代价的倡导。
上古神话对复仇的倡导,对复仇精神的褒扬在后来的复仇文学中衍生的正是对直接体现复仇精神、复仇者命运的复仇事件发展过程、复仇事件的结局、复仇主体命运的关注。
同时,儒家鼓励、重视复仇的思想,经汉人的复仇世风传递,[17]逐渐形成以能否完成血亲复仇的义务来判断其人的道德品质的评价标准,这种价值取向在古代中国复仇文学中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古代中国史传描述载录的众多行孝尽伦、行侠尽忠的复仇故事中,复仇与否,往往成了个体人格品位评定的重要风标。
在《史记·伍子胥列传》结尾,“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
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
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
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18]对于伍子胥引吴兵灭楚国及入郢后的倒行逆施,司马迁认为“怨毒之于人甚矣”,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但是对伍子胥所选择的复仇之路,却是非常赞赏的,他认为假若伍子胥为尽孝而与父亲一块死,那么他的死“何异蝼蚁”?
毫无价值和意义。
而伍子胥为复仇选择了“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隐就功名”之路,司马迁认为“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在此可见司马迁对复仇的肯定,复仇与否成为伍子胥为“蝼蚁”或“烈丈夫”的个体人格品位评定的风标
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为内核,偏重个体尊严及其人格价值。
西方人的价值观认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和出发点,人必须为自己个人的利益而奋斗,为自己才能维持社会正义,爱自己才能爱他人和社会,为自己奋斗也是为他人和社会奋斗。
在这种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下,复仇的价值取向往往是维护个体的荣耀尊严,异于中国文化以家族、社会为本位,复仇乃是行孝尽伦的社会使命。
这种价值取向在复仇文学中直接表现为对复仇主体精神世界的冲突、复仇主体的人格变化,完善成熟的过程以及复仇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与世界、宇宙、命运等的关系的关注。
此外,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西方文化圈中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对曾经得罪过自己的人“怀恨在心”,念念不忘,这不是善的本分。
基督教认为灾难是由人自身的过失造成的,人的性格和行为是其祸福的根源。
而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文艺复兴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崛起,对人世生活乃至人本身价值的关注,使得西方平等、正义等观念普遍被接受。
在这种追求善,追求公平与正义的文化背景之下,西方复仇文学的褒贬性倾向呈现出一种动态性的流变,明显地显示着文明演变的轨迹。
在这个流变过程中,它更多地体现出对复仇的方式、手段及其目的的思考。
大体上说,西方复仇文学表现可分为古希腊神话传说、文艺复兴后以及18世纪后这三个阶段。
[19]西方文化对复仇的反思,可以说从古希腊传说中就埋下了种子。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复仇观念丰富复杂,每每表现一些不全是正义的、有争议的复仇,以及让复仇主体饱受灵魂撕裂、懊悔不已的甚至非正义的复仇。
复仇主体在手段实施过程中的犹豫、焦虑及其复仇后的心灵搏斗,连同复仇的代价都给人以深深的启迪。
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复仇文学中对复仇褒贬的倾向就更加减弱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悲剧中的复仇颂歌在很大程度上打了折扣。
文艺复兴时期,在人文主义思潮中,复仇文学主题倾向了对生命与宇宙的重新认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这种社会批判,又往往是站在一种抛开所有片面之见的公正立场上,而力求揭示一种深层的人性深蕴。
《哈姆雷特》中复仇主体“生存与毁灭”的疑问,主体对荒芜黑暗的现实的认识与这种现实激起的强烈的责任感,以及贯穿整个复仇行为过程的对人灵魂的拷问,都显示西方复仇文学中复仇观念的深刻复杂,这种状态下的复仇主题,就决不会驻足于伦理上的具体个别的是是非非、善恶美丑。
[1]王立:
《原始心态与先秦复仇文学》,《求索》1992年第2期。
Q
[2][3][4][6][7][18](西汉)司马迁:
《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
[5][8]《左传选》,徐中舒编注,中华书局,1963年。
[9][10][11][12][13](英)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朱生豪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
[14][16]王立:
《孔子与先秦儒家复仇观初探》,《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15][17]刘厚琴:
《论儒学与两汉复仇之风》,《齐鲁学刊》1994年第2期。
[19]廖炜春:
《〈哈姆雷特〉与文艺复兴英国复仇悲剧》,《国外文学》1998年第4期
西方古典英雄比中国的好色?
作者:
米琴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大都不好女色,而西方的古典英雄却颇有好色者。
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大多与女色无缘,与女色有缘的几个主要英雄则都有拒绝女色的光荣业绩,头号英雄宋江被形容为“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出于怜悯,宋江娶了婆惜,但因其“好汉胸襟,不以女色为念”,冷落了婆惜,至使后者发生婚外情,可见在中国传统观念里,英雄好汉的本色之一是不恋女色,所谓“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英雄气概与对女性的情爱似乎是矛盾的。
打虎英雄武松初遇潘金莲时,但见其“脸如二月桃花,暗藏风情月意”。
可是他毫不动心,潘金莲百般勾引,武松“不凭么理会”,石秀对于“暗里教君骨髓枯的”的巧云也不理会其“风话”,并且后来还替杨雄杀了巧云的情人,那潘金莲,巧云都是别人的妻子,英雄好汉自然不可动丝毫念头,最经得起考验的要数浪子燕青,李师师并非他人之妻,只是名妓,且与燕青才艺相当,情趣相投,在燕青眼中,李师师色胜“桂宫仙姐”,然他毫不动情,李师师用话“嘲惹”燕青,燕青却是“好汉胸襟”不敢承惹,李师师一再也“言语来调他”,他逐心生一计,拜李师师为姐姐,作者在此处评论道:
“因此上单是燕青,心如铁石,端的是好男子!
”燕青亦言道:
“大丈夫处世,若为酒色而忘其本,此与禽兽何异!
”似乎对女性动情者便称不上是好男子,若为此情忘了大丈夫应作的根本大事则与禽兽相同,由此可见男女之情的地位是如何之低。
其它古典文学如《西游记》、《三国演义》也都类同,正面英雄好汉都不近女色,非英雄特别是反面人物则都是好色之徒,如孙悟空对女色毫无兴趣,而又馋又懒的八戒却十分好色。
《三国》里正面英雄好汉都无恋情,刘备虽然有“乐不思蜀”的念女色记录,但他视结拜兄弟为手足,妻子为衣服,此等英雄对女性的态度可见一斑。
而“贼臣”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则都被称为好色之徒。
其实,董吕二人对貂婵的痴情倒有几分动人之处。
貂婵不过是假意勾引,二人皆为之大动其情。
李儒劝董卓为江山大业,以婵赐布。
貂婵假称“宁死不屈”,董卓竟为其言所惑,作出宁要美人,不要“心腹猛将”的决定。
那吕布见貂婵挥泪便感“心碎”。
貂婵假意跳池自杀,吕布便抱住她道:
“我今生不能以汝为妻,非英雄也。
”不过作者对这等言行并无赞词。
董吕二人在书中都是作为“死于妇人之手”的反面例子来写的。
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似乎没有将英雄本色与男女之情对立的概念,荷马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描写特洛伊战争,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女色,伊利亚特的王子帕里斯特诱走了希腊阿凯亚族的首领之一墨涅拉奥斯的美貌妻子海伦•阿凯亚人便由墨的哥哥阿加门侬王率领讨伐特洛伊人,史诗一开始,二位主要英雄阿加门侬与阿基琉斯就因女色而发生争执,在一次战争中,阿加门依俘获了奉祀太阳神阿波罗的僧侣的女儿,僧侣请求用赎金赎回女儿,遭到拒绝。
阿加门侬宣称他爱那位年轻姑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