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docx
《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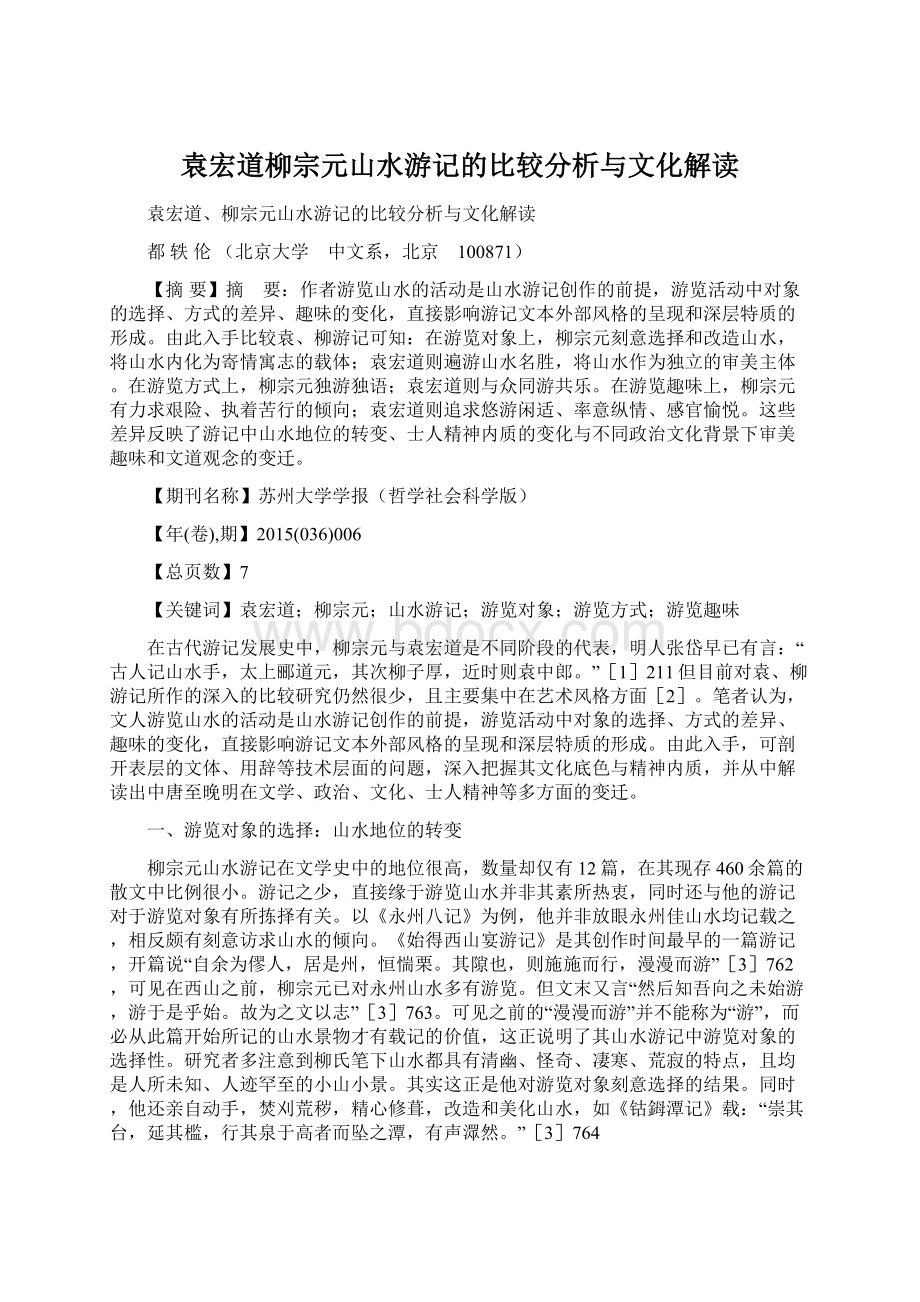
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
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比较分析与文化解读
都轶伦(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摘 要:
作者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游记创作的前提,游览活动中对象的选择、方式的差异、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游记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和深层特质的形成。
由此入手比较袁、柳游记可知:
在游览对象上,柳宗元刻意选择和改造山水,将山水内化为寄情寓志的载体;袁宏道则遍游山水名胜,将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主体。
在游览方式上,柳宗元独游独语;袁宏道则与众同游共乐。
在游览趣味上,柳宗元有力求艰险、执着苦行的倾向;袁宏道则追求悠游闲适、率意纵情、感官愉悦。
这些差异反映了游记中山水地位的转变、士人精神内质的变化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审美趣味和文道观念的变迁。
【期刊名称】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6)006
【总页数】7
【关键词】袁宏道;柳宗元;山水游记;游览对象;游览方式;游览趣味
在古代游记发展史中,柳宗元与袁宏道是不同阶段的代表,明人张岱早已有言:
“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
”[1]211但目前对袁、柳游记所作的深入的比较研究仍然很少,且主要集中在艺术风格方面[2]。
笔者认为,文人游览山水的活动是山水游记创作的前提,游览活动中对象的选择、方式的差异、趣味的变化,直接影响游记文本外部风格的呈现和深层特质的形成。
由此入手,可剖开表层的文体、用辞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深入把握其文化底色与精神内质,并从中解读出中唐至晚明在文学、政治、文化、士人精神等多方面的变迁。
一、游览对象的选择:
山水地位的转变
柳宗元山水游记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很高,数量却仅有12篇,在其现存460余篇的散文中比例很小。
游记之少,直接缘于游览山水并非其素所热衷,同时还与他的游记对于游览对象有所拣择有关。
以《永州八记》为例,他并非放眼永州佳山水均记载之,相反颇有刻意访求山水的倾向。
《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其创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游记,开篇说“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
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3]762,可见在西山之前,柳宗元已对永州山水多有游览。
但文末又言“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故为之文以志”[3]763。
可见之前的“漫漫而游”并不能称为“游”,而必从此篇开始所记的山水景物才有载记的价值,这正说明了其山水游记中游览对象的选择性。
研究者多注意到柳氏笔下山水都具有清幽、怪奇、凄寒、荒寂的特点,且均是人所未知、人迹罕至的小山小景。
其实这正是他对游览对象刻意选择的结果。
同时,他还亲自动手,焚刈荒秽,精心修葺,改造和美化山水,如《钴鉧潭记》载:
“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
”[3]764
《石渠记》载:
“予从州牧得之。
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而盈。
”[3]770均是按照柳宗元本人的审美眼光,对自然景观进行重构。
可见柳氏不仅刻意寻访山水,还刻意改造山水。
与柳氏不同,袁宏道山水游记小品数量很多,现存文集中所收共计86篇,时间跨度纵贯其一生。
可见游览山水在袁宏道人生历程中的地位。
他游记中的游览对象,全然没有柳宗元那样着意拣择的倾向,而皆为其历官宦游或闲居林下时所经所见;也不像柳宗元那样刻意找寻人所未知的小山小景,而多为名山大川。
如他游览江南时所作《虎丘》《西洞庭》《东洞庭》《灵岩》《百花洲》《姑苏台》《游惠山记》《西湖》《孤山》《飞来峰》《灵隐》《龙井》《禹穴》《兰亭记》等,无一不是当地久已闻名、游人趋之若鹜的胜地佳境。
他赴京城后所作《满井游记》《游盘山记》为京郊胜景,而闲居公安时所作《入东林寺记》《云峰寺至天池寺记》《由舍身岩至文殊狮子岩记》《由天池踰含嶓岭至三峡涧记》《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识庐山记后》均为庐山胜景,任职陕西时所作《游骊山记》《华山记》《华山后记》《华山别记》《嵩游》《游苏门山百泉记》亦均为名山大川。
游览对象的特点,体现出袁、柳二人对山水的不同态度。
柳文中的山水已经不是自然形态下的山水,而是按作者主观好恶着意选择和改造的山水。
有研究者认为,柳宗元游记为再现型游记,以描摹和刻画自然山水为主,而自我感受的抒发不占主导地位[4]183。
实则不然。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本质上并非为描摹山水,而是一种隐喻,是其在永州期间复杂心态的隐晦记录。
所以他笔下的山水景色均带有清幽、怪奇、荒寒的特点。
袁宏道则大为不同,他所赏爱的更多是山水本身,所以风格各异的山水风景均为其所欣赏流连、由衷赞叹。
表面上看,柳宗元更多是客观静摹山水,拟人与个性抒发较少;而袁宏道游记的个人情感抒发则大为增加,自我的地位在游记中得到提升[5]。
但从本质上看,柳宗元是将自我隐于山水之间,其笔下摹写的山水就是其自我人格的展现,看似是客观描写,实际上却已经过了人格化的投射。
若就作者对山水的精神内化程度而言,柳宗元是胜于袁宏道的。
游览对象的区别,还反映出山水在游记中地位的转变。
在柳宗元游记中,山水作为作者情感的投射,缺乏独立的地位,实质上只是喻体而非主体。
在袁宏道游记中,山水和作者是平等交流的关系,有其独立地位,而成为游记的主体。
袁宏道在《题陈山人山水卷》中言:
“唯于胸中之浩浩,与其至气之突兀,足与山水敌,故相遇则深相得。
纵终身不遇,而精神未尝不往来也。
”[6]1582直把山水作为与己平等的至交好友。
他在《游高梁桥记》中又言:
“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设色以娱游人。
”[6]682可见山水美景并非专为袁宏道一人,而是以一种独立开放的姿态面对所有游人。
江盈科在《解脱集序》中也说:
“中郎所叙佳山水,并其喜怒动静之性,无不描画如生。
譬之写照,他人貌皮肤,君貌神情。
”[6]1691此语肯定袁宏道笔下山水的人格化特征,而其中所言“貌神情”,是山水自身之神情,而非袁氏本人之神情。
也正因为其笔下的山水有着独立的主体地位,而非作者情感的单向投射,所以袁宏道游记中呈现出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山水形象也就不奇怪了。
更进一步说,柳宗元是为己而游、为己而记,作者本人是其所游景致的主宰者,是发现者和改造者,游览过程是刻意为之的,作者的情感心志是游记的内核;而袁宏道是为游而游、为游而记,作者更多是其所游景致的欣赏者,是旁观者和对话者,游赏过程是自然率性的,对风景的审美愉悦是游记的内核。
山水在游记中地位的转变,又与两者不同的游览动机直接相关。
柳宗元贬谪之前并未措意山水,贬谪后才被迫流连山水,山水只是一种寄托,在游记中也自然无法成为真正的主体。
而袁宏道则是主动游览赏爱山水。
他在《游惠山记》《答陶周望》等篇中均明确直言其山水癖之深,如“意未尝一刻不在宾客山水”“游山若碍道,则吃饭着衣亦碍道矣”等,把游览山水视为生活之必需,与日常吃饭穿衣同等重要,甚至主动辞官而悠游山水。
山水在袁宏道人生中所占据的这种重要地位,促使他重视和欣赏山水本身的美,其游记中山水占据主体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游记中山水地位的转变,并非是袁宏道这一个体的单例,而是有着整个山水游记发展变迁的大背景。
明代中后期开始,对游记的认识较前代有了较大突破,游记小品大量出现,对过去以山水比德,借山水抒幽愤,由山水体悟哲理等写作模式有所改变。
清初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中就指出柳宗元游记“不过借山水一丘一壑,以自写胸中块垒奇崛之思,非游之大观也”[7]1270,而推崇《徐霞客游记》以山水为主
体,对山水进行亲身游历和真实记述。
《徐霞客游记》虽与袁宏道等人的游记小品有很大区别,但同为明代中后期游记的代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与前人不同的更重视游览对象的主体性,对山水在名教道德功利之外的本身的意义和地位加以重新发现和提高。
山水由士大夫借以托情寓志的附庸,转为更纯粹的欣赏和游玩的直接对象。
这或许也是文学和文化开始走向世俗和平民,以及山水从古典情志审美文化走向近现代旅游休闲文化的一种反映。
二、游览方式的差异:
独乐与众乐
柳宗元的游览方式具有鲜明的“独”的特征。
正如他在《江雪》诗中所描摹的“独钓寒江雪”那样,柳宗元的山水游览方式也经常是独来独往,形单影只的。
《永州八记》中,《小石城山记》《石涧记》《石渠记》《袁家渴记》四篇皆仅有柳宗元一人出现,游览兴叹均为其独自一人所为。
其余四篇游记中虽然出现了一二位别的人物,但这些人或者并未参与游览活动,如《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卖地于柳宗元者;或者虽与柳氏同游,却并未真正成为山水游记中的主要人物,也未与柳宗元在游览中发生互动,而只是具列姓名作为实录而已,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的同游者和《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仆人。
因此,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虽偶有他人的存在,本质却是柳宗元一人的独游、独语和独感,是自记游踪、自我抒写的孤寂篇章。
与柳宗元不同,在袁宏道的山水游记中,除他本人以外的其他人物,也占了相当的分量。
袁宏道所游多风景名胜,游人如织的情况是常有的,这在其游览东南苏杭之地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虎丘》[6]157-158一文共分四节,第一节从“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开始,大量篇幅所述均为游人之多,场面之热闹。
第二节更以整节的篇幅,描绘歌者吟唱之声之态,亦备极形容。
此篇以游人、歌者的出行娱乐场景为主,而将作者本人和景物置于次要地位,由喧哗众生构成的世俗场面成了主要的描写对象。
这与柳宗元以本人作为游记唯一的中心人物,以清幽凄静的景色为主要描写对象,恰好相反。
除《虎丘》之外,《荷花荡》一文更是全篇皆述游人游冶之态而不叙荷花荡之风景,直以游人为风景。
《光福》《西湖二》《湖上杂叙》等篇叙述游人情态的篇幅亦复不少。
除了游人之外,友人对游览过程的直接参与和互动,也常是袁宏道游记中的要素,往往占据大量篇幅。
其谓:
“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
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
”[6]506袁宏道眼中三大败兴之事,无友朋相伴占据其二,可见友人在其生活特别是游览活动中的地位。
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篇末仅列同游者姓名作为记录。
袁宏道《上方》则在具列姓名之外,还记录了同游者直接参与游览活动的情况:
“乙末秋杪,曾与小修、江进之登峰看月,藏钩肆谑,令小青奴罚盏,至夜半霜露沾衣,酒力不能胜,始归,归而东方白矣。
”[6]160情致盎然,其乐融融。
类似者还有如《飞来峰》篇末所记“初次与黄道元、方子公同登,单衫短后,直穷莲花峰顶,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6]428。
有些游记还以对话形式将游览过程中作者与友人的互动过程加以生动记录。
如《鉴湖》[6]445《西施山》[6]446二文记录了作者与陶望龄游赏对答之语,《百花洲》[6]178更将作者与江进之的对话作为全文的主要内容。
更有甚者,直以与友人同游之事构建全篇,形成多人游览的场景,如《御教场》[6]435《五泄一》[6]447-448二文。
以上所述袁、柳之异,其实体现出了二人“独乐”与“众乐”之别。
而这种不同的游览方式的取向与前文所论山水在二人游记中地位变化有直接关系。
柳宗元游记中的山水景观世界是他心灵的内化,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自我的,独自欣赏玩味便可,不愿也无法与他人分享,故而不需要他人的参与。
而袁宏道的山水世界则是常人所乐的人间胜境,是开放的、共享的。
人间的烟火气,朋友之间的人情温暖,与在美景中的自适,构成了袁宏道游记中同等重要的审美要素。
这种由“独”到“众”的转变,特别是游人的大量出现,反映出在社会与文化背景的转变中,文人士大夫从独特的个人审美趣味走向寻常的世俗审美趣味,从个人的精神世界走向现实的人情世界的明显变化。
在袁宏道游记中,游人大众带来的喧嚣热闹、众乐和合,友朋知己间的同乐、笑谑,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世俗情调,更是一种太平繁盛的假象,一种人情温暖的寄托。
在众乐之中,袁宏道对现实的忧虑以及精神上的无奈苦痛或可得到缓释。
矢志革新而遭远贬的柳宗元所面对的现实的困境与精神的苦痛深于袁宏道,他游
览山水也时有友朋或仆从相随,但他显然不愿意通过与游伴的对答笑谑来消解现实与内心的双重苦难,而选择在孤寂的自我精神世界中独自面对、消化和承担,这体现出士大夫独立、孤高的精神力量。
相较而言,晚明士人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