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的重读乡贤系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兰台的重读乡贤系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兰台的重读乡贤系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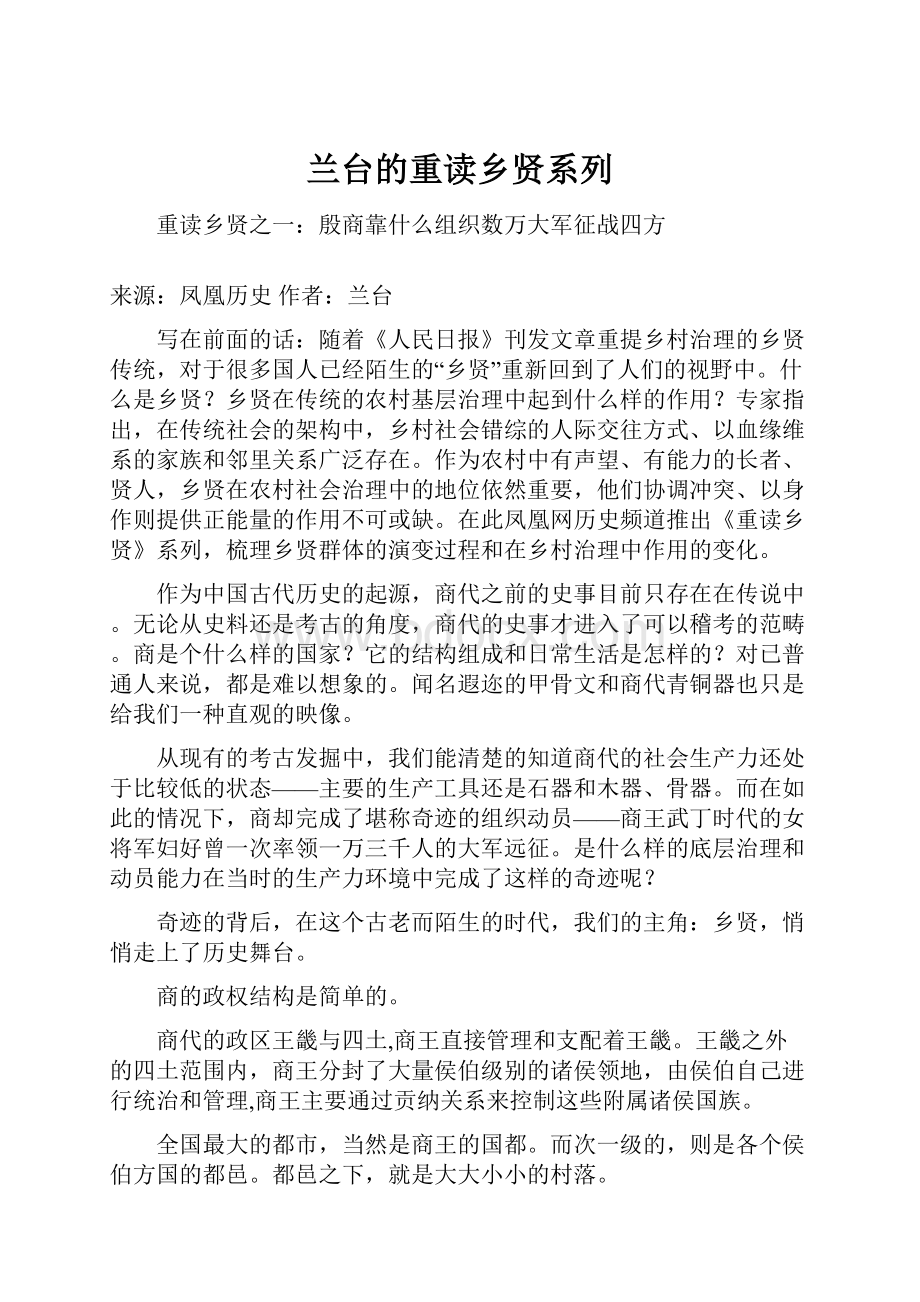
全国最大的都市,当然是商王的国都。
而次一级的,则是各个侯伯方国的都邑。
都邑之下,就是大大小小的村落。
但是,村落之间,却有着有机的组织联系。
商代的村落可以分为两级:
第一级是较大型的村邑。
这类村邑往往有名称,如甲骨文卜辞中提到的“西邑”、“柳邑”、“旅邑”,等等均是;
有围墙与邑门。
在意境发掘的这种大型村邑遗址中,往往有铜器、玉器出土,说明这个大型村落中有贵族阶层的存在。
也有玉器和卜骨的出土,说明该种大型村落中宗教祭祀及其他礼仪也确实存在着。
这种大型村落往往是宗族长所居,又多有祭祀功能,是家族宗庙之所在,所以称为“宗邑”。
第二级是小型村落。
它们没有较大型村邑的特征。
此类村落应当没有自己的祭祀中心,没有宗庙之所在,也缺少或没有权势人物或富有人物,基本上可以视之为只具备生产与生活功能的较为贫困的小村落。
这种小村落中的居民基本没有等级差别,内部所有居民基本上是平等、自主的,他们基本是属于同一血缘关系的小氏族,族人们过着平等、单一的农耕生活,聚族而居、聚族而葬。
简言之,即小村落为平民所居,宗邑则是贵族与平民杂居。
无论是小村落还是宗邑,其基本组织状态都是宗法血缘关系的组合,具体而言,都是聚族而居,一个小村落或一个宗邑是由一个或若干个家族组成。
村邑与宗邑的关系,也就是宗族长所在之家族邑落与其他分支家族之关系。
小村邑是商代社会组织中的最基层单位,各村落之间基本上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村落群中,这些小村邑依附于宗邑,与后者共同组成社会共同体。
以一个宗族的宗族长所在的宗邑为核心,围绕它的数个同族小村落共同组成一个邑落组合,而一个邑落组合就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宗族组合。
在这种宗族组合中,村邑家族只是生产单位,而不是独立的经济、政治、军事单位;
这些村邑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的贫困化,没有财富集中于一室一户的权力人物,也没有祭祀、军事等功能。
宗邑及其所统领的村邑家族则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军事、祭祀单位。
而我们的主角:
乡贤。
就出现在宗邑中。
作为最早的基层治理核心,就出现在这种村邑组合中。
在这里,最早的乡贤就是作为村邑组合核心存在的宗族长。
整个商代基层的邑落体系中,各级宗邑作为基层管理者宗族长的聚集地,在具有亲缘关系的邑落群中,它具有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并建有祖庙社翟之类的庙堂建筑,形成了在宗教上统合全社会的宗教神权。
而宗邑周围的、小村邑,则失去了平等、独立的性格,与宗邑形成了主从依附关系。
而这种主从依附关系的实际执掌者,就是以宗族长身份出现的,中国最早的乡贤。
而商代的地方治理,基本上完全依靠他们而存在。
这与商代的政权结构也有密切关系。
商王及诸侯统治者并不将小村落纳入自己亲自管理的视野。
商王关注的是诸侯的都城及王袭内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等大型聚落。
诸侯首领关注的,上为商王,下为其辖区内的宗邑;
其上效忠商王,为商王纳贡,随商王出征助战,下统御各宗邑,向其征收租赋、劳役。
诸侯首领在保持其辖区内政治稳定的同时,还肩负着保卫各村落安全不受外敌侵犯的职责。
而宗邑则负责了直接管辖、统御其周围的小村邑,在负责向它们征收租赋、劳役的同时,也肩负着保卫其安危不受侵犯、并及时向上通报各种信息的职责。
小村邑即自然村落是这一金字塔式统治体系的最底层,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其上各统治阶层的统治;
其中的居民日常从事农耕和渔猎生产,并负有对上纳贡、服役的义务。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宗族长控制下的宗邑是商统治集团联系基层组织的最重要一环。
作为中介,他是统治集团治理基层村落社会的代表或代言人。
小村邑是村邑群体的基本单位,规模虽小,数量却占绝对多数,明显地构成了群体的社会基础。
在商代,这类村落组合(众邑)内的宗族长,同时又是商奴隶制政权系统中基层行政单位的低级下吏的最早乡贤,在甲骨文中被称为“邑子”,而商代村邑中的居民,甲骨文称为“邑人”以族氏组织相集约。
在宗族长管辖下的村邑群中,尽管社会地位不平等,存在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现实,但大小村落中的居民基本过着规律而有序的、以定居的农耕生产为主、以渔猎为辅的自给自足的日常生活。
虽然他们以定居的农耕生产为主,但渔猎仍是其必要的生产补充手段。
从发现的制陶工具和标准化的陶器来看,还有部分居民从事手工业生产,即制陶手工业生产,所以其生产类型并不同于一般村落中的单纯农业生产。
从居民成分看,大部分是普通劳动者,但宗族长及类似己有身份、地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附有治理基层使命的最初乡贤形成了管理阶层这个阶层中甚至分化出专门从事占卜活动的贞人阶层。
凭借这样的政权结构和动员体系,在商王武丁时代,商王朝已经能动员超过一万人的部队征伐远方。
这在远古时代低下的生产力环境中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而著名的商纣王,能够在军事上多次远征,同时还在国都大兴土木,其人员征发、后勤保障等完全依赖全国的村邑组合在宗族长控制下的供给。
这就是中国乡贤的最原始形态——商代村邑群中的宗族长们。
他们的出现代表着贯穿传统中国的治理基层乡村社会的乡贤正式成型,并在一开始就成为了国家政权在底层的基石。
虽然商代的宗族长们因为缺少材料而显得性格不明,特征也不清晰,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却越发清晰起来。
重读乡贤之二·
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实际是怎样的
引言:
上一期《重读乡贤》我们从最早的商代开始了解最初的乡贤人群。
商代之后就是西周。
西周的制度一直是孔子梦寐以求的对象。
那么这个孔子心中的理想社会,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我们的话题中心“乡贤”在这个社会结构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这一期《重读乡贤》我们来仔细聊一聊。
在武王伐纣,西周代商后,在国家的组织结构上,有明显的制度化改变
究其改变的原因,在于周朝政权的本质。
西周王朝的政治基点是分封制,而分封制的实质又是一种“殖民统治”,是通过少数部族的移民实现对土著多数部族的统治。
为了满足这种通知,周人发明了国野乡遂制度。
《周礼》中把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划分为国与野两个部分。
国包括王城及周边四郊之地,野则是郊之外的区域。
王城之外、四郊之内,设六乡;
此外的野则设六遂,是为国野乡遂之制。
想对应的,卿大夫的采邑称“都鄙”,也在野的范畴之中。
乡和遂的区别既有所处地区的区别,也就是既有国与野的区别,又有居民身份的区别。
在《周礼》中,乡和遂的居民虽然都可以统称为“民”,但是,六遂的居民往往“甿”、“氓”或“野氏”、“野人”,六乡的居民则可以与王城中的居民一道称作“国人”。
诸侯国的乡遂制度应当是一种政治制度。
国野乡遂制度的核心是,新的统治者与原有居民之间是一种政治界限清晰而地域关系交错的空间格局。
凡国人或居于国中,或在国之附近建立聚居点,或者如卿大夫也要被分封到封国中较为僻远之地,无论在何处,其所居除封国所在的城邑之外,均属“乡”的范畴;
而被统治族群,无论是居于原有的城邑还是居于村落,均属“遂”的范畴。
远道而来的周人及其随从的其他人员是这一地域的统治部族,也就是“国人”;
当地居民不论尊卑都是附庸,是被征服者部族,也就是“野人”。
国与野的区分其实并非空间上的里外概念,也不是很多人理解的城乡之别,而是部族概念。
乡与遂的区分也是如此。
为了实现这个制度,受分封者到封地之后,要创建城郭,因为统治及经济、政治生活的需要,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其他附属人员都居于城中或城市附近,随行的国人或居于城中,或居于周边,多数还是以农为业,自成村落。
在国君建国的同时,也分封其卿大夫至特定地区,卿大夫之采邑实际上也是小型城郭,随行的国人也是或居于城中,或居于附近的聚落。
而在在各封国内的被统治部族野人仍保留着原有的城邑与村落的依存关系,他们与新到达的周人征服者的卿大夫族群采取大交错、小聚居的模式同时并存。
从考古所掌握的空间布局资料看,他们并不从属于附近的卿大夫,而是直属于封国。
因此,在西周时代,城乡关系与国野乡遂制度形成了两个交叉概念。
国野乡遂是政治属性概念,区分了政府族群和被政府族群,而城乡只是聚居点的分类与分级概念。
国一般可以等同于城市,野则是由城邑和乡村共同组成;
国之四周的郊、乡区域,一般也是大小不等的乡村村落。
至于分封到各处的卿大夫往往是以采邑为心,统辖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国人”的城乡共同体。
国野乡遂制人为制造了族群的区分,这一区分在经济生活上也深刻体现了出来。
那就是井田制的世纪形式。
《国语·
鲁语下》载孔子曾追述周代制度:
“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
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
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
寡孤疾。
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
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
”
“籍田以力”是说野人之八家共井,“赋里以入”谓国人之“九夫为井”。
“任地事而令贡赋”、“有军旅之出则征之”,当然是指对国人兵役之征发,即“赋里以入”。
“田一井所应上交之“稯禾、秉刍、缶米”,则属于国人之任土作贡,属象征性上贡。
若是野人,其八家共养之公田之上的所有收获物均应悉数上交。
由孔子所述,我们可以略知国人贡赋之大概。
从而还原西周春秋时代井田制的基本状况,也可以大致推测居于其中的乡村居民的基本状况。
土地之分为公田与私田是没有问题的,但公田、私田的区分仅限于野人。
国中的平民当然也主要从事农作,但他们的土地没有公田、私田之分,只是“什一使自赋”而已。
这个“自赋”包括自行承担军役并上交一定的税赋。
国人的土地也是“方里而井”,但因为不须同共养其公田,所以是“九夫为井”。
而且,作为征服者族群,国人有从军的权力。
而野人只有老实服役的义务。
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分野,明晰一至于斯。
这是商周嬗代造成的明确的基层组织变化。
但是,商周嬗代也有另一面,在嬗代过程中,基层乡村的形态其实并未受到太大的破坏,而是保持了较强的连续性,关于这一时期聚落考古调查的结果已证明了这一点。
因而,殷商时代的乡村宗族形态自然会得以延续与发展。
论延续和发展表现在,西周春秋时代的乡村形态与殷商一脉相承,只是在宗法血缘体系、管理体系以及物质生产水平上有所提高而已,城邑与乡村、血缘与地缘以及乡村中的家庭与家族都处于同一个连续发展的体系之中。
作为征服者族群,在西周分封的过程中,被分封者是举族而往,抵达之后建都立国,其基本维系是宗法血缘关系,自国君至于士以至于同族中的庶人应当同处于一个宗法血缘关系体系之中。
而遂之中的士之下的庶民是农业生产的基本承担者,也是城邑之外的普通村落的基本居民组成。
无论国中还是野中的村落,都在宗法血缘关系的笼罩之下,宗族是最为基本的社会组织。
宗族是基本的生产单元与社会活动单元,从生产的组织到具体劳作直至基层社会组织的构建,都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生相聚,死相从,是此期宗族的基本特色。
这就使我们的主角最初的“乡贤”宗族长们,在这个体制中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从社会生产与经济活动的组织看,无论是公田、私田,还是国中庶民的土地,都是以宗族为单位
的集体耕作。
因此,宗族长对于宗族农耕活动的安排和控制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好坏。
从祭祀与其他社会活动看,主要也是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的。
对于庶民之祭祀活动,多限止于其祖。
祭祀的家族性是由其祭祖特性决定的。
西周乡村居民的最大特征是“死徙无出乡”,同祖子孙聚居为族,因而祭祖就是族祭。
宗族长对于祭祀的掌握,也成为团结凝聚整个宗族的契机。
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之以农业为主体的凝固而内向的经济结构,乡村人口乃至城邑
人口都是“死徙无出乡”,流动性极小,即使统治者以规范的行政编制管理其臣民,行政编制之中所蕴含的也不仅是地缘关系,而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主体的组织关系。
宗族长从而成为政权掌握底层民众的行政体系中最基层的一员。
这就是周代“乡贤”的作用。
但是,也必须看到。
因为国野乡遂制造成的族群区分,虽然同为宗族长,但国人乡贤与野人乡贤在权利与义务上却是完全不对等的。
作为国人的宗族长握有征服者从军控制武力的权利,国人乡贤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更多地享有政治权利。
而作为被征服者的野人乡贤,没有多少政治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在公田上服役。
周代的乡村结构是商周时期乡村社会的最终定型,也是孔子心中标准的理想模式。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马上就要走进春秋战的动荡时代,这种秩序井然的理想模式最终会被时代的洪流荡涤瓦解。
而已宗族长身份出现的最早的乡贤,也会在这个大时代中变换出新的面目
重读乡贤之三:
秦国怎样打造横扫天下的虎狼之军
上一期的《重读乡贤》中,我们研究了西周经典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作为最初乡贤的宗族长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而随着时间的退役,西周的经典社会面临着一场天崩地裂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秦国的虎狼之师统一了天下。
那么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社会的结构发生的怎样的变化?
我们的主角乡贤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期《重读乡贤》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时期。
春秋战国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的一套规则已完全失去了效用,周天子被完全抛在一边,诸侯之间会盟、朝聘不再,大国小国间的争霸、灭国战争此起彼伏。
政治上的沧海桑田,自然会波及到基层社会的结构和治理。
变化最明显的是战争。
在西周到春秋早期,战争是一种贵族化的行为,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国家大事,唯祀与戎”。
“野人”与奴隶是没有相关权利的。
他们即使参与战斗,也不是作为战斗人员而出现,而是担任扈从以及与战争相关的杂务。
战争方式也是以车战为主的艺术化战争,双方在开阔地带列开阵势,有兵法而无诡计,甚至有一套看起来比较可笑的规则。
一直被后人嘲笑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宋襄公,实际正是恪守这些规则的。
但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方式逐渐转向残酷和杀戮。
战争场面日趋惨烈,为了在兼并战争中胜出,各国不仅以战胜敌人为目的,而且试图在战争中大量杀灭敌国有生力量。
在新的战争目的下,激励军队的士气,从而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就成为首要选择。
“首功”成为计算军功的新方式,凭借军功,兵士不仅可以获得田宅,还能得到象征身份与社会地位的爵位。
在大规模战争和“首功”记功方式的推动下,由军功起家的农民开始成为社会新贵,旧贵族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了。
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战国主要的战争形式是野战和攻城战,先是步兵,后来还出现了骑兵。
步兵的装备低廉,可以大量征召,农民就逐渐成为军队主体。
为了证照动员更多的人力参与战争以获得充沛的兵源,战国各国都相继进行变法改革。
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了更加广泛而深刻的政治经济改革,这次改革的矛头所指之一就是井田制度,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国野制度。
“废井田,开阡陌”、打击宗法贵族、奖励军功等一系列措施,为“野人”改变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机遇,从而彻底铲除了国与野、国人与野人之间的界限,四业之民杂居共处,编户齐民成为新社会制度的群众基础,相应地,西周严密分明的针对国人和野人而设的“国野乡遂”两套行政系也统渐趋统一。
另一个方向就是将宗族解体。
在西周的模式下,基层聚落实际以聚族而居的形式存在。
一个个宗族构成了社会的基层结构。
而一个个宗族长就是我们最初的乡贤。
在这个结构下,农民个体都被宗族有机组织起来。
对于觊觎扩大征发和动员人力参与战争的国家来说,要想顺利地榨取民间人力资源,必须打散宗族组织,使农民个体原子化,这样才能被国家有效控制的动员,成为战争机器零件的不尽来源。
商鞅变法中就明确规定废除大家庭的存在,一家如果有二男以上必须分家,否则要被罚以双倍的赋,“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宗族逐渐解体。
宗族解体,意味着宗族过去庇护依附民的功能丧失,自由民随之而大量出现。
自由民的来源,一是贵族降为皂隶者,
另一个来源就是原来依附于贵族的庶民。
对自由民的统治方式就成为各国面对的问题。
这个时候,国家不再是一些血缘部族的简单组合,而是直面于广大民众的统治机构,它能够最大限度的集中国力,使之能够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成为第一个霸政权力中心。
为了集中国力,各国千方百计加强户籍管理,直接控制人口。
井田制废除以后,国家开始倾向于向农民授田,即孟子所说的“一夫百亩”,这些农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被政府以什、伍的方式组织起来编为户籍,作为征发税役的凭据。
在“足食、足兵”要求的推动下,各国都加强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
在编户齐民中采取什伍连坐制。
什伍连坐既是一种监督制度也是一种居民编制,“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商鞅变法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行“什伍连坐”之制,加强国家对人民的统治。
与之相应政府的控制对象也由土地向人倾斜,而以人丁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也开始出现,户籍与地簿也分别而立,后世所通行的新户籍制度出现了。
相应地,与之适应的社会基层组织——乡里组织应运而生。
乡里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加强国君对地方的控制。
商鞅变法,合小乡聚邑以为县,将秦国分为国君直接统辖的四十一县,县以下设乡、里,再辅之以作为治安监察机构的亭,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控制体系。
与此同步进行的还有人口的统计和户籍的编订,整个社会被严密地组织起来,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整合得以实现。
这就是郡县制的成熟。
随着郡县制的成熟,中央集权和强干弱枝成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强大的君主政权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基层社会进行整合,控制基层的人力、物力资源才是国家进行基层管理的直接目的,但是利用郡县直接管理广阔的基层社会也是不太现实的,郡、县只是国家控制基层社会的过渡机构。
于是国家在县以下,将政权范围内的各种聚落体按人口的多寡和地域的大小划分为更小的行政区划——乡,乡以下再设里,将人民用户籍的方式管理起来,形成一张严密的行政网络。
而亭也以新的面貌作为乡里之间的一种特殊机构而出现,乡、亭、里制最终形成了。
战国后期,各诸侯大国基层居民单位的里中,普遍设有低级里吏身份的伍长、什长,有的国家可能只设有伍长而没有什长,因为各国的具体里吏设置会不尽相同。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战国时期各国管理社会基层的制度设计十分接近。
齐国实行的是兵农合一制度,北方其他几个强国从其拥有数量庞大的兵员动员能力推测,国家的管理体制与齐国当相近。
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把整个国家纳入军事化管理体制。
而将国家的统治贯彻至位于末端单位正是居民单位“里”。
随着里的基层政权化逐步加强,里中职事增多,战国后期新增设了里监门、里佐、田典三种里吏。
级别比伍长、什长高,职责较伍长、什长更重要。
正是在国家如此严密的控制之下,才有可能动员起如此巨大的人力资源投入战争。
也正是这种国家强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组织,将每个人和家庭原子化后再重新进行编排控制的体制,才打造出了统一天下的秦国虎狼之师。
我们注意到,这里,作为国家治理社会的最基层单位,伍长、什长也好,里监门、里佐也好都是从国家的角度设置来控制和管理乡里的。
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底层的控制。
而相应的,作为民间自发权力的代表,最原始的乡贤宗族长随着宗族的解体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在国家强力控制基层指导每个个人的郡县乡里体制下,还有乡贤存在的空间吗?
答案是存在的。
国家从上到下的强力控制也不能填满底层个人的全部生活。
乡贤的空间虽然被秦帝国体系的从上而下控制压缩到了极致,但依然存在。
在郡县乡里体制下,他们被称为“父老”。
“父老”是闾里老人,道德品质好,长事于人,受到闾里民众的尊重,凡是符合这一基本特征的老人,都属于“父老”。
乡贤“父老”的存在空间何在?
那是因为国家政权和每一编户民通过各级政权形成对应关系,编户齐民以原子化的个人独立存在,编户之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互相之间也没有法理意义上的责任和义务。
但当编户生产生活上出现实际困难时,仅靠国家层面的救助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自发性邻里自治的重要作用便凸显出来了。
自发性邻里自治的存在,就是“父老”的存在空间。
他们正是作为自发性邻里自治的实际操作者存在的。
邻里经济自治,在编户民无法维持基本生存时得到富裕民户的借贷或者无偿救济,在最低限度上保证了个人家庭的存在和延续。
收养孤弱,其意义更为重要。
足够的人口是国家强大的前提,而较为富裕的编户收养婴幼儿,把他们抚养成人,这无论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国家利益层面上讲,都是极端重要的。
并且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排解邻里之间的矛盾,避免了因头脑发热,一时想不开而可能引发的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从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里部秩序,就是促进了国家的稳定。
这就是香艳在秦制度下生存的空间。
虽然这种自发性邻里自治与秦帝国模式下对底层个人的直接控制有矛盾,但这一作用也使得国家权力无法忽视其作用。
乡贤,在战果走向秦帝国的巨大动荡和秦帝国组织结构的高压之下,依旧在夹缝中生长着,并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读乡贤之四:
西汉从秦的灭亡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上一期《重读乡贤》中我们提到,战果各国运用国家强力粉碎了原有的宗族组织,将每个人和家庭原子化后再重新进行编排控制,最终诞生了统一天下的秦国虎狼之师。
但秦国却很快二世而亡。
一般都认为这是因为秦国虐用民力,残酷剥削,激起民变导致亡国。
但问题是,实际上,紧接秦朝建立的汉朝,其赋役之残酷沉重,与秦相比不遑多让,为何能长治久安?
西汉究竟从秦朝的灭亡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这一期《重读乡贤》我们就来谈一谈。
秦汉的基层统治,首要任务是进行户籍、田籍的登记与管理。
秦汉的赋税即是按照土地和人口征收的,户口、田数准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国家税役摊派的重大问题,故而对于基层政府来说,核实户口和田数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登记之后,就是进行赋税和徭役的摊派。
秦汉赋税繁苛,政府向农民征收的赋税主要有按户籍征收的算赋、口赋、户赋和按田籍征收的田租、刍藁税等,前者以人丁和财产为主要征收标准,后者则是按照土地数量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
汉代基本沿袭了秦代的征收方式和数额。
算赋和口赋是按照人口缴纳的税种。
除了按照人口征收以外,还有针对商人而设的算缗,即向车、船、货物等征收算赋。
除了税收还有劳役。
秦代兵役徭役繁重,已经不能用《汉书·
食货志》所称商鞅所定的数额来形容了,《食货志》云:
“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秦帝国的徭役和兵役征发无度直接导致了其崩溃。
汉代也基本继承了秦代的兵役、徭役制度。
上期《重读乡贤》也提到,战国开始,政府都致力于创建以小农家庭为主的基层社会,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秦汉社会的家庭一般是五口之家。
这样的小家庭型社会有利于政府管理,却十分脆弱。
战国时的李悝就指出:
一个供养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