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汲取叫做永恒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有一种汲取叫做永恒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有一种汲取叫做永恒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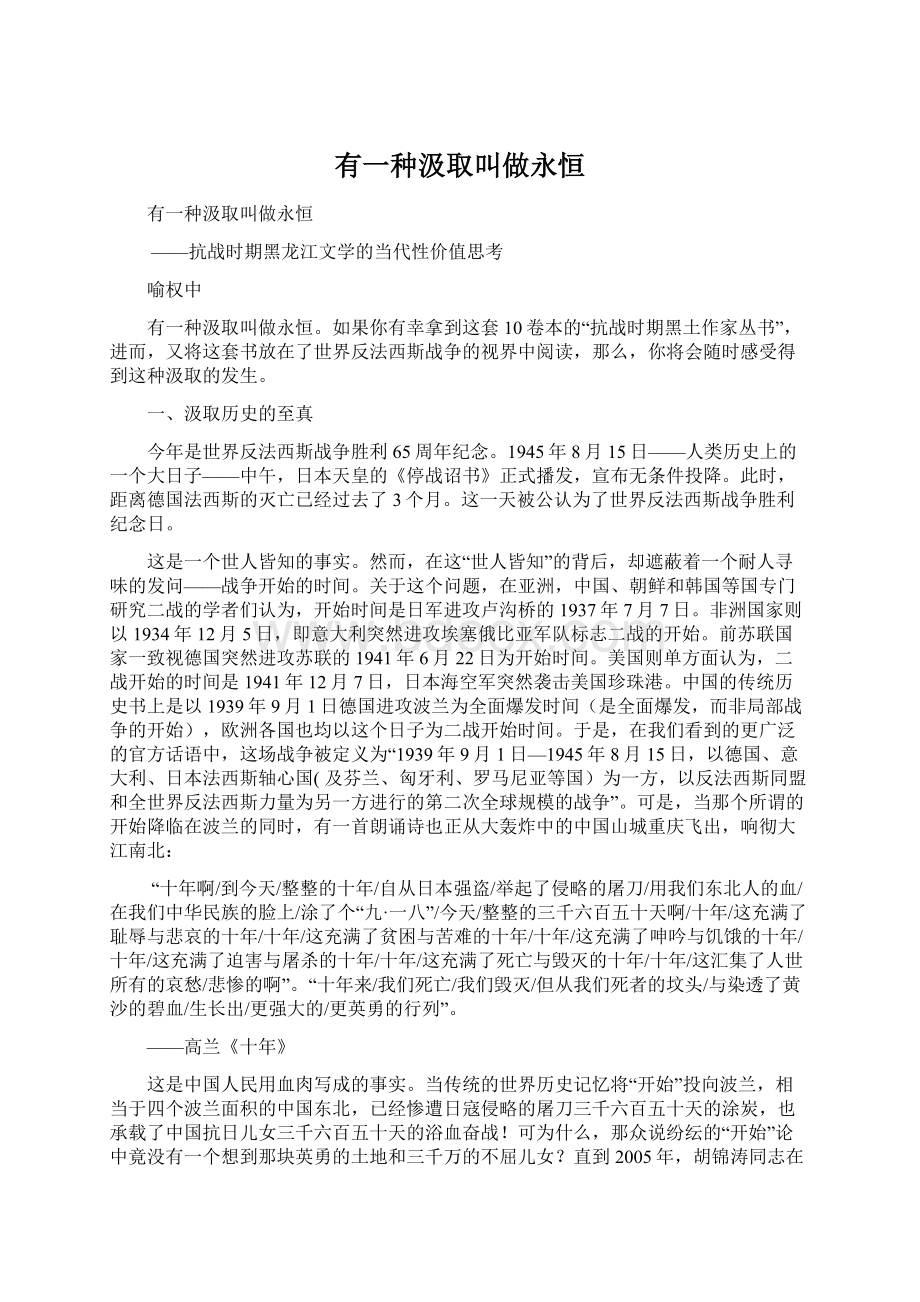
当传统的世界历史记忆将“开始”投向波兰,相当于四个波兰面积的中国东北,已经惨遭日寇侵略的屠刀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涂炭,也承载了中国抗日儿女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浴血奋战!
可为什么,那众说纷纭的“开始”论中竟没有一个想到那块英勇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不屈儿女?
直到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宣布:
“1931年‘九·
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这段10年的抗战史才算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
据说,听到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时年82岁的抗联老战士李敏,徒步来到当年抗联的密营,涕泗滂沱,呼唤着当年战友的名字说:
你们听到了么,历史没有忘记你们!
请记住:
1941年,当传统的“开始”论中的前苏联和美国还在和平里熟睡,黑龙江这块热土上,被胡锦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的头一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已经殉国一整年;
“杰出代表”中的群体,“八女投江”的英雄们,已经为国捐躯3年;
另一位“杰出代表”,永远的民族英雄赵一曼女士,则更是壮烈牺牲了5年有余!
这就是“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力图展现的历史真实——在白山黑水间,一群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中华民族14年的抗战史的发端,撕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与此相关联,“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也以对一直坚守在沦陷区的抗战作家们致敬的行为,再次提请人们关注那段曾经被忽视的历史。
1936年8月15日,以笔为枪的金剑啸烈士,因在哈尔滨从事不屈不挠的抗日宣传斗争,被鬼子残忍地杀害在齐齐哈尔,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年仅26岁的青春生命!
1936年,也是“东北作家群”正式步入中国政治史与文学史舞台的标志性年月。
生活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不顾当局的严密控制,收集当时影响最为显著的东北作家的一批短篇小说,计有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战地》、李辉英的《参事官下乡》、黑丁的《九月的沈阳》、穆木天的《江村之夜》、白朗的《沦落前后》、宇飞的《土龙山》和陈凝秋的《在路线上》等八篇,出版单行本。
因为当时文学界已经普遍地称他们为东北作家,因此这个单行本就取名《东北作家近集》。
当然,由于这本书的畅销,东北作家这一称谓也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熟知。
遗憾的是,同抗战史长久地忽略了东北本土抗战一样,“东北作家群”一直被定义为“‘九·
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而将东北沦陷区坚守中的作家排斥在了其外。
历史的真相是:
1936年8月16日,金剑啸在东北被日寇杀害的噩耗传到上海,舒群、罗烽、白朗、姜椿芳、塞克、金人、萧红、萧军等为之震惊义愤,大家商定,力争次年8月金剑啸殉难一周年,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即由白朗、金人主编,作为“夜哨丛书”之一出版的《兴安岭的风雪》。
这部长诗收录了金剑啸生前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附录还收录了萧红的《一粒土泥》、姜椿芳的《金剑啸》、白朗的《遗憾,留给了我们》、舒群的《死讽》及罗烽、金人、萧军、林环、高潮、夏懿等人的作品。
这件事情说明,传统认识中的“东北作家群”不仅一直将在沦陷区坚守的抗战作家视为同事战友,更将金剑啸奉为了自己的先驱。
45年后,历史的被误读才第一次得到正视:
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剑啸诗文集》,内容有反映东北抗联战斗生活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小说《云姑的母亲》、《夏娃的四个儿子》、《瘦骨头》、《王二之死》、剧本《海风》、《黄昏》、《母与子》、《车中》、《幽灵》,散文《企望》、《致词》以及漫画、连环画等。
直到此时,金剑啸烈士才有了自己的作品结集。
今天,又一个卅年之后,“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的出版,第一次让传统认识中的“东北作家群”与在沦陷区坚守的作家们,在“抗战”的旗帜下拥抱在了一起。
在收集得更加齐全的金剑啸文集背后,还波澜着关沫南、支援等一整条有待历史重新阅读与认同的文学长河!
而我有幸,由此较早地领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中国黑土抗战文学篇的感人至深。
汲取历史的至真,仅此,“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便具备了传世的理由。
二、汲取救赎的至爱
2010年,不止有人在关注历史,也有人力图展示未来。
2010年3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说世界大趋势》。
被称为“公司治理方面的世界顶级专家”的郎咸平,在书中“外围就是中心”一节中传达的思想,与“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的精神不期而遇。
郎咸平的目光犀利地扫向了黑龙江的腹地哈尔滨,预言“这一城市复兴潮流的领导者之一就是北方的老工业城市哈尔滨。
2005年,哈尔滨因为上游320公里处一家化工厂爆炸污染了水源而引发了媒体的密切关注。
但这并没有延缓这个中国最伟大的城市规划。
哈尔滨正在松花江对岸建造一座可容纳900万人口的新城。
”着眼於未来,使郎咸平独具慧眼地指出:
“在现在的中国,用‘外围就是中心’来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
”
对未来的信仰与热爱,从黑土抗战作家起,就构筑起了一种文化呈现与生命叙事上的魅力所在。
我有一个朋友,20世纪70年代初,由师范学校毕业当了哈尔滨城市里的一名中学教师。
有一天,他突然放弃刚刚评上的先进教师名誉,和方见成效的事业,义无反顾的去了黑龙江的边陲小镇黑河。
不光是亲友们,连当时市人事局办手续的工作人员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再无二人的行为被我的朋友称之为“我有迷魂招不得”,迷就迷在他当时读到了高兰抗战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
七月,长途客车驶下小兴安岭,停靠在终点站黑河镇,站在王肃大街上,我的朋友情不自禁地吟诵着高兰的诗,让高兰对家乡的激情与江风一起陶冶自己的心胸:
七月里的天空多么晴朗!
漠河去淘金,
鹤岗去挖矿,
兴安岭的深林啊!
一钻进去就是百里不见太阳!
一根根的砍下去,
一根根的捆绑上,
扎成了排木便顺流而放,
顺着呼兰河,
顺着嫩江,
一直流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意犹未尽,那个朋友又连写了四篇短文,在《黑河日报》上连载,介绍高兰的朗诵诗,感叹高兰对家乡的热爱产生出的感染力。
后来,由于工作的变故,这位朋友离开了深爱的黑河。
然而,高兰诗歌的萦绕,却令他愈来愈关注黑龙江的地域文化。
35年过去了,有高兰朗诵诗的护佑,我的那个朋友已经成长为了省级重点学科“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学科带头人。
爱,曾是一个早被使用得泛滥的词句,但当“爱”字的前端被加上“最后的”、“失去的”、“被怀念的”、“被希望的”文化背景与词语后,所有的人性魅力便会再次神奇地从这一词语中喷射而出。
而抗战时期的黑龙江,恰恰聚集了上述的全部文化语境。
少年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地为都德的《最后的一课》热泪盈眶;
那时,还没有机会读到赵一曼女士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
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加入少先队的我,在东北烈士馆的墙壁上与这一遗书不期而遇,一瞬间,灵魂似乎被爱的火焰焚成了舍利: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
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短短数语用生命写就的手书,却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爱的语言。
从此,那个风雪交加的下午成为了我生命的救赎日。
多少个人生的关键路口,我都能听到一个母亲的声音在风雪中飞扬:
“宁儿,希望你……”。
多少年后,我读到了又一代黑龙江诗人李琦的咏菊诗“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李琦《白菊》1996年夏)我才领悟到赵一曼遗书所代表的黑龙江抗战文学精神是怎样被至爱所充盈着。
塑造了大雪意像的李琦诗歌、以《赵一曼女士》命名的阿成的小说,众望所归相继夺得鲁迅文学大奖,谁能不承认他们得恩惠于赵一曼遗书所代表的黑龙江抗战文学精神呢?
在博客上,无意中搜索到根据当年日军特高科高级探员佐藤(当时的刑讯记录员)撰写的《对赵一曼女士的审讯记录》整理。
作者以第一人称记录了事件经过,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位活生生的女英雄形象。
其中,太多惨绝人寰的刑讯过程与细节,已经远远超过了经典的江姐受刑记叙。
这种惨绝人寰下的坚贞,与手写遗书的隽美和那声“宁儿”的呼唤,一起在为中国黑土抗战文学的不朽诠释着。
限于篇幅,抗战时期黑土文学丛书未来得及收录赵一曼的遗书,以及李兆麟、于天放、陈雷那与日月长存的《露营歌》: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兴安岭的风雪》、《吊“天照应”》等诗文中,感受到同样意义的超越生死的至爱。
《兴安岭的风雪》,金剑啸的与赵一曼遗书同年问世的长诗。
诗歌再现了32名抗联健儿在白雪皑皑的兴安岭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敌人优势的兵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壮举,在作者笔下,这一切都最终化为了充满了“热和爱”的“娓娓动听的歌声”:
“在天上落着雪花的时候/我遇到一种/娓娓动听的歌声/歌声里有着血、热和爱/在空中飘动着太阳的彩带。
”《兴安岭的风雪》因为这救赎的至爱而不朽。
正如萧红听闻金剑啸惨遭日冠杀害时所作的诗歌《一粒土泥》中预言的:
“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了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要记起,亡友剑啸,/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
转年,1937年10月,高兰先生怀着沉痛又悲愤的心情写了《吊“天照应”》一诗。
此诗是悼念驰骋于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中国的夏伯阳——天照应将军!
”。
天照应将军本名张振武,字“天照应”,是高兰大学毕业后,在北平义勇军指挥部秘书处工作期间结识的一位东北义勇军将领。
在鲁迅先生周年祭时,从哈尔滨赶来的杨朔,向高兰讲述了这位东北义勇军将领为国殉难的动人事迹。
高兰愤然写出了报告文学《记天照应》和诗歌《吊“天照应”》。
《吊“天照应”》的开头写道:
“我希望这是个梦/虽然梦也梦得太凄凉/天照应/你传奇一般的英雄/你中国的夏伯阳/你为了我们民族的解放/壮烈地死亡/六年来/你一天也没有忘记/为祖国,为奴隶们/你的战马/踏遍了东北/你的刀锋/指着敌人的胸膛......”这首诗的结尾,高兰写道:
“借秋风吹向故乡/告诉你/今后不再是孤军抵抗/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都拿走了他的刀枪/我们将相会于一个战场/胜利和光明就在我们的头上/天照应!
你中国的夏伯阳”。
至爱,将为国殉难的悼歌酿成了坚信未来“胜利和光明”的交响曲。
而舒群的名篇《没有祖国的孩子》、萧红的《生死场》等,更是以对故乡那深入骨髓的热爱而家喻户晓,世代传颂。
从1931年“九·
一八”到1945年“八·
一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其中,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
而这一切,竟是从中国的白山黑水承受一切苦难开始,又最终以日本关东军在白山黑水间的彻底覆灭为标志,宣告终结。
记载了这场伟大的救赎的抗战时期黑土文学丛书,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再现那段传奇般的历史,更可以使人们接收到:
救赎的至爱播撒下的“精神的大雪”般的洗礼!
三、汲取越轨的至美
10卷本的“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铺展开在我的面前,走过来的是“五·
四”新文学方阵中最年轻的一支:
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金剑啸、高兰、塞克、孔罗荪、关沫南。
20世纪30年代,当命运让这支未来的黑土抗战作家们齐聚松花江畔,先后开始新文学创作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塞克,1928年出版诗集《追寻》时,也只有22岁;
转年,萧军脱颖而出,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在当年5月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又刚好22岁。
而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关沫南,1936年推出小说《醉妇》时,尚未满17岁;
至于孔罗荪,1928年发表处女作时,应该才16岁出头。
多么年轻的行列,然而,在那个每天都涤旧扬新的年月,他们年轻的肩头也早已肩起了各种生活的磨砺。
其中,舒群、塞克、高兰先后投身过抗日义勇军;
金剑啸、罗烽则早早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而有着讲武堂经历的萧军、逃婚流浪而来的萧红,又携来了中国沦陷区城市底层体验和家园记忆的怅惘。
年轻,让他们不惮于传统;
年轻,同时赋予了他们开拓生活的资本与空间。
于是,当面对这样的年轻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对萧红个人的评价做一延伸。
1935年,鲁迅在《萧红作<
生死场>
序》中写道“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强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鲁迅是写给萧红的,但当时整个黑龙江抗战作家,用上“越轨”二字评价也很妥帖。
因为在表现北方人民的生活与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上,黑土抗战作家群体的创作为当时的文学界别开了生面。
如周立波先生在1936年末发表的题为《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回顾——丰饶的一年间》中所言:
“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深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的文学的一般的水准。
的确,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坛被关注的还只有“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学派别。
大体说来,“海派”是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城市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畸形繁荣的产物。
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又感染着都市“文明病”。
正是对都市文明既留念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境,使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派艺术,有着较为自觉的先锋意识,追求艺术的“变”与“新”。
而以北京等北方城市为中心的“京派”是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也即非职业化的作家。
他们一面陶醉于传统文化的精美博大,又置身于自由、散漫的校园文化氛围之中,天然地追求文学(学术)的独立与自由,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
这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
至于“左翼”作家,则自觉以现代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对封建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同时展开批判,要求文学更自觉地成为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
只是“左翼”文学的初期,“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流行一时,蒋光慈的《短裤党》、《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在初期革命小说中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
三大文学派别(潮流)创造了不同的文学景观,但又统一生存于3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因而在整体文学的张力场上又显示出某些共同的趋向。
然而,他们却都还没来得及去展示反法西斯战争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张,要到1936年6月才由胡风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中第一次提出;
“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就更要晚到42年的“讲话”时才出现。
而得天独厚的黑土抗战文学群体,却因为独特的生活际遇,较早地触摸到了中国社会最伤痛的一面。
譬如萧军,东北作家中的标志性人物,1935年便以《八月的乡村》震惊中国文坛,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以其特异的风貌出现于上海文坛的宣言式的作品”。
而同时的舒群小说创作,在主题囊括之广,思想开掘之深,结构艺术上孜孜的探索和追求等方面,与同时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相比,确实够得上“越轨”的评价。
至于高兰,以其“越轨“的才情开创了一个抗战朗诵诗时代,《我的家在黑龙江》和《哭亡女苏菲》等思想与艺术俱佳的名篇佳作,不仅代表个人创作的艺术高峰,同时,也扩大和提升了朗诵诗歌这一体裁的表现功能和审美质地,以至于高兰诗歌成为了中国抗战朗诵诗的代名词。
当然,时至今日还能让人享受到“越轨”的至美的,非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的萧红莫属。
她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
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她在最早的小说之一《看风筝》中,就已经把无产阶级献身大众的意识融入到小说人物刘成身上,“为的是把整个的心,整个的身体献给众人”,“一切受难者的父亲他都当作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
收入丛书中的萧红代表作之一《生死场》,其“越轨”的至美是双重的。
首先,《生死场》突破了一般左翼小说只注重单一表现“抗日救国”的主题的局限,多层面地展示出自己故乡的农民,在自然灾害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下,“挣扎着生死的生活,并展示了他们从‘蚊子似地为死而生’到‘巨人似地为生而死’的过程。
因此,它的主题是多义的。
它超越了作品所写的表层范围,成了走向反抗之前的中国人的人生概括。
这种超越,是小说的主题升华到哲理的高度。
”其次,《生死场》以风俗画卷的写法谋篇布局,极具个性的语言和散文化的结构艺术,颠覆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促进新文学文体创新方面做出了扎实的贡献”。
萧红的写景,惯于在皴染与铺排中去彰显自然的气质与性格,在其中投入“厚重的生命体验和深沉的情感寄托,使这些描写景、物、人的景语,更是情语”。
萧红的叙事,则全然一副“拼命三郎”的力度。
其现场描摹的真切大胆,令人心魄为之震颤;
及至人物命运的集中描绘,更是不惜中断情节的发展,使读者无法不深陷于人物的命运氛围中。
我以为,萧红小说被称之为具有当代性的,正是这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写景与叙事吧。
自从中国20世纪50年代普及小学教育以来,所有读过了小学四年级的中国人,其实都早已被“越轨”的至美陶冶过。
就是那篇几乎家喻户晓的课文《火烧云》: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爷爷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
“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
“你老人家必要高寿,你老是金胡子了。
”
……
多少年后我才得知,这美仑美奂的文字,就出自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
新鲜而生疏、直率而自然的性情文字,这个当代性的内在标志,其实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注入了当代中国人的血脉中的。
许广平曾说过,《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
(许广平《追忆萧红》)其实,这种“新奇与惊动”还在时时刻刻地生发着。
例如,当你读到:
太阳的光线渐渐从高空忧郁下来
阴湿的气息在田间到处撩走,早晨和晚上都是一样,田间憔悴起来。
——《生死场》
或者:
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
一张叶子落到王婆的头上,叶子是安静的伏贴在那里。
王婆驱著她的老马,头上顶著飘落的黄叶;
老马,老人,配著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
你就会觉得有一句话很适合萧红: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
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
”萧红就是在故事的花架之外,用“新奇与惊动”、用“越轨”的至美,为这世界“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诗意的栖居”。
同样,你不能忽略了白朗。
她的短篇小说《伊瓦鲁河畔》、《轮下》、《生与死》以及散文《探望》均有很鲜明的艺术特色。
《轮下》,一篇带有报告文学特点的纪实性小说,为中国当代纪实文学立传的请记住,这一文体的“越轨”,就源自白朗。
《轮下》以1932年秋哈尔滨大水灾为背景,表现了难民与日伪反动当局的斗争。
情节中有难民代表被宪警推进囚车,他的老婆抱着孩子横卧在囚车轮下被活活碾死的悲惨场面。
侵略者的残暴统治由此被揭露得淋漓尽致。
以后有学者评价她的这篇作品说:
“笼罩着凄楚沉郁的悲剧气氛,描绘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并且在描写时采用电影蒙太奇的结构手法,把人物对话、动作心理刻划,组合成一组组电影镜头,平行交叉,迭复剪辑在一起,使小说文简流畅,人物个性突出,情节迭宕,节奏明快”。
至于塞克的救亡歌曲、孔罗荪的评论、金剑啸的舞台剧本、罗烽的《满洲的囚徒》、关沫南的《蹉跎》,都各有其“越轨”的艺术表现之所在,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又是一套极具收藏价值的珍本书。
不但尽量收录了10位作家当年的初版作品,而且整理了尽可能完整的作家创作年谱、年谱、提供背景的文集序言。
比如高兰,本卷收入了建国后出版的几部高兰朗诵诗集中未曾收录的包括诗歌、散文等体裁在内的30余篇作品。
又如,丛书所收录的舒群诗歌作品源自舒群1934年出版的诗集《黑人》,这些诗歌未收入《舒群文集》之中,为建国后首次面世。
还有一些资料是作家们的亲属第一次提供,弥足珍贵。
这次有机会完整地弥补上历史的缺憾,也算文坛的一件幸事。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的10位作家,今天都已经走入了历史的白山黑水:
最早的金剑啸,至今殉国74年有余;
最后的关沫南,也已经辞世7个春秋。
然而,当我合上这沉甸甸的文集时,耳边分明响起羽泉的清唱:
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
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我以为,“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2010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