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一Word下载.docx
《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一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一Word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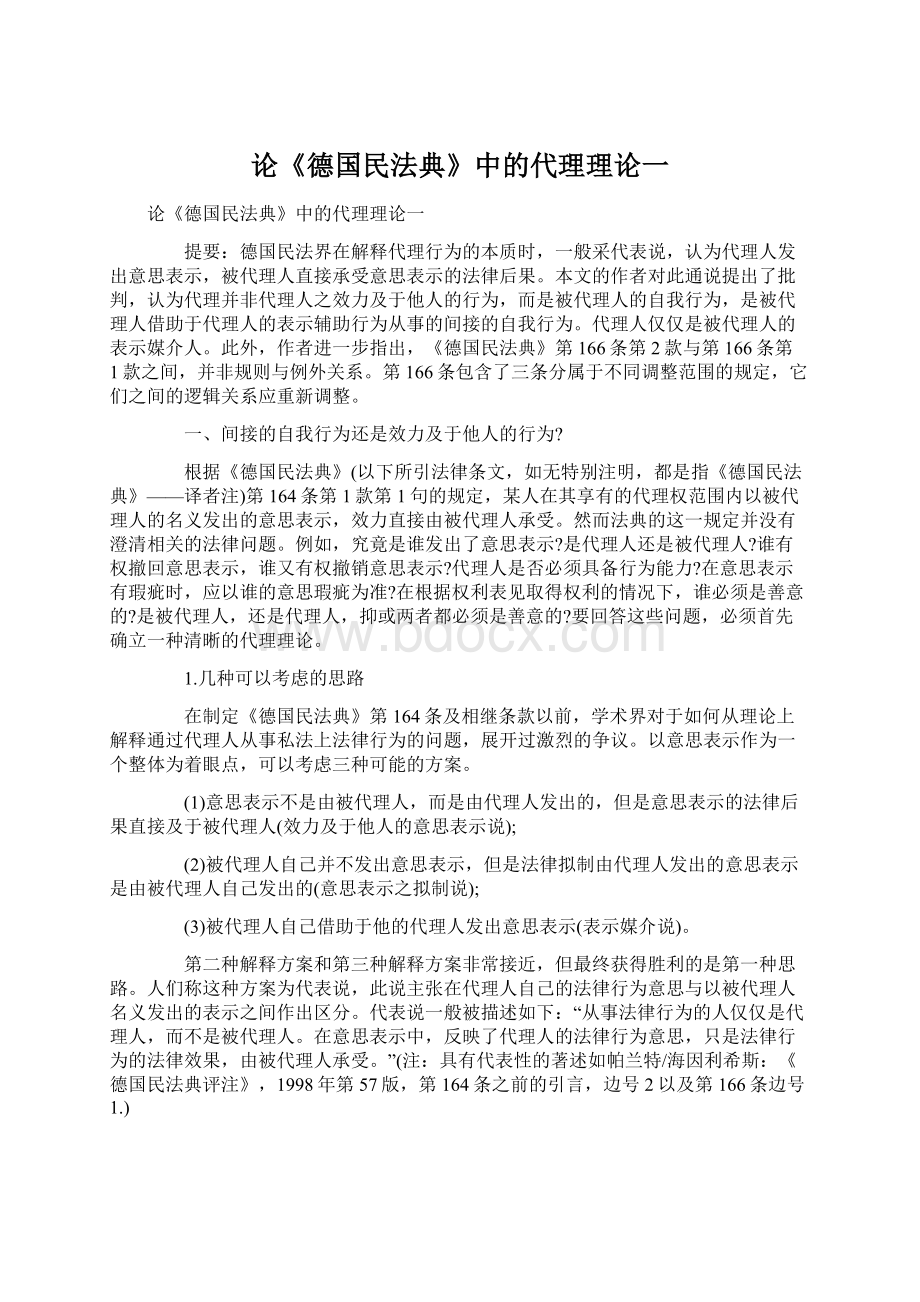
第二种解释方案和第三种解释方案非常接近,但最终获得胜利的是第一种思路。
人们称这种方案为代表说,此说主张在代理人自己的法律行为意思与以被代理人名义发出的表示之间作出区分。
代表说一般被描述如下:
“从事法律行为的人仅仅是代理人,而不是被代理人。
在意思表示中,反映了代理人的法律行为意思,只是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由被代理人承受。
”(注:
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如帕兰特/海因利希斯:
《德国民法典评注》,1998年第57版,第164条之前的引言,边号2以及第166条边号1.)
今天,学术界大多数人都持这种代表说。
但是,人们对法律行为学说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依然有不同的看法,而这方面的分歧又反映在对代理制度的理论解释上。
因此,有必要对通行的代表说作出批评。
2.本人说与代表说之间的历史争端
根据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意思说,法律行为上的意思表示之所以会对表意人产生效力,是因为表意人自己形成了作为意思表示基础的效果意思。
而某人能够为他人从事法律行为的想法,与这一“个人意思说”似乎是不相吻合的。
不过,由于在当时的条件下,代理就已为一个劳动分工型的经济制度所必需,所以要努力避免出现“意思上的代理”这种概念上错误的提法。
当时两种对立的代理理论,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维系私法自治的原则。
不过两种理论都半途而废,未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底。
本人说(注:
此说由萨维尼(CarlFriedrichvonSavigny)创立,见其著作《债法作为今日罗马法之部分》,1853年,第二卷,第57章,第59页。
)将代理人的意思排除在外,把代理人理解为被代理人私法自治意思的载体,代理人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并且以被代理人的计算从事法律行为的,只有被代理人才想在法律上从事代理人行为。
与本人说相反,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代表说(注:
此说由布林兹创立,见《潘德克吞教科书》第四卷,1892年第2版,第577章,第333页以及第581章,第360页以下。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温德沙伊德(《潘德克吞法教科书》第一卷,1879年第5版,第73章,第193页)。
当然,他们都没有使用今天才通行的“代表”这一概念。
)则认为,只有代理人才形成其法律行为上的意思。
代理人不过是把以他人名义发出的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转移给被代理人而已。
无论是法律行为上的代理权,还是法定的代理权,都肇源于被代理人,由此被代理人方面的私法自治原则能够得以维护。
这也即是说,根据本人说,被代理人要想从事法律行为。
而根据代表说,代理人要想从事法律行为。
无论如何,都是由代理人为被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
在这两种学说(注:
媒介说(Vermittlungstheorie)试图走出一条第三条道路。
此说认为,“并非代理人单独地,也并非被代理人单独地和排它地在法律上从事行为,而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一起从事行为,他们都是法律行为的生产者”(米特埃斯(Mitteis)言,《代理学说》,1885年,第110页;
德恩堡(Demburg)也持此说,见《潘德克吞》第一卷,1892年第3版,第117章)。
此说的正确之处是,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在法律上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
不过媒介说无法解释法定代理。
在法定代理中,被代理人自己没有行为能力。
而人们应该把代理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
参见下文三3.)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只存在对表示的代理,而不存在对意思的代理。
因此,两种学说都试图消除对意思的代理。
这种对意思和表示进行区分的做法,依然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弗卢姆(Flume)的法律行为学说(注:
参见下文三4.)中。
二、意思自由与意思归属
个人意思说仅在有限的范围内为《德国民法典》所采纳。
由于意思表示的发出通常都构成一项社会交际行为,因此法典把交易保护这一方面补充了进去。
法律应当考虑第三人应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利益。
这一点反映在意思归属和知情归属的原则中。
一项意思表示,并非在表意人所想赋予的意义上发生效力,而是在受领人所理解的意义上发生效力。
此即为客观表示价值说。
如果一项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已进入受领人的控制领域,而且受领人在通常情形下可以知悉其内容,则受领人就知道了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到达原则)。
法律行为上的私法自治制度,乃基于对社会利益的平衡。
表意人之所欲,以其可能者为限(意思实现);
社会之典型期待,以其必要者为限(意思归属和知情归属)。
三、代理人行为在法律上被归属为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归属作为共同的事实构成
民法上的意思归属和知情归属,对代理理论起着反作用。
如果法律行为上的意思不仅可以自身形成,而且还可以在法律上进行归属,那么对意思上的代理提出的主要异议(即违反了个人意思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这样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各种古老的代理学说是否已经过时了。
特别是代表说还有什么用处?
此说细加探究,就会发现其异常复杂。
它没有回答“代表”的具体所指,也没有指出“代表”概念与“代理”概念之间的区别。
此外,代表所指向的对象也是不明确的。
究竟是仅指在意思上代表本人(注:
参见舒尔茨/封?
拉索尔克斯(Schultze/vonLasaulx):
《德国民法典》,第一卷,1967年第10版,第164条之前,边号9.)呢,还是也指在表示上代表本人?
代理人究竟是仅仅在意思上“代表”本人呢?
还是代理人在表示上“代理”本人?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者虽然采纳了代表说的思路(注:
《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6页:
“草案采纳第一种看法,行为是代理人的行为;
只是行为的后果指向被代理人。
),但是”代表“这个概念本身没有进入法典。
有人认为:
”代表原则“(注:
Repraesentationsprinzip.使用这一概念的有帕兰特/海因利希斯(Palandt/Heinrichs):
《德国民法典评注》,1998年第57版,第164条之前的引言,边号2;
施陶丁格/狄尔希尔(Staudinger/Dilcher):
《德国民法典评注》,1979年第12版,第164条之前,边号32.)反映在法律的内容中。
不过这一点殊成疑问。
对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这条代理法方面的重要规定,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注:
有关《德国民法典》第166条之规定,参见下文三2.)该句规定”某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发出意思表示“。
这说明,代理人从一开始就说明,不是他自己,而是另外一个人才是本人。
也正因为这样,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才会在法律交易中”直接为被代理人的利益和对被代理人的不利益产生效力“(第164条第1款第2句)。
既然一项意思表示作为一个整体,亦即在其所有的要素方面,并非完全由本人决定,它何以能直接对本人产生效力?
本人要想成为合同当事人一方,难道不是非得由他最后发出意思表示才行吗?
代理人实施的法律行为,不是要经过被代理人自始至终的亲自首肯才合法吗?
而无论是授予代理人的代理权,还是代理人依法享有的代理权,抑或是其依职权享有的代理权,难道不仅仅是一种旨在将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转移给被代理人的法律技术上的手段而已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对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不一定非得在坚持二分思想(代理人发出意思表示,被代理人承受法律后果)的代表说的意思上作出解释。
毋宁说,从本人说角度来解释164条第1款第1句(在代理行为中,是由本人自己在发出意思表示),也可以得出合理的结论。
从本人说出发来解释,则被代理人就不仅仅是承受代理人意思表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的人。
被代理人也不是被视为是他自己发出了意思表示一样。
关于此种表示拟制的不必要性,参见下文三2.)毋宁说,被代理人在法律交易中自己借助于他的代理人发出了意思表示。
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在法律上作为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全部归属于被代理人。
据此原则,权利主体既可以亲自发出意思表示,也可以让代理人来发出意思表示。
代理人虽然发出了一定内容的东西,但是由于他是以他人的名义从事行为的,因此他的表示行为对他来说并不是意思表示。
只有在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针对于自己发出意思表示时,才存在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行为。
而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从事的恰恰不是这种行为。
在代理行为中,代理人明显地是针对着另一个人从事行为,代理人不过是被代理人的表示辅助人而已。
2.与给付媒介的比较
如上文所叙述的代理法上的表示辅助行为,对于私法制度而言并不陌生。
给付媒介可以表明这一点。
参见博伊庭(Beuthien)文,载《法学家报》1968年,第323页以下。
)接受债务人指示的人,相对于债权人并不履行自己的给付。
虽然被指示人转移了给付对象(商品或金钱)上的所有权,但是他只是发出指示的债务人的给付媒介人。
从法律上来说,债务人是在借助于被指示人,向债权人为给付。
在被指示人方面,他是在向指示人为给付,虽然被指示人实际上并没有向指示人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行为(参见第362条第2款,第185条的规定)。
此种给付媒介行为的特点是涉及到整个给付事实构成,亦即扩及至财产流转。
这里所称的财产流转,是指被指示人与债权人之间实际完成的价值流动。
因为不存在无财产流转的给付,因此发出指示的债务人也是财产给予者。
)
3.代理作为表示媒介
与上述情形相适应,代理人可以被理解为被代理人的表示媒介人。
作为表示媒介人,代理人并不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因为他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从事行为的)表达他人的(并非仅仅是效力及于他人的)意思表示。
法律意义上的表意人是作为本人的被代理人。
依此解释,代理人为被代理人从事行为,而被代理人则是通过代理人从事行为。
这不是一种概念上的对立,而是从两个方面描述了同样一个过程。
这即是说,代理不是代理人之效力及于他人的行为,而是被代理人借助代理人的表示帮助,间接从事的自我行为。
从这个角度观察代理行为,虽然代理人在形成效果意思,代理人在构建意思表示的内容并将意思表达出来,但是他形成的和表示的不是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一个在法律上属于他人的意思表示。
因此,对于第164条第1款第1句,可以作出如下解释:
由代理人表达出来的意思表示,由于是由代理人以他人的名义发出的,因此从法律上来说,自始就是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
或者,至少也可以这样解释:
由于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和对其不利益产生效力,因此该意思表示依法成为被代理人的意思表示。
第一种解释在概念上要比第二种解释简单些。
第二种解释中,包含了一种类似“逻辑秒”的想法。
这样,我们不再需要用表示拟制(注:
上文一。
)之方法来说明问题。
因为拟制是一种法律技术上的权宜之计。
拟制作为概念上的最后的应急措施,只有在找不到思想上更为简便、更符合法律体系以及实质上更为明白易懂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
而表示媒介说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简便的、符合体系的和易懂的解决方案。
它要比令人捉摸不透的,把意思、表示和表示效力割裂开来的“代表原则”清晰明了。
所以,至少就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法律后果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舍弃代表说来解释。
关于代表说对《德国民法典》第166条的必要性,参见下文五。
对一种现代的代理理论而言,重要的是在理念上不再在意思上的代理和表示上的代理之间作出区分,而是要把由代理人在法律交易中作出意思表示作为一个统一体,即作为一个法律行为上的整体事实构成,归属于被代理人。
由于意思表示是由意思和表示组成的,因此第164条第1款第1句所称的意思表示的代理,理应包含了意思上的代理。
除此之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将法律行为上的代理(第167条)、法定代理(条1626条第1款)以及依职代理(第1793条,第1909条),归结到代理这一法理上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去。
米勒—弗赖恩弗尔斯(《法律行为中的代理》,1955年,第342页以下)对代理法中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统一的基本结构表示过怀疑。
)正是因为表示媒介说将意思上的代理包含在内,因此此说不问被代理人自己能否有效地形成或表示出由代理人表达出来的意思。
4.与弗卢姆法律行为学说之比较
弗卢姆(注:
《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载《德国法律生活一百年——德国法学家大会一百周年纪念文集》1960年,第135页以下(第160页以下);
《民法总论》,第2卷法律行为,1979年第3版,第43章第3节,第755页。
)为了克服源于个人意思说的困难,区分了作为表示行为的意思表示以及作为通过该表示行为而形成的规定的法律行为。
他把意思上的代理称为“神秘主义”(注:
《德国民法总论》第43章第3节,第755页。
),认为这种提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他想通过这一区分,避免意思上的代理。
他认为,由于代理人是从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因此只有由代理人达成的法律上的规定(Regelung),才能归属于被代理人。
意思表示的概念,既可被理解为表示行为,也可被理解为表示结果,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在民法的财产法中,还存在着其他包括多重含义的概念。
我们可以根据概念的文义、规范目的、体系关系以及形成历史,对概念进行解释,得出这个概念在有关规定中的具体意义。
最常见的例子是给付的概念。
根据法律规范所属的不同体系,给付既可以解释为给付行为,也可以解释为给付结果。
很明显,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规定并不涉及到意思表示的发出,而是涉及到已经发出的意思表示。
因此,此条规定所调整的并非是作为表示行为的意思表示,而是作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表示结果的意思表示。
第164条第1款第1句正是旨在将这种表示结果转移给被代理人。
因此,在“意思上的代理”和“表示上的代理”之间作出区分,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意义的。
应该把意思表示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上归属于被代理人。
《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的文意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该条规定并未区分意思和表示,而是把由代理人“发出的意思表示”全部归属于被代理人。
有关第166条的规定,参见下文五。
)在代理法上,既必须将意思归属于被代理人,又必须将表示归属于被代理人。
这也即是说,我们无法在不同时将他人的意思归属于被代理人的情况下,将他人的表示行为归属于被代理人。
恰恰是由于代理人是从事法律行为的人,亦即是代理人发出了意思表示,(注:
这也是弗卢姆的出发点!
)并在订立(注:
弗卢姆(《民法总论》,第43章,第3节,第755页》所言“在履行法律行为时的代理”易生误解。
因为,仅仅为他人订立法律行为者,并非履行该法律行为,特别是该人并不实施该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的时候代理了被代理人,因此,由代理人表示出来的意思进入到了法律行为中去,而该法律行为作为规定,应该归属于被代理人。
所以,认为以上面的方式可以避免“意思上的代理”的提法的人,(注:
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是无用的。
有关这些尝试的精神上的各种表现形式。
参见温德沙伊德:
《潘德克吞教科书》,第73章,注16b(第194页)。
特别是在意思与表示之间作出区分的做法,如坎斯坦在其载于《格林胡特杂志》第三卷第684页中所为,完全是徒劳无益的。
根据这种看法,代理之“要旨在于:
代理人并非代替被代理人欲为,而是代理人代替被代理人表示出被代理人的意思”。
但是,如果存在一项意思表示(而要使法律行为成立,必须存在此项意思表示),那么总有某一个人欲为之。
被代理人要么无法欲为(如在法定代理情形),要么(根据代理制度之劳动分工意义)授予他人代理权。
这即是说。
利他的意思形成,只能产生于代理人处(《立法理由书》第二卷第227页谓“代理人之意思行为”,这是正确的)。
)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此种对(应归属的)意思上的代理的畏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种畏惧是法律生物学思维方式残留下来的对概念把握的困难。
根据法律生物学思维方式,由于从自然科学来看,只有一个自然人才有能力欲为,因此在法律上,由另一个人来代替此本人,为此本人欲为其自身之事,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既然在私法上,不仅自己事实上所为之行为有效,而且归属于自己所为之范围的行为亦有效,那么,上面所说的困难也就不再存在了。
这一困难从概念上就消除了。
为此,我们不需要一种新的行为学说。
弗卢姆(文载《德国法学家大会纪念文集》,第162页)认为代理法在这里“具有范例性”。
如本文所示,这一看法并非恰当。
此外,在合同订立过程(第145页以下)中,法律行为还包含合同对方当事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该意思表示毋须在代理法上特别归属于代理人。
合同之所以生效,源于拘束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订立行为(第305条)。
合同的订立,仅需双方当事人发出意思表示。
故此,弗卢姆提出的原则性批评(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不应使用“意思表示”,而应使用“法律行为”的概念),是扑了个空。
3.撤回权和撤销权的归属
如果把被代理人视为本人,即被代理人不仅是欲为者,而且是表意者,则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何被代理人可以根据第130条第1款第2句行使撤回权,根据第119条及相继条款行使撤销权,而不是由代理人来行使此类权利。
因为,这些情形中涉及的意思表示是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被代理人有权撤回意思表示,因为他作为本人不愿意受应对他产生效力的意思表示的约束;
被代理人有权撤销意思表示,因为他在借助于其表示媒介人从事表示行为的时候搞错了或者对其表示产生了误解。
被代理人有权撤销意思表示,因为他在他的代理人方面(也即是间接地在他自身方面)受到了欺诈或胁迫。
依代表说,代理人发出的是自己的意思表示。
这样,被代理人就必须撤回或撤销他人的意思表示,才能避免自己承担该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
这种解释,不免牵强附会。
6.与授权之界定
代理(第164条第1款)与授权(第185条)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代理人是以他人名义从事行为,而被授权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为的(二者都是为他人的计算从事行为)。
除此之外,授权仅仅涉及到某项他人的权利客体;
而代理权则依据代理的公示性原则(第164条第1款第2句),涉及到被代理人自身。
与此相适应,代理与授权情形中的本人是不同的。
在授权情形,本人是被授权人,他根据自己的意思处分某项他人的客体。
由于他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行为的,因此他发出的是自己的意思表示。
而在代理情形,由于代理人是以他人的名义从事行为的,因此他只是媒介了他人的意思表示。
所以,本人是自身承受法律行为后果的被代理人。
而如果采纳代表说,认为代理人是法律行为上的行为人(虽然其行为是指向另一人的),并且由代理人发出自己的、法律行为上的意思,(注:
如帕兰特/海因利希斯(同注1,第166条,边号1)所认为的那样。
)那么代理与授权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7.与传达人的界定
传达人与代理人不同,他仅仅是传达他人的意思表示而已,而并不参与对他人意思表示内容的构建。
人们批评本人说模糊了代理人与传达人的界限,因为此说将代理人的意思归属于被代理人自己的意思;
与此相反,代表说则认为代理人具有自己的意思。
然而,这一讨论是一种无谓之争,因为代理人与传达人显而易见地承担着不同职能。
代理人为被代理人构筑意思表示的内容,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表示辅助人。
相反,传达人只是帮助被代理人转达内容已经确定的意思表示,传达人只是被代理人的到达辅助人而已。
由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从二者承担的不同的任务角度,对代理和传达作出明确的区分。
我们毋需采用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