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文档格式.docx
《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溪罗先生一贯编文档格式.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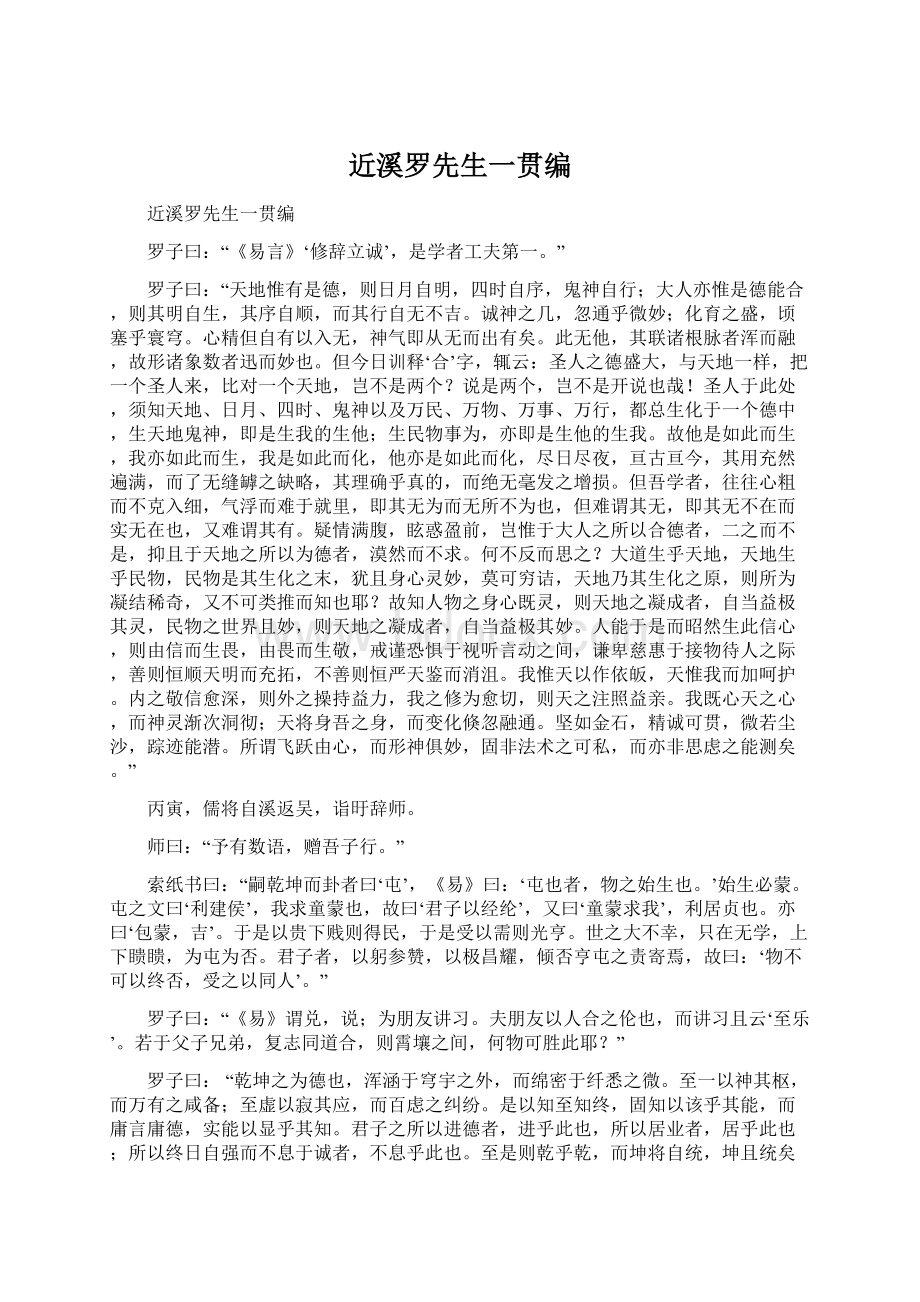
为朋友讲习。
夫朋友以人合之伦也,而讲习且云‘至乐’。
若于父子兄弟,复志同道合,则霄壤之间,何物可胜此耶?
“乾坤之为德也,浑涵于穹宇之外,而绵密于纤悉之微。
至一以神其枢,而万有之咸备;
至虚以寂其应,而百虑之纠纷。
是以知至知终,固知以该乎其能,而庸言庸德,实能以显乎其知。
君子之所以进德者,进乎此也,所以居业者,居乎此也;
所以终日自强而不息于诚者,不息乎此也。
至是则乾乎乾,而坤将自统,坤且统矣,而况于六十有奇之卦,三百有奇之爻耶!
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纯阳,善言学圣者,必曰通明。
“《易》言: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下却继之以‘神无方而易无体’。
盖神、易是心知微处,微则入里而渐次浑融,方、体是心知显处,显则发外而益加昭著。
显微,虽均属心知,而为用则互相胜负。
吾人日中不免应酬事物,事物则必有方体,方体是以显而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有之,而人人亦习见之,所以自夜而通之日也,不难言矣。
吾人夜间,必须安舒意气,意气则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含其显也。
故心知在夜间,虽人人亦皆有之,而人人却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实难言矣。
今人亦自心粗而不细察,若细察则夜间当更精妙,亦更昭著也。
试看,每夜更深,则此心自然晓得去睡,睡则自然晓得要安,安则自然晓得要熟。
呼而问之,则睡中意味,或美或恶,或长或短,一一如烛照数计也,其中更无一时不知,知亦更无一时不显。
至其变化而为梦境,祸福而示先知,则灵妙较之日中,又增万倍而无算矣,谓此非知之相通,而何哉?
或曰:
“天者群物之祖,其妙变化而鬼神,通人心而善应感,亦无足为异矣。
兹欲祈天永命,不识亦有其要乎否?
“约哉问乎!
盖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之为德也,脉络潜行,枢机统运,上则达乎重霄,下则通乎率土,物无一处而不生,生无一时而或息。
善学者,于所遇也而能先开是见,于所见也而能悉显是机。
活泼满前,欢欣盈掬,于己固欲其生,然不惟于己已也,而人亦欲其并生焉;
于人固欲其生,然不惟于人已也,而物亦欲其同生焉。
夫物无不生,天之心也,生无不遂,天之道也。
吾心其心而道其道,是能与天为徒矣。
夫既与天为徒,则感应相捷影响,而长生不为我得耶?
所谓根苗花实,共贯同条,有是真种之投,斯有妙果之结也。
“天之与我,三纲五常,百行万善,而我之事天,乃专在好生之一端,何哉?
“子独不观夫孝弟乎?
夫孝弟固纲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亲,弟之事长,其无方之养,先意之承,非悉不且备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寿之焉耳。
夫寿也者,岂惟子日期诸其亲,弟日期诸其长,即亲长亦日所冀望于其子弟也已。
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独至,而所以为孝且弟者,必归之矣。
岂独孝弟为然哉?
推而君臣而夫妇、而朋友、而万民、而庶物,固无一而不在好生之中,亦无一而或出于存心之外。
近而即之,若云‘庸行之常’,远而通之,实称‘太上之德’,又要其极而言之,则成乎变化之神,而妙乎情识之表。
甘泉之味,或涌见枯庭,双鲤之跃,或日呈冰冻,萌竹笋于寒冬,女天姬于凡世。
彼愚夫愚妇,且诚感而神应焉,而况于有道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
子固可以直信而无疑,坦行而无泥也已。
“六十四卦,统总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虚位,故谓之曰六虚。
惟大明之终而始也,斯六位时成矣。
明谓之知,大明之所始,谓之‘复以自知’也。
复之一爻,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气周,即冬至一日,次第成三百六十日而岁功成。
所以夫子许颜氏庶几于复者,以其知‘一日克己复礼而天下归仁’也,天下归仁,即卦气周而岁功成矣。
“何卦气、岁功之数不同?
岂岁功之外又有卦气耶?
“乾、坤主体,坎、离主用,然统总只显出一箇阳之纯处、知之明处,则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当主体,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谓三百六十日也。
“明字与易字,皆用日月二字为之。
明以日月相并,正显阴阳之体,而易以日月相函,却显阴阳流行之用也。
故天以日月,时时尽卦爻,而人莫知,圣人以卦爻,时时象日月,而人莫测。
卦爻者,日月运行于天上之度数也。
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极下处,月在天之最上处,冬至一复,则日从地而渐上,月从天而渐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则阳不得一百八十爻耶?
其时月在地之极下处,日在天之最上处,夏至一姤,则月从地而渐上,日从天而渐下,日上一百八十遭,而又十一月中,则阴不得一百八十爻耶?
问:
“月是每月周天,恐与日不同。
“行虽不同,望则有定。
盖夏至望在地极下处,冬至望在天极上处,如此定来,方见其与日交相上下也。
“易以乾为体,乾以复为用。
夫乾纯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
乾之善,神妙不可见,而几见于复。
《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虽兼闰以成岁,而始诸冬至之一日。
冬至元阳一复,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时行,百物生,斯其称纯粹以精为性善,善之至也。
且也我夫子五十而学《易》,继乾坤资始资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谓易’。
夫子以易为学,以学为教,易则生生,生生则日新,日新则学不厌,学不厌则教不倦,不厌不倦则其德曰仁。
夫唯仁,斯其人曰圣乎!
故夫子示天下万世求仁之旨,必曰: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夫亲亲为仁之大,其仁大则其人亦大,其学斯名大人之学也已。
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则老老而民兴孝,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则长长而民兴弟;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恤孤而民不倍。
此之谓仁于家而齐,仁于国而治,仁于天下而平,若运掌而无难者。
要之,孩提知爱,少长知敬,未学而嫁知养子,是人人能仁者也。
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机自不息,性乎性而生恶可已。
所谓万物皆备,我可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贯。
故己能己焉,是谓‘中行独复’,中行独复,惟颜氏之子庶几。
夫子所以语之曰‘克己复礼’又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信哉,复其见天地之心矣乎!
盖一阳元气,从地中复,所谓由乎己,黄中通理,正位居体也。
由是视听言动,一之于礼;
由是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国家视诸掌,则美在其中。
畅四肢,发事业,是美之至,善之极。
颜氏之子,真圣于复,复而圣者乎?
下是唯孟轲氏可欲之善,信有诸己。
夫惟信而后能克,未有克而不始于信者。
一信乎己,即而美而大而圣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
甚矣哉,孟之似吾颜氏也!
甚矣哉,轲之善学吾夫子也!
“大禹‘安汝止’,止者,即更善之谓也。
文王于君臣父子国人之止,穆穆缉熙而敬止,方是‘安汝止’。
此禹几康之心,万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问:
“凤凰来仪,恐非实事?
“子未读《易》乎?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圣人作而万物覩,自然之理也。
盖天地民物,本是一乾变化,特性命各正耳。
如手之扪足,足之随手,此动彼随也。
心和,天地之和应之;
心顺,夷夏之顺归之,况凤凰乎?
此孔子叹凤凰之不至,亦有感凤兮德衰之歌,岂可以来仪非实也?
诸友惟当益振雝雝喈喈之响,以来仪于圣庭是愿。
众皆欣然曰:
“天地变化,草木蕃;
学问变化,禽兽舞。
大家当自猛也!
会中问: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岂有一命令以宠降之哉?
“尧舜止言心,而性则自得言也。
明于‘性’之一字,则降之义,自明矣。
盖性从心生,是上帝生生之德也。
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万世之民,天下万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
固其生之为性,即帝之性。
只此一‘降’字,汤乃为下民警之。
其实,下民即上帝,如子之于父,精神血脉,皆父所受也。
大众恻然。
“伊尹曰:
‘习与性成。
’然则习之所系,大矣哉!
《易》曰:
‘不习,无不利。
’《孟》曰:
‘习矣不察。
’可见不习之利、不察之习,出之于天也。
孔子‘习相远’与此‘习’字,不可不慎之于人矣。
“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即梦帝賫良弼?
“语云:
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
则诚之极也,况其所思者道乎?
思道又恭而默乎?
盖道本相通,质鬼神而俟后圣者也。
一能思之,思则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道,故上帝賫以学道之人,教以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教以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则向之思不能学者,今时敏学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复旧物以承汤之绪,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
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此哉!
且不惟有补于高宗,学之一字,言自傅说,万世而下,人人知学,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书》云‘不虞天性。
’夫曰‘恒性’矣,复曰‘天性’见性而非天,则有不恒。
试观父子之间,其当孩提之时,父之抱子,子之恋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状?
所以孟子曰‘形色天性’,只见人于形色,莫知莫觉,自会保爱,则天性,又可不虞乎!
或问:
“‘惟天阴骘下民’,其曰何如?
“子谓‘阴’字之义,乃天之默默然也?
曰:
“然。
“然则帝之震、风之烈、鸟兽之喧吼、昆虫之唧喁,何为不体天之化也?
盖天以一神,神则妙万物,既妙万物,虽有声而无声也,推之乾不言、天何言、默而识,皆是此意。
“《书》曰:
‘思曰睿,睿作圣。
’弟子未尝不思,何以不长进也?
“子所谓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
夫心之官则思,君子九思,乃出于何思之真体也。
以真体而思,则便是圣人不思而得矣。
子其憧憧往来,何以通微而入圣哉?
所以箕子述《禹范》曰:
貌言视听思,孔子教颜复,视听言动礼,皆是一意,皆是先立乎其大。
此乃万古入圣要诀,其实只在勿忘勿助之间,百姓日用不知耳。
“弟子亦知,思非礼勿视。
“孔子见南子,亦以南子为圣耶?
如以南子为圣,则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为非,勉强禁之,则助之矣。
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遇至人,则箕之睿、颜之复,只成一个空谈耳,何益于圣哉?
所以今时学者,问以力学何先?
皆曰‘思曰睿,睿作圣’,又曰:
只在克己复礼,非礼勿视、听、言、动。
及见人有一毫拂逆于我,即迁于怒矣,复礼已剥矣,睿几已窒矣。
予尝向人提醒,彼皆漫然。
子有作圣之志,须于岁月凝神,自有启其衷者在也。
勉之勉之!
“克念狂作圣,罔念圣作狂。
可见念之动处,乃心之精神,能动精神谓圣,不能动精神即狂。
圣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动乎?
孔子曰:
‘罔之生也幸而免。
”哀哉!
“先儒云:
欲观王者皡皡气象,须读芣苡四五过,则可知皡皡矣。
夫皡皡,则室家和平矣,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则大家保合太和。
太和则无不平,与不平则无事,无事须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荣。
《易》谓:
天地化,草木蕃,况于人乎!
此皆由于亲亲、敬长始,所以孟子称皡皡曰: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
’善乃良知良能,无不爱亲敬长,此采芣苡之所以皡皡也。
“圣人顺事无情,胡为《黍离》之悲?
“此正顺事无情也。
夫人情贵于相安,不安不可以为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恶恶之,宗室尽为黍离。
如此而不动心,岂人情乎?
此《春秋》继《黍离》作也。
有歌《伐木》: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某玩此诗,神听之听,与他听不类。
“何以不类?
“诗之兴义,原取诸友声,声即言也。
言之为德,以和平为贵,如曰:
友声和平,则神乃听之。
神既听之,即可以终和平也,则此‘听’字,当与听受相类,而与神其吐之之意相反也。
众咸曰:
“《诗颂》‘思无邪’,何也?
“子必明于思之义,方知思之无邪也。
知思之无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篇也。
夫人之思,出于心田,乃何思何虑之真体所发,若少有涉于思索,便非思矣,安得无邪?
“《诗颂》“濬哲维商’,复以‘圣敬日跻’言之,何如?
“敬者,圣学传心之要,而况契乃商之始祖也。
其家学乃是敬敷五教在宽也。
既以敬而敷教,又以宽而俾人人得入其教。
当时父子皆有亲,君臣皆有义,夫妇、长幼、朋友皆有别、有序、有信,倘非心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
此汤之所以世守其敬,以至贤圣之君六七作,及后高宗中兴,恭默思道,虽至式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其敬敷五教在宽之留也。
信乎!
‘濬哲维商’也。
“高宗下民有严,乃若始终典于学,方知天视民视,天听民听。
此所以赏不僭,刑不滥,见民即天也,非学务时敏者,孰能至此?
“《礼》首云:
“毋不敬,俨若思。
’是其所思者,岂徒一己已哉?
必曰‘安民’。
安天下国家之民,方是文王缉熙之敬,所以曰:
‘毋不敬’。
观‘毋不’二字,则民即该之矣。
孔子学教不倦,真是复礼,以一部《礼记》付之颜子。
“‘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夫行而曰善,乃天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
故君子不息不怠,须于可欲之善,以求继善之性,则全交而通天下国家矣。
“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于大同也?
“大同之世,人忘其私,天下为公也,外户不闭,相游于天。
孔子所以东奔西走,只为这场,所以忘食忘忧,只为这件。
倘大道不行,孔子之忧,断然不已,吾辈须力学以求释孔子之忧。
“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何其耐烦如是也?
“圣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见得人者天地之德,又见人者天地之心。
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德天地之德;
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
以天地之德为德,即欲人同天地之德;
以天地之心为心,即欲人同天地之心。
譬之,人家兄弟四五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贤子,必曰:
我四五人,我父俱是爱,如何令我明彼昏,我富彼贫,所以日夜皇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
故曰:
中心安仁,天下是一个人。
又曰: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不得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
噫!
仁以人之,杨子亦言之,不人则不仁,不仁则不人。
未有人而不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也,故曰:
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予尝读《礼》“天下之肥’不觉泪下,何也?
肥瘠相并,不肥则瘠,子瘠则亲心戚,天下瘠则圣心忧。
“一部《春秋》,乃孔子负罪而作,把来比拟以牵合词章,则其义如何得明?
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大学》一书,总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止。
知止则意之定、心之静、身之安、国家天下之虑,不患其能得之难也。
知止未能,而求定静安虑固不可得,以定静安虑,与知止并论,亦于明德宗旨相去远甚,学何自而能大也耶?
今日用力须打将一切精神,于知止处透悟,即所透次第,便分作定静安虑,至了结处,即谓之能得,而明明德于天下矣。
知格工夫浑沦圆妙,如眼法尚眩,幸汲汲先口心也。
“孟子《形色天性》章,重在一‘形’字。
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道不远人’,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曰人、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
孟子因当时学者,皆知天性为道理之最妙极神者,不知天性实落之处;
皆知圣人为人品之最高极大者,不知圣人结果之地,故将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说一番。
如云:
此个耳目手足,其生色变化处,即浑然是天下所谓最妙极神的天性,故我此个耳目手足之形,一切世间贤人君子,都辜负空过了他,惟有圣人之最高极大者,乃于此形之妙,方为率履不越也。
如此便见得万物皆备于我,我能诚于反身,即其乐莫大焉者矣。
仁德浑是个人,为道而远人,即道不可以为道矣。
“如何便不可以为道?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
学者言天,便见得甚大,若言人,便见得甚小,殊不知天人只是一个,如不一个,便不是道也。
“必是圣人,方能口代天言,身代天工,如何都说得一个?
“经上明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如何不皆是一个?
圣人但能知得天视即民视,天听即民听,而率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别有伎俩也。
故不肖尝作一俚语,对朋友说:
某于讲道学,则有未能,若说圣人,则若做过许久时也。
朋友皆以某为妄言,某引证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大人与天地合德,某固不敢当,至如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许久来耶?
邵康节诗云:
‘耳目聪明男子身,洪钧付与不为贫。
’今日在会诸友,谁不耳目聪明,谁不洪钧付与,又谁不可承受付与一个大圣人哉?
“《有子其为人》章,意何如?
“此有若之言语,所以似孔子也。
孔子云‘仁者人也’。
盖仁是天地生生的大德,而吾人从父母一体而分,亦只是一团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
故色容温,没有一毫干犯的气象,口容止,没有一毫干犯的言词。
盖由他心中有个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恶可已。
生恶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此本。
如是则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在父母则为孝子,在天地则为仁人,方不负父母生我一番,故曰:
‘其为人也。
’然则下之为仁,宁非即仁者人也意义哉?
“既云孝弟本矣,复言道生,岂非本自本而道自道?
“既云‘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宁可分而二之也。
盖孝道至大至久,塞天地而横四海,沦草木而及禽兽,有许多大的道理,皆是此个本子,非本之外又有道也。
故孔子是孝的人,自言其为人,发愤忘食,耐以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称回之为人,择乎中庸,只要庸德之行,复礼天下归仁。
甚矣!
有若之言似孔子也。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本犹根也,树必根于地,而人必根于亲也。
根离于地,树则仆矣,心违乎亲,人其能有成也耶?
故顺父母、和兄弟,一家翕然,即气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树之蕃茂也,将不可御矣。
然则厚其亲者,实所以厚其身也夫!
“弟子之职,要入则孝,出则弟。
但孝弟不难于知而难于行,不难于行而难于扩充以尽其道也。
盖孝弟之人,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便谨而信也。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便是汎爱众而亲仁也。
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为父子兄弟足法,便是余力学文,以显亲扬名于天下后世也。
“曾子告门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只是浑然。
夫子告子贡,却曰: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
“大约圣贤经书道理只是一个,更无精粗。
精粗生于所见之浅深,所造之生熟焉耳。
故刍荛之言、孺子之歌,圣人闻之,即是至理。
若所见尚浅,所造未纯,即精一执中之语,亦作猜疑过也。
曾子当时初唯一贯,心地洞然。
但捻动,便全体跃然在目,其视忠恕、一贯,又更何别?
若子贡之问,正在见解之处,孔子只得就他分下阶级,方可进步。
要之,至理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亦何莫非取譬之方也?
“先生强恕如是,于一贯何如?
“一贯,非浅陋可识,但窃意一以贯之者,无所不贯者也,而况于恕乎?
是故良知明觉,遍体不遗,必此体在我,然后强恕而行,方能恳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
曾子曰: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固是悟得一贯之为妙,而亦是见得忠恕之不容已也,岂专于教门人之语哉?
“孔子《吾未见刚》章。
“世之目刚者,类以廉介猖直,仅得其一端,而负气好胜者,亦托于刚以自命。
果若而言,则行行之由,愈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宫入室矣。
故夫能辟能阖、能燠能寒、能荣能悴,而后为天地之刚,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进能退,而后为君子之刚,方是浩然塞于天地。
此孟子所以善养,而愿学孔子以慰其见也。
或问先生道不可离、良知不昧之语,屡屡作疑处起。
问曰:
“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如何孔子复有此叹?
“圣人此语,正是形容良知无须臾离处,如曰:
人皆晓得由户,则其终日所行,何莫而非斯道也!
其友复曰:
“即是人人皆晓得,何为却有殴父骂母之辈也?
“此辈固是极恶,然难说其心便自家不晓得是恶也?
“虽是晓得,却算不得。
“虽是算不得,却终是晓得。
可见,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须臾离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说得‘知’字,如此尊贵。
又说:
知之者不如好、不如乐,两个‘不如’则知亦似未妙也。
“不止于知,虽好、乐亦有生而好且乐者,则学与困者,亦弗如之矣。
“良知在人,原无二体,乃相去远甚,何也?
“此‘知’字,乃知觉之知,正与《大学》致知‘知’字相同。
生知者,则所谓先知、先觉,而学知、困知者,则所谓觉后知、觉后觉者也。
“然则又何以见其无二体耶?
“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无二体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学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故曰:
‘及其知之一也’”
子谓熊君应皋,曰:
“德之不修,由学之不讲也。
盖学则有义可徙,有过可改,故四者之忧,惟不学为大也。
其或讲之,而不于徙义改过,是急吾夫子之忧,又当何如?
“孔、颜乐处?
“圣贤之道,原只寻常,而学者讲求,善当体会。
所谓乐者,窃意只是个快活而已,岂快活之外,复有所谓乐哉?
活之为言生也,快之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泼,了无滞碍,即是圣贤之所谓乐,却是圣贤之所谓仁。
盖此‘仁’字,其本源根柢于天地之大德,其脉络分布于品汇之心元。
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则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则欢爱无尽。
盖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机,故人之为生,自有天然之乐趣,故曰:
‘仁者人也。
’此则明白开示学者以心体之真,亦详细指引学者以入道之要。
后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蘗,生化浑融,纯一无二。
故只思于孔、颜乐处,竭力追寻,顾却忘于自己身中,讨求着落。
诚知仁本不远,方识乐不假寻。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然二者亦交相为用。
盖学者立得地步大,则存驻可久,积得岁月深,则收蓄难方,所计限也。
要之,其初亦只于吾人本分上见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处。
盖人即是仁,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
久孰侔焉?
不能以仁观人,以人体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孔子之所绝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俱没有的。
盖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空本体,况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必、固、我也哉?
“《颜渊喟然叹》章,须与《为仁由己》章、《乐正子善信》章参看,其旨始得。
盖见善可欲,正是从圣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钻,而有高矣、美矣之叹也。
信其有诸己,却是反求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礼约我之礼,而‘为仁由己’之谓也。
既知由己,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已,而至于卓尔有立焉,此即孔子所谓‘三十而立’之‘立’也。
此时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谓欲从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
盖孔子点化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