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一页Word文档格式.docx
《回到上一页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回到上一页Word文档格式.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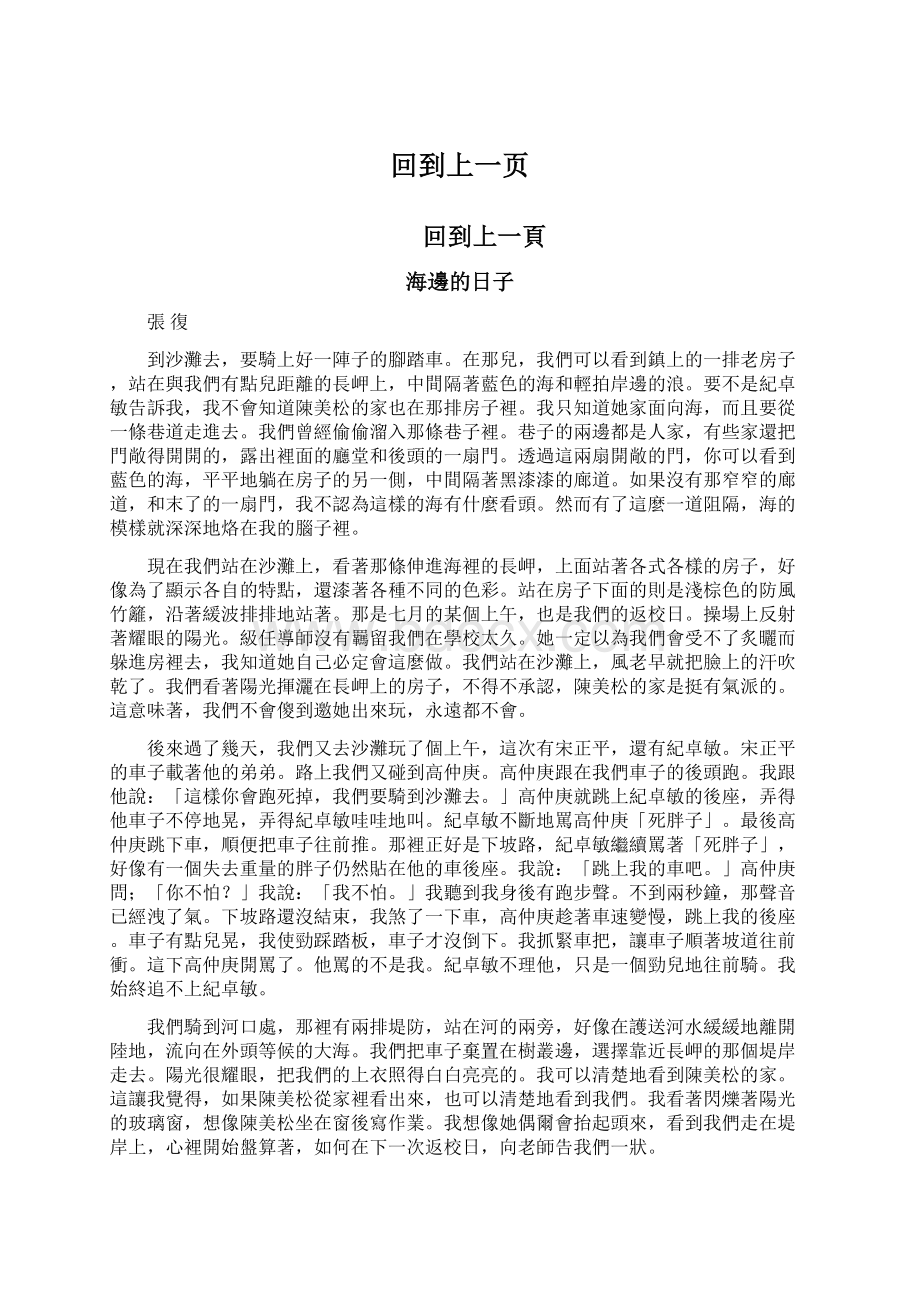
」我聽到我身後有跑步聲。
不到兩秒鐘,那聲音已經洩了氣。
下坡路還沒結束,我煞了一下車,高仲庚趁著車速變慢,跳上我的後座。
車子有點兒晃,我使勁踩踏板,車子才沒倒下。
我抓緊車把,讓車子順著坡道往前衝。
這下高仲庚開罵了。
他罵的不是我。
紀卓敏不理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騎。
我始終追不上紀卓敏。
我們騎到河口處,那裡有兩排堤防,站在河的兩旁,好像在護送河水緩緩地離開陸地,流向在外頭等候的大海。
我們把車子棄置在樹叢邊,選擇靠近長岬的那個堤岸走去。
陽光很耀眼,把我們的上衣照得白白亮亮的。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美松的家。
這讓我覺得,如果陳美松從家裡看出來,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
我看著閃爍著陽光的玻璃窗,想像陳美松坐在窗後寫作業。
我想像她偶爾會抬起頭來,看到我們走在堤岸上,心裡開始盤算著,如何在下一次返校日,向老師告我們一狀。
我們走到堤防的盡頭,河水在那兒注入海裡。
海水對著我們咆哮,好像沒吃飽的獅群,阻止別人接近牠們的食物。
我們走累了,在水泥塊上坐下來。
宋正平跟他的弟弟說:
「你要坐在這裡,就得把拖鞋放到一邊。
」他弟弟說:
「你自己還不是穿著拖鞋。
」這小鬼顯然還沒上學(所以我們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不曉得如果你膽敢跟老師說:
「妳自己還不是──」你就死定了。
如果你還敢跟訓導主任這麼說,我告訴你,你在訓導處跪完一堂課,還得在教室後站一小時。
宋正平說:
「你敢穿了鞋過來──」他弟弟噘了個嘴,把鞋脫了,卻不走到我們這邊來。
他開始比手劃腳,好像是為了打拳,才脫下鞋子來。
宋正平又說:
「你敢對著我比拳!
」他弟弟一溜煙跑了。
不一會兒,我們看到那小鬼出現在對面的堤岸,一口氣跑到盡頭的地方。
紀卓敏說:
「你弟弟要跳海自殺了。
」宋正平不理他,也不往那兒看。
其餘的時間,我只是坐在那裡看著海,然後躺在那兒看著天。
躺了一陣子,我把眼睛閉起來。
世界很快變成紅冬冬的一片。
水泥的熱氣緩緩地從我的背部爬上來。
海水仍然對著我耳朵咆哮,還有一些不知名的蟲子在我頭上嗡嗡地飛。
宋正平弟弟的聲音一會兒近,一會兒遠。
我聽到紀卓敏說:
「我敢打賭,那艘船是向遠方開去的。
」接著我聽到高仲庚說:
「難道就沒有船向我們開來?
」我坐了起來。
在紅冬冬的視野裡,我看到一艘巨大的貨輪遠離我們而去。
「你有沒有看過船向我們開來?
」紀卓敏看到我在看,就把問題重複了一遍。
「我沒有看過。
「這不表示沒有船向我們開來。
」紀卓敏很有把握的說:
「所有的船都向遠方開去。
」我看著那艘即將遠去的船,沒有再答話。
不去沙灘的時候,我也會想起海邊的日子來。
特別是坐在教室裡,我的眼前會飄過海水拍打岸邊的景象,接著我的眼前會出現那艘遠離而去的船。
我常常因為如此而被老師逮個正著。
尤其是音樂老師,總在這時候把我叫起來。
「你好像心情很好嘛。
」她會這麼對我說:
「唱個歌給大家聽吧。
」同學就陪著音樂老師笑。
陳松美也陪著笑,直到發現我在看她,才假裝皺著眉,好像在想別的事。
也許是因為我們開始補習的緣故,那年冬天來得特別早。
降旗典禮以後,我們仍然返回教室去。
天色逐漸變暗,服務股長卻堅持要等老師來才點亮日光燈。
我趁著夕陽沒有消逝以前把生字寫完,知了也趁著日落以前發出最後的叫聲。
帶點兒涼意的風吹到我臉上的時候,教室裡已黯淡得做不了任何事情。
我坐在那兒發呆,假裝聽不到遠處戲臺所發出的弦樂聲。
這時我注意到紀卓敏不斷地對高仲庚做鬼臉。
照在他臉上的陽光太微弱,我看不出紀卓敏的表情來。
我聽到高仲庚對他說:
「誰都曉得你在想甚麼!
」這話引起我的好奇心。
「我就不知道他在想甚麼。
」我插進了話。
他們兩人都不理睬我。
不久,冬天真的來了。
我們必須打開日光燈才能繼續寫功課。
好像要防止不夠明亮的燈光外洩,服務股長同時關上教室兩旁的玻璃窗。
我偶爾走到外面去,走廊上的風把我的外套吹得鼓鼓的,水龍頭流出來的水弄痛了我的手。
跑回密閉門窗的教室裡,我仍然捨不得脫去那件深色的外套。
穿著這種衣服,我可以忘掉窗外沒有起色的天氣,忘掉不知在甚麼時候已全然消失的歌仔戲聲。
我不再回想海邊的日子。
即使坐在前往城裡的客運,我也會把視線避開海面,把眼睛盯在土坡上的廟宇。
歌仔戲台仍然搭建在土坡下的廣場,上面卻空無一物。
我注意到廟宇裡還點著香火,覺得在這個時候能住在那裡也是一種安慰。
我突然想,也許船隻只在冬季才開到我們這裡來,這是為什麼在夏天我們只看到它們離去。
接下來是冗長的雨季。
我們上學經過的小徑,雨水積滿在牛車壓出的軌痕裡。
其後的一兩天不落雨,細細密密的綠苗趁著空檔從柔軟的泥巴裡冒出來。
不久雨又落下來,把綠苗泡在水泊裡。
有一個早上,我們看到牛車新壓的軌痕,把綠苗壓進了泥巴裡。
我們看到兩旁灌了水的稻田,不久插上了新秧。
你真的分不清長在田裡的跟長在小徑上的綠苗有甚麼不同,雖然你知道農人絕不會把寶貴的種籽隨意灑在路上。
即使地上有這樣的變化,天空依然烏雲密佈,晴天看起來遙遙無期,就像傳說甚久的海水浴場的計畫一樣。
太陽好不容易出來了。
出現的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們的級任老師卻給我們留下一大堆功課。
等我寫完大部分的作業,太陽已經重新躲進雲裡。
吃過晚飯,我決定照原先計畫去鎮上看一場電影,把剩餘的功課留到次日早晨完成。
媽媽也鼓勵我出門,還問我是否要找同學一起去。
我出了門,雨水並沒有如預期般落下。
陽光反而掙破雲朵,射出金色的光芒。
我身上帶著媽媽給我的零用錢,心中充滿了想像。
我想像自己會在電影院外碰到陳美松。
我已經好多天沒有看到她的臉。
她的背影卻鮮明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
那飽滿而膨鬆的黑髮,像半捲的簾子,掛在她的頸子上。
只要她一講話,甚至準備講話,我就會看到那相互簇擁的頭髮輕輕地晃動著。
我覺得我必然會跟她在電影院外相遇。
我覺得,我這時想去看電影,就是她將出現在那裡的明證。
我甚至懷疑,媽媽要我去找同學看電影,也在暗示她的出現。
我沒有在電影院外碰到陳美松。
我假裝在外等待朋友,遲遲不肯移動。
收票的小姐叫了好幾次電影快開演了,我才帶著微熱的面頰走進戲院。
好在我很快就被電影的情節吸引。
那是一部美國海軍跟日本海軍作戰的電影。
然而大多數的情節都發生在艦長室裡。
艦長戴了個像體育老師戴的那種帽子,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他身後是大片玻璃所組成的窗子。
這時是夜晚,窗外一片漆黑。
艦長憂心忡忡地看著外面,我卻什麼都看不到。
隔一會兒便有人進來跟他報告,報告讓他更加憂心。
後來,海戰終於爆發了。
砲火點亮了窗外的天空,炸碎了玻璃。
艦長受傷了,倒在高腳椅下。
我很喜歡這個電影。
它不會讓你覺得有人永遠在你上面,永遠不會倒楣,不會受傷,不需要擔心受怕。
走出電影院,我發現緊鄰賣票窗口的攤子打烊了,剩餘的也擺出即將撤離的模樣。
我走過其中的一個攤子,看了一眼已經封存在玻璃紙裡面的醃製水果。
小販察覺到我的眼神,問我要買甚麼。
我沒有回答他便快步離去。
好在還有一場電影等著上映,否則四周會變得更加淒涼。
想到我坐在電影院的時候,竟然還偷偷地許諾自己,要去陳美松家的那個巷子走上一圈,我就有一種罪孽的感覺。
我步行過菜市場,從那兒回家是近路。
星期天的早晨,我陪伴媽媽來這兒買菜。
走在擁擠的過道上,我看到的是雜亂無章的攤販和緩慢步行的人群。
現在的這裡卻成了一片平靜的廢墟。
攤子都收了,剩下的是空無一物的平台,以及同樣空盪的木架子,上面掛著鉤子和沒點亮的燈泡。
水泥地已經讓人清洗過,不平的部分則積著死水。
有一種輕微如雞屎的味道飄進我的鼻子,夾在帶有些許涼意的微風裡。
我很快就穿過走道,轉進一條小巷。
巷口的水果店還開著,此時根本無人光顧,只有一個阿巴桑坐在那裡。
我從來沒有像注視陳美松那樣看著阿巴桑的臉,只知道一向坐在水果後頭的就是她。
難道她一輩子都要坐在那裡?
連偶爾去看個電影都不能?
我開始為她感到難過。
走過菜市場以後是漆黑的路。
我可以聽到溝渠裡的流水聲,和不知哪一家的收音機所播出的歌聲。
聲音異常微弱,我聽不出它到底在唱甚麼,只聽得到拉得長長的尾音。
我突然覺得,我走過的只是鄉下地方,陳美松永遠也不會涉足這樣的場所。
我甚至覺得,一旦她考上外面的學校,會頭也不回地離開這裡。
我下定決心,以後再也不來鎮上看電影,更不會去海邊浪費時間。
暑假就要來了。
這年的暑假跟往年不同。
在暑假出現以前,我們要先通過聯考的關卡。
我意識到這一點,是在發放第三次月考成績的那一天。
那是個下午時光,我們不必留在學校補習。
出校門時,太陽依然在天空,空氣裡有些悶熱。
我以為在路上會碰到宋正平或紀卓敏,號召騎腳踏車的人往沙灘衝。
我已經發誓不去那兒,卻覺得不妨破例一次。
不知何故,這些人早就不見蹤影。
路上走著的全是些垂頭喪氣的人。
你一看,就知道他們的書包裡裝了成績單,要等著爸媽簽字。
媽媽看到我的成績單,趁著我站在那裡不能走,對我說,不僅我的名次退到第二名,連總成績也在節節後退。
她沒有提到陳美松的名字,否則會在我的臉上找到明顯的答案。
我對媽媽許諾,我會在剩下的日子裡好好讀書。
我沒有再到海邊去。
想起這個念頭,我就會感到厭惡。
更奇特的事情發生了。
一向用考試和功課來折磨我們的級任導師,竟然在畢業典禮結束的那一刻跟我們道了別。
我以為她會把我們重新集合在教室裡,囑咐以後要好好讀書,才肯放我們走。
我不曉得紀卓敏,高仲庚,或宋正平怎麼想。
我們都在典禮結束的那一刻分了手,連討論這事的機會都沒有。
我也不再有機會看到陳美松。
每天坐在窗前讀書,我仍然看得到她的背影和她輕輕擺動的頭髮,就像坐在教室裡所看到的那個模樣。
然而,對陳美松來說,沒有人在背後偷看她不會是甚麼了不得的損失,也許連坐在窗前眺望大海都不是甚麼偉大的事。
紀卓敏來找過我。
我只在門外跟他交換幾句簡單的話語。
他問我最近在忙些甚麼。
這問題讓我感到惱怒。
他離去以後,我才想到聯考對他可能不像對我那麼要緊。
臨走前,他跟我說,海邊的戲台最近正在重新布置,問我想不想去看看。
我隨口說了些連我自己都記不得的話,忘了跟他約好時間一起去看。
當咿咿啞啞的弦樂聲在黃昏的空氣中升起,我想起我們以前補習的日子。
我想起那迅速轉涼的空氣,很快變暗了的光線,以及紀卓敏臉上含混不清的表情。
我以為紀卓敏會很快回來找我。
他卻沒有再出現。
有一個下午,我聽到歌仔戲的聲音提前在空氣裡升起,而且很快就跳過戲前的弦樂聲,邁入主戲的階段。
我想起那天是星期六,平日的這時我們早已放學。
我突然興起去海邊的念頭。
我跟媽媽說,我要去同學家借模擬試題。
媽媽沒有阻止我出門,只隨口問了些問題,並囑咐我趕快回來。
當我的車快速馳往海邊,歌仔戲的樂聲已經在天空中飄盪了好一陣子。
這是個出太陽的下午。
天空上有一點灰矇矇的色調。
我騎著車向下坡路衝去,沒有迎面吹來的涼風,只有一股淡淡的煙味。
纏繞在電線桿上的爬藤,也紋風不動地豎立著。
連海面都平靜得很,一點波浪都沒有。
我把車停靠在樹叢邊,烤香腸的煙味已經繚繞在我的鼻子裡,鑼鼓的聲音更把我的魂都敲了出來。
歌仔戲台搭建在馬路的另一邊,面對著土坡上的廟宇。
走過馬路的時候,我碰到一個似乎在學校裡看過的學生。
我問他這裡怎麼這麼熱鬧,是不是海水浴場的計畫通過了。
那低年級學生被我問得一頭霧水,謙遜地對我說,他甚麼都不知道。
戲臺上已經站了好幾排角色。
站在最後一排的,位置高,官位也高。
站在中央的那個人,面龐特大,我好像在哪裡看過,也許在國畫裡,或者舊曆年貼在門口的壁畫裡。
原來這種人物的臉並不是刻意被放大的。
他只是吃得胖,又戴上那種活像一盆花的帽子,臉孔看起來比旁人大了許多。
站在他前頭的那個人,明明是個女性裝扮的,卻穿著官服,頭上還戴著形狀像蒸汽火車頭的帽子。
在她的前排站了更多的人。
他們穿著最華麗,動作最誇張,偏偏身份最卑微,你只要看當中的一個老頭就明白。
那老頭也是女性裝扮的,眼簾上畫著好濃的眼影,頭上卻頂了個跟臉蛋毫不相稱的帽子。
我在人群中找到宋正平的弟弟。
這沒名字的小孩,大家都只叫他老五,不知有何本事,居然鑽到了戲臺的前頭。
觀眾把目光都放在戲臺上,沒有人注意到他緊貼著戲臺,巴望著台上的人。
好像他站在果樹下,看著那些從樹枝垂下卻搆不著的果子。
台上的演員,儘管有那麼多人在看他們,包括台下的那個老五,卻表現得完全無動於衷的模樣,就像我們的老師,在校長陪伴督學來巡視的時候,也表現得若無其事的樣子。
我朝老五站著的地方移去。
觀眾太多了,在人群中移動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容易。
移動的當中,我看到一個老先生,頭髮已經花白,獨自一個人坐在木凳上。
他側著身子,一動也不動地看著戲臺,連臉上的皺紋也不動,好像他從年輕的時候就坐在那裡,欣賞著這齣戲。
這讓你覺得,戲臺上演出的戲就是古人演的,就像這世界在你出生以前就已經是這個樣子。
我好不容易挨到老五身邊。
他看到我卻不理會我,像是給震耳欲聾的鑼鼓敲傻了。
我從來沒有站得離戲臺這麼近,可以清楚地看到敲鑼打鼓的師傅。
沒看到他們以前,我總認為只要演員發出動作,鑼鼓聲便會自動出現,就像村裡的小孩學著戲子比劃,嘴裡會自動發出「罄鏘、罄鏘」的聲音,又像電影裡的主角講到激動時,抒情的音樂也會自然出現。
看到這些聲音都是師傅弄出的,我不禁開始懷疑,到底是甚麼人跟著甚麼人?
是戲子跟著師傅,還是師傅跟著戲子?
雖然看起來,好像誰都沒有跟著誰。
好像各人只是在做各人的事。
特別是那兩個師傅,好像並不熱衷台上的表演;
輪到他們休息時,立即表現得像洩了氣的皮球。
我不想逗留在臺前太久。
我的鼻子裡仍然聞得到烤香腸的味道,陽光依然照在我的臉上。
我沿著戲臺邊緣慢慢地走到後台去,我估計從那裡走才能繞出人群。
戲臺的聲音很快變小了,好像你走到飯店後面的廁所,顧客講話和划拳的聲音立即變小了,代替的是洗碗筷的聲音,和爐火裡發出的「噗噗噗」的聲音。
我走到戲臺的正後方,那兒完全是靜謐的,靜得有些讓人害怕。
我走上土坡上的小路,聽到一隻鳥振翅飛走的聲音,意識到我可能壞了牠的好事。
我看到後台罩在像紗窗那樣的的網子裡。
有一個演員坐在幽暗的光線下,對著鏡子給自己化妝。
他絲毫不在意我的出現,也不在意自己的臉變成了古怪的模樣。
我看到堆在他身後的好幾個長方形的箱子,想到人們常講,歌仔戲的團員都是從鄉下拐來的小孩。
我的腦海裡出現那些個子都十分短小的演員,想像他們在箱子裡待過很長的時日。
我開始快步走離那個地方,直到我重新聽到喧嘩的鑼鼓聲,看到表情依舊的觀眾,看到老五依然呆呆地貼在戲臺前。
我不再羨慕老五所在的位置,也不想花力氣擠到那裡,警告他不要走到後台去。
我朝海灘的方向走去。
走過馬路以前,我看到我們班的張月妹,站在一個攤販的後面。
看到我走過去,她想躲到另一個女孩的身旁,可是來不及了。
年紀大的那個女孩問我要買甚麼。
她這麼做也許只是在為張月妹解圍。
這讓我不知道要說甚麼好。
我假裝審視她們所賣的東西。
那是一盆海螺絲,浸泡在混了醬油與辣椒的汁液裡。
我聞到那鹹鹹又辛辣的味道,發現我的唾液也察覺到那味道。
我問她們:
「聽說海水浴場的計畫通過了,妳們曉得嗎?
」
年紀大的女孩搖搖頭。
張月妹則做出若有所思的模樣。
「這對妳們的生意有甚麼影響?
」我繼續問。
年紀大的女孩朝張月妹看了一眼。
她們一齊笑了笑。
我看到張月妹面對我,便問她:
「你有沒有看到紀卓敏?
她又做出若有所思的模樣,然後搖搖頭。
「不知他到哪兒去了?
「好多天都沒看到他。
張月妹沒有回答我。
她跟年紀大的女孩開始談論歌仔戲。
有一位她們共同認識的人正在台上表演。
我沒有購買東西就跟她們道了別,彷彿尋找紀卓敏的事讓我無心在那兒逗留太久。
跨過馬路以後,我走到置放腳踏車的樹叢邊。
歌仔戲的喧鬧聲頓時減低了很多。
我突然感到若有所失。
在騎車回家的路上,歌仔戲的聲音離我越來越遠。
我看著座落在長岬上的那排老房子,這時正歇息在自己所製造的陰影裡。
房子的上方則是一片乾淨無雲的藍天。
這可是讀書的好時候,陳美松必定老早從午睡中甦醒,而且坐在窗前讀了好一陣子書。
我想到大家都畢業了,張月妹開始做事賺錢,說不定紀卓敏也找到事情做了。
只有我,這時卻一事無成。
■
重新想起這一天,我已經移民美國,輾轉遷移了好幾個城市,最後定居在南加州。
有一段日子,我固定開車經過一條濱海公路,去接就讀大學的女兒回家度週末。
我會駛過一個山坡,看到上面站立著一排有錢人家的房子。
我知道,站在這些房子的玻璃窗後,你可以看到蔚藍的海水,而行駛在馬路上的人則看不到它。
有一個黃昏,天氣特別陰暗,四處一片迷茫,開車需要特別小心。
當我駛入早已熟悉的彎道,依然看到那排房子站立在灰暗的山坡上,還看到其中的一個屋子提早點了燈。
駛過彎道以後,我突然領悟到,那排房子吸引我的並不是它的造型,也不是房主人的富裕,而是在某個難以判定的角度下看起來有點兒像陳美松家的那排房子。
這個發現在我的心頭埋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紀卓敏從台灣來拜訪我。
紀卓敏是來看望他的親戚,聽說我住在附近,主動打了個電話給我。
他看起來有一副精明商人的模樣,頭髮稀疏,小腹突起。
我猜我自己也變了樣,紀卓敏卻沒有明說。
我開車帶紀卓敏走過那條馬路,特意放慢了行車速度,最後乾脆把車子停在路肩。
我指出那排房子給紀卓敏看:
「它們像不像我們在沙灘所看到的房子?
」紀卓敏起初說:
「台灣哪有那麼漂亮的房子。
」接著又說:
「也許像吧。
可是我不確定,我已經很久沒去那裡。
我問紀卓敏,海水浴場究竟興建了沒。
紀卓敏反問: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那是你出國以後好幾年才興建的。
」我聽了很興奮,卻賣了個關子說:
「我可是消息靈通人士。
」紀卓敏突然省悟說:
「這是為什麼我很久沒去那裡了。
以前我們常去的那塊地現在是海水浴場的一部份,上面還蓋了十多層的大樓。
「這樣,陳美松家窗前的景色豈不被破壞了。
」紀卓敏問:
「這跟陳美松有甚麼關係?
「難道你忘了,我們在那兒玩耍時,還擔心陳美松看到,會告我們一狀?
」紀卓敏想了一會兒,才說:
「不對,從陳美松家看不到那裡。
她家的房子向南,我們去的地方在北。
這消息對我有如晴天霹靂。
我再三向紀卓敏求證,有沒有搞錯海水浴場的位置。
他說:
「沒有錯,就是我們以前去的地方。
」我回應:
「可是,那時你自己說──」紀卓敏等我講下去,我卻改變了話題:
「你記不記得,那年聯考以前,有個歌仔戲在海邊上演。
你到底去看了沒?
」紀卓敏說:
「每年都有歌仔戲在那兒上演,我記不得這麼多了。
送走了紀卓敏,我心裡有說不出的失望。
我反覆咀嚼著我們之間的對話。
每想一遍,我眼中所出現的影像就變得更加黯淡。
我有一股衝動要拿起電話來,請紀卓敏幫忙打聽陳美松的下落。
我記得他曾經說,陳美松應該像我一樣住在美國。
然而我很快就打消這個念頭。
我知道,即使找到陳美松,也不可能帶給我任何補償。
有很長的一段時日,我刻意不去看山坡上的那排房子。
直到某個週末,我照例開車去接我的女兒。
如往常一樣,我直接從辦公室出發。
上了路,我才想到女兒曾經交代,那晚她有事不能回家。
我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又有一種突然得到自由的感覺。
我依舊把車子向前駛去。
這次我駛出公路,朝我所估計的方向開去。
路途很順利,我很快就找到那個山坡,不懂以前我怎麼沒嘗試這麼做。
車子開始駛入蜿蜒的坡路。
就在一個轉彎處,我看到期待中的大海。
那只是一片灰暗的大海,卻在我的心中激起興奮的漣漪。
我明白,這一切的一切只源於我自己的想像,因此也只有我自己能夠享受它所帶來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