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docx
《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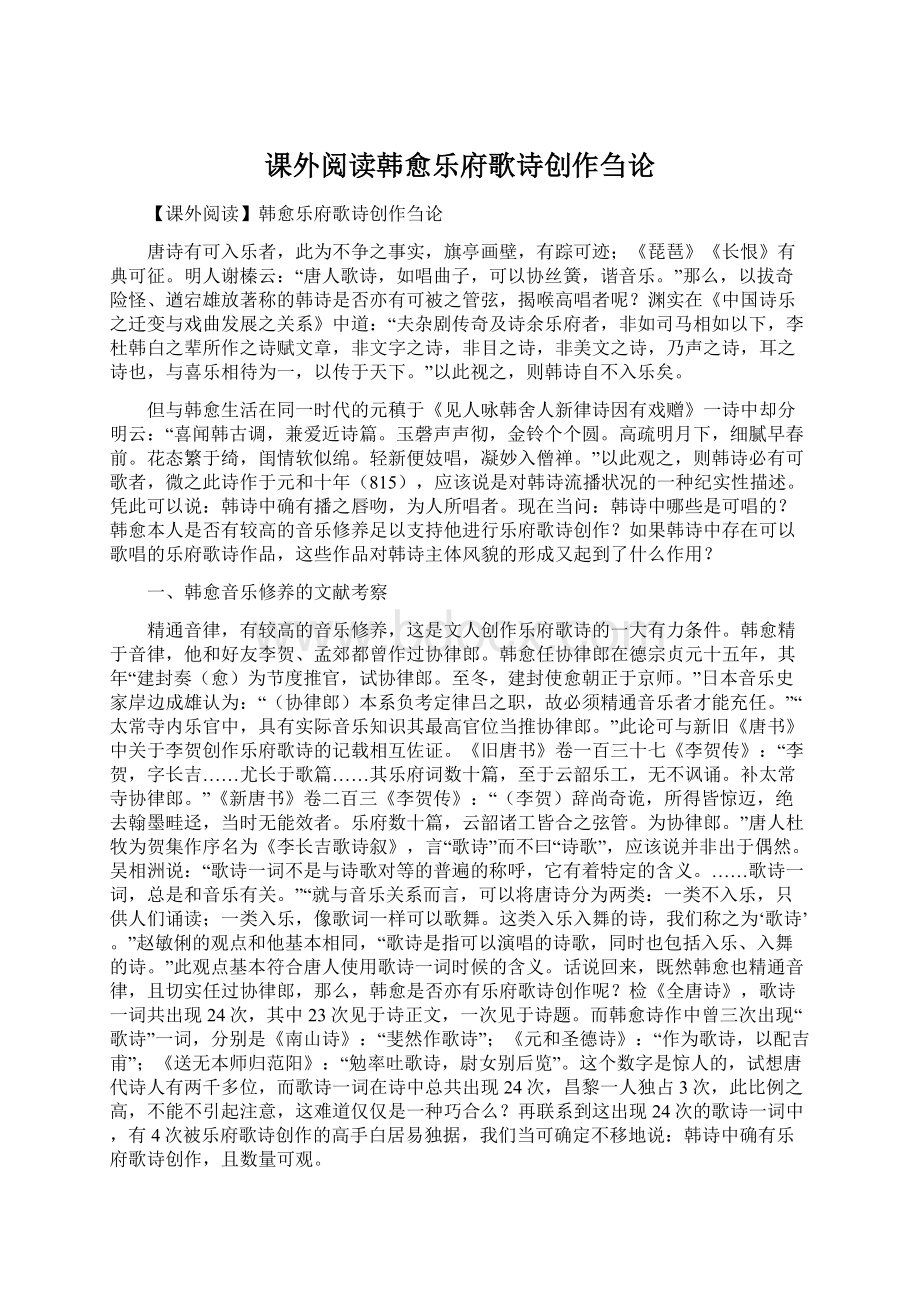
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
【课外阅读】韩愈乐府歌诗创作刍论
唐诗有可入乐者,此为不争之事实,旗亭画壁,有踪可迹;《琵琶》《长恨》有典可征。
明人谢榛云:
“唐人歌诗,如唱曲子,可以协丝簧,谐音乐。
”那么,以拔奇险怪、遒宕雄放著称的韩诗是否亦有可被之管弦,揭喉高唱者呢?
渊实在《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中道:
“夫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者,非如司马相如以下,李杜韩白之辈所作之诗赋文章,非文字之诗,非目之诗,非美文之诗,乃声之诗,耳之诗也,与喜乐相待为一,以传于天下。
”以此视之,则韩诗自不入乐矣。
但与韩愈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元稹于《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一诗中却分明云: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
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
高疏明月下,细腻早春前。
花态繁于绮,闺情软似绵。
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
”以此观之,则韩诗必有可歌者,微之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应该说是对韩诗流播状况的一种纪实性描述。
凭此可以说:
韩诗中确有播之唇吻,为人所唱者。
现在当问:
韩诗中哪些是可唱的?
韩愈本人是否有较高的音乐修养足以支持他进行乐府歌诗创作?
如果韩诗中存在可以歌唱的乐府歌诗作品,这些作品对韩诗主体风貌的形成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一、韩愈音乐修养的文献考察
精通音律,有较高的音乐修养,这是文人创作乐府歌诗的一大有力条件。
韩愈精于音律,他和好友李贺、孟郊都曾作过协律郎。
韩愈任协律郎在德宗贞元十五年,其年“建封奏(愈)为节度推官,试协律郎。
至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师。
”日本音乐史家岸边成雄认为:
“(协律郎)本系负考定律吕之职,故必须精通音乐者才能充任。
”“太常寺内乐官中,具有实际音乐知识其最高官位当推协律郎。
”此论可与新旧《唐书》中关于李贺创作乐府歌诗的记载相互佐证。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李贺传》:
“李贺,字长吉……尤长于歌篇……其乐府词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
补太常寺协律郎。
”《新唐书》卷二百三《李贺传》:
“(李贺)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
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
为协律郎。
”唐人杜牧为贺集作序名为《李长吉歌诗叙》,言“歌诗”而不曰“诗歌”,应该说并非出于偶然。
吴相洲说:
“歌诗一词不是与诗歌对等的普遍的称呼,它有着特定的含义。
……歌诗一词,总是和音乐有关。
”“就与音乐关系而言,可以将唐诗分为两类:
一类不入乐,只供人们诵读;一类入乐,像歌词一样可以歌舞。
这类入乐入舞的诗,我们称之为‘歌诗’。
”赵敏俐的观点和他基本相同,“歌诗是指可以演唱的诗歌,同时也包括入乐、入舞的诗。
”此观点基本符合唐人使用歌诗一词时候的含义。
话说回来,既然韩愈也精通音律,且切实任过协律郎,那么,韩愈是否亦有乐府歌诗创作呢?
检《全唐诗》,歌诗一词共出现24次,其中23次见于诗正文,一次见于诗题。
而韩愈诗作中曾三次出现“歌诗”一词,分别是《南山诗》:
“斐然作歌诗”;《元和圣德诗》:
“作为歌诗,以配吉甫”;《送无本师归范阳》:
“勉率吐歌诗,尉女别后览”。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试想唐代诗人有两千多位,而歌诗一词在诗中总共出现24次,昌黎一人独占3次,此比例之高,不能不引起注意,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么?
再联系到这出现24次的歌诗一词中,有4次被乐府歌诗创作的高手白居易独据,我们当可确定不移地说:
韩诗中确有乐府歌诗创作,且数量可观。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韩愈的音乐修养。
我们知道,中唐的元白是乐府歌诗创作的巨匠高手,他们创作乐府歌诗的目的在于“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尊”,也就是说要通过乐府歌诗的写作、传播来达到“闻至尊”,进而移风易俗的目的。
那么这其中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即元白,或者也包括一切乐府歌诗的创作者,当他们的作品尚未被朝廷乐府机构采录,被之管弦之时,这些乐府歌诗作品是可以唱的么?
鄙意认为,可唱与不可唱似仍有待于作者的音乐修养,就是说,如果诗人本身是精通音律,善于歌唱的话,其所作乐府歌诗便容易美听,即使不被诸管弦金石,也自然能够通过转喉发声歌唱出来。
不妨说,古人所说的善不善歌,实际上是说一种音乐素养,与今人所理解的能不能、会不会唱歌并无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在进入正式论证韩愈擅歌之前,先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古“歌”不与今“歌”同齿。
《汉书卷九十三》: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颜师古注:
乐人也。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
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
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而李夫人产昌邑王,延年繇是贵为协律都尉。
”由此不难看出,古所谓善歌,实际上是能够根据诗词语音的平仄清浊,通过发声的长短变化使一篇文字之诗词顿时生动起来,唱出来,而弦管所配合的应当就是歌者歌唱时候的调子。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只要想一想唐宋人对歌妓的倚重就自然通悟了。
所以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
”或曰:
汉时情状亦适合唐么?
回答是:
大体不差。
王灼云:
“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之云:
‘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
’自注云:
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
乐天亦醉戏诸妓云:
‘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
’又《闻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云:
‘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
’”于此可见,能歌,就能将一首文本状态存在的诗词,通过转喉发声来完成向其音乐形态——曲子——的过渡。
初唐诗人元兢《诗髓脑》之《调声》云:
“声有五声,角徵宫商羽也。
分于文字四声,平上去入也。
宫商为平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角为入声。
”既然文字的平上去入与音律的宫商角徵羽之间存在着这种对应关系,那么所谓善歌者,必是精通此道,可以将静态的“文本”激活为流动的“曲子”,这是对古代所谓善歌、能歌等词语的应有理解。
韩愈善歌,有典可征。
韩门弟子皇甫湜《韩文公墓铭》有云:
“(韩愈)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食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
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
”昌黎《送陆歙州诗序》有云“于是昌黎韩愈道愿留者之心泄其思,作诗曰:
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陆君之去兮,谁与翱翔?
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胡不为留?
我作此诗,歌于逵道;无疾其躯,天子有诏。
”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未几,果有以韦侯所为十二诗遗余者,……读而歌咏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
《荆潭唱和诗序》“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巨者也。
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
”
《送李愿归盘谷序》:
“昌黎韩愈闻其言而壮之,与之酒而为之歌曰:
……。
”如果说,第一例尚有强辩的余地,即以“歌”为歌别人已经唱过的诗词,那么,后举四例则显是在说昌黎本人能歌,或取他人之诗以歌之,或于筵间饯别之际,当场为诗并歌之,联系到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之“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则韩愈为诗且自歌之情境岂不栩栩生动?
再,韩诗中有许多篇章在涉及到“歌”字的时候都是在说这首诗作本身或者明显就是“歌唱”的意思(详后)。
另外,关于皇甫湜文中提到的“啸歌”一语,宋人郑樵《通志二十略·正声序论》有云:
“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
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
”⑤今之论者或认为“所谓啸,乃是古人的一种特殊习尚,……啸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以及文人生活的结合,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⑥“啸歌就是以啸声对歌的曲调进行模拟。
”⑦执此以观皇甫之文,则一个雅善啸歌的昌黎形象顷刻凸显生动起来。
以上对昌黎精通音乐的索探可证其确实具有创作乐府歌诗的先决因素。
二、韩愈的乐府歌诗创作
虽然已经能够确证韩愈是精音律通歌啸的,但是由于韩诗中除了前举三首明确标识“歌诗”外,余皆未有显著标识,所以要区辨韩诗中的乐府歌诗之作并述论其意义和成就,仍需借助相关文献来认证韩诗中的作品哪些是可歌的。
依据相关文献来认证韩诗中的乐府歌诗,除了有坚确内证者(如前举三首诗在内容中明确显示是“歌诗”)可定其为乐府歌诗之外,还应从诗题、诗体的角度对韩诗中的乐府歌诗进行区辨、判析,这就需要还原唐人的乐府歌诗观念,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明确唐人在诗题、诗体中所提示的此诗是否可歌可唱的信息。
与韩愈同时而年龄稍小的元稹作有一篇著名的《乐府古题序》,其文有云: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
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旨。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
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
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
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甿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
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
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
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
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
”
上引文献中,元稹将“诗之流”分为两个大类,一类是“在音声者”,这一类“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包括八种,即操、引、谣、讴、歌、曲、词、调,其特点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词以配乐也”;一类是“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者,包括九种,即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其功用是“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
也就是说古乐府以两种形态存在,一种是先有了乐曲,随后配之以词;一种是先有了词,再与弦管和之。
但无论是播诸金石的第一类,还是处于准备状态的第二类,它们都具有可歌性应是无疑的。
对此,宋郑樵《通志二十略·正声序论》云:
“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
歌行主声,二体主文。
诗为声也,不为文也。
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
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
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也。
诗者乐章也,或形之歌咏,或散之律吕,各随所主而命。
主于人之歌者,则有行、有曲;主于丝竹之音者,则有引、有操、有吟、有弄。
各有调以主之,摄其音谓之调,总其调亦谓之曲。
凡歌、行虽主人声,其中调者皆可以被之丝竹。
凡引、操、吟、弄虽主丝竹,其有辞者皆可以形之歌咏。
盖主于人声者,有声必有辞,主于丝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辞,其有辞者,通可歌也。
”若依元稹之标准则可将韩诗中在当时可以被之管弦供人传唱着缕析如左。
首先来看元稹所说的第一类,即操、引、谣、讴、歌、曲、词、调,这八种。
1.题目中明确标明“歌”字样的有:
《芍药歌》(德宗贞元元年)、《苦寒歌》(贞元十一年)、《夜歌》(贞元十八年)、《短登檠歌》(宪宗元和元年)、《和虞部卢四汀酬翰林钱七徽赤藤杖歌》(元和四年)、《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元和六年)、《石鼓歌》(元和六年)、《大行皇太后挽歌词三首》(元和十一年)、《梁国惠康公主挽歌二首》(元和十一年)、另外,韩诗《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尽管没有明确标明是“歌”,但是张建封却有和作名为《酬韩校书愈打毬歌》,可见韩诗仍然是“歌”。
2.题目中明确标明“操”字样的有:
《琴操十首》(元和十四年),即《将归操》、《猗阑操》、《龟山操》、《越裳操》、《拘幽操》、《岐山操》、《履霜操》、《雉朝飞操》、《别鹄操》、《残形操》。
其次来看元稹所说的第二类,即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
1:
题目中明确标明“行”字样的有:
《嗟哉董生行》(贞元十五年)、《丰陵行》(元和元年)、《南山有高树行赠李宗闵》(穆宗长庆元年)、《猛虎行》(长庆元年)、《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元和十一年)、《永贞行》(顺宗永贞元年)、《忆昨行和张十一》(元和元年)、《三星行》(元和二年)、《剥啄行》(元和二年)、《鸣雁行》(贞元十四年)。
2:
题目中明确标明“诗”字样的有:
《南山诗》(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