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吓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Word文档格式.docx
《惊吓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惊吓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中国民商法律网Word文档格式.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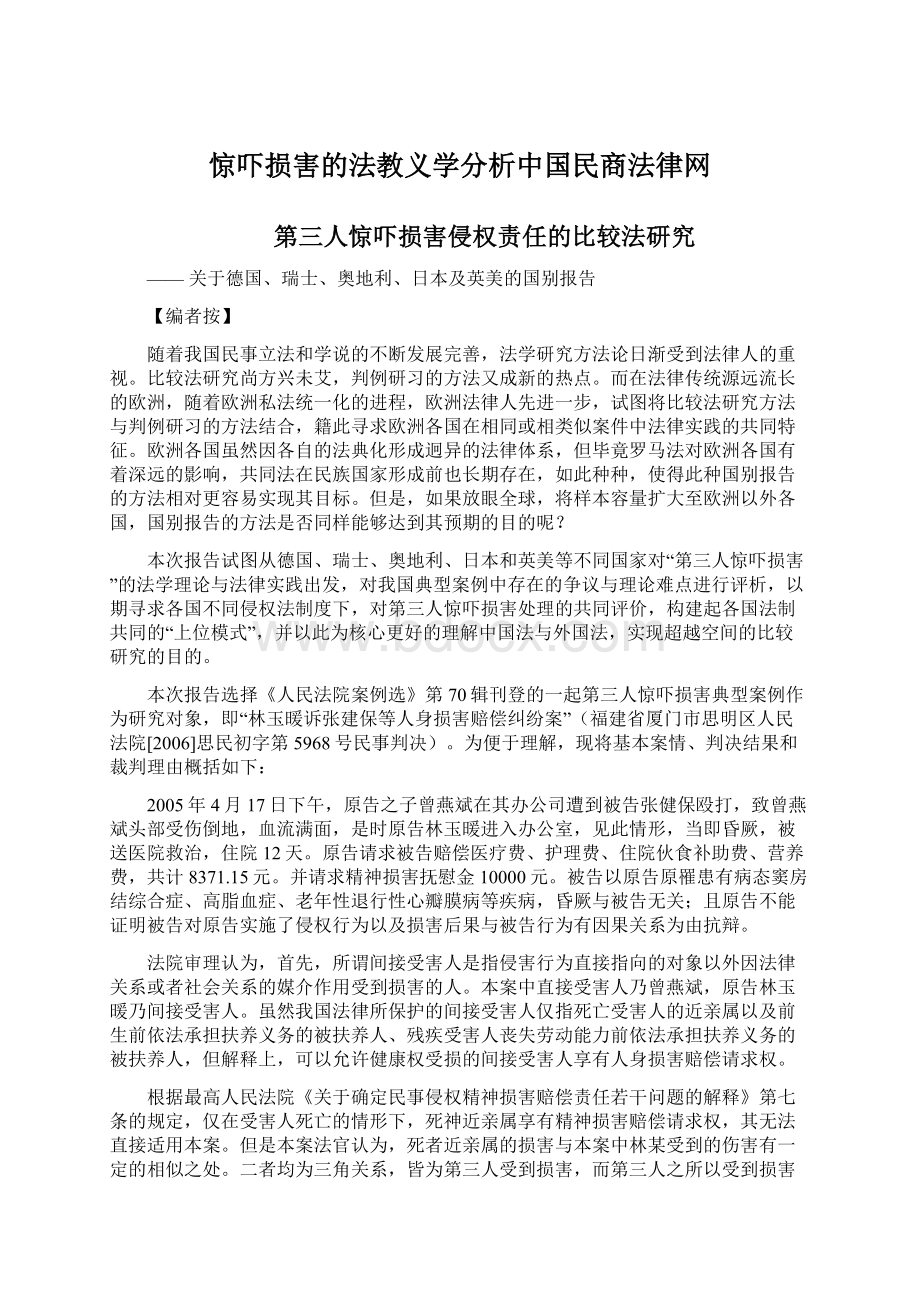
但是本案法官认为,死者近亲属的损害与本案中林某受到的伤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二者均为三角关系,皆为第三人受到损害,而第三人之所以受到损害,是基于其与死者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
而且不管是死亡还是伤残,受害人亲属精神上均受到极大痛苦。
因此,此时在伤残情况下可以通过扩张性法律解释的方法适用我国关于死者近亲属损害赔偿权的规定。
至于近亲属在此类案件中受到的损害与侵权行为存在多大程度上的关系,则需综合考虑。
其次,原告由于自身原患有疾病是为主要原因,目睹儿子受伤是为外因,因此,被告应承担原告损失的20%,计1554.23元。
另外,原告目睹儿子血流满面,精神必定痛苦,有抚慰之必要,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张建保支付原告人身损害赔偿金1554.23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
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
——基于德国民法的理论与实务的比较法考察
朱晓喆
目录
一、从外部体系透视惊吓损害在德国民法上的定位
1、间接受害人?
2、健康损害、惊吓损害与第三人惊吓损害
3、第三人之精神痛苦金请求权
4、小结
二、第三人惊吓损害侵权责任的结构检验
1、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该当性
(1)法益侵害
(2)受害人
(3)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
(一):
等值性理论
(4)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
(二):
从相当性理论到法规保护目的
2、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违法性
3、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有责性
(1)损害的范围及精神痛苦金
(2)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3)过错相抵
4、第三人惊吓侵权的损害赔偿
三、我国民法上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请求权基础
侵权行为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受害人的损害填补,俾使其恢复到受害之前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亦须恰当划定损害赔偿的界限,不过分限制加害人在人身和经济方面的发展空间。
因此,侵权行为法须协调“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本专题所讨论的案例“林玉暖诉张健保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以下简称“林玉暖案”)所蕴含的“第三人惊吓损害”(Schockschä
denDritter)法律问题,突出地反映了上述侵权行为法的价值两难:
侵权事故间接地引发直接受害人以外第三人的损害,法律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但如果法律毫不区分地广泛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又将施予行为人过重的责任并有限制行为自由之嫌。
因此,如何平衡惊吓损害事件中加害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乃是各国侵权法理论与实践的重点与难点。
但我国学界迄今尚未有较为全面的德国民法学说和实务的介绍评析,为此,笔者将依据德国侵权法的结构,梳理第三人惊吓损害的体系位置及具体责任构成要件,在此基础上总结德国民法关于该问题的价值判断,最后通过比较法的视角,检讨我国民法原理和实务裁判的得失。
一、从外部体系透视第三人惊吓损害在德国民法上的定位
德国民法方法论将法律体系分为外部体系(ä
uß
eresSystem)与内部体系(inneresSystem)。
所谓外部体系,是以抽象概念为基础,建构一种对法律素材清晰而概括的表达和区分结构,这种体系对于法律判决的可预见性和法律安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与此相对,隐含在法律制度内部的统一而有序的价值原则和意义脉络,构成了法律的内部体系。
尽管近来很多德国学者倡导以内部体系思想纠正抽象概念体系的弊端,但外部体系的作用仍不可低估,因其指示个别概念和法律问题在整个体系中的应有位置,而且有助于辨识具体的案件事实涵摄于何种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熟悉(外部)体系的判断者能随即将事件划定范围,因为他能认识可得使用的规范所属的领域。
”基于此,对于本文拟解决的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案型而言,将其置于何种法律视角和法律规范下予以考察,最佳的切入方法是判定其在外部体系中的位置。
首先须讨论的是,惊吓损害的受害人是否为侵权行为的“间接受害人”,得依有关法律进行裁判。
以惊吓损害的典型案件为例,通常是直接受害人的人身受侵害,其近亲属目睹或听闻噩耗,精神上受刺激或受惊吓,从而自身发生健康损害。
正如“林玉暖案”的法院裁判理由指出:
“受到直接伤害的是原告之子,而原告作为母亲目睹儿子被殴致血流满面而昏厥,是间接受害人”,健康权受损的间接受害人可对加害人享有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
但德国民法理论对此存有不同观念。
尽管同一事件可能导致除直接受害人之外第三人的损害,但并非因该事件引起的、凡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均可请求赔偿;
准确地说,在违反契约义务时赔偿请求权人是契约相对人或受契约义务保护的第三人,在侵权行为中则是权益被侵害的受侵害人。
从《德国民法典》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BGB§
§
823,826)来看,立法者将人身损害的诉讼原告资格限于直接受害人(primä
reVerletzten),拒绝提供受害人的亲属针对第三人直接请求权。
但例外的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和第845条,因受害人死亡而负担丧葬费、或丧失抚养请求权、或失去受害人劳务的第三人(通常是受害人的近亲属或继承人),作为间接受害人对加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该请求权为间接受害人自身固有的请求权,因而上述条文可谓损害赔偿权利人的扩张。
可见,德国侵权法原则上不考虑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只在特别规定情况下允许第三人对加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
基于上述原理,德国学者法恩克尔(Fraenkel)指出,虽然第三人因目睹或听闻直接受害人遭受人身伤害,发生精神惊吓并致健康损害,但由《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和第845条的立法目的可见,立法者仅将第三人对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因此第三人就惊吓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教义学上根据。
但这种观点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摒弃。
权威的民法典评注书均认为,惊吓损害实质上是通过加害人对另一人(如近亲属)侵权行为的媒介而侵害到自己的健康(必须达到自身健康损害程度),因此惊吓损害根本不是“第三人损害”(Drittschaden),恰是受害人自身的法益损害,如其符合《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的构成要件,损害后果必须予以填补。
就此,拉伦茨适切指出,第三人通常遭受一般性经济损失(allgemeinerVermö
gensschaden),如其可得赔偿,将导致赔偿责任的无限扩大,应为法律所拒绝;
相反,在第三人惊吓损害,恰是受害人自身遭受第823条第一款意义上的“法益侵害”,第三人当然得为请求权人。
因此,惊吓损害不是赔偿权利人范围或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扩张问题。
事实上,德国法院向来认为惊吓损害的第三人是自身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
1931年9月21日帝国法院(RG)对首例惊吓损害作出判决,该案中一位母亲因听闻其女儿因车祸去世,虽然其未亲历现场,但已然发生健康损害,因而原告请求加害人损害赔偿,法院的判决理由指出:
间接损害是指某人自身并非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而是侵权行为在该人财产上的反射后果。
然而,就当下(惊吓损害)案件而言,原告因侵权行为而自身健康受到损害,其诉讼请求正是针对该健康损害。
在帝国法院的实践中,从未声称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列举的法益和权利,必须是被直接侵害的、而间接的侵害不足以构成(侵权行为)。
1971年5月11日德国联邦法院(BGH)在一起标志性的惊吓损害案件判决中接受帝国法院的观点并指出:
(民法典)立法者认同,在亲历或听闻事故时发生不寻常的“损伤性(traumatisch)”影响而导致自身身体或精神/心理(geistig/seelisch)的健康损害,则该人享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帝国法院(RGZ162,321)完全清楚,在惊吓损害中,涉及的问题是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法益受直接侵害(unmittelbareVerletzung),而并不是如同民法典第844条、第845条那般涉及间接损害的赔偿。
由上可见,在德国民法学理与实务上,第三人惊吓损害之所以被称为“第三人”或“间接受害人”,只是相对于第一受害人而言。
但其遭受的损害并非第844条、第845条意义上的“间接损害”,而是自身的身体健康所受损害。
德国学者施密特(R.Schmidt)指出:
将第三人惊吓损害称为间接损害,这种不准确的表述有时会引发混乱。
总之,按德国民法通说,第三人惊吓损害不可与第844条、第845条间接损害相提并论,二者不能作相同或类似评价。
德国民法中“损害”一词通常是指某种行为的责任后果及范围,准确地说“惊吓损害”问题的关键不是损害,而是“惊吓侵害”(Schockverletzung),即以惊吓方式侵害他人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法益。
但“惊吓损害”已被用来固定地描述这种特殊的侵权责任问题,而且侵害往往伴随着损害,因此按德国民法的习惯用语,仍称为“惊吓损害”。
惊吓损害须达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的侵害健康程度,才能予以损害赔偿。
“侵害健康”是指对人之内在生命过程(innerenLebensvorgä
nge)的功能损害,它并不取决于人之器官和躯体的完整性是否受损(虽然身体侵害常常导致健康损害)。
此外,健康损害包括身体的或心理的疾病状态,身体疾病须借助医学知识查明,而心理病态须借助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的认知。
后者虽然难以把握,但一般认为,如果人们对于事故、死亡等事件的惊恐、伤心、痛苦和情绪低落的反映,超出心理-社会(psycho-sozial)的正常程度,就存在心理健康损害。
“惊吓”(Schock,或休克)概念在医学上用来描述一种因某种事故而发生的急性循环障碍(akuteKreislaufstö
rung),其性质为短暂的,但也可能导致机体的损害。
法学上的界定与此不同,施密特指出:
惊吓是“一种突然对个人产生影响、与心理有关的外界事件造成的心理故障(psychischeStö
rung)或心理刺激(psychischeErregung)。
”在事故中受害人只要出现一种医学上可验明的身体上或/和心理上的反映,即构成“惊吓”。
因此,惊吓在法学上是指一种健康损害,而且侵权法对此并非广泛保护,仅对那些达到一定强度并持续一段时间的惊吓损害,才考虑损害赔偿的问题。
作为一种健康损害状态,惊吓损害普遍存在,且不限于第三人身上发生。
德国民法学理上,一般将惊吓损害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1)直接惊吓损害(unmittelbarePrimä
rschockschä
den)。
此种损害不需受害人的某种法益(如身体、健康、自由或所有权)损害作为媒介,而是受害人特殊的心理敏感性(psychischePrä
disposition)对损害事件的心理反映而产生。
例如,因烟花爆竹的爆炸声而引起惊恐,因顾客在饮食中发现异物而产生恶心(Ekelgefü
hl)和忧虑(Ä
ngstigung)、超市营业员怀疑顾客偷窃而对其大声呵斥或令其当众出丑,使顾客受惊吓,等等。
这些惊吓如请求损害赔偿,须达到明显的心理损害程度,且加害人之行为自由超出法律保护范围。
除此之外,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日常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惊吓,属于一般生活风险(allgemeinesLebensrisiko),如果一律予以损害赔偿,则个人的创造性将受阻滞。
(2)作为某种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
上述直接惊吓损害不以某种法益损害为前提,与此有别,当受害人因自身其他的某种法益受侵害后,随即导致该受害人的惊吓损害。
例如,受害人身体受伤出血因目睹鲜血而晕厥,即为侵害身体而引发惊吓损害。
此外,因财产权受侵害也可能导致惊吓损害,例如,入室行窃者突然惊醒沉睡中的屋主,或因自己的宠物猫、狗突然被伤害致死而精神上受刺激。
作为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与一般的法益损害后果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同。
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上认为,它本质上属于法益受侵害的损害后果范围,加害人原则上应予赔偿。
例如,因伤害事故导致脊椎严重受损(身体侵害),受害人因长期承受伤痛而演化成心理疾病,并丧失劳动能力。
德国联邦法院对此类侵权后果指出:
如果某人因过失引起他人身体或健康之损害,且在责任法上应由其负责,那么,其责任也及于由此所生之后续损害(Folgenschä
……对侵权行为所致心理(损害)后果的损害赔偿义务,并不必以器质性(损害)原因(organischeUrsache)为前提,毋宁说,只要如下这一点能够确定就足够了,即如果没有发生事故就不会产生这种心理上的损害后果。
此外,也不要求加害人对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后果(损害范围)必须预见。
由此可见,作为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比较容易认定其相当因果关系,从而计入损害赔偿范围。
此外,德国民法学说提出用“法规保护目的”来限制其责任范围。
例如,受害人因身体伤害所致皮肉血肿或青瘀,而发生神经衰弱(Nervenzusammenbruch),进而导致两星期不能工作。
因为这种轻微的身体损害不具有显著性,构成一般生活风险,不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所保护的利益范围。
再者,因物之所有权受侵害而发生惊吓损害后果虽然普遍存在,但也不属于第823条第一款的保护范围。
(3)第三人惊吓损害。
德国民法文献中经常讨论的惊吓损害案例,是受害人(第三人)因经历、目睹或听闻他人遭受死亡或重伤,从而引发其自身的健康损害。
德国民法理论上认为,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被认可,而是其界限在何处。
一般而言,第三人惊吓损害基本构成要件包括如下三方面:
(1)惊吓损害必须基于合理的诱因(verstä
ndlicheAnlass),即第三人现场经历或事后听闻亲近之人因事故而死亡或重伤。
如果事故仅造成身体轻伤害(如胳膊受伤)或物之损害(例如宠物狗死亡),或警察错误地通知其近亲属有犯罪嫌疑,均不产生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2)第三人所受损害超出正常承受的痛苦程度,构成健康损害。
如第三人尚未达到病理上须治疗的状态,单纯的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足以产生赔偿请求权。
(3)第三人原则上须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和子女)。
综上所述,惊吓损害是一种由心理原因引起的健康损害,包括直接惊吓损害、因法益受侵害引起的惊吓损害、第三人惊吓损害。
虽然三者都表现为受害人的健康损害,但其责任问题的侧重点不同:
第一种在于责任成立,第二种在于责任范围,第三种在于责任成立及责任范围。
第三人目睹或听闻亲人死亡或重伤而发生惊吓损害,有时仅表现出悲痛、哀伤、情绪低落等心理反应,尤其是近亲属死亡时的“丧亲之痛”(Trauerü
berdenVerlustvonAngehö
rigen),那么,第三人可否就这种“纯粹精神损害”请求赔偿痛苦金(Schmerzensgeld)呢?
在目前的德国民法中,这一诉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原因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按《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原第847条),精神损害痛苦金仅在身体、健康、自由或性自主受到侵害时,才可请求赔偿。
近亲属因亲人的死亡或重伤,虽然承受巨大的心理悲痛,但如其自身没有发生法益损害,仍将无从请求痛苦金。
其二,《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845条规定可赔偿的近亲属死亡的间接损害仅限于财产损失,并不包括精神损害痛苦金。
其三,在未有明确立法的前提下,法院自然也不甘冒“续造法律”的风险,主动填补法律漏洞。
就此,德国联邦法院认为,要求法院去衡量人的生命价值过于苛求,故而在判决中向来不支持这一诉讼请求。
相较于欧洲其他各国,德国显然属于落后状态。
例如,在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判例认可因亲人死亡或重伤所受之单纯悲痛可得赔偿。
葡萄牙和意大利将赔偿限于亲属的死亡。
英国、瑞士、希腊、波兰、荷兰等国家,以立法明确规定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
奥地利、瑞典虽然没有立法,但其最高法院近年来也逐渐认可。
通过比较可见,德国民法不保护近亲属死亡的纯粹精神痛苦,与欧洲各国的法律发展已经脱节。
德国学者极不满意这种法制状况,称德国几乎是最后一个不承认这种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家,这成为一个“时代错误”,甚至戏称德国为特立独行的“莫希干人”(Mohikaner)。
有鉴于此,近年来理论界对德国损害赔偿法的改革呼声日益增加,为克服死者近亲属不能请求纯粹精神损害痛苦金的弊端,大致有如下几种思路:
第一,近亲属作为继承人主张死者的精神损害痛苦金(BGB§
823,1922)。
即直接受害人在受伤至死亡持续一段时间,产生痛苦金请求权,并转移给继承人。
在1990年之前,因为痛苦金请求权具有高度人身性,除非以契约承认或发生诉讼系属,原则上不得让与和继承。
1990年之后立法者消除了这种限制,当事人未承认或未有诉讼主张,痛苦金请求权也可让与和继承,并可计入遗产之中。
但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
其一,死者的精神痛苦金很难认定,尤其在事故发生现场或在送医不久后即去世,受害人没有恢复意识状态,因此无从产生精神损害痛苦金。
其二,虽然死者的精神损害痛苦金请求权可以继承,但它毕竟不是抚慰近亲属本身的丧亲之痛。
第二,第三人惊吓损害可令加害人对死者近亲属承担金钱赔偿义务(包括精神痛苦金赔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死者遗属不赔偿精神痛苦金的法律不公。
在此基础上,法院可以放低惊吓损害的门槛条件,使近亲属更容易获得赔偿。
但目前德国司法实务掌握其构成要件还是比较严格,尤其是第三人须达到健康损害程度这一要件恰恰说明,用该制度作为近亲属纯粹精神损害的功能替代,正是其弊端所在。
德国学者克林格(Klinger)借用奥地利最高法院的一件判决理由来批评该制度的不公正:
对近亲属所受之纯粹的情感损害不予赔偿的法律状况,越来越令人不满。
痛苦是否伴随疾病而生,其界限经常存在问题。
因子女死亡而悲痛的遗属父母着实难以理解:
因为没有达到疾病状态,所以他们的痛苦金请求权被驳回,这属于他们自身应承担的一般性生活风险。
轻微的身体伤害,例如瘀伤或扭伤,立马产生精神痛苦金请求权,然而失去近亲所致的纯粹心理悲痛(bloß
eseelicheSchmerzen)——尽管这种痛苦通常会被强烈感受到——却不存在这样的请求权。
由此可见,德国学者也认为,丧亲之痛是比一般的身体伤痛更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法律对一个轻度的人身伤害都赋予痛苦金赔偿,反而对一项更为严重的精神痛苦却视而不见,这的确有违“同等事物同等对待”的正义理念,并有教条主义之嫌。
第三,最根本解决途径是承认近亲属在受害人死亡时,自身遭受纯粹精神痛苦,即使尚未达到健康损害程度,也可主张痛苦金请求权。
但因其欠缺请求权基础,故而学者建议以一般人格权作为近亲属纯粹精神损害痛苦金的请求权基础。
克林格主张,近亲属的精神利益主要体现在与死者的家庭联系之中,鉴于德国《基本法》第六条有保护婚姻和家庭的价值理念,司法实务围绕家庭利益形成一组一般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群,例如,母亲因医生误诊而导致孩子不当出生(wrongfulbirth)、因丢失精子致不能生育、破坏和阻止父亲与儿子建立联系,均得依一般人格权主张痛苦金请求权。
既然根据宪法产生的法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家庭计划不受侵犯,那么,同样地,法秩序也应保护家庭现有状态免受他人侵权行为的破坏,因此,在受害人死亡或重伤时,其近亲属得基于一般人格权请求精神痛苦金赔偿。
但以上建议尚未形成理论通说,亦未见诸司法实践。
由上可见,第三人惊吓损害在德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上,部分替代了死者近亲属丧亲之痛的损害赔偿功能。
但由于其构成要件过于严格,须以健康损害为前提,难以充分满足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
从积极意义来看,第三人惊吓损害不限于近亲属的死亡情形,而且包括重伤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这有利于受害人近亲属的利益保护。
以上我们将德国民法上的第三人惊吓损害置于间接受害人、惊吓损害和第三人精神痛苦金的框架内分别予以考察。
通过这种外部体系的认识,初步了解第三人惊吓损害的产生来源、损害形态、构成要件及制度功能。
由此明确,第三人惊吓损害并不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845条的间接损害赔偿问题,也不是直接产生第253条的精神损害痛苦金请求权。
作为一种惊吓损害的特殊形态,它在本质上是第823条第一款意义上的健康侵权行为。
第三人惊吓损害既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形态,下文拟就该侵权行为的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逐项进行检讨分析。
德国民法学理通常按三阶段理论(Dreistufigkeit)认定侵权责任的成立,即行为的该当性(Tatbestand)、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和有责性(Verantwortlichkeit);
如果侵权责任成立,继而考虑责任范围,即具体损害赔偿后果。
因为三阶段论有助于准确判明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能够实现法律的安定性和明晰性。
因而下文依此方法,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的侵害健康意义上,对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逐次分析检验。
侵权行为的该当性系指受害人存在法益侵害,且加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于此首先讨论法益侵害问题。
第三人因亲人死亡或重伤通常会遭受心理痛苦或精神打击,但并非都能成立侵权责任,只有那些造成第三人健康损害的情形才有可能产生责任。
虽然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均明确认可心理上影响也构成健康损害,但并非所有的第三人惊吓的心理后果都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