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内在张力文档格式.docx
《论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内在张力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内在张力文档格式.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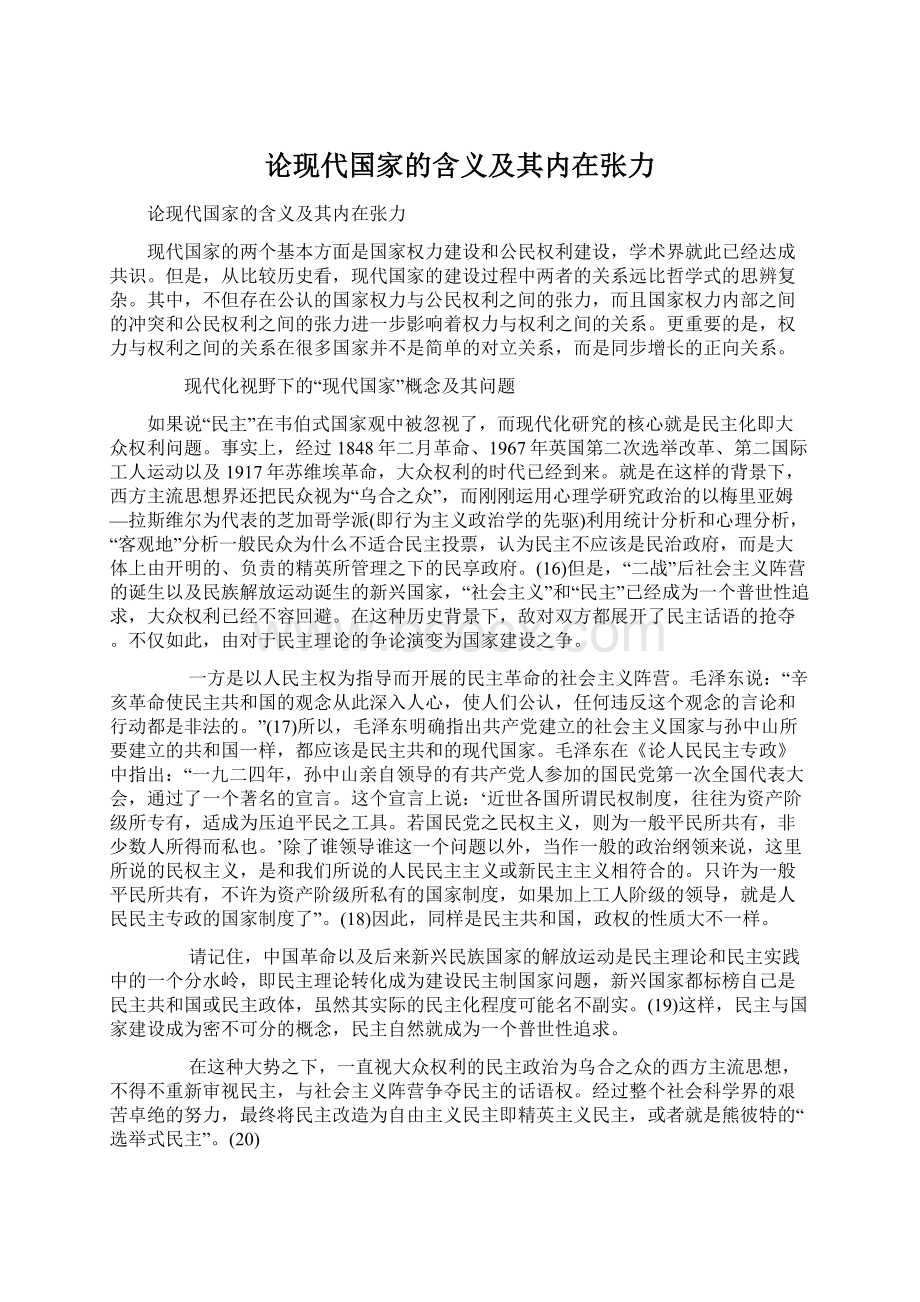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
这个宣言上说: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18)因此,同样是民主共和国,政权的性质大不一样。
请记住,中国革命以及后来新兴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是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中的一个分水岭,即民主理论转化成为建设民主制国家问题,新兴国家都标榜自己是民主共和国或民主政体,虽然其实际的民主化程度可能名不副实。
(19)这样,民主与国家建设成为密不可分的概念,民主自然就成为一个普世性追求。
在这种大势之下,一直视大众权利的民主政治为乌合之众的西方主流思想,不得不重新审视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民主的话语权。
经过整个社会科学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将民主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即精英主义民主,或者就是熊彼特的“选举式民主”。
(20)
这样,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即国家建构时,民主也就自然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变量。
沃德和拉斯托在《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中将现代化政治即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定位为“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虽然他们未必参与决策”。
在《政治发展的面面观》中,派伊认为政治发展过程中成功地处理了五种危机之后,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这五种危机是:
认同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性危机、参与性危机、整合性危机。
(21)参与性危机就是民主危机。
那么政治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呢?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基本方面:
权威的理性化、政治功能专门化以及广泛的政治参与。
在现代国家中,不管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公民已直接置身于各种政府事务中,并直接受其影响。
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或团体在超越村镇层次上参与政治,以及创立能够组织这种参与的新的政治制度(如政党、政治社团),是政治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22)
可见,西方学者关于建设现代国家的路径可能存在争论,但是都把民众的政治参与即民主定位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
有了这种共识,西方政治学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民主化问题而展开。
且不说政治哲学上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争论,在政治科学脉络中,比如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李普塞特的“发展带来民主”引起巨大的共鸣和争论。
(23)在政治文化研究中,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概念到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当下影响极大的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表达”,无不围绕民主化问题。
但是,民主权利只是公民权利的一种,难道有了民主权利,民众的所有民主都解决了吗?
或者说,是否有了民主,民众就安于现状了?
是否有了民主,国家建设问题就算完成了?
对此有清醒认识的要算亨廷顿了。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西方学术界憧憬于“发展带来民主”的乐观方程式时,亨廷顿一句发展导致“政治衰朽”给发展主义当头棒喝。
在亨廷顿等人看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秩序和经济发展问题。
笔者认为,当亨廷顿谈论经济优先还是民主优先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触及公民权利的不同部分,因为经济发展实现的就是公民权利中的民生权利或社会权利问题,只不过没有从公民权利理论着眼而已。
与亨廷顿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眼中的公民权利只有民主。
这种认识必然为现代化即国家建设问题带来误区。
当我们把T.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引入国家建设时,我们对国家建设中的权力与权利、权利的优先顺序无疑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从而有利于我们深化关于国家建设认识的复杂性。
社会学家马歇尔1949年提出“公民身份”概念包括公民的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公民的权利包括以自由、财产权和司法权等个人自由所必需的基础性权利,与之相对应的机构是法院。
(从历史阶段看,公民的权利主要是指自由基础上的财产权,因而也可以称为经济权利——作者注)政治权利是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相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
社会权利主要包括公民享有的经济福利与社会安全以及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与之相对应。
上述三种权利是分阶段实现的,并不是一蹴而就。
根据马歇尔的划分,从光荣革命到1823年天主教解放,英国实现了公民的基础性权利;
在之后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实现的是以1832年宪政改革和1867年宪政改革为标志的政治权利;
“二战”后集中于社会权利的实现。
(24)
可见,在英国为代表的早发达国家,其国家建设历程是分阶段的,是渐进的,是漫长的。
但是,现代化理论家似乎都忘却了自己的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即国家建设理解为民主化问题。
他们这样做既可能因为其遗忘自己的历史所致,也可能故意遮蔽自己的历史而为意识形态推动。
第三波民主化复兴了现代化理论,民主似乎是不期而至。
此时此景,批判乐观发展主义的亨廷顿也开创性地总结了民主的“第三波”,福山更是要为历史画上休止符,提出“历史的终结”即自由主义民主的全面胜利。
但是,到1990年代中期,鉴于民主衰败和索马里、阿富汗等失败国家的挑战,亨廷顿重回其著名的权威—秩序—发展论断,福山也开始谈“国家建构”问题,从国家力量强度、政府职权范围以及制度能力供给三个维度论证,国家建构比国家治理更重要,因为失败国家根本谈不上所谓的国家治理。
(25)不仅如此,福山今天又沿着其导师亨廷顿的道理大谈特谈“政治秩序诸起源”问题,认为现代政治秩序离不开三要素即强大的国家、国家对于法治的尊崇和全体公民对政府的问责。
(26)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福山还在《金融时报》(2011年7月12日)撰文,指出西方很难做中国现代化的老师。
在今天的福山看来,历史非但没有终结,新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在“现代国家”范畴内,作为公民权利的民主是重要的,但是同样重要的既有作为前提性的国家权力和权威秩序的确立,也还有公民的其他权利。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理清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内在张力
如前,国内外学者在论及现代国家时,主要在国家权力—公民权利的维度进行论证,甚至把公民权利简单理解为民主权利即政治权利。
我们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把问题大大简单化了,而理论上的简单化处理(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技术知识)势必影响到对实践性知识的认识,跟不上实践性知识,甚至以简单的技术性知识来衡量复杂的充满智慧的实践性知识。
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下,我们认为,国家建构中不但充满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还有权力内部之间的张力以及权利内部之间的张力。
权力内部之间的张力。
现代国家其实就是现代秩序问题,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将分散的封建化的权力集中于中央。
法国和德国是这样,其实英国何尝不是如此?
早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就解决了中央集权问题。
从光荣革命直至19世纪中期即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外实行的一直是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政策。
但是,英国对外宣传的却是世界主义的自由贸易。
这种行为被李斯特称为“踢掉梯子”,即踢掉成功走向现代国家的梯子以防别人模仿。
(26)美国呢?
《联邦党人文集》本身讨论的就是建构国家和国家集权问题,谈论的是制度供给问题。
但是,我们从基于英美经验的早期自由主义中似乎看不到国家的影子,国家被有意地淡化甚至去除了,留下的只是刻意建构起来的“社会契约下的自然权利”,即只是社会和个人的权利。
德国和法国的国家作用已经是常识,因为其道路的理论化中赤裸裸地标榜国家主义。
也就是说,所有的早发达国家在建构现代国家中依仗的都是强有力的国家权力。
20世纪是帝国解体的世纪,20世纪头20年,奥斯曼帝国、清王朝和沙皇俄国纷纷解体,而帝国的遗产便是一盘散沙,即国家没有官僚制这样的组织系统,国家失败了。
新的组织者即政党适时出现。
俄国、中国和印度等巨型国家都是依靠政党组织起来的。
这样,党国体制就是这些后来者绕不开的路径,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成为后来者绕不开的国家权力问题。
也就是说,在国家权力建制中,后发国家比早发达国家多出一重重大的横向权力关系。
对于早发达国家而言,只要建立好传统意义上的政体和官僚制就够了,但是后发国家还必须处理政党与政体、政党与官僚制的关系,而且作为国家组织者的政党就意味着是国家权力的源头。
在这种条件下,后发国家的国家建构就意味着一直有一个政党的位置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政党的安全问题。
这也就意味着,后发国家的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张力往往比早发达国家更加复杂,因为其中存在政党安全问题。
弄不好,政党失败也就是国家的失败,比如苏联。
后来国家尤其是后来的巨型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不仅存在横向权力关系上的复杂性,还有纵向权力关系的挑战。
这些巨型国家不但是因为其规模巨大,还因为其种族多元,不像早发达国家那样主要在单一的种族之上建设所谓的“民族国家”。
在多种族面前,所谓的合法垄断暴力看上去压制了民族自决诉求,但难以泯灭其潜在的自主性。
苏联解体就起源于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
今天,印度不时爆发出的恐怖主义活动也离不开民族矛盾,尽管实行的是代议制民主。
在中国,从2008年的西藏“3·
14”事件到2009年的乌鲁木齐“7·
5”事件,以及2011年春天内蒙古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都说明在多种族的巨型国家中建构现代国家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样,这些巨型国家的中央—地方关系带有种族矛盾性质,这种矛盾不是合法地暴力垄断和普遍性法律所能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国家认同”难题。
国家认同危机必然影响政权的合法性,并进而为处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平添一道屏障。
可见,后来的巨型国家尽管看上去已经构建了早发达国家一样的保障国家成立的强大的国家权力,但其现代化中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种族关系,以及由此而塑造的不同政治发展道路,决定着看上去强大的国家权力的脆弱性一面。
其中既有党国体制引发的政党安全问题,又有民族矛盾而可能导致的国家解体和国家失败问题。
国家权力的这些内在紧张关系意味着,在谈论中国这样巨型国家的国家建构时,并不简单地只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问题。
权利之间的张力。
虽然财产权等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是公民的权利,都是公民的福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冲突。
首先,三种权利的来源不一样。
如前,基础性权利对应的是法院,政治权利对应的是议会,社会权利对应的是公共服务体系。
这就意味着,实现这些权利的主体是不一样的,到来的方式也不一样。
抽象地说,所有这些权利都是上下博弈的产物。
具体而言,法院无疑是国家的象征,即只有国家这个第三方才能公正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没有任何其他政治机构能够胜任这样的职能。
从历史上看,国家对于这种权利的保障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议会对公民的开放在很大意义上是公民抗争的结果,尽管也有1867年英国宪政改革这样的保守党为自救而主动设计的权利开放。
公共服务体系基本上是国家的管理职能的应有之义,尽管社会权利的到来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的工人运动。
显然,对于国家或管理者而言,最愿意做的是提供基础性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保护,而不愿意开放国家权力,开放权力将直接威胁统治者的政治地位。
当然,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也有一个统治学习和治理学习的过程,比如社会权利一开始并不是传统理论上国家职权的应有之义,是在制度演化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国家职能。
这样,我们看到英国依次是基础性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美国也大致如此。
读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才能理解亨廷顿为什么说美国没有通过革命而实现的社会现代化即社会民主。
美国的社会民主是与生俱来的,但政治民主即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晚于基础性权利,19世纪30年代对大多数白人开放选举权,而黑人的权利直到1964年的《民权法案》才得到保障。
美国的社会权利实现得更晚,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到今天还没有建立起来,奥巴马的医保方案又被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大打折扣。
其次,不仅权利的实现主体和实现方式不一样,民众对不同的权利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从历史上看,富人最需要的首先是关于言论自由、人身保护尤其是财产保护的基础性权利,这是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提。
下层阶级最需要的是社会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哪怕再多的基础性权利和政治权利也不能根本性地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
政治权利对于富人和穷人是喜忧参半的东西。
当富人获得基础性权利而进一步壮大以后,他们无疑会寻求政治权利。
但是,富人毕竟是富人,当他们的政治权利满足以后就惧怕下层阶级的政治权利,因为下层阶级政治权利的到来会通过选举“合法地”剥夺富人的财产,会形成“社会暴政”。
因此,不同的权利对于不同的人群具有不同的意义,从而会形成权利实现过程中的冲突。
上述是英美发展历程的理论写照。
法国呢?
大革命一开始实现的就是政治权利即民主。
我们知道,当时的多数暴政下的滥杀无辜所导致的不但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侵害,也使得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对公民的基础性权利保护的制度和传统被颠覆。
(27)早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权利的实现不但关乎国家以及国家权力,更重要的是还有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
再次,国家建构的阶段性需求。
当国家权力建制完成以后,不同的公民权利很难在同一个时期内一步到位,前述的英美法都是这样。
但是,大多数现代化研究者所推崇的就是一步到位的政治权利,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完全不顾政治权利与其他公民权利的关系,只向后来者推销其长期演化而来的终端性的政治模式而不是政治发展过程。
很多后来国家因此陷于泥潭而不能有效地真正保障民生。
比如被称为发展中国家代议制民主典范的印度,多党制、代议制、公民组织等都很发达,公民利益表达自由,但是利益聚合即权威性政策形成过程却形成梗阻,大家公认的好的目标(比如改造贫民窟)永远得不到实现。
可见,哲学家眼中的公民权利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比较历史中的公民权利实现的过程,却显得无比复杂因而也无比漫长。
处理不好公民权利的实现秩序,反过来又会危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家权力建制,导致国家失败。
笔者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曾鼓吹“历史的终结”的福山转而又开始强调“国家建构”和“政治秩序起源”问题。
这更是我们的困惑,身处中国转型时期的我们时刻面对着无比强大的国家权力因而主张更多的公民政治权利,而公民政治权利一方面可能不是其他人群的优先需要而没得到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受到高强度支持的公民政治权利又面临特殊的党国体制、民族自决意识的考验。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只有在系统地考察并理解权力内部之间的张力以及公民权利之间的困惑以后,才能历史地在比较意义上更好地理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不能笼统地讲权力与权利的对立关系,这种判断是哲学的而非历史的,是革命性的而非研究性的。
即使将二者对立化的西方政治思想,也没有历史地客观地看到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
比如,基础性权利和社会权利都是国家的自主性诉求的结果。
即使对于政治权利,也是从少数人特权向多数人权利的普及化过程,其间国家权力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激进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成长,国家的力量强度和职权范围都是越来越大,其中重要原因是起源于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
因此,就早发达国家而言,总体上可以认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同步扩张同步增长的过程。
就后发国家而言,一般都是面临国家失败而出现的新政权和新型组织者,新政权主导商业组织的发展,最后才是社会组织的建构和发展。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作为现代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发达国家的同样规模的国家职能,否则就没有公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
另一方面,垄断权力的国家组织者面临着公民政治权利诉求的挑战,这既挑战着权力支配者的政治安全,也挑战着因多种族因素而可能影响的国家认同问题,从而使国家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对待公民权利。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化问题已经难以回避。
第三波民主化和2011年出现在中东北非的伊斯兰世界的“第四波”民主化都告诉我们,对于不少公民群体而言,他们不需要考虑政治权利对于国家建构到底意味着什么,重要的是政治权利的实现!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公民才能包容自己权利实现下的各种后果,因为好坏都是自己造成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印度老百姓对于一个月(2011年7月)出现4次火车事故致多人死亡而无动于衷,为什么在个别中国学者看来他们“安于”贫民窟现状。
最后,我们不得不想到政治发展研究关于后发国家的国家建构的判断,即后发国家面临的危机症候群(即国家认同危机、政治合法性危机、参与性危机、分配性危机和权力渗透性危机)不是一个接一个地依次到来,而是同时爆发。
这是后发国家的国家建设所面临的空前挑战,有的国家战胜挑战而成功转型,而很多国家则因这些挑战而处于转型危机甚至导致国家失败。
从历史上看,解决了公民的基础性权利和社会权利(渗透性危机和分配性危机)将有助于解决国家认同危机和政治合法性危机,而参与性危机的解决即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则既可能加剧合法性危机(政治转型),又可能刺激国家认同危机(国家分裂)。
国家不但有自己的安全需求,国家对于不同权利的秩序也是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性既可能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也可能因理性地回应民众的优先诉求所致。
这就有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
理想地说,这既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共同地、理性地、客观地分析公民诉求,有序地满足民众的不同诉求,最终渐进地和平地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
但是,现实地看,国家转型其实是诸多不同层次的“行动者”被相互冲突的观念矩阵和相互冲突的利益网络牵着鼻子走的过程,非预期结果总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