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重点Word格式.docx
《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重点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重点Word格式.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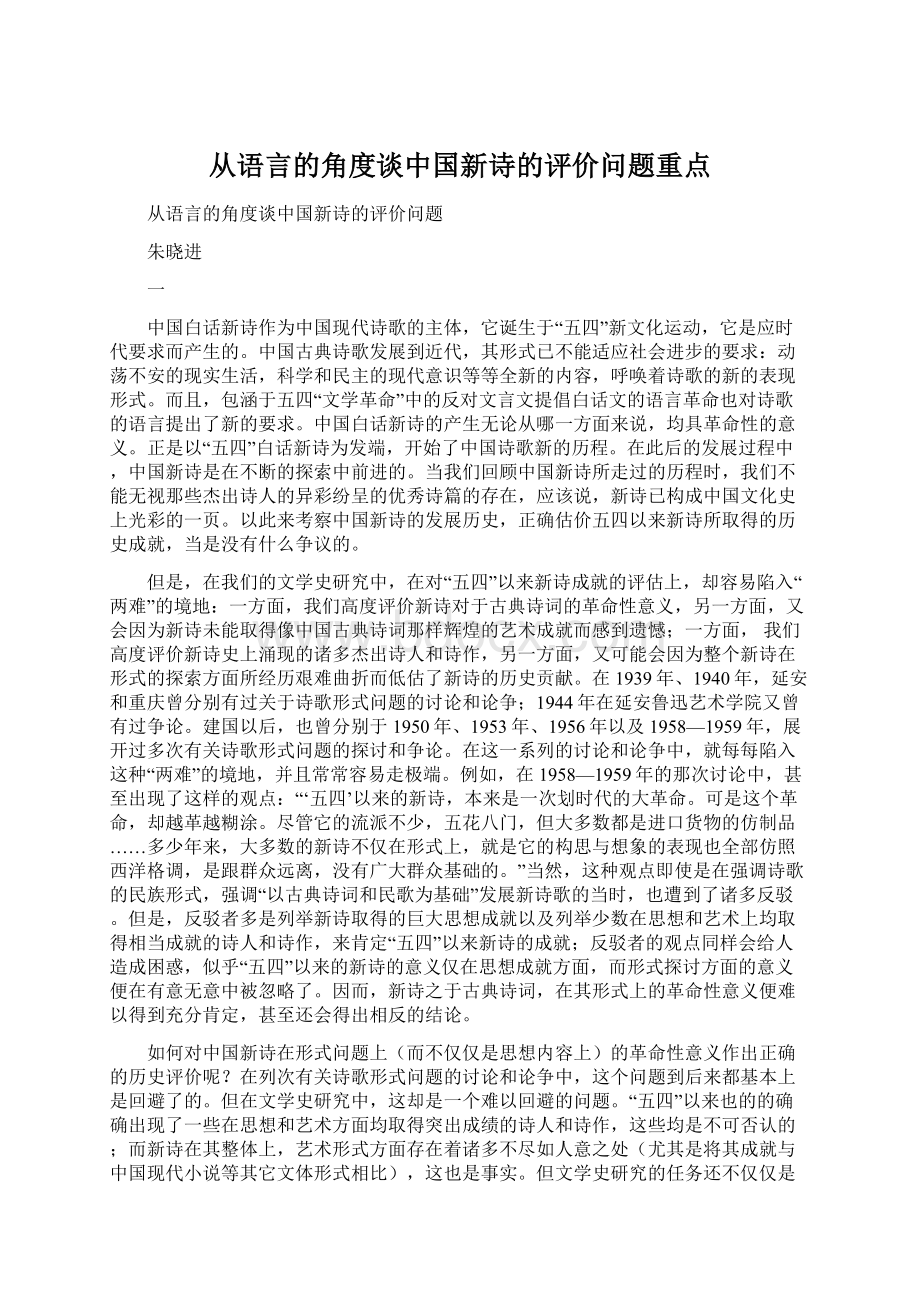
尽管它的流派不少,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都是进口货物的仿制品……多少年来,大多数的新诗不仅在形式上,就是它的构思与想象的表现也全部仿照西洋格调,是跟群众远离,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
”当然,这种观点即使是在强调诗歌的民族形式,强调“以古典诗词和民歌为基础”发展新诗歌的当时,也遭到了诸多反驳。
但是,反驳者多是列举新诗取得的巨大思想成就以及列举少数在思想和艺术上均取得相当成就的诗人和诗作,来肯定“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
反驳者的观点同样会给人造成困惑,似乎“五四”以来的新诗的意义仅在思想成就方面,而形式探讨方面的意义便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
因而,新诗之于古典诗词,在其形式上的革命性意义便难以得到充分肯定,甚至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如何对中国新诗在形式问题上(而不仅仅是思想内容上)的革命性意义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呢?
在列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和论争中,这个问题到后来都基本上是回避了的。
但在文学史研究中,这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五四”以来也的的确确出现了一些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均取得突出成绩的诗人和诗作,这些均是不可否认的;
而新诗在其整体上,艺术形式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将其成就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其它文体形式相比),这也是事实。
但文学史研究的任务还不仅仅是满足于指出这些,同样重要的是,还必须对之作出解释,并从而对之作出历史的评价。
正视新诗形式上存在的问题与充分估价新诗形式所具的革命性意义,这二者并不矛盾,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二者之间某种必然联系。
何其芳曾经这样评价过新诗:
“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五四以来的新诗是‘破’得多,‘立’得少;
‘破’得很彻底,‘立’得很不够。
也曾有少数作者作了建立格律诗的努力,然而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有些问题,未能成功。
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恐怕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并不一定是道路迷失得太久”这段话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却可以看到一种思路:
在发展与曲折之间找寻某种必然的联系,这样既正视了新诗形式探索上的不成功之处,同时又不会简单否定这种不成功。
可惜的是,何其芳并未对“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展开论述,甚至没有对之作出含义上的解释。
因此,当何其芳在五十年代末的有关诗歌问题的讨论中提出这一看法时,并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
当然,分析新诗形式发展的“必要的曲折”,可以从许多方面入手,这不是一篇论文所能完成的任务。
因此,本文仅想选择一个侧面,从诗歌语言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
作这一角度的选择,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既然新诗产生于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重要内容的文学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这场语言革命对新诗形式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新诗是这场语言革命的产物,新诗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语言革命的后果。
二
发端于“五四”之初的白话文运动,是顺应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历史要求而兴起的。
在这场运动中,白话文的倡导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文言文为代表的旧语言文字具有模糊、含混、不精确等方面的弊端,认为这种不精确必然带来中国人思维的模糊。
在近代被看作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的演绎推论,是以概念的精确为前提的。
对于科学的思维,文言文所代表的中国语言文字算不上是一种完善的媒介。
出于文化进步的考虑,出于对中国传统语言所标示的思维方式与现代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焦虑,先驱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而提倡白话文的目的,正在于丰富中国语言的科学思维能力,使中国人“可以发表更明白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
”毫无疑问,这场语言革命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由旧向新转换,促进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中国新诗作为这场意义深远的语言革命的具体实践,其历史贡献是不言自明的。
语言革命的成果常常是必须依赖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来得到巩固的,因此,新诗的产生,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诗歌的发展自身。
“新诗从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中解放出来冲破了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打碎了旧的枷锁,复活了诗的生命。
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而新诗对代表着旧的语言方式的古典诗词的冲决,这对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新诗的产生,其历史贡献就不仅仅只属于诗歌这一具体的领域,而且是属于那场反对文言文提出倡白话文的语言革命乃至属于整体文化由旧向新的历史性转换的时代的。
然而,也无须讳言,中国语言也正是在这场革命中步入了“两难”的境地:
为了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语言必须追求精确性、界定性,但这又必须以丧失中国传统语言方式中固有的隐喻性、模糊性等带有文学色彩的风格为其代价;
而要保存中国语言方式中的被西方称之为“诗”的风格,则又难以使中国语言适应科学思维的要求。
“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在科学与文学之间的二难选择中,无疑是倾向于科学的,这与“五四”时期所面临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
当时以“文学”二字为标目的“文学革命”,其目的并不在于文学自身,不在文学的本体特性,而在于借用文学为整个文化革新和新文化的发展服务。
在“五四”时期的许多文化人眼中,科学与文学确实难以两全。
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一文中就曾把东、西文化的区别归结为“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天平倾斜于西方,倾斜于科学时,文学性自然地会受到忽略。
语言目的的选择正体现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趋向。
文学语言有着特殊的要求,如语义的多层次性、情绪性、含蓄性、感受性、暗示性等等。
这与科学语言的确相去甚远。
用J·
浮尔兹的话说就是:
“科学——就其字面意义而言,是不惜任何代价的精确,诗歌——则是不惜任凭代价的包揽”。
鲁迅在《诗歌之敌》一文中也曾指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于诗美也一点不懂的科学底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这里也暗示出“科学”与“诗美”的冲突。
由于“五四”时期过分强调语言的明确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文化在整体上的转换,但对文学界一具体领域而言,其损失也是不言自明的。
文化的整体性历史转换,似乎不得不以牺牲局部的文艺的本体特性为代价。
尤其是那些最具文学性的文学门类——例如诗歌——所受的损失要更大一些。
相比较而言,小说、杂文等文学门类要幸运一些:
语言的精确性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是玉成了以陈述为主要语言特征的小说(增加了叙事的清晰度)和以说理为其语言特征的杂文(增加了说理的逻辑性);
而以含蓄、寓义、多义、暗示、抒情为其语言特征的诗歌,则不能不受到不利方面的影响。
而且,即使在诗歌领域中,语言的精确化、理性化又使得叙事诗、哲理诗的境况要好于抒情诗。
诗人艾青曾经说过,“诗是借助于语言以表现比较集中的思想感情的艺术”。
因此,“无论诗人采取什么体裁写诗,都必须在语言上有两种加工:
一种是形象的加工,一种是声音的加工”。
所谓“形象的加工”,即是以形象、含蓄的语言创造出诗的意境和诗美。
抽象和直语,是“形象的加工”所忌避的。
诗歌语言一旦因过于明确而失去其含蓄,因界定性过强而失去暗示性,因抽象化而失去具体可感性,则意境和诗美便会受到极大影响而有所减色。
然而,白话作诗的难处也正在这里。
艾青曾指出,有些新诗“缺乏感情,语言也不和谐,也没有什么形象”;
他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选择和使用语言,也没有考虑到诗之作为艺术所必备的条件”,没有认识到“诗的语言比散文语言更纯粹、更集中、因而概括力更高,表现力更强,更能感动人。
”这里指出了诗歌缺乏感情、缺少形象的原因是在其语言使用上的失当,这是很有见地的。
但如果不追溯到新诗所使用的白话语言自身的不足,仅责备作诗者,似乎又有欠全面。
俞平伯曾说过,“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因为“他是赤裸裸的”,使诗成为“专说白话”而缺乏“诗美”,所以他认为“中国现行的白话,不是做诗的适宜的工具”,白话缺少诗的蕴含,“缺乏美术的培养”,“往往容易有干枯浅露的毛病”。
这倒可视为中的之语。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
许多新诗人却很热衷于写旧体诗。
诚如萧三所说,“许多一向写新诗的诗人,或则现在都有作起旧诗来了,或则在写新诗之余,间或写几首旧诗,而这很少的旧诗每每比他自己所写过的很多新诗好”。
即如鲁迅,他不仅所写旧诗数量远远超出新诗,而且就其艺术性而言,也是旧体诗精品偏多。
新诗史上首屈一指的郭沫若,出版于1938年的《战声集》中,就收入旧诗若干首,到了《蜩螗集》中,旧体诗词则已近半数,越到后来,郭沫若所作旧体诗词越发多起来,以至于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压倒他的新诗创作。
初期白话诗人康白情、沈尹默等在短期的新诗创作生涯之后,纷纷向旧体诗词回归。
白话文学家郁达夫,在诗歌创作方面主要也是以旧体诗词见长。
曾致力于新诗格律化,并取得了新诗创作杰出成就的闻一多,在废旧诗六年后,又“复理铅椠”,“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僵做旧诗”。
九叶诗人郑敏在从事新诗写作和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大半辈子之后,转而表示自己“崇尚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灵’”,“要重新从中挖掘出它真正的精神来”,也就是说,“她正回头走向中国古典诗词”。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诗人、作家们对于旧体诗的依恋,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臧克家的话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现象,他说:
“我个人认为,不精炼或不够精炼,确是新诗写作上的一个大问题。
新诗运用口语(所谓‘白话’)来写作,打破旧格律,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胜利成果之一。
……但运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语言)而不疏于松懈、散漫、噜苏,对于诗人来说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可是从‘五四’到目前,也有不少作品没能够顺利地通过这一关”。
似乎可以说,由于白话写诗这一关难以通过,才致使许多诗人产生了对旧体诗词的依恋。
萧三早在1939年就曾对此现象作过类似的解释,他认为,由于白话新诗未能很好地解决诗的形式和内蕴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许多的天才文人或非职业的诗人文人”,甚至“一向写新诗的诗人”,“遇有真情实感,想寄之于诗时,还是写旧诗,而且写得非常好”。
他认为鲁迅就是如此。
“你只要去读一读他伤悼柔石、殷夫几个青年作家惨死的诗,你会大大地深深地感动,你会想到柳亚子先生评鲁迅先生的诗所说的‘郁怒情深,兼而有之’这句话极其正确”。
诗歌的破与立,远较其它文学样式更为复杂。
鲁迅白话小说的成就一下子就超越了自己的文言小说(《怀旧》),而他写的新诗却很难说有哪一首超越了他自己那些脍炙人口的旧体诗,此中缘由,无疑可以从白话语言中找到。
卞之琳曾将新诗与旧体诗作过对比,他指出,“对中国古典诗歌稍有认识的人总以为诗的语言必须极其精炼,少用连接词,意象丰满而紧密,色泽层叠而浓谈入微,重暗示而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
凡此种种正是传统诗的一种必备的要素。
今日的新诗却普遍地缺乏这些特质。
反之,白话诗大都枝蔓、懒散,纵然不是满纸标语和滥调,也充斥着钝化、老化的比喻和象征”。
这里对白话诗的评价虽说是太严厉了些,但也的确是在比较之中揭示出了白话诗的或一症结。
趋向于精确化、理性化的白话,在诗的内蕴上的确逊于古典诗词的语言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白话便于精确地传达思想、分析和论证问题,但许多文言能表达的诗境,白话却是无法表达的,用白话写诗,很难保证新诗能像古典诗词那样蕴藉深厚。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思考,一大批现代诗人、作家才在欲寄情于诗歌时,往往选择旧体诗的形式。
三
诗歌语言的“加工”,除了“形象的加工”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声音的加工”。
所谓“声音的加工”,无非是利用“旋律”、“节奏”、“音韵”来造成“声音的变化,唤起读者情绪的共鸣,也就是以起伏变化的声音,引起读者心理的起伏变化”。
白话给这种“声音的加工”同样带来了困难。
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着中国新诗的大问题。
早在“五四”白话诗刚刚兴起时,作为白话新诗的首倡和最先尝试者的胡适,他那篇题为《谈新诗》的文章,虽然中心意旨是在谈新诗体的解放,但谈论的角度却不出“文的形式”。
为了给新诗正名,他竭力从“新诗的音节”(节:
顿挫、段落;
音:
声调、平仄、用韵)方面为新诗找立足的理由。
几乎是同时,俞平伯在《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一文中,为探讨“社会不能容纳新文艺”,新诗“不受欢迎”的“原故”时,也首先关注到了新诗的形式问题,认为“是因为新诗句法韵脚皆很自由,绝不适宜‘颠头播脑’、‘慷慨悲歌’的。
所以社会上很觉得他不是一个诗”。
这可以看出,在白话新诗初起之时,倡导者和尝试者们尽管力图打破格律,寻求诗体的彻底解放,但他们事实上却避不开诗歌的节调、音韵等形式问题,而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却遇到了麻烦。
可以说,这种麻烦是与用白话写诗相伴随而来的,而且一直在困扰着诗人和批评家们。
二十年代中期,新月派诸多诗人曾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倾注了很大气力,但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十年代,鲁迅又曾多次论及新诗的形式问题,他说:
“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
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
“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
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
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李广田、何其芳等人在四十年代又提出了与此相同的问题。
李广田说,在读有些新诗时,“时常为诗人觉得可惜”,为这些诗歌缺乏“更完美的形式”“更好的章法和句法”、“最好的格式与声调”而遗憾。
何其芳也指出,“中国的新诗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
他甚至表示:
“以前,我是主张自由诗的,因为那可以最自由地表达我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动摇了。
因为我感到今日中国的广大群众还不习惯于这种形式,不大容易接受这种形式。
而且自由诗的形式本身也有其弱点,最易流于散文化”。
。
以上诸多诗人、批评家对诗歌的节调、音韵等形式问题所作的理论探讨,以及其后四十、五十、六十年代文艺界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其实都正说明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在形式问题上所陷入的困境。
那么,中国新诗形式问题难以解决的症结在哪里呢?
我认为,鲁迅的话可谓是点到了要害:
“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
”既然新诗的形式问题大致上可具体化为节调和音韵问题,而白话押韵又不容易,那么以白话为工具作新诗就给形式的完善带来了某种先天的不利因素。
如果换种说法,就是“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一方面,未曾注意到新诗的艺术和原理一方面”,人们“注意的是‘白话’,不是‘诗’”。
因此新诗普遍缺乏“音节”,“读起来不顺口”,虽然“有人能把诗写得很整齐,例如十个字一行,八个字一行,但是读时仍无相当的抑扬顿挫”。
卞之琳也认为,用白话写成的诗,“撇开无法‘吟咏’(严格说是‘哼’,还不是‘唱’)这一点不谈,即使用朗诵的标准来衡量,在声音效果上当然远逊于古典诗词和民歌”。
他们道出了白话语言给新诗在“声音的加工”上带来的困难。
应该说,上述所提及的诗人和批评家们对于新诗存在的不足之处都是有一定的清醒认识的,甚至有不少人是看到了新诗所面临的困境与写新诗所采用的白话之间关系。
但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解决新诗存在的问题,需要时间和条件。
所谓时间者,是指郭沫若曾经说过的:
“新诗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而旧诗的历史却有三千多年。
把三十多年的成绩和三千多年的成绩对比,应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不应视作是在为新诗发展中留下的诸多遗憾找寻某种获得宽解和宽慰的理由,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均须有它必经的过程。
同时,白话新诗的发展也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过程:
新诗最初是作为“五四”初期的那场语言革命的一种实践出现的,它首要的任务似乎还不在自身艺术品性的完备,而在于助新的语言方式的确立,因此诗歌体式的解放、诗歌语言与白话口语的一致性等是当时最主要的要求。
在白话文的提倡者中,多数人都从事过白话诗的尝试,他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即如鲁迅所谓之“敲边鼓”者,而非做一个诗人,他们是为了向文言文挑战,示威,用以证明文言文之所长者白话文未必做不到。
总之,白话新诗的产生首先就是扮演了语言革命实践者和语言革命成果的巩固者的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应高度评价它的历史贡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白话语言已经得到普遍的确认,新的语言方式已经真正确立之后,新诗作为文学之一种,其自身的文体完善的要求亦应提到相应的重要位置上来。
当然,这也有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在这种转换到来之前,理应视为新诗“历史发展的必要的曲折”,而且这种“曲折”也仅仅是从文体完善的角色来说的。
除了“时间”问题上也还有一个“条件”的问题。
所谓条件者,是就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而言的。
关于客观条件问题,我们在下面要专门论及。
而主观条件,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指,新诗完成了在白话文运动中应承担的任务之后,写诗者必须在主观上相应地确立文体意识,重视诗歌语言的创制。
必须认识到如茅盾所说的:
“诗的语言”必须在一般语言的基础上“加工提炼使其更精萃,更富于形象性,更富于节奏美。
……为了适应诗的特殊性,诗的语言可以比散文(小说、戏剧等)作品的文学语言更多些加工,或者说,可以和口语的基本要素有较大的距离。
”也就是说,新诗在完成了助白话语言方式确立的任务之后,应该不再将“与口语保持一致”看作对自身的要求,从而使新诗的语言尽快完成对白话口语的升华。
的确,用白话写诗“对于诗人来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没有文体意识的自觉,没有对诗歌语言创制的明确认识,是很难“顺利通过这一关”的。
在中国新诗史上,有不少诗人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他们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这正是与他们对新诗歌语言创制的自觉意识分不开的。
例如臧克家,运用白话写诗却不疏于松懈、散漫、噜苏,很注意诗歌用语上的“炼字”,闻一多就曾以孟郊的“苦吟”来比喻臧克家诗歌语言推敲上的功力,由这种“炼字”,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内蕴和诗歌形式严整性。
再如艾青,他自觉追求诗歌语言“形象的加工”和“声音的加工”,他的诗歌特别注重意象和语境创造,因此,艾青的诗虽仍是自由体的,但却在诗的内蕴和诗的内在节奏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又如田间对独特的诗歌节奏的追求,李季对醇化了的民歌语言的采用等等。
在他们的探索中,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
但也无须讳言,多数的诗人是没有能够顺利通过白话语言作诗的这一关的。
这当然与其主观条件有关,但又不完全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这就涉及到客观条件的问题。
四
客观上的困难就是指客观条件的不成熟。
这种客观条件是多方面的,前面所述的时机问题、新诗产生之初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的问题,以及诗歌艺术探讨所必要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等等都属客观条件之列。
而作为客观条件,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
到底能为诗歌语言的创造提供多少可资借鉴的东西。
中国古典诗词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的诗歌形式规范,积累了无数约定俗成而又含蕴丰富的诗的语汇。
这使即使诗歌天才不太高的诗人也能据此写出像样的诗来。
这是白话诗所难以相比的。
用白话写诗,不仅不能像用文言写古典诗词那样,可以有现成的格律加以利用、有现成的典故可以征引,而且甚至对写诗时所用的白话的语言特性也缺少较深透的了解。
因为白话语言方式施行的时间太短,人们还来不及对白话语言的声音特性和语境特性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
诚如朱自清所说的“白话的传统太贫乏”。
由于白话传统的贫乏,带来了新诗找寻借鉴的困难:
“新诗的模型、声调、修辞、造句,都得重新草创,它的困难是比别种作品大得多。
”
新诗找寻借鉴的困难还不仅来自于白话传统的贫乏,而且还来自于外国诗翻译的困难。
新文学是受外国文学影响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小说、散文、戏剧的翻译相对容易,而诗歌在本质上是不可翻译的。
鲁迅曾反复指出,“翻译外国的诗歌也是一件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
“可惜翻译最不易,……即使以俄文改写俄文,尚且决不可能,更何况用了别一国的文字”。
茅盾也曾指出过,“任何民族的文学作品翻译为其他语文的时候,或多或少总不免要丧失它的民族风格。
比较接近的两种语言在互译时或者还能多保存一些,但译诗还是比译散文为难”。
这种翻译的不易,就使得新诗与其它新文学体裁相比,可资借鉴的方面更为缺少。
的确,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方面:
中国白话诗的传统太贫乏,小说、戏剧尚有一些白话传统,可是白话诗歌就几乎是白手起家了;
而外国诗的难以翻译,又使新诗不能像小说、散文、戏剧那样尽情地汲取异域的养分来发达自身。
这也许是新诗形式较之小说、散文、戏剧更难确立的又一原因。
事实上,诗歌的借鉴方面,不仅因翻译的困难而有诸多不便,而且诗歌在实质上也有对外来语种诗歌的不可仿效性。
“因为中文和外国文的构造不同”,因而在“音节”、“格调”等语言形式上根本不能“模仿”,“用中文写Sonnet永远写不像”。
这是新月社理论家梁实秋在新月社后期的认识。
他认为,中国的新诗模仿外国诗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一些“中文写的外国诗”,而中、外文构造的差异,使中国诗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外国诗实际上很难取得成功。
他主张,虽不必否认“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但在新诗方面,“在模仿外国诗的艺术的时候,我们还要创造新的合于中文的诗的格调”。
不知道梁实秋的这些认识是否包含了他对新月派“格律诗”主张的反思。
不满于自由体白话诗的过于散文化、过于直白浅露,提出建立新诗格律的要求,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
新月诗派是最早提倡新诗格律的,此后仍不断有提倡者出现,这可以视为文体意识自觉的表现。
但新月诗派“所主张的格律诗的形式为什么没有能够为更多的写诗的人所普遍采用”?
何其芳认为,这除了内容上的原因外,还有形式本身的原因,即他们的“格律诗的主张照顾中国的语言的特点不够,有些模仿外国的格律诗”。
很清楚,由于诗歌文体对于语言使用的特殊要求,使中国新诗在形式上甚至不可能象小说等文体那样走一条“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的向外国文学借鉴的道路。
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也多少隐伏了对新诗形式发展的不利因素。
新诗的成就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其它文体相比,其不能尽如人意之处相对明显,这种客观条件的不利也是原因之一。
由此,我们也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历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向古典诗词和民歌学习的议题总是反复被人提起,过可以视作为解决新诗找寻借鉴的难题所作的一种努力。
但这种学习最忌简单化。
就拿古典诗词的形式来说,它是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的完全适应于文言语言系统的东西,新诗向古典诗词学习并非对其形式的袭用,而应是通过研究和发现古典诗词形式与文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