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钵舍那第15讲广论卷十九文档格式.docx
《毗钵舍那第15讲广论卷十九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毗钵舍那第15讲广论卷十九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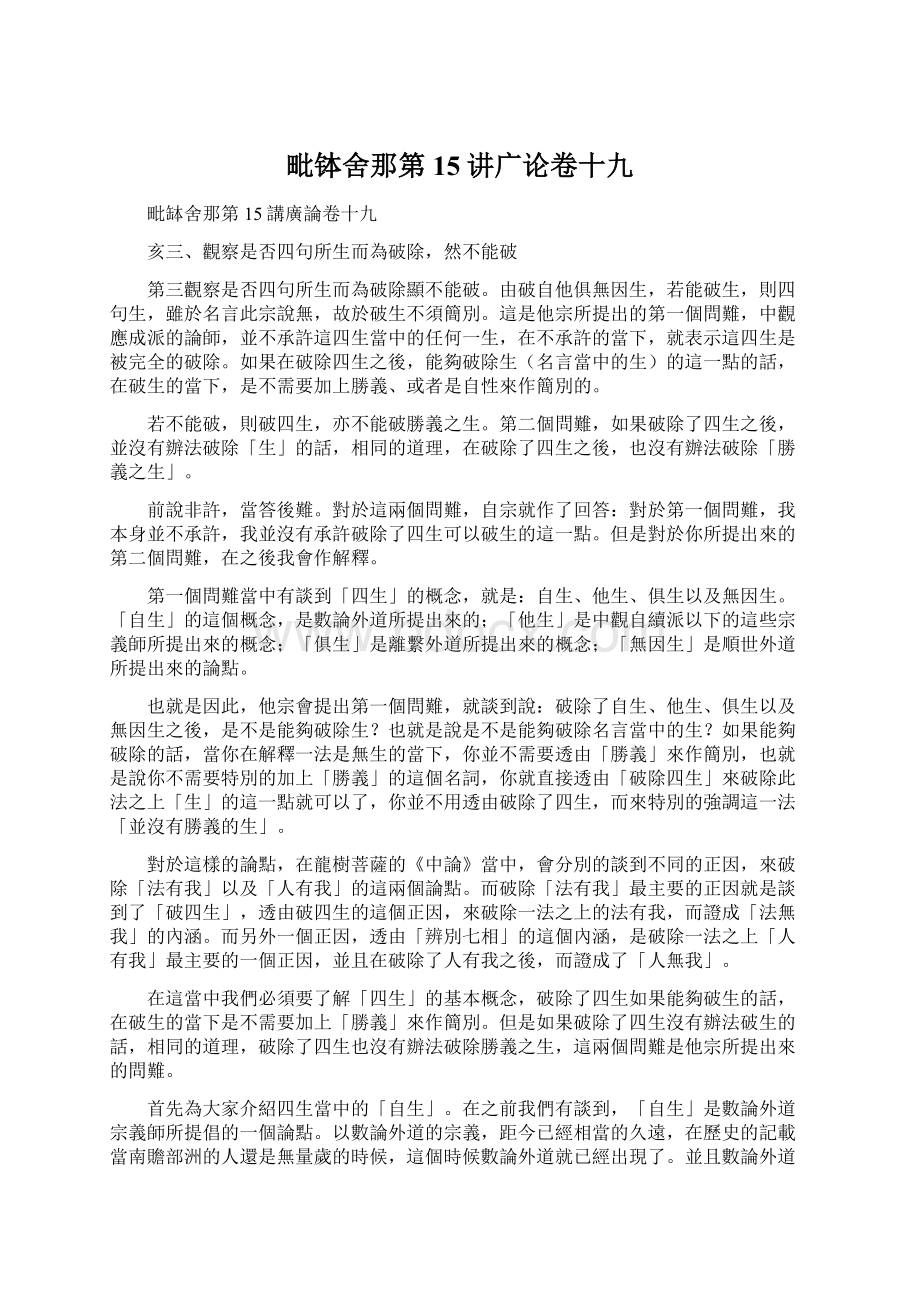
但是如果破除了四生沒有辦法破生的話,相同的道理,破除了四生也沒有辦法破除勝義之生,這兩個問難是他宗所提出來的問難。
首先為大家介紹四生當中的「自生」。
在之前我們有談到,「自生」是數論外道宗義師所提倡的一個論點。
以數論外道的宗義,距今已經相當的久遠,在歷史的記載當南贍部洲的人還是無量歲的時候,這個時候數論外道就已經出現了。
並且數論外道所闡釋的宗義,是一切外道宗義的根本、也是它的基礎。
一切外道的宗義,都是在數論外道的宗義之上而衍生出來的。
對於「自生」的這個內涵,以種子跟苗芽來作譬喻的話,我們都知道苗芽是從種子而產生的,也就是從種子會生起苗芽。
對於這樣的論點,數論外道他認為,在種子形成的當下,苗芽就已經形成了。
但是它形成的方式,是以不明顯的方式形成出來的。
甚至他更進一步的會談到,在種子形成的當下,「苗芽的自性」也在此同時形成,但是它本身並不明顯。
如果在種子形成的當下,苗芽沒有辦法形成的話,那我們怎麼能夠說,苗芽是從種子而生出來的呢?
這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以這種方式來解釋「自生」的這個概念。
第二個部分是談到了他生,「他生」是中觀自續派以下的論師所談到的一個論點。
以種子跟苗芽這兩者而言,我們都知道這兩者是相異的個體,苗芽雖然是從種子而生,但並不是說苗芽從種子而生的當下來闡釋所謂的「他生」,並不是透由其他的一法而產生的。
這當中的「他生」是更進一步的,它是由一個「有自性」的因而產生的。
對於這一點中觀應成的論師並不承許,雖然他也認為苗芽是從其他的個體(也就是種子)而產生的,但他認為苗芽從種子而產生的這一點,是完全皆由分別心去安立的。
(446“8)
若許勝義之生,須許堪忍觀真實性正理觀察。
爾時須以正理觀察自他等四從何句生?
由許勝義生,故定須許四句隨一觀察。
如果承許「生」它本身是有勝義的,在承許了勝義生之後,我們也必須要承許這一法在透由正理觀察之後,必須要能夠「堪忍正理觀察」。
因為境界它本身是有勝義、有真實的話,透由正理在觀察之後,它必須要能夠找到一個真實的境界,這一點叫做「堪忍正理觀察」。
如果一法它是勝義生的話,透由正理來觀察之後,它必須要能夠安立這一法是自生?
還是他生?
還是俱生?
還是無因生?
它必須要從這四生當中找到一個最究竟的答案。
所以得到的結論就是,如果你承許了「勝義生」的話,你就必須要更進一步的承許「我所承許的勝義生是四生當中的哪一生?
」因為這一點是透由正理觀察之後所得到的一個結論。
若僅受許依此因緣有此生起,未許實生,未許彼故,云何能以觀真實之理,觀從自他等何者而生?
如果你只是僅承許「透由因緣所生起的緣起法」,而你並沒有承許「這種由因生果的緣起法是有勝義、或者是有自性」的話,表示你並沒有承許「真實的生」、或者是「勝義的生」。
既然你在承許「生」的當下,並沒有承許真實生、或者是勝義生的話,那透由正理來作觀察之後,並不需要得到一個最究竟的結論,也就是「它是四生當中的哪一生?
」
以不須許堪忍正理所觀察故。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呢?
因為由因生果的「緣起生」,它是無法透由(就是無法堪忍)正理觀察的。
因為剛開始它在安立的時候,它就是在一種不簡擇、以及不追究的情況之下所安立出來的。
既然它是在不簡擇、並且不去探討、不去追究它究竟的本質之上而安立出來的話,透由正理來觀察,我們並沒有辦法找到一個真實的境。
所以由因生果的緣起生,是無法堪忍正理觀察的。
(446“11)
又依緣生,即能破除四句之生,入中論云:
「諸法依緣起,非分別能觀,故此緣起理,斷諸惡見網。
」不僅如此,透由由因生果的「因緣生」,是能夠破除四句生的,這一點在《入中論》當中就有談到:
外在的有為法是透由「緣起」而產生的,這種緣起法,透由觀察四生的分別心(或者是這種正理),是沒有辦法得到一個真實的結論。
因此透由緣起的道理,能夠斷除我們內心當中顛倒的執著。
故月稱論師,許依緣生破四句生,汝若許不從四句生則全無生,故違月稱所許而說。
因此從《入中論》當中的這一段文可以知道,月稱論師本身是承許「因緣生」能夠破除四句生。
但是你認為如果沒有辦法安立四句生(也就是破除了四句生之後),也會更進一步的破除了生,這與月稱菩薩他所提出來的「依緣生」能夠破除「四句生」這個理論是完全相違,而且一點關聯都沒有。
(446“13)
又彼論云:
「無因自在等,及從自他俱,非能生諸法,是故依緣生。
」「彼論」就是月稱菩薩所造的《入中論》,當中也有談到一個偈頌,在這偈頌裡面有探討到「無因自在等」,這當中的「無因」是談到了無因而生,「自在」是談到了果的形成是透由大自在天王所造作出來的,這是不相順的因緣而產生的。
並且更進一步的探討到自生、以及他生、以及俱生的內涵。
不管是無因、或者是大自在天,甚至自生、他生、俱生皆沒有辦法產生諸法。
既然法的形成,並不是透由四生當中任何的一生所形成的話,那法是如何的形成呢?
法的形成是必須要依賴著「因緣」才有辦法產生的。
如汝則成自語相違,故依緣而生之緣起,永離四邊,莫更問云:
離四邊者為四何邊?
對於月稱菩薩所提出來的這個論點,透由四生並沒有辦法生成一個果,既然透由四生沒有辦法生果的話,就表示「果」的形成是必須要觀待因緣的。
也就是因為它是「因緣生」,而推翻了四生的這個論點,但是你卻不這麼認為。
你認為推翻了四生之後,也必須要能夠推翻所謂的因緣生,因此你所提出來的論點,與月稱菩薩所主張的論點是有相違的。
從這當中我們就可以知道,「緣起法」它本身是遠離了四邊,對於遠離了四邊這一法而言,我們不需要再一次的去探討說,它是四邊當中的哪一邊?
因為它本身就已經遠離了四邊。
此等亦是未分自性無生、無生二者差別而成過失。
之所以會有以上所談到的這些過失,是因為沒有辦法仔細的去分辨,「自性無生」與「無生」這兩者之間的差別,而產生的過失。
四生裡面所謂的「他生」的這個概念,我們要稍微的釐清一下。
所謂的「他生」,是談到了「果」的形成是必須要依賴「有自性」、或者是「有自方」的因,才有辦法產生的這種論點,稱之為「他生」。
但實際上如果「果」的形成是依賴著「有自性的因」而產生的話,到最後果與因之間會變成相異(毫無關係)的這種特性。
比如以瓶子跟柱子,這兩者是相異的個體(並不是同樣的個體),瓶跟柱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我們稱這兩種個體是相異、並且沒有任何關係的個體。
如果「果」的形成是必須要依賴著「有自性的因」,才有辦法形成的話,推論到最後,它們這兩者也會變成如同瓶柱般是相異、而且沒有任何的關聯。
我們都知道「果」的形成是必須要觀待因、必須要依賴因,「因」從果的角度而言,它是「他者」,甚至在佛教的專有名詞當中,是談到這兩者是相異的。
但是不是代表果跟因之間,它所相異的內涵,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種相異呢?
並不是。
我們知道果跟因之間它是有關係的,果的形成是必須要觀待因。
平常我們講麥子跟麥苗,麥苗的形成是必須要觀待、甚至必須要依賴著麥子,它才有辦法形成。
所以這就表示麥苗與麥子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相異的,但是它是有關聯的,因為麥苗的形成,是必須要觀待麥子才有辦法形成。
但由於麥苗的形成,不需要觀待「米」的緣故,所以麥苗與米之間的關係是相異、但是是毫無關聯的。
也就是因為毫無關聯的緣故,麥苗並不會從米當中而產生,所以這當中我們可以知道,相異之間又可以分為是「有關聯」以及「無關聯」的這兩種方式。
但如果「果」的形成是必須要觀待著「有自性」、甚至是「獨立的因」,才有辦法形成的話,那到最後所形成的果、與形成的因之間,都是會有一種自性、獨立的這種情形發生,到最後這兩者之間會變成是「毫無關聯」,就有如同是瓶柱般,它們是不需要互相依賴就能夠形成的。
如果這樣的論點是成立的話,如果「果」的形成是可以透由「自性」的因而成立,甚至推論到最後,與它毫無關聯的一者能夠生起一果的話,那從光明當中應該也是能夠產生出黑暗的這種特性。
但實際上我們都知道,光明與黑暗它們兩者是相違、而且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黑暗是沒有辦法從光明當中現起來。
這個地方最主要是談到了「他生」的這個概念,所謂的「他生」就是在安立果的當下,果是必須透由「有自性的因」而產生的一種因果法則,我們在這個地方稱之為叫做他生。
(447“2)
云何論說:
「真實時若理,觀從自他生非理,以此理名言亦非理。
」這是他宗提出的一個問難:
如果自宗安立「生」的方式,是以之前所談到的論點來作安立的話,那你怎麼解釋《入中論》以下的這一段話?
如果透由觀察真實的正理去觀察之後,到最後我們可以知道自生、他生等四生法這是不合理的。
相同的道理,我們去觀察的話,在名言當中也並沒有辦法安立生。
此顯若許自相之生或實有生,則於名言由彼正理亦能破除,然非破生。
接下來自宗就作了解釋:
這段文最主要闡釋的內涵是談到,如果承許了生,它是自相之生、或是實有生的話,對於自相之生、或者是實有生,在名言當中透由觀察真實的正理在觀察之後,是有辦法破除的;
但是在破除自相之生、以及實有生的當下,並不是要破除「生」,而是透由正理在名言當中能夠破除「自相之生」、或者是「實有生」。
即彼論結合文云:
「若謂染淨之因須實體生,此說唯餘言說存在,何以故?
真實時等。
」這當中的「結合文」也就是連接上下文的一段文。
也就是在《入中論》的釋論當中,還沒有引這個偈頌之前有談到一段文。
「染」是染污,「淨」是清淨。
如果染污以及清淨之因,它本身是實體生的話,那安立實體生的當下,根本就沒有辦法在名言當中安立生的存在。
那你說「生」是存在、是有辦法安立的,這只不過是你說說罷了。
為什麼呢?
在以下所引的這段文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真實時等」。
廣引彼頌,其釋又云:
「故自相生,於二諦中皆悉非有,雖非樂欲亦當受許。
」也就是在引這個論典之後,而來證成了之前所談到的這個理論。
並且在《釋論》當中又再次的提到:
因此「自相生」從勝義、以及世俗的角度來作觀察的話,皆沒有辦法安立。
自性生在勝義以及世俗當中,皆沒有辦法安立的這一點,雖然你不想要承認,但你也不得不承認。
故自性生是勝義生,若許此者,雖名言許,如破勝義生而當破除。
因此自性生本身就是所謂的勝義生,如果你承許了自性生的話,雖然從你的角度會認為「名言當中的自性生」是有辦法安立的、「自性生」是存在的。
但就如同你會破除勝義生一般,自性生本身是勝義生,所以如同破除了勝義生之後,透由正理的觀察,自性生也應該要被破除。
是此論師所許勝處,故於名言亦不應許有自性生,入中論云:
「如石女兒自體生,真實中無世非有,如是諸法由自性,世間真實皆不生。
」這一點是中觀應成派的論師,他們所提出來的不共見解。
因此在名言當中,不僅僅「勝義生」是不存在的,「自性生」也是不存在的。
它在解釋這一句話的時候,是引了《入中論》當中的這一段文來證成說:
就如同石女兒是的自體生(它本身),以勝義的角度而言是沒有辦法安立的,而且以世俗的角度也是沒有辦法安立的。
如果色身等諸法它本身是有自性的話,以世間(也就是世俗)、或者是真實(也就是勝義)的角度而言,皆沒有辦法產生。
因此引了《入中論》當中的這一段文,來證成在名言當中「自性生」也是不存在的。
(447“8)
若執自性無生或無生自性,謂全無生,反難緣生與無自性生二者相違,呵為無耳無心。
以他宗的角度而言,生的本質就是勝義生,因此破除勝義生的當下,生的這一點也應該要能夠被破除。
對於這樣的一個理論,自宗就有作了回答:
如果執著「自性無生」或「無生自性」是完全不存在的生,並且在這個執著之上、在這種見解之上,你反而提出一個問難,認為「緣生」與「無自性生」這兩者是完全相違的話「呵為無耳無心」。
「無耳無心」在下面的文裡面會作介紹。
說無自性生,未聞所說自性,妄執無生意謂無耳,及說自性未解其義,意謂無心。
當對方在談到「自性無生」這個名詞的當下,如果你沒有聽到前面「自性」的這兩個字,而只聽到「無生」的這兩個字的話,因為你自己本身沒有聽清楚,而你執著了無生的話,「意謂無耳」這表示你的耳朵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的耳朵很正常,你聽到「自性」這兩個字的之後,你沒有去思惟「何謂自性的內涵?
」而執著「自性無生就是所謂的無生」的話,這因為你沒有如理的去思惟「自性」的內涵的緣故,所以表示你是一個「無心」的人。
(447“9)
如六十正理論云:
「緣生即無生,勝見真實說。
」在龍樹菩薩所造的《六十正理論》當中有談到兩句話。
這當中的「勝見」是指著佛陀的意思。
其釋中云:
「若見緣起,諸法自性皆不可得,以依緣生者,即如影像,無自性生故。
在《六十正理論》的釋論當中有作了一段解釋:
如果見到了緣起,就表示這一法它本身的自性是沒有辦法獲得。
如果這一法它是必須要觀待因緣、依賴著因緣而產生的話,它的本質就有如同鏡中臉的影像,是沒有任何自性的生。
若謂既依緣生,豈非是生,云何說彼無生?
若云無生,則不應說是依緣生,故此非理互相違故。
對於自宗所談論的內涵,他宗在就作了一個問難:
如果這一法的形成是必須要依賴著因緣才有辦法產生的話,為什麼你在字面上要強調「緣生即無生」的概念?
難道觀待因緣所生的法,它不是生嗎?
如果是生,為什麼你要談到「無生」呢?
第一點,如果它是無生的話,你在解釋它的當下,你不能夠解釋說「它是依靠著因緣而產生的」,如果你安立「緣生」就沒有辦法在這法之上安立「無生」的道理,因此這兩點是完全相違的。
噫唏!
嗚呼!
無心無耳,亦相攻難,此實令我極為難處。
自宗感到相當的感歎,就談到說,跟我作問答的這個人,他既然是一個無心、而且無耳的人,縱使他有耳,他也不懂得去思惟這段文當中的內涵,現今我要跟這種人作問答,這實在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若時我說依緣生法,即如影像自性無生,爾時豈有可攻難處?
」故應珍重判彼差別。
對於自宗所要談的內涵就是:
我所謂的法在形成的當下,它是依賴著因緣而產生的,而它的本質就有如同是影像般沒有任何的自性。
對於我所提出來的這個論點,你難道能夠提出什麼有力的問難嗎?
因此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必須要先能夠先分辨得出來,「自性無生」與「無生」這兩者的差別。
(447“13)
無熱惱請問經云:
「若從緣生即無生,於彼非有生自性,若法仗緣說彼空,若了知空不放逸。
」「仗」有依賴的這個意思,「不放逸」就是不墮入常斷二邊。
觀待因緣而生的法它是無生的,這種無生(緣生法)的本質是沒有生的這種自性(沒有自性的生),若是以這種方式去認識空性的話,是不會墮入常斷二邊的。
這兩者它不僅不會相違,而且是必須要能夠相輔相成,透由緣起了解空性,藉由空性認識緣起。
初句說言「緣生即無生」,第二句顯示無生之理云:
「於彼非有生自性。
」是於所破加簡別,言謂無自性生。
接下來解釋到,在第一句話當中有談到「觀待因緣所生的法它是無生的」,這當中的「無生」是什麼內涵呢?
所謂的「無生」,從第二句話當中可以顯示出來:
「這種緣生法它的本質是『沒有生』的這種自性,也就是沒有自性的生。
」因此在第一句話裡面所談到的「無生」,是必須要加上自性的勝義作簡別,而談到了「無自性生」的這個概念。
頗見一類,聞彼諸句未解彼理,專相違說,「生即無生,依即無依」,狂言愈大,知見愈高。
但是過去有很多的論師,尤其以西藏的論師為主,在看到這些文義的時候,或者是聽到這一方面的法則時,並沒有深入的去探討,經論當中所要表達的內涵,並且會闡釋一些相違的概念,比如「生即無生,依即無依」,生它就是無生,依即是無依。
而實際上這些論師,對於經論當中的內涵根本就不認識,他們自己本身所持的見解也是完全錯誤的。
明顯句論引楞伽經云:
「大慧!
無自性生,我密意說一切法無生,」此說極顯。
在月稱菩薩所造的《明顯句論》當中,引了佛經《楞伽經》裡面的一段話,就是對著大慧菩薩而談到:
「我以無自性生作為講法的動機,而談到了一切法是無生的這個內涵。
」這段文當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來,所謂的「無生」最主要強調的內涵是「無自性生」。
又破生等應不應加勝義簡別,義雖已答,然分別答至下當說。
更進一步的探討到,在破除生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加上勝義來作簡別?
也就是破除生的當下,是不是要破除勝義的生的這一點,它的內涵已經透由之前的文義作了簡單的回答,但要更進一步的來解釋這一點,在下文當中還會繼續的作介紹。
對於這一點中觀應成派以及自續派的論師,他們所持的論點並不相同的。
以中觀應成派的論師而言,在破生的時候必須要加上「勝義」作簡別,也就是「生」在名言當中雖然有辦法安立,但是如果要破生的話,「所破的生」是必須要加上勝義作簡別,也就是必須要破除勝義之生。
這一點以中觀自續派以下的論師,並沒有辦法認同。
(448“5)
此等皆是,顯示彼一切能破,皆不能破無自性中因果建立。
在之前的文裡面,最主要就是要談到,在無自性當中能夠建立因果的這一點,透由正理、或者是透由種種的方式,是沒有辦法產生任何的違害。
這當中的「能破」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問難、或者是應成。
透由種種的問難,它是沒有辦法破除無自性裡可以建立因果的這一點。
似能破中最究竟者,謂自破他如何觀察,即彼諸過於自能破無餘遍轉。
「能破」就是你能夠提出有力的正因,來破斥、或者是破除對方所安立的宗,這稱之為是能破。
「似能破」就是你所提出來的正因,並沒有辦法直接的對「他人所立的宗」產生任何的傷害,這稱之為叫做「似能破」。
在「似能破」當中最糟糕的一種狀況,就是對於你自己所提出來的論點,你不僅僅沒有辦法破除對方所立的宗,甚至對方以相同的方式來詢問你的時候,你可能都沒有辦法作出正確的回答。
汝等所立,即似能破最究竟者,以破他宗觀察正理害、不害等皆被遮迴,其能破理成所破故。
以自宗的角度在看待他宗的時候就認為,你(他宗)所立的這些觀點,正好是「似能破」裡面最究竟,也就是最糟糕的一種理論。
對於你之前所提出來的種種問難,不僅沒有辦法傷害到我,而且你認為能夠破斥對方的這些正理,到最後都會被你自己所提出來的理論而破斥。
若謂汝許有色等,故於彼等此觀察轉,我等無宗故,彼觀察不能轉入。
最後他宗又談到說,如果承許色等諸法是成立的話,這一切透由正理來觀察會產生種種的過失。
但是我並不承許色等諸法是存在的,所以透由正理來觀察,對於我所立的宗,並沒有辦法產生任何的傷害,這是他宗最後所提出來的一個論點。
此答不能斷彼諸過,於應成派及自續派,何決擇時茲當宣說。
自宗就回答說:
縱使你以這種方式在逃避種種的過失,但實際上這樣的回答,並沒辦法斷除、沒有辦法解決你自己本身的問題。
對於這樣的論點,之後在解釋應成派以及自續派,這兩派當中所提出來的宗義時,會作詳細的介紹。
(448“10)
亥四、觀察有事無事等四句而為破除,然不能破
第四、破除有事無事四句無能妨害。
若謂中觀諸教典中,破一切事,或破自性有無二俱二非四句,無不攝法,故以正理能破一切。
之前我們在破勝義生、或者是在破自性生的時候,有談到四生的這個概念,透由破除了四生而破除了有勝義、有自性的生。
那相同的在中觀的諸多教典裡面也會再次的談到,要破除「勝義有」或者是「自性有」的當下,必須要破除四邊,這當中的四邊就是「有自性的邊」、「完全不存在的邊」、以及「二俱邊」、「二非邊」,要破除了這四邊,才能夠破除有自性的有。
而實際上這一點的內涵,跟之前所談到的「破生」的這個內涵是很類似的。
因此這一法它必須是在「四邊」當中的任何一邊,「無不攝法」四邊當中是包含一切的萬法,萬法是必須要能夠被四邊所涵蓋的,因此破除了四邊也能夠破除所謂的法。
這是他宗所提出來的第一個觀點。
此如前說事有二種,若以自性所成之事,隨於二諦許何諦有皆當破除,能作用事於名言中非能破除。
對於這個論點接下來自宗就談到了,這就如同之前我們在探討「事」或者是「事物」的時候,「事物」本身可以分為兩大類。
如果事物它本身是有自性的,有自性的事物在勝義以及世俗二諦當中,是沒有辦法安立的。
另外一種是有作用、能作用的事物,也就是一切的有為法它都能夠稱為有作用的事物。
而這種有作用的事物,它在名言當中是沒有辦法破除的。
又無事中,若於無為許由自性所成無事,如此無事亦當破除,如是之有事、無事二俱當破,有自性之俱非亦當破除。
「無事」就是沒有作用、或者是不能作用的一法,稱之為「無事」,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談到的「無為法」。
在安立無事(或者是無為)的當下,如果是以「有自性」的角度來安立的話,這樣的一種無事「亦當破除」。
「如是」就是有自性。
如果一法它當下是有事、又是無事的話,它是以有自性的有事、無事的這個內涵存在出來的話,這個內涵應當是要被破除的。
相同的,「俱非」如果是有自性的話,這一點也應當是被破除的。
也就是一種法它在形成的當下,它不可能成為「有自性」跟「完全不存在」這兩點的交集點,這是不存在的。
相同的,雖然它並不是這兩種的交集點,但是「非這兩種交集點」它本身是「有自性」的這一點,也是會被破除的。
(448“13)
故一切破四句之理,皆當如是知。
若未能加如此簡別而破四句,也就是在破除四句的當下,有一些是必須要加上「勝義」或者是「自性」來作簡別的。
如果在破除四句的過程當中,不刻意的去加上「勝義」作簡別的話,會產生以下的過失。
破除有事及無事時,作是破云:
「俱非彼二」,也就是在破除了有事以及無事的這個和合體的當下(它的交集的這一點的當下),會談到了「俱非彼二」也就是「非有事和無事」,這一法它並非有事和無事。
次又破云:
「亦非非二。
」是自許相違。
但是接下來在談到「二非」的時候,又會談到:
」如果不加上勝義作簡別的話,就會談到說,並非非有事及無事。
之前在破除有事以及無事的當下,既然已經談到了非有事和無事的話,就表示非有事和無事的這一點應該是存在的。
但是更進一步在談到二非的時候,如果不加上勝義作簡別的話,就會談到「亦非非有事和無事」,這兩個論點本身是完全相違的。
雖知如是而云無過,強抵賴者,我等不與瘋狂共諍。
自宗就談到,你對於自己所提出的理論都不清楚,甚至你知道自己本身有過失的當下,你還狡辯的話,那我是不會與你這位瘋子一起來討論這件事的。
復次,破蘊自性之體,或破其我便發智慧,了無自性或了無我。
更進一步的,如果破除了蘊體本身是「有自性」的這一點,或者是破除了「有我」的這一點,便會生起證得「蘊」是無自性的智慧、以及獲得了證得無我的智慧,並且透由這個智慧是能夠了知「無自性」以及「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