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一Word文件下载.docx
《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一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德日犯罪成立体系比较分析一Word文件下载.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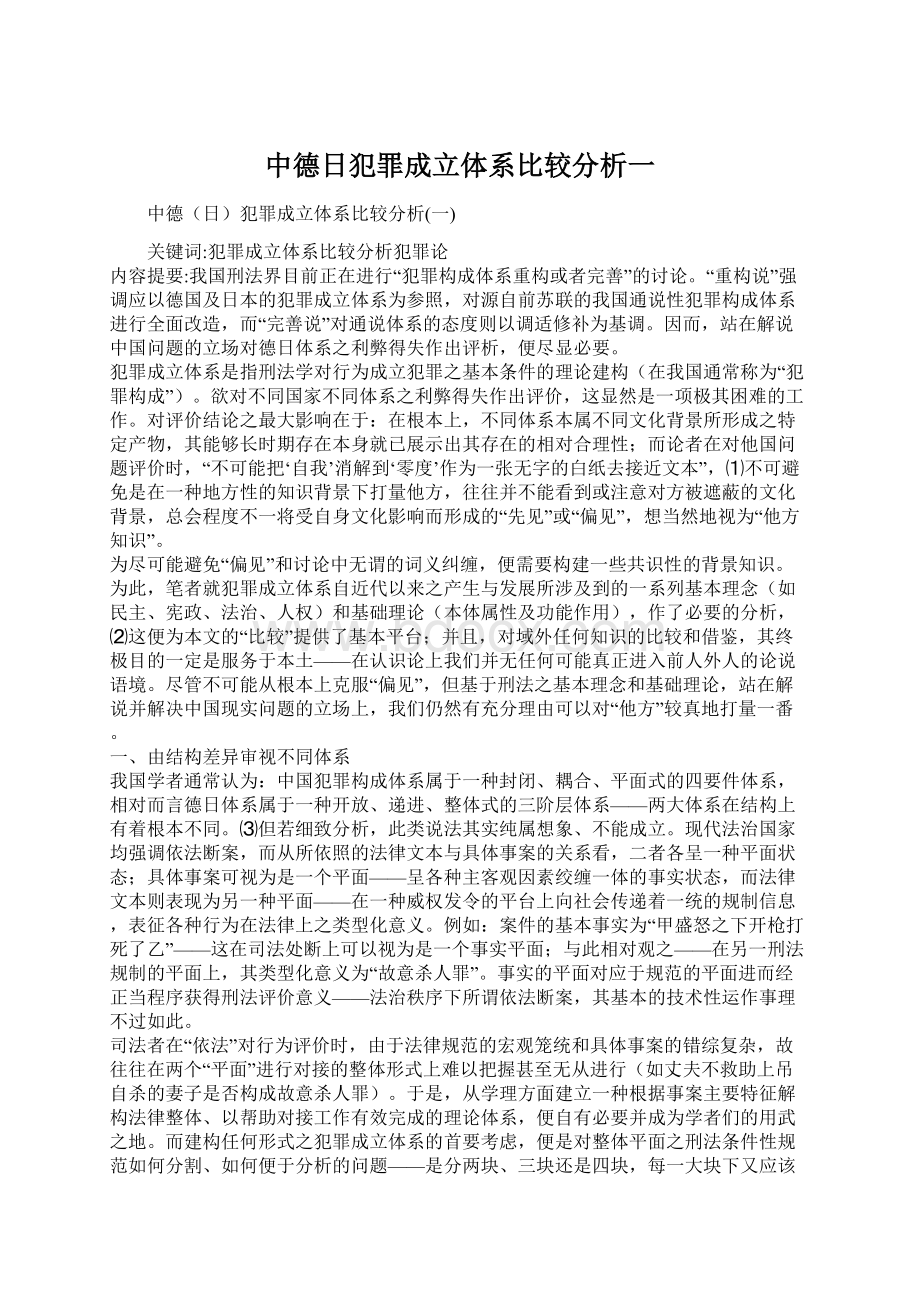
一、由结构差异审视不同体系
我国学者通常认为:
中国犯罪构成体系属于一种封闭、耦合、平面式的四要件体系,相对而言德日体系属于一种开放、递进、整体式的三阶层体系——两大体系在结构上有着根本不同。
⑶但若细致分析,此类说法其实纯属想象、不能成立。
现代法治国家均强调依法断案,而从所依照的法律文本与具体事案的关系看,二者各呈一种平面状态;
具体事案可视为是一个平面——呈各种主客观因素绞缠一体的事实状态,而法律文本则表现为另一种平面——在一种威权发令的平台上向社会传递着一统的规制信息,表征各种行为在法律上之类型化意义。
例如:
案件的基本事实为“甲盛怒之下开枪打死了乙”——这在司法处断上可以视为是一个事实平面;
与此相对观之——在另一刑法规制的平面上,其类型化意义为“故意杀人罪”。
事实的平面对应于规范的平面进而经正当程序获得刑法评价意义——法治秩序下所谓依法断案,其基本的技术性运作事理不过如此。
司法者在“依法”对行为评价时,由于法律规范的宏观笼统和具体事案的错综复杂,故往往在两个“平面”进行对接的整体形式上难以把握甚至无从进行(如丈夫不救助上吊自杀的妻子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于是,从学理方面建立一种根据事案主要特征解构法律整体、以帮助对接工作有效完成的理论体系,便自有必要并成为学者们的用武之地。
而建构任何形式之犯罪成立体系的首要考虑,便是对整体平面之刑法条件性规范如何分割、如何便于分析的问题——是分两块、三块还是四块,每一大块下又应该包含哪些具体要素(此为犯罪成立体系所具之条件列示功能);
分割的结果便必然是形成一块块条件性碎片,于是便又产生一个各种“碎片”应如何按照司法客观认知过程进行再组合、以形成有效析罪路径的问题(此为路径导向功能)。
从刑法总、分则不同条文中所分离出的看似孤立的条件碎片,在理论上被重新组合进而结成具有高度自洽性的逻辑性碎片体系。
司法断案时司法者们一旦认可、接受并采纳了某种理论体系(不会是法律本身),便会受该“碎片体系”的引导,从而也相应地会将整体平面的案件事实拆分为若干对应性碎片——再逐一对事实碎片同条件碎片进行精细的符合性比对,事实上都只能是形成一种“块块分割、逐块分析、综合评价”的犯罪认知思路。
不同的犯罪成立体系在结构上之真正差异,只能是存在于“块与块”在条件列示功能上是如何分割、在路径导向功能上是如何排序两个方面。
在德日三阶层体系下,是将一个整体平面的刑法规范裁分为三块:
构成要件该当性与中国体系的客观方面要件大致相似——均系对客观外在之事实特征的符合性分析;
违法性实质上是讨论刑法规范中必然隐含的法益侵损问题——与中国体系的客体要件意义极为相似而只是排序不同;
有责性涉及的是主体的一般性资格及具体心态问题——中国体系之主体和主观方面两要件可以完整将其包容。
由此可见,德日体系的所谓阶层递进,只是一些学者们的一种想象式理解。
如果将德日体系理解为是一种递进路径,那中国体系又有何理由不能如此相称呢——从客体递进到客观方面,再递进到主体,最后达到主观方面——呈一种较德日体系更为清晰、更为合理的递进理路。
中国体系还被指责为是四个要件“齐头并进”,但“这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一种想象的状态,并不符合人类思维的实际情况:
在考虑具体问题的时候,是不可能所有情况‘一哄而上’的,总要有个先后秩序。
四个要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在司法者脑海中一起涌现。
”⑷
须注意的是:
尽管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相对而言各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平面,且不同理论体系为解决两者的有效对接问题,均事实上将刑法规范的“一个”整体性平面切分为主客观两大块;
德日体系再将两大块分为三阶层,而中国体系却分为四要件。
但不管是三阶层还是四要件,块与块(条件与条件)之间静态的分割意义都只是相对的——都属于一种理论上为简化问题便于分析的人为拟制,并无可能真正彻底地在本体存在形式上将其各自孤立。
换句话说,整体的规范虽然被理论切分为若干要件(阶层),但要件相互之间仍然会存有一种内在的、彼此制约的联系;
离开其中任一要件,其余要件之规定性均难以从根本上厘清。
而在将静态的理论模型及其孤立要件运用于动态的具体事案(原型)分析时,由于事案本身诸因素的复杂绞缠,更可能使要件之间的内在制约关系凸显。
日本刑法学者大冢仁应该主要是就上述现象而认为:
中国的犯罪构成体系,把犯罪的构成要素区分为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当然是可能的,但是仅仅这样平面地区分犯罪要素,并不能正确地把握犯罪的实体。
例如,主观的违法要素虽然是主观要素,但应该像客观的违法性要素一样被作为违法性判断的对象;
同时,像客观的责任要素尽管是客观的事实,但也同其他的主观要素一样,应在决定可否对行为人进行责任非难时加以考虑。
⑸但实际上,大冢仁的批评虽切中要害却仍然不能否定在方法论上设置静态的要件模型,将主客观层面加以分离的宏观必要性和大局可行性;
而司法在运用理论模型动态地切入具体事案时,这种“分离”的分析思路对绝大多数案件也是非常有效的。
在德日有学者倡导的“不法构成要件——罪责”之两阶层体系下,这种主客观的分离思路及对合关系其实更为明显。
⑹
在深层次上,之所以犯罪成立体系中主客观层面不可能绝对分离,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行为所必然内含之“有意性”——组成行为的每一动作几乎都同意志相关,均受意志的支配和控制。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立法者在制定刑法撰写分则个罪的罪状时,都不可能像德日刑法理论所理解的那般——只是就客观的构成要件作出描述;
而是对生活中千千万万的同类案件进行高度抽象,以形成类型化的概念以及由诸概念结成的条件性规范。
在这种源自生活事实的类型化概念中,由于生活事实本身是主客观的统一,故在事理关系上分则规范的罪状中当然也包含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只是主观方面的内容在文意上一般不显)。
这里须强调的是:
罪状意义上之构成要件同理论意义上之构成要件并不等同,前者只可能是主客观的统一,而后者却可以被学者们进行多种学理性的构造——德日体系将其视为“纯客观的”(却又由于罪状中主客观要素的纠缠,于是又不断能够发现其中的“主观违法要素”)。
沙俄时期俄国的刑法学者们并非按照这种思路,而是根据立法的实际过程将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视为整个刑法规范的统领(并非专指分则个罪的构成要件),转而进一步对犯罪成立体系重新进行布局,将理论上之犯罪构成首先顺应立法定式也视为一个类型化的整体,再按司法解决该整体规范同整体事实进行有效对接的实际分析需要,人为地拆分为四大要件以便能够分别作精细比对,从而形成四要件的理论体系。
⑺
生活行为本身是主客观相统一的有机整体,同样,法律规范也只能是一种类型化意义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有机整体(立法不大可能逆生活而孤行)。
而唯有理论化之犯罪成立体系,不再可能保持这种“统一”和“有机整体”(若简单保持则势必失去理论之指导意义)。
事实上任何现代意义的刑法学理论,为了帮助司法顺利完成整体规范与整体事实的对接,均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在犯罪成立体系的模型设计上考虑绝大多数情况,将法定之主客观一体化的概念及罪状,人为剥离开来设定为主客观两大基本层面(可进一步拆分为具体层面、要件或要素)——再对两层面之具体意义作出细致的语义阐释(特别是罪状中往往隐含不显的主观面),以引导司法按两层面分离的基本思路将案件也拆分为两大方面分别进行分析。
由此可见,德日体系中能够同主观层面相对立而存在的客观的“构成要件”,可以肯定已并非法律本身而属于一种理论构造。
德日体系下“该当性”与“有责性”始终被分提并论——主客观层面实际上也呈两相分离的格局,但由于“分离”的指导思想并不十分明确,且由于要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故一般误认为德日体系每一层面均是对行为整体的分析。
⑻但实际上既然是称为“分析”,便只能一点一滴分层而为,绝无可能直接以“整体的规范”对“整体的行为”进行。
在韦尔策尔的目的论体系出现及其以后的发展中,阶层之间的关系及所谓的整体性分析思路被构造得异常繁杂——主客观要件交错分析的情况比比皆是,并不断出现所谓的“回旋飞碟现象”(欲解决某一问题而经过繁琐的论证最终又回到问题起点)。
⑼
今日中国一些刑法学者强调应以德日体系为蓝本而重构中国犯罪成立体系,更多认可“该当、违法、有责”三阶层的古典体系,但其实这种体系早已被后来的德日学者不断批评和改造。
而推动变革之主要动因,就在于对三阶层深层次纠缠关系的不断厘析。
但相比较而言,在刑法理论对刑法规范进行解读以致“重构”所产生的多重效果方面,古典犯罪论仍不失为一种理路清晰、方便操作的析罪体系;
将罪状中主客观一体化的构成要件,从理论上尽可能解释描述为是纯客观的,并将其中必然隐含的主观要素予以剥离另行设置为有责性的并列层面,以使分析工作能够有效进行。
将刑法的罪状从理论上截然分离为主客观两大层面,在方法论上对注释刑法学构造犯罪成立体系极为重要——早期的德国刑法学家贝林对这一点反而保持了较清醒的认识。
尽管贝林已经意识到“作为主观要素的责任也可能与法定构成要件存在联系”,但仍然强调:
“如果硬要把‘内在要素’从行为人精神层面上塞入构成要件之中,那么就会陷于踏上一个方法论的歧途。
因为,这种不纯粹的构成要件根本不可能再发挥其作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共同指导形象的功能。
果真如此,则不仅心理因素在会混迹于实行行为中也即在客观的行为方面出现了,而且主观方面也就成了一个完全受压迫的形象会受到挤对,责任也必须扩张,直至所有的犯罪成立要素责任必须同时扩展到一个责任自己的构成要素上面。
”⑽贝林以后的犯罪论可以说真的是“踏上一个方法论的歧途”——事实、规范与理论不分,原型和模型难辨;
结构上叠床架屋,术语上诘屈聱牙。
对中国四要件体系和德日三阶层体系共有之根本逻辑缺陷——要件与要件(阶层与阶层)之间无法绝对分离的问题,这在方法论上目前看来是不可克服的——人类可怜的智识能力对各民族同样均等!
我们设想:
在主要方面,基于犯罪成立体系本身所具有的条件列示和路径导向两大功能,主客观要件的分离是非常必要也是基本可行的——它们各自从不同角度清楚地列示了成罪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并循条件序列能够有效切入具体事案,由此可以解决生活中绝大多数案件之“对接”问题。
在次要方面,虽然疑难事案中凸显要件与要件之间的牵连关系——对任一要件深层含义的理解都只能是在诸要件之关联关系中进行,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仍然可以视为(或想象为)各要件本身系一种“孤立”的存在;
只是在对每一要件之确切语义的阐释过程中,必须引入其他要件之规定性具体加以说明。
二、由客体(法益)要件之必要性审视不同体系
中国体系对犯罪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客体(法益)要件,就案件事实循客体要件之规定性而在分则罪名体系中基本定位的前提下,再行展开其余要件的具体分析。
而德日体系之析罪起点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一开始便是在茫茫“罪海”中撒大网式地进行所谓纯客观的分析;
面对疑难事案(刑法学理论建立犯罪成立体系之意义主要是为解析疑难),首先遭遇的就是“该当性”问题。
由于该当性主要强调的是客观方面条件——即对行为外观意义的诸基本事实特征的类型化描述与抽象,故复杂变异的具体行为很难在这种高度概括的条件中直接定位——即“该当何罪、该当何分则条文”的问题,完全可能因并无先例或并无定论而难以解决。
而中国体系则由于客体(法益)要件的先导性作用使疑难事案的要害得以显露——刑法设定某罪意欲保护什么法益而行为是否对之侵损——循此思路便能够针对性地切人条文及个罪。
虽然刑法条文在大多数情况下均未规定客体要件(只在分则章节的类罪安排上宏观体现),但就理性的立法来说,设置每一罪名均必须考虑具体欲保护什么法益——反之行为侵损什么、其多重危害性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诚如德国刑法学者李斯特所言:
“制定法律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人们的生存利益。
保护人们的利益是法的本质特征;
这一主导思想是制定法律的动力。
”⑾准确、深刻、完整地揭示这一行为成罪的根本理由,正是注释刑法学构建犯罪成立体系之最首要、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对司法解决疑难案件之最大贡献。
诸如盗采国家因考虑地面公共安全而封闭的矿体的案件(是侵犯财产、矿产资源、还是公共安全)、医院护士将购买疫苗的款项据为己有而给多名幼儿注射蒸馏水的案件(是侵犯家长财产、儿童健康、由众多健康而集合的公共安全、医院秩序、还是公共卫生)、以暴力手段抢回自己财物的案件(是否侵犯财产权利),都只有从行为究竟侵犯何种客体(法益)着手思考,才有可能将案件在具体条文(具体犯罪构成)中大致定位,进一步准确地切人客观方面要件——对行为、结果、因果关系、时间、地点及方法等要素作细致分析。
而德日体系面对这类真正需要体系来解决的所谓“第一次处理行动”(罗克辛语)的案件,显得似乎有些无能——至少较之于中国体系更为低能。
在犯罪成立体系的构造方面,德国人也许早已迈过了帮助司法“找法”的阶段——该当何条何罪的问题对高素质的专家型法官来说,似乎并不成为问题。
但无论如何,正因为客体问题在犯罪认知过程中客观存在不可回避,故德日刑法理论往往在犯罪成立体系之外前置性地讨论法益问题——其意图事实上仍然在于为司法提供一种个罪定位的分析思路;
但由于犯罪客体(法益)在体系内并无明确地位,其对司法的实际指导意义显然是大打折扣的。
就依法断案的简便性、贴切性和最相适应性而言,中国体系在客体要件的设置上显然胜出一筹。
德日刑法理论之所以始终对法益在犯罪成立体系中不予正面承认并给予相应地位,其根本原因应该在于对犯罪成立体系之本体属性采“法定说”的看法。
在欧陆,罪刑法定的理念几乎是随生活挤迫而自生自发形成,国家事先颁行的成文刑法对法域内的任何人均具有不可逾越之至上效力——对刑法的解释及适用均不得超越法典本身的文本意域。
在此常规范式约束下,任何成立犯罪所须具备的条件以及由诸条件所结成的犯罪成立体系,都只能是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应当是其它说明方式。
⑿在犯罪成立体系之本体属性“法定说”的思维定式下,飘忽不定、见仁见智、任人界说的法益问题,自然不可能在体系中获得明确地位。
但我们如果能够还犯罪成立体系之“理论说”的本来面目,则客体(法益)要件便可以名正言顺在体系中取得首要地位。
犯罪成立体系本身并非法律的明文规定,它仅仅只是学者们将刑法作为学问对象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一种理论;
一种有助于司法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加以对接的中介性理论工具,它源于法律但更超于法律;
只要有助于简单准确完成对接工作,对法律本身没有直接规定隐含不见而又极为“有用”的各种要素,在理论体系中予以显形构造,当然是允许且本身就是理论之重任。
于此,将犯罪客体(法益)置入犯罪成立体系,在规范注释论上本无技术上的障碍而在实质方面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⒀
同德日刑法理论相比较,中国体系中的客体要件还具更微妙、更精巧之功效。
多年来德日理论存在“主观主义立场”和“客观主义立场”的论战——客观主义立场明显胜出成为主流;
而在客观主义立场中,“结果无价值”(相对于“行为无价值”)的声音又极为响亮(特别是在日本刑法界)。
这里的所谓立场,在犯罪论中应该是指一种分析犯罪之逻辑原点问题——站在哪一点上开始对“犯罪”进行分析打量——凡符合这一原点之规定性的,方才可转入其它问题的分析。
⒁应该说如果真能坚持这样一种鲜明坚定的立场,对于切实保障犯罪人的人权、防止司法擅断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但遗憾的是,结果无价值的立场至少在德日的犯罪成立体系中并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由于这里的“结果”只能是指法益,而法益恰恰在体系构造中并未给定逻辑原点的地位;
作为分析起点的是构成要件该当性——该当性中之前置要素却是行为!
故现阶段德日刑法理论在犯罪成立体系上,只可能贯彻的是“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在体系构造对分析犯罪之逻辑原点的提示方面,只能是被要求从“行为”开始。
而在中国犯罪构成体系下,却可以顺理成章真正贯彻和落实“结果无价值”的立场。
中国体系是以客体(法益)要件为析罪起点的——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法益和违法性两部分内容被合二为一、名正言顺设定为首要要件;
凡欲进入其余要件的分析,在逻辑上必须首先符合客体之规定性——不具备这一原点之规定性则后续的任何问题都只得免谈。
于是可以说,至少在体系的构造上,中国体系阴差阳错而实实在在形成了一种“结果(法益)无价值”的立场!
三、由违法性之逻辑关系审视不同体系
就中国体系中客体要件之规定性而言,实际上同德日体系中违法性阶层之实质意义有相似之处——二者均关涉的是法益侵损问题,但由于两大体系中对法益的序列安排不同,故事实上造成其功能作用亦有很大差别。
中国体系除客体要件因其前置而独具罪名定位的功能外,在进入具体罪名后的评价方面,同德日体系之违法性的思路存在重大差别。
在德日三阶层体系的汉译语境中,通常认为第一阶层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判断——案件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之诸要素,若符合则“递进”到高一级的违法性层面。
而第二阶层违法性相对于该当性,被视为是一种反面的、消极的判断——主要考察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阻却事由”,若存在则在该层面予以出罪。
对同一实然行为从不同层面进行判断:
一正面一反面、一积极一消极,可谓全面细致不枉不纵。
但细分析此说法其实根本不可能成立(至少在汉语语境下不能成立)!
就语词的字面含义及通常用法而言,所谓积极或消极,是指认识主体对事物的一种评价态度;
而正面或反面,则是指观察评价事物的不同角度或方式。
在认识论上,对同一事物之所以能够形成不同的分析层面,是由于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
反之,不同的评价标准便架设起不同的分析层面。
并且,在每一分析层面皆可根据该层面的同一基本评价标准,对事物作出正面或反面、积极或消极的认知。
在具体的分析活动中,不管对事物是作出正面或反面的评价,还是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判断,都必须是在同一层面、取同一标准才可有效进行。
在该当性和违法性两个不同的层面,是以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分别评判行为:
一是客观要件之规定性是否符合,二是实质的法益侵害性是否具备。
在两个层面中,分别都可以并且也只能在该层面以同一基本标准进行正面或反面、积极或消极的判断;
即分别在该当性或违法性层面,才可从正面或反面多角度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从而积极地得出行为是符合还是不符合的结论。
⒂对大量属于公理性、常识性的认识,多数情况下都只须消极地肯定(不允许消极地否定)而并无必要专门进行论证,并自然而然转入下一层面的分析。
当进入违法性层面后,以实质的法益侵害性为评价标准,可正面或反面地分析行为是否具备,从而积极地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但这种积极性的分析理路,只是针对个别可能存在异常的案件;
绝大多数常态案件都会被“消极的”视为符合而放行通过,全无必要进行违法性的分析。
对个别在违法性方面存在异常的案件,必须以违法性判断的具体标准(实质的法益侵害性)积极地细细斟酌,一旦能确认行为并不符合便可反面认定违法性的阻却,从而中断犯罪的确证过程。
当然,也可能在经过反复论证后才可从正面认定违法性的存在,从而转入有责性层面的分析。
须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当行为之违法性被阻却后因其犯罪基本条件缺损,至多只是出现一种行为不构成犯罪而属于非罪行为的认识——即只能得出“不是犯罪”的结论,并不可能认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无法推导出行为之“正当”或“合法”的结论。
本来,按照构造犯罪成立体系的基本要求——设定成罪的基本条件并架构合理的条件分析路径,在违法性层面只须设定违法性自身的判断标准即可满足要求——具体运用时在该当性符合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积极地排除不具违法性的非罪行为;
在体系构造上并无必要也不应该对所界分出的“非罪行为”再作精细分类——至少这方面内容已不属于犯罪成立条件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部分。
但是,德日刑法理论却将任何与犯罪相关的问题都试图纳入犯罪成立体系进行评说,于是“违法阻却事由”的庞大内容便在违法性层面下全面铺开。
由于违法性标准(所谓的“排除不法的根据”)只能界分出非罪行为而不可能厘定违法阻却事由之具体性质,于是只能是在违法性标准以外再分别提出每一种具体事由各自的判断标准(即所谓的“正当化的根据”)⒃——毕竟具体的违法阻却事由也需要在广义的犯罪论中进行讨论(刑法不仅要惩恶也须扬善)。
在宏观上,似乎只要能够阐明事理关系如此构造体系也未尝不可——在违法性的大标准下再具体设定不同事由的小标准。
但如此一来,在体系构造的微观方面便又产生出新的难以协调之矛盾。
由于该当性和违法性通常都被认为属于纯客观的判断,则若在违法性的大标准下再设定不同事由的具体标准,就似乎不应超出“客观”的范围。
但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或者说是无意义的——纯客观的标准是根本无从区分各种免责事由的。
由于“世界上所有的法律体系,在事实上都对自我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辩护要求一种主观要素”,⒄于是,德日体系只能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并设定主观意图方面的标准,将本属于有责性层面的内容又穿插在违法性中分析,致各阶层之间的事理关系在各种具体事由的分析中混杂不清。
由此,一些在体系上明明是划归违法阻却事由范围内讨论的事由,但其实在“违法性”方面根本就不可能阻却——即行为在实质上仍然具有法益侵害性,必须转入有责性层面分析才可能免责——即事实上又属于“责任阻却事由”。
于是,同一法定事由(如紧急避险)就既可能是违法阻却事由也可能是责任阻却事由,将本来较为简单的问题却由于体系的层面分离搞得异常复杂,以致不但会使司法者一头雾水,就是理论家们时常也晕头转向、难梳理路。
综上可见,德日犯罪成立体系中根本区别于中国体系之最要害的违法性层面,恰恰是最成问题、最难以自圆其说的。
在成立犯罪之基本条件的意义上,违法性的内容对行为成立犯罪几乎不具任何积极性的认知识别作用;
而事实上可以用作反向判断之违法阻却事由,却又不直接属于成罪基本条件的内容——须另行设定主客观标准具体厘定。
而在中国通说体系下,对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实际上是通过客体要件进行的;
客体要件既有对疑难事案在分则体系中的罪名定位功能,也有对不具实质违法性(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的出罪功能——积极地予以出罪后在犯罪构成之外另行以专章形式,设定不同的主客观标准再分别作“可谴责”(如自损行为)、“允许”(如自救行为)或“鼓励”(如正当防卫)的正面评价。
说到底,对诸多阻却事由之所以能够厘清其具体性质,并非违法性(或有责性)之单一层面足以完成,而是一个多层面、跨要件以至超要件的问题。
罗克辛教授为此叹道:
“正当化的根据是如此数量庞大,并且来自如此不同的法律领域,以至于在刑法总则的理论说明中,远远不能对它们的全部进行处理。
”⒅将所有问题统统直接并人犯罪成立体系,对司法运用来说并非一种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