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Word格式.docx
《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Word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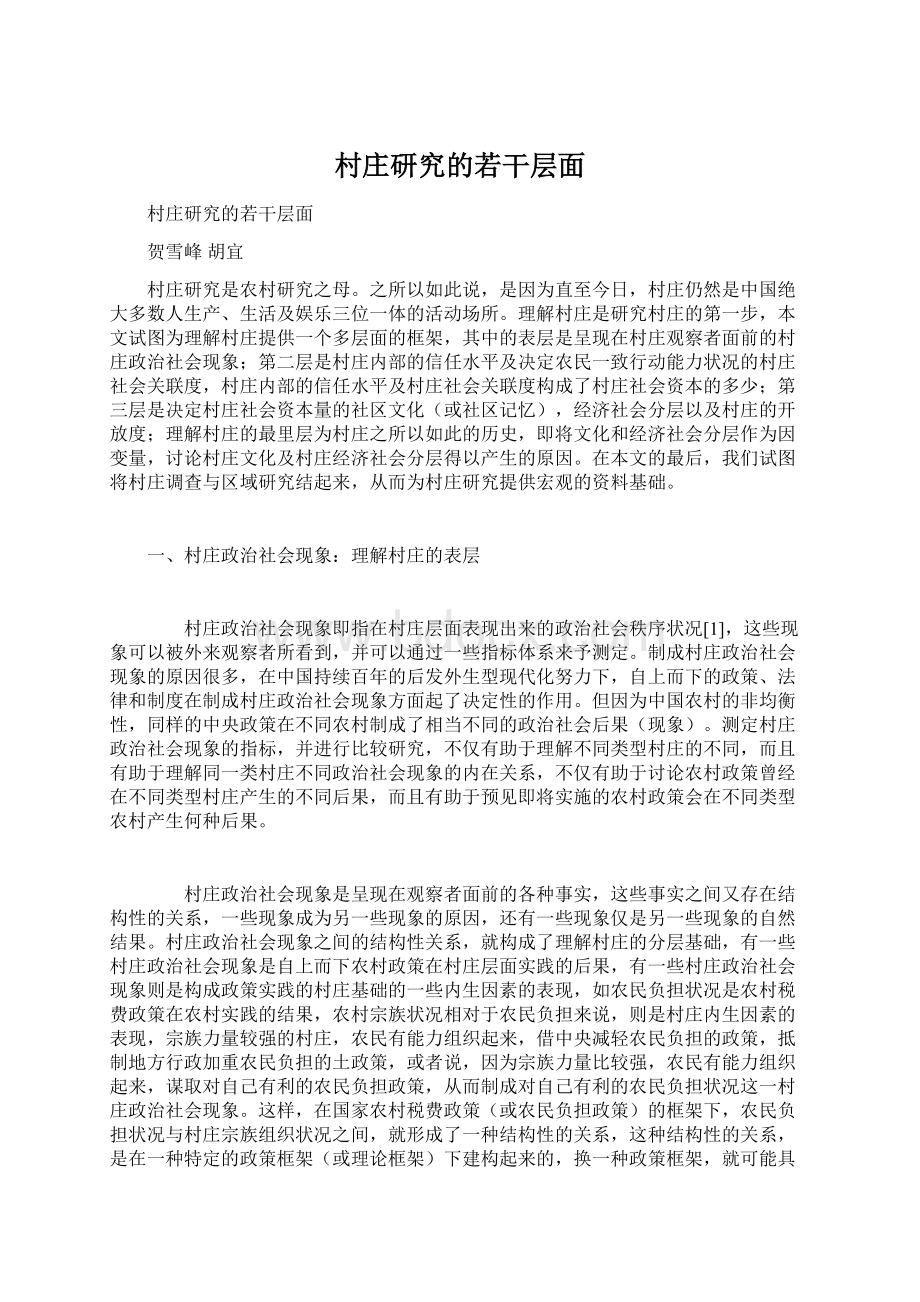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是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各种事实,这些事实之间又存在结构性的关系,一些现象成为另一些现象的原因,还有一些现象仅是另一些现象的自然结果。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就构成了理解村庄的分层基础,有一些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是自上而下农村政策在村庄层面实践的后果,有一些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则是构成政策实践的村庄基础的一些内生因素的表现,如农民负担状况是农村税费政策在农村实践的结果,农村宗族状况相对于农民负担来说,则是村庄内生因素的表现,宗族力量较强的村庄,农民有能力组织起来,借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抵制地方行政加重农民负担的土政策,或者说,因为宗族力量比较强,农民有能力组织起来,谋取对自己有利的农民负担政策,从而制成对自己有利的农民负担状况这一村庄政治社会现象。
这样,在国家农村税费政策(或农民负担政策)的框架下,农民负担状况与村庄宗族组织状况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关系,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是在一种特定的政策框架(或理论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换一种政策框架,就可能具有不同的结构性关系。
比如,在送法下乡的框架下,宗族组织本身的活动状况与方式被国家法律所限制和改造(如不允许族规家法超过国家法律等),宗族组织状况成为表层的政治社会现象,而农民的宗族意识则成为宗族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性力量。
这样,观察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就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个角度是从平面上寻找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尤其是因果性关系和联动性关系,另一个角度是从纵向上区分村庄现象与村庄本质,并因此建立村庄研究的层面。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不仅是理解村庄的前提和基础,而且为村庄研究的分层推进提供了可以观察和测量的指标。
二、村庄社会资本: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内生原因
理解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一是要理解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一是要理解在同样外来制度(政策及法律)面前,不同村庄会制成不同政治社会现象的原因。
或者为什么同样的政策会在不同类型农村产生不同的政策后果。
当前学术界借用社会资本一词来描述一个社会中合作能力的含量。
对于村庄社会来说,村庄社会资本的含义就是村庄在形成内生秩序方面的能力状况。
不过,构成村庄内生秩序基础的社会资本,含义十分广泛,难以清晰表达。
从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来看,学术界也大致是在社会信任水平与自组织状况两个方面使用社会资本。
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越高,社会资本就越多,自组织能力越强,社会资本也就越多。
在村庄研究中,我们同样可以从村庄内部的信任水平及自组织能力两个方面来讨论村庄社会资本的多少。
我们曾以“村庄社会关联”一词来描述村庄农民的自组织能力,具体地说,村庄社会关联是指村民一致行动的能力,这种一致行动能力的实质就是在解决村庄秩序问题时,村民有多大可能集体行动[2]。
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的方法有结构和功能两种,结构的方法是,理解村庄中存在的宗族组织,小亲族组织,业缘组织,趣缘组织乃至其他各种可以观察到的小群体的数量及这些小群体的行动能力。
功能的方法是,在解决村庄秩序问题时,村民整体及部分的行动能力状况,他们是否会为解决村庄秩序问题而行动起来及能否成功。
村庄信任水平与村庄社会关联有一定联系,一般来讲,村庄信任水平越高,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就越强,村庄社会关联就越容易产生。
同样,村庄社会关联度越高,村民之间的联系就越是密切,村民与村民之间的相互约束就越多,村庄社会信任水平就会越高。
一个高度信任的村庄,容易成为一个强社会关联的村庄,一个强社会关联的村庄也容易成为一个高信任的村庄。
但是,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信任在截面上仍然具有相当的不同,村庄社会关联主要是从社会行动方面来展开讨论,这个方面,每个村民的行动都有理性算计的因素,只是这种理性算计因为将小群体人与人之间长期交往本身的收益(或损害)包括进去,而与经济人假设中仅仅将人作为计算经济利益的原子化个人大不相同。
原子化的经济人因为不能解决搭便车的问题,而不能集体行动,陷入所谓集体行动的困境。
但在村庄社会关联度高的村庄,因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小群体内部,形成了相互之间密切的社会联系,将这些社会联系计算进入村民理性算计的结果中,便是村庄集体行动得以达成,村庄秩序问题得到解决。
村庄社会信任与村庄社会关联的大不同,在于村庄社会信任往往来自于村民的下意识,这种下意识又来自于习惯,传统,信仰等文化因素,并未进入理性算计的层面。
在宗族意识强的村庄,村民会当然地认为本族人可信;
在一个少流动较封闭的村庄,村民因为世代在村庄生活,相互之间熟悉,很少出现言而无信的情况,因此会在达成集体行动时,当然地按习惯行动。
随着村庄与大社会交往的加深,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深入,言而无信的情况频频出现,村民按习惯做出的判断可能出现错误(对方失信等),村民行动就更多考虑在信任他人及集体时,不是下意识,而是理性算计有无对方失信后予以反制的办法,也就是越来越依赖于村庄社会关联的状况,来决定自己是否信任他人及集体。
无论如何,不同村庄,不仅村庄社会关联度是不同的,而且村庄社会信任水平也是不同的,不同村庄信任水平制造了村庄社会关联发生作用能力的不同基调。
仅仅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而缺少人与人之间下意识的社会信任,这类村庄的社会关联度就较低,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就较差。
举个例子来说,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度很高,类似于经济学所讲重复博弈关系。
因为村民世代生活于村庄之中,不守信必有大的代价支付,且村民对未来的预期十分长远。
同时,村民之间的交往是全方位的交往,而非仅是经济交往。
这样,村民与村民的关系,就非经济学上原子化个人之间纯粹的经济利益的算计,而不得不考虑本次行动对今后行动的影响,人与人之间自然形成社会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开始时仍然在理性算计的层面,但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纯经济的算计。
日子越久,时间越长,这种社会层面的多方位的理性算计成本很高,便逐步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传统或文化,这样就发展出村庄的社会信任来。
当前村庄越来越开放,市场经济的渗透,现代法律、观念的渗入,以及村民越来越频繁的流动,就将村庄信任逐步还原为了全方位的理性算计(再到原子化个人的经济利益算计?
)[3]。
村庄社会信任作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对于决定村庄整体的集体行动及小群体的集体行动,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简单地说,既不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算计,也不是出于社会舆论及长远预期的算计,而是出自本能,出自惯习,这就使得村庄集体行动具有了全方位的特征。
高社会信任的村庄,应该有较高程度的村庄文化活动,节庆典礼活动及表达性的人情往来活动。
有强烈的“我们人”的意识。
高度信任的村庄,“我们人”在行动中主要不是考虑个人得失,而会视我们的集体行动为当然。
村庄社会关联与村庄社会信任的大不同,在于村庄社会关联强调村民与村民之间经济、社会诸方面关系的程度及在此种关系下面村民的行动能力,这方面的行动能力,不仅由村庄社会信任这些文化层面的惯习所决定,而且由村民之间因为全方位的长期的理性计算所引起,由长远利益的预期所引起。
对于由村庄信任及村庄社会关联共同构成的村庄社会资本,可以进行测量。
举例来说,可以通过测定村庄文化活动的频度来测定村庄社会信任水平,而通过测定村庄社会活动的频度来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
在村庄社会活动中,相当部分系由村庄经济社会分层所制成的资源分配不均衡所引起,此方面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三、村庄社会资本量的测定
要在理论上解决测定村庄社会资本量的办法,十分困难,其原因之一在于村庄社会资本本身的精确定义十分困难,原因之二是中国农村的情况过于复杂,很难有一套理论框架可以将所有村庄的情况包容进来。
要解决测定村庄社会资本量的难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的简化入手,一是寻求某些容易测量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与村庄社会资本的相关关系,从而以可以测定的这些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来测量村庄社会资本,其中尤其可以从与村庄社会资本有相关关系的不同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测定数据中进行交叉印证。
二是允许这种测定将一些特殊村庄作例外处理。
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寻找一些既简化、容易测量,又具有相当包容性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来划分村庄类型,从而测定村庄社会资本的量。
(注意,这里的村庄社会资本因为多面构成,而具有矢量性质)。
我们曾从村庄社区记忆与村庄经济社会分层两个维度讨论村庄类型[4]。
这种讨论,通过选择两个最为重要的维度来划分村庄理想类型,对于理解中国村庄的多样性乃至非均衡性,大有用处。
但是,如此讨论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划分理想类型时,容易脱离当前中国农村最大多数的实际,而成为理论游戏。
特别地,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看起来是无缝隙地覆盖了所有村庄(依据将村庄社区记忆与村庄经济社会分层组成一个连续统),却往往只是表达了从而也就是揭示了一些特殊村庄的内涵。
或者说,这种讨论策略容易将一些特殊村庄作为讨论的重心,而忽视占全国村庄大多数的普通农村,尤其难以对占全国大多数的普通村庄进行精细研究。
为了测量占全国村庄大多数的普通村庄的社会资本量,我们需要寻找一些虽然有缝隙从而不能包容全部村庄,但较为容易测量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来测定具有矢量性质的村庄社会资本。
这种测量仍然从村庄社会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两个方面进行。
测量村庄社会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途径有二,一是结构性的途径,即通过寻找容易测定出的结构性的因素来测定村庄社会资本的量,二是功能性的途径,即寻找容易测定的村庄社会资本功能表现来测定村庄社会资本的量。
无论是结构途径还是功能途径,能够直接测定的因素,必须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即我们要分别从结构和功能两个方向寻找可以测定村庄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度的政治社会现象,然后以这些不同方面测定出来的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量,来交叉验证村庄社会资本的实量。
先从结构途径展开讨论。
我们可以从村庄表达性活动和功能性活动的多少,来对应讨论村庄信任水平与村庄关联度。
一般来说,表达性活动多的村庄,村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因为表达性活动对于重建村庄整体意识,对于加强村民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对于强化“你们”与“我们”意识,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并且表达性活动本身就是文化层面的活动,是一种功利程度较低情感程度较高的活动。
(需进一步展开表达性活动与村庄社会信任水平的相关性)。
如果我们依据村庄表达性活动的多少来测量村庄信任水平,则可以解析村庄表达性活动如下:
所谓村庄表达性活动,就是非功能性的村民集体行动的总和,具体如村庄娱乐活动,文化活动,节庆典礼,表达性的人情往来等等,我们可以初步对村庄表达性的活动进行列举,并依据活动的强度排序。
如果一个村庄频繁举行表达性的活动,并且这些表达性活动具有深刻的情感性、神圣性,乃至神秘性,能够有效调动村民心灵体验,则这个村庄是表达性活动较多的村庄,这个村庄的社会信任水平较高。
我们还可以更具体地将表达性活动数量化,从而从结构方面排出村庄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来。
村庄功能性活动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从经济人角度来予解析的经济活动,这类活动不具有集体行为的特征,因此不需我们在讨论村庄社会资本量时考虑。
另一类功能性活动是指功能性的村民集体行动,这些功能性的村民集体行动的多少及能力,即村庄社会关联度。
(此方面尚需展开讨论。
究竟什么是功能性的集体行动,要举例说明,如因为担心不帮村民抬丧,而在自身办丧事对无人抬丧,从而出现抬丧时的合作;
再如合作用水,兄弟合用耕牛等)我们可以从测定村庄中功能性集体行动的数量,来从结构方面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并由此将不同村庄的社会关联度进行排序。
村庄的一些集体行动,往往难以区分究竟是功能性活动还是表达性活动,例如,村庄往往既有功能性的人情往来,又有表达性的人情往来。
对此的区分及测量办法,可以分别依据村庄人情往来的实际频次及村民对人情往来的评价(如这样频次的人情往来是否应该,是否正常,是否被迫应付,所谓“人情大于债”等等),来判断村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关联度,并由此判断村庄社会资本的量。
从结构方面进行测量的另一个办法是,直接通过问卷调查不同类型村庄的村民,由他们来判断村庄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和村庄社会关联度的大小。
比如可以设定如此问卷:
你认为邻居可信吗?
亲戚可信吗?
如果生了病,邻居是否会愿意借钱给你治病?
亲戚呢?
如此设置若干道题,然后根据选择是与否的比率,来判定村庄信任水平或村庄社会关联度的高低。
从功能方面来解读及交叉验证村庄社会信任水平高低和社会关联度大小,则可以从村庄内生秩序的方面来予展开。
村庄内生秩序如民间纠纷发生的频次及主要在何种层面得以调解,村庄小水利的合作状况,村庄道路等公共设施维护的好坏,村庄公共舆论的水平等等。
村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村庄社会关联度越大,则村庄内生秩序的能力就会越强,因为村民集体行动的能力越强。
不过,村庄信任水平因为重于表达性的方面,而在为增加村庄社会资本量的贡献中,更多是一种弥散的,整体的贡献,这种贡献提供了村庄共同的舆论力量,提供了村庄内生秩序的基调。
村庄信任水平高,则村庄整体行动能力强。
村庄社会关联则因为重于功能性的关系,而在增加村庄社会资本量的贡献中,更多是一种具体的、片段性的贡献,这种贡献尤其提供了村庄小群体的行动能力。
可以推测,在宗族意识强的村庄,村庄社会资本总量高,其中尤其来自很高的村庄社会信任水平,而在宗族意识解体,小亲族活动较为频繁的村庄,村庄的表达性活动相对较少,而功能性活动较多,小群体频繁活动使得村庄社会关联度较高,村庄社会资本总量大多来自小群体的活动能力。
也正是村庄社会信任水平与村庄社会关联的非同步变化及非同等强度,使得村庄社会资本成为一个有着方向的矢量。
这一点在讨论村庄社会资本量的变迁中,尤其从历史维度讨论村庄社会资本时,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四、历史的维度
以上我们试图为从村庄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度两个方面测量村庄社会资本量提供思路和手段,这样测量出来的村庄社会资本量只是村庄当下的社会资本量,是一种静态的量。
问题是,当前的中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变迁过程中,不理解静态测定的村庄社会资本量的历史及未来的变迁方向,我们往往难以清晰理解正在村庄发生的政治社会现象的含义,也就不能理解农村政策在不同村庄实践后果差异的原因,不能充分理解农村政策未来的可能后果,也就不能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从历史维度展开,就是要将构成村庄社会资本量的村庄社会信任和村庄社会关联作为因变量,而予研究。
村庄社会信任因何而来?
村庄社会关联将往何去?
这不仅对于理解村庄社会资本量,而且对于理解农村政策基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维度可以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是微观层面,即每一种类型村庄的社会资本量是如何获得并将往何处去的问题;
另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即随着时间的推延,不同类型村庄将会如何演变。
先从微观层面看,20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社会渗透,基层社会不断被融入到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之中的过程,有人称之为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张静、王铭铭等),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强大的国家权力借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力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和每个方面。
传统的村庄社会信任和村庄社会关联均被强有力的现代因素所改造,尤其被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行为规范所改造。
不过,比起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现代因素对农村渗透的程度来说,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向农村社会的渗透显得粗暴且粗糙,这种国家权力下乡将农村从面貌上进行了彻底改造和改变,但这种改变在有些时候也只是改变了农村的表面(脸面),而没有改变农村本质的方面,比如说,有些改变往往只是“新瓶装旧酒”,公开的敬鬼神仪式没有了,家庭内部的敬鬼神仪式仍在;
宗族不再以族规惩罚不孝子女,生产队却在全队社员大会或有线广播中点名批评某某子女的不孝行为,甚至将不孝子女捆起来游田梗;
文革中造反派之间为争正统的派性斗争往往只是村庄历史上存在矛盾的再次爆发;
统购统销制度与传统社会中小农的自给自足不谋而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同时也就强化了农民的村落意识及村庄舆论的力量,总之,人民公社时期,话语可能是新的,新话语的意思却是数百年来就一直存在的,是当地人历来都如此理解和如此使用的,在这样的小传统中,村民们讲的话语是“法”,理解其意思的语境基础却是当地农民历来公认的“理”。
相反,市场经济较人民公社更彻底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状况,从而更深刻地改变了村庄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状况。
相对于人民公社来说,市场经济对农村的渗透更加精致,细密,可以用浸入骨髓来形容。
正是市场经济的力量,在彻底改变和改造农村的外貌与内核。
市场经济改变农村的核心在于它正将传统的中国农民改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将原来的道德农民改变为理性农民,将依附于共同体的农民改变为原子化的个体农民。
市场经济改变农民的途径有以下一些:
一是市场经济以货币结算一切关系,农民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下的货币结算关系,而不得不逐步成为经济人,不得不适应抽象大传统的规则,不得不放弃小传统的规范;
二是市场经济使得货币成为一切关系的等价物,货币关系逐步主导并替代了其他各种关系,包括各种原本神圣和神秘的关系;
三是市场经济使得村庄边界被打破,自给自足的封闭的村庄生活不再存在,开放的村庄和可以自由流动的村民,使村庄传统和村庄舆论变得不再重要,村民可以自由流动及村庄边界更加开放,使得村民对村庄生活的预期也变得不再重要,村民有了更多按照理性算计来决定行为方向的空间;
四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传媒多样化,尤其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电视广告,时时日日改变着农民的价值观,并形成着农民新的价值观。
农民的生活目标逐渐变得与村庄没有多少关系,逐渐成为由一个全国性媒体控制的统一价值观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相对于人民公社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来说,市场经济彻底地改变了村庄的社会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状况。
或者说,相对于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来说,人民公社打破笼罩在村庄之上的器物方面的传统,比如没收了族田,打碎了庙宇,却没有完全改变世代生活在农民心中的传统。
市场经济则打破了笼罩在村庄之中的精神方面的传统。
两者结合,就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
不过,问题不仅在于,市场经济本身因为极化效应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非均衡,一些地区的农村(尤其是沿海农村)因为经济快速发展,获得了较多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不仅哺育着现代的关系,而且滋润着传统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反而容易看到,在沿海农村,市场经济与传统复兴一并呈现,相互支持,共同生长。
(除市场经济以外,人民公社解体,国家权力的后退,也使传统的复兴具有了较大的公共空间)。
相反,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市场经济使得村庄更加破败,农村的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在中西部农村,不仅现代的关系生长不起来,而且传统的关系也因为得不到足够经济资源的滋润,而无法生长起来。
问题还在于,市场经济在将全国农村置于一种甚至全球化的处境时,市场经济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达九亿的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
市场经济不可能为如此众多的农民提供就业,也不可能为如此众多的农民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更加不可能将如此众多的农民转化成为市民,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在改造村庄社会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状况,从而在改变村庄社会资本量,改变村庄内生秩序能力时,不能为农民提供像样的替代性的生活生产秩序。
市场经济一方面将大部分村庄的人财物资源吸取进入城市,一方面系统地破坏了传统的村庄内生秩序的能力,一方面又不能为农民解决出路问题,这就是将来中国农村政策研究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而从市场经济对构成村庄社会资本两个关键要素的村庄社会信任水平和村庄社会关联状况的影响来看,这种影响不仅在不同类型农村会不一样,而且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影响。
总体来说,市场经济正如人民公社一样,会对传统的村庄信任造成破坏,从而降低村庄内部的社会信任水平,减少村庄社会资本量。
但市场经济也如人民公社一样,可能反而会加剧村庄内部小亲族的活动能力,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从而增加村庄内部的小群体行动能力。
一句话,市场经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破坏表达性的社会关系,而可能增加功能性的社会关系。
从中国农村从而从中国九亿农民未来的出路来看,不加区分地消极等待市场经济来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当市场经济在系统减少农村社会资本量从而在破坏村庄内生秩序的能力,却又没有强有力的外生秩序进入村庄时,农村政策研究部门必须想出新的办法。
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进行乡村建设,特别是从文化和信仰层面重建农村生活从而重建农民的归属感和提高农民的信任水平。
市场经济是一个远远超出农民可控范围的庞然大物,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农民彻底感到了个人的渺小,他们尤其需要从本体上确认自己生活的价值。
这个意义上,不是顺着市场经济,而是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逆着市场经济,进行村庄建设,应是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
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是农村政策基础研究以外的另一个课题。
历史维度考察村庄社会资本,需要有更多区域性的研究。
村庄本身也是有历史的,村庄历史往往决定了村庄的社会信任水平及村庄社会关联状况。
例如,江西近世较少战乱,原生型的宗族村庄较多,一个姓数百户聚居在一个村落,成为江西农村的常规景观。
而湖北近世战乱很多,不断移民组成的村落,往往是多姓杂居,从而就使宗族的发展程度及发展途经,与江西大不一样。
等等,不再一一展开。
五、结语
以上事实上区分出理解村庄的三个层面,其表层是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正是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构成了研究村庄的可以观察和测量的要素,从而将村庄研究变成了实证研究,而不同于某些玄想。
构成理解村庄中间层面的是村庄社会资本量。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的村庄社会资本量是一个有方向的矢量,这个社会资本的定义,与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使用的社会资本要复杂一些[5]。
构成理解村庄里层的是历史的维度。
正是过去的历史,为研究农村政策在不同村庄的不同实践后果,提供了基础。
同时,正是在历史维度,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是如何变动着影响中国村庄内生秩序的状况,并因此为将来改进九亿生产、生活和娱乐在村庄的农民的福利状况,埋下了伏笔。
*本文系笔者关于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系列论文的第3篇。
系列论文的主要灵感来自最近数年与一些朋友的共同调查与讨论。
本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