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钟情爱美的白先勇Word文件下载.docx
《人物专访钟情爱美的白先勇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人物专访钟情爱美的白先勇Word文件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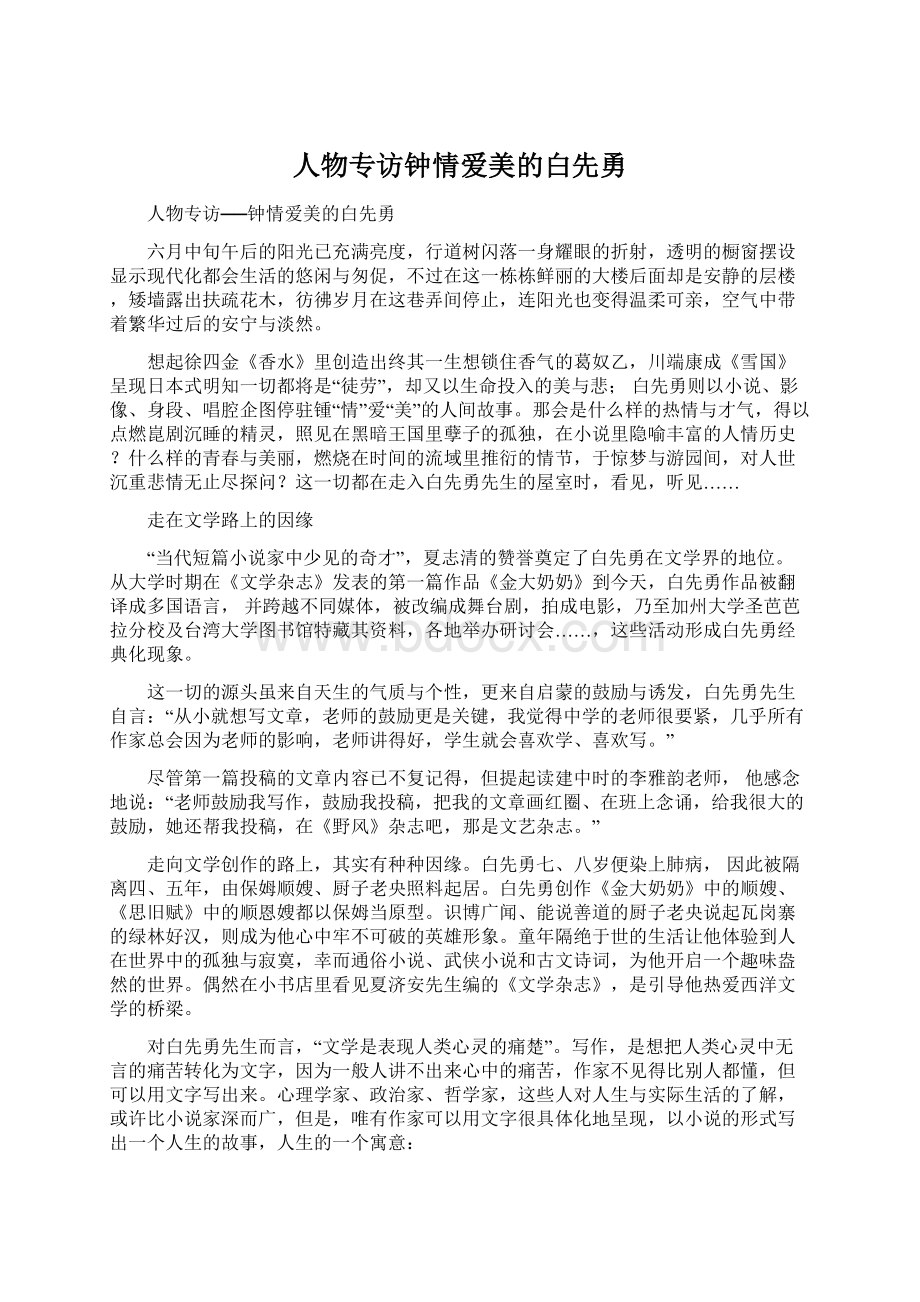
写作,是想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苦转化为文字,因为一般人讲不出来心中的痛苦,作家不见得比别人都懂,但可以用文字写出来。
心理学家、政治家、哲学家,这些人对人生与实际生活的了解,或许比小说家深而广,但是,唯有作家可以用文字很具体化地呈现,以小说的形式写出一个人生的故事,人生的一个寓意:
“我一向对文学有热诚,对我来说写作是心灵最深刻的,我觉得文学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影射,所以我想藉文字表达内心最深的一言一语。
我觉得,写出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的理解很重要。
文学是表现深刻人性、真实人生的一种艺术形式。
当然音乐、绘画及很多艺术都有这种可能,但文学是文字艺术,它可以呈现、可以说明、可以分析。
电影兴起来后,有人说它代替了小说,电影可能很深刻,但基本上电影还是一个技术上的,technology的科技跟娱乐成分在里面,我想文学才真正能够更深入。
当问起是否有以文章为不朽之盛事的期待时,白先勇先生谦称自己是以很尊敬、很严肃的态度对待文学。
文学对他而言始终是一种信仰,至于在写作里的位置和成就则留与后人说;
而文学对他而言,有些读者平常根本不可能认识、不可能交流,但是透过作品,那种了解,那种心灵上的沟通,让他交了很多知己朋友,这是他最大的安慰。
以技巧彰显主题之韵
白先勇的起点就是高点。
二十三岁发表小说就受到瞩目,二十八、九岁写《游园惊梦》,那么年轻怎么能写出那么老的东西,怎么写出那么老的感觉?
有人说那一定不是白先勇写的,而是他的前世写的。
白先勇也自认为二十八、九岁写《游园惊梦》,的确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写,能体会到的。
那么,白先勇是如何在艺术上求精进?
阅读经验如何滋养他的写作?
他如何选择题材,改变技巧?
除却儿时所读唐诗、宋词、笔记小说、《红楼梦》,就读台大外文系时接触乔伊斯、卡夫卡、卡谬、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他们笔下对存在思索的氛围也深深影响白先勇,让他体认成功的小说一定是作者选对了表达方式:
“这些作家经过两次战争,梦想被打碎了,他们处于一种哀挽之心……,比较悲观,与我所经历时代变动的心境契合。
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不能废掉,现代的世界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世界,他们的内容上、组织上有很大的吸引力。
技巧上,现代主义小说比较创新,挣脱了现实小说的传统。
现代主义也不光是小说,还有绘画、电影,那时候有一批新潮的电影,刚好在台湾看得到,像《广岛之恋》……,那时看了一大堆外国的新潮电影,整个现代主义的浪潮,对我们冲击而来。
他认为文学真正的精髓都是传统的,文化的陶养使作家在有形、无形中接上传统,因此如何赋予古老文化现代意义,就是文学所关注的。
此外,一个作家要写一个题材、一件人事物,一定得想一个最合适的风格来表现那个题材,否则便无法彰显故事,所以成败在于怎么去呈现的技巧。
例如他二十一岁写《玉卿嫂》,在摸索中选中了用小孩子的视角去说这个故事,不下任何价值的判断,以形成一种距离感。
当问及怎么抓每一个故事风格的表现方式?
曾经失败过吗?
白先勇笑说:
“先有了题材,才找最适合的文学形式来表现它的内容,愈深奥的题材所需要的技巧愈高,这是经过一些思考的。
以《台北人》这本书为例,是经过一番计划的写作。
我在爱荷华念完硕士,涉猎各家经典之后,想藉这本书创立自己的风格。
这一系列创作主题讲的都是民国的沧桑,人物虽然教育程度不同,但都是从大陆迁来台湾的,故事的背景都在台北,为有所区隔,使十四篇每篇风格迥异,特意让每篇小说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的视角,所以用词遣句也有所不同。
书里的人物是各省来的,我小时候走过很多地方,四川话啊、广东话啊、上海话啊,很多方言都会,就适当的运用一些。
我希望每个人物的不同个性,不同身分都能表现出来,也许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台北人》中十四篇的主题都是灭亡、没落,时间都属同一个时代,但风格各自不同,原来这是透过技巧与用词遣句所致。
除语言与视角等技巧上,白先勇也常运用现代的手法来写中国的古典传统,如以向秀诗《思旧赋》为题,借以写怀念故人之情;
以诸葛亮典故《梁父吟》为题,并作为军人的象征;
或以对往昔荣华的追忆,强化现时的败落,如《谪仙记》、《游园惊梦》,以完成对传统情殇叙事“伤逝”的哀悼。
换言之,除却一贯微观角度的呈现、偏重细节描写的笔法,在抓每一个故事风格的表现方式时是经过设计的,如写《台北人》时,同时也写《纽约客》,为使两本书的人事地与情调、风格不同,会因内容、人物而调整。
有些叙事手法是交叉的写法,像波浪般在过去、现在间摆荡,这是有意如此的。
因为很多重要事情是回忆,回忆是音乐性的,回忆对前后的撞击,有如听了音乐勾起来的一种情绪,像浪一样翻腾,而不是平铺直叙的。
以作品反映生命境遇之情
白先勇小说丰富的多义性,形成研究面的发酵,论者大抵着重于其悲悯情怀、民族乡愁、历史文化等国族关怀的层面,或就生命课题、表现技巧探讨,但同时也架空了作品特定的脉络。
事实上,他的小说题材与生命经历、个人生活有密切关系,从桂林、重庆、南京到上海、香港、台湾,不断迁徙流离的过程,接触的南腔北调、民情习俗,丰富了白先勇写作的背景,如小说《游园惊梦》便以南京秦淮河崑曲艺人为题材;
在南京家中出入的军政要人,形成《台北人》的主题;
十里洋场的京沪文化,令他创作出《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永远的尹雪艳》、《孤恋花》、《谪仙记》等小说。
这些或参与、或见证历史、或被影响的人物,成就了《台北人》强大的历史感,因此夏志清赞誉它是一部民国史。
贯串《台北人》的主旋律是沉重的昔今对比,眷恋过去的慨然,那诚然是身遭家国巨变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悼念,但何尝不是生命无常的感叹!
多年之后,回首年轻时所写,是否依然感慨深沉?
白先勇先生是这么回答的:
“我觉得最叫人感叹的,是美人迟暮、英雄老去。
人总会经历生老病死,总会老去,但是英雄老去,就格外叫人不舍……。
我写的很多都是美人迟暮、英雄老去,这个题材让我特别揪心,现在看还是如此。
佛家以一个『空』字道尽一切,也就是无常,像《桃花扇》最后的《余韵》: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想那一种心情,多少总会有的。
讲历史的沧桑,像《三国演义》的开场诗: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我想我写的可能是历史沧桑,改朝换代的历史沧桑。
从大的历史源流来看一九四九年的大转折,其实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元朝、清朝的外族入侵,社会价值、家庭结构没什么太巨大的变化,但这次是几乎连根拔起,搞得天翻地覆。
我在写《台北人》的时候,正好是大陆文革时候,看到外国记者拍红卫兵一个榔头挥下,千年佛像就粉碎了,那时候我想完了,我们的中国文明完蛋了。
这样破坏下去,完了,那时候心中相当沉痛、悲哀。
或许生长在台湾的这一代,无法了解时空异变、文化浩劫的沉痛悲伤;
没有经历过战乱的这一代,无法体会那种落败、回不去又无奈的历史沧桑,但时间的流转,生命的无常,必然是每个人都将面对的课题。
二十五岁那年,母亲过世,白先勇到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攻读硕士课程,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那一年《芝加哥之死》开启《纽约客》的伤感,叙述留学生面对离乡背井、空间地域、社会文化改变后的各种冲击与认同,与外在世界抗衡的生存中,小小的自足圆满空间都无可避免地崩塌,那种失根的状态是白先勇切身的感悟。
在白先勇的心目中,散文写的是真正的心里话,小说是虚拟的,在虚拟的中间也可以说你的悄悄话、真话,但是前面有一个面具,隔了一层。
所以阅读白先勇的散文跟小说时,会发现散文写的方法比较平缓,小说则很细腻,无论形容主角的出场、穿着或动作,空间气氛、表情与心情都写得很精致,就像崑曲一样。
散文则比较直接,散文真摰而感动人。
譬如《蓦然回首》点出母亲过世与出国是他生命与创作生涯的分水岭,密西根湖那段场景,隐喻在异国的孤独;
《树犹如此》娓娓细说与王国祥在建国中学相识相知三十八年的友谊与命运抗争的过程。
特别是以“树”象征好友,见证曾经存在过的生命以及人间的至情,树在人在,树亡人亡。
这一段最深厚的情感与最沉重的回忆烙印在作者心灵深处,其实也镌刻在读者心版上。
大陆开放以后,白先勇以散文记录寻根之旅,如《惊变》等。
对《台北人》里的移民而言,“台北”只是战乱之中不得不移居之所,只是企图还原怀旧情绪的空间,而非得到重生、系结情感与未来的原乡。
但白先勇以永远的台北人自居,他说:
“在美国住了四十几年,在台北仅住十一年,在人生中不算最长。
但从十三、四岁到二十几岁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期在这里,因此我一直以台北人自居。
台北对我很重要,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台北发生,从台北看出去的,所以对我而言,台北是创作的泉源。
尽管住在美国多年,那彷彿是很遥远的一段,还是没有这种与台北之间人事熟悉的感觉,没有属于那里的那种感觉,充其量只因为夏天很舒服,有很安静的环境写作。
以《国葬》吊挽时代结束之悲
《台北人》选了很多台北不同阶层的人物,有风尘女子、戏子、舞女,或是退休将领、老仆,以及《冬夜》里的老教授等,但“台北”是个引子,后面的回忆很大,包括整个大陆。
谈及为何以《台北人》为名,描写的人物却聚焦在这几类角色时,白先勇先生说道:
“其实我那时候写《台北人》,心中已有定位,第一篇就引了那首诗(指刘禹锡的《乌衣巷》),可见写的时候有一个大的方向,一个蓝图,否则我不会引这首诗。
那首诗的意义,就是西晋从洛阳东迁到南方建康,跟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台湾的处境很相似,所以有这种对比。
白先勇对于翰林国文课本选录《国葬》有点意外,一方面因为这篇蛮沉重的,另一方面是相较于其他篇,比较少人注意到这一篇,直到七○年代才有一个德国博士生以这篇做为博士论文。
对于《国葬》里面浓郁的吊亡送葬、时不我与之感,白先勇是这样解说的:
“我写父亲那一代,从人生来看,经过北伐、抗日、国共内战,这么一大串下来,历史怎么会不沉重?
那段历史的漫长、沧桑,恐怕第二代很难了解、很难承受,也不愿意承受,因为这个担子太大了,国破家亡的重担,会造成两代之间的隔阂,很难去理解。
由此可见,这种“家国之感”是时代造成的,很多老兵都有这种感怀。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李浩然这个人物可说是个象征,他是一段历史,他的死亡是一个结束,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篇是《台北人》的完结篇,等于是画下一个句点。
有人说《台北人》整本书是一首诗,哀挽一个时代的诗,《国葬》是这首挽诗的最后一句、最后一联。
白先勇个人的看法是:
“我觉得这个结尾很重要,如果拍电影的话,它的最后一幕是中山陵,我当时写的时候有意无意的选了这一篇,现在想选得太对了,整本《台北人》最后的image意象选什么最合适?
中山陵嘛!
我想中山陵是一个很大的象征,而且它是李浩然将军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告慰国父在天之灵的地方,最后一句:
『敬礼——』,可算是对那个时代的礼敬。
我昨天看到一本大陆出的书《抗战中国国际通讯照片》,好感动,里头收集抗战时候外联社的照片,看了这些,就知道多少国军打得前仆后继,要抹杀这段历史是不应该的、不可能的,多少性命为了那场民族圣战死了。
台儿庄大战川军的师长王明璋,领着全师打到最后一个全倒掉,全师全倒、一个不留……我想这些历史都是不可磨灭的。
这些壮烈忠勇的历史,应该有电影或史诗来还原,在高中课本里选了《国葬》,虽然沉重,但是含有许多意义。
和其他作品比起来,这篇叙述更贴近史实,论者多认为写的是其父白崇禧将军,白先勇先生的回答是:
“感觉上……是觉得写我父亲,事实上不是如此,事实上是痕迹。
其实李浩然这个人物是个象征,象征民国那段历史,他的死亡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
听见白先勇先生如此慷慨激昂地叙述,大时代虽然结束,却意义非凡的分析,先前大家对于白先勇总写回不去的感觉,好像还耽溺在那个光荣的历史、那段辉煌回忆的疑惑顿时一扫而空,甚至从心头发出感叹,的确应该把这些历史写出来。
接着,老师指著书上的照片说道:
“这张是台儿庄,在徐州,李宗仁是第五战区的司令官,我父亲被派去和他一起指挥台儿庄。
这是最重要的一战,台儿庄大捷全国士气大振,所以我想这是对过去历史的一个回顾,一个悼念,一个礼敬。
就像文章里以“中山陵”标志革命建国,寓意整个民国,但是也有历史的悲怆在里面,因为大陆到一九四九年就失去了。
而《国葬》是对那段历史的致敬,也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致哀。
这让我们思及全球化的时代,要如何教导学生具有国家的认同?
白先勇乐观地说:
“对国家的认同是本性,是对国家很自然的感情。
这和国家主义不同,但政治上拿来利用便成为很可怕的毁灭力量。
特别是外族入侵,像抗战的时候,国家主义高涨,那是对付外敌;
反过来,用国家主义来控制人民,或侵略别的国家,那就非常可怕了。
说到认同,白先勇先生强调:
“我心中的中国是文化的中国,是《诗经》、《楚辞》传下来的文化,是黄河、长江这种地理上的大中国。
当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毫无关系,因为没有在那边生活过,没有任何关系。
”他心目中的中华民国在一九四九年后就消失了。
父亲那一辈的“中华民国”已经结束了。
台北的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章节,是另外一个架构,历史的另外一个架构。
因此《台北人》写的是那一代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感和文化上的乡愁,是“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溢着兴衰无常的回顾。
以浪漫写青春与情欲之美
笼罩着灰蓝色调的“王谢堂前燕”,那没落与变迁的沧桑感已成为白先勇小说中鲜明的基调,但为一个时代结束而书写的同时,何尝不意味对青春美好的耽溺,对人情浪漫的看重?
每个人都有年轻的一段岁月,作家总会写些年少情事,而白先勇显然十分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尤其在同性情谊上着墨甚多,早期短篇小说集更以“寂寞的十七岁”为书名。
就白先勇自己的说法是:
“我们经过十七岁,像《孽子》那样的青少年的成长是我蛮关切的,或许因为自己蛮懂他们吧!
”当我们好奇地问,是很懂他们的成长经历,还是跟个人亲身体验有关?
白先勇先生的回答是:
“我想是有吧。
每个人的青少年成长都有一番挣扎的过程,而同性恋青少年的成长更加复杂崎岖。
童年因肺病被隔离在上海郊外四、五年,那时候大概十岁左右,那寂寞使我变得很敏感而多愁,加之以不断换环境,陌生学校是很令人害怕的。
其实那不是我的本性,到大学时候恢复我原来面目。
《寂寞的十七岁》在某个方面大概有我孤僻的东西存在,不过那种孤独感是人生的寂寞,倒不一定是遭遇如何。
那种情境我特别感觉得到,而且我喜欢。
的确,从早期的《月梦》、《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经过《台北人》中《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孤恋花》,到集大成的长篇小说《孽子》,再到后来发表的DannyBoy、TeaforTwo,隐然自成一系列的同志主题创作,在白先勇个人与艺术生命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他还写了篇《给阿青的一封信》,表达同志们渴望获得家人认同的沧桑心声。
或许是天生对于青春的关切,使得白先勇在书写青春主题时,无论描写情与欲、灵与肉、青春与死亡都含着某种程度寻找美、诠释美的心情。
对此白先勇认为:
“『情』与『欲』都是天生的一部分,很难去区分,是一种人性,很难说清楚。
希腊神话里半人半兽的怪物,有人类的身体,而兽一切原始的信念也在那里,头是往上的,是升华,又有沉重的肉体在拖累他,是以灵与肉、精神与肉体都在人里面。
成功地塑造人物是白先勇写作的最大关键,他尤其喜欢写边缘人物的情与欲。
很多人好奇从《玉卿嫂》、《金大奶奶》……,写的多是中年妇女,或是舞女等边缘人,当我们问到这点时,白先勇笑着说:
“这些人爱起来很勇猛,猛烈得很,这么激烈的爱情,动人心弦,像玉卿嫂为爱杀人,卢先生为大陆上的表妹守着这段情,或像王雄那样讲不出来却有满腹的激情,也是热情,我想有时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就是passion、激情。
”至于被问到在现实生活中是否也憧憬这种激烈的爱情时,白先勇以“哈!
”做为应答,继而笑道:
“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现实生活里若是这样子就闯祸了。
以艺术留存文化之美
幼年时与家人在上海听了梅兰芳复出演唱的崑曲《游园惊梦》(俞振飞、言慧珠等合演),自此爱崑成痴,加之以文革大举破坏的撞击,白先勇自许要为这“此曲只应天上有”的文人戏剧当义工,因而三度制作演出崑剧《牡丹亭》(一九八四年徐露版、一九九二华文漪版、二○○四年推出青春版)。
白先勇之所以再推出青春版《牡丹亭》,除却因为以美传情的《牡丹亭》是他心目中“至于极尽”的代表,更缘于想培养年轻演员与年轻观众,激起他们对美的向往与热情,最重要的是振衰起敝,并树立崑曲的典范,让大家能看见精致的崑曲美学。
二○○八年十一月《新版玉簪记》首演,至于选择《玉簪记》是因为:
“《玉簪记》可爱,很讨喜,年轻人看起来比较轻松,和《牡丹亭》是不一样的感觉。
一个是传统、古典,一个是可爱,再加上字、画、琴等元素,可看见古文化的灿烂。
此外,第一,它是崑曲的一个经典,很注重生旦戏表演,是相当典型的崑曲。
第二,词很美,曲也很美,出嫁那一段更是缠绵。
第三,爱情啊,这是永远会打动人心,永远吸引人的主题,更何况这个故事很了不得,戏里女人不惜一切地追求爱情,道姑追到江心,演得好像全台都波动起来。
无论是《牡丹亭》或《玉簪记》都集合了两岸三地戏剧、舞蹈、舞台、灯光、服装设计等艺术界菁英,让崑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白先勇特别强调:
“我一直觉得要创新、创新、创新……,我很能接受创新的东西,但我也尊重传统。
传统,我觉得很了不得,何况我们的书法、水墨、崑曲、古琴多么优秀。
因此在制作《玉簪记》时大量运用了书法跟水墨画,在灯光设计也做了些改变,也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整合各种艺术特质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
这齣戏以情传情,以诗传意,一方面尽量保持崑曲抽象写意、以简驭繁的美学传统,也适度运用现代剧场概念来衬托。
因此运用最古老的元素,如董阳孜的书法融入舞台设计,奚淞画的佛像、水墨画相互辉映,古琴放在现代的舞台上面,让它有现代的生命。
显然这种想法很受欢迎,年轻学子看得欢天喜地,白先勇说起这段,笑说最快乐的是:
“把董阳孜、奚淞……叫出来,磨合、讨论的时候很开心。
在白先勇心目中,崑曲是五百多年前古老的剧种,集中国表演艺术及美学的大成,曾经独霸剧坛两百多年,深入民间,后来衰微,因此一心想重振崑曲的他,开心的并不仅是集当代名家共襄盛举,不单是让戏在舞台上风光亮丽地演出,更在于唤回文化的青春:
“我对于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信念,觉得有一天,不是哪一天,是很快,中国文化有一个契机。
我觉得几千年的文化有韧性跟生命力,应该要有新的契机,而那个契机应该就在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世纪再不复兴,我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中华文明危险了。
当全球化时,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会完全的西化,甚至失去自己的语文。
我想所有巴布达人、伊拉克人,面对他们的古文明沦落到这个地步,那种文化消失的心情,民族没有希望的挫败感受必然很深。
文化不复兴起来,那个民族就没有希望,所以我做崑曲怀抱着一种希望,要给我们的语文现代精神,要给我们的文化一种现代生命的青春版,要把这股青春生命唤回来。
目前《牡丹亭》已演出了一百六十多场,从中国大江南北各名校到台湾,从美国、欧洲、亚洲各国,吸引二十多万人观看。
西方人为之惊艳,赫然发现中国人的歌剧早已这么成熟、精美,比他们的歌剧还早了两百多年。
《玉簪记》也引起热烈回响,但如果没有白先勇登高一呼,必然无法完成《牡丹亭》经典示范,而我们也深信崑曲的种子已播下,不信青春唤不回!
寄语年轻惜时筑梦
对高中生的读物,白先勇认为如果从《台北人》里选,他会选读《一把青》,一则容易懂,另一则叙述爱情、失落,或者选《冬夜》讲五四运动时的知识分子,背景比较贴近历史。
《游园惊梦》适合在大学里读;
至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有戏剧感也适合,可以与电影对照。
大家一定好奇,白先勇对想写小说的学生,有哪些建议?
他的建议也正是许多国文老师所殷殷叮咛的话:
“先读经典,从《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醒世姻缘》这些好的小说看起,再把外国的经典也看十几本做底子就不会虚了。
当然要念我们的故事,古时那些诗词语言,美到最精致,那是文字营养的成分。
我很担心很多年轻孩子光看一大堆翻译的东西,那些句子都欧化,先学那些东西就学坏掉了。
我在写作时,会刻意避免欧化的句子出现在我的小说中,这是我最在乎的一点。
对于章回小说,白先勇特别说明:
“《红楼梦》是一本天书,那是每个人都要看的,而且要看一辈子的。
十八世纪突然蹦出这一本书,这是直的;
从纵的来说,中国最早的小说是《三国演义》吧;
横的来讲,十八世纪时,西方小说是到十九世纪才遍地开花的。
《红楼梦》的好说不尽!
基本上,它的视野广阔,结合中国的人生观,以小说的形式来隐含儒家、佛家、道家哲学的思想,那么深刻、广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人物这么复杂,就像洒豆成兵,每个人写得鲜活灵动,这太不容易了。
小说第一考验人物写得好不好,《三国演义》、《金瓶梅》的人物都写得很好,但是《红楼梦》更宽广,不只写贵族阶级,连刘姥姥这种乡下老太太,谁写得过它?
这么一个乡下老太婆,已经成为一种典型了,贾府就不用说了,连这样的乡下老太太都写得这样好,没有人比得过它。
第三点,小说里的对话,最厉害的是,你随便翻开一页,看人物讲话的样子就知道是写哪个人物,每个人都是个性鲜明的,对话更是了不得。
第四是叙述文字华丽,这全得力于古典文字诗词。
第五是它的寓言架构,象征手法严谨,伏笔千里,这种架构是以前没有的。
白先勇对于现在的年轻孩子的建议则是:
“因为年轻,千万不要浪费青春。
时间一去就不回头了,做年轻时候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该念的书去念,该玩的去玩,该交朋友去交。
青春太可贵了,千万不要浪费,如果书没好好念,朋友没好好交,或是去做伤害的事,那便是浪费时间。
去看好电影,去旅行,去跳舞,去唱歌,哈……我喜欢跳舞,我也爱唱歌。
我大学时候跳舞,什么都来,不要浪费。
好好念书,好好玩。
所谓“人不痴狂枉少年”,白先勇所谓青春勿虚掷,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