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俞宣孟与于连的对话Word文件下载.docx
《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俞宣孟与于连的对话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俞宣孟与于连的对话Word文件下载.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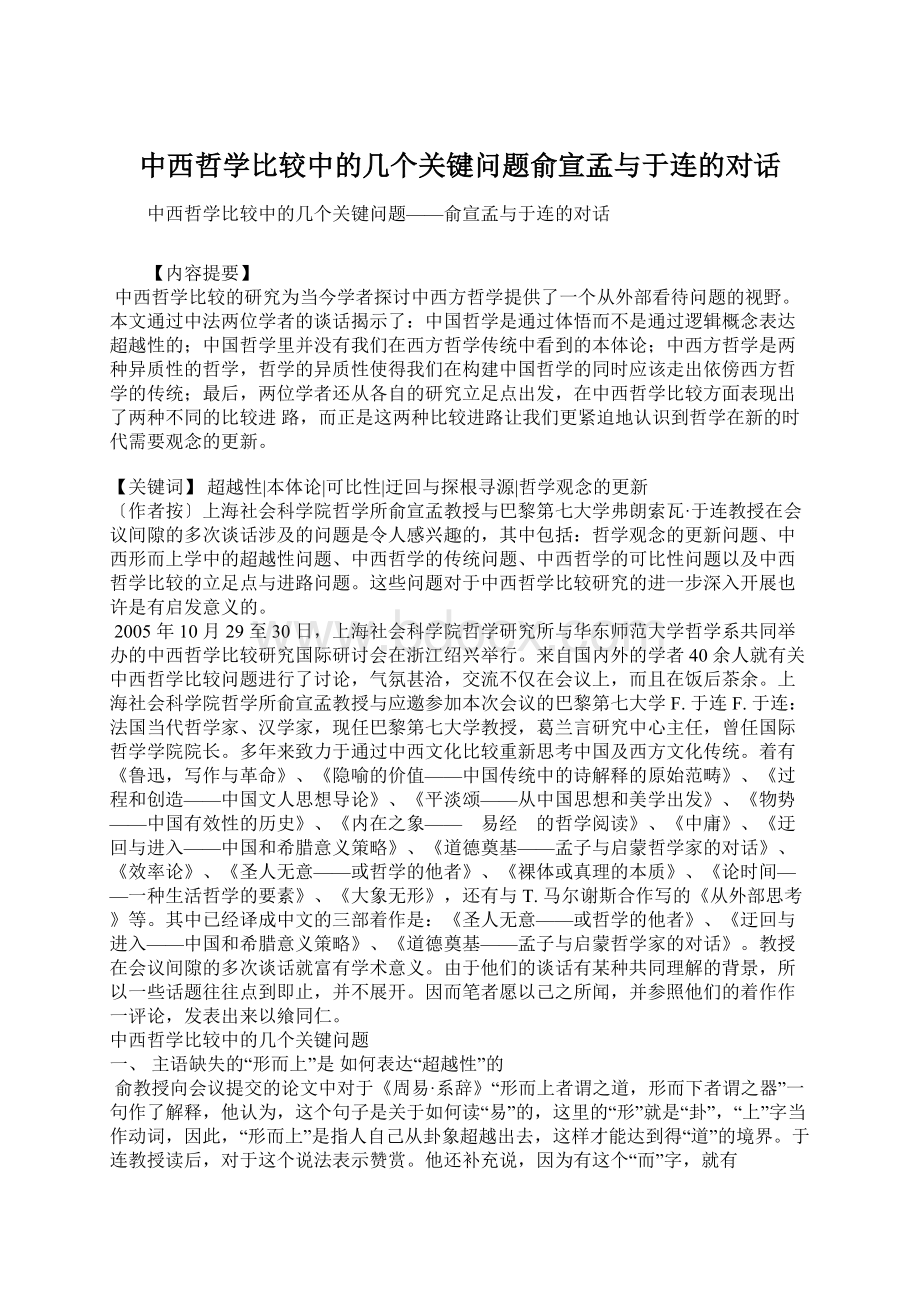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巴黎第七大学F.于连F.于连:
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现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葛兰言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
多年来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重新思考中国及西方文化传统。
着有《鲁迅,写作与革命》、《隐喻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解释的原始范畴》、《过程和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平淡颂——从中国思想和美学出发》、《物势——中国有效性的历史》、《内在之象—— 易经 的哲学阅读》、《中庸》、《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效率论》、《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裸体或真理的本质》、《论时间——一种生活哲学的要素》、《大象无形》,还有与T.马尔谢斯合作写的《从外部思考》等。
其中已经译成中文的三部着作是:
《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
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就富有学术意义。
由于他们的谈话有某种共同理解的背景,所以一些话题往往点到即止,并不展开。
因而笔者愿以己之所闻,并参照他们的着作作一评论,发表出来以飨同仁。
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主语缺失的“形而上”是如何表达“超越性”的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对于《周易·
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作了解释,他认为,这个句子是关于如何读“易”的,这里的“形”就是“卦”,“上”字当作动词,因此,“形而上”是指人自己从卦象超越出去,这样才能达到得“道”的境界。
于连教授读后,对于这个说法表示赞赏。
他还补充说,因为有这个“而”字,就有…………上升的意思。
俞教授说,“者”字在此,不是指“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复指词,指“形而上”这个过程。
但是,于连要求知道把“形”说成“卦”的理由。
俞教授说,首先,这句话出于《周易·
系辞》,那是释《易经》的,在《易经》中,“卦”又称为“卦象”、“象”,“象”和“形”在这里是同等性质的东西,故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
其次,同样是关于读易方法的王弼主张,“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忘象”就是忘卦,但是人只能有意记住某些东西,却不能有意忘掉什么东西,可见这里的“忘”字是人主动放弃对象的执着,是指人自己生存状态的转换。
更主要的是,“形而上”指人自己状态的转换,这符合传统中国哲学一贯的精神,即,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得“道”的境界是需要人自己去追求的,“道”并不是脱离了人生而“客观”存在的东西。
谈到这里,于连教授说,看来中西哲学的不同还与语法相关。
中文句子可以没有主语,这就给俞教授那样的解释留了余地。
俞教授补充说,黑格尔也注意到了汉语的这个特点,他指出汉语中没有被动语态,这与没有主语是相关的。
但是黑格尔意在说明,中文是一种含糊的语言,不利形成哲学概念。
依据俞教授论文中讲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虽然是西方超越观念的源头,但是在一些英文版本的柏拉图着作索引中都没有列出Transcendence这个词,因此可能柏拉图本人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于连教授纠正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章末尾应当提到这个词。
从上面的谈话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缺乏主语的,即我们看不到“形而上”主语是谁,也就是说,当谈到“超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在“超越”以及“超越”的意义何在。
然而,我们也并不因为这句话欠缺主语就阻碍对这句话的理解。
事实上,古代汉语缺乏主语这种语法现象,并不表明中国思想不指示哲学意义,相反,却显示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意义,这种哲学意义不像西方传统哲学家那样追求特定的结论性的东西,而在于呈现“彼-我”相一致的协调或适应状态;
中国哲学不存在刻意追求一种客观的“道”,“道”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人所体验,而对于具有文本阅读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个未被言明的主语其实就是读者。
“形而上者”的“者”,通过复指,是要读者体验“形而上”时的情形。
于连教授还提出:
语法对哲学形态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现书写文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语法结构了;
而在中国古代却并未出现像西方语言里那样严谨的语法结构,只是到了现代中国,汉语语法才依傍着西方语言诞生。
虽然“形而上”没有标明主体,但是也只有我们大家在阅读文本和体悟文本中的哲学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超越活动,而这里所说的“超越”也只能是在意识中的一种领悟性“超越”。
不存在主语,却时刻要求主语存在,只有不忘记自我的体悟才能理解“道”;
在希腊和罗马哲学语言中一个句子存在主语却忘掉了主体与客体的适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西方出现主体去主动逻辑地构建一种客观的概念体系。
俞教授进一步说,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往往通过对应一个具体的“实”来理解,也就是说词的意义通过“实”来表达,即名副其实。
当柏拉图说,动词一开始也只是描述一个动作的名称,这说明西方人最初也是名实相符的,只是在本体论中,才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特别是在柏拉图哲学那里,一个词的意义最终要通过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来建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
中国古代哲学并未出现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以本体论为主要形态的形而上学。
从“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中国哲学中也有“超越”的特征,然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只是基于“形”的一种对“道”的体悟,它仍然是人自己的体悟,并不是对不可感的东西的概念性的思考。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史要依据中国哲学中的特质、而不是依据西方哲学传统,更没有在中国哲学中追求或建立一种概念发展史的必要。
二、本体论问题在中西哲学
比较中的意义在于连教授向会议作的主题报告中,他谈到自己与福柯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
他介绍说,福柯不承认西方传统有什么特点可言,那是因为福柯站在西方传统的内部,看到西方传统还在向各个方向发展。
但是,如果站到西方传统的外部,譬如从中国传统的背景去看,那么,西方传统的特点就会凸现出来。
但是,于连对于当场被提问:
相对于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特点是什么,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在会见的交谈中,俞教授又提起这个话题,并且明确指出,标志西方哲学传统特点的是本体论。
对此,于连表示赞同。
而且,他明确表示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本体论与西方语言的系词Etre有关,是纯粹概念的体系。
俞教授一向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
他认为,肇始于柏拉图的本体论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而理性主义则代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
这不仅表现在怀特海等人所说的,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而且,还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反叛主要也是针对着本体论的。
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抓住本体论就是抓住了比较对象的主要特征。
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二者以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那么本体论具有哪些特点呢?
俞教授认为,本体论是通过逻辑概念相互结合形成的超验的普遍原理体系。
首先,本体论构建了一个超验领域,也就是说一个超越感觉的领域,只有理性才能把握,这就是二元论;
其次,本体论的语言使用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逻辑范畴,这种逻辑范畴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的意义不是通过指示“实”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的;
再次,本体论是以最普遍的形式表达事物本质的第一原理。
所谓宇宙规则、绝对真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最后,俞教授还指出西方哲学重在人们通过学习达到一种逻辑思维训练。
于连教授在他的着作中也明确表示过,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建立起一座如我们在西方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大厦于连:
《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
于连教授还深入论述过西方本体论这种哲学和语言的关系。
他说:
“西方传统意义上的Etre,在古典中文中找不到相对等的概念。
因为正如本弗尼斯特告诉我们的,Etre的话语,即‘本体论‘,只是说明在某些希腊的语义根源和语法范畴中意谓的东西也是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传统,也就是语言学传统所意味的东西。
”杜小真:
《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在于连教授看来,本体论的特点就在于以其逻辑规定的语言追求普遍,而哲学家通过‘抽象-建构‘来设定普遍性原理同上,第51页。
。
他还认为,西方哲学离开智慧,走得太远了,因而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创造力,他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一种异质的哲学中获取启发,为理性打开一扇门,恢复理性应有的创造力。
三、哲学观念的更新
虽然于连教授不愿意直接指明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什么,但是在他的谈话里还是能够体现出,中国哲学更多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哲学。
于连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建立起本体论的大厦,智慧是‘道’。
”于连:
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
于连教授说:
这种智慧之学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普遍性的原理,而是一种自然的内在性流露,它保持了“中”的开放姿态,而不是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走上了一个极端的寻求普遍原理的不归之路。
智慧的语言可以说是从内在性流露出来的;
智慧通过连续流动而起作用,进而达到一种穿越;
“智慧的圣人‘无意’,比如儒家的‘中’。
道家的‘虚空’,也就是避免固定在某一局部之中,而在‘可能性’中追求‘变化’。
”《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第51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
于连教授在一本谈话录中曾说过:
“中国思想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是哲学地形成的:
规定自己的术语,明确辩论的模式等等。
其实,我认为中国人知道哲学,中国有哲学的可能性,但又是‘反哲学’的。
……而且,中国古代也有争论的传统,比如墨家在这条道路上就走得很远。
但是,许多伟大的中国思想家,比如庄子、孟子,他们怀疑‘辩驳的陷阱’。
”所以,他说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立足策略。
于连教授一方面不否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有哲学的可能”。
这似乎表明,他对于缺少“论辩”的东西是否是哲学还有疑虑。
俞教授主张,应当突破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并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哲学观念更新的时代。
比较起来,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对于哲学有极大贡献的哲学家都没有面临过哲学观念更新的任务,因为他们仍然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
这种突破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
我们不应该把哲学仅仅看成是理论。
实际活动是理论的根据,它本身也是哲学的。
对此,于连教授感到疑问,他问,一切民族都有活动,那么是否他们都有哲学呢?
俞教授的回答是,哲学作为学说,当然要有所说,说不限于理论性的说。
把对于实际生存活动的方式的反思说出来就是哲学。
反思的方式也有不同,西方哲学的反思方式是“看”,idea和theory的词根都与动词“看”有关,在“看”的反思中,人必须从自己当下的活动中抽身出来。
中国哲学的反思不是像西方那样理论性的,它是当下的体悟,其所说的内容是对自己体悟的描述。
生存活动是哲学的基础,只要对自己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形之于说,就是哲学。
照俞教授的说法,甚至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作为一种学说的哲学的那些民族,他们一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说出来,也可以有哲学。
他认为生活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生活的自觉。
四、中西哲学的可比和不可比性
俞教授认为,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到了近代显得更为突出。
在如何看待中西方哲学的时候,俞教授认为这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
无论从各自的关注视域、哲学语言性质、表达形式还是在各自哲学目的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既然中西哲学是异质的哲学,那么这两种哲学的比较似乎就成了问题?
然而,当我们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出过这两种哲学是否可比的问题,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于,由于没有考虑中西哲学可比性在哪里,现当代学者往往依傍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来构建中国的哲学史。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是本体论的传统,但是中国哲学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于是,一部依傍西方哲学构建的中国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特质被遮盖的哲学史。
所以,中西哲学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存在可比性,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是可比的就成了一个隐而不显的问题。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试图变不可比为可比,他认为,中西两种哲学是异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可比的;
但是就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事哲学活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又是可比的。
从事哲学活动用英文讲就是“tophilosophize”,人的生存活动应当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不同的超越方式造成了不同形态的哲学,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不同生存方式却具有相同的结构。
从同一个生存结构描述各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并从不同的生存方式去解说不同的哲学形态,这就是比较哲学所能做的。
于连教授对于不可比的问题似乎并不关切,对他来说,为了暂时跳出西方哲学的传统,越是差异性比较大的哲学越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异质的哲学,因为它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脱离印欧语系——存在一个大印欧语系;
脱离历史、影响和交流的关联;
最后,要找到的是一个在文本中陈述出来的远古思想,而且具有原创性。
同小注⑥,第4-5页。
于连教授还引用了福柯的“异域”这个概念来分析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并从差异性出发阐述了中西哲学可比性观点。
他认为中西方哲学是各自发展出来的哲学,并遵循了各自不同的途径,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异域”的哲学。
但是,虽然并不相关,却并不代表二者不能平等的对话,所以于连教授就是要借助“个体案例”的阐释并通过文本的解读,找到一种可以让这两种哲学平等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彼此的无关性,同上,第36页。
进而呈现两种哲学的“所未思”以恢复中西哲学各自应有的创造力。
对不可比的关注和不关注,使俞教授和于连教授走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
对于俞教授来说,不可比的问题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虑,为了克服疑虑,必须为中西哲学之为哲学寻找到一个一致的说明,这就是深入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源。
对于于连教授来说,他没有为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做说明的压力,异质的中国哲学反而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
五、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两个进路
两位教授从各自的研究立足点出发,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表现了各自不同的进路:
一种是从远到近的“迂回”的进路,一种是自下而上的“探根寻源”的进路。
于连教授按照自己“迂回”的策略:
首先以希腊为起点并离开希腊前往中国,然后从中国哲学里发掘西方哲学中所“未思”的东西,反过来又以平等的姿态来看待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从而凸现出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
于连教授曾在《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那本谈话录里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在哲学传统内部很难进行彻底的问题探讨,因为在哲学中必然保留一种未被提问的基础——我们总是由之提出问题,而对这个基础我们不能提出问题。
”⑨这在同时回答了为什么他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从西方传统内部解构,而是利用“迂回”的策略,从外部这样一个“异域”来解构西方哲学传统,当然,于连的本意不只是解构,而是解决,如他所说的,“我们如何思想”的问题,从而“为理性打开一扇门”,而迂回中国进而回到希腊就是他所选择的途径。
俞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试图给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探根寻源”式阐释:
他首先从海德格尔的“生存状态分析”回溯到巴门尼德的“真理说”,再从巴门尼德的“真理说”返回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及其初创的“本体论”,然后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直至黑格尔所代表本体论巅峰:
《逻辑学》。
经过从西方现代哲学到古希腊哲学的回溯,从而澄清了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特征及其起源、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
在谈到如何看待中西哲学关系的问题时,俞教授进一步说明,中西哲学并非是两种毫无关联性的哲学,西方哲学也并非代表一种普遍性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但是这种差异也并非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
中国仅仅处于前哲学状态。
恰恰相反,中国保持了哲学的根源,所谓西方普遍的哲学原理也只不过是这种根源的一种表达而已。
俞教授还从“超越”这个词出发,阐明了中西哲学各自“超越性”及其生存状态结构性特征。
他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性不同于形而上学的超越性,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已经说明中国哲学中的“道”不离“形”、“形”不离“器”的特点,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具有像西方传统那样的经验与超验的二元分离世界,具体说,就是指,在中国哲学里不具有追求纯粹知识的普遍性原理传统,即本体论传统。
中国道家传统哲学虽然强调形而上的“道”,但是获得“道”不是一种纯粹知识性的理论,而是依赖于人们的体悟以达到的一种与“万物合一”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
中西方传统哲学虽然具有差异性,但是这两种哲学都可以从同一种根源得到解释。
这是因为,西方传统哲学虽然是一种追求普遍原理的哲学,但是这种哲学离不开其历史根源,即离不开人们实践活动,也就是古希腊哲学家进行哲学实践活动。
事实上,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人们从事哲学活动的产物,而两种哲学活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各自所具有的生存结构的差异,这里的生存结构也不是任意的主观实践活动结构,而是一种“beingintheworld”特定结构,“彼—我”就是在这个限定的结构里得到说明的,而当中西方哲学利用各自不同方式进行阐明的时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显现层面,而要去追溯其所以然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