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5篇Word文档格式.docx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5篇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5篇Word文档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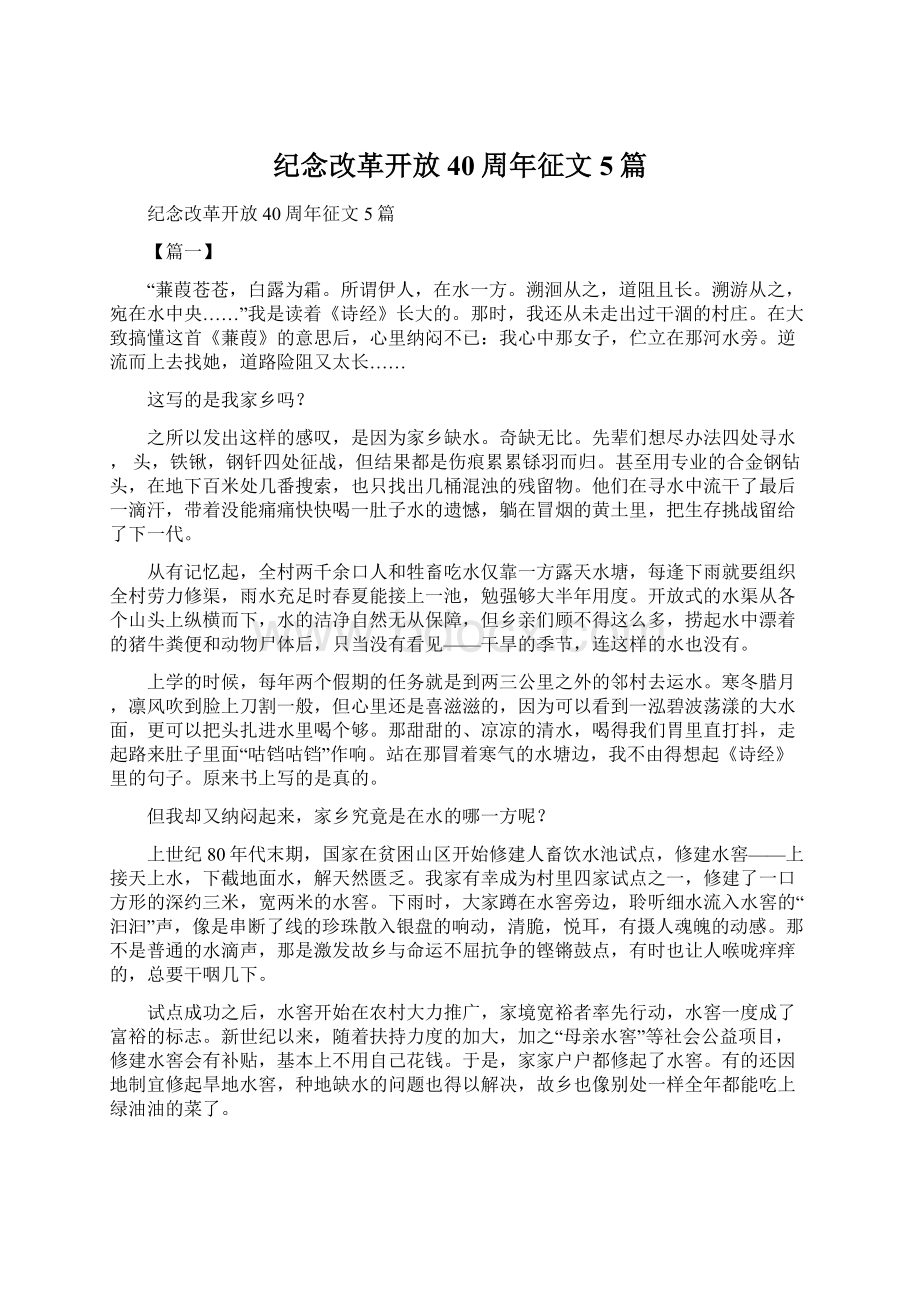
新世纪以来,随着扶持力度的加大,加之“母亲水窖”等社会公益项目,修建水窖会有补贴,基本上不用自己花钱。
于是,家家户户都修起了水窖。
有的还因地制宜修起旱地水窖,种地缺水的问题也得以解决,故乡也像别处一样全年都能吃上绿油油的菜了。
从村子里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见到的世面也越来越广。
他们讨论着别处的河流如何宽广,自来水如何方便。
听到这些,母亲说,人们不知足,有水吃就行了,还想用自来水,咱们这儿根本就没有河。
那么高的山,水咋过得来?
母亲没读过书,也没见过大世面,她不相信那根细细的水管能穿过崇山峻岭,越过沟涧来到这个世代干旱的地方。
父辈们大多也不相信。
2009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试点移民搬迁启动,乡亲们通过电视得到这个消息,都还半信半疑;
从丹江口调水到北京?
那么远咋去啊?
直到附近的亲戚们跑来告知要搬迁的消息后,他们才相信这个事实。
他们开始关注这项发生在身边的重大工程,闲暇时都围在电视边,打听着工程的进展,还做着那些难离故土的外迁亲戚的工作:
哪里水土都养人!
2014年12月12日,围坐在电视旁边,乡亲们亲眼目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丹江口水库的水一路欢声笑语,咆哮着向北冲去,兴奋之情像是那渠水来到了自家门口。
一张张黝黑、干涸的脸上笑靥如花,他们搜肠刮肚想寻找个赞美的词语,但最后发现如同当年四处寻水一样,并没有什么结果。
有人带头说:
真厉害!
于是大家纷纷附和,厉害!
太厉害了!
让乡亲们真真正正感受到厉害的是我们村里真正通上自来水的那一天。
母亲打来电话兴奋地说,咱们这儿也吃上自来水了!
通过电波我仿佛都能看到母亲那手舞足蹈的样子,随后,手机里传来人们嘈杂的说话声和笑声,便掉线了。
急于想求证自来水是从何处引过来的,我赶回家乡。
看到每家每户门前伫立着白色的水管和银色的水龙头,它们高傲地昂着头,俯视着村庄的一切。
欢快的水流冲击着地面,溅起的水花形成一个巨大的笑脸,饱经沧桑,幸福满足。
母亲满脸笑容地洗着刚从地里摘回的青菜,回应着我的话:
国家都能把水从丹江口调到北京,咱们这点距离根本不算啥。
不远处的学校,传来孩子们整齐的读书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在水一方,曾经是乡亲们朝思暮想的梦境。
而如今,这个梦终于实现。
【篇二】
衣服也会说话。
人潜在的秘密会通过穿的衣服传达出来。
也许,这些衣服已经存放箱底,已经被遗忘,但是,这些衣服一直没有忘记述说,一直没有忘记表达,它们代表了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真实记忆。
这天,母亲收拾衣柜,抖落出一件小巧的白色衬衣对我说:
“这的确良衬衣是七几年给你买的,已经四十多年了,不记得了吧。
”母亲递给我,因为在衣柜里存放太久,一股轻微的霉味扑面而来。
我捧着白衬衣走到窗前,仿佛看见自己穿着白衬衣走在乡村小路上的样子,一摇一晃,帆布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
微风在身后跟着,我觉得那时候风都是幸福的。
那时候拥有一件的确良白衬衣,就像是拥有了全世界。
关于白衬衫,母亲还给我讲过一个“笑话”。
那时候家里缺钱,一年四季都穿劳动布衣服,一天,我看见邻村的伙伴穿了一件熏白的的确良衬衣。
回到家,我就死缠着母亲要白衬衣。
咋办?
没钱买呀。
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就去问猪圈里的那头小猪崽。
“老大想穿白衬衣。
”小猪崽答:
“哼。
”意思再明白不过了,类似于知道了。
“没钱呢。
“哼哼。
”“再哼哼,把你卖了,就有钱给老大买白衬衣了。
”就这样,母亲一狠心把猪崽卖了,给我买了这件白衬衣。
我站在窗前,想着母亲讲笑话的那个情景,心里酸酸的,青涩少年哪懂生活的愁苦。
这时看着母亲在屋里转来转去,她一头的白发和我捧着的白衬衣,晃得我眼睛痛。
那时候,尽管家里穷,却影响不了一个少年跃动的心,小巧的的确良白衬衣里面藏着充满梦想的我,像一轮从山口喷发的日出,跃跃欲试。
我一直忘不了那些年的夏天,和伙伴们躺在草坪上望天空的情景。
把的确良衬衣遮在自己头上,隔着白衬衣看天,天变得低了一些,天空一下子温柔下来,无数蓝色的小天空在眼前晃来晃去。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尝到了土地“包产到户”的甜头——种的包谷第一次吃不完,往粮站卖。
父亲为了感谢母亲在土地上的辛苦刨弄,给母亲买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
我正读初中,当时学校最流行的穿着,就是黄军装。
村里比我大四岁的军哥去部队当兵,一次探亲回来,穿了一身黄军装,威武极了。
他来我家给父母拜年,当时看得我两眼发直,我缠着问他,没有给我带东西?
他笑的样子也很好看,问我:
要啥子?
我盯着他身上的黄军装说:
黄军装。
他立马答应回部队给我寄一身回来。
军哥回到部队,我就立马写信给他,我把信写得情真意切,甚至说了,长大了,一定像他一样当个军人,为祖国作贡献,报答军哥。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军哥寄给我的一套旧军装。
我迅速穿在身上显摆,衣服大了点,我瘦弱的身材在肥大的军装里摇晃。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穿着军装在校园里照了一张彩照。
现在翻出那些照片,一阵阵好笑,黄军装里面藏着我那些年的无邪、天真。
一天,我把军装洗了晾晒在学校窗台上,一节课下来,我的军装不见了!
一天上课都没了心思,到了夜里,我一边想是谁拿了我的黄军装,一边想着那空空的窗台,辗转反侧。
过了几天,我在一个早上,突然看见刘同学穿了一身黄军装,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我的黄军装,一滴蓝墨水还清晰地印在袖口。
我激动地跑过去,俩人目光碰上了,我却紧张得不敢说话,先前想好的词全跑了。
他看着我笑,我傻乎乎看着他笑。
我看他脸上的表情,好像他不是贼,而我自己倒像是贼一样,我赶紧像贼一样跑了。
后来,刘同学当了兵,他从部队给我寄了一套崭新的黄军装,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我理解到他内心想要表达的那种歉意。
我一直存放在衣柜里,没有穿它。
我想,我是藏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黄军装懂我一直想要说的话。
从那时起,我心里明亮了许多。
衣服穿在身上不仅是为了好看,更多的是为了衬托我们那一颗温暖热烈的内心。
九十年代初,我参加工作。
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乡上的“万元户”表彰大会,当时那个“万元户”穿一身西服,胸前戴着红花。
那次会议激发我用领到的第一个月工资,也买了一套当时流行的西服来穿——蓝色斜纹布料的。
第一次穿西服怯生生的,走在街上,好像有许多双眼睛在看着,走路都有些不自然了。
我急匆匆穿过小镇街道,回到自己寝室,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以为哪里不对。
我站在镜子前,对自己说:
“蛮好看的嘛。
”
没有哪里不对,我自信多了,穿上西服再次走上街时,挺直身子,让西服衬托我年轻挺拔的身体。
走过供销社玻璃窗,我故意放慢脚步,慢悠悠从玻璃窗下走过,看自己穿蓝色西服的身影印在玻璃窗上,我的身影看起来那么自然、那么庄重,让我暗自欣喜起来。
我走上小街台阶,坐在一家小饭馆里,声音洪亮地喊:
“老板,来碗牛肉面,大碗的。
”我端坐在饭桌边,一遍又一遍用纸巾擦拭着桌面,生怕有一点油星污染了我的西服袖子。
在小街上碰上一个熟人,我耸一耸身体,刻意把西服展现给人看,如果熟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再耸一耸,直到熟人惊讶地问一句:
新西服?
我自豪地应一声:
新的,第一个月工资买的。
我想我内心的那一点浮夸,相信所有人都看出来了,但他们并没有说出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大潮奔涌向前,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汇集在我们一件件衣服上。
走在大街上,人们穿着不同颜色、不同质地、不同款式的衣服,真是五彩斑斓。
我自身的衣着也回归了本源,回到自然、简单、舒适的层面,没有了童年时不懂节制的攀比,也没了少年时傻乎乎的那些拘谨,更没了青年时虚荣的那点浮夸。
我变得更自信更从容了,穿了很久的衣服,还觉得喜欢。
一件土布白衬衣穿了两三年,还舍不得丢。
每次找出来穿上,带着自己熟悉的气息,简单舒服。
四十年,衣服对我们表达的,既是向过去的告别,也是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篇三】
一
早先,“出远门”这个词,并不在我的常用词汇表当中。
生活的车轮日复一日旋转,轮子上的纹理是固定的,碾压过的地标很少很简单。
祖父母家、学校和外祖父母家,都在小小的桂林城中,公共汽车顶多两站路的范围之内。
此外所有的地名都是“远方”。
比如广播里听到的“自治区首府南宁”、比如祖父提起的“永定老家”和“你爸爸上大学的广州”……一个比一个远,只能停留在故事的某一段情节里或地图的某一点上,任凭想象,无法抵达。
缓慢规则的突变,发生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1978年。
新鲜的元素从四面八方加入,冰河解封,万物复苏,希望的田野上一派生机盎然,“出远门”随之变成实实在在的事。
先是祖父返回“永定老家”省亲。
老家在闽西山区,祖父说过很多很多次。
要回去的话,得从桂林坐火车先到江西鹰潭,然后转车到福建龙岩,再坐长途汽车到永定县城,然后走几十里山路回乡下。
整个旅程要两天?
三天?
我没有很清晰的概念,只记得祖父此行一去月余。
他回来之后,家里连续好几年有过要送我回永定的提议,总因这一段旅途太长太复杂而一再搁浅。
虽然不能回老家,没多久我自己也“出远门”了,被市里送往“自治区首府”南宁参加比赛。
在当时的桂林“南站”上火车,除了带队老师以外,同行的参赛同学都是第一次坐火车。
汽笛一拉响,蒸汽机车冒着呼呼白烟,牵引着绿皮的车厢,敲打着“咣当咣当”的节奏,无边田野无数峰峦房屋向后掠去,四百多公里跑了十一个小时。
将座位旁边的窗户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总有些新奇被我们叽叽喳喳地发现,一路上兴奋得不得了。
到1982年,家父因落实政策调往广西大学任教,两年后接我到南宁就学。
此后每年的寒暑假期我必定在南宁与桂林之间的火车上往返,穿山越岭的铁道线上,火车从普快换成了特快,行程从十一个小时缩短到九个多小时。
无论朝着哪头跑都是“回家”,都算不得“出远门”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高中校园,悄然兴起了学生社团。
我们的“白鸽文学社”在广西的评选中胜出,我因此被选送去参加“中南五省中学生文学夏令营”。
1986年盛夏,命运将我推送到童年遥不可及的、家父曾经的就学之地——广州。
那真是中国人民全线起跑的时代。
繁花渐欲迷人眼,新生事物频涌现,我们的词汇量不断扩展。
“夏令营”这个词已经够时髦,通往“夏令营”的这一趟“旅游客运特别快车”也时髦。
这趟每天一班广州—桂林对开的专列不卖站票,中途只停靠衡阳和郴州两个大站,为桂林这个最早开放境外旅游的西南小城运送着成千成万的港澳游客。
推小车的乘务员过来了,边走边喊“香烟、瓜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这种在我看来和咳嗽糖浆没太大差别的碳酸饮料,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普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火车上卖6元一瓶。
我向来只喝茶,所以更记得那天的火车上,带队老师用的那个茶杯。
那是一个广口的玻璃杯。
杯身套着手工编织的银绿色胶线套子,比一般的杯子高,且厚,到中间收窄一点,恰好方便用手握住。
这种不怕开水烫的玻璃杯其实是“雀巢”速溶咖啡的外包装瓶,通常是一对,与咖啡相配的那种蛋壳色粉末叫做“咖啡伴侣”,都是和“可口可乐”一样稀罕的东西。
广东夏令营的半个月里,我们见识到的新事物、学到的时髦词还不止这些。
广州市区内,刚开业不久的“东方乐园”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个大型现代“游乐园”,也是“国际游乐场协会”的第一个中国会员。
乐园里“摩天轮”“过山车”“太空漫游”等一系列娱乐,都是让当时很多胆敢尝试的人吓得尿裤子的项目。
还有“高第街”,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步行街”之鼻祖,整整一条街的各种服装鞋帽、日用杂货,品种丰富到令我们瞠目结舌。
在深圳,我们进入改革开放后中国创建的第一个“旅游度假村”——西丽湖度假村。
“第一长廊”总长千余米,蜿蜒于青山绿水之间,链接起亭台楼阁的雕梁画栋,点染千顷碧波照影,万树繁花争艳。
在蛇口码头,我们登上了九层高的“明华轮”。
这一艘为全国人民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的大船,由邓小平同志题名“海上世界”,是集酒店、娱乐为一体的中国第一座综合性海上旅游中心。
手边触摸到的一切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宣示正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国。
“可口可乐”和“咖啡”、“游乐园”和“步行街”,外来的新名词携带着新鲜的生活方式,新鲜的文化符号,从此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
到1993年夏天,当我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第七届全运会的圣火在“海上世界”引燃,还记得当时这艘大船上喝到第一杯“生果鲜榨”葡萄汁那种深紫色的、新鲜的甜香。
三
成为我生命轨道上最关键分岔点的那个冬天,并不是很冷。
时代的变革,终于将我推入出国留学、异域寻梦的大潮,家父陪我坐上了从桂林开往上海的列车。
来送别的亲朋好友挤满了我车窗前的站台。
一个接一个和我握别,只说今后万事要自己当心,都不敢说“再见”,因为根本不知道我这一去究竟几时能再见——甚至于,还能不能“再见”。
从当时正在扩建的虹桥机场起飞,我离开了我的家园,飞向更远更远,远到地球另一端的“远方”。
那时飞机要在阿拉斯加停留加油,才能飞过辽阔无比的太平洋,整个旅途要二十几个小时。
到了异邦,两眼一抹黑,一切从头学起。
学说话、学开车、学端盘子打工、学自己做饭,等到遇见犹太裔的汉肯老太太,又跟着她学做生意:
从国内进口羊绒毛衣。
刚开始真的不容易,许多细节,许多障碍,每一张订单都有无数预想不到的问题。
为了出口创汇,国内的厂家非常坚韧,非常耐心,全力配合。
样衣一次不行再做一次,染整、织造的工艺一再调整,为了赶船期全厂上下连夜加班……那种工作态度和效率,时常让汉肯老太太惊叹。
当她把柔软、轻薄,做工精良细致的羊绒毛衣成品拿到手上,惊叹之余,才明白那片土地不仅并非她想象的那样荒凉,更充满了莺飞草长的活力,布满了无限商机。
于是,她决定送我回国。
1995年春天,我从纽约直飞香港,再转往广州,参加第七十七届春季“广交会”。
那时的广交会堪称花城最盛大的节日。
展馆门外,卖小吃的摊贩和倒卖摊位的“黄牛”吆喝声此起彼伏,大学生们排长队寻求当翻译的机会,星级大酒店也摆开了阵势卖盒饭。
广交会场馆里数天内人潮汹涌,川流不息,成交额以百亿美元计。
全球的商家朝着低端廉价的“中国制造”纷至沓来的同时,很多中国企业却已不再满足于世界低端产业链上加工车间的地位。
这一届广交会一楼辟出了重点展区,两百多个展位,全是高附加值的国内名、优、新品牌商品。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后来声名鹊起的“鄂尔多斯”牌羊绒毛衣,从款式设计到编织工艺都可圈可点——“中国制造”从此不再单纯依靠廉价抢滩,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崭露头角。
广交会结束之后我飞回桂林。
哥哥手里提着板砖大小的“大哥大”,借了单位的车,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来接机。
我这个人是稀罕的,老祖母老外婆拉着左看右看;
姑父和叔叔舅舅们一个劲儿地追问今天想吃什么?
我带回去的东西也是稀罕的,姐妹们翻开我的行李箱逐件检视……
可我终究还是要走的。
这一次送我,不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了,改到机场的候机厅,还是乌泱泱几十号人。
我在大雨中走向飞机,哭得抬不起头,因为还是不知道下一次能回来是什么时候。
四
目光短浅又缺乏想象力如我,绝没有料到就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以及所有海外游子这种“君问归期未有期”的集体焦虑会被迅速消解。
先是绝大部分国内的家人都有了电话,国际长途的电话费也着实便宜下来。
联系方便了,千山万水间阻隔人的感觉就没那么强悍。
然后学校中国同学联谊会的活动却多了一项过去从未有过的活动:
欢送毕业生学成归国,“国内机会”和“美国就业”的比较迅速成为我们这些预备硕士、博士生们之间的热点话题。
“海归”们陆续回国大展身手之际,中国快速提升的综合实力也向世界重新定义着“中国”形象,带来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兴起。
2004年,我接受圣·
彼得大学的教职,负责设立该校“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系”的汉语课程。
在大学的讲台上,面对那些肤色各异的脸上求知若渴的眼睛,讲汉字结构,讲李白的唐诗鲁迅的小说;
在百老汇的剧场、加州的葡萄园,讲“广州十三行”的联保旧例和清末徽商“汇通天下”的理想……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的静水流深,成为我在异邦安身立命的依靠。
太平洋水域依然浩瀚无垠,而回家的路却迅速缩短。
从前读诗读到“天涯若比邻”,只感慨王勃胸襟开阔,气度宏大,意境旷达。
天涯就是天涯,迢遥就是迢遥,迢遥的天涯怎么可能“若比邻”?
可天涯真的就在比邻了。
随着中美之间文化、教育领域越来越深广、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互动,我因公回国的机会渐多。
多到自己的笔下再也没有了化不开的乡愁,多到当年火车站台上、机场候机厅内浩浩荡荡的家人接送场面再也不会有。
姐妹们利用长假期动不动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国内国外,游山逛水,见多识广,对我回国的行囊逐渐失去了瓜分的兴趣。
而回国之于我,也不再是独自一人飞来飞去。
陪新泽西州政府的商务代表团去上海,走遍江浙一带;
陪加州农业协会的代表团去广东,去福建……“经济特区”逐渐模糊了严格的地域划分,到处都在发展,到处都可以发展,“自贸区”“免税港”为外来投资提供越来越高效、便捷的贸易环境。
带着孩子们回桂林、回南宁,高铁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
甚至连带她们回到闽西山区已经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的永定土楼,也易如反掌,二级公路已经通到了我家祖屋的小溪边……
“二十一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英国知名学者马丁·
雅克多年前的判断,如今已是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而我脚下自己生命的旅途,也始于中国的1978年。
四十年来无数大事件波澜壮阔的演绎,成就了亿万中国人个人生活轨迹的由近及远、脱贫致富,成就了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的世界影响力。
当所有“远方”的时空概念因此而被压缩,当一本美国刊物用中英双语发出“中国赢了”的赞叹,炎黄子孙不论身在何处,与故土故园之间,都不再有天涯。
【篇四】
7月的一个上午,专程来广东、福建两省采风的我,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
看到人们举着手机一个接一个地围着邓小平同志塑像拍照,想想沿途看到的改革开放之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知怎的,竟然眼中含起了泪花。
回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姑姑的一双儿女都会照相,一个在陈集公社开照相馆,一个在高集公社开门市。
那时候,会照相是令人羡慕得流口水的技术活,能开照相馆更不是等闲之辈。
相片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一家人能照个全家福绝对是小康人家;
女孩说婆家一般是先见照片,男孩找媳妇也常常是先见照片,能相中照片,婚姻大事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表哥表姐到我家走亲戚的时候,常常带着照相机,借看望我父母的机会,顺便给姥娘门上的亲朋好友照个相。
红布一蒙,黑里透红,站好别动,一分钟就成。
表哥表姐把自己的头盖在红布里,调好照相机,然后再把头从红布里抽出来,右手扬起,左手握住气棒一类的东西,说道:
“往这里看!
靠左一点,向右一点,收住下巴,抬抬头,笑一笑!
”随着“滋”的一声响,人像定格,照片就照好了。
我们家在村里是大辈,别人喊我表哥一声表爷爷,喊我表姐一声表姑奶奶,照一张相就能便宜五分钱。
在那个时代,五分钱可是大钱,在我们村里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钱也就八分钱!
能在我们家照相,省钱不说,还少跑六七里路去集市,更主要的是有的大姑娘或者小伙子借照相的机会,把该见的人直接见了。
我家不算大的院子仿佛成了集市,村里的男男女女常常在这个时候到我家串门,有照相的,有看照相的,有蹭茶水吃瓜子的,也有不少借机相亲的。
我父母拿出瓜子、糖果和茶水招待他们,他们喝着茶水,嗑着瓜子,聊着天,有说有笑。
母亲从里帘屋内进进出出,一会儿去端糖果,一会儿去倒水。
平时脾气暴躁的父亲见谁几乎都要打招呼,给人家敬烟,让人家进屋喝茶水或者嗑瓜子,给人家说中午或者晚上别走了,有现成的肴盅,坐下来一起喝酒。
这些来的村人,有的摆摆手,说一声:
“大爷爷,您快去忙吧,我们照个相就走!
”有的一打招呼就进了我家正房,在八仙桌子旁坐下来,从国际大事到家长里短,一直聊到傍晚月亮挂上树梢。
家里所有供村人享用的糖果和瓜子,包括烟酒,都是平时我父母从自己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自己不吃不喝,也不让我们这些儿女们吃喝。
母亲私下对父亲说,你和孩子对这些烟呀酒呀糖果瓜子呀,连个牙印都没有沾过,省了一年的东西都让这些串门子的和外甥外甥女吃了,我心疼得慌呀!
父亲却说,咱家四五个跟牛犊子一样的男孩子眼看着一个个长起来了,有人能进咱家的门就是咱家的福气,说不定来吃吃喝喝的,就是咱家的贵人,就是咱家孩子的媒人。
能给儿子个个讨上媳妇,是我父母最大的心愿。
可在1979年,我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老人家至死也没有看到儿子个个找个媳妇,更没有与后来都有老婆孩子的儿子们照上一张全家福。
因为对照相有着神圣和美好的记忆,我军校一毕业,就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款傻瓜相机。
拿到相机,我如获至宝,轻易不敢示人,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晚上,才从箱子底里翻出来,一遍又一遍地把玩。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后来,认识妻子后,我才买了第一盒胶卷,正式把这款傻瓜相机挎在肩上,记录起我的生活。
它几乎成了我外出时形影不离的朋友,在“咔嚓咔嚓”声中,记录了妻子与我从相识、相知到相恋,再到结婚生子的一个个美妙的瞬间。
在这款相机拍摄的所有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令我印象最深刻,它是拍摄于山东聊城环城湖上的一张生活照。
1998年的春夏之交,一个难得的好天气。
这个上午,妻子没有班,我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带上两岁的儿子和七旬的母亲去环城湖上度周末。
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我在船头划船,母亲和儿子坐在船中,妻子在船尾注视着他们。
船在我的操纵下,时而急驶,时而缓游。
母亲的面容慈祥,儿子的样子可爱,妻子挽起长长的秀发,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
下船时,妻子立在一旁,母亲探着头、拉着儿子的手正要离船,得空的我连忙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在我看来,照片上的船仿佛是我和妻子组成的小家,母亲照看着我的儿子,而我经常漂泊在船的外面,生活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
自此之后,或许受了我的影响,妻子也爱上照相这一行,从我那台傻瓜相机开始,到2006年的数码相机,再到后来的手机照相,妻子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生活在哪里拍到哪里。
今年3月,我与妻子认识二十五周年那天,我帮她换了一台内存128GB的华为手机。
妻子高兴地说,这么大的内存够我用两年的了!
世事沧桑,时代变迁。
照相的故事,见证着不同的时代,记录着不同的人生,诉说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永远的向往和追求。
【篇五】
我有个毛病:
烦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