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资料Word文档格式.docx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资料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资料Word文档格式.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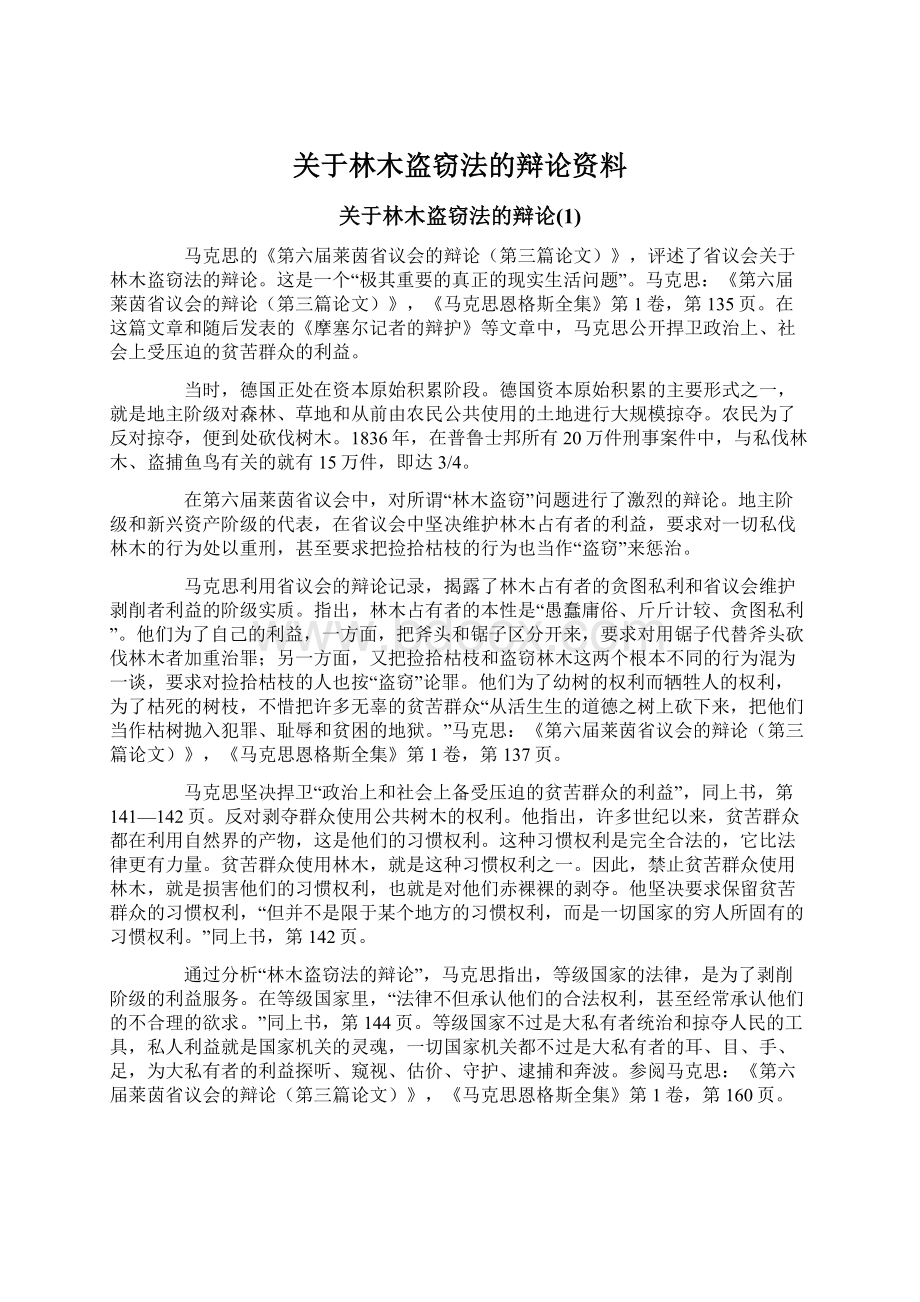
因此,禁止贫苦群众使用林木,就是损害他们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对他们赤裸裸的剥夺。
他坚决要求保留贫苦群众的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
”同上书,第142页。
通过分析“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等级国家里,“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
”同上书,第144页。
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参阅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0页。
等级议会也是保护私人利益的工具。
马克思写道:
"
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6页。
省议会对待每个问题的态度,都是以剥削阶级的利益为转移的,它践踏了法律,袒护了特定的私人利益,并把私人利益作为最终目的。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自私的、虚伪的两面派。
马克思通过分析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的发言,深刻揭露了他们两面派的嘴脸。
(从省议会的辩论中,)我们看到,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副眼镜,一副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副把一切都染成粉红色。
当需要别人充当自己工具的牺牲品时,当问题是要粉饰自己的两面手法时,自私自利就带上粉红色的眼镜,这样一来,它的工具和手段就呈现出一种非凡的色彩;
它就用轻信而温柔的人所具有的那种渺茫、甜蜜的幻想来给自己和别人催眠。
它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闪耀着善良的微笑。
它把自己敌人的手握得发痛,但这是出于信任。
然而突然情况变了:
现在已经是关于本身利益的问题……这时,精明而世故的自私自利便小心翼翼而疑虑重重地带上深谋远虑的黑色眼镜,实际的眼镜。
自私自利像老练的马贩子一样,把人们细细地从上到下打量一遍,并且认为别人也像它一样渺小、卑鄙和肮脏。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6页。
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情况的论文,虽然主要的不是从经济方面,而是从政治和法律方面揭露剥削阶级的本性,但是,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已经初步按照人们的经济地位来研究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看出国家和法不过是大私有者的工具,公开表明自己站在备受压迫的贫苦人民一边。
这就说明,他对社会的观察已前进了一步。
像其他论文一样,马克思这篇文章也得到德国先进人士的热烈赞扬。
1843年2月28日,《曼海姆晚报》对这篇文章作了如下评论:
这篇长文的读者还都很清楚地记得,作者在钻入代表们的空论以后从内部加以摧毁时所表现的那种机敏和果断的智慧,那种真正令人敬佩的辩证法;
具有这样的势如破竹的摧毁力的批判的智慧是不常见的。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第三篇论文)》笔记
(2008-10-2210:
56:
36)
转载
标签:
马克思
原著
笔记
分类:
思想天地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写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三篇。
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
普鲁士政府便想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为。
莱茵省议会在1841年6月15日至17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了辩论。
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林木所有者更多的好处。
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
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一、马克思要求保存贫民的习惯权利,认为这些习惯的根源是肯定的和合法的。
为什么要把贫民采集和砍伐林木的行为当作盗窃行为而加以惩罚,一位骑士等级的代表这样认为,“正因为偷拿林木不算盗窃,所以这种行为才经常发生。
”马克思在这里依照这位代表的逻辑作了一个精彩的推理。
“照这样推论下去,同一个立法者还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正因为打耳光不算杀人,所以打耳光才成为如此常见的现象。
因此应当决定,打耳光就是杀人。
”
“偷拿枯树或者捡拾枯枝也应归入盗窃的范围,并应和砍伐活树受到同样的惩罚。
”针对这一观点,马克思指出,“如果法律的这一条款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一大批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
如果省议会否决这一条款,那就可能使几棵幼树受害。
未必还需要说明:
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捡拾枯树,一种是情况极其复杂的林木盗窃!
“要占有一棵活树,就必须用暴力截断它的有机联系。
是一种明显地侵害树木所有者的行为。
”“谁偷窃砍伐的树木,谁就是偷窃财产。
“捡拾枯树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同财产脱离。
脱离财产的只是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它的东西。
”“可见,捡拾枯树和盗窃林木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
“法律不应该逃避说真话的普遍义务。
法律负有双重的义务这样做,因为它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
因此,事物的法理本质不能按法律行事,而法律倒必须按事物的法理本质行事。
但是,如果法律把那种未必能叫作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称为盗窃林木,那么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合法谎言的牺牲品了。
马克思认为,“同一类罪行具有极不相同的各种形式,如果你们否认这些形式之间的差别,那么你们也就把罪行本身当作一种和法不同的东西加以否认,你们也就是消灭了法本身,因为任何罪行都有某种与法本身共同的方面。
因此,不考虑任何差别的严厉手段,会使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它会取消作为法的结果的惩罚,这是一个历史的,同样也是合乎理性的事实。
二、马克思点出问题的实质在于法律保护的林木所有者也就是封建贵族、特权阶级的特殊利益。
“在确定对侵犯财产的行为的惩罚时,价值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如果罪行这个概念要求惩罚,那么罪行的现实就要求有一个惩罚的尺度。
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
因此,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惩罚就应该是有界限的,为了使惩罚成为公正的,惩罚就应该受到法的原则的限制。
任务就是要使惩罚成为罪行的实际后果。
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表现为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表现为他自己的行为。
所以,他受惩罚的界限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
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
因此,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
对于财产来说,这种尺度就是它的价值。
一个人无论被置于怎样的界限内,他总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而财产则总是只存在于一定的界限内,这种界限不仅可以确定,而且已经确定,不仅可以测定,而且已经测定。
价值是财产的民事存在的形式,是使财产最初获得社会意义和可转让性的逻辑术语。
显然,这种由事物本身的本性中得出的客观规定,也应该成为惩罚的客观的和本质的规定。
如果在涉及数目大小的场合立法能够仅仅以外部特征为依据,而不致陷入永无止境的规定之中,那么它至少必须进行调节。
问题不在于历数一切差别,而在于确定差别。
“林木所有者——我们在下面就要更详细地谈到这一点——不仅要求小偷赔偿一般的简单价值;
他甚至还要使这种价值具有个性,并根据这种具有诗意的个性要求特别补偿。
……讲求实际的林木所有者是这样判断事物的:
某项法律规定由于对我有利,就是好的,因为我的利益就是好事。
而某项法律规定由于纯粹从法理幻想出发,也应该适用于被告,那就是多余的、有害的、不实际的。
既然被告对我是有害的,那么不言而喻,凡是使被告受害较少的事情,对我都是有害的。
这真是非常实际的高见。
马克思指出了习惯法的本质。
“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法,而且要求的不是地方性的习惯法,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的习惯法。
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
但是,“所谓特权者的习惯是和法相抵触的习惯。
”马克思分析,
“人类分成为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决定他们之间的联系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律所确定的不平等。
不自由的世界要求不自由的法,因为这种动物的法是不自由的体现,而人类的法是自由的体现。
封建制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王国,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它和有区别的人类世界相反,因为后者的不平等现象不过是平等的色彩折射而已。
“当特权者不满足于制定法而诉诸自己的习惯法时,他们所要求的并不是法的人类内容,而是法的动物形式,这种形式现在已丧失其现实性,变成了纯粹的动物假面具。
贵族的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普通法律的形式相对立的。
它们不能具有法律的形式,因为它们是无视法律的形态。
这些习惯法按其内容来说是同法律的形式即通用性和必然性的形式相矛盾的,这也就证明,它们是习惯的不法行为,因此,决不能违反法律而要求这些习惯法,相反,应该把它们当作同法律对立的东西加以废除,甚至对利用这些习惯法的行为还应根据情况给以惩罚。
要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并不因为已成为他的习惯就不再是不法行为,正如强盗儿子的抢劫行为并不能因为他的特殊家风而被宽恕一样。
如果一个人故意犯法,那么就应惩罚他这种明知故犯;
如果他犯法是由于习惯,那就应惩罚他这种不良习惯。
在实施普通法律的时候,合理的习惯法不过是制定法所认可的习惯,因为法并不因为已被确认为法律而不再是习惯,但是它不再仅仅是习惯。
对于一个守法者来说,法已成为他自己的习惯;
而违法者则被迫守法,纵然法并不是他的习惯。
法不再取决于偶然性,即不再取决于习惯是否合理;
恰恰相反,习惯所以成为合理的,是因为法已变成法律,习惯已成为国家的习惯。
因此,习惯法作为与制定法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领域,只有在法和法律并存,而习惯是制定法的预先实现的场合才是合理的。
因此,根本谈不上特权等级的习惯法。
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非分要求。
特权等级没有权利预示法律,因为法律已经预示了他们的权利可能产生的一切结果。
因此,他们坚持要求习惯法,只不过是要求提供能够得到小小乐趣的领地,目的是要使那个在法律中被规定出合理界限的内容,在习惯中为超出合理界限的怪癖和非分要求找到活动场所。
然而,贵族的这些习惯法是同合理的法的概念相抵触的习惯,而贫民的习惯法则是同实在法的习惯相抵触的法。
“它们取消了各种地方性的习惯法,但是忘记了各等级的不法行为是以任意的非分要求的形式出现的,而那些等级以外的人的法是以偶然让步的形式出现的。
……这些立法只要认为任意的非分要求具有合理的法理内容,它们就把这些要求变成合法的要求;
同样,它们也应该把偶然的让步变成必然的让步。
“这些立法必然是片面的,因为贫民的任何习惯法都基于某些财产的不确定性。
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即不能明确肯定这些财产是私有财产,也不能明确肯定它们是公共财产,它们是我们在中世纪一切法规中所看到的那种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
“因此,理智取消了财产的二重的、不确定的形式,而采用了在罗马法中有现成模式的抽象私法的现有范畴。
立法的理智认为,对于较贫苦的阶级来说,它取消这种不确定的财产所负的责任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因为它已取消了国家对财产的特权。
然而它忘记了,即使纯粹从私法观点来看,这里也存在两种私法:
占有者的私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法,更何况任何立法都没有取消过国家对财产的特权,而只是去掉了这些特权的偶然性质,并赋予它们以民事的性质。
但是,如果说一切中世纪的法的形式,其中也包括财产,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混合的、二元的、二重的,理智有理由用自己的统一原则去反对这种矛盾的规定,那么理智忽略了一种情况,即有些所有物按其本质来说永远也不能具有那种预先被确定的私有财产的性质。
这就是那些由于它们的自然发生的本质和偶然存在而属于先占权范围的对象,也就是这样一个阶级的先占权的对象,这个阶级正是由于这种先占权而丧失了任何其他财产,它在市民社会中的地位与这些对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相同。
“作为整个贫苦阶级习惯的那些习惯能够以可靠的本能去理解财产的这个不确定的方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阶级不仅感觉到有满足自然需要的欲望,而且同样也感到有满足自己正当欲望的需要。
”以贫民捡拾枯树枝为例,“正如,蜕下的蛇皮同蛇已经不再有有机联系一样,枯枝同活的树也不再有有机联系了。
自然界本身仿佛提供了一个贫富对立的实例:
一方面是脱离了有机生命而被折断了的干枯的树枝树杈,另一方面是根深叶茂的树和树干,后者有机地同化空气、阳光、水分和泥土,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形式和生命。
这是贫富的自然表现。
贫民感到与此颇有相似之处,并从这种相似感中引伸出自己的财产权;
贫民认为,既然自然的有机财富交给预先有所谋算的所有者,那么,自然的贫穷就应该交给需要及其偶然性。
“正如富人不应该要求得到大街上发放的布施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得到自然界的这种布施。
但是,贫民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权利。
人类社会的自然阶级在捡拾活动中接触到自然界自然力的产物,并把它们加以处理。
那些野生果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只不过是财产的十分偶然的附属品,这种附属品是这样的微不足道,因此它不可能成为真正所有者的活动对象;
捡拾收割后落在地里的谷穗以及和诸如此类的习惯法也是这样。
由此可见,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
而所谓的“富人”反对贫民的习惯权利,“把穷人的习惯法变成了富人的独占权。
”因为“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财产的利益想出了这个主意。
某些财迷心窍的生意人想出的时髦主意,只要能使枯枝给原始条顿式的土地占有者带来利益,就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三、对犯罪与惩罚的关系的深入分析
“在民间的习惯法受压制的地方,遵循这些习惯法的做法,只能作为单纯违反警章规定的行为来对待,无论如何不能当作犯罪来惩罚。
违警处罚是用来对付那种根据情节可称为外部混乱而不破坏永久法律秩序的行为的一种手段。
处罚不应该比过错引起更大的恶感,犯罪的耻辱不应该变成法律的耻辱。
如果不幸成为犯罪或者犯罪成为不幸,那么这就会破坏国家的基础。
马克思对林木所有者进行了讽刺,正是由于林木所有者为自身的利益的最大化,推动立法机构制定惩罚贫民的法律。
“利益的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灵魂只是看到自己吃亏的事情;
就好比一个粗人因为一个过路人踩了他的鸡眼,就把这个人看作天底下最可恶和最卑鄙的坏蛋。
他把自己的鸡眼当作观察和判断人的行为的眼睛。
他把过路人和自己接触的那一点当作这个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唯一接触点。
然而,有人可能踩了我的鸡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优秀的人。
正如你们不应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看待他们。
私人利益把一个人触犯它的行为夸大为这个人的整个为人。
它把法律变成一个只考虑如何消灭有害鼠类的捕鼠者,捕鼠者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他只把老鼠看作有害的动物。
但是,国家不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只看作违法者、森林的敌人。
难道每一个公民不都是通过一根根命脉同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难道仅仅因为这个公民擅自割断了某一根命脉,国家就可以割断所有的命脉吗?
可见,国家也应该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看作一个人,一个和它心血相通的活的肢体,看作一个保卫祖国的士兵,一个法庭应倾听其声音的见证人,一个应当承担社会职能的集体的成员,一个备受崇敬的家长,而首先应该把他看作国家的一个公民。
国家不能轻率地取消自己某一成员的所有职能,因为每当国家把一个公民变成罪犯时,它都是截断自身的活的肢体。
有道德的立法者首先应当认定,把过去不算犯罪的行为列入犯罪行为的领域,是最严重、最有害而又最危险的事情。
马克思进而指出,“残酷是怯懦所制定的法律的特征,因为怯懦只有变成残酷时才能有所作为。
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因为那种随时都可能遭到劫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就是私人利益的心和灵魂。
有谁会面临失去心和灵魂的危险而不战栗呢?
如果自私自利的立法者的最高本质是某种非人的、异己的物质,那么这种立法者怎么可能是人道的呢?
四、法律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奴仆
法律规定,“凡超出两英里以外者,由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根据当地现行价格确定价值。
”“作为护林官员,护林人应该维护私有者的利益,但是作为估价者,他又应该保护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的利益,防止私有者提出苛刻的要求。
……一方面,他是林木所有者利益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又应该是反对林木所有者利益的保障。
”“其次,护林官员就是告发者。
……,护林官员丧失了自己身为法官的尊严,而法官的职能也受到莫大的侮辱,因为这时法官的职能同告发者的职能已毫无区别了。
”“最后,这个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是受林木所有者的雇用并为林木所有者效力的,不论作为告发者或护林官员,他都不宜充当鉴定人。
”针对护林官员角色定位的混乱,而省议会视而不见。
有议员认为,“把护林官员的终身任命当作信任其证言的条件,这对小林木占有者是非常不利的”,“保护应该对大小林木所有者同样有效。
”马克思借这个问题揭开了林木盗窃法的阶级属性。
“在这里他们并不是想要同样地保护林木所有者和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他们只是想把大小林木所有者一视同仁地加以保护。
当问题涉及林木所有者时,大小林木所有者之间的完全平等就成为定理,而当问题涉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时,不平等就变成公理。
为什么小林木所有者要求得到和大林木所有者同样的保护呢?
因为他们两者都是林木所有者。
但是,难道林木所有者和违反森林管理条例者不都是国家的公民吗?
既然大小林木所有者都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国家的保护,那么,难道国家的大小公民不是更有同样的权利要求这种保护吗?
而小林木所有者要求护林官员对大小林木所有者一体保护,护林官员实际上成为林木所有者的雇佣者。
“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它的这种非分要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切实的考验。
如果国家哪怕在一个方面降低到这种水平,即按私有财产的方式而不是按自己本身的方式来行动,那么由此直接可以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适应私有财产的狭隘范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
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
因此,且不说国家受到的最大屈辱,这里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有人会用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来对付被告;
因为高度重视狭隘的私有财产的利益就必然会转变为完全无视被告的利益。
既然这里明显地暴露出私人利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手段,那么怎能不由此得出结论说,私人利益即各个等级的代表希望并且一定要把国家贬低到私人利益的思想水平呢?
任何现代国家,无论它怎样不符合自己的概念,一旦遇到有人想实际运用这种立法权利,都会被迫大声疾呼:
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
“如果前来告发的护林官员就像你们所描绘的那样,终身任命并不能使他在履行自己职责时具有独立、自信和尊严的感觉,相反,却使他失去了履行职责的一切动力,那么这个人一旦成为供你们任意驱使的、百依百顺的奴仆,我们还能够指望他会对被告采取公正态度吗?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把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为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
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
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五、法律成为林木所有者剥削的工具
针对林木所有者要求对所谓“盗窃者”罚款并索取价值和损失补偿的要求,“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变为林木所有者的流通硬币,把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变成一项收入,使自己获得更有利的投资机会,因为对林木所有者来说,违反林木管理条例者已成为资本了。
”“罪行变成了****,林木所有者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能中彩。
这里可能产生额外价值,因为即使他所得的只是单纯价值,但是由于四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他仍然能赚一笔钱;
如果他所获得的不只是单纯价值,同时还有损失的特别补偿,那么这种四倍、六倍以至八倍的罚款无论如何完全是白赚了。
”“现在惩罚却由公众的惩罚变成对私人的赔偿了;
罚款并未归入国库,而是落入林木所有者的私囊。
“有立法权的林木所有者一时间就把自己作为立法者和林木所有者的身分混同起来。
一次他作为林木所有者强迫小偷因偷窃林木而支付赔款,另一次他作为立法者强迫小偷因犯罪意图而支付罚款,而且很凑巧,两次的钱都为林木所有者所得。
因此,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普通的领主权。
我们通过公法时代到达了加倍的、多倍的世袭权利时代。
世袭所有者利用屏弃他们要求的时代进步,以便窃取野蛮人世界观所固有的私人惩罚和现代人世界观所固有的公众惩罚。
马克思进而指出,“公众惩罚是用国家理性去消除罪行,因此,它是国家的权利,但是,它既然是国家的权利,国家就不能把它转让给私人,正如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良心让给别人一样。
国家对罪犯的任何权利,同时也就是罪犯的国家权利。
罪犯同国家的关系不可能由于中间环节的介入而变成同私人的关系。
即使人们允许国家本身放弃自己的权利,即自杀而亡,国家放弃自己的义务毕竟不仅是一种疏忽,而且是一种罪行。
接着,马克思又指出,“可见,林木所有者既不能从国家获得实行公众惩罚的私人权利,他本身也没有任何实行惩罚的权利。
但是,如果我在没有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把第三者的罪行变成收入的主要来源,我这样做难道不就成为他的同谋者吗?
难道仅仅因为他该受惩罚,而我坐享犯罪的好处,我就不是他的同谋者吗?
如果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