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Word文档格式.docx
《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疑古与考信钱穆评古史辨派的古史理论Word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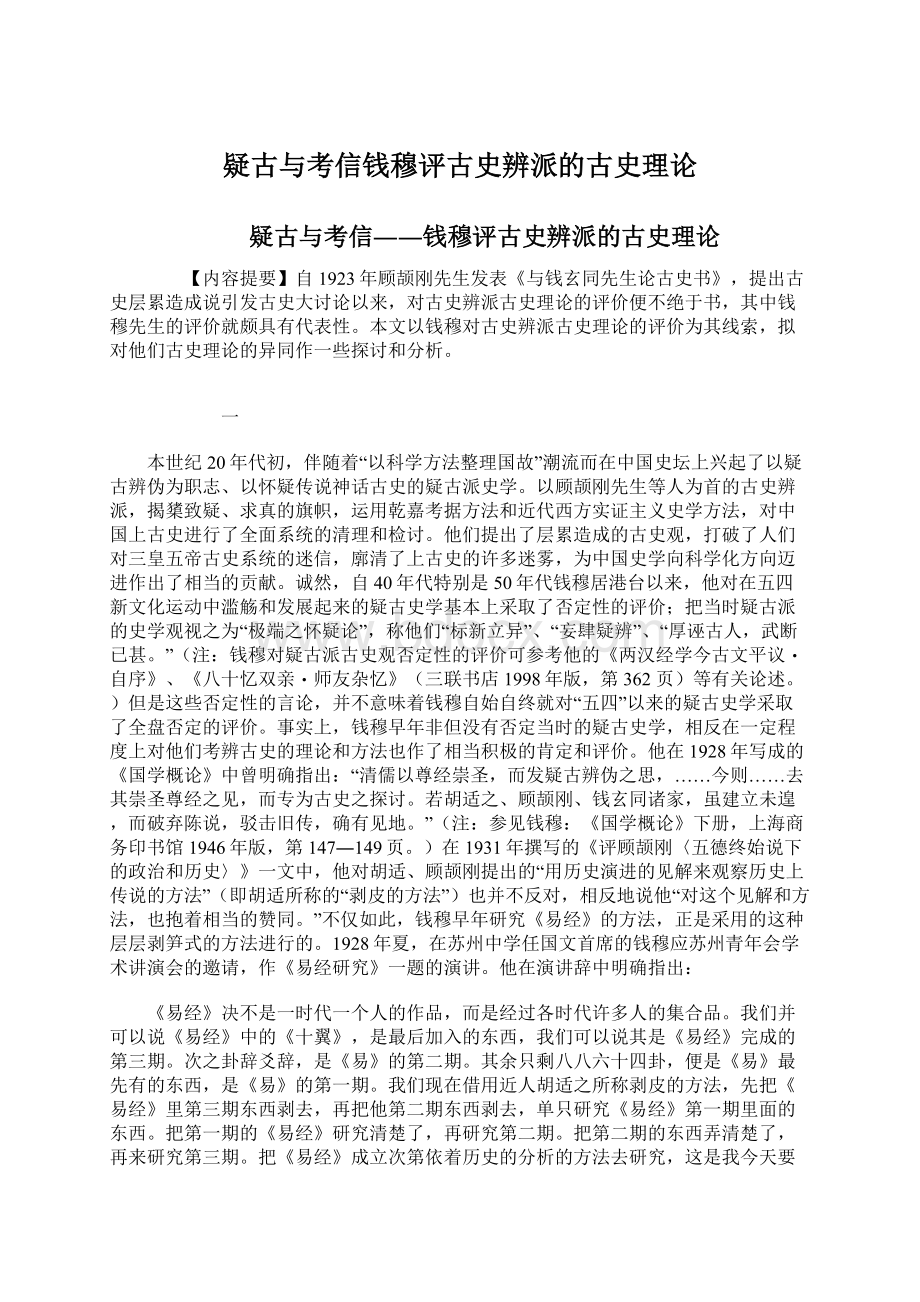
《易经》决不是一时代一个人的作品,而是经过各时代许多人的集合品。
我们并可以说《易经》中的《十翼》,是最后加入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其是《易经》完成的第三期。
次之卦辞爻辞,是《易》的第二期。
其余只剩八八六十四卦,便是《易》最先有的东西,是《易》的第一期。
我们现在借用近人胡适之所称剥皮的方法,先把《易经》里第三期东西剥去,再把他第二期东西剥去,单只研究《易经》第一期里面的东西。
把第一期的《易经》研究清楚了,再研究第二期。
把第二期的东西弄清楚了,再来研究第三期。
把《易经》成立次第依着历史的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
(注:
钱穆: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
显然,钱穆早年治古史的一些见解与“五四”以后的疑古派的古史观有某些相同之处,他考订古史的方法也曾受到过疑古派“剥皮”方法的影响。
同时,钱氏本人也是一位以记诵潇博、考订精审而名播学界的学者,他早年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他与顾颉刚古史辨派的同仁同样具有大胆的疑辨思想与批判精神。
钱穆本人也称自己“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两者分辨,仅在分数上”。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第167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研治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和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派确有一些相同的见解。
二
钱穆先生与古史辨派在治古史的某些方面虽然有共同之处,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他们的治史主张却又是同不胜异的。
我们认为,在20―30年代,钱穆对“五四”以来的疑古派史学的评价大体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
在20年代特别是20年代后期写成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对疑古派正面肯定的居多,对其古史理论与方法抱有相当的赞同。
30年代中期以后批评的言论转多,1935年发表的《崔东壁遗书序》可为其代表。
而对疑古派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全面而公开批评的,则以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为标志。
在书中,钱穆把疑古派的治史主张称之为“极端之怀疑论”,声称“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亦应稍加修正。
《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4页。
)综观钱穆对疑古派治史主张的批评,我们认为他们在治古史的理论和方法上主要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分歧:
第一,对“疑”与“信”、“破”与“立”的不同理解。
和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一样,钱穆同样也主张疑辨,认为“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
但是,在对待疑与信、破与立的关系上,他们的看法又不尽相同。
尽管古史辨派也主张“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为求建设。
《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
)然而在具体的古史研究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奉行的是以疑破信的原则,主张通过怀疑来达到推翻传统上古史的目的,所以他们常常把疑作为治古史的最高目的,其着眼点在疑不在信,在破不在立。
钱穆并不一般地反对疑古,但与古史辨派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怀疑本身并不是目的,疑是不得已,是起于两信之不能决。
他在1933年给《古史辨》第四册所作之序中就明确提出了“怀疑非破信,乃立信”的观点。
信亦有广有狭。
疑者非破信,乃所信之广。
信乎此,并信乎彼,而彼此有不能并信,于是乎生疑。
若世之守信者,信其一,拒其余,是非无疑,乃信之狭。
若必尊信,莫如大其信。
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
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
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再一次重申了这一主张,“夫为辨有破有立,破人有余,立已不足,此非能破之胜也。
”后来他把这一主张更精简地表述为“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
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
《学术与心术》,《学钥》1958年香港自印本,第140页。
)显然,在钱穆看来,怀疑本身并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一味怀疑必然流于破而不能立。
他的目的是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而不是以疑破信,推翻古史。
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被疑古派誉为“科学的古史家”崔述的古史观提出了批评。
他说崔述“主于尊经而为之考信”,因其不敢破经,故“信之太深”;
又因其过分疑古,故“疑之太勇”,指出崔氏之病在于所信之过狭,其弊陷于所疑之过多,故崔氏“所疑未必是,即古说之相传未必非。
《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89页。
)钱穆认为崔东壁这种疑古太甚、辨驳太刻的疑辨思想生前虽不为清儒所重,但到了“五四”时期却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承继和发展,演变成对一切古典文献的怀疑。
他说胡适“于古今人多评骘,少所许,多所否,顾于东壁加推敬,……最为疑古著者曰顾君颉刚……深契东壁之治史而益有进”,(注:
《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4页。
)“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
《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167―168页。
)在钱穆看来,这种对古代典籍普遍怀疑的主张对研究古史特别有害,它势必会导致对上古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所以他对当时只破不立的疑古学风大加批评道:
“数年以来,有闻于辨伪疑古之风而起者,或几于枝之猎而忘其本,细之搜而遗其巨,离本益远,歧出益迷”(注:
),称“近人尽从疑古辨伪上来治史,所以终难摸到历史大动脉之真痛庠。
《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4年版,第30页。
第二,对清末今文经学的不同看法。
诚然,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经历了对今古文经学继承和批判的双向认识过程。
他对钱玄同提出的“用古文批判今文,以今文批判古文,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的主张非常赞同,也曾站在古文经学求真的立场上批评康有为“拿辨伪作手段,把改制当目的”,“非学问研究”态度,也曾多次声称“决不想做今文家,不但不想做,而且凡是今文家所建立的学说我一样地要把它打破。
顾颉刚:
《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32页。
)但据此便得出顾颉刚已自觉地、有意识地超越了汉宋藩篱、今古门户的结论,似乎还有些勉强。
众所周知,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关系甚巨。
两汉以后渐为湮没的今文经学,到清代由庄存与开其端、刘逢禄奠其基,至龚(自珍)、魏(源)而蔚为大观,到廖平、康有为时集其大成。
特别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之风和顾颉刚的古史辨伪。
然而,康氏之书写于戊戌维新时期,其书主要是借经学谈政治,为变法维新鸣锣开道。
两书在政治上打击泥古守旧思想,意义甚大。
但是从学术的角度去衡估它,其结论不免牵强、武断、难以令人信服。
即便是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之也有“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的批评(注: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
由于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颇受康有为今文学派观点的影响,因此他对晚清今文学家的疑辨思想和历史解释比较推崇,其著述不免用康有为等人的今文家说来为其古史观张目。
他说读了《新学伪经考》,“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注:
《古史辨》
(一)“自序”,第26页。
),读《孔子改制考》上古事茫昧无稽、夏殷以前文献不足征,认为“此说极惬心餍理”,“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注:
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这是他阐述其古史理论的又一力作。
该文在方法论上显然受到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认为刘歆所作的《世经》,是媚莽助篡的东西,《世经》里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统,是出自刘歆的伪造。
他说:
康先生告诉我们,在今文家的历史里,五帝只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没有少昊。
在古文家的历史里,颛顼之上添出了一个少昊,又把伏羲、神农一起收入,使得这个系统里有八个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来证实古文家的伪经《周礼》里的三皇五帝。
这个假设,虽由我们看来还有不尽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经》和《月令》的死命了(注:
《古史辨》(五),第254―255页。
后来在《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他仍坚持古文经为刘歆有意伪造这一观点(注:
《古史辨》(五),第631页。
对于顾颉刚所坚持的刘歆造伪说,当代学者多有批评之语。
曾亲自参加过当年古史辨运动的杨向奎认为,无论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顾颉刚),还是“古史的分化演进说”(童书业),“在方法论上都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他们都是反对古文经的健者。
参见杨向奎:
《论“古史辨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22页。
)汤志钧也指出,顾颉刚攻击刘歆造伪,“仍然是今文学派的方法,多少重复过去的老路”,“有时还没有完全脱离经学家的圈子。
”(注:
参见汤志钧:
《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58页。
在对待《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为刘歆伪窜和假造这一问题上,钱穆与晚清以来的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看法截然异趋。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政治还是学术,从汉武帝到王莽,从董仲舒到刘歆,只是一线的演进和生长,绝非像晚清今文学家和疑古派所说的其间必有一番盛大的伪造和突异的解释。
所以钱氏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主要便是针对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而作的。
钱著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向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事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凡康氏曲解史文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加以说明,廓清了风靡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
钱氏虽然用历史考证的方法否定了刘歆造伪说,但是他并没有站到古文经学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
因为他认为今古文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
他声称是“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出版。
)1931年钱穆在《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分析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与晚清今文经学的不同之处外,还主要针对顾氏《世经》出于编造,少昊是刘歆插入古史系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本有少昊,并非刘歆在后横添。
”“以汉为尧后,为火德,及主五行相生三说互推,知少昊加入古史系统决不俟刘歆始,刘歆只把当时已有的传说和意见加以写定(或可说加以利用)。
《古史辨》(五),第629―630页。
)由于钱穆主张五德体系并非刘歆无端伪造,所以他致力于探寻从汉武帝到新莽王朝之间的学术渐进演变之迹,力主用自然的演变说取代刘歆造伪说,并劝告古史辨派“应用历史演进的原则和传说的流变来解释,而不必用今文学说把大规模的作伪及急剧的改换来归罪刘歆一人。
《古史辨》(五),第630页。
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
参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的有关论述。
)显然,钱穆试图在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比较自觉地在做超越今古门户的工作。
我们认为,20―30年代钱穆对晚清今古文之争以及古史辨运动与清季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其批评的言论不失为持平之论。
第三,如何看待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
如何理解传说与伪造的关系。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认为传统中的上古史即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基本上是后人层累造伪构建起来的。
具体言之,则是经战国秦汉时人造伪而逐步形成的。
参见顾颉刚:
《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七)。
)所以他们大多不相信先秦诸子和汉儒对古史的解释,认为他们所称述的古史无非是某些理想的注脚,某些学说的附加品或为某些政治目的的佐证。
钱穆也同意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并非古史的真貌,它在演进过程中确有后人作伪的地方,特别是有战国诸子和秦汉时人托古改制的理想渗入其中。
所不同的是,钱穆认为战国诸子所称述的古史和汉儒对先秦古籍的整理和解释,固然有不少歧异和矛盾之处,但相同的地方也不少,它们大多是可信的,是分析和研究上古史的有用材料。
比如先秦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和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疑古派因诸子喜欢托古或“取于寓言”,故多不信诸子之言。
钱穆认为诸子之书的托古和寓言固不足信,但“其述当世之事,记近古之变,目所睹,身所历,无意于托古,无取于寓言。
率口而去,随心而道,片言双语,转多可珍。
《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版。
)又如晚清今文学家和古史辨派大多怀疑儒家之与六经,全盘否定依据六经所建构的古史体系,钱穆则坚持“六经皆史”说,认为“治东周不能无取于《春秋》与《左氏》,治西周不能无取于《诗》、《书》,此皆儒家所传,六籍所统,可信多于可疑。
《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86页。
)再如对唐虞禅让说的理解,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是战国形势下形成的新古史观,它首起于墨家的尚贤、尚同学说,经过广泛流传后,被儒家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和融铸吸纳到儒学中去了。
从墨家首倡禅让说到禅让古史最后被写进儒家经典《尚书・尧典》,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
)钱穆认为舜尧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主推选制,经后人追忆、传述而理想化。
后人追忆、传述未必全属当时实况,但也绝非子虚乌有,向壁虚构。
所以他说:
“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全出后人捏造。
《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
)显然,在钱穆眼中,依据儒家六经建立起来的古史系统,虽有后人造伪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事实为其依据,因此疑经疑古尽可,但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古史。
为此他强调说:
“谓六经不尽出孔孟可也,谓尧舜禹文武周公之圣统无当于古史之真相亦可也,然苟将从事于古史,儒家要为古学一大宗,六经要为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要为占古文中一大部。
拘拘乎是二者,而以定古史之真相,其观点为已狭;
若将排摈乎是而求以窥古史之全体,其必无当,则断可识也。
《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290页。
基于古史系统为后人层累造伪的理解,“五四”以后的疑古派大多否定甚至抹杀文献记载中的神话传说,认为上古流传之文字,多不可信,春秋战国以前的历史,皆后人之假托。
比如胡适以《诗经》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宣称“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
胡适:
《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
(一),第22页。
)所以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东周以上的历史即“存而不论”。
顾颉刚也说:
“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
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
《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
(一),第35页。
)与此观点相反,钱穆认为上古流传的神话传说包含有许多可信的成分,是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材料。
既不能因传说有不可靠的成分便将之弃置不用,更不能因传说里搀杂有神话而否定传说。
因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忆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
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
《国史大纲》上册,第4―5页。
)当然,传说也有许多不可靠的成分,对之不能盲目轻信,但是它与伪造、说谎却有本质的不同。
为此,钱穆作了具体的分析:
传说是演进生长的,而伪造可以一气呵成,一手创立。
传说是社会上共同的有意无意――而无意为多的一种演进生长,而伪造却专是一人或一派的特意制造。
传说是自然的,而伪造是人为的。
传说是连续的,而伪造是改换的。
传说渐变,而伪造突异。
《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620页。
由于钱穆主张古史体系为自然的演进而非人为的造伪,所以他对当时的疑古派采用今文家说把大规模的作伪统统诿之古人的作法进行了批评,“传说来源非全无因”,“后人不得其说,而缘饰之以理想之高义。
更后之人益不得其说,则谓全属古人之妄造。
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之学人专好造谣乎?
《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5页。
)“近人全认传说为伪造与说谎,此所以治古史多所窒碍也。
第四,关于上古史的研究方法。
30年代,钱穆执教北京大学,主讲上古史。
面对弥漫学术界的疑古思潮,他在讲台上却宣称,讲上古史“若亦疑古,将无可言。
”钱穆认为研究上古史应“通观大体”,不可对古史作“过细推求”。
因为自西周逆溯而上,历商夏唐虞,乃至远古,人物无可详说,年代亦渺茫难稽,故不能仅凭年代、人物、制度学术去细推古史。
为此他作了如下分析:
(一)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不够按年逐月推求。
(二)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人物个性活动之事业尚少,若专从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则仍是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公一套旧观念,不免多带有神话教训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
(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注:
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
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
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
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注:
《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294页。
),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
)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
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
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
诚如所言:
“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
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
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
《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11日,署名“公沙”。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
钱穆指出:
“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
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
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
《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1卷第8期(1934年)。
)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
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
“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
)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
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
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
“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
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
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
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
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
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
《国史大纲》上册,第5页。
又见钱穆:
《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3卷第1期(1935年)。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
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
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
《中国文化史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