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论文DOCWord格式.docx
《中国经济史论文DOC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经济史论文DOCWord格式.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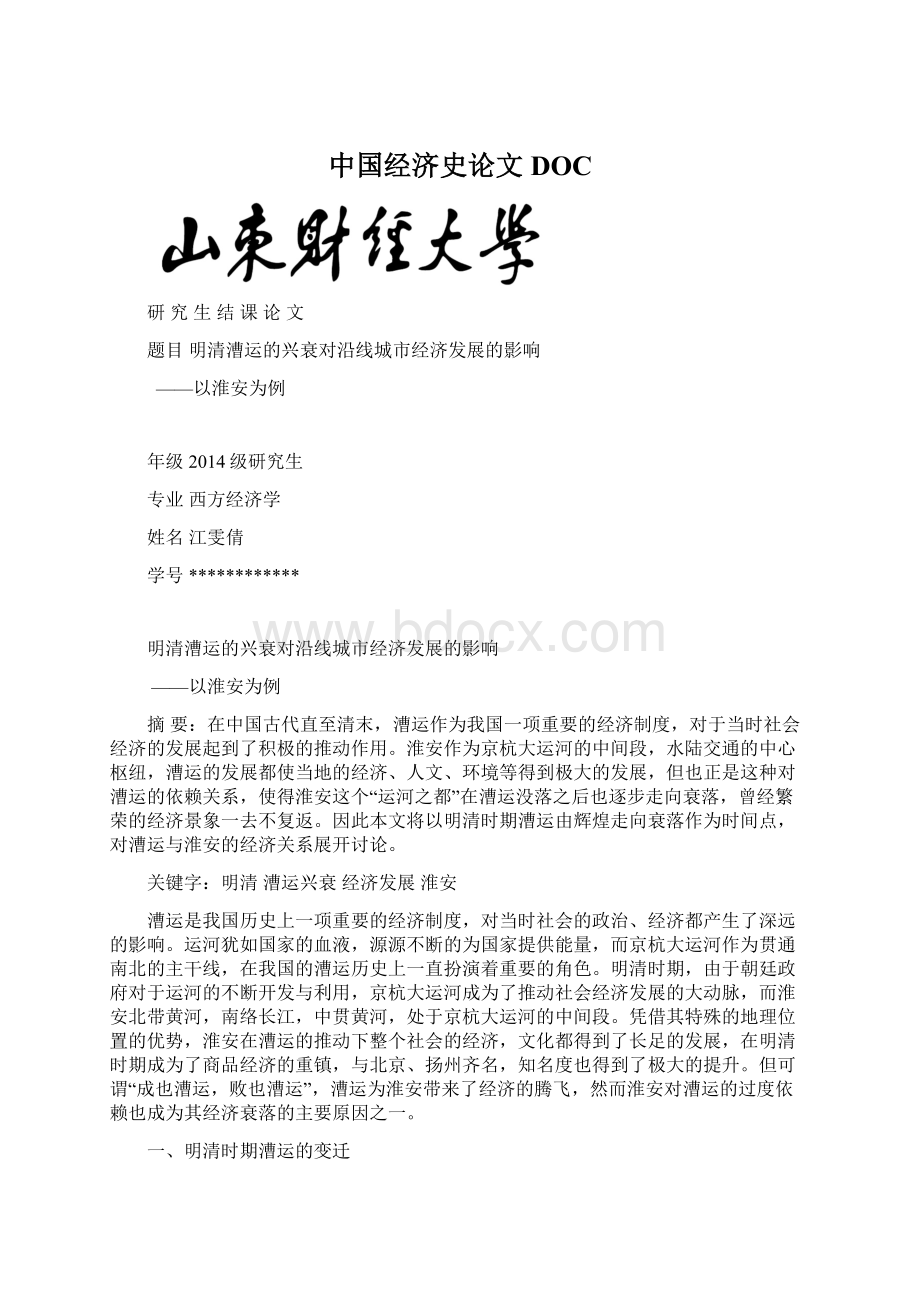
文传》有云:
“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
”从中可以看出漕运在早期只是与陆运相对应的水路运输,与运河的关系并不密切。
但春秋时期运河的兴修使漕运发生了质的变化,楚汉之争后更是将漕粮与供应京城乡连在了一起,此后在各朝各代漕运均得到了不同的程度的发展,其中以明清两代发展的比较充分。
(一)明代漕运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明代经历了由海运改为漕运的过程。
在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主要以海运为主,而到明成祖时,由于都城改迁至北京,这就要依托京杭大运河来进行贸易往来,故而将海运改为漕运,并将漕运作为运输粮食的唯一途径。
明朝对运河进行疏浚改道,明代的漕运机构与各朝代相比当属最完备的。
明代漕运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军运,一类是民运。
《明史·
食货志三》有云:
“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
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
故按输送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支运、兑运和长运。
所谓支运是指在京杭大运河沿线设徐、淮、临清、德州等仓。
随着当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明代的漕运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即从洪武元年到永乐六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就近运送粮草物资,以满足社会发展和军队征战的需要。
第二阶段是支运阶段,时间跨度在永乐六年到宣德六年,在该阶段支运由暂停又重新得以恢复,主要采取的方式是军队与百姓共同参与漕运。
第三阶段是兑运阶段,在宣德六年,为了降低“耗米”,朝廷规定当地百姓可以就近将粮运到附近的府、州、县的水路兑给卫所官军,由官军运往京师,人民贴给“耗米”。
在该阶段兑运逐渐取代了民运,成为了主要的漕运方式,而该种方式不仅使百姓避免了遥远的运粮路上的艰辛,而且增加了国家的军队收入。
做后一个阶段为长运阶段,成化七年推行长运,主要是由官军承担漕粮的全部运输任务。
在明朝后期也曾提出过海运或是恢复支运,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而没有了下文。
明朝是漕运得到完善与发展的一段时间,因此其在漕运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并有相应的一套管理系统。
据《明史》记载,明初遍设立了武臣来掌管海运,并且尝试设立漕运都督,又先后任用御史、侍郎和员外等官员分管漕运,而成祖年间,景泰二年就在淮安设立了漕运总督,与总兵、参将共同管理漕运的大小事务,从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漕运的重视,而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漕运对于当时社会的重要意义。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统治者的对漕运的管理制度、人员配置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愈加细致的考虑,开始设置数量庞大的行政官员分管漕运,并且规定了行事规范,比如“主事都兑,其制不一”,对各级官吏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各官吏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此外当时的统治者还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遵循这种追究机制,针对在漕粮的运输过程中遭遇的不同问题,责罚不同责任人。
逐步形成了集管理、保卫、监督、惩罚为一体的管理方式,从而使漕运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掌握在朝廷手中。
除了设置数目客观的官员对漕运进行管理外,漕运的发展还带来了大批的就业岗位,漕军、漕丁、漕夫数量惊人。
除却以上严格的管理体系外,明朝政府为了鼓励漕运,在嘉靖年间曾明确规定:
每条货船允许装载货物二成,自由在沿途贩卖,并允许漕船在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
如此一来,运输漕粮的大运河遍成为了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沿河城市诸如淮安、扬州、德州、济宁商业发展迅速,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城市。
漕运贯穿于整个明王朝,在其整个兴衰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形成如此严格的管理制度,分工明确的领导机制以及数目庞大的丁夫苦役,足以说明漕运对于明朝的人民生活及国家存亡的重要意义。
(二)清代漕运的由盛转衰
清朝继承了明代的漕运体制,依然以大运河作为主动脉运输漕粮。
清代漕运的畅通,对于促进国内经济的交流、发展以及政治的稳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清政府平粜粮价即是藉漕粮仓储来实现的,每遇米价上涨,“将庶内旧贮米石减价平粜并行文直隶总督,凡近水州县,可通舟揖者,俱令赴通仓领运,平粜便民。
”基于运河畅通而兴盛的漕运自然构成了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繁荣的基础,在清朝,苏州、扬州、淮安与杭州并称沿运“四大都市”。
而至清中叶,受到经济、军事、自然诸多因素的影响,运道堵塞日渐严重,漕运也就逐步荒废,道光年间试行漕粮海运,咸丰以后漕粮同办海运,光绪时漕粮海运,运河治理鲜有关注,其功用日渐衰退,漕运也益加难复,清代漕运兴衰复废,与运河通塞相互影响。
具体而言,清代漕运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首先是运河畅通,清初漕运兴盛阶段。
如范承谟《请改折漕粮疏》所云:
“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在清初朝廷对漕运很是重视,无论是整顿漕政,还是疏通河道,都颇有作为。
因此在清初漕运畅通,仓储充裕,在康熙五十八年,“京城通州仓内,贮米甚多,各省运至漕粮,亦无亏欠;
在仓内堆积,恐致红朽”。
然后到了清朝中叶,由于漕政的败坏,清朝漕运进入了第二阶段,此时漕运的良性发展已经难以为继。
至清朝中叶,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漕运官员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贪渎,并将贪渎的目标锁定在押运、税收、看仓等环节上。
贪污腐败的盛行使得漕运各职能部门的官员争相谋取私利、互相欺骗,漕务各级机构变成了一个上下庇护的贪污网。
在乾隆、嘉庆年间,漕督不但不能制止漕运官员的腐败行为,反而成为了他们贪污不法的护身符,官官相护。
贪污腐败也成为了清政府难以解决的痼疾。
伴随着漕政的衰败,政府整理运河的力度不断下降,清朝漕运进入第三阶段,漕运只能勉强维持了。
时至清代,黄患不断,运道渐趋淤塞,政府虽提倡治河以利漕,但不见成效。
咸丰五年,黄河于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山东利津入海,与运河交叉于山东张秋以南,长江以北运道因黄河淤塞而几近浅涸,漕运亦因此一度不行。
最终由于运道淤塞的进一步加重,进入了第四阶段,漕运废止。
面对运道浅阻而给漕运带来的困难,清廷不是力图治河利运,而是别筹海运。
漕粮海运,运河、漕运之于清廷的重要日渐不再,清廷之于运河、黄河的治理也因此日益荒疏,运道湮废,漕运复兴于是益加无望。
漕运的衰落除了上述提到的因素外,其实还与清政府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
漕运衰败是在世界进入工业时代的背景下发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闭关自守的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欧美国家的新科技产品传入中国,交通运输工具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此时以洋务运动为先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开始起步,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参与到了海漕事务中,这无疑为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形成了直接的打击,冲击了原有的漕运秩序,而后修通的津浦铁路也对原有的漕运体系形成打击之势。
当然给漕运以沉重打击的当推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
这两次运动以漕运征集地作为其活动地区,从根本上掐住了清政府漕运的喉咙。
因为战争的频仍,导致江浙一带的漕运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漕运走向衰败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尽管漕运最终走向了灭亡,然而不可否认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
二、淮安“运河之都”地位的确立
运河的畅通催生了运河两岸城市的繁华,而淮安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淮安凭其地理位置的优势最终确定了“运河之都”的地位,成为了维系运河流域全局的关键。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明朝《永乐大典》主纂姚广孝曾为楚州留下的赞美诗句,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淮安在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文人骚客、各路商人纷至沓来,有些俊杰亦从此在淮安扎根生活,催生了淮安文化经济的发展,也使淮安在彼时成为了一个社会都市,培育了诸多的文化名人,诸如吴承恩、关天培和周恩来等。
淮安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近长江而濒黄海,古淮水、泅水在此交汇,境内水网密布、河湖交错,被誉为“漂浮在水而上的土地”,其似乎天生就是为运河而生。
事实上,我国历史上有迹可寻的第一条运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的邢沟,其入淮处就选在了末口(今淮安区)。
但是,淮安以“漕运”为核心的城市功能并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早期淮安最初更多地是凸显了军事要地的作用,而在隋唐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国家政治中心东渐北移和经济中心南移的变化,使得开通的大运河一跃成为连接南北交通的干线,漕运量开始猛增。
淮安的主要城市功能亦由此开始慢慢转变为漕运要津。
由于淮安市运河干线上的重要一环,因此为了搞好淮安的转运衔接工作,隋就在其地设立了漕运专署。
元代对大运河进行了重大改道:
一是将隋运河“北京一洛阳一杭州”的走向取直,把旧运河的中段东移至山东境内;
二是修通京、津河道。
这样就使得前代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从而南北之间得以更直接地相连,由此奠定了今日京杭运河的基本走向和规模。
但终元一朝,对于漕运,其实行的是以海运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南北运输线路。
尽管如此,元对于运河的管理却是日益完善。
至元十九年(1282),政府设京歌、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分段责成其年各运粮200万石。
后来,又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和利津分司,实行长短途两种纲运。
这对淮安具有着重要意义:
一是运河的取直,淮安因此成为大运河的南北适中之地;
二是政府的漕运管理机构开始进驻淮安。
这为淮安成为明清时期成为运河制度奠定了基础。
明代南粮北运,初以海运为主,永乐初改以海、河兼运;
以后则以河运为主。
河运由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期。
明永乐年间为保证漕运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始设漕运总兵官掌漕运河道之事,正二品衔。
明代的漕运组织,在宪宗成化年间已趋完善。
设漕运都御史1人,理刑主事2人,皆驻淮安。
其职责是每当漕期处理军民交兑纠纷或运军犯法等案件,官员每三年一替换。
管厂(指管理清江等船厂)的工部主事2人,驻清江浦。
监仓(指负责粮仓驻在的漕粮保管事宜)的户部主事4人,分驻淮安、临清、徐州、德州。
设提举2人,一驻清江浦,一驻临清,值运(指催促漕运)粮储,镇守地方,总工官1人,协同漕运;
参将1人,皆驻淮安。
此外,朝廷还时差户部主事,亲临现场监督漕粮的交兑工作。
其中于成化七年,设总理河道,驻地济宁,与总漕平行。
从此,河道与漕司分成两个系统,成为常设。
嘉靖三十六年,由于倭寇骚扰,于淮安增设提督军务以加强护漕的武装力量。
嘉靖四十年,提督军务之职并归漕运总督。
明朝漕运制度和漕运之法虽有改变,但其沿运河广置粮仓、收储漕粮的原则却始终不变。
会通河开通后,淮安、徐州、德州始设仓,加上原设的临清仓、天津旧仓,共称五大水次仓。
这些设仓之处,都是漕粮集散的中心,这也标志着淮安在明代已基本确立了运河之都的地位。
而在清初,漕运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委派都主要参考明朝的各项规章制度。
中央专设统掌全国漕运的最高机构,最高长官称漕运总督(从一品),不驻京师,而驻淮安。
此为中央派出的机构(亦为中央权力的外放),其亲临漕运在线,以便更有效地进行漕运管理。
此外清朝同样重视在运河要卫设水次仓。
淮安作为运河枢纽,一直为仓储要地。
明代永乐年间即在山阳县清江浦设立常盈仓。
而清同治七年开建的丰济仓,则是南粮北运的中转仓库,运河沿岸四大粮仓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储粮库,占地2万平方米,当年储粮达100万石。
总之,漕运在有清一代发展到了顶峰。
其组织与管理制度之完备,法令之严整,皆是此前历代所不及,也正是在漕运发展的全盛时期,淮安最确立了其运河之都的地位。
作为漕运的中枢,河务的关键以及盐务重地,从明至清中期时期的淮安,其经济中心的地位达于极盛。
由于与大运河漕运的兴盛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永乐年间漕运总督的总兵官平江伯陈瑄在清江浦首创全国最大的船厂清江船厂,俨然成为全国的造船业中心。
而清代淮安的经济也因此发展到顶峰。
在乾隆时期人口已有54万,胜于苏州。
仅河下一处,因为侨民商贾的聚居就有22条街、91条巷,同时还有大量的外籍商人在淮安设立会馆,淮安商贸经济的繁盛可见一斑。
然而自清朝后期开始,因为洪涝灾害、河道瘫痪、海运崛起、漕运改制、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以及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等原因,淮安走向了衰落。
1905年,因无漕粮可运,淮安的漕运总督部院撤销,这也意味着淮安不再具有南北枢纽的作用。
然而淮安作为曾经的漕运中心、运河之都的历史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
三、明清时期漕运与淮安经济的发展
漕运令淮安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飙升,而淮安最大的经济来源,一是漕运;
二是盐政。
(一)漕运促使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
淮安地处黄淮交界,是大运河沿河一南北交冲城市,在海道未通之前,每年秋夏之际,南方数省的运粮漕船都衔尾入境,停泊于城西运河以待盘验。
“牵挽往来,百货山列,河督开府,清江浦文武厅营,星罗棋布,俨然一省会”帆墙林立,盛极一时”,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酒督盘查,以次出运河”。
清江浦不仅仅是运粮船队北上航行的必经之地,还要停泊下来等待酒运总督的检验。
那时清江浦的河面上停满了鱼贯而至的酒船,每只船上又有数百个酒军水手,都需要吃饭、娱乐。
再加上船上又夹带着许多土产,漕军们便很自然与当地人做起了生意。
这些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在清代,淮安城的发展已相当完善。
其城市商业区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街市的数量多、密度大;
其次是城市规划严整,强调方正、对称,行政中心居中,突出表现了都城政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理念;
最后一点是出现了许多专业性商业街,这意味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
常盈仓不再作为转运漕粮的基地,用仓不多,且淮安多雨地湿,墙体纪毁。
隆庆六年(1572年)都御史王宗沐重建八十余间,又纪甚。
此后,淮安等仓仅仅作为京通仓之预备仓。
至万历时,“临、德尚有岁积,而淮、徐二仓无粒米”。
清代沿袭明制,漕仓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
同治九年酒运总督张之万委派候补知县许佐廷建丰济仓,历时十四月建成,可储粮达100万石,为全国最大的皇粮储备仓,不仅是南粮北运的中转仓,还用来备荒储粮,平时春案秋来,遇到灾荒年份,开仓放赈。
到了近代,由于海运输业的发展和京沪铁路的建成,漕运废止,丰济仓彻底被遗弃。
此外尽管淮安的商品经济在明清两代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其农业经济却并未同商品经济一道得到发展,相反由于其地理位置以及政府原因,受到了忽视,故其农业经济薄弱,一旦漕运受到影响,由于农业的薄弱,其经济必呈现下沉的趋势,而这也成为日后淮安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二)淮安的盐业经济发展
淮安是淮北食盐集散中心,盐业的发展与漕运也是密切相关的。
漕运给纲盐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大运河的便捷使得淮盐能顺利运抵大江南北。
此外,漕船夹带私盐己经成为公认的事实,私盐的泛滥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盐业经济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淮安盐业发展得益于漕运的发展。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盐基本都是国家专营的。
盐是老百姓生活不可替代的口用品,利润非常的丰厚。
淮安府境内因为沿海,是重要的盐产地,也是淮北纲盐囤积之地。
明初的盐政使用“开中法”,令商人输粮于边。
粮入仓后,发给凭证(盐引),到各运转使司指定的盐场支盐,并运到指定地点销售。
在明代各盐运衙门中,两淮盐课数最多,有“两淮盐课,足当天下之半”之说。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治所在扬州城,下辖三个分司,其中泰州、通州二分司皆位于淮南,为淮南盐运分司;
淮安分司则地跨淮河南北,治所设在安东县,为淮北盐运分司。
根据刘森对明初和嘉靖年间两淮三司亭兆、卤池的数据对比分析表明,淮安分司亭兆、卤池的发展幅度要比泰州、通州二分司大得多。
另外,嘉靖年间灶户和灶丁额也是淮安分司最多。
盐的转运主要以商运为主。
无论是官盐还是商盐,必须持有盐引,而且须经批验盐引所称掣才能离场外运。
在两淮运司设有仪真、淮安两个批验盐引所。
淮安批验所原在淮南,“历正统以来,屡因淮水冲塌,迁徙无常”,到正德十年,迁徙到淮北河下大绳巷,“开支家河接涟水,据十场津要,以通公私,舟揖往来,民甚便之”。
在淮盐转运中,淮安的地理位置很重要,“自高堰而北,由板闸则通淮北诸盐场,自高堰而东,由径河、黄埔则通淮南诸盐场,自堰而西,则通盯胎,自堰而南,则通天长,东西二百余里,其地至为要害”。
几乎同时,淮北盐运分司署也因为黄河夺淮入海的缘故迁移到淮安河下,与淮安批验所同处于河下。
河下遂成为淮北盐必经之地,当地经济繁荣趋于鼎盛。
淮盐暴利的背后隐藏着重重的利益纠葛。
盐商、灶户以及政府之间的利益纠葛不清。
为了增加政府盐赋收入,明代中期的叶淇盐法改革始“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购置军储,“每引输银三、四钱”,后又增至一两三钱。
政府把对灶户的直接控制剥削权,转让给了一些大的盐商。
盐商们便充分利用这一特权,对广大灶户和消费者进行剥削。
大盐商们凭借政府给与的特权,“多方网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
或诡称盐将缺,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
且复每包缺少分两,掺和泥沙”,场商们对灶户更是“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57。
除官方批准的贩运外,私盐也很盛行,嘉靖时御史徐蟾就曾指出,“淮、扬之间,私贩盛行”。
淮盐的高利一直持续到清朝中期,相互妥协的利益关系终于因为矛盾重重而面临土崩瓦解的地步。
“引地最广,故赋课亦甲于天下”5”的两淮盐务衰落的显著标志是盐价上涨,淮盐滞销,盐商从“两年三运”到道光初期的“一运两年”。
运盐船只因为卖不出去盐而滞留在口岸,需要“年半乃能回空”。
道光6年至10年间(1826-1830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澎奏称两淮“每年所销之盐不及额引十分之四”,淮盐滞销使“商人资本占搁,完课甚属拮据,视办运为畏途”,与之相反的则是私盐市场的繁荣,一时间盐袅大行其道。
为了打开官盐销路,增加盐税,道光十二年(1832年)七月,清政府采纳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澎建议,在淮北试行票盐制。
票盐制取消了行之百年的盐引制度,打破了原有盐商的垄断经营模式,在淮北境内取消了行盐地界的限制,承认了盐袅的合法性。
淮北试行很是成功,基本完成了初衷,增加了盐税,但对于世代从事引商、运商的盐商们却是致命一击。
以前的巨商甲族“夷为编氓”,过去的“高堂曲谢,第宅连云”,“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
旧口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己”。
道光三十年淮南也改行票盐法,同样获得了成功,盐价下降,民众欢呼雀跃。
淮安作为漕运总督的管制之地,巨额的财政拨款充实了当地的府库,又是南北漕运交通的咽喉,便利的环境造就了民间贸易的繁荣。
此地又是淮北纲盐的集散地,催生了大批盐商,带动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国家政策的改变会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漕运改海运后,运河得不到政府补贴维护,愈来愈堵塞,最终被彻底废弃。
没有了人来人往,市场逐步萎缩,人口也向发达地区流动,整个淮安城衰败了。
清咸丰五年(1855年),由于运道淤塞,漕运式微,海运崛起,淮安的商贸地位一落千丈。
安徽的捻军攻陷清江浦后,清廷裁撤河道、漕运官员,拨发的努金口渐减少。
“百事废罢,生计萧然”是当时淮安彻底被抛弃后的真实写照。
淮安的民俗又是“乐安居,惮远出”。
本地人不擅长行商坐贾,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家靠着佃户的租金、提成吃饭,无产阶级寄生于漕河盐荚,徽、扬商人做生意,各有分工,在大变故之前倒也能和平发展。
可是大厦将倾,富人家口益贫困,每次遇到水旱灾,佃户、贫民们就背井离乡,扶老携幼,结伴到江南地区乞讨。
而江南地区也是刚刚饱经太平天国战火的洗礼,很多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便招徕这些流民垦荒安置。
因为江南的土地肥沃,且不用再受水患,很多流民也就留在南边,而本地的田地越来越荒芜。
淮安城市缺乏农业的支持,商业也迅速衰弱下去,成为淮安经济发展几百年来最显著的一次变化。
四、“运河之都”兴衰的思考
淮安城市兴盛的缘由是漕运,而衰落的原因却有很多方面。
首先是淮安农业的不发达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淮安从明至清,一直饱受水害之苦。
山阳城内行舟,禾苗荡然无存,漂溺人畜甚众等现象时有发生,所以淮安的农业基础相当薄弱。
“老赢乞讨,填门塞途,仅能慰谕而己”。
在封建农耕时代,农业的发展是关系到城镇居民生活的基础。
而淮安的农业基础地位因为其当地的自然条件及传统观念的原因而被忽视。
由于淮安城市经济的发展过分依赖漕运。
漕运是一项政治活动,受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很大,因此作为经济发展唯一支柱的漕运一旦罢行,衰落就成不可足阻挡之势。
最为明显的是,伴随着漕运而生的相关产业迅速衰败,大量从业人员失业,特别是服务业因为客流量的减少而极度萎缩。
此外,盐商的衰落和普通市民的贫困导致了淮安消费能力的下降。
票盐制的实行,打破了原有盐商的垄断地位,加之盐商们奢侈腐化的生活使得他们的经济每况愈下。
普通市民也因为经济的普遍萧条而陷入了捉襟见肘状态,“耕读之家口益穷困”。
然而官吏的贪污腐败以及政府的无作为使得淮安人的生活雪上加霜。
总之,淮安是一个典型的运河城市,漕运的兴衰决定其兴衰。
淮安城市经济的衰落有其先天不足的一面,农业基础的薄弱使得商业的发展无基可凭,由于商业的发展依据单一,因此一旦失去了漕运和盐业的商机,城市经济只有迅速衰败。
此外,封建社会制度的缺陷也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衰落。
因此我们需要以史为鉴,城市发展需要走多元化道路,要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各种产业相互促进,才能真正的走向繁荣,而不只是昙花一现。
如今,江苏省政府立志于将淮安建设成为苏北经济中心,因此淮安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已呈现出上扬的态势,这也让我相信未来淮安市的经济发展定将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高元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张强:
《漕运与淮安》,《东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四期。
[3]赵明奇、韩秋红:
《运河之都淮安及其历史地位的形成》,《江苏地方志》2006年第四期。
[4]刘清平:
《明代漕运史浅谈》,《史志学刊》2005年。
[5]吴鼎新、张杭:
《明清运河淮安段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研究》,《淮阴工学院学报》2009年。
[6]高寿仙:
《漕盐转运与明代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学海》2007年2月。
[7]张照东:
《清代漕运与南北物资交流》,《清史研究》1992年。
[8]彭云鹤:
《明清漕运史》,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李文治,江太新:
《清代漕运》,北京:
中华书局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