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我的家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的家史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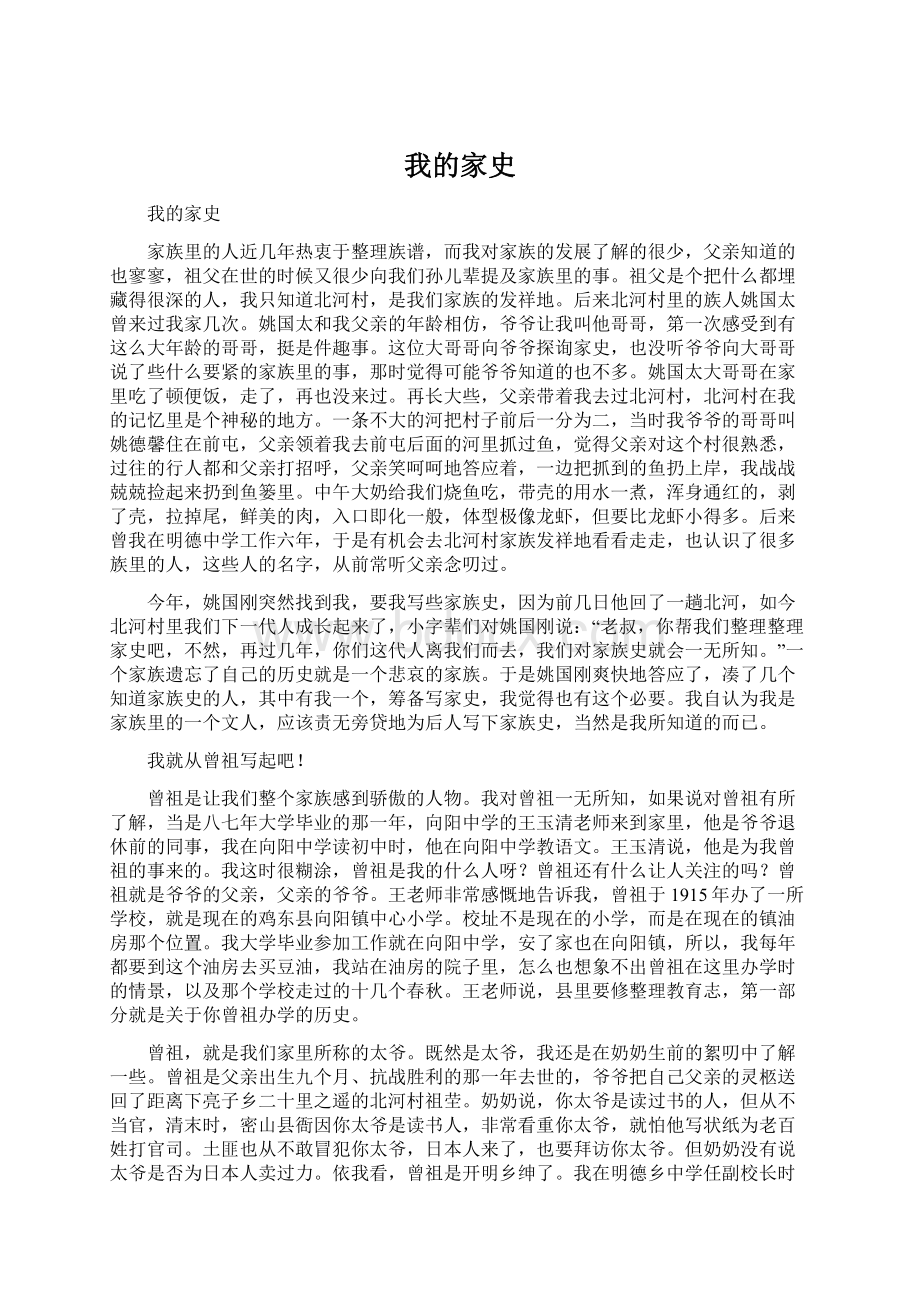
王老师非常感慨地告诉我,曾祖于1915年办了一所学校,就是现在的鸡东县向阳镇中心小学。
校址不是现在的小学,而是在现在的镇油房那个位置。
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就在向阳中学,安了家也在向阳镇,所以,我每年都要到这个油房去买豆油,我站在油房的院子里,怎么也想象不出曾祖在这里办学时的情景,以及那个学校走过的十几个春秋。
王老师说,县里要修整理教育志,第一部分就是关于你曾祖办学的历史。
曾祖,就是我们家里所称的太爷。
既然是太爷,我还是在奶奶生前的絮叨中了解一些。
曾祖是父亲出生九个月、抗战胜利的那一年去世的,爷爷把自己父亲的灵柩送回了距离下亮子乡二十里之遥的北河村祖茔。
奶奶说,你太爷是读过书的人,但从不当官,清末时,密山县衙因你太爷是读书人,非常看重你太爷,就怕他写状纸为老百姓打官司。
土匪也从不敢冒犯你太爷,日本人来了,也要拜访你太爷。
但奶奶没有说太爷是否为日本人卖过力。
依我看,曾祖是开明乡绅了。
我在明德乡中学任副校长时,乡里黄秘书的爷爷是我家的长工,他从爷爷那里听了些我太爷的轶事。
从他的描述中,曾祖身穿黑大褂,足登黑布鞋,白色包脚布常年干干净净,那时曾祖年事已高,他老人家经常到田间走走,或到穆棱河里里打打鱼,消遣着晚年的岁月。
黄秘书还有谢意地说:
“我爷爷从吉林逃荒来到黑龙江,给你家放牛,是你太爷收留了他,后来还给我爷爷成了家,才有我们这个至今兴旺的家族。
”
有个远房亲属,是我大姑父的大姐夫,叫韩百庆,我也随姑姑家的表弟叫他姑父。
今已耆耋,二十年前我去过这个姑父家,是为了我的工作。
韩百庆姑父是北河村生人,和我家是邻居,谈到我曾祖时,韩家姑父兴致勃勃,乘着酒兴,聊起了我太爷。
那时他年龄还有小,在向阳镇上小学,就是我太爷筹建的那个小学。
他说,我每天放学回来,都能在河边看到打鱼的你太爷,你太爷待人极和蔼,特别让我们这些孩子喜欢。
只要看到你太爷打鱼,我们都会欣然地跑过去,围着他,问这问那。
有时还向他要鱼,你太爷会一抬手,指了指,河叉的稳水处,用柳条编制的鱼囤子,自己去拿,太爷打的鱼,吃不了就放在水囤子里,任人想吃即取,从不理会。
太爷打鱼的事我听说过,不是主要不是为了自己吃,大凡是消闲,打发时光,和修身养性。
一个暮春,太爷曾用鱼叉叉了一条百斤重的黄色的huá
i子。
这个字字典里没有收录,我只好用拼音代替了,从别人的描述中,约略知道,这种鱼就是长成的超大的鲶鱼(其实不是),但不是同一种类,只是外形极像而已。
太爷根本无法搬运,索性搁在河边,太爷扛着鱼叉,悠闲地走在田塍上,遇到同村一个温氏族人,给了他,拉回去喂了猪。
我感到很惊奇,我生在新中国比较贫穷的年代,吃鱼如过年,那个年代鱼怎么能轻易地喂猪呢?
后来知道,那时鱼就是多。
有个刘汉武(我老姑父三妹妹的公公)说,他小时过年,赶狗爬犁掉进了冰窟窿,一抬头,冰层下面冻着一层鱼。
每条都有二斤多重。
我记得他曾哀叹地说,这年头,鱼快绝种了。
曾祖三十岁那年开始办学,也就是爷爷出生的那一年。
当时办学的人很多,可见我们这个中国边陲之地,也开始重视教育了,但大多是私塾。
曾祖办的这所学校是公学,所谓的公学,是中华民国性质的学校,执行中华民国的教学大纲,教授中华民国的统一教材。
之所以曾祖当年办学至今仍有这样的轰动,就是在中华民国成立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在中华大地的东北偏远之地,竟办起了公学,当然这是个谜。
太爷的生活来源是出租土地,而土地是清朝末年经满清政府批准跑马占荒得来的,建国后,我家成分是地主,和太爷拥有很多土地关系极密切。
这些土地的分布:
一是现今明德乡新光、曙光朝鲜族两村;
二是鸡东县永安火车站南。
共有四方地,“方”是土地面积单位,好多人已不知道了,一方地是四十四垧四,一垧地是十五亩,所以一方就是六百六十六亩地左右。
曾祖把这四方地平均分给我爷爷,爷爷的哥哥、弟弟、妹妹四人。
太爷把土地均分给四个孩子是在曾祖母去世之后,曾祖母葬在祖茔,曾祖父去了我家,当时爷爷带着我们一家人在下亮子乡正乡村做日伪政府的一个小官。
除爷爷外,其余的土地分别被三人买掉,爷爷的哥哥用买来的钱赌钱,喝酒挥霍一空,爷爷的弟弟吃喝嫖赌花得分文皆无,爷爷的妹妹用钱做了嫁妆。
只有爷爷准备守着这些土地想过安生的日子。
可是解放后,爷爷成了地主成分;
爷爷的哥哥是贫农,后来还入了党,成为一名会计,是柴河林业局的,但因贪污后被辞退了;
爷爷的弟弟也是贫农,分文皆无后,因不务正业,妻子与他离了婚,独自带着未成年的儿子另嫁了他人。
爷爷的弟弟成为北河村一个五保户,独自生活在生产队里,由族人养老,于一九八四年秋去世。
爷爷的妹妹,也是贫农成分,嫁到双鸭山一个冯姓人家,无嗣,有个养女,取名冯艳,七十年代曾多次来我家,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无了音讯。
爷爷的哥哥,娶了杨姓女为妻,无子,仅生一女,姚志贤。
爷爷的哥哥于一九九四年去世,比爷爷去世晚一年。
爷爷一九一五年出生在北河村,比爷爷的哥哥小二岁,曾祖是读书人,曾祖必然要让爷爷读书,爷爷毕业于东安师范,东安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鸡西密山市。
爷爷一九三零年与奶奶赖明芝结婚,奶奶长爷爷四岁,这一年爷爷十五、奶奶十九。
伪满时期,爷爷做了日本人的一个小官。
我后来和朋友打趣说,我爷爷是个汉奸,大家都是一笑了之,不在意爷爷究竟是不是汉奸,或许朋友鄙视我把这不光彩的事当作了荣耀。
但是四五年光复那一年冬,日本人撤退,伪政府倒台。
爷爷搬家回了北河村,我家的大劫难就发生北河村的这一年冬天。
爷爷当过伪政府小官的下亮子乡正乡村的农会派来一队人马,要抓爷爷回去审判,这是光复时的一种通例。
据说,那个村已枪毙了几个所谓的恶霸,没有严格的审判程序,只是公审,村民的口号就是判决。
如果爷爷被抓,命决不保。
族人姚风伍、姚风立,两位均是我的伯父,比爷爷的年龄小一些,也是北河村里的代表人物,和下亮子正乡村派来的农会成员有些交往,在两位伯父力保下,爷爷没被带回去受审而留下一条性命。
留下农会成员杀猪宰羊隆重地吃了顿大餐,夕阳西下时分,两位伯父终于送走了农会成员。
但农会抄了我的家,奶奶说,当时农会只给我家留下一个碗架柜和一个刚生崽不能掠走的母猪。
一队人马就这样气势汹汹地消失在淡红的夕阳里,厚厚的雪野上留下了串串零乱的脚印。
从此,爷爷带着一家六口人以春耕秋收为生。
这样在北河村度过了九年光阴,老叔、三姑、老姑都出生这期间。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需要教员,爷爷是那时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族人的劝说,奶奶的支持,爷爷走上了近二十年的教书之路,直到一九七四年因病退休。
爷爷在很多村的学校教过书,家有时能随爷爷工作调转而搬迁,不能随之搬迁的时候,爷爷就住在外地。
奶奶领着六个孩子艰难地生活。
我们家在下列村屯住过:
鸡东县明德乡更新村、建政村,鸡东县向阳镇新建村、红星村、古城村、东河村。
最后定居于东河村,虽然后来爷又调到别的村工作,我们家再也没有搬迁。
直至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因哥哥在县城鸡东镇工作而搬到了鸡东如今已十六年多了。
我们哥三个现都在鸡东镇工作和居住,东河村就是我们记忆和情感上的故乡。
现在只有叔叔还住在哪儿,有时我们也回去看看。
有时哥几个聚会的时候酒使我们洋溢于对往事的追忆。
父亲说,我们家是应当时东河村一部分村民之邀定居在这里的,善良的村民帮助我家盖了二间茅草房。
我的记忆中房前是条宽敞的村道,道南一个水泡子,我之所以称其为“泡”,而没称池塘,是因为,规模小得可怜,旱季会干涸;
水中没有任何翠草装点出秀色,在这里晚霞也不能辉映出田园的宁谧;
但水泡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只要秋季水量充足,冬季,就能冻出一个光滑的冰面。
这冰面就成为我们村里儿童的乐园了。
从此三十多年生活在东河村,这三十多年我家既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家族史,亦是从此走向昌盛的开端。
整个文革我家都在这个村度过的,因为前文说过我家因爷爷没有把太爷分给的土地买掉而成为地主成分,这个成分当时是极高的成分,成分越高遭受的打击越惨重。
爷爷是地主,父亲成了“子弟”,是富家子弟,我们家自然是革命的对象。
可是我们家有什么呢?
贫穷的比被当时称为贫农的还贫穷,我们家的房屋都是善良的贫农帮助盖起来的。
我不想把我的家史和历史相联,因为我不想把这部家史写成日后历史参考的佐证。
但是我不可能,也不想把这段家史省略,所以只写几段相关的事件!
定居东河时,大姑、二姑已结婚,家中七口人(爷爷、奶奶、伯父、父亲、叔叔、二个姑姑),后来陆续地伯父上了中学,继而父亲上了中学。
家里再穷爷爷也要供孩子们上学,伯父考上了当时密山县重点高中——密山一中,现在密山一中是省级重点高中。
这是很荣耀的事,爷爷认为从此家中又有了光宗耀祖的儿女。
伯父功课很好,在一中读书时突然生了心脏病,休学在家,没多久病故了,年仅十六岁。
爷爷的理想破灭了,可想而知这对爷爷和奶奶的打击多么惨重,死去的不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更是一个家庭需要经历多年才能培养出和期待得到的希望,而这个希望于将近实现的时候破灭了。
社会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人民公社成立,村里诞生了生产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新生的事物,我国历史自从进入封建社会就没出现过集体现象,生产队是集体经济形式,这必然是中国历史上最新鲜的历史现象,百姓在狂热的政治潮流的感召下都向往着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而走进了人民公社,我们家不是其中的成员,爷爷教学,是教师,奶奶是家庭妇女,伯父、父亲是学生,叔叔、二个姑姑还是孩子。
像我们这样的村民这时在村里常常受歧视,因为家庭里没人在生产队里劳动,为集体做贡献。
每到秋天生产队分口粮,不成熟的粮食分给我家,又短斤少两,每年口粮接济不到下一年,一家人常年勒紧裤带过艰苦的日子。
为了扭转这个悲惨的家庭局面,爷爷决定让没读完书的父亲辍学,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提高家庭在生产队中的政治地位。
当时这倒是个明智之举,但对父亲一生的命运是不公允的。
然而这样的决定是只能由历史造就,又有谁能超越历史呢!
历史能成就一个人灿烂的前程,也能改变和摧残一个人的命运。
父亲与母亲于一九六二年结婚,一九六三年哥哥出生。
从老姑一九五三年出生至今我们家已十年没有新生命诞生了,哥哥出生预示着家庭的兴旺,也彻底湮没了伯父去世给一家人带来的痛苦。
我于一九六五年出生,我和哥哥是同一个生日:
农历十月十七。
我们家因我出生又兴奋了一阵子,一个家庭连续二个男丁诞生真是个好兆头。
我出生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
其实文革并非一九六六年开始,早于母亲怀我的时候,奶奶因是地主老太婆,而受到村民在生产队大会的公开批斗,那时奶奶的这个称号,常常是虐待儿媳的代名词。
这必然需妈妈出会作证,幸好母亲怀着我,挺个大肚子,不便出会,母亲躲过一次尴尬的经历,一面是一家人的婆婆,一面是残酷的社会政治。
偏向婆婆,社会政治不容;
顺应潮流,于情不容。
所以我长大后,母亲每每想起这事,对我心怀感激,说我还没出生,就给她带来了好运。
文革中,父亲记忆最深的就是受批斗最残酷的三户地主家庭:
一个是李迎权家,一个是康庭满家,一个是我们家。
生产队里的批斗会常常开到冬天里的深夜,每次批斗结束,奶奶拖着疲惫的身体,一言不发地回家。
奶奶抬头看着满天的繁星,眨呀眨的,泛着冷涩的光。
奶奶没读过书,她也许永远都不能明白,这个悲剧的原因和结局,只要听到村里生产队里沉重的钟声,在星星升起时响起,奶奶就要抖抖瑟瑟地穿上衣服,板着面孔奔到生产队广场的木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任凭台下的贫农问些不着边际的话,也要委心地答到自己如何像黄世仁的母亲在昏暗的夜里,用针扎过为她槌腿的喜儿,剥削过贫农,虐待过下人。
村里的人这时为什么忘记了,是为人忠厚的爷爷打动了东河村民,才要求我们家定居在这里,能让学校有个固定的老师,为村民们培养下一代。
我们一家也感谢东河村的百姓对我们家人的信任。
是什么力量改变了村民纯朴的风化,是什么力量让友善而狰狞。
在文革中最让父亲记忆深刻一个人叫穆春生。
我读大学期间的寒假,我常到穆春生家去,在昏暗的灯下,和这位我称之为二伯父的穆春生评论《三国演义》中的历史故事,觉得二伯父很有文化。
这个村中只有他用看书打发闲暇又漫长的冬季。
每次从二伯父家回来,父亲脸有愠色,母亲也愀然。
这年的除夕,父亲终于告诉我穆春生的所作所为,一年冬天,生产队里批判年逾六旬的李迎泉,李迎泉站在学生坐的长条板凳上,蹶着腰,脖子上挂了一桶水,保持这样艰难的姿势长达几小时接受贫农批斗。
穆春生批的兴起,语言已不能表达他对李迎泉的愤恨,飞起一脚,把板凳揣翻,逾六旬的李迎泉,人仰马翻,重重地摔在地上,冰冷的水溅了他一身,可是李迎泉吃力地站起来,又默默地把水桶自挂在脖子上,扶好板凳重新站好接受再教育。
村里从未传言过地主李迎泉的恶行,也没有人对他嫉恶如仇
七十年代,我和哥哥都上了小学,文革留给我的直接印象,是书包里装本毛主席语录,背诵每一句真言要语,虽背诵了很多最高指示,能记忆犹新的很寥寥,虽常与他人谈论毛主席语录,都是后来在别人的口中偷来的。
一本小小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真是一书难求,走遍了前后二屯,最后在忠信村的供销社买到了红彤彤塑料皮包装的《毛主席语录》。
书包里装着这本书才敢踏实地走进教室,恭恭敬敬地拿出来放在书桌上,丝毫不敢怠慢,虔诚地等着老师讲解。
一个同学是邻居家的叫刘君华,居然顽皮地把《毛主席语录》无知地放在了家门前的粪堆上,他母亲看到,吓得浑身颤抖着忙恭身拾起,将儿子拖回家,狠狠地教训了一番。
一年冬天,父亲和三姑到村西头的学校去排练样板戏《白毛女》,三姑在戏中扮演受尽苦难的喜儿——白毛女,父亲拉京胡伴奏。
这是个美差,因为三姑有演艺天赋,父亲擅长乐器,积极地参与这些红色活动多少能避免因家庭成分高而带来的政治破坏。
这时我还是个孩子,不懂得政治与家庭息息相关的联系,趁天黑时,愉愉地趿拉着鞋,踩着冰冷而厚厚的积雪跑到学校看父亲和姑姑他们排练样板戏,有个和父亲一同拉弦的,叫李子英的伯父还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巴掌。
政治生活的悲惨给人以精神上的压抑和摧残,一个人生活在不幸福的政治年代远比物质生活的贫乏要痛苦得多。
然而物质生活的困乏也不得不逼迫人去思考生存的第一要务。
妹妹一九六七年出生,弟弟一九七二年出生,都出生在国家最贫困的年代,也出生在我们家庭最贫困时候。
母亲的奶水不足,我们姊妹几人在婴儿时都要吃一种母亲自制的代乳品:
将白面满满地压实一碗,放在锅中蒸熟,我们饿的哇哇哭叫的时候,母亲将蒸好的白面挖出一块用温水冲开加少许糖,灌进奶瓶扣上奶嘴,匆匆忙忙地塞进我们的嘴里,呜呜的哭声渐小渐止。
母亲现在想起这事,泪水盈眶,做了母亲却不能让自己的宝贝吃得饱,眼看自己的孩子在那个年代,一出生就和自己忍饥受冻。
至亲的母爱在这个扭曲的年代备受着煎熬。
本来父亲辍学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以期从生产队的生产总值中分得可观的一块蛋糕,但是生产队成立没几年,青黄一年,人均产值还不够一年的口粮。
父亲丧失了学业,实质上又没有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累死累活了一年,也不能满足温饱。
如今还是这块土地,依旧是那么人口,甚至比那时人口还有增加,可是现在的生活水平要比那时高得多。
在我十九岁的那年,生产队这个当初被奉为最先进的集体形式走到了末路。
留给我们的至今仍是从思想层面上的一个思考。
弟弟出生的那年冬天,我们家先于集体经济形式,走到了分家的边缘。
叔叔要结婚,没有房子,奶奶忍痛让已有四个孩子的父亲母搬出去另立了门户。
分家的时候,父母并没有从大家中分得什么物什,那时我已省事。
搬家是在一个冬夜,繁星渐起,灯火初上,妈妈哭泣着搬走了属于自家的几套被褥,一点粮食,一个水缸。
母亲内心一定很沉重,前边的路一片茫然,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近十年,分得的除了几个急待抚养的孩子,一无所有,我也有些痛恨奶奶的无情。
父亲是木匠,乐观豁达,没有锅盖,父亲在灯下抢制,一定要在明天早上,自家开锅造炊时让孩子们吃上热饭。
母亲的忧伤亦没有挂在心里,第二天就快乐的领着自己的孩子生活了。
虽然是初次独立,母亲因为三岁就没有了母亲,已练就了一身独立的本领。
第二年开春,阳光无比和煦,封冻一冬的土地被洒得,干燥而温暖。
家中无以烧饭的柴草,父亲快乐地命令哥哥和我领着妹妹到去年的大豆地里拨豆茬,装满筐,抬回来放在房东家的庭子里洒一小会儿,填进灶中呼呼啦啦地窜着蓝火苗,扒在灶前,任火炙烤着小脸,也要尽享亲手带来的炽热与温暖。
年少不知愁滋味,热乎乎的粗粮淡饭,就着一点咸菜,只要吃得饱孩子就能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房东家一个叫小伟的孩子小我两岁,是个不足月的早产儿,看上去营养不良,但他是个男孩子,天生出奇的淘,我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两个野小子在一起自然快乐无比。
冬天下雪要帮助扫雪,夏天要抢着洒扫庭院,生怕房东不高兴,下逐客令。
共在小伟家租居了两年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七四年春天,我家搬到小伟家西院的赵玉文家住了。
搬家时,住在明德二姑家的大表姐来帮搬的家。
那天春光明媚,柳枝柔柔在风中曼舞,阳光消融了冬天的冰雪,融化的雪水让搬家的路变得泥泞,天气虽好,只因路碍心里滋生了一些惆怅。
赵家的房比小伟家的小得多,赵玉文的妻子姓张,是本村的姑娘,妈妈让我们叫她大婶。
大婶是个孤僻的媳妇,在我记忆中,大婶脸上总挂着不知因为什么而来的愁容。
大婶家不富,但干净无比,所以母亲最怕我这个淘气的家伙闯进去。
母亲的反复叮咛,虽没有让我对大婶产生神秘感,反倒让我怜悯大婶是个可怜孤独的人,当时大婶结婚好几年了,还没有孩子,生产队一收工,她家里的赵叔叔,沉默地回来,大婶准备好了饭菜,两人坐在火炕上小桌两边,默不声息地各吃个的饭。
她家每次吃饭都好像是重复着同一出哑剧。
爹妈时常关起门来小议一阵,小议后是一阵笑声,然后还不忘记瞪着眼睛叮嘱我们,出去不要乱讲刚才的话。
这一年家里发生了很多事
先是生产队批了一块宅基地,让我们这个六口之家,有一个安身之所。
队长是谁我记不清楚了,这不亚于美国的林肯总统颁布《宅地法》给美国黑人带来的兴奋,我们一家人非常感谢这个队长大叔,只觉得那时父母干起活来非常有力气。
好像整个宇宙或整个社会都在关照着他们的慈爱的灵魂。
夏天,村里的叔叔阿姨们都来了,叔叔们和泥,脱坯,不一会儿工夫,叔叔们就在生产队的场院里脱出一大片阳光一照就亮晶晶的土坯,我幻想我们的家就在这大片平面的土坯中。
阿姨们忙里忙外的做饭,那时生产队里的劳动繁重无比,年轻的阿姨们无暇释放浪漫的心灵,她们摘着菜,打趣另一个阿姨的丈夫。
叽叽喳喳地做好了叔叔们喜欢的菜蔬。
秋天晒干的土坯,码成垛用草一苫。
看着成垛的土坯,爹妈感觉希望光临了我们家,幸福从此开始了。
虽然这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灾难,但没有阻止我们家好运的到来。
生产队长张金山、裴树祥给我家派了一个马车工,以上山帮我家砍柴为由偷伐些木料,以备明春盖房。
当时父母非常高兴,父亲觉得辍学十多年在生产队政治地位终于有了提高。
这样的好事,母亲在家里筹备些酒肴,等着上山回来的父亲和帮助偷伐木料的帮工,夕阳西下,淡红的落霞笼罩着美丽的乡村,全村的炊烟已落尽,母亲到村口眺望了几次,不见落日的余辉中满载木料归来的车。
母亲的心嗵嗵地跳着不停。
夜已来临了,暮星寥落,伴着明亮的常更星,父亲没有回来,大凡是出了什么事。
我和弟弟妹妹睡醒一觉时,发现父亲回来了,沮丧地坐在炕上,眉宇间愁云浓布。
车夫张廷珍伯父将马车驾翻,辕马被卡死在车下。
一匹壮年的白马,为我家盖房捐躯了。
父亲赔不起这匹马,任凭生产队怎么处理吧;
可是出乎意料地队长命令屠夫将马肉分给了全队社员改善伙食了,第二天队里重派了一辆马车将扔在途中的木料运了回来,堆满一院,父亲看着这堆木料,有些伤感白马英年早逝,超载是肇事的祸手,贪婪就会丧失生命,抑或是别的生命,然而让别人付出代价,自己获得利益,伦理难容。
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家梦寐以求的房子落成了,但也只能说是个毛坯房,尽管如此心灵终于有了依归,这一年我十一岁,看着自己家的房子,好似漫漫十一年的漂泊终于有了停靠的港口。
秋天,大队卫生所大夫周凤鸣叔叔到我家说,大队决定让妈妈去县里学习接生,其实这时妈妈已会接生,妈妈的师傅是一个姓吴的老太太,村里人都称她“老吴太太”。
老吴太太是个善良、利落、有威望的长者。
妈妈每次带我到她家,我总能吃到甜甜的糖果。
大队决定让母亲去县里学习就是因为妈妈有接生的基础,也算是让母亲在这方面深造。
妈妈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我休学在家为父亲做饭,又要照看两岁的弟弟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
这年冬天是我们家最艰苦且给我的记忆最深的一个冬天,这年冬天我长大了,我是这个家庭中的小“主妇”,起早为父亲做饭,很难想象我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当年是如何吃了这苦。
新盖的毛坯房,没有门板,父亲用向日葵桔秆编了一个帘子挂在门上,外衬一个棉被,遮挡寒冬肆意的西北风,晨光熹微,残星寥落,我持一簸箕,揭开门帘,匍匐着爬出去,尽量把门帘开得低,避免寒风冲进水缸常结冰的家。
新批的宅基地处于村子的最北面,是一趟新街,爬出门,站起来,透过熹微的晨光,老街袅袅的炊烟盘旋着升入乌蓝的天空,缕缕炊烟深处一定掩藏着温馨。
回望自家,孤零零的一座残破的新房子顿感孤独。
三岁的弟弟成了我唯一的伙伴,我做饭,弟弟常常把土窗台上结的冰溜子塞到嘴里,满嘴泥巴,还笑眯眯地看着我,我急忙擦干手上淘米水,抠出弟弟嘴里的一大块冰,弟弟就坐在地哇哇地大声哭叫。
白天父亲到生产队劳动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俩,有时太阳温暖地照耀着,领着弟弟躺在外面的柴草垛上晒太阳,数着母亲回来的日期。
母亲回来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吃罢晚饭还不见母亲的踪影,我和弟弟蹲在村边的猪圈旁,瑟缩着守望母亲归来,夕阳微红地挂在天边,渐渐地落下去,只给我和弟弟留下一片淡淡的殷红,母亲就是从这片殷红中回来的。
可是母亲在家只住了一宿,我和弟弟争着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星期日的下午母亲回学校了,我和弟弟又把母亲送进一片日光留下的淡淡的殷红中。
第二年春天母亲毕业,成了附近村子最有名气的接生员,母亲一生善意浓浓,深更半夜地有人来叫门,母亲就急忙穿上衣服,拿了接生的器械(一个白布口袋,里边装着一个白洋膝盆,盆里有简易的工具和一些药物),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生孩子寻常无比,几乎是每天村子里都有生产的女人。
母亲越发忙了,我们一家人最不高兴的是每年除夕母亲都在外接生,一家人很少能在一起过一个团圆的春节。
这时村里的“老吴太太”主动退了休,每当有人求她接生时,老太太就说去找我的徒弟吧,又耐烦地指点我家的住址。
那时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