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Word文档格式.docx
《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Word文档格式.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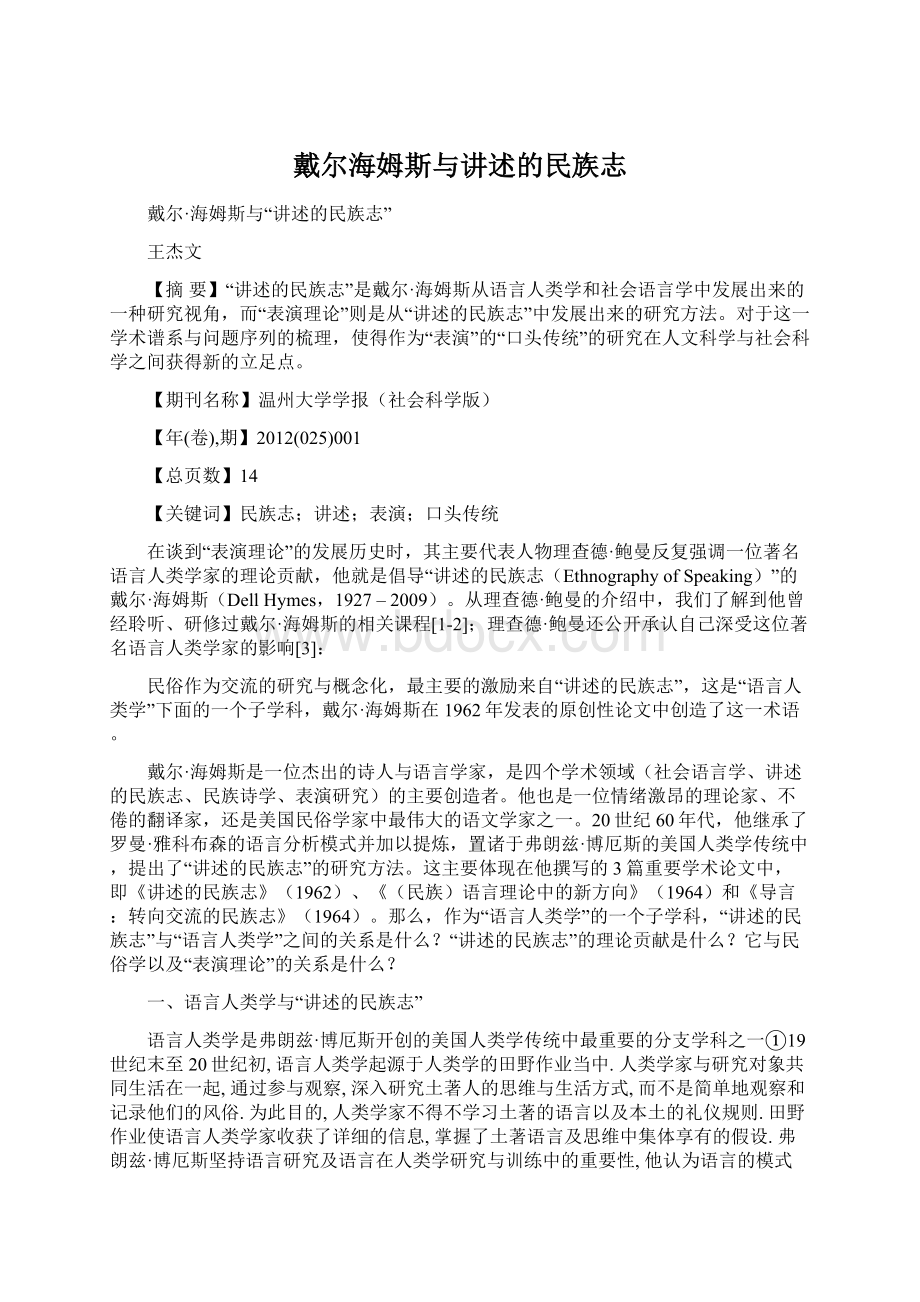
博厄斯的美国人类学传统中,提出了“讲述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这主要体现在他撰写的3篇重要学术论文中,即《讲述的民族志》(1962)、《(民族)语言理论中的新方向》(1964)和《导言:
转向交流的民族志》(1964)。
那么,作为“语言人类学”的一个子学科,“讲述的民族志”与“语言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讲述的民族志”的理论贡献是什么?
它与民俗学以及“表演理论”的关系是什么?
一、语言人类学与“讲述的民族志”
语言人类学是弗朗兹·
博厄斯开创的美国人类学传统中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语言人类学起源于人类学的田野作业当中.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共同生活在一起,通过参与观察,深入研究土著人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而不是简单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风俗.为此目的,人类学家不得不学习土著的语言以及本土的礼仪规则.田野作业使语言人类学家收获了详细的信息,掌握了土著语言及思维中集体享有的假设.弗朗兹·
博厄斯坚持语言研究及语言在人类学研究与训练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语言的模式是无意识的,不懂其语言便无法知道其无意识的文化模式.爱华德·
萨皮尔与本杰明·
吴尔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假设,即语言(语法)是个体思维的手段,甚至决定了文化的思维、概念与世界观.参见:
文献[21].,其基本关注点是“语言、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美国人类学传统当中,民族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早在弗朗兹·
博厄斯时代,这种学科间的合作关系就已经形成了[4]。
因此,作为语言人类学的一个发展,“讲述的民族志”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界兴盛起来,自然有它的根源存在。
但是,在此之前,对于语言的研究,语法学家倾向于把语言看作是抽象的、自足的语法结构;
而民族志专家又倾向于从语言中抽象社会生活的程式与结构。
他们都没有把语言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
作为一名美国“语言人类学家”,戴尔·
海姆斯正是在批评与反思民族学与语言学这两门学科的学术史的基础上提出“讲述的民族志”的。
“讲述的民族志”综合了上述两门学科的研究视角,把关注的视点转向“讲述”,即社会生活中语言应用的问题。
具体地说,他是在运用民族志的研究方式拓展语言学的研究思路。
然而,“讲述”是美国语言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对象,因此,“讲述的民族志”,与其说是语言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补充性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语言人类学主要是对那些不识字的文化群体的语言进行描述,也就是说,语言人类学是对“异”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及语言体系进行描述的一门学科。
而“讲述的民族志”主要关注的却是语言的使用问题。
语言人类学家研究语言被组织起来的语法规则;
而“讲述的民族志”关注的是语言的社会应用(或者不被应用)是如何并通过何种文化规则被组织起来的。
传统的语言人类学的另一个基本的关注点是不识字的文化群体的语言中的历史问题,关注初始的语言、语言特征的借用、传播以及地域模式问题;
“讲述的民族志”也关注上述问题,但是,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对讲述者而言必不可少的具体的交流语境,因此,“讲述的民族志”在对“洋泾帮”语言以及“混合语”的研究方面颇有成绩。
近年来,语言人类学关注民族文化科学以及结构语义学,尤其关注诸如亲属关系、颜色分类、疾病分类中的符号特点、符号关系及分类体系的问题,视之为澄清本土文化的类型与分类体系的关键。
“讲述的民族志”同样感兴趣于符号体系、结构及其语言表达,但是,重点关注的仍然是讲述中语言形式的社会应用。
传统的语言人类学习惯于搜集口头艺术形式的文本,尤其是口头叙事的文本,视之为获得分析语言的自然扩展的话语的手段。
以句子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同时考察句子之外的语言学模式,相应地,语言学模式的分析也在叙事结构的分析方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讲述的民族志”最重要的关注点是口头艺术的表演或者社会互动中口头艺术形式的其它交流性应用,重点考察的是讲述的模式与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如何组织了语言的应用。
当然,讲述的模式与功能是有文化特殊性的,又是跨文化地变异的,它们程式化地存在于每一个特定社会中,都可以满足讲述者的需要。
在某些场合,戴尔·
海姆斯又被称为“社会语言学家”,事实上,他曾经编辑过《社会语言学的方向:
交流的民族志》一书②详见:
文献[11].。
那么,“社会语言学”与“讲述的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按照科纳德·
科纳[5]的介绍,“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术语出现于1952年,真正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则是1966年以后的事。
科纳德·
科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社会语言学”直接与威廉姆·
拉波夫有关。
他故意把来自社会学界的学者所做的语言学研究称为“语言的社会学”;
把来自语言人类学界的学者从事的语言学研究,尤其是以戴尔·
海姆斯为代表的语言人类学家们的研究称为“讲述的民族志”;
把支持互动论的学者的研究称为“话语分析”。
在科纳德·
科纳看来,这些研究方法的历史背景不同于“社会语言学”。
在他看来,“社会语言学”起源于“方言地理学”、“历史语言学”以及“双语种或多语种之间接触的研究”,此外,还有来自语言学之外其它学科(比如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刺激与参与。
奇怪的是,科纳德·
科纳恰恰没有谈到人类学,尤其是语言人类学家对于“社会语言学”的贡献,根本没有涉及弗朗兹·
博厄斯、爱华德·
萨皮尔、本杰明·
吴尔芙等人的贡献。
他似乎努力要在“社会语言学”与“语言人类学”之间做出区分。
与科纳德·
科纳不同,戴尔·
海姆斯对于相关术语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提出语言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6]:
1.人类学当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inAnthropology);
2.语言人类学或者语言的人类学或者民族语言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ofLanguage;
Ethnolinguistics)。
前者倾向于研究语言的语法,后者倾向于研究语言在情境当中的应用。
因此,戴尔·
海姆斯认为,“语言人类学”这一术语似乎可以更恰当地概括上述两种研究立场。
此外,许多人倾向于认为,“民族语言学”即是“语言人类学”。
在这一问题上,戴尔·
海姆斯更愿意站在学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问题的立场上来命名学科。
因为无论语言学还是人类学,在关于自身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都趋于变动不定,所以,无论是“民族语言学”还是“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它们的适用性都得依赖于它们在更大的学术语境当中的位置。
在许多专业语境当中,“语言人类学”的命名更恰当,它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相平行。
海姆斯认为,困扰卡尔·
梯特的学科名词应当清理成如下的归属关系:
在这里,“人类学中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语法结构,“语言的人类学”研究的是语言在实际生活当中的讲述。
“语言人类学”这一术语在两个不同层面上被使用。
而“民族语言学”是联系“语言”与“言语”的一个“关系性”的术语。
同理,“语言心理学”与“语言社会学”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归属关系:
事实上,在“语言人类学”、“语言心理学”以及“语言社会学”之间又有交叉,虽然三者都关注“描述的语言学”,但是,只有“语言人类学”关注“历史的语言学”,而且,从实际成绩来看,“语言人类学”要远远超过其它两者。
纵然如此,同样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新兴学科,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在混合交叉地使用着上述三个术语。
二、戴尔·
海姆斯的学术反思
从语言学的历史来看,戴尔·
海姆斯认为,费尔迪南特·
德·
索绪尔与爱德华·
萨皮尔这两位顶级的语言学家似乎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即语文学是一种历时性地研究书面文本的学问,而语言学是一门共时性地研究口头语言的学问;
语言学家把语言视为人类思维的基础,倾向于强调人类思维的集体产物(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等)以及一套相互依赖的功能,他们试图在这些人类思维产物的本源中寻找一致性①在美国,共时的结构语言学始于弗朗兹·
博厄斯,他指导爱德华·
萨皮尔等人研究印第安人的语法.语言在博厄斯的文化观念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使他抛弃了民族中心主义的分析模式.因为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语言体系的“主体间的客体性”.这种观念在所有继承了博厄斯传统的人类学家中非常流行,比如萨皮尔本人就认为语言具有自主性;
他强调语言中的声音模式;
试图把结构的语言模式扩展进其他交流性模式当中;
而且,他试图使结构语言学(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学)的方法论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基础.参见:
文献[22].。
费尔迪南特·
索绪尔与列维-斯特劳斯显然都是沿着这一思路从事研究的。
海姆斯发现,大多数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忘记了B·
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语言学理论,没有充分地关注社会行为的结构与情境,没有把行为与事件的整体作为调查的起点与阐释的框架,从而在行为与事件中寻找统一性。
综合起来看,戴尔·
海姆斯发现当时通行的语言学理论至少具有如下一些缺点:
1.在面对特定的文化事实时,如果不参考语言讲述的背景信息,不参考同一种语言的讲述者中存在的重大差异,共时的语言学理论将会变得没有解释能力。
共时的语言学理论也许可以进行逻辑分析,可以提供一系列实验性的变异,但是它无法考察语言交流行为中具体的、丰富的活动,无法处理个体讲述能力的整体范围、讲述是否恰当以及讲述的功能等问题。
2.共时的语言学理论似乎可以保存它长期以来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界定,但是,语言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这种“界定”最终会变得不合时宜。
3.共时的语言学理论中存在一些概念,比如“本土讲述者”、“流畅的讲述者”、“一种语言”、“一个讲述的社区”,然而,这些术语所意含的讲述行为与讲述情境,都是假设好的而没有被细致地考察过。
这些概念,如果不是共时的语言学理论的一部分,那也一定是基于语言学理论的一种理论(讲述的民族志)的一部分。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它们的考察都是民族语言学的任务,是结构主义民族志与比较人类学关注的对象。
海姆斯认为:
“没有结构的功能是盲目的,没有功能的结构是贫乏的;
功能与结构相互需要对方,民族语言学理论既需要功能研究,也需要结构研究。
”[7]换言之,“语言人类学”需要“讲述的民族志”。
反之亦然。
海姆斯有意识地强调说,“讲述的民族志”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不是“社会语言学”。
他并不是要发明一门新的学科,而是要在现存的学科体系中发展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
他所谓的“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要为充分地理解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奠定基础。
通俗地说,把“语言”与“社会生活”关联起来的就是“讲述”活动,可惜的是,在“语言”研究的历史上,对于“讲述”的研究几乎被忽略掉了。
如上所述,关于“讲述”的研究主要涉及两门学科,一门是语言学,一门是人类学。
传统上,语言学主要研究的是语言的“语法”,而很少会去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讲述”行为,更不会去研究讲述活动中指导参与者讲述的规则;
人类学以及其它相关社会科学又只关注“讲述”的内容,却从不关注“讲述”的方式。
换句话说,语言学家从讲述的内容当中抽象出“形式”来,而人类学家却从讲述的形式中概括出“内容”来,可某些重要的信息恰恰是从极端关注“语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论之间遗漏掉了。
二者都没有解释语言在当代世界中的实际功能。
既然正如语言学家诺姆·
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学的目标是解释语言应用中创造性的方面”,那么,语言学的研究就不是仅仅考察语法,而且还需要考察这种语法被恰当使用的场景以及支配语法与场景的更高层面的规则;
既然大部分人类学家都赞同沃德·
古德纳弗的说法,“民族志的目标是描述在一个社区中恰当地行为所必须了解的内容”,那么,就需要“讲述的民族志”——对于语言使用的描述与解释——作为一切研究活动的基础[8]。
然而,现代语言学家一直轻视语言的应用。
从费尔迪南特·
索绪尔开始,他虽然区分了“语言”与“言语”两个基本概念,但是,语言学家不假反思地认定“语言”才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除了像爱德华·
萨皮尔、罗曼·
雅科布森等少数语言学家之外,很少有人关注“言语”的研究。
唯一例外的是诺姆·
乔姆斯基,他用“能力”与“表演”来取代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在他看来,“能力”指的是讲述主体具备的知识,尤其是指“语法知识”;
而“表演”则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的是语法之外的所有知识以及语言使用当中的所有能力,另一方面指的是“纯粹的”表演,或者说“纯粹的”行为①转引自:
文献[13].。
表面上看起来,“能力”与“表演”研究的是人的能力与行为,不再是从人的行为当中抽取出来的研究对象。
可事实上,诺姆·
乔姆斯基的理论推进工作仍然是表面的。
语言学家研究的仍然是作为理想法则的语法、语义的逻辑特征,对于讲述行为的可接受性的判断完全依赖直觉,而不是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应用。
对于不同讲述的解释最终被归结到语言的基本结构中共同的、潜在的起源,或者人类头脑中某种深层的起源。
语言学家根本无视语言讲述情境中语法的、语义的、语音的社会特性。
没有人关注特定讲述方式的情境及潜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总之,语言学极少关注“讲述行为与讲述事件”。
传统上,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把“讲述”(或者“话语”)视为隐匿不现的、透明的玻璃,透过它,研究者可以看到话语的现实、社会关系、生态实践、信仰体系,但是玻璃本身——话语及其结构,透过这一媒介,知识(语言与文化)被社会成员和研究者生产、想像、传承与获得——却很少受到关注。
事实上,“语言-社会-文化-个人”都是话语创造性实践的资源。
在“讲述的民族志”中,讲述是语言应用最广泛、最具有包容性的层面。
在这个意义上,讲述或者话语建构的过程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核心。
在人类学与语言学领域,“讲述的民族志”是一种理论的立场,也具有方法论的意涵,既然讲述是一种体现,一种过滤,一种文化创造、再创造以及传播的方式,那么,人类学家就必须研究讲述的真实形式如何被社会与个人所生产与表演[9]。
三、“讲述的民族志”:
走向描述的理论
既然语言是按照两种基本功能——“所指的”与“风格的”——被组织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与意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焦点。
一方面,他们仍然关注语义的、指称的内容,另一方面更关注讲述的“风格”。
由此看来,充分地理解语言讲述的手段,即是去理解两种相互依赖的基本功能:
所指的功能与风格的功能②参见:
文献[23].戴尔·
海姆斯进一步把风格的功能分析划分为两种类型:
即结构的功能与使用的功能;
前者指的是语言特征及其组织模式;
后者指的是在特定语境中语言元素的应用.参见:
文献[24].。
作为“讲述的民族志”的主要倡导者,戴尔·
海姆斯在借鉴罗曼·
雅科布森语言分析模式[10]的基础上,把其中“情境的功能”一分为二,分成“参考的功能”与“场景的功能”两个层面,提出了“讲述的民族志”的分析框架。
海姆斯认为,“讲述的民族志”关注语言的是讲述的“语境与应用”,考察讲述的模式与功能需要细致的田野作业。
他引述J·
L·
奥斯汀的话说,“在整个讲述情境中,整体的讲述行为是唯一真正的现象,这是我们最后要澄清的地方”③转引自:
文献[25].。
后来,戴尔·
海姆斯又对这一“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进行了修订,更加关注与强调描述语言讲述与社会生活之间互动模式的问题。
总结起来看,“讲述的民族志”至少有如下几个核心关注点:
(一)讲述的手段
弄清楚讲述行为中社会成员可资利用的资源的复杂体系是“讲述的民族志”的核心关注点之一。
同一种文化对应于同一个社会、同一套单一的语言模式的观念被抛弃了,在情境化的话语活动中,不同的话语资源被投入应用。
语言资源、口头类型、语言行为以及解释/框架是“讲述”据以成形的手段。
语言学家习惯于以抽象的形式术语来描述它们,但是“讲述的民族志”更感兴趣于描述具体的语言讲述活动。
1.语言资源
这一概念直接反对“同一种文化对应于同一个社会、同一套单一的语言模式”的假说。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在更大的语言体系中,它们都具有各自的社会意义与功能。
民族志专家关注的是异质的语言资源被整合的方式。
2.口头类型
作为特定文化中习惯化的讲述类型,口头类型可以被应用于话语的建构。
“讲述的民族志”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具有文化特殊性的类型形式及体系,考察特定社区的成员是如何应用口头类型来组织讲述的。
3.语言行为
在特定的讲述社区中,社会成员可能是按照语言行为而不是口头类型来指称讲述活动的,事实上,行为与类型只是一种分析性的区分,即讲述行为以及讲述行为的产物之间的区分。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一个语言行为即是一个言说,一种用语言做事情的方式,这是对于J·
奥斯汀在《如何用语言做事》中所表达思想的转述。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语言社区的讲述行为构成了讲述的活动的手段——它们表征了用语言做事的习惯性方式,用业已组织好的建构性材料建构话语。
4.解释/框架
“框架”的概念来自社会学家乔治·
贝特森,戴尔·
海姆斯称之为“解释”,它是一种交流性的策略,标志着一种阐释性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一个信息得以被理解,换言之,它是一套分辨信息之间秩序的阐释性指导。
框架即是特定文化中习惯化的“元交流”。
作为讲述的手段,这种“元交流”内在于语言行为中,是讲述的建构性材料之一。
(二)社会角色与交流性能力
考察讲述者本人及其社会角色与讲述相关的方面是“讲述的民族志”的又一个关注点。
这里考察的不只是角色的界定问题,而且包括角色的动态性。
“讲述的民族志”关键在于揭示讲述在社会与文化生活中分布的多种方式。
(三)讲述事件
讲述行为发生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行为的工具。
在讲述事件中,讲述者与讲述手段结合在一起。
从一开始,讲述事件的分析就是“讲述的民族志”的核心,在经验性语境当中,讲述活动发生并获得意义。
罗曼·
雅科布森提供的初始模型就是一个讲述事件的模式。
他从讲述事件出发,阐明了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从任何一个构成要素出发都可以进入事件本身。
海姆斯进一步区分了“讲述的事件”与“讲述的场景”,认为前者是按照讲述的规则描述出来的一个情景;
后者则是讲述发生于其中的一个语境,但它是按另外一套活动秩序组织起来的。
与人类学的其他分支一样,“讲述的民族志”也感兴趣于描述文化生活,尤其关注“讲述的事件”及与讲述相关的其它结构的独特性及呈现中的特征。
一个基本的分析性前提是:
所有的讲述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既要欣赏其独特性,又要欣赏其共同的整体的结构。
呈现中的结构研究关注的是讲述事件的三个方面,即事件本身、文本以及社会结构。
文本的民族志研究在表演当中呈现,分析传统的讲述手段、个体讲述者的能力以及特定场景之间互动性的动力学可以理解民俗文本的独特性。
(四)讲述的社区
关注向谁习得讲述、由谁使用以及向谁讲述,即是在关注讲述行为的社会单元。
无论这些社会单元是什么,“讲述的民族志”都倾向于把它们构想成“不同的”的组织。
讲述的资源与能力有差别地分布于社会成员中间。
80年代中期,戴尔·
海姆斯把描述“语言与社会生活互动的模型”进一步细致化,传统的三分法(讲述者-讲述的内容-听众)被十六分法代替,他把这16种因素归纳为“SPEAKING”[11]35-71这一术语,其中8个字母分别对应着8个单词的首字母。
1.背景(Setting)
又分背景(讲述行为的时间与空间,指的是物理环境)和场境(区别于背景,专指心理背景,或者是作为某种类型的场景的一个情境化的文化界定。
讲述行为常常被用来界定场景,常常被关联于场景来判断其合适与否)。
背景与场景本身也相互关联,用以判断讲述行为是否合适。
二者被视为行为情境的构成要素。
2.参与者(Participants)
又分讲述者或发送者、发件人、听众或接收人和收件人。
不同群体对讲述事件中参与者的定义不同,尤其是在界定参与者、缺席者是否在场上的问题上观念不同,上述多种构成要素被总称为参与者。
3.结果(Ends)
又分目标结果(惯例化地认为的预期的结果)和目标意图(参与者的意图也是千差万别的。
从社区的立场出发,一个事件的目标不一定与参与者的目标一致。
参与者的策略是讲述事件的一个本质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无论是结果还是意图,传统赋予的预期的需要与纯粹个人的需要应该区别开来。
也要与潜在的未曾预期的需要区别开来,描述习惯的文化地恰当的行为与千差万别的个体行为同样重要,前者是理解后者的先决条件,二者不容混淆。
4.行为序列(Actsequences)
又分信息的形式[这是最基本的问题,“如何说”是“说什么”的一部分,虽然人们常忽略它。
表达的手段情境化、控制着表达的内容,掌握讲述的方式是个体表达的前提条件。
这就需要关注那些艺术化的类型、日常生活中的惯例、信息的形式的分析(怎么说)可以揭示艺术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和信息的内容(主题及主题的变奏,人们维持主题或者变化主题,这是他们交流能力的一部分,对于话语连贯性的研究尤其重要)。
这两个方面是讲述行为的核心,也是“语法结构”的焦点,二者相互依存,成为“行为序列”的构成要素。
5.基调(Keys)
指行为呈现的风格、方式或者精神风貌。
大略对应于语法类型当中的形态。
背景、参与者及信息形式可能相同的情况下,基调可以完全不同,比如“嘲弄,严肃或者敷衍了事,勤恳细致”等等。
基调习惯上被赋予某些场合,参与者、行为、符码或者类型,也存在着对于变化性基调的习惯化理解。
基调与个体行为的公开的内容相冲突时,它常常会使后者不起作用,基调的信号可以是非语言的,这些特点常被定义为“表达性的”或者“风格性的”,与表演者的情感无关,它们被使用于特定的社会情境当中。
6.工具(Instumentalisties)
又分信道(口头的、书面的、电子的、旗语的等等或者其他媒介,描述的两个重要目标在于记录互动中信道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相互的等级关系)和讲述的形式[一个主要的理论与经验问题是区别一个社区当中的口头资源,语言被组合为多种讲述的形式,目前有三种标准需要认识到:
语言资源的历史起源(语言/方言);
相互理解的存在与缺失(符码);
应用当中的特殊化(变异与语域)]。
信道与讲述的形式都是讲述的手段,都是符码与工具。
7.规则(Norms)
又分互动中规则(与讲述相关的特殊的行为与特征,人们一定不能打破的规则或自由地应用的规则,它涉及到社区当中社会结构的分析)和阐释的规则(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对于行为的阐释规律不同,它涉及到社区的信仰体系)。
哈罗德·
加芬克尔研究的“为特定的目的”的阐释过程也属于这一类型。
8.口头类型(Generes)
包括“诗、神话、故事、谚语、谜语、祈求语、宣誓词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讲述的民族志”对行为中讲述的分析即是对“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