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快乐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九十年代中国小说Word文档格式.docx
《文本的快乐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九十年代中国小说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本的快乐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九十年代中国小说Word文档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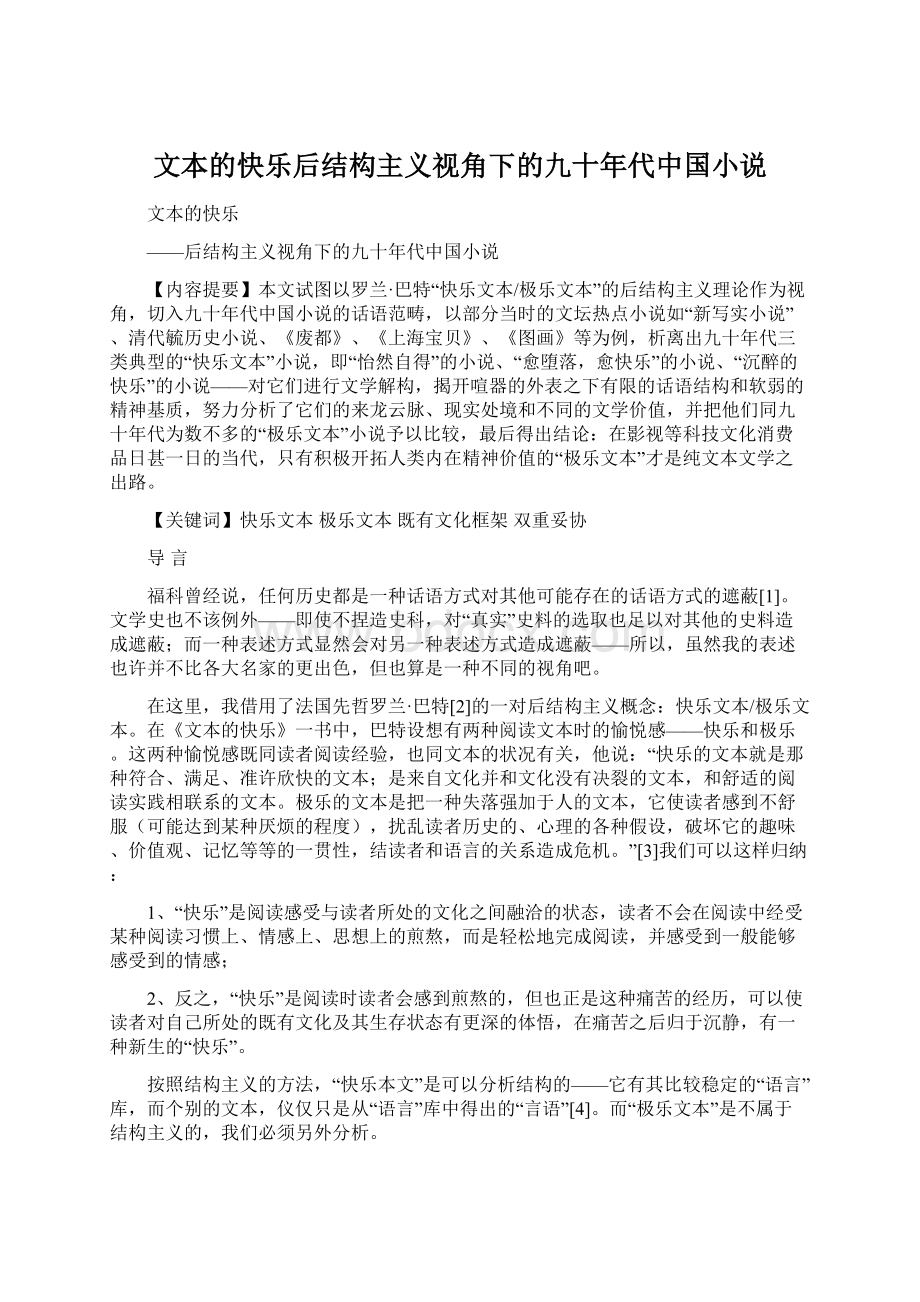
在这里,我借用了法国先哲罗兰·
巴特[2]的一对后结构主义概念:
快乐文本/极乐文本。
在《文本的快乐》一书中,巴特设想有两种阅读文本时的愉悦感——快乐和极乐。
这两种愉悦感既同读者阅读经验,也同文本的状况有关,他说:
“快乐的文本就是那种符合、满足、准许欣快的文本;
是来自文化并和文化没有决裂的文本,和舒适的阅读实践相联系的文本。
极乐的文本是把一种失落强加于人的文本,它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可能达到某种厌烦的程度),扰乱读者历史的、心理的各种假设,破坏它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等等的一贯性,结读者和语言的关系造成危机。
”[3]我们可以这样归纳:
1、“快乐”是阅读感受与读者所处的文化之间融洽的状态,读者不会在阅读中经受某种阅读习惯上、情感上、思想上的煎熬,而是轻松地完成阅读,并感受到一般能够感受到的情感;
2、反之,“快乐”是阅读时读者会感到煎熬的,但也正是这种痛苦的经历,可以使读者对自己所处的既有文化及其生存状态有更深的体悟,在痛苦之后归于沉静,有一种新生的“快乐”。
按照结构主义的方法,“快乐本文”是可以分析结构的——它有其比较稳定的“语言”库,而个别的文本,仪仅只是从“语言”库中得出的“言语”[4]。
而“极乐文本”是不属于结构主义的,我们必须另外分析。
如果把这个理论放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特定环境中来,试着找寻“言语”之下的“语言”,会在前台美丽的风景背后,浮现文坛故事的若干基本道具。
因为,九十年代正是一个盛产“快乐文本”的时代。
在全民族的激越的高潮过去之后,会有一些真正的思想者坚守思想的苦痛,但也会有更多曾经激越满怀的知识分子转向对既有文化框架的妥协。
为了论说的方便,我选取九十年代小说作为本文视角的焦点。
一、怡然自得的“快乐”
以武汉作家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崛起,到九十年代,正是如日中天,成为所谓“严肃文学”中小说文体的主流派别。
特别是池莉,创作热情非常之高,《小姐你早》、《来来往往》、《口红》等长篇相继问世,而且都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一时间成为文坛的红人。
但正是这一派,在九十年代带动了严肃小说的全面“快乐”化。
池莉的小说,是此种文学现象的活标本。
比方说,她的一个小说叫做《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从表面上看,这篇小说(从题目到内容)说的是主人公猫子、燕华等人对物质条件的妥协与容忍,但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的人,物质也是社会的物质,怎么能不包括精神上的妥协与容忍呢?
这里的精神上的容忍,绝不是六、七十年代那种简单的政治媚俗,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媚俗。
而这种媚俗包括两个层面:
1.以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向不公正的物质和精神待遇妥协;
2.以作者的身份,向存在于民间的这种妥协而妥协。
即使单就第一个层面来说,也绝不是“生活原生形态”,因为生活中有消极妥协的,也有为理想而进取、抗争的.作家可以这样取材,也可以那样取材,取材的标准,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利益,但偏偏给自己贴上“原生形态”的金纸,未免有些霸道。
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李俊国先生就曾经尖锐指出:
池莉不如鲁迅等伟大作家,在于她站得太矮,矮到与自己创造的人物站在一起。
不过这句话未免把池莉想得太傻,作为一个本领相当高强的作家,她自己不会一点都认识不到,她如此行文完全是作家意识的主体选择。
从外表上看来,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和八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从文学实验或者思想进发的风潮,回归到传统而更为细致、生活化的现实主义上来。
但如果认真探究内在的气息,就会发现实际上新写实小说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蜕变。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新写实小说的阵营中,还有许多作品,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叶兆言的《艳歌》、方方的《风景》,在“消解激情”的冷静叙事中,隐约闪烁着一种讽刺精神:
所有这些琐碎的小事,就构成了生活:
生活就的这样,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正如陈思和先生指出的,“这样一种建立在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的软弱上的讽刺是无法持久的”[5]——讽刺必将向默认转化,再从默认到认同,从认同到委身下嫁。
所以才有池莉在九十年代的走红——她在八十年代写的《烦恼人生》等作品还无法同刘震云等人的冷叙事相提并论,但九十年代以后,却迅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切合点:
生活就的这样,大家也就这么过吧。
在池莉的小说、特别是九十年代的小说中,人物的出场、说话、甚至思想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
所有的人生故事似乎都只是文艺家所总结的人生规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论断性的句子:
这种没有危险只是把关系变得更复杂的情形是最好的爱情佐料;
签单与爱情最匹配:
可是人有时候就是无可救药,道理是懂的,无耻的事情也还是忍不住要做的……
在这样简简单单的句子中,省却了作家、人物和读者的无数辛劳,免却了描写、表现和自省,图得故事的顺溜、理解的简便。
就像所有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的民间故事一样,它并不打算有什么作为,它只是告诉你一些经过改装的“别人的生活”,让你多少叹一口气,放下心来——原来别人也并不比我好到那里去——然后像康伟业一样,“站起来,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回到了他日常的忙碌的生活中”(《来来往往》中篇小说版结尾)。
所以,以池莉为代表的九十年代“新写实小说”,是与既有文化框架相融合的文学,因而是“快乐的文本”——用最流利、直接的叙事,述说大家很容易接受的故事,摈弃文学的敏感的内省、尖锐的介入(对作者、书中人物、读者都省事)——哪怕有一点讽刺、哀怨或者彷徨,也是我们所司空见惯的那种讽刺、哀怨和彷徨,没有什么需要多想的,看完了,也就可以合上书,继续在“大家也就这么过”的生活中沉浮。
除了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如此令人快乐的小说还有一些,比如《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一系列历史小说,《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一系列移民小说。
如果我们冷下眼睛,会发现,历史小说里的皇帝总是那么忧国忧民、鞠躬尽瘁;
移民小说里的外国常常也含着亲切与温情。
总之,我们想看到什么,总会有些什么——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
至少,也会超出太远。
新写实小说,等等,这一类小说,是恰然自得的“快乐”。
怡然自得的秘诀在于:
既同既有文化框架相妥协,又同它保持一定的距
离。
既让我们在小说中得到若干的(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又不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太远。
——“极乐文本’’也会让我们感到满足,但往往是我们本身所未有想到过或很少想到的满足。
总之,既要投合我们,又不要搞得太过火,让我们一望而知是假的。
就像陪领导打牌一样。
作者、读者都怡然自得,与我们的文化共生。
二、愈堕落,愈“快乐”
和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也有许多“前卫”或称“先锋”的小说’风格各异,但其精神基质是一样的软弱。
在精神基质在软弱背景下,方法上的所谓创新往往显得脆弱无力。
比如新潮女性小说,先有广东的缪永等人,后有上海蜚声一时的卫慧等人,写作了《欲望号街车》、《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上海宝贝》、《糖》等一系列紧跟南方发达都市之时代脉搏的小说,但是,哪怕她们在叙事上突破了传统意识,故意制造出一种。
“分裂”的感觉,但软弱的精神基质仍然无法使之从分裂中升华和自救。
从一个方面来说。
继八十年代王安忆以《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一系列大胆描写性爱的小说震动中国文坛后,九十年代又有不少人企图从这方面突破。
其中当然有优秀的作品,但也不乏糟糕之作——故意的张扬和故意的压抑一样是装神弄鬼;
名为背叛,但这样的背叛,来得多么轻松,一方面可以博得“叛逆者”之名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与自己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阴暗心理相安无事,又谈何背叛?
假的背叛,真的软弱。
这其中的代表就是《废都》和《上海宝贝》,两部争议很大的小说。
在批判《废都》和《上海宝贝》的文章里,很少有能真正戳到其痛处的。
他们所大批特批的性描写,也许正在作家引以为得意的地方,所以更加认识不到自己作品的关键点所在,这样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作品的缺点越来越严重,批评却越来越不得要点。
《废都》从《浮躁》一脉相传,但是在对自我的颠覆之后,在囚笼中丧失了自己灵魂的所在,这是一个灵魂没有归宿的《废都》,活在废都里的人都如作者一样,不知道自己从那里来,也不知道自己从那里去。
作者借书中人物周敏之口吐出了自己心中的郁结:
“我走遍东西,
寻访了所有的人,
我寻遍了每一个地方,
可是到处不能安顿我的灵魂。
”
整部《废都》,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两只手在拼命地抓,抓任何可能拯救自己的东西——有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有昆德拉式的哲理现实主义,有中国的老庄哲学和禅、道、神秘主义,有《红楼梦》式的“色”、“空”情幻主义,但归根到底还是救不了自己,并且几乎沦落到《金瓶梅》式的市侩主义和色情主义——只是多带了些文人色彩而已。
且看:
1.庄之蝶的个人主义:
既没有封建文人为国(皇帝)分忧的精神,也没有红色知识分子解放全人类的豪情,也没有“资本主义”作家的人权、民主等等观念。
人大代表会会场外请愿的百姓的惨状,庄之蝶看也似乎没有看见。
此时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唐宛儿。
2.庄之蝶的色情主义:
小说中对性爱的追寻,也并非什么纯粹的爱情。
举一个例子:
庄之蝶对唐宛儿的脚的迷恋,甚至要“长啸”,只能说是封建文人的阴暗心理和变态情调。
3.庄之蝶的市侩主义:
一到关键时候,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名声。
农药厂的假药事件.庄之蝶只关心自己曾经给他们写过宣传文章,会受到牵连,就不惜继续隐瞒事实,牺牲农民的利益——可笑,在刚刚听说农药有假的时候,他还想到过受坑害的农民!
当然,他也常常想到自己作为作家“应该”有的清高,可是一到“危急”关头,这“清高”马上廉价换了小人的种种手段。
《废都》所迷失的不仅仅是理想,而且是生活的热量和文学的热情。
反映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走失“救世”的理想之后,继续连自己也走火了的心境。
但这走失,当然不是释迦牟尼的走火,物极必反在这里并不灵验——走失之后不是精神的全面超脱,而是向肉体的彻底投降,退步到最凡俗的生存状态。
而且更可怕的是,作者本人也很大程度上沉浸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无法摆脱出来。
从而形成了快乐文本典型的“双重妥协”。
而《上海宝贝》呢?
在言语的能指层上,有一种破碎、撕裂的企图,但往往落入情节上“快乐文本”结构的圈套。
在所指层上,试图传达出某种心灵的震颤,可是到了关键地方,往往不能直面自己的心灵,转而求助于“快乐文本”既有的文化模式。
比如在情感的归属与纠葛中,就把天天设计成一个没有性能力的角色,而把马克设计成一个性能力极强的角色,舒舒服服地一头栽进“肉体/精神”这一能够被作者、人物和读者轻松接受的心理防线。
原本似乎想要有所开拓的卫慧一下子又跌进“快乐文本”屡试不爽的陈陋“结构”中来。
像这样的硬伤,在《上海宝贝》中比比皆是,使得小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