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Word格式.docx
《《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Word格式.docx(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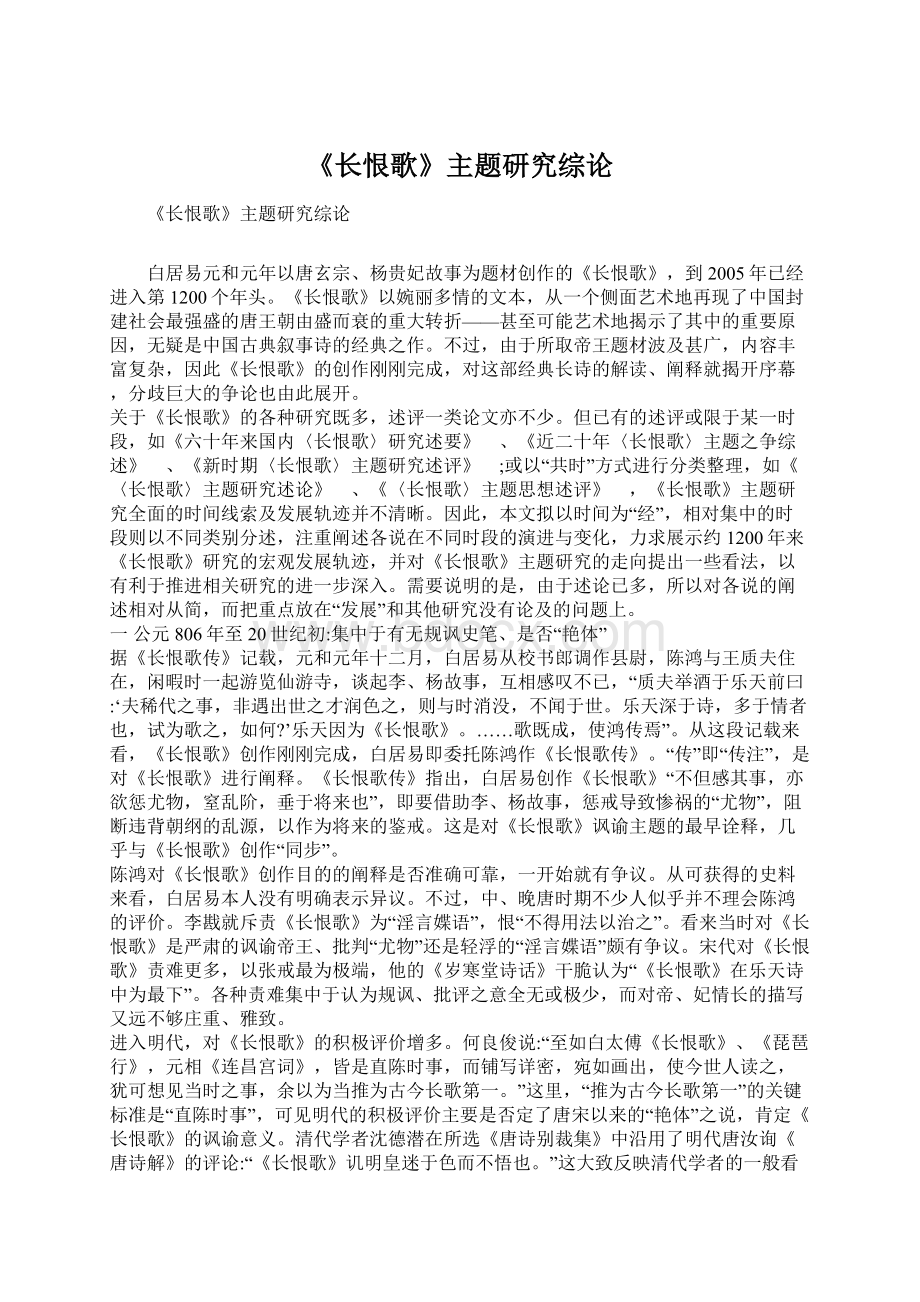
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
‘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
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
’乐天因为《长恨歌》。
……歌既成,使鸿传焉”。
从这段记载来看,《长恨歌》创作刚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
“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
《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
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目的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一开始就有争议。
从可获得的史料来看,白居易本人没有明确表示异议。
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的评价。
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媟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
看来当时对《长恨歌》是严肃的讽谕帝王、批判“尤物”还是轻浮的“淫言媟语”颇有争议。
宋代对《长恨歌》责难更多,以张戒最为极端,他的《岁寒堂诗话》干脆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
各种责难集中于认为规讽、批评之意全无或极少,而对帝、妃情长的描写又远不够庄重、雅致。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
何良俊说: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
”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了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肯定《长恨歌》的讽谕意义。
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
“《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
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
因此清代基本上稳定了明代以来对《长恨歌》讽谕意义的肯定。
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
二20世纪50年代前后:
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 ,由于大多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尽管后来不乏响应者,但仅属于大胆假设或想象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
4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 ,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 。
《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
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谕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
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
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
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
……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
” 不过,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
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
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 。
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
由于讽谕、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谕、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
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
“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 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 。
三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
多向延伸,新论叠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
首先,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
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谕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单纯的讽谕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长恨歌》通过“净化”等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特殊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 ,对典型爱情说作了精微的发挥,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说的代表性阐释。
此外,在“帝王爱情说”、“典型爱情说”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寄托说”及“爱情品格说”。
“作者寄托说”认为白居易借帝王之事,写一己之情。
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在徐州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深厚,为礼教所限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自己的“长恨”。
丁毅、文超作了进一步发挥 。
极端的作者寄托说进一步向“湘灵”倾斜,全面淡化李、杨关系,代之以白居易与湘灵的恋爱经历,“《长恨歌》哭为湘灵” ,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长恨歌》似乎可称《湘灵歌》了。
不过,尽管存在偏颇,寄托说从作者心理内部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探索文艺创作的规律。
“爱情品格说”则认为诗人批评唐玄宗宠妃行乐而误朝,目的是为了说明唐玄宗爱情的社会品格不高,必须把爱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与以前爱情说有所不同。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谕说发展的基本趋势;
关于唐玄宗的悼念、方士觅魂,即一般所指的后半部分,认为突出了“无比的痛苦,意义很为深刻”,“是更为深入一层地鞭挞这个悲剧角色的灵魂”,最后“写出唐玄宗永远也饮不尽他自己所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题从而也就得以彻底完成” 。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多少有些重情轻理相比较,《唐代文学史》的相关论述沉稳而多理性分析。
此外,在传统惩戒说及50年代的暴露、批判说基础上,提出了“揭露阴谋说”、“解剖制度说”。
“揭露阴谋说”认为,《长恨歌》以国史实录和未入史的史料为素材,写宠爱、赐死、唐玄宗自杀三部曲,采用的方法与“隐事说”近似,也是搜求《长恨歌》背后的隐秘“事件” 。
“解剖制度说”认为,《长恨歌》把探寻的触角伸到封建君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内部,揭示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 ,带有新的极端化倾向。
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
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
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
“《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 。
在爱情、讽谕、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应摈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
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
金学智先生认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串起了追怆感伤的正主题和追念盛世、讽谕规正的副主题 ,也包含多重主题。
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的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 与“矛盾主题说” ,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谕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
黄永年先生以大量篇幅考证《长恨歌》描写的真实性问题,判断有违史实甚多,但并不深究白居易进行创造的目的,认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则说不上什么”。
刘维治先生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时代不同,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基本上不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主题或主要思想倾向 。
80年代前后至今的多向延伸把《长恨歌》研究推向深入,也使《长恨歌》主题的争论更加纷繁歧异,迷雾重重。
四白居易对《长恨歌》主旨的自述及归类研究
元和十年,即《长很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持爱情说者一般认为:
“作者自述主旨如此,当不容置疑。
” 持讽谕说者则认为“长恨”与“秦吟”并举,属于互文,恰恰表明《长恨歌》与“秦吟”等讽谕诗一样表达讽谕主题 。
基本上各执一端。
要破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只有详考“风情”在汉唐时代的涵义。
从白居易“风情”、“正声”对应的表述来看,“风情”指《诗经》“风诗之情”没有问题。
现在认为,所谓风诗其实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
但经秦火之后,“诗三百”在汉代始立为经,汉儒开始不遗余力搜求所谓“微言大义”,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风诗的政治作用被明显夸大,“风”也逐渐被赋予婉转以“讽”的含义。
从孔颖达的疏证来看,唐代不但接受,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汉儒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