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过藻溪.docx
《雁过藻溪.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雁过藻溪.docx(4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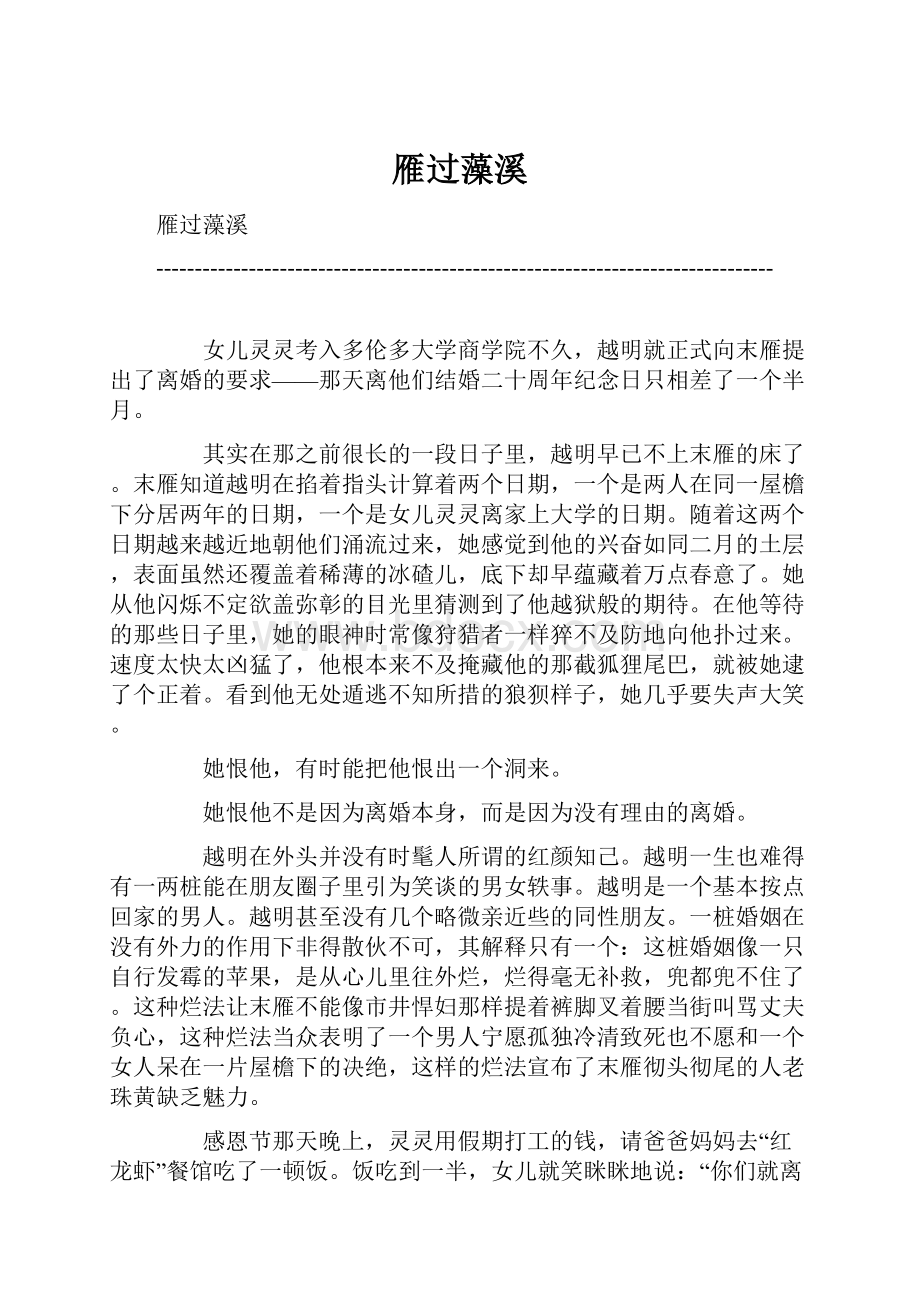
雁过藻溪
雁过藻溪
--------------------------------------------------------------------------------
女儿灵灵考入多伦多大学商学院不久,越明就正式向末雁提出了离婚的要求——那天离他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只相差了一个半月。
其实在那之前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越明早已不上末雁的床了。
末雁知道越明在掐着指头计算着两个日期,一个是两人在同一屋檐下分居两年的日期,一个是女儿灵灵离家上大学的日期。
随着这两个日期越来越近地朝他们涌流过来,她感觉到他的兴奋如同二月的土层,表面虽然还覆盖着稀薄的冰碴儿,底下却早蕴藏着万点春意了。
她从他闪烁不定欲盖弥彰的目光里猜测到了他越狱般的期待。
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她的眼神时常像狩猎者一样猝不及防地向他扑过来。
速度太快太凶猛了,他根本来不及掩藏他的那截狐狸尾巴,就被她逮了个正着。
看到他无处遁逃不知所措的狼狈样子,她几乎要失声大笑。
她恨他,有时能把他恨出一个洞来。
她恨他不是因为离婚本身,而是因为没有理由的离婚。
越明在外头并没有时髦人所谓的红颜知己。
越明一生也难得有一两桩能在朋友圈子里引为笑谈的男女轶事。
越明是一个基本按点回家的男人。
越明甚至没有几个略微亲近些的同性朋友。
一桩婚姻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非得散伙不可,其解释只有一个:
这桩婚姻像一只自行发霉的苹果,是从心儿里往外烂,烂得毫无补救,兜都兜不住了。
这种烂法让末雁不能像市井悍妇那样提着裤脚叉着腰当街叫骂丈夫负心,这种烂法当众表明了一个男人宁愿孤独冷清致死也不愿和一个女人呆在一片屋檐下的决绝,这样的烂法宣布了末雁彻头彻尾的人老珠黄缺乏魅力。
感恩节那天晚上,灵灵用假期打工的钱,请爸爸妈妈去“红龙虾”餐馆吃了一顿饭。
饭吃到一半,女儿就笑眯眯地说:
“你们就离了吧,我没事的。
只是以后要搬得越远越好。
最好妈妈还住多伦多,爸爸搬到温哥华。
这样我就可以在多伦多过夏天,在温哥华过冬天了。
要是你们再结婚就更好了,我一下子能有两副爸爸妈妈了。
”
末雁和越明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只觉得在加拿大长大的女儿,和国内那些同龄女孩子相比,似乎是太成熟了,又似乎是太憨嫩了——倒是放下了心。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了律师去办。
几年里存下的退休金,两人各拿了自己名下的那一份。
车子也是一人一辆。
只有房子略微麻烦一些,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前后其实也就花了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卖出去了——净赚了四万加币。
卖房所得的钱,在银行和律师手里走过了一圈,就一分为二地归入了各自的账户。
灵灵有全额奖学金,剩下的开销,半年跟爸住,半年跟妈住。
跟爸住时由爸负担,跟妈住时由妈负担。
没有子女监护权的混战,也没有赡养费的纠纷,事情就很是简单明了。
搬家的那一天,越明替末雁雇了搬家公司。
大件家具,都给了末雁,剩下的无非是一些日用物件,越明也都尽量让末雁先挑。
客气谦让的样子,仿佛不过是送末雁出一阵子差而已。
前来帮忙的朋友见了,忍不住问末雁:
“那吵翻了天的都没离,你们离什么呢?
”末雁忍无可忍,终于将保持到最后的一抹淑女形象像蚊子似的捻灭了,随手抓起一个花瓶,朝着越明的汽车砸去。
“好你个李越明,天底下的好人,都让你做完了!
我就成全你吧!
”众人哪里拦得住?
车尾早砸出一个弯月形的坑来。
越明不说话,只蹲下身来,捡地上的花瓶碎片。
一片一片的看得末雁很是无趣,想说句什么话,搜肠刮肚,终无所得,只好讪讪地坐进了搬家公司的车。
车开出去,看见自家那幢红砖房子在反光镜里越变越小,变成了一个小红点,最后消失在一片混杂的街景里头,心想这些年里听了好多关于离婚的恐怖故事,大概居多是夸大其词的。
十几年里经营起来的家,拆起来,其实远没有想象的那样麻烦。
搬进单身公寓的当晚,末雁就梦见了母亲。
“小改,小改。
”
母亲在窗外轻轻地叫她。
她出生在一九五二年,母亲怀她的时候,正赶上土改,所以就给她取名叫“土改”——末雁是她上大学以后改的名字。
末雁站起来,推开窗,一眼就看见母亲站在窗前的那棵大枫树底下。
月色黄黄的,照得枫树叶子一团团一簇簇的,仿佛是一只只愤怒的拳头。
母亲走了很远的路,鞋面上有土,脸上有汗,两手在灰布衬衫的袖子里不停地蠕动,嘴唇抖抖的,半晌才扯出两个字来,是“藻溪”。
末雁正想问藻溪怎么了,母亲突然低了头,转身就走。
脚步窸窸窣窣的,走得飞快,末雁追了三条街也没追上,却把自己追醒了——方知是南柯一梦。
双手捂着胸,心跳得一屋都听得见。
急急地站起来,打开窗,窗外果真是一棵蔫蔫的枫树,树影里漏下来的,果真一片黄不黄白不白的月光——却是无人。
便知道是母亲催她回家了。
末雁的母亲黄信月,是浙南藻溪乡人。
那个名字听起来有几分诗意的小乡镇,在几十年前却只是一个纯粹的乡下地方。
黄信月是在土改那年离开藻溪,来到温州城里,经人介绍与末雁的父亲结了婚,从此就住在温州城里,再未回过藻溪老家。
末雁的父亲宋达文,是大名鼎鼎的三五支队刘英手下的干将,解放后做过第一任温州地委组织部部长,后来又升任了地委副书记。
在温州那么个小地方,也就算是个大官了。
母亲很少提起藻溪。
末雁对藻溪的模糊印象,似乎是和那些偶尔来城里找母亲的乡党有关。
末雁依稀记得那些衣着寒酸皮肤粗糙的乡下人在暮色的掩盖下敲响她家后门的情形——他们从来不敢从前门进屋。
他们敲门的声音是怯怯的,两脚在门前的草垫上来回交替着蹭了又蹭,仿佛要把脚掌连同鞋底的泥土一起蹭落。
他们把装着土产的竹篮子放在门里,如果母亲没有说话,他们就会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仿佛他们的心,也随着篮子落到了可以依托的实处。
他们和母亲交谈的时候,把原本口音浓重节奏极快的方言,小心翼翼地嚼碎了,轻轻地压在喉咙和舌头之间的空隙里,听上去似乎含了一嘴的棉絮。
其实,把这叫做交谈真是一种夸张,因为母亲几乎完全不说话,母亲似乎也没有认真在听,母亲只是面无表情地倚门站着。
这样的姿势通常只维持几分钟,乡下人便知趣告别了。
他们走后,屋里还会长时间地充溢着腊肉鱼鲞和劣质纸烟交织起来的复杂气息。
这种气息如烟如气在家具和家具门和门窗和窗之间的缝隙里暧昧地飘来飘去,母亲的脸色,在这样的气味里也有些阴晴不定起来。
这些乡下来的人是到城里看病的,找工作的,办事的。
找母亲当然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不言而喻是找父亲。
母亲是一扇门,父亲才是门里的景致。
门虽然不是景致,但景致却必须要经过门的。
在末雁的记忆中,作为门的母亲是沉默而高深莫测的,而作为景致的父亲反而是一览无余温和容忍的。
只是父亲在8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入葬在城里的老干部公墓。
从那以后,来找母亲的乡党就渐渐地少了起来。
母亲做了多年的小学教员,才提升到教务主任的位置上,临退休也不过是一所普通小学的校长。
身体一直硬朗。
三个星期前洗澡时突然跌倒,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当时末雁正和一群京都协议项目的科学家在北极考察,住在加军军事基地,来往内陆的飞机十天才有一班。
等末雁终于搭上最快一班飞机回到多伦多时,母亲的后事都已经由妹妹操办完了。
所谓的后事,也就是遗体告别火化仪式等等。
这些事情全部加起来,其实也只是后事的一半。
另外的一半,却是要等着末雁回来办的——母亲反复交代过,身后不沾父亲的光,骨灰由长女末雁送回老家藻溪归入祖坟埋葬。
那日末雁梦见母亲之后,当即决定回国一趟了却母亲的心愿。
灵灵学校里正好有两个星期的社会调查假,末雁就带了女儿同行。
临走的前一天,末雁去唐人街做了个头发。
做头发是一种时髦的说法,其实当时末雁只是想把留了三十年的齐肩发型略微剪短一下而已。
那天平素给她剪头的那个女理发师没在,招呼她的是一个新来的年轻小伙子。
小伙子一看就是广东福建那一带的移民,身架瘦小,装扮超前,举止乖巧精明。
他把她的头端在手里,转来转去地看,却不着急下剪。
一直看得末雁有了几分不自在,才说:
“大姐我给你换个发型,[FJF]NC523[FJJ]点颜色吧。
”见末雁犹豫不决,就笑:
“要是不行,一两个月就留回来了,变动变动,怕什么呢。
”
就是这“变动”两个字,不知怎的一下子触动了末雁心里的那根筋,她便横了一条心,说你看着办吧,大不了世界上再多出个把老妖精来。
小伙子嘴里说着哪能哪能呀,手就很是麻利地动了起来。
末雁将眼睛闭了,由着那小伙子的手指在她的头发里蚯蚓似的钻来钻去。
在剪子喀嚓喀嚓的声响中,她竟混混沌沌地睡了过去。
醒来时,只见那小伙子正在啪啪地抖着围布。
她一眼就看见了大镜子中有个女人,头发剪得极短极薄,只有额上的几缕刘海,长长俏俏地插入眉梢。
那头发是黑色的,又不全是黑色的,夹杂了几缕棕黄,灯光一照,就有了几分流动的感觉,衬得脸儿有些细瘦生动起来。
末雁提了提嘴角,镜里的那个女子也朝她微微一笑——这才知道那个女子就是自己。
慌慌地去柜台付了钱,又给那个小伙子塞了一张五元的小费,便飞也似的逃了出来。
到了街上,不住地拿手去摸脖子耳根,摸到哪里哪里是一片凉意。
在过了季的太阳里,末雁第一次有了要飞起来的感觉——才明白头发原来是有重量的。
一时兴起,就去商场买衣服。
末雁平时很少买衣服,要买也是去大众化的平价商场。
这天她突然想起灵灵说起过一家叫温娜的商店,是专卖减价的名牌衣装的,就开车去了那里。
进了商店,花红柳绿的,就看迷了眼。
随手挑了几件,素的太素,艳的太艳,都放了回去。
这时走过来一个黑人售货员,问需要帮忙吗?
那售货员和末雁岁数不差上下,矮矮胖胖的,说起话来脸上阔阔的都是笑。
末雁觉得那女人笑得憨厚亲切,原想问我这个年纪穿什么合适,话到嘴边,拐了个大弯,竟成了:
“我想,变个花样,你看,我刚离了婚……”
黑女人依旧是笑,却换了一种意味深长的笑法,问末雁穿几号。
末雁说了,女人就噌噌的穿过走道,直直地走到最里面那个架子上,麻利地取了一套衣服,挽着末雁的手进了试衣间。
进去了,也不离开,等着末雁窸窸窣窣地换完了衣服出来,两人便一起站到穿衣镜前看样式。
女人给末雁选的是一件黑色的丝绸衬衫,配的是同样料子的长裤。
末雁穿着觉得老气,正摇头间,黑女人就将那黑衬衫上的扣子全解开了,露出里头那件葱绿色的软缎贴身背心——也是她选的。
末雁觉得这一扣一脱之间,镜子里的那个人突然就变了。
似乎是变高了,变瘦了,但又不仅仅是变高变瘦。
她在心里换了很多个形容词,又觉得那些词都不够准确,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侧面。
最后她才发觉最准确的那个形容词是风情。
对,风情。
镜子里的那个女人突然变得有了几分风情。
末雁被这个形容词吓了一跳。
在这之前末雁从来没有把这个词和自己联想在一起。
更确切地说,末雁一生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这个词。
五十年里没有学会的词,却在这样一个下午,从那个年轻理发师手里,从这个黑人售货员手里,如此飞快地学会了。
黑女人将衣服叠好了,又领着末雁去收款台交了钱。
送末雁走到门口,突然将一只十分厚实的手臂搭在了末雁的肩上,轻轻地说:
“离婚只是一张纸,锁在抽屉里就行了,用不着带在身上的。
”
末雁听了,不禁怔住。
末雁和灵灵登上横越太平洋的飞机,经东京、上海抵达温州城,已是两天以后的事了。
去藻溪的车子,妹妹一家早安排妥当了。
那边接应的,是一个叫财求的人,据说是母亲的一个远房堂兄。
次日早上八点一刻,是事先择好的送殡吉时。
妹妹怀着身孕,不便远行,末雁和灵灵母女俩就捧了骨灰盒,按照择定的时辰上了路。
路不太远,却很是高低不平。
到处在修路盖房,尘土如蝇子飞扬,遮天蔽日。
末雁将骨灰盒搂在怀里,怕冷似的端着双肩。
盒子是檀香木做的,精精致致地镶了一道金边,像是从前富贵人家的首饰匣。
末雁搂了一会儿,手和盒子就都黏黏地热了起来。
母亲生前是个结实的妇人,躺在这么个狭小的匣子里,怎么能舒展得开手脚?
车子在坑洼之间一颠一簸的,母亲在盒子里一下一下地拍打着末雁的膝盖,仿佛有话要说,末雁突然有了一丝陌生的亲近感。
末雁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她生下来三个月就被送到了龙泉的奶奶身边,是奶奶雇了奶妈把她喂大的。
一直到十岁的时候她才回到温州的父母身边,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个妹妹。
童年的隔阂已经很难在少年时代弥补,更何况她十六岁就再次离家。
下乡、考大学、结婚、出国,她从此就长远地生活在外边的世界了。
在末雁的记忆中,母亲似乎永远是沉默寡言的,对她和对妹妹都是如此。
然而末雁还是知道这中间的差别的。
末雁和妹妹相差十岁,她从龙泉回来的那年,妹妹才出世不久。
在很多个夜晚,母亲会站在窗口,长久地一动不动地抱着妹妹,那时母亲的眼里淌着月光,那光亮将妹妹从头到脚地裹了进去,却将世界挡在了外边。
当然,世界的概念里也包括了末雁,甚至还有父亲。
有一次末雁突然萌生了想闯进这片光亮的意念。
那天母亲也是用同样的姿势抱着妹妹,末雁突然走过去,伸出一个手指,轻轻刮了一下妹妹的鼻子。
母亲吃了一惊,眼神骤然乱了,月光碎碎地滚了一地。
母亲闪过身去,将妹妹更紧地搂在了怀里。
刹那间,末雁看见了母亲眼角那一丝来不及掩藏的厌恶。
那天末雁哭着跑到自己的屋里,翻开墙角那面生了一些水锈的小镜子,看见了镜子里那张雀斑丛生毫无灵气的脸。
这张脸伴随着她走过了黑隧道般走也走不到头的青春岁月,到了中年才让她渐渐平息下来。
所以初中毕业那年她迫不及待地报名下了乡。
车子终于出了城,房子相隔远了,景致才渐渐开阔,露出些山水田地来。
虽是个晴天,太阳却是灰蒙蒙的,照得远处的山近处的水都不甚明了。
田里种的似乎都已经收割了,只剩了些黑黄黑黄参差不齐的茬子在风里抖着,如折了翅膀的鹞子。
再过去一些,就看见了水田,混浊的水里倒映着些边角模糊的天和云,像是水墨画里洇在景致外边的墨——却什么也没种。
灵灵趴在后座窗上,看见灰褐色的水田里浮着两块青褐色的大石头,就尖声去推末雁:
“妈妈,那是牛吗?
是不是水牛啊?
”见末雁木木的没回应,就扫了兴:
难怪爸爸说你没有好奇心。
灵灵这些年在多伦多,虽然周末一直上中文学校,可那中文水平却只够说事,不够抒情的。
这“好奇心”三个字,就是用英文来替代的。
末雁听了,一愣,心里仿佛塞了几根茅草,尖尖糙糙的很是扎人,拔也拔不出,咽又咽不下,却碍着司机,没有发作,只淡淡地说妈妈下乡的时候见多了,所以不奇怪。
你没见过,当然是少见多怪。
过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冷冷一笑,用英文添了一句:
“你爸爸的意见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假如你没忘记的话。
”
母女俩正说着话,突然听见正前方劈劈啪啪一阵爆响,碎纸屑红雨般从空中纷纷坠落——原来是有人在放鞭炮。
行人吓了一跳,四下飞散开来,瞬间又如饿鹰朝着热闹围聚过来。
司机嘎的一声将车停在路边,推了推末雁,说到了。
末雁吃了一惊,问这么快吗?
司机摇摇头,说这只是第一个凉亭——从温州到藻溪,一路上四个凉亭,个个都要停的。
这时人群破开一个小口,流出一队身着孝服的人马来。
领头的是个黑瘦的老头,走近来,见了末雁和灵灵,也不招呼,却砰的一声跪在地上,冲着末雁手中的骨灰盒,低低地将头磕了下去,口中喃喃说道:
“信月妹妹我来接你,接晚了……”后边的半句,是末雁顺着意思猜测出来的——老头的声音已如枯柴从正中折断了,丝丝缕缕的全是裂纹。
末雁心想这大概就是妹妹说的那个财求伯了。
末雁不懂乡下的规矩,只见财求伯的裤腿上粘了几团湿潮的泥土,脑勺近得几乎抵到了母亲的骨灰盒,一头稀疏的头发在晨风里秋叶似的颤簌,一时不知该和他一起下跪,还是该去扶他起来。
正犹豫间,老头已经自己起身了,从怀里抖抖地掏出两片麻布条子来,换下了末雁和灵灵胳膊上的黑布条:
“近亲戴麻,远亲才戴黑。
”末雁发现老头戴的是麻。
末雁跟着老头挤过人群,进了凉亭。
只见凉亭正中放了一张母亲的放大黑白照片,是二十几年前的样子,穿了一件中式棉袄,围了一条方格子围巾。
一丝笑意,从嘴角凉凉地流下,流得脸上也有了凉意。
再看地上白花花地跪了一群人,衣袖上裹的都是麻布,便暗暗惊诧母亲在老家竟有这么多的亲戚。
这时财求伯在末雁肩上轻轻拍了一拍,末雁身子一软,就情不自禁地在母亲遗像前跪了下来。
用眼角的余光扫了扫斜后方,发现灵灵不知什么时候也跪下了。
一路上末雁再三交代过灵灵要入乡随俗,却没想到这么一个八岁就离开了中国的孩子,竟肯跟着她当众下跪,也算是给足她面子了。
有人端过一杯清茶来,财求伯接了,拿手试过了热度,高高地举起来,对着照片说:
“信月妹妹,五十几年了,哥今天总算把你请回来了。
喝了这杯茶,哥带你回家……”话到了末尾,又颤颤的要断。
老头扬手将那杯茶往地上一泼,一线粉尘细细地飞扬起来,人群里便渐渐响起一片嘤嘤嗡嗡的哭声。
末雁抬头偷偷地看了一眼,发现哭的居多是老人,虽然不是想象中那种惊天动地的嚎法,却也哀哀切切眼泪婆娑的似乎有那么几分真情。
她知道乡下有雇人“哭灵”的习俗,却没想到哭灵的人竟有这样的专业水准。
这时财求伯又在末雁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拍,末雁猛然醒觉,意识到这一屋的排场其实都是背景。
那些眼泪,那些表情,那些声音,都是为了她的来临而做的铺垫。
她才是雷声后边的那场大雨,龙套之后的那个主角。
她紧闭双眸,试图回忆母亲的点点滴滴。
然而在失去了母亲照片的参照物时,她竟然完全记不起母亲的模样了。
她渴望能想起母亲的一个温存的眼神,一句关切的话语,甚至一次狠毒的责骂,任何一个可以让她流出泪来的温馨的或者委屈的时刻。
可是记忆如掌中的散沙,纵使握了满满的一把,却始终无法在她渴望的那一刻聚拢成团。
随着年华的老去,这几年她发觉自己的泪腺如一条原本就营养不良的细弱河流,渐渐地干涸在沙漠的重围之中。
即使是在绝对的独处时,悲喜之类的情绪都很难让她流泪,更何况是在这么一个众目睽睽的公众场合。
“雁,哪天你能哭了,你就好了。
”
末雁突然想起在北极考察时,那个叫汉斯的德国科学家对她说过的话。
她现在还不能哭,不愿哭,不会哭。
她知道她离“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就在这一刻,她的腰被人抵了一下,一个男人低低地对她说:
“跟我学。
”那声音轻得如同树叶间漏下的一缕风,痒痒地抚过她的颈子,与其说她听到了,倒不如说她感觉到了。
那风停了一停,又吹了过来,这次是一阵低沉而含混的喉音。
那喉音如同一口被堵塞了的泉眼,又如同一阵被拦截在死角里的风,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又似乎蕴涵了多种意义,在那种场合听起来,竟就有几分接近悲凉的呜咽了。
末雁清了一下喉咙,也开始含混地发出声音来。
末雁的声音攀缘在男人的声音之上,羞羞答答高高低低地走过了几圈,就渐渐地找着了感觉,有些平展自如起来。
众人终于放下心来,哭声便达到了高潮。
趁着混乱,末雁腾出一只手来探灵灵,发觉灵灵的位置空了。
睁开眼睛,看见灵灵远远地站在角落里,拿着数码照相机在拍照。
虽然看不见灵灵的表情,末雁却有了一种在女儿面前赤身裸体般的羞愧。
末雁一程又一程地送完了母亲,下了坟山,天就傍黑了。
财求公说你母女两个不如就在我家里歇了吧,明天早上再赶回温州误不了你的事。
末雁已经累得浑身没有一块不疼的地方,的确不想赶夜车回去。
却不知这老头家里干不干净,女儿住不住得习惯。
正在心里打着小九九,老头就说本来就打算留你们两个过夜的,屋子都找了婆姨们打扫消毒过了。
非典刚过,我们乡下人也知道害怕,都讲点卫生了。
末雁听了这话,就不好推辞了。
老头从人群里招出一个人来,说这是我孙子百川,他先带你们回去洗把脸,歇一歇,我去菜馆端几个下酒菜回来——我家婆姨死得早,没人做饭,你们将就点儿。
末雁和灵灵跟在百川后头,拖拖趿趿地走了一刻钟,就到了财求的家。
是一幢两层的砖房,方方正正的,外墙镶了一层白花花的马赛克,在暮色里新得有些龇牙咧嘴。
铁门上贴了一对大福娃娃,两边的春联已经有了些风吹雨淋的痕迹,字迹却还可辨。
上联是:
一世人生有炎凉,晨也担当暮也担当;下联是:
丈夫遇事似山岗,毁也端庄誉也端庄;横批是:
稳如泰山。
末雁觉得这副春联和寻常的喜庆春联很有些不同,就问百川这是你爷爷写的吗?
百川哼了一声,说他知道个球,这是汪小子的诗,汪国真,你知道吗?
见末雁摇头,就笑:
“不知道也好,省得受骗。
”
末雁心想这个叫百川的男人论辈分应该叫她一声姑,说话却完全没有拘泥礼节,虽有几分鲁莽,倒也叫她整个人都放松了,跟着他无拘无束起来。
灵灵从书包里掏照相机,掏了一半又放回去了,说一路上怎么都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新房子呢?
妈妈你下乡时照片上的那些老房子,怎么这里都没有呢?
百川开了门锁,屋里嗖地蹿出一条其丑无比的大黄狗,一阵恶吼,震得铁门铁窗嗡嗡地抖,几欲将灵灵扑倒在地。
百川噌地脱下一只鞋,照着狗脸就NCF28:
“客人来了,你知不知道?
嚎你个嚎。
”那狗挨了揍,顿时就蔫了,蹲在地上,软得像一摊水。
偏偏灵灵从小就养狗,最是不怕狗的,就往地上一坐,将狗一搂,两个立时就玩成了一团。
百川进了屋,三下两下脱掉了身上的丧服,胡乱卷成一团,往门后一扔,拖过一张板凳,坐下来挤脚上的水泡。
一边挤一边叹气:
“我说信月姑婆啊,我与你一面都没见过,你就这么整治我。
我自己的葬礼,都不用走这么多的路呀。
”
说得末雁忍不住笑了起来。
百川又转身对灵灵说:
“灵灵你跟你妈坐车,我跟我老爷子走路,这叫阶级区分,你懂吗?
”灵灵问什么是阶级?
百川朝末雁咧了咧嘴:
“那你得问你妈,不过你妈也是前清的中国人了,你也别全信她的话。
你想看旧房子呀,藻溪有得是。
你要是明天不走,我就带你去看你外婆家的老宅——三进的院子,正间、西厢、东厢,旧是旧了,却全是古书上的样式呢。
不过,千万别让我们家老爷子知道。
”
灵灵就拿眼睛来试探末雁。
末雁不说话。
百川依旧在挑泡,挑得一脚是血,就随手扯过一张纸来擦。
擦一下,咝一声,眉上轻轻地挂上了个结。
脱了那一身的布景衣装,只剩了一件汗衫,就看出人的高壮来了。
肩头如犁过的田垄,一丝一绺的全是硬肉。
戴了一副宽边眼镜,目光从镜片后头穿过来,刀片似的锐利清爽。
胡子散漫地爬了一脸,像疯长了一季的藤蔓,虽是秋了,却让人看上一眼就津津地冒汗。
末雁擦着额上的汗,说灵灵我们明天一定要赶回温州的。
百川终于挤完了泡,找了几张创可贴横七竖八地贴上,鸭蹼一样扁平的脚掌上就有了些错乱的景致。
“藻溪的妙处,你连个边都还没擦到呢。
”百川的眼睛看着灵灵,话却是对末雁说的,“你要是多住几天,你学到的就不只是怎么哭丧了。
要是呆到头七,那‘哭七’才真正有意思呢。
”
末雁恍然大悟,那个在凉亭里教她怎么哭丧的男人原来就是百川。
一路四个凉亭,她一程比一程哭得自然。
刚开始时,眼泪流过嘴角的那丝辛咸味道让她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她才明白她哭了。
汉斯,汉斯,我终于,有了眼泪。
她喃喃地对自己说。
待到坟山封口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就已经像使坏了的车闸,想停都停不住了。
那眼泪仿佛不是从她眼中生出的,只是借了她的脸,惶惶地赶路。
她起先是在哭母亲的,哭那些与命运阴差阳错擦肩而过却让妹妹毫不费心地拿走了的母爱。
后来又似乎在哭自己,哭的是自己生活河床里边那些细细碎碎石子似的不如意。
虽然是真性情的流露,却因了开坏了那个头,后面的一切多多少少就有了些世故的味道了。
“‘哭七’是什么东西?
”灵灵追着百川问。
“总结,评估,鉴定,你懂吗?
”
百川见灵灵一头雾水的样子,就甩开灵灵,直接对末雁说:
“死人下葬第七日叫‘过七’,那天,就有唱鼓词的来,在你家门前支起鼓,唱死人的事。
唱鼓词的是不请自来的,你还不能赶他走,他吃的就是死人这碗饭。
当然,唱的还不见得都是好事,得看你给的是什么样的赏钱,当然,现在叫红包。
给得多,唱的自然就是花红柳绿的好风光。
那给得少的,还有不给的,人家就先给你点破一层皮,无非是你们家那点鸡零狗碎的小玩艺,不痛不痒的,可就让你坐不住了。
懂事的,就赶紧端茶递水,茶杯底下悄悄把赏钱添上。
遇见那不懂事的,就渐渐进入剥皮见血的阶段了。
若到了那时还不肯拔毛,接下来唱的就是你们家公公扒灰儿媳妇偷人的事了。
”
“扒灰是什么东西?
”灵灵问。
百川看了末雁一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看你妈给你这中文教育,关键的都没学好。
”
灵灵听出这大概不是一句好话,也就不敢往下追问了。
“妈妈你看百川哥哥的脚趾头,和你一样呢。
”
末雁凑过去看,只见百川的小脚趾头旁边,突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圆骨,仿佛是多长了半个趾头。
末雁的脚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