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不见宁波四明中学.docx
《再见不见宁波四明中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再见不见宁波四明中学.docx(2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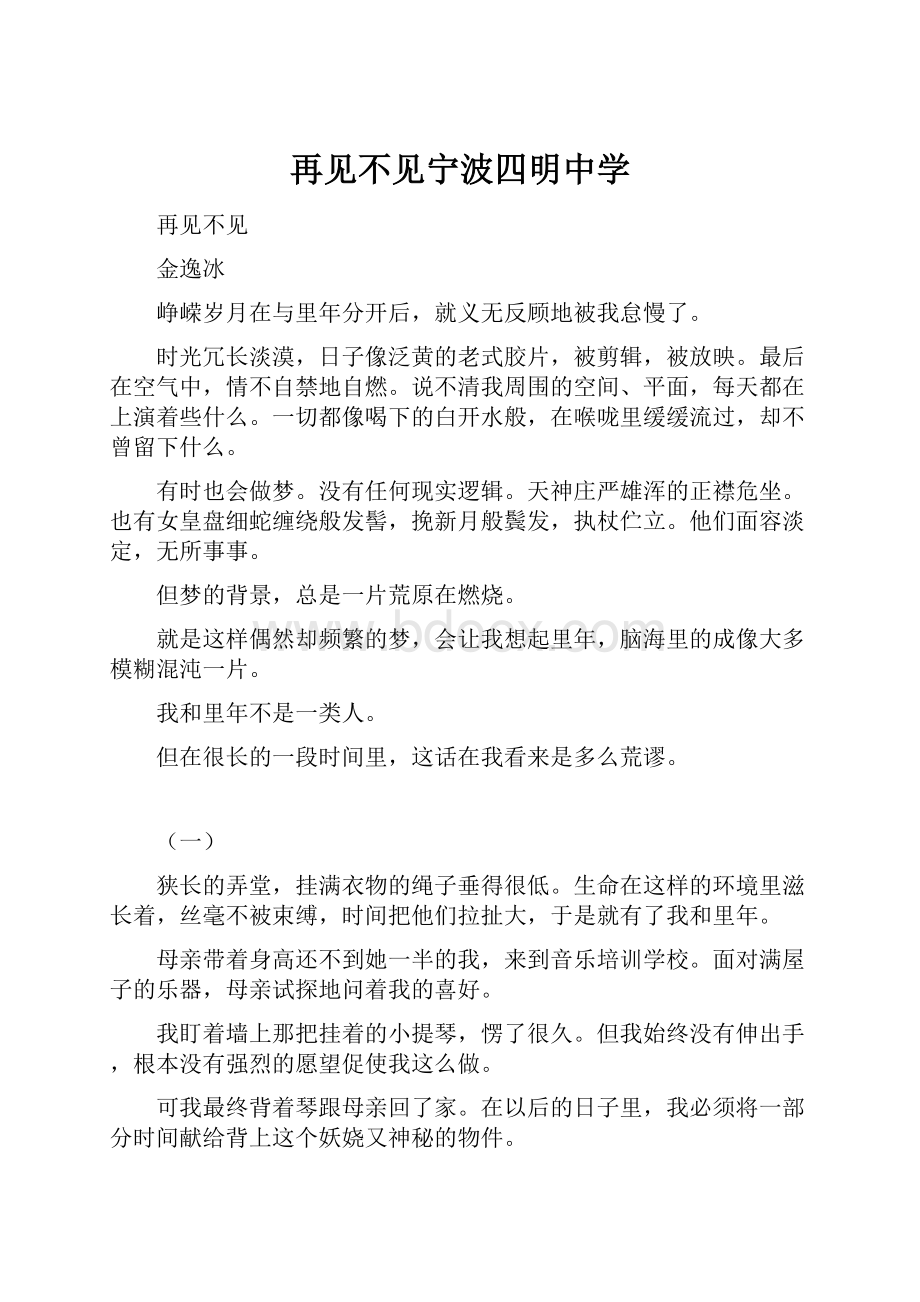
再见不见宁波四明中学
再见不见
金逸冰
峥嵘岁月在与里年分开后,就义无反顾地被我怠慢了。
时光冗长淡漠,日子像泛黄的老式胶片,被剪辑,被放映。
最后在空气中,情不自禁地自燃。
说不清我周围的空间、平面,每天都在上演着些什么。
一切都像喝下的白开水般,在喉咙里缓缓流过,却不曾留下什么。
有时也会做梦。
没有任何现实逻辑。
天神庄严雄浑的正襟危坐。
也有女皇盘细蛇缠绕般发髻,挽新月般鬓发,执杖伫立。
他们面容淡定,无所事事。
但梦的背景,总是一片荒原在燃烧。
就是这样偶然却频繁的梦,会让我想起里年,脑海里的成像大多模糊混沌一片。
我和里年不是一类人。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话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
(一)
狭长的弄堂,挂满衣物的绳子垂得很低。
生命在这样的环境里滋长着,丝毫不被束缚,时间把他们拉扯大,于是就有了我和里年。
母亲带着身高还不到她一半的我,来到音乐培训学校。
面对满屋子的乐器,母亲试探地问着我的喜好。
我盯着墙上那把挂着的小提琴,愣了很久。
但我始终没有伸出手,根本没有强烈的愿望促使我这么做。
可我最终背着琴跟母亲回了家。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必须将一部分时间献给背上这个妖娆又神秘的物件。
我从未忘记是什么让我做出断然的决定。
音乐教室的后门传来响亮的巴掌声,那个男孩红肿的脸,以及他父亲从牙齿缝里挤出的话:
“再不好好学你对得起谁啊你!
”
谁也不能放下,既然已经拿起来了。
可谁又知道,对于后来的我,这竟然成为奢求。
在当时看来,我是可以拒绝学琴的,但那男孩的遭遇却让我产生反向的意念。
男孩和我住在同一个巷子里。
于是从此弄堂里的两种琴声就如同报时一般准,风雨无阻。
每晚七点整,优雅的钢琴初级练习曲和刺耳的小提琴入门音阶。
两种声音从不同的窗口传出,但却在浑浊的夜色中变得和谐起来,掩盖了冬天大风的呼啸与夏天盛大的蝉鸣。
我终于认识了里年。
那一天过得极不顺利。
下午到老师地方回琴,没有很好的通过,母亲一直绷着脸。
之后晚上练琴,又不情不愿。
结果被父亲说了几句,就气急败坏地乱拉一通。
一记巴掌适时地落在我的脸上。
“你到底练不练?
不练滚出去。
”父亲终于无法再控制情绪,把我拽出了门,“想清楚了再进来。
”说完,屋内的一切就与我隔绝了。
我走了几步,在黑暗中蹲下来,不知应该把小提琴放哪儿。
我一点也不想对这东西好,可现在只有它陪着我。
对面街角传来一阵阵酒瓶破碎的声音,嘶吼声,关门声。
之后的世界又掉进了寂静里,黑暗包容了一切,悄无声息。
我从膝盖间抬起头,看见路灯下晃动的人影,渐行渐远。
不知他是否朝我走来,但我是希望的。
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样的人。
我突兀地喊了声“喂”,那人顿了顿,便走了过来。
是一个干净明朗的男孩。
穿着件红色的T恤,低着头,脸和第一次我在培训学校见到他时一样肿。
“我在音乐室见过你,你是弹钢琴的吗?
”我好奇的问他。
“嗯……"男孩应声道,但仍低着头。
“我也是刚开始学琴,小提琴。
哦……我叫夏安,你呢?
”
“里年。
嗯……你怎么坐在这里呢?
”他终于抬起头问。
“没好好练琴,被我爸赶出来了。
”我用不痛不痒的语气来陈述这个事实。
“啊……我也是……但也不全是。
”里年在我旁边的草皮上坐了下来,拔了根草在手里玩弄。
沉默吞噬了一长段时间,思绪也乘机开始漫无目的的游走。
“你什么时候回家?
”里年又开口问。
“我爸说等我想清楚。
”
“那你想清楚了吗?
”
“没有,你呢?
”
“我又不用想,我只有等。
”
“啊?
哦……其实我也不用想,我妈肯定会把我拉回去的。
”
里年在一旁没来由地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
周围躺着许多纳凉的邻居,他们席地迷迷糊糊地睡着。
没过多久,母亲真的在家门口叫我名字。
我起身和里年说再见,末了又回头问:
“你还会等多久?
”里年扬了扬眉毛说:
“我也不知道,你先回去吧,再见。
”
第二天清晨,我从窗外望出去,里年仍在那块草皮上,但显然,他还在睡梦中。
自那次以后,我越来越厌恶拉琴了,特别是每回临近暑假就要参加小提琴考级。
我一直认为,音乐本身是惹人喜爱的,可偏偏套上了考级的紧箍咒,原本自由无边的有灵魂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活力,全被束缚住了。
暑假里,我偶尔和里年一起逃课。
对此他很干脆,说逃就逃。
我有时候还要犹豫再三,怕有什么后患。
实际上后患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逃课常常被发现。
不是我,就是他。
打骂是避免不了的了,不过我们都不怎么在乎。
第二天还要兴致勃勃得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叙述给对方听。
这年我和里年十一岁。
我们将自己的岁月与音符绑定,经历着别人不曾经历过的。
最终无法言语的快乐和痛苦。
如同催化剂般,在眨眼间,成就了两个迥异的生命。
(二)
在人们的脑子里,冗长的时间与经历的事物是被揉成一团的,没有任何记号。
所以很多事情都好像发生在昨天。
但其实,生命正如海绵般吸水,时间被稀释成轻薄的一长条,所有事件都如同细菌般粘附在上面,一同在头顶缓缓流过,毫无知觉。
我和里年上了初中。
在同一个班级里。
也许是单亲家庭的缘故,里年时常保持沉默,也没有什么朋友。
他用大多的时间来听歌。
但偶尔也会走过来和我说话,这在其他同学看来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对此,我曾有过猜测,或许他也认为我们是一样的人。
一切都已不再如从前了。
里年的个子开始疯狂的窜高。
在他身上我似乎能听到骨骼生长的声音。
但依然是那张干净明朗的脸,不过轮廓更加鲜明了。
他的身后时常会有二三个女生,与他保持着三到五米的距离,微笑着窃窃私语。
这些青春的迹象,都在我脑海里一次次被沸水泡开,散发着热腾腾的清香。
里年修长的手指,已能弹奏出行云流水般的钢琴曲。
肖邦、莫扎特过后,他开始在市里的一些钢琴比赛里得奖。
那双手目前在我看来充满神奇的色彩。
而我也终于把小提琴拉出味道来了。
没有了空弦,音阶,初级练习曲。
塞茨、罗德、维第、马扎斯,旋律逐渐圆润流畅。
费奥里多、海顿、莫扎特、约翰斯特劳斯,没有了刺耳的破音。
眼下正在练习萨拉萨蒂的《浮士德幻想曲》。
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感觉的音乐小青年,于是就继续朝这方向发展,个性越来越凸显。
长头发不做弄的让它披着,不再用梳子梳头,偶尔用手理一理,营造一种随性的感觉。
穿宽松的大T恤,有时把衣角在腰上打个结,就当紧身衣穿。
套着一条松垮的丹宁裤,脚下踏一双滑板鞋。
这样的装束可以维持一个夏天,晃过无数个大街小巷,结识些不同的人,再回到原地。
那天和里年一起回家,他推着脚踏车,我背着琴在他身边走,嘴里哼着歌。
“唉,我觉得你越来越像……”里年皱着眉头,思索着后半句话。
“什么?
”我问。
“做音乐的人。
”
“啊哈?
”我一听就笑开了。
看着他穿着整整齐齐的校服,车兜里放着一堆乐谱,笑问: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
“像什么?
”
“教音乐的人。
”
最后他笑得比我还夸张。
或许很少有人会认同,音乐里所表达的是岁月的情绪,而并非人的。
那些情绪不容反悔,不容抵抗。
只是在颤音之后,变得意味深长。
学校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又在喧哗中到来了,似乎是趁着秋天这点感伤,来捕捉点艺术的灵感。
里年一下课就拉着我去看教学楼下的艺术节海报。
海报前围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
我没法挤进去,里年就仰着头,把海报内容念了一遍。
我的耳朵抓住了零星几个关键的词语。
“乐器”、“选拔”、“现场”、“投票”。
“我不想去,”我断然的拒绝,“这么多人,还要选拔,挺烦人的。
”
“啊……你已经不得不去了。
”里年转头,狡黠一笑说。
“为什么?
”我皱着眉头奇怪地问。
“因为我已经填好两张表格交上去了。
”
“你也去?
”
“为什么不去呢?
不错的机会啊。
”
“我还以为你很低调呢。
”
“我主要是想让你去。
你已经拉得不错了,应该展现一下。
”
最终我妥协了。
但后来,我借着里年的光混上了台。
这么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里年能弹一手好钢琴,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
选拔当天,我在音乐老师面前拉了一首《查尔达什舞曲》。
一曲完后,老师就直白地对我说:
“小提琴独奏声音太单薄,是上不了台的,更何况你连背景配乐都没有。
”
出来后见到里年,我就将老师的原话转述给他。
我面无表情,就像完成他给我的任务一般,说完就走了。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当时的心情,觉得有点恨,可不知道这恨到底该对准什么。
第二天,教室里的空气闷闷的。
明明已把窗子开得很大,但这闷似乎怎么也逸散不开去。
课间我趴在课桌上睡,恍惚间有人将一只耳机塞到我耳朵里。
指尖的凉意过了很久还留在我的耳垂上。
我直起身,此刻头脑已经快被劲爆的摇滚乐灌满,仅有的空间用来装下我看到的里年的侧脸。
他微微笑着,拨弄着手里的播放器。
“看不出嘛,原来你也会喜欢摇滚。
”我整了整桌上的东西说。
里年边点着头边说:
“欧美的摇滚很纯正,很有释放的感觉。
”
“有空我给你带本书吧,是关于摇滚史的,上回在那家小书店里淘到的。
”我想了想说。
“好的……对了,你上台想拉什么曲子?
”里年盯着音乐播放器的屏幕,轻声地问我。
“什么呀,都被别人刷下来了,还拉什么?
”我错愕地看着他。
“老师说我们可以合奏。
”
我看了他一眼,笑了。
“骗谁啊你,老师说?
你说的吧!
”
“都一样嘛,赏不赏光?
”
我歪着头,斜斜地看着他,最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手臂,笑说:
“好好练,不准拖我后腿。
”
也就在那时,我深刻的感觉到里年变了,不再闷声不吭,难以接近。
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如此潜移默化的将一个人全身上下的细胞进行洗礼和整改。
虽说我拥有可能的答案,但却不愿说出口。
因为从没有人问过我,你到底喜不喜欢小提琴。
我想应该也不曾有人问过里年。
而在我们的内心也无法追寻到答案。
有些秘密的情绪和一晃而过的思想,在曾经稚气的岁月里就已尘封了,而如今的一切又能说明什么呢?
艺术节那天,舞台下黑压压的一片。
我和里年是第五个节目,合奏的曲子是舒伯特的《小夜曲》。
我们上台的时候,一束聚光灯强烈的照射下来。
掌声象征性的又齐又响。
一切和我们练习的时候配合的一样好。
奏出的音符都很有灵性,它们将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最后我用婉转的滑音作为亮丽的收尾。
曲毕,掌声阵阵。
下台后,里年展现了他标致的微笑,轻快地对我说:
“合作愉快。
”我点头笑了笑当做回应。
后台有几个同班同学是兴奋的跑来祝贺的,难免的,要被他们调侃几句。
“一个弹得好,一个拉得好。
你们俩干脆搞个组合吧,肯定红。
”一个戴眼镜的男生笑笑说。
“就是嘛,那也难怪的,他们俩,一个是校花,一个钢琴王子,不配也配了。
”
对于这种有些恶俗的话,我的耳朵向来是会自动过滤的,偶尔听进些,可也没觉得反感。
他们的话,倒让我想起里年曾经在华丽的橱窗前睥睨着看名牌看到流口水的我说,你的睫毛是我两倍长。
这话,在之后让我诧异了好久。
里年并非是如此直白的人。
之后出场的是一个弹吉他的女生,高高瘦瘦,坐在一把无背的钢椅上,麦克风在她嘴下方一点。
短发女生抬了抬头,对着麦克风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
“给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创作的歌曲《荒野里的光》。
”
这句话引起台下不小的骚动,有人叫喊了几声,是为了煽动气氛。
吉他声响起,女生用轻轻的气声唱到:
城市有点慵懒
它好像是在溃烂
我需要一片荒野
那里有美丽的光源
台下的学生们已经被她的歌声感染,大多数人站起来,小部分人不停地尖叫。
我不得不承认她很有气场。
而且就她的歌和唱功来说,她应该很有音乐天赋。
坐在我旁边的里年也看得出神,我碰了他一下,问:
“你觉得怎样?
”
他目光毫不转移地说:
“不错啊,很有感觉。
”
“可你不觉得这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颓废很肤浅吗?
”
“可这也是一种音乐取向啊。
这女孩叫兹瑾,六班的。
”
“你怎么知道?
”
“节目单上写着。
”
看了眼节目单,“兹瑾。
”我在嘴里轻声念道。
必须承认,我并不是毫无心机的人。
有时,我的询问带有试探,我的话语带有目的。
但并非绵里藏针,只是内心某种正常的心理会提醒我要警惕,守住那些曾经属于我的东西。
一二三等奖是通过学生投票选出来的,最终兹瑾毫无悬念地获得了一等奖。
我和里年拿了个二等奖。
那天是里年去政教处领奖状。
回来后他把奖状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就放在我的桌子上,摸了摸鼻子说:
“你留着吧,当做纪念。
”虽说我收下也是合乎情理的,但我内心总希望不要对里年有所亏欠,毕竟是我们俩一起的演出。
为此,我很快的思索了一个推脱的理由。
“客气什么呀,你拿着吧,我这人习惯不好,东西爱乱放,到时候肯定要被我弄没的。
”我懒懒的说。
这样的借口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但里年总会相信,然后事情会继续朝着我预料的方向发展。
永远没有裂痕。
(三)
生命中的许多转折经不起碰撞,它们会偏离轨道,再也无法扭转。
至于一些向往过的美好,就更不必提及了。
这年夏天,我和里年十七岁。
里年以优秀的成绩考入了市里的重点中学,我也因为艺术加分上了自费线。
我们仍住在那个细长狭小的弄堂里。
一到夏天,女人们在茶余饭后围坐在一起。
流言和蜚语沐浴着她们嘴里的潮气,在弄堂里疯狂地滋长。
曾有一回,我意外地听到了一些关于里年父亲的传闻。
酗酒,耍酒疯。
攒了几年的工钱给儿子买下钢琴,然后打骂他。
但里年又是他唯一的骄傲。
这样的父与子让我觉得不可捉摸。
可他们的确是这样生活着,享受上帝给予的昏天与暗地。
没有说出口的,是他们内心都懂的。
我总有冲动,觉得自己应对里年再好一些。
但这些半路杀出来的冲动最终会被我的理智打趴下。
因为理论上我是没必要这么做的。
也就是这年夏天,我突然喜欢上了乡村音乐。
买了各种各样的CD,书籍,最后还无可救药的想买吉他。
自从有了这个念头之后,我经常想起那个叫兹瑾的女孩,弹着吉他,唱自己的歌。
母亲拒绝了我买吉他的要求。
她把这理解成我的心血来潮。
但最终我得到了它,是爷爷给我买的。
一把民谣吉他,一把电吉他。
于是之后的整个夏天,我就在琴弦的拨拨弄弄中度过了。
离开学还有一段日子,我在巷口碰见了里年,他正扛着一台双排键,手里拿着琴架。
“嘿,你从哪儿弄来这东西?
”我新奇的走上前碰了碰琴键。
“荒草酒吧,他们看我琴弹得不错,就把这坏掉的双排键送我了,刚刚拿去修,竟然还能用,这家伙音质挺不错。
”
“荒草兄弟送的?
看来他们酒吧的生意应该越来越好了,不然怎么出手这么大方。
”
“是啊,记得我们当时去看他们兄弟俩演出时,乐器还很简陋呢。
”
“唉,你怎么会去那里?
”
“暑假闲着没事,反正和他们认识,去打点零工。
结果他们请我上台弹钢琴。
还教我学双排键。
”
“这么说,这东西你已经会玩了?
”
“那倒还没有,不过有钢琴的基础,学起来还挺快的。
”
“真不错,不过还是敲键盘的。
我也买了把吉他玩,还是弦乐器。
”我笑着说。
这回似乎是我们自己选的,但这决定如同种下的种子,要等开花还要很久,不知到时候是芳香还是恶臭。
开学第一天意外地发现里年还是和我一个班,其实这早已不算什么意外了。
课间,里年跑来说找我帮忙。
我们来到音乐教学楼,我同他一起将学校的一架钢琴从一个琴房朝另一个琴房推,顺便把里年从家里带来的双排键安顿好。
干完后,里年拍了拍手中的灰说:
“以后就可以在学校里练琴了,对呀,你也可以把乐器带来。
”
“有时间吗?
高中学习会很紧。
”我漫不经心地问。
“我们有活动课啊。
”
“也对。
”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我根本懒得回头看。
但当脚步声停止时,我分明看到里年脸上瞬间闪过的惊讶,之后又全然被微笑代替。
这时我也看见了,是兹瑾,她背着Gibson吉他。
这牌子的吉他是摇滚吉他里的泰山。
我想起前几天一些八卦人士的只言片语,说兹瑾家境很好,父亲是有名的企业家,母亲是大学老师。
我对此很不屑,觉得这群人包括话题人在内都很庸俗。
“你也在这里?
”里年站起来笑着招呼。
“是啊,上回还要感谢你替我领的奖状呢!
”兹瑾含笑说。
“那没什么,哦,对了,这是夏安,以前都是一个初中的。
”里年很不自然地介绍着。
“哦,我有点印象,是和你一同上台演奏的,记得她小提琴拉得很好呢。
”
“没有没有,只是业余随便玩玩。
”我有些不好意思。
之后他们的谈话我没怎么听进去,什么兴趣爱好,组建乐队之类的。
我是插不进话的。
突然意识到我的身份似乎接近局外人了。
有人帮忙领奖状,有人说感谢,所有相识的契机都顺其自然。
一些被剪辑的记忆在脑海里更迭,里年曾反驳我“那也是一种音乐取向。
”,而如今兹瑾依然低声轻唱。
这些早已与我无关了。
我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洒脱,很直白,没有过滤。
但自己的内心却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几乎是不愿过问任何人,哪怕是我很在乎的事。
宁可之后在自己心里默默揣测,零零碎碎的自我折磨着。
重点高中采取精英式教学。
有些不太重要的课时,直接让我们查资料自学。
老师讲课速度很快,只稍稍拎一拎基础与重点,然后就用大部分时间解说深奥的难题。
试卷更是有些刁难人,题目常常超纲。
里年的成绩仍在年级里位居前列,而我早已支撑不住,节节败退。
但我依然花时间在乐器上。
某种心理让我对乐器开始变得固执,促使我的手一天也不能停下来。
我一直跟随着他们,现在也是一样的。
里年,兹瑾,荒草兄弟,那些仍在音乐里沉溺的人们。
晚上回家,屋里的灯光灰暗。
我拽着书包往房间里走。
母亲在客厅里叫了我一声,听不出什么感情色彩。
我转身朝客厅走去。
我爸陷在沙发里,一手夹着烟,一手握着遥控器,目不转睛的盯着电视。
母亲则坐在一旁,背挺得直直的。
“学校来电话了,让你在学习上抓把紧,不然以后考大学,连上线都有问题。
这是你们老师的原话,你自己好好去想想吧。
”母亲的语速很快,估计她比我还不希望听到这话。
我“嗯”了一声,不想再多呆,就转身准备回房间。
“还有,”母亲又说“不要在乐器上花时间了,这东西是不能当饭吃的。
一门心思学习,以后还有希望。
到时候随你弹什么我都不管,但你现在必须把成绩搞上去,不然……”
母亲有点激动,半句话落在空中没了底。
“她熬得住啊?
她个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要我说,你干脆狠点心,把她那些东西全部扔掉,要么锁起来,不然她又不肯放手的。
”我爸盯着电视恨恨地说,听得出他心里有火气。
母亲在一旁点头了,她看了看我说:
“那只能这样了,你把那些东西都拿出来,我替你保管着,以后考上大学了再给你。
”
我知道我是不会反抗的。
自以为会很难过,但发现现实还可以忍受。
当我把乐器拿出来,放在他们面前时,至少那时,我内心的伤感与愤怒还未将我的理智吞噬。
我轻拿轻放,没有一点感情的透露。
这或许是在他们意料之外的。
如果按照逻辑,我应该拿着乐器狠命的摔在他们面前,但是没有。
可无论怎么轻拿轻放,琴弦在落地时仍放出空灵的呻吟。
当时,这是唯一让我感到心痛的声音。
感觉之后我体内的血液仍在正常循环,但似乎从此再没有了节奏感。
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永远地少了一拍。
日子依然颠来复去,用一个模子,换着不同的外衣,来掩人耳目。
课间依然是最难熬的时光,我趴在桌子上无所事事。
已经很少会有人再跑过来和我说话了。
其实我根本不想去在意这些细微的变化,但意识总是不自觉地去审查。
中午吃饭的时候,里年端着饭盒走到我对面的位子上坐下。
他笑着和我说起了关于组建乐队的事。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以为在听一件别人讲述的事不关己的事。
直到里年问我有没有意向加入时,极度的失落顷刻袭来。
我在我们曾经擅长的方面已经一无所有了。
过不了多久,我的左手就会僵硬,它骨子里是没有记忆芯片的。
可我还是不自禁的应了一声,这让里年误以为我答应了,于是和我说起了详细的筹划。
其实我真的说不出口,这导致我后来什么也没听进去。
连我自己都无法缓冲过来的事实,怎么镇定自若地告诉里年呢?
况且这一切还是因为成绩的缘故。
这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
那天晚上,我坐在写字台前,不知是怎样的思想过度,让我想到了里年所说的关于乐队的事。
所有的向往从里年的嘴里说出也就成了我的向往。
但我已经失去实践的条件与资格了。
始终无法抑制内心对于音乐和加入里年圈子的狂热,思绪在漂移之后开始向理智勒索。
先是极度地悔恨当时他们让我把乐器拿出来时,怎么连抵抗都没有。
之后开始厌恶地捶打自己的头。
最终我走向父母的卧室,企图翻找杂物间的钥匙,我的那些东西都锁在里面。
床头的抽屉,衣橱,枕头下,柜子里,曾经父母没收我的东西然后藏过的地方都被我翻了个遍,可是没有。
突然眼神落在卧室里的装饰花瓶上,我将手伸进去,先是废报纸,然后摸到一块软软的海绵,最后是瓶底。
还是没有。
但就在这时,我的食指触碰到一小块金属,是钥匙。
掏出来看,是杂物间的。
内心深处有低声的尖叫,似乎感觉到挽回了什么。
我捏着钥匙快步走向杂物间。
“把手里的东西给我。
”一个克制着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的心一紧,手也握紧了。
如果再失去,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转过身,用镇定的声音说:
“什么?
没有啊。
”
“拿出来。
”父亲的声音重了起来。
我愣在原地,不愿把手伸出来,但也不知道怎么办。
母亲已经闻声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我已经无路可逃了,所有的罪状都有凭有据。
后来我交出了钥匙,瘫坐在地上,听他们数落。
“每天音乐音乐,玩什么心情啊?
你给我清醒点,小时候不是没让你学过,让你学的时候不好好练,不是偷懒就是逃课。
要高考了你倒给我装模作样要练琴了。
真以为这能当饭吃啊,到时候连大学也混不上,你拿什么玩心情?
你玩得起吗,啊?
”父亲边说边掏出手机,查找了一会儿,朝我扔来。
“看啊,你自己看,是你的月考成绩吧,排第几?
这数字你说的出口吗?
你就不觉得可笑又可耻吗?
还有心思找钥匙,你脸还要不要?
你不要我还要呢。
”
心中有怒气不断的涌上来,最终冲破了克制的底线。
“那你以为这样有用吗,我不一样要挖空心思去想。
成绩还是一样差,别人还是一样看不起,那还不如……”
话还没有说完,巴掌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
父亲边打,边朝我摔着东西。
我已不想躲了。
母亲愣在一旁,一言不发。
窗外的夜色已经很浓了,弄堂里都亮着灯。
大大小小的事件正在这昏暗的世俗中上演。
能感觉到悲伤,但都是无关痛痒的。
或许有人会察觉到一丝的不安分,隐约听到肮脏的诋毁,谩骂,还有物体支离破碎的声响。
一些人的绝望正在一些人的美梦中孕育。
我家的大门被父亲“呼”的拉开,然后连托带拉把我拽到门前。
他已经有点控制不住情绪,在旁人看来或许就像发了病一样。
我知道他的恨。
所以我面无表情,朝远处的一个点直直的望着,像是没了魂一般。
不反抗,是我对父亲最好的态度。
“扔了好吧?
都扔出去,这样就不会再折腾了。
”父亲用征求的口吻问我,声音有点发抖,让人听上去有点像请求。
我流着眼泪,喘着气,什么也不说。
母亲走回卧室,关上房门,她已经失望得看不下去了。
父亲仍站在门口,望着外面漆黑一片,很久没说话。
他需要一根烟。
我起身朝茶几走去,泪水还是不断涌出来,从一包烟里抽出一根,拿上打火机,又向门口走去。
“抽烟吧?
”我把烟和打火机递给他。
他先是一愣,然后默默地抽起来。
冷风从门口灌进来,夹着淡淡的烟味。
父亲开始走动,来来回回,从屋内走到屋外。
最后一把抓起桌上的钥匙朝杂物间走去。
自上次以后我又听到了零碎的琴弦震动声,很低沉,很抑郁。
父亲拖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弦乐器来到门口,把他们狠狠的抛向黑夜。
我突然很想笑,因为这让我想起一个在脑中存留了很久的画面。
那天放学,路过工地,我看见了里年的爸爸,这个第一次见他竟是狠狠给他儿子一巴掌的男人,正穿着肮脏破旧的白背心,将一袋袋水泥扔到另一个工人手里,他只能用劳力与汗水为儿子积累微少的财富。
而如今我的父亲正用同样的姿势将我从小到大拿过的乐器扔向门外的那片空地。
他的嘴唇微微抖动着,似乎与乐器落地时琴弦的震动有着一样的频率。
“烧了它们,好吧,你也该死心了。
”父亲气声说道,但已没了底气。
我不想思考。
一切总该有结局,无论好坏。
我已陷入神情恍惚的状态,嘴角微微抽了抽。
“烧了吧,是该烧了。
”连我自己也不确定这是不是我该说的话,可此时我已经笃定地说出来了。
我走到门外,看见黑暗中四处散开的乐器。
七岁时的第一把小提琴,十一岁时因为手长长而换的第二把小提琴,十五岁换上的最后一把小提琴,十七岁得到的两把吉他。
它们都已经死了,要火化,但是没有坟墓的。
我回头,发现父亲不在那里了。
可后来他从弄堂的自行车棚里出来,手里捧着大把木柴、旧报纸。
所有的所有都成了定局,是不容更改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唯一能看清的是父亲将嘴里一点残留的烟头扔向那片黑暗,瞬间,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