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docx
《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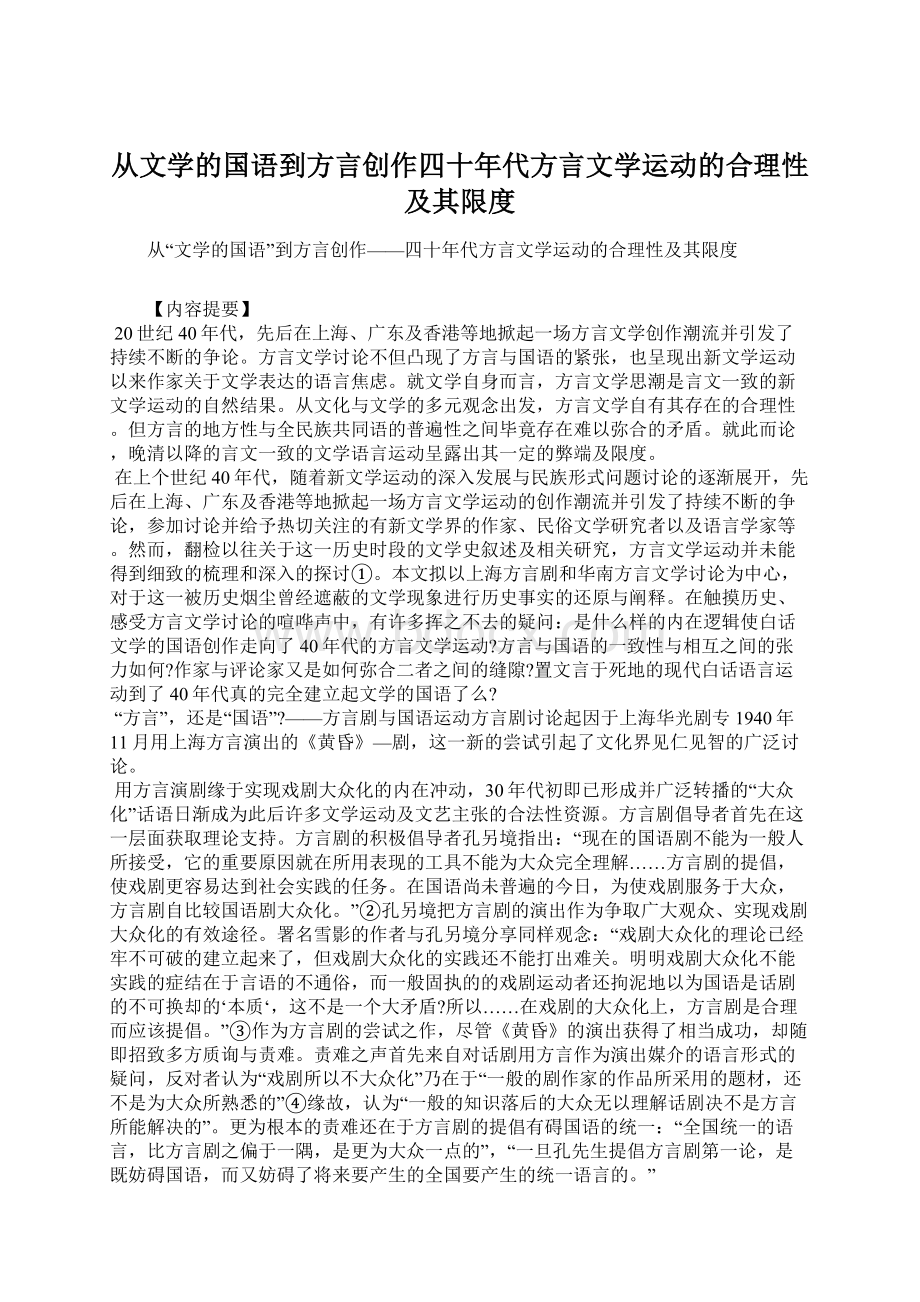
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从“文学的国语”到方言创作——四十年代方言文学运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先后在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掀起一场方言文学创作潮流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
方言文学讨论不但凸现了方言与国语的紧张,也呈现出新文学运动以来作家关于文学表达的语言焦虑。
就文学自身而言,方言文学思潮是言文一致的新文学运动的自然结果。
从文化与文学的多元观念出发,方言文学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方言的地方性与全民族共同语的普遍性之间毕竟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
就此而论,晚清以降的言文一致的文学语言运动呈露出其一定的弊端及限度。
在上个世纪40年代,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逐渐展开,先后在上海、广东及香港等地掀起一场方言文学运动的创作潮流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参加讨论并给予热切关注的有新文学界的作家、民俗文学研究者以及语言学家等。
然而,翻检以往关于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史叙述及相关研究,方言文学运动并未能得到细致的梳理和深入的探讨①。
本文拟以上海方言剧和华南方言文学讨论为中心,对于这一被历史烟尘曾经遮蔽的文学现象进行历史事实的还原与阐释。
在触摸历史、感受方言文学讨论的喧哗声中,有许多挥之不去的疑问:
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使白话文学的国语创作走向了40年代的方言文学运动?
方言与国语的一致性与相互之间的张力如何?
作家与评论家又是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缝隙?
置文言于死地的现代白话语言运动到了40年代真的完全建立起文学的国语了么?
“方言”,还是“国语”?
——方言剧与国语运动方言剧讨论起因于上海华光剧专1940年11月用上海方言演出的《黄昏》—剧,这一新的尝试引起了文化界见仁见智的广泛讨论。
用方言演剧缘于实现戏剧大众化的内在冲动,30年代初即已形成并广泛转播的“大众化”话语日渐成为此后许多文学运动及文艺主张的合法性资源。
方言剧倡导者首先在这一层面获取理论支持。
方言剧的积极倡导者孔另境指出:
“现在的国语剧不能为一般人所接受,它的重要原因就在所用表现的工具不能为大众完全理解……方言剧的提倡,使戏剧更容易达到社会实践的任务。
在国语尚未普遍的今日,为使戏剧服务于大众,方言剧自比较国语剧大众化。
”②孔另境把方言剧的演出作为争取广大观众、实现戏剧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署名雪影的作者与孔另境分享同样观念:
“戏剧大众化的理论已经牢不可破的建立起来了,但戏剧大众化的实践还不能打出难关。
明明戏剧大众化不能实践的症结在于言语的不通俗,而一般固执的的戏剧运动者还拘泥地以为国语是话剧的不可换却的‘本质‘,这不是一个大矛盾?
所以……在戏剧的大众化上,方言剧是合理而应该提倡。
”③作为方言剧的尝试之作,尽管《黄昏》的演出获得了相当成功,却随即招致多方质询与责难。
责难之声首先来自对话剧用方言作为演出媒介的语言形式的疑问,反对者认为“戏剧所以不大众化”乃在于“一般的剧作家的作品所采用的题材,还不是为大众所熟悉的”④缘故,认为“一般的知识落后的大众无以理解话剧决不是方言所能解决的”。
更为根本的责难还在于方言剧的提倡有碍国语的统一:
“全国统一的语言,比方言剧之偏于一隅,是更为大众一点的”,“一旦孔先生提倡方言剧第一论,是既妨碍国语,而又妨碍了将来要产生的全国要产生的统一语言的。
”
大众化问题是一个无须争辩的自明前提与实现目标,在这一集体认同的框架之下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大众化——用方言还是用国语?
即使是用方言,那么它的限度何在?
这正是方言剧倡导者不得不面对的,倡导者坚信:
“方言剧的提倡不但不会妨碍国语剧的发展,反而帮助了它的发展。
这等于方言文学的提倡不但不会妨碍国语文学的统一,反而帮助了它的统一。
”⑤至少在表面看来方言与统一的国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与分野,那么,方言能够促进国语的统一的内在根据与正当性何在?
方言剧倡导者则认为:
“为了消灭方言而发展的方言,不仅没有降低今天的国语地位,而是人工促进了语言交融的过程,更符合了语言从分歧到统一的科学法则。
”⑥方言剧倡导者坚信方言与国语之间的一致性,而反对者却较多关注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起初为求观众了解和发生兴趣,不妨用方言演出,但是到了一个相当时间,必须改用国语;因为我国的地方辽阔,言语不同,以致影响民族团结力,所以我们的政府一再推行国语运动,话剧既是教育大众的工具,那么负起推进国语运动,也是它的神圣职责之一⑦。
在此,方言剧讨论早已溢出涉及戏剧演出方式的文学语言框架,却关涉到现代语言运动中方言与国语复杂关系的思考。
也许方言剧创作及演出的尝试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一开始就与语言运动密切相连。
值得注意的是:
把吴天的国语剧《被迫害的》改编成方言剧《黄昏》的改编者倪海曙,当时在孔另境主持的上海华光剧专担任方言口语课程,出于尝试演出的需要改编成方言剧。
倪海曙在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积极推行者,与国语罗马字运动相比,由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更多取鉴苏联的经验似乎带有左翼激进的色彩。
不论是国语罗马字运动还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倡导与实践者有多么深刻的矛盾分野,二者都是以改进“难读、难记、难认”的中国方块汉字实行拼音化为宗旨的语言文字运动。
上海的中国语文社于1939年年底创办的《中国语文》月刊即是以倡导拉丁化新文字为主要目标的语言刊物,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向来以刊载新文字理论为主,极少讨论文学问题的刊物于1941年的第3、4期合刊竟以大量的篇幅登载了“方言剧讨论专号”。
仔细阅读这十多篇所谓方言剧讨论的文章,其实“讨论”的色彩并不明显,并没有像前文论及的围绕《神州日报》、《中美日报》、《青年戏剧》等讨论所形成的众声喧哗的局面。
专号的文章则大都承认方言剧的提倡是势在必然,并从方言与国语的统一、方言剧的语文建设性等角度论证方言剧存在的历史合法性。
方言剧的提倡不仅出于对文艺大众化的自觉要求,同时也是对以北方方言为主的国语统一运动的有意矫正与反思。
在有的论者看来,方言剧是“从国语的牛角尖以外去找寻丰饶的原野”的新的尝试
我敢大胆的说,一个没有方言的戏剧是“死”的戏剧,是不真实的戏剧,今日我们的话剧观众,当他们看到一个舞台上的典型商人,车夫,乞丐,或乡下佬,也说着一口挺漂亮的“国语”,大概在心里总不会忘记这“到底是做戏”的吧?
……真正“人”的戏剧,是一定在“标准国语”以外的,一定要方言的,因为我们在实世界里有方言的存在。
⑧
这位署名为易贝的论者拟设了两组相互对立的概念——方言/标准国语以阐述方言文学的持久生命力与其应运而生的历史必然性,这似乎延续了“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中胡适及其追随者关于白话/文言的语言思路,只不过把一个带有时间色彩的文言白话问题转换成更具空间与地域色彩的方言国语问题而已。
其实,关于方言与国语问题在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初就已产生,只是沉潜于文言与白话论争的强势声音之下显得微弱而已。
当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宣判文言的死刑、定白话为文学创作之正宗,这种言文一致运动一旦落实到不同作家的创作实践即产生许多必须切实面对的具体问题。
胡适认为“国语的标准决不是教育部定得出来的,也决不是少数研究国语的团体定得出来的”,⑨而是文学家造就的,他通过考察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以论证“文学的国语”的合法性。
但中国的情形似乎更为复杂,由于国土幅员辽阔而历史地形成了语汇及语音有重大差别的方言区域,来自这些不同语言区域并试图反映该区域民众生活的作家所面临的语言书写困窘值得关注。
倘若真如胡适所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⑩,那么言文一致的新文学运动走上方言文学之路应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
新文学初期,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语言资源要么到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要么在大量译介的西洋文学的范本中寻求,惟独缺乏对民间资源及方言口语的采取——虽有刘半农诗歌创作对江阴方言的看重,这并非主流。
胡适极为明确地指出创造新文学的次序在工具上应“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等,在方法上“只有一条法子:
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着做我们的模仿”11。
胡适的追随者傅斯年针对白话文学的提高与发达在1918年底也提出类似的主张,他认为白话文除“留心说话”之外,还应找出一宗高等凭借物,这高等凭借物“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技……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12尽管欧化的国语文学在模仿西洋方面取得了一些实绩,但毕竟与本土语言资源的相对隔绝难以被一般人接受。
撇开守旧派的反对不论,即使新文学内部质疑欧化的声音也接连不断。
13这种对欧化语体的不满在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及大众语讨论中达到极致。
瞿秋白批评“五四”以来的文学是“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
”14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产生的新文学是“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
”15
当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把文学从言文脱离的文言的泥淖中救出,又一次跌进言文再次脱离的欧化泥潭,那么,针对这种言文再次脱离的情况,如何纠偏补弊呢?
倘若真正要彻底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言文一致,只能是以地方方音进行文学记录、以地方方言进入文学书写。
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的第一次新文字代表大会呈露出这一对方言书写重视的讯息,同时伴随着对统一国语的不满与反省。
大会决议中明确指出:
“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
所以不能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并积极主张“在各方面研究中国的方言,扩大地来发展这个研究工作。
”16重视方言调查问题是在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中逐渐兴起,当初主要出于对地方民歌的记录研究、歌谣采集整理的需要,鲜有人注意到方言调查对建立“文学的国语”可能产生的巨大作用,而周作人却是一个例外
平心而论,国语文学之成立当然万无疑义,但国语的还未成熟也是无可讳言。
要是只靠文学家独立做去,年深月久也可造成“文学的国语”,但总是太费力,也太迂缓了,在这时国语家便应助他一臂之力,使得这大事早点完功。
我觉得中国语体文的缺点在于语汇太贫弱,而文法之不密还在其次,这个救济的方法当然有采用古文及外来语这两件事,但采用方言也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方言调查如能成功,这个希望便可达到,我相信于国语及新文学的发达上一定有不小的影响。
17
联系到胡适关于以文学促进国语的单方面主张,周作人对方言土语的看重及对国语运动者努力的认可似乎是有意的纠偏,可惜,这一清醒的潜在对话在五四以后语言欧化浪潮中并未引起时人的充分注意。
30年代逐渐展开的新文字运动既是对方言拉丁化的提倡又伴随着对国语统一运动的普遍质疑:
“国语罗马字崇奉北平话为国语,名为提倡国语统一,实际上是北平话独裁……叫一个上海的、福州的或广州的苦人同时学北平话又学罗马字,那几乎是和学外国话一样的难。
”18这是1935年12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征求各界人士签名中极富鼓动色彩的宣言,签名者广泛涉及文学界、艺术界、语言学界等社会文化界的多方要人达688人。
如果不过多考虑纠缠于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之间的意气之争,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对方言及地方区域的重视的确得到了时人广泛认同。
尤其在1931年“九?
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渐加剧的局势使民族救亡这一普遍的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地方性问题,用地区的方言唤起该地区的民众比用相对隔膜的不成熟国语也许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正是在这一点,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
正如一位论者所言:
“新文字的提倡是一个必要的救济;尤其在这宣传与教育刻不容缓的抗战时期,这更是值得利用的宣传工具。
”19
现在回头重新检视上海方言剧创作及其讨论,会相对获得较为清晰的历史图景,因而我们也约略获知为什么一个专门刊载语言文字改革的刊物会对方言剧这一文学新形式产生那么多异乎寻常的热情关注——他们正是认识到方言剧的语文建设性:
“方言剧有它的必然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