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支西地兰.docx
《最后一支西地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后一支西地兰.docx(2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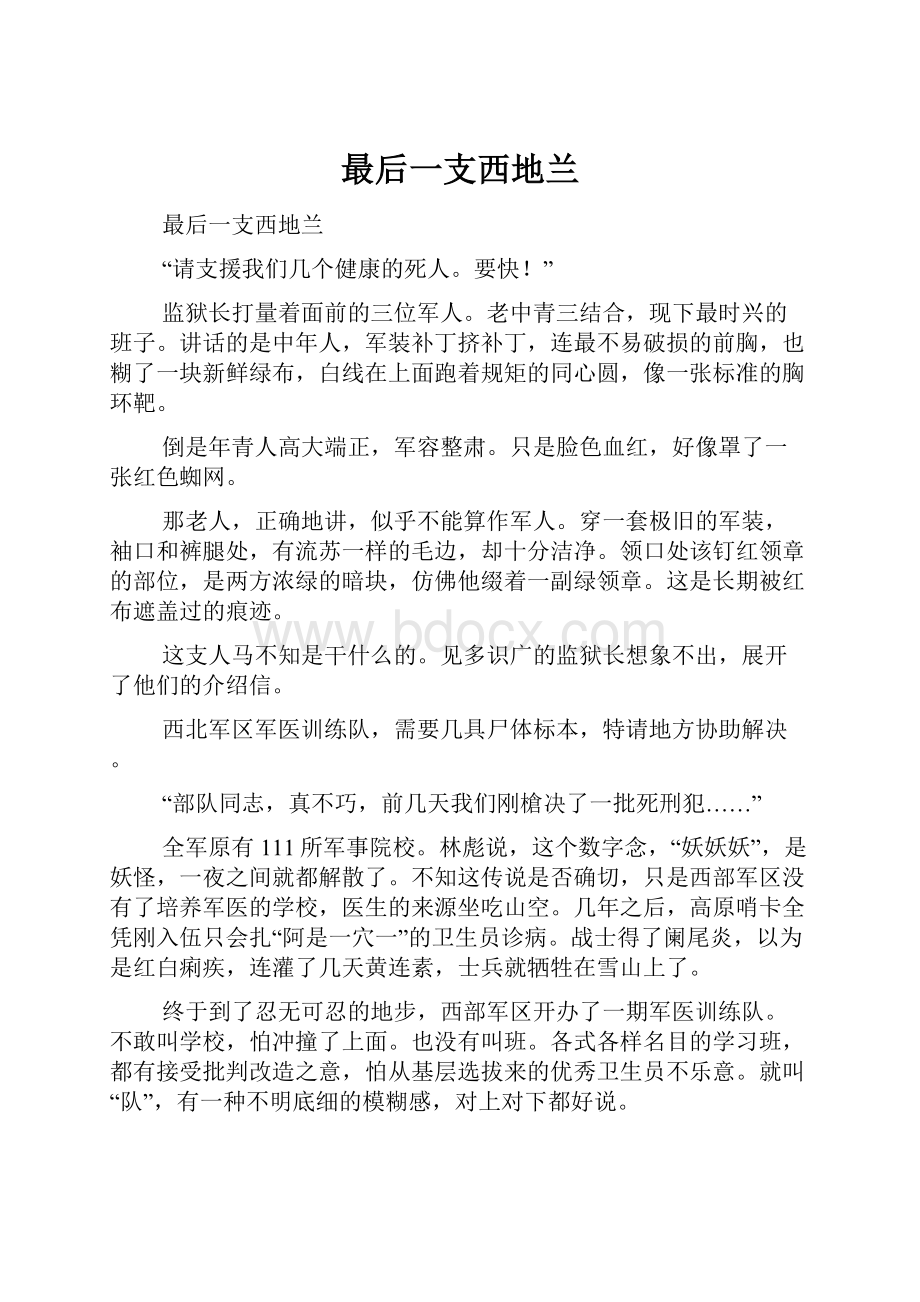
最后一支西地兰
最后一支西地兰
“请支援我们几个健康的死人。
要快!
”
监狱长打量着面前的三位军人。
老中青三结合,现下最时兴的班子。
讲话的是中年人,军装补丁挤补丁,连最不易破损的前胸,也糊了一块新鲜绿布,白线在上面跑着规矩的同心圆,像一张标准的胸环靶。
倒是年青人高大端正,军容整肃。
只是脸色血红,好像罩了一张红色蜘网。
那老人,正确地讲,似乎不能算作军人。
穿一套极旧的军装,袖口和裤腿处,有流苏一样的毛边,却十分洁净。
领口处该钉红领章的部位,是两方浓绿的暗块,仿佛他缀着一副绿领章。
这是长期被红布遮盖过的痕迹。
这支人马不知是干什么的。
见多识广的监狱长想象不出,展开了他们的介绍信。
西北军区军医训练队,需要几具尸体标本,特请地方协助解决。
“部队同志,真不巧,前几天我们刚槍决了一批死刑犯……”
全军原有111所军事院校。
林彪说,这个数字念,“妖妖妖”,是妖怪,一夜之间就都解散了。
不知这传说是否确切,只是西部军区没有了培养军医的学校,医生的来源坐吃山空。
几年之后,高原哨卡全凭刚入伍只会扎“阿是一穴一”的卫生员诊病。
战士得了阑尾炎,以为是红白痢疾,连灌了几天黄连素,士兵就牺牲在雪山上了。
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西部军区开办了一期军医训练队。
不敢叫学校,怕冲撞了上面。
也没有叫班。
各式各样名目的学习班,都有接受批判改造之意,怕从基层选拔来的优秀卫生员不乐意。
就叫“队”,有一种不明底细的模糊感,对上对下都好说。
训练队的楼房盖在山里,附近有一家野战医院和附属药厂。
就地取材,请老师,看病人,都很方便。
好比猪圈都修得离伙房不远,取天时地利人和。
从工兵部队一抽一了个“硬骨头连”的连长来当队长,让在药厂劳动改造的反动学术权威焦如海,边改造边讲课,医训队就算正式组建起来了。
开学典礼就设在走廊里。
灯泡小,悬得又高,幽暗得像条半夜的胡同。
本来可以借野战医院的礼堂,队长认为大可不必。
工兵连队经常在旷野中训话,他的嗓门早练出来了。
他穿着那件有许多线轨的军装:
“我们人民军队的第一支工兵部队,是在安源煤矿创建的……”这是他最喜一爱一的装束。
学员们坐在小马札上,双脚并拢,手半握空心拳,团在膝盖上,很乖的样子。
新来乍到,都想给领导个好印象,腰板笔直,绿油油的,像一畦雨后的菠菜。
“工兵的‘工’字,左边加个绞丝旁,念什么?
”队长征询地望着大家。
“念‘红’!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走廊里有回声,显得地动山摇。
“对!
”队长兴奋地肯定,好像这是一个多么高深的问题。
气氛就是这样烘托上去的,这番话是他的拿手好戏,哪该停顿,哪该夸赞大家,他都烂熟。
“工兵一颗红心永向党。
我再问,‘工’兵的工字,左边加个三点水,念什么?
”
他满怀信心地等待着。
有了上面那段一操一练,现在该是更加众志成城的“念江”的吼声,可惜,卫生员们似乎觉得这题太容易,恐领导另有深意,回答错了怕惹大家笑,居然没人吭声了。
只有一个脸细小如韭菜叶的小兵,不知深浅地答道:
“念江。
”他叫翟高社。
有文化水平的兵就是难带!
明明认得,却偏不答话,晾你一个难堪。
队长心里很恼火,改了程序,不再启发诱导,兀自说下去:
“念江。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靠的是工兵。
右边若加个力呢?
念功,要为人民立新功,右边加个弯弓呢?
念巧,工兵就是要心灵手巧……”
所有的人都在这一瞬给队长起外号叫“工兵”,不叫这个名字,对得起队长的一片痴情吆!
人们开始分心。
工兵突然停止讲话。
他的耳朵善于分辨任何异常响动,成功地预防过重大塌方。
寂静使大家都听到两枚牙齿清脆叩击的音响。
一个漂亮的女兵,在玩自己的指甲刀。
一精一巧的琵琶形指甲刀,运用杠杆原理,剪下女孩珠贝似的指甲,然后小锉又细细打磨,银似的粉屑飘然而落。
工兵用沉默警告女兵,真正的士兵会对这种反常的宁静噤若寒蝉。
女兵却毫不在意地继续修理指甲,仿佛那是一段象牙。
“快别挫了!
领导正盯着你呢!
”一个黧黑面貌的男兵,在这一触即发的时刻,奋不顾身地通知女兵,并且英勇地挪动了一下马扎,企图用铁器的响动掩护小锉的声音。
他叫郁臣。
“你好好坐着吧!
我是成心不想听他罗嗦。
”女兵一撇嘴。
“你给我站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
”工兵气咻咻地把花名册翻得像雨打芭蕉。
“咦?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梅迎,你不是6床吗!
”女兵笑嘻嘻地站起来。
前排的学员回过头去,在走廊幽暗的黑绿底色之上,浮动着一张像葵盘一样鲜丽明亮的脸庞。
后排的学员只看到两根又细又长的发辫悬在柳条一般柔韧的腰间。
萎顿的学员们立时振作起来。
工兵的说教已经使他们搞不清,自己将来是坑道作业还是给人治病。
工兵愣在那里,6床这个悲惨的名称,使他的右臂又火一辣辣地疼痛起来。
那是他勇排哑炮时受的伤,住进梅迎所在的医院。
所有的女hushi戴上口罩都一模一样,工兵分不清她们的区别。
但他应该记得梅迎,梅迎曾专门守护过他三天三夜,梅迎打针一点不疼。
工兵张口结舌,但他很快将自己从病号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梅迎,你坐下吧!
军人要服从命令,再玩指甲刀,我就没收。
”
这一次梅迎很听话,乖乖把指甲刀藏了起来,指甲刀上镶着一块一精一致的少女浮雕,曲线玲垅。
这种图案,现在几乎属于黄色的范畴,真叫工兵收走了,你到哪里去找!
“现在我把教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姓焦,焦如海。
你们就叫他老焦好了。
”叫梅迎一气,工兵忘了自己说到哪儿了,索一性一进行下一项。
从暗影里摇摇晃晃走过来一个人,戴两页绿领章。
天下竟有这么瘦的人!
两颊猛烈地向里收缩,好像一颗子弹洞穿腮部,将所有的肉都掳走了。
纸一样菲薄的皮肤,敷在嶙峋的骨茬之上。
双耳到高一耸的鼻梁之中,是两个深陷的坑。
一眼望去,仿佛脸上不是七窍,而是九窍。
“一妈一呀!
这还能当大夫!
不等把病人医好,自己先就瘦死了!
”翟高社吐吐像小狗一样鲜红的舌头。
工兵的话,叫大家费琢磨。
部队是最讲究长幼尊卑的。
一般都是官衔高的首长谦虚地说:
你们就叫我老某好了,透出官兵一致的亲一热。
其实谁敢叫他老某呢?
还是要叫某首长的官阶。
大家都是正规军来的,自然懂得这规矩。
工兵这番指示,明摆着要大家不必尊重焦教员。
“我是牛鬼蛇神。
”焦如海讲第一句话。
走廊里极静。
尽头的厕所里有水管滴水,很长时间才坠下一滴。
不单因为老焦是牛鬼蛇神,还因为他讲这话时的安宁。
“大家也不必四下打听我的事,那会影响你们听课。
我的罪行是解放前在日本读医科大学,抗日后回国,参加了国民党军,当过医学教官和医院院长。
官至上校。
国民党溃败后,被收编入解放军。
现在是反动学术权威,接受改造。
队长,我有些站不住,能否给我张椅子?
”焦如海双手杵着讲台,嘴唇苍白,像扇死贝。
看样子不像是装的。
工兵想给他椅子,又想,自己还站着同大家讲话,他就想坐下?
准是摆臭架子,显示自己不周一般。
他冷冷地说:
“你咋娇气了?
听说批斗你的时候,让你撅一着,三四个小时你都撅得挺标准,怎么退步了?
”
焦如海说:
“那是批斗,这是讲课。
”
工兵说:
“讲课比批斗轻省多了!
哪有百斤扛得,八十斤反倒扛不得!
”
焦如海说:
“要是现在斗我,也还站得下来。
不是要我讲课吗?
力气要用在脑子和嘴巴上,腿上腰上就没有那么多劲了!
”
工兵气愤得直哼哼。
心想这一精一老头子硬是该斗,知道要用他的一技之长,马上就摆谱拿搪。
罢!
忍了。
为了让学员们早点把老家伙肚里的墨水掏出来,椅子就椅子!
郁臣看出工兵的心思,起身搬来椅子。
工兵看这小伙挺有眼神,决定让他当班长。
老焦坐了椅子,脸色稍好些:
“大家除了学习上的事,不要同我讲话。
见了面,也不必同我打招呼。
”
工兵插了一句:
“特别是有关边防站国境线的情况,当着焦如海,一句也不要谈论!
”
梅迎真替她的6床难过,就算需要这样如临大敌,也不必当着老焦说。
焦如海很平静,仿佛工兵说的是另外的人:
“现在,我要把同学们的文化基础,摸个底。
”
走廊内一阵騷动。
招收学员时只说要路线斗争觉悟高各方面表现好的,并没提到文化水平。
怎么反动权威竟敢考试?
大家便去看工兵。
工兵倒挺支持焦如海这一手。
他在连队时就经常考核风钻手、装填手的,要心中有数吗!
“大家不必紧张,不过是问几个化学元素符号。
说出10个就算及格,我就知道你起码是念到初中了。
”老焦说着,翻开花名册。
“翟高社。
”
学员们东张西望,竟没人站起来。
“我再念一遍:
翟高杜。
”
“你才‘瞿’呢!
我叫翟高社!
”韭菜脸的小兵气愤地站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叫圆素,什么叫方素,就知道艰苦朴素!
”他越怕叫到自己,越偏叫到自己,料着老焦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便耍起赖。
老焦想是自己眼花喊错了他的姓,才惹得小兵不高兴。
说:
“对不起。
空气中含有的这种成分叫什么?
”老焦用毛笔管一般细的手臂,在空中画了一个圈。
“零。
”翟高社毫不迟疑地说。
大家哄堂大笑。
“你读过几年书?
”老焦手僵在半空,走廊里的穿堂风,将他的袖筒吹得像个鱼膘。
“高社高社吗,我成立高级社那年生人,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上小学四年级。
”
1966年,像一副普遍的凝固剂,少年们那时读到几年级,便永远地停止在那里,不再长大。
“那你怎么能学医生呢!
”老焦深深地叹息。
“我根本就不想学医生!
你不想要我,正好!
我这就打起背包一皮回家!
”翟高社高兴得双脚一蹦高,差点踩坏了小马扎。
翟高社说的“家”,不是指乡下的父母,而是自己的老部队。
他爹是木匠,自小耳濡目染,也会吊个线扯个锯。
到了部队,领导说你年纪小,恐怕吃不了连队那个苦,当个卫生员吧,等二年大白馒头把个头撑起来,再去摸爬滚打。
当了卫生员,也就会搽二百二什么的。
看见装药的柜子挺肮脏,就用废罐头箱子板打了个新柜。
领导见了,说你这么热一爱一本职工作,正好有个地方要培训医生,就定了让你去吧!
翟高社稀里糊涂来了。
心想既然领导对咱挺好的,还不如回去好好表现,过个一年半载,有招土木建筑的训练队,自己再去可不美气,强似在这里听一个反动老头念神念鬼!
“翟高社,你给我坐下!
”工兵一嗓子把翟高社钉在马扎上。
焦如海指着一个满脸血红的学员说:
“你是从喜马拉雅山、岗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全军区最高的哨卡来。
”
那学员站起身来,脸红得像要沁出一血珠:
“我叫岳北之。
您怎么知道?
”
“你的脸色就是高原病的招牌。
我去过那个边防站。
”
“我们那儿经常因为高原病死人,我愿意好好学一身本领。
”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
岳北之初到平原,被过多的氧气灌醉了大脑。
自学过的化学元素符号,像是浑身沾满粘一液的活鱼,看着鳞光闪闪,待要去捉,滑一溜溜的尾巴一甩就不见了。
学员们都是从各部队来的,基础不一样。
从医院来的,就像富家子弟,见多识广,把医学名词念叨得跟他们家亲戚一般熟络。
从小地方来的则透着可怜。
一个边防站,拢共就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槍,就算每人都生过病,病得都还不重样,你才见过多少病种呢?
当医生是门经验科学,见过同没见过,就是不一样!
学员丛中响起了窃笑声:
不会就坐下算了,站那戳电线杆子,逞什么能!
岳北之不服气,他镇定一下自己,开始说:
“Na钠,K钾,P磷,Ca钙……”
一共说了9个,再也说不出来了。
嘴唇涨得发紫,补充说:
“C碳……”
“你已经说过了。
好了,坐下吧!
”老焦向他示意。
充其量,这个学生不过是自学了些医学知识,如此而已。
但岳北之顽强地站在那儿拧着眉头苦苦思索。
因为高原缺氧而滋生出的过多的红血球,像蜂群一样撞击着他的血脉。
他一遍又一遍重复筛选自己的记忆……
“怎么还有这么死心眼的人!
要是叫到我,一口气能说出50个。
”郁臣炫耀地对梅迎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行!
可梅连不想同他争辩,她真心为红脸汉子着急。
谁都有这种非常窘迫又不肯认输的时刻。
她把嘴唇嘟成一个圆筒,对着岳北之:
“呜——呜——”像一只焦虑的猫。
可惜岳北之完全不看她,冥思苦想。
郁臣倒是看懂了,恨不能用手把梅迎的嘴捂上。
漂亮女孩对另一傅孕子有好感,是令人气愤的事。
梅迎百般无奈,猛地扯了一下岳北之裤腿,岳北之一低头,看见梅迎笔直地竖着手指,直指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什么?
岳北之狐疑地抬起头。
天花板上有一枚灯泡,像一颗黄澄澄的鸭梨。
在梨核的部位,有曲折而闪亮的灯丝。
“w——钨。
”
岳北之终于回答出了第十个元素符号。
考试很糟,大家心中忐忑不安,预备挨先生批。
他们不敢叫“老焦”。
大部分是农村来的孩子,对师长有一种遗传来的敬畏。
也不敢叫“焦教员”,因为队长已明令不准。
他们找到一个折衷,称他“先生”,这个词在当时绝不像后来那样风光,它有遗老遗少的腐朽气息,又隐含一着曲折的敬意。
全凭呼叫人当时的口吻,对大家都方便。
工兵也做出老母(又鸟)护小(又鸟)的姿态。
谁要是想把他的兵赶走,他先叫他滚蛋!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糟糕水平的医学生!
老焦缓缓站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对你们进行考试。
以后,这样的考试……”
他略微顿了一下,所有的同学都在心里续上了他的半截话:
“……还要进行多次……”
“以后,这样的考试,我再也不会进行了。
我也不会提问。
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
”他把花名册还给工兵:
“我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名字。
”
医学,是需要天才的。
现在,人家随手塞给你一把谷,你不知道哪一颗能长成栋梁,哪一颗会半路枯萎,你当然可以仔细分辨,就像一个音乐大师去看琴童们的手。
但是,你是一个野人,你不知道有什么野兽在半路等着你。
云彩下了雨,哪怕只有几滴,你除了把种子洒出去,别无选择。
“既然是开学典礼,我送同学们一句话:
桐油罐子装桐油。
这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我学医之时,我的老师送给我的。
”焦如海准备离开。
“桐油罐子装桐油”,什么意思?
“你那老师是日本人吧?
”工兵追问。
不。
中国人。
一位能生死人、肉白骨的老中医。
”
二
老焦每天踩着上课铃声走进来,不带讲义,佝偻着腰,不看任何人,侧坐在专为他预备的椅子上,对着教室的门讲课,仿佛他随时要从那里走出去。
平心而论,他的课讲得极好,深一入一浅一出,字字珠玑。
不过,听他的课很累。
他从不板书,黑板洁净得如同少女的乌发,学员们只有全神贯注,埋头笔记,像是记录重大案件的法院书记员。
岳北之感冒,撕下一张纸,敷在脸上,哗地擤擤涕。
课问,翟高社走过来,指着笔记本中间的空白说:
“你赔你赔!
”
“赔什么?
”岳北之不解。
“赔笔记。
你的脸有一平方米吗?
用那么大一张纸,声音像甩炸药包一皮,害得我老长一段没记下来。
”翟高社本来就无兴趣,抱惯锤刨的手,写起字来就是不惯,借机把责任一股脑地嫁给别人。
岳北之到了平原,反而生病。
好像贫寒人家子弟,突然大鱼大一肉,不适应。
慌着要给翟高社补笔记,钢笔又没水了。
提着钢笔囊到窗台上去灌钢笔水。
部队什么都是供给制,小号暖壶那么笃实的一瓶墨水,敞开供应。
不想梅迎一把拦住他:
“你看这墨水是什么牌子?
以前用的是什么牌子?
”
瓶签上一只大一鸟,张着孔明羽扇般的翅膀,连跑带颠。
至于上回灌的什么墨水,他一门心思用在学习上,哪里记得!
只有憨憨一笑。
“是北京牌!
你不记得了?
那个华表多气派!
”梅迎对自己家乡的饰物被人如此轻饰,表示偌大不满。
岳北之很抱歉。
墨水吗,只注意过是蓝的还是红的。
“牌号不同的墨水混在一起会产生沉淀,这是化学基本知识!
”梅迎很着急,好像那是驼鸟牌砒霜。
岳北之的大脑袋钢笔拢共才值一块来钱,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刚才被梅迎轻微触过的手指,异样跳动,仿佛扎了一根刺,他不愿拂这位美丽女兵的意,窘急地问:
“那怎么办?
我到水房去洗洗笔。
”说着要跑。
梅迎一把拉住他,“马上就要上课了,哪里来得及!
”她掏出一支苹果绿色的小钢笔,”我这支还是北京牌墨水,先援助你好了。
”不由分说,拧开笔帽,往岳北之的大脑袋笔尖里对水。
两支笔舌一舔一在一起,一滴又一滴幽蓝色的墨水,如钟一乳一石的眼泪,缓慢地滴注着,从纤巧的果绿色坠入粗旷的黑色。
很难说梅迎为什么对这个红脸汉子产生了特别的好感。
也许因为他来自三山交汇的高原,也许因为他的成绩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很快要超过成绩最好的梅迎。
也许只因为他从不理她。
纤巧的笔舌吐出一个大而稀薄的蓝泡,好像就要从中钻出一只蓝色的小螃蟹。
岳北之对着翟高社说:
“谢谢!
我赶紧帮你补上,千万别落下课!
这么好的先生讲课,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你我这种乡下孩子,恐怕听不着。
”并不看梅迎,脸却又像回到了高原。
郁臣看见梅迎关切岳北之便有气,对岳北之说:
“你的高原病,我在书上看到了一个治法。
”
岳北之边抄笔记边说:
“这病到了平原,不治也能慢慢好。
”
“我就不信你不想好得更快一些?
告诉你——把血放出来,输点盐水进去,血自然就稀释了,你这一脸的一精一神焕发才能彻底好。
”郁臣一脸揶揄的笑容。
“我以为什么高明主意呢!
整个一个恶治!
蒙古大夫!
”翟高社大叫。
岳北之疾速抄写、无暇答话。
焦如海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像一根孤零零的输液架子,挑着一套清洁而破烂的军装,自动在地面滑行。
即使在正午的陽光下,在人声鼎沸的教室里,也有一种鬼魅似的感觉。
“懂吗?
”他问。
“不懂!
”翟高社抢先答话:
“你看这书上的人眼珠,明明是圆的,怎么画的像座桥?
”
那张图挺漂亮,彩色的。
可你真是想象不出,人人都有的黑眼珠,掉到纸上,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学医生不是学数学,必须要有实物。
老焦去找工兵。
工兵正在帮炊事班改造炉膛,力争把每顿饭的人均煤耗再降下两钱。
满面尘灰烟火色,用雪白的眼球看着老焦说:
“这我早想到了。
到野战医院去实习。
”
妇产科外平日拥滞大肚子孕妇的长椅子上,坐着像刚出炉的面包一皮一样新鲜的医学生们。
他们浆洗一新的工作服嘎嘎作响,嘴角抿成一字形,竭力作出成熟老练的神态,恨不能在唇下粘一缕胡须。
手心里却窝着一汪汗,工作服在腕口处扣得铁紧,里头的军装袖子都捋到肘关节以上了。
今天,他们将摸胎位,听胎心,这类似隔着瓜皮判断西瓜的生熟,全凭的是手上的感觉。
大家摩拳擦掌,跃跃一试。
他们傻呆呆地坐了一个下午,没有一个产妇登门。
大肚子们一看重兵压境的阵式,互相转告,远远觑了一眼,打道回府了。
反正产前检查也不是急诊,早一天晚一天无妨。
肚里的宝贝叫这伙学手艺的一折腾,还不得早产?
“这帮老一娘一们,忒封建!
本想学一招,等日后俺娶了媳妇,有了革命接班人,咱也给她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
没想到把咱们当成日本鬼子了,花姑一娘一全藏起来了!
”翟高社没心没肺地嚷嚷。
郁臣平日把女一性一生理解剖钻研得挺透彻,今日想理论结合实际,没想到落了空,挺扫兴。
岳北之想,这一门不能实习也就罢了,比较起来还是最不重要的一科。
但愿别处别这样!
唯有梅迎高兴。
妇产科把女一性一所有的秘密都悬挂起来示众,简直令人丧失尊严。
看来女人的心是相通的,她们把自己坚壁清野了。
妇产科的医生欢送他们:
“欢迎你们再来。
我们今天难得的清静。
”
望着垂头丧气的部下,工兵拍拍手上的烟灰说:
“那号东西,有啥学的?
在我们工兵,连蜘蛛和耗子都是公的!
接生婆子干的活,血光之灾,还嫌晦气哩!
”
队伍哈哈大笑,萎顿之气一扫而光。
焦如海找到工兵:
“当医生的,必须什么病都能看。
任何一个行当,都可以挑选原料和产品,唯有医生不能。
他不能说我会看这个病,不能看那个病。
在医生手下,没有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的区别,他们只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就是——病人。
医生面对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矿藏——人的生命。
”
工兵吃了一惊。
这个瘦干老头,除了讲课,打扫楼道卫生,就是在自己的小屋里劳动改造,从来没听过他振振有词他讲出这么一番大道理。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工兵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在活人身上实习之前,必须先学习标本。
”
工兵知道标本。
岩石也有各式各样的标本,比如花岗岩,石英岩。
“你就明说要什么吧!
”工兵不喜欢绕圈子。
“要尸体。
”老焦说得很平静,就像跟熟人要一支烟。
“到哪里去找死人?
”工兵为难了,工程部队倒是常死人,可隔着多少架山把人拉到这里还不得长大尾巴蛆!
再说,塌方啦抢险啦牺牲的都是烈士,能叫你领着一伙毛孩子把人给零碎了吗!
工兵心里便怨老焦多事,让你讲课就是够宽大的了,还这么没完没了!
不过凭心而论,工兵到底是技术兵种出身,知道说十遍不如看一遍。
“我再到野战医院去想想办法。
”工兵拔腿走了。
焦如海平静地等待着。
医学院校怎么能办在这种偏僻之处呢?
医学生是一种娇贵的植物,他们应该生活在人烟稠密的大城市。
设备先进,病人众多,病种繁杂,经验才会像雪球一样迅速膨一胀。
只是,谁会听焦如海的?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
果然,野战医院说军人病故都需妥为安葬,无法供医学生们整体解剖。
当地老百姓因为地处边陲,较为闭塞,更无法接受这一要求。
简言之,无论花多少钱吧,也买不到一具死尸。
何况工兵还没钱。
“将来我死了以后,遗体供医学解剖。
”焦如海说。
工兵心想,你是当医生的,当然会自我保养。
揭发他的材料里就说他经常给自己吃药打针,随身带药,肯定大补。
纵是别人都死了,他大约也能活在世上。
别看瘦,筋道。
倘真死了解剖,肯定像劈一盘古树根。
只可惜远水解不了近渴。
“还有一条路可以试试,要行刑犯人的尸体。
”焦如海迟疑了一下才说。
如今冤案太多。
“你怎么不早讲!
”工兵高兴地一拍焦如海后背,差点把他搡一个跟头。
三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所写的那一幕。
下次再同监狱打交道的时候,工兵就独自去。
这回可惨了,盖着苫布的解放卡车,裹一着浓烈的血腥气奔驰回来。
工兵脸色蜡黄地对老焦说:
“你要的那些个,全在这儿了。
剩下的事,你看着办吧!
”说完,找个地方喝点酒压惊去了。
焦如海围着褐色胶皮围裙,戴一双长统胶皮手套,像个屠宰工人,一反平日的冷漠,风风火火进了教室。
尸体到了!
消息像野火燎着学员们的心。
真正的人体标本!
你在书本上熟知的心肝脾肺肾,全都立体地鲜活地藏在这具还微热的躯壳里。
好比你早就有了一口箱子内藏货物的清单,现在这口箱子到了。
你急于想知道箱里真像你知道的那样吗?
特别是你本人也是一口同样的箱子!
对知识奥妙探索的渴望和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使大家好奇而紧张。
“谁愿意同我一道解剖尸体?
”焦如海问。
他曾经带领过无数次医学生解剖尸体,早已激不起一丝涟漪。
但这一次,他有些激动。
已经许久没有干这个活了。
他突然想到,在他的医学生涯中,也许是最后一次。
就像一位大师的告别演出,他要借此遴选最优秀的学生,把自己的心血传给他们。
“我愿意。
”郁臣第一个站起来。
他是班长,而且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私心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不怕死亡才是男子汉的风度,他希望梅迎注意到这一点。
“我也去。
”岳北之沉稳地站起来。
他不愿意见死人,而且还是恶死。
小时候一妈一妈一就告诫他,不要穿过坟地,那里有瘴气。
可是,你要当一个优秀的医生,你必须从死人开始。
岳北之白杨一样的身躯站得很直,声音镇定而响亮,好像他一百年前就决定了此刻的挺身而出。
其实,他的内心很恐惧,他是一逼一迫自己这样做的。
许久,再没有人站起来。
焦如海刻骨铭心地伤感了。
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开始翻捡花名册。
“翟高社——”这一次,他没有叫错。
“到——”翟高社不情愿地站起来,把桌椅碰得乒乓响:
“好事咋不轮到我头上?
比如到食堂炸油条,都三回了,也不叫我去趟。
”
老焦扫了一眼,站起的都是男学生。
梅迎何等聪明,一看这情景,开始往椅子下出溜,好像那是一架滑梯。
草绿色的军装包一皮裹一着她柔软的胴一体,现在,那躯体像水一般地流去,只剩下一套蝉蜕似的衣服,摆在椅面上。
活动着的物体总是最易招致注意。
老焦没用花名册,就叫出了这个学习成绩最优异的女生的名字。
“梅迎——”他认为这是对她的一次奖赏。
“我……我不去……”梅迎不肯站起来,葵盘如同被人拦腰砍断,柔软地垂在胸前。
“为什么?
”老焦焦灼地问。
他距离年青的医学生的生涯已经太远,他不知道这个优秀的学生为什么如此退缩。
这样,她会荒废的。
按图索骥,连马都对不上号,何况是人!
“我……害怕……”梅迎老老实实地承认,显得很可怜。
“死人没有了生命,他有什么可怕的?
在这个世界上,死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活人……”焦如海一精一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