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郭嵩焘悲剧人生综述.docx
《浅议郭嵩焘悲剧人生综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浅议郭嵩焘悲剧人生综述.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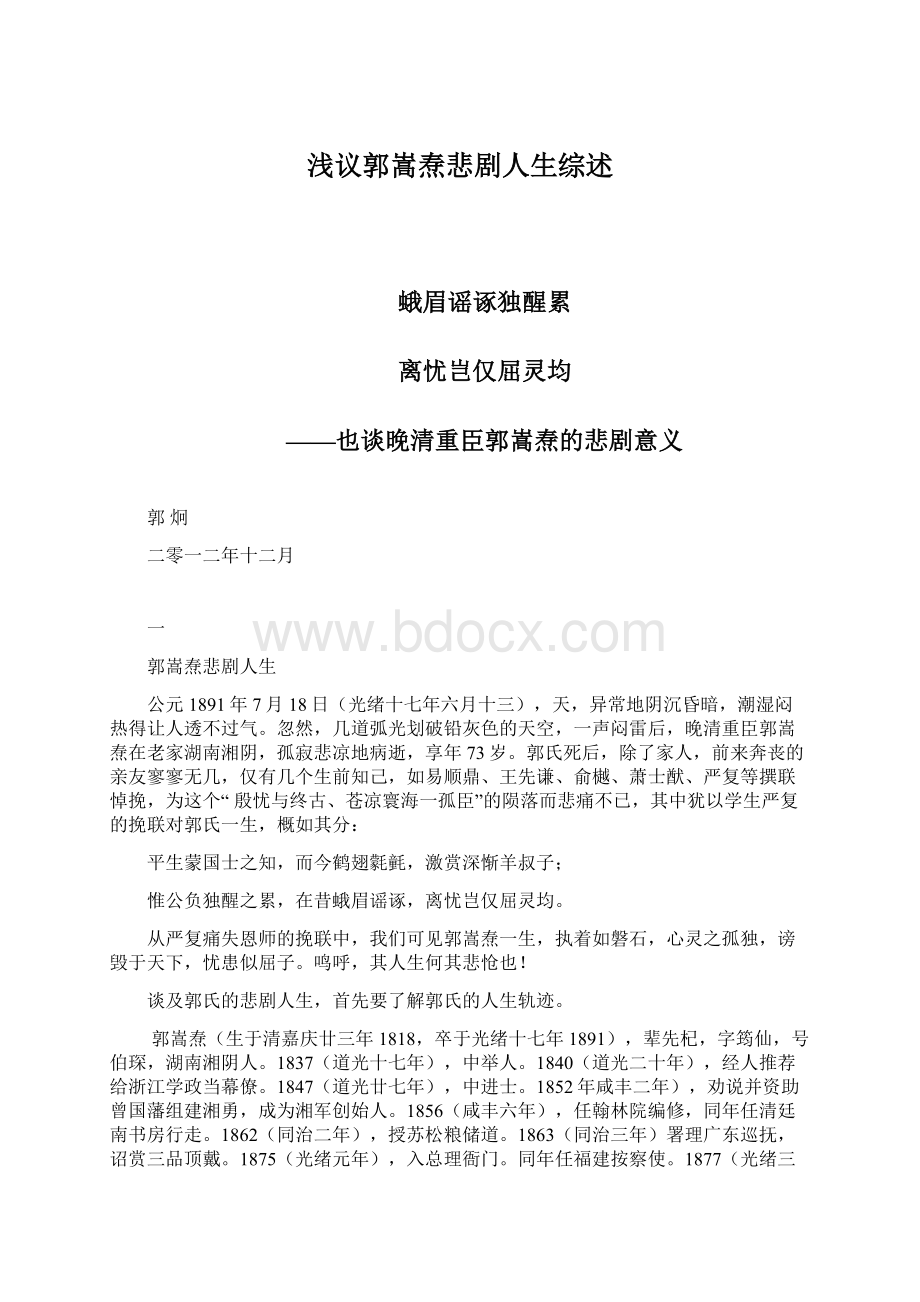
浅议郭嵩焘悲剧人生综述
蛾眉谣诼独醒累
离忧岂仅屈灵均
——也谈晚清重臣郭嵩焘的悲剧意义
郭炯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一
郭嵩焘悲剧人生
公元1891年7月18日(光绪十七年六月十三),天,异常地阴沉昏暗,潮湿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
忽然,几道弧光划破铅灰色的天空,一声闷雷后,晚清重臣郭嵩焘在老家湖南湘阴,孤寂悲凉地病逝,享年73岁。
郭氏死后,除了家人,前来奔丧的亲友寥寥无几,仅有几个生前知己,如易顺鼎、王先谦、俞樾、萧士猷、严复等撰联悼挽,为这个“殷忧与终古、苍凉寰海一孤臣”的陨落而悲痛不已,其中犹以学生严复的挽联对郭氏一生,概如其分:
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
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从严复痛失恩师的挽联中,我们可见郭嵩焘一生,执着如磐石,心灵之孤独,谤毁于天下,忧患似屈子。
鸣呼,其人生何其悲怆也!
谈及郭氏的悲剧人生,首先要了解郭氏的人生轨迹。
郭嵩焘(生于清嘉庆廿三年1818,卒于光绪十七年1891),辈先杞,字筠仙,号伯琛,湖南湘阴人。
1837(道光十七年),中举人。
1840(道光二十年),经人推荐给浙江学政当幕僚。
1847(道光廿七年),中进士。
1852年咸丰二年),劝说并资助曾国藩组建湘勇,成为湘军创始人。
1856(咸丰六年),任翰林院编修,同年任清廷南书房行走。
1862(同治二年),授苏松粮储道。
1863(同治三年)署理广东巡抚,诏赏三品顶戴。
1875(光绪元年),入总理衙门。
同年任福建按察使。
1877(光绪三年)任清政府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
1878(光绪四年),兼任驻法国使臣。
同年,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老家湘阴。
郭氏把出使英国等欧洲国家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写成《使西纪程》,向清政府大力介绍“西洋”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政治措施,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要向西方效仿和学习的建议。
却遭到“皇上”、满朝文武以及顽固守旧势力的误解、仇视和污蔑。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等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罪名,郭氏被清廷申斥,书稿被毁。
而后又遭到其副手刘锡鸿的诬陷,郭氏无奈,因病请辞。
于1879(光绪九年)乘船抵达长沙,又遭到守旧乡绅和不明事理的百姓的谩骂和围攻,骂他“勾通洋人”、“汉奸”,并张贴大字报来侮辱他。
郭氏病死后,虽有李鸿章,王先谦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可被清廷否决。
直到义和团运动,还有人向慈禧太后上疏,请戮他的尸首谢天下。
郭嵩焘方生未死,经历了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五个时期,从他一生坎坷的心路历程来看,我们足可窥视到郭氏大起大落和大“爱”大“痛”的悲剧人生。
要探究郭氏悲剧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大致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发展背景。
16世纪—19世纪的400年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方位的转型。
在欧洲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法国革命、意大利革命、俄国农奴制改革、奥地利民族解放运动。
在美洲发生了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工人运动、废奴运动和约翰·布朗起义。
在亚洲也发生了日本明治维新等运动。
这些波澜壮阔的革命和运动的冲击波,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广泛渗透和波及,都把矛头直指那个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和集权制度。
因此,中国也不例外,晚清这个时候的“天朝帝国”,两对根本的社会矛盾分外激烈,一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于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满清帝国,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实行高压统治,激起广大汉族和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纷纷揭竿而起。
先后爆发了新疆维吾尔族、汉族人民起义;山东爆发了王伦起义;甘肃发生撒拉回民起义;台湾发生了林爽文起义;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以及广东、广西的瑶民起义和金田太平天国起义。
二是中华民族和西方列强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的帝国主义发展过渡,不断向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商品输出。
英国在1840(道光十九年)发动“鸦片战争”,其结果,大清帝国一败涂地。
清廷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之后,接着就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不断地向列强割地、赔款,中华民族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
这两对矛盾相互交织,又互为矛盾,清政府内忧外患,岌岌可危。
整个晚清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受到的震荡也格外强烈,历史赋予近代中国的严峻现实就是:
“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铁的事实表明,不改变中国的现状就无法抵御西方列强和“富国强民”。
在这跌宕起伏和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潮中,郭嵩焘生于斯,其“求实效不为虚语”,时时作为弄潮儿处于风口浪尖上,又不时被大风大浪推至深深谷底。
其最初的理想抱负到最终的失望潦落,其中大起大落和大“爱”大“痛”,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当然与他个人落拓不羁的人文情怀紧密相关,但更与那个时代的震荡和矛盾深深相连。
深刻反映出方生未死之际一个思想先行者的孤独身影和历史悲剧命运。
正如著名学者钟叔何先生说的那样:
“郭嵩焘对封建政治、文化及洋务的批判和坚持真理的态度,决定了他悲剧的人生,注定了他会在‘天朝帝国’里演出一场人生悲剧。
”
那么,郭氏的人生悲剧具体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笔者不揣浅陋,以为应该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出生商贾家传影响
笔者藏书《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有记载:
郭家是湘阴有名富室,富甲一方,致富的原因主要由于经营商业和利贷。
其曾祖父(号望湖),“善居积,富中一邑,亦乐施与。
沉厚敏捷,才气沛然有余。
”其祖父(字括榘)“性豪迈,尚气谊,然诺一语,千金不惜,乐善好施”。
其父亲家彪(字春坊)仍营借贷,“尤喜济人之急,夷然不为有无顾虑,亲故假贷,必盈其意,或相称贷,邀一言为质。
及其,辙代偿,精医,岁储药饵,供人求乞。
”可见这三代人不仅是好商人,还都是慈善家。
这三代人,在其祖父(括榘)这一辈,就立下了郭氏家族的祖训:
“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以训诫后人,要修好品德、操行和文化、知识,才是做人的根本。
同时也将这条祖训作为子孙繁衍的辈序(其祖父为“世”字辈,父亲为“家”字辈,郭嵩焘为“先”字辈)。
这几代人,虽然都读过书,但最多只读到贡生、秀才为止,并没有都走上读书做官,即“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19世纪初,湘阴所在的洞庭湖区因“北枕大江”,其商业和手工业也已经较之湖南其他地方发达,其水路、陆路也很发达,城镇已经集中聚集了一定的居民和财富,借贷资本已经同商业资本一道在经济活动中出现并发挥出积极作用,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相当发育。
郭氏家族的情形与通常意义上的“耕读传家”(以地租为经济来源,以读书做官为目的)的地主阶级不同,其封建意识和小农意识可能较少,而已具备向资本家转化的条件。
因此,商贾家庭的背景以及祖辈忠孝节义、诚信经商、正直公平和乐善好施的家传精神,不可能不对郭氏在人生道路中效礼义、尊儒教、讲诚信、守信用、重公允以及开拓进取潜移默化地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
后来郭氏进入仕大夫阶层,就有一个异乎寻常的特点,就是没有传统的“重农轻商”的思想。
这在当时“仕农工商”四民等级的时代,就连《康熙大词典》都不能有“商”字的清代,实属异类,难能可贵。
“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已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明确化。
但封建社会,这种四民划分,却逐渐发展成阶级对立。
孟子说: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这样,“学而优则仕”便成为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观。
然而,官位总是有限的。
人们都会趋之如骛往这条道上挤。
这种重“士”,轻“农、工、商”的“四民等级”始自唐代,至宋以后尤甚。
郭嵩焘对此提出了严肃批评:
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
宋儒讲经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
于是士之数视农、工、商三者相倍焉。
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
重士。
其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
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
故夫士者,国之蠹也。
……(见《郭嵩焘评传》377页)。
郭氏对冗官成灾,国家的财富被其无度地侵蚀和消耗的现状,已憎恶之极。
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四民惟农商二者为常业”和“商贾与士大夫并重”的思想。
如1860(同治元年),郭氏在写给有换帖之交的曾国藩的信中说:
用才各有所宜,利者儒生所耻言。
而汉武用孔僅,桑弘羊皆贾人,斯为英雄之大略。
1878(光绪八年)郭氏退休还乡后,还在省城长沙禁烟大会上大力提倡商贾与仕大夫并重之义,强调清政府要看重商贾,尊重商人的言行,要扶持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的主张。
并一贯主张反对轻利,批评重士,以工商为本,力主民营,建立财政税等制度。
应该说,郭嵩焘的商贾家族背景和“商贾与仕大夫并重”的思想是超越那个时代的,是前瞻社会发展的治世大略。
与他后来能够欣然接纳和吸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技法”,不无关系。
当郭嵩焘出使西洋后,对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更加明确提出了以“工商为本”的思想,而且反复强调中国发展近代工商业时,要坚持民办,反对官办或官商合办。
这些,都鲜明地反映出他商贾家庭出身以及家传影响所形成的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
(二)独立根性众必非之
《湘阴郭氏家族史全书》中有这么一个记载:
一日暑甚,先杞默坐斋中,钧公台(郭嵩焘伯父)与二三挚友纳凉阶下,相与言曰:
“先杞遇事恂恂,独其读书为文,若猛兽鸷鸟之发,后来之英,无及此者。
然观其意志,无幾微让人,岂徒欲为诸生之雄哉”。
这段记载,活脱脱勾勒出郭嵩焘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读书少年的生动形象。
其弟郭昆焘曾描述其兄:
“心直口快,往往面责之处,直与人以难堪。
”说明郭氏常常是得理不饶人,很是傲慢。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种“无幾微让人”的个性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郭氏后来的一生。
人的一言一行,真正要融入社会并不容易,尤其郭氏的独特个性,尤其在晚清这个“末”流之世,更容易动辄得咎。
郭嵩焘的一生,还特别厌恶“流俗”。
那么,什么是“流俗”呢?
对此,郭氏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447页)中有过具体描述:
君子之拘于见闻,染于气习者,皆谓之流俗。
俗人之时所趋而流焉,,君子之所恶也。
往在京师,见一事之得失,一人之用舍,俄而毁,俄而誉,俄而怒,万口附会,众目睢盱,不移时而议论又变,举国呶呶然互相辩论,问以事情之原委,漠然不知。
袭古人之一说以为准则,问心以古人之事势得失奚若,今日之时令因革奚若,茫然无以为应。
凡此者,皆所谓流俗是非也。
三代以下,事之得失,人之贤否,蔽于流俗之议论。
不得其实者多矣。
论天下事以识为主,识力透出人一层,自能剖析是非得失,不随众附会。
故欲脱除流俗气习,以读书广识为本。
隐,非议也。
人皆鹜于富贵,而独介然不屈,所以为贤。
死谏,非正也。
人皆习于避就,而独毅然不顾,所以为贤。
是二者,流俗之所惊叹,亦必有超出流俗之心,乃能及之。
若夫观理道之精微,揽天下之奥秘,审事于几先,创论于独见,言之而人以为忤,行之而众以为疑,君子人与,流俗乌能测之。
庄生曰: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超出流俗者,入流俗波靡之中而不失其守者也。
可见,所谓“流俗”乃指一种社会风气。
这种社会风气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但却并不一定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潮流。
这种社会风气往往以种种“议论”、“辩论”的形式反映出来。
如郭嵩焘时代一些顽固派仕大夫利用古人“夏夷之辩”的观点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就是为此。
这说明,“流俗”是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思维,它不但存在普遍的百姓之中,而且可以反映到社会上层的仕大夫之中,而郭氏讲的“流俗”,更多地是指社会上层的一些偏见。
郭嵩焘以为,要避免习气,就要提倡正气。
他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447页)中还说道:
天下之嚣气靖而后天下之正气倡。
能知此者难矣。
此当大臣之事也。
气之嚣也,气之靡也,一动而嚣然,一反而靡然矣。
大臣养吾气以致天下之气,忠孝廉节之道其常,言论事功之标其准,而何有嚣哉。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理解,所谓“气之嚣也,气之靡也”,是说表面上气势汹汹,其实是色厉内莅。
郭嵩焘讲的“养气”,就是要“集义”,就是要用“义”去战胜和克服流俗的习气。
至于那些阿谀逢迎之流,郭氏更是十分鄙视。
1859(咸丰九年),郭氏奉咸丰之命,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
但僧格林沁这位蒙古王爷根本不把郭嵩焘这个汉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漠。
而郭氏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上他“无幾微让人”的个性,认为自己是皇上亲自派遣,并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不是“随同效用”,所以咽不下这口气。
一个是居功自傲,一个是秉公执政,针尖对麦芒,二人合作极不愉快。
还在同年,郭氏奉咸丰之命赴山东查办税收案例,由于郭嵩焘生性耿直,清廉方正,严于律己,不谙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得罪诸多官员反被参劾,倍受歧视和冷落。
他感慨万端:
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
在返京途中的馆驿题一绝句于墙上:
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
(见《天朝首使》430页)
可见,郭氏坚持自己独立之个性,对当下蛮横傲慢之辈和阿谀逢迎之流的鄙视和不屑。
当年,李鸿章欲保奏郭嵩焘到江苏做官,而深信郭氏之秉性的曾国藩就不赞成。
说:
“筠公芬芳悱恻,然著书之才,非繁剧之才也”。
知道郭嵩焘的傲骨秉性,且喜议论,好批评,极易对现实不满,近乎屈贾之流。
他一生受到挫折和攻击很多,但他独特之个性,坚持“成仁成义志犹坚”,无怨无悔,一贯“凭仗文章自写神”,决不趋同“流俗”,决不向“流俗”妥协。
他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第544页):
君子之行道也,进退揆之义,得失喻之心,审乎其时而安乎其分。
见乎其大而道乎其常,如是而已。
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
大道隐而小惠,眩流俗之耳目。
而立身之大节与行道之实功两无当焉,君子弗尚也。
“冯妇攘臂下车”的故事出自《孟子·尽心下》。
冯妇善搏虎,后来成为“善士”。
一次,他在野外见许多人在打虎,虎负隅顽抗,众人不敢近前。
众人见冯妇,都迎接他。
冯妇也捋起袖子,欲与众一道打虎。
这一举动,博众喝彩,却为士人讥笑。
士人为何讥之?
因为冯妇既为“善士”,就不该从众操旧业打虎。
郭氏引用这个典故表明他决不像冯妇一样趋于流俗,只推崇“确然持定论”的人。
我们还可以从郭氏《戏书小像》中给自己画的图像,也可见郭氏的独特之个性和不流俗的性情。
世人欲杀是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摘自湘潭郭兆芳敬书郭嵩焘《戏书小像》)
1865(同治四年),郭氏奉朝廷之命出任广东巡抚,也因其办事认真,为人耿直,丝毫不流俗,加上清政府官场体制的缺陷,官场倾轧,自然就与同僚,如两广总督毛鸿宾及继任瑞麟等合不来,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于愤慨中写诗一首:
生平自信我亦颇,出门顾影与人左。
万事异趣谁肯亲,但求无忤不官可。
起骚鬓发犹觰沙,门前官鼓颇三挝。
居高致早吾当耻,拂衣归隐湘江搓。
(见《郭嵩焘日记》第二卷286页)
个性较强的人一般都较自信,自信好了,还要加上一个“颇”,当然就会“与人左”。
由于郭氏很多方面都有自己独立见解,所以总是与人“万事异趣”,“但求无忤不官可”,宁可辞官不做,也决不流俗而移其志。
这种独特个性,真可谓“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故郭氏一生很长时间处于“孤愤塞五洲之间,众醉独醒”的清高孤傲之中,安之若素。
然而在这个蝇蚁蚊蚤横行的社会,“行高于众,人必非之。
”
(三)维新改革专制不容
近代史上的湖南,在中华大地上占有非常奇特而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守旧固然守得很凶”,另一方面“趋新也趋得很急”。
在“趋新”方面,各个时期相继出现了一些最大胆、最活跃的“开风气之先”的风流人物,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刘蓉、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谭嗣同等,这些“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溪径,不为古学所囿”的精气面貌和惊世骇俗的言论行为,使得举国上下都为之侧目,有如黑暗的长夜将灿烂的明星反衬,显得愈加夺目。
陈独秀先生曾把湖湘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湖南人的精神”。
这已成为今天“湖湘文化”的精髓。
而郭嵩焘在这些“开风气之先”的风流人物中,更是“义不淑群,行以厉色,开一代之风气”。
郭嵩焘是一位近代探求中国富强而倍受攻击的洋务思想家,是清廷政府派遣“夷狄”的首位外交使节。
清政府在面临“千古之变”的危局下,郭嵩焘看到大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后深感痛苦,看到西方列强与清王朝强弱对比悬殊深受震动,从而自觉走上探索富强之国的道路。
客观地说,郭氏的富强观是从1840(道光九年)开始的。
这一年,他经人推荐到浙江学政当幕僚,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炮把大清打得一败涂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屈辱的印象,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后,他感到西方枪炮之威力动摇了“天朝自大”的观念。
后来,在其长期的政治生涯中,通过反复观察和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富强观和思想体系,直至穷尽一生。
1875(光绪元年),郭氏就向光绪上奏了《条陈海防事宜》,在这个奏折中,他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器“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
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效仿西方政权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郭氏一时名噪于朝野上下。
郭氏一生忧国忧民,一直在艰辛执着地思考着他的富强观。
他在致好友曾国藩的信中深邃地指出:
富强者,秦汉以后所称太平之盛轨也,行之固有本矣,渐而积之固有基矣。
振厉朝纲,勤求吏治,其本也。
和辑人民,需以岁月,汲汲求得贤人用之,其基也。
未闻处衰败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富强者。
天下之乱之原,全在吏治,而其根本则在朝廷。
(见《郭嵩焘日记》第四卷77页)这样,他便将“治本”的政治改革目标更加集中地指向朝廷,具体地讲,就是直接指向皇上,其实质,就是要求大清皇上或朝廷处理好君与民,君与臣“相交维系”的关系。
对于晚清此时的腐朽吏治郭氏的批判集中于三点:
一是颟顸无知,虚骄自大;二是徇私枉法,颠倒是非;三是贪污受贿,卖官鬻爵。
改革吏治其措施就是要治吏以严,治民以宽。
循西洋政教建立法律制度,建立法治政府。
试想,这些思想和主张,从根本上将整个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都否定了,怎么不引起封建统治者的仇视和抨击。
1875(光绪元年),在遥远的中缅边境,突然发生了英国外交官与当地居民冲突被杀的“马嘉理案”。
在福建任按察使的郭嵩焘被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拟派他作为钦差大臣到英国去代清廷“道歉”,郭氏不曾料到,这一件事恰恰是他悲剧人生最致命的一步。
1877(光绪三年),郭氏临危受命出使英伦,这时的欧洲,早已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经过了工业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以及诸多社会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已走在世界前列。
面对西方国家与民同富“君民兼主国政”之气象,来自颟顸自大的大清的郭嵩焘,必然为之震撼。
郭氏一抵达伦敦,就立即将50多天行程中的见闻记录在《西使征程》中,力图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
如见到一些西方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出却秩序井然,不禁叹道:
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
还称赞伦敦:
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从途经数十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宗教信仰,铁路、电力、机器、通讯、港口、哲学、经济学、天文、地理、生物、化学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政等,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尊民”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等,他都包罗万象极尽所能地介绍,让国人尽可能知晓外面的世界,摆脱关闭锁国夜郎自大的状态。
他如饥似渴地考察“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议会)和“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他亲眼看到了西方“国政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真实情况,联想到大清政体,认为西方政体比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仰仗“君德”的做法更有保障。
接触了阿达格斯密斯(AdamSmith,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了解英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
当他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以及民风民俗,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后,他醍醐灌顶,开始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他说:
推原其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散,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
(见《郭嵩焘日记》407页)对中国秦汉以来2000多年来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他看到了西洋之国以政教为本的治国优势,发出“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于的学”的惊呼。
为了探索西洋繁荣兴盛的原因。
他通过大量考察调查,发现西洋富强的关键在教育即人才的培养,是富强之“故”。
其“故”有三:
一是西方普遍重视学问,特别是科学技术;二是实事求是的实学精神;三是十分重视学校教育。
他在日记中说:
英、法两国制造学问,穷极推求。
法国立国尤久,其学馆书籍亦驾欧洲。
以二千余里之地,称雄海外,非无因也。
日本晚出,汲汲仿而效之。
其学精且锐,日进无穷。
中国乃一以虚骄之大言当之,吾真无如此蚩蚩之士大夫和矣。
(见《郭嵩焘日记》第二卷211页)这段话说了这样一个情况:
英、法两国“穷极推求”制造学问,所以能“称雄海外”;日本虽晚出,但能“汲汲仿而效之”,所以来势咄咄逼人;而中国士大夫却仍然沉迷于“虚骄之大言”中,岂不是作茧自缚,自甘落后吗?
他在《西使征程》里发表这样的建议:
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幾者。
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
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
其择官治事,亦有阶级、资格,而所用必皆贤能,一与其臣民苦之。
朝臣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即不得安其位。
自始设议政院,即分同异二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
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
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
其风俗之成,酝酿已久矣!
(见《走向世界丛书》第27页)显然,郭嵩焘已在描绘大清帝国政治改革的蓝图了。
郭嵩焘通过对中西方政治体制的对比,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两个方面比中国封建君主专政制度优越。
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集大权于皇帝一身,不可能长久、稳定和繁荣;而西方的民主制度,把“政权公之臣庶,愈久人文愈盛”。
他说: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方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幾者。
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
一身之盛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
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
愈久而人文愈盛。
(见《郭嵩焘日记》第三卷373页)郭氏的意思是,我们有圣人,西方没有。
但我们靠圣人治国,圣人不能代代常有;即便西周有文、武、成、康四王,虽皆圣人,其治也不及百年。
西方靠民众自治,却可以推衍无穷。
另一方面,中国治国治民崇尚德治,而西方治国治民崇尚法制。
他继续阐述:
圣人之治以德。
德有盛衰,天下随之治乱。
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
西洋治民以法。
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
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
(见《郭嵩焘日记》第三卷548页)郭氏的意思是,德治是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素质的,如个人好,德操高,政治就有可能清明一些。
反之,政治则混浊不堪。
而西方民主制度重制度、重法制,把国家、人民的安危系于制度和法制之上,岂不“愈久人文愈盛?
”简言之,中西方治国治民,一个是人治,一个是法制,其优劣自然明了。
郭嵩焘将“蛮夷”政体与华夏“三代”之政作了优劣比较,显然,深深刺痛了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们脆弱的软肋,这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愤怒。
当然,郭氏的这一番比较和言论,国内对他的抵牾、谤诽,自然是一片哗然。
一些友人如曾国藩等,劝他莫谈洋务,少惹是非。
郭氏却毫无顾忌,仍诤诤呼吁:
吾谓并不见人,然固不可不谈洋务。
所以谈者,欲使人稍知其节要。
以保国有条,苟坐听其昏顽而已,不动兵则坐则削,一旦用兵,必折而印度,此何等关系,而可以不言乎?
世俗之说,但谓不知言之人不可与言。
此为无关系言之。
苟有关系,忍生视乎?
彼于中国强且逼,然其意犹然尊视中国,略无猜忌之意,诸以乃视言及洋务为忌讳,然则将听其终古错顽而莫只省也?
果可以昏顽终古,则自洞庭以南,蠢蠢之三苗至今存可也,而其势固必不能。
传曰:
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
以能使魑魅魍魉魔莫能逢之。
夫惟其知也,以先知觉后知,心先觉觉后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