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docx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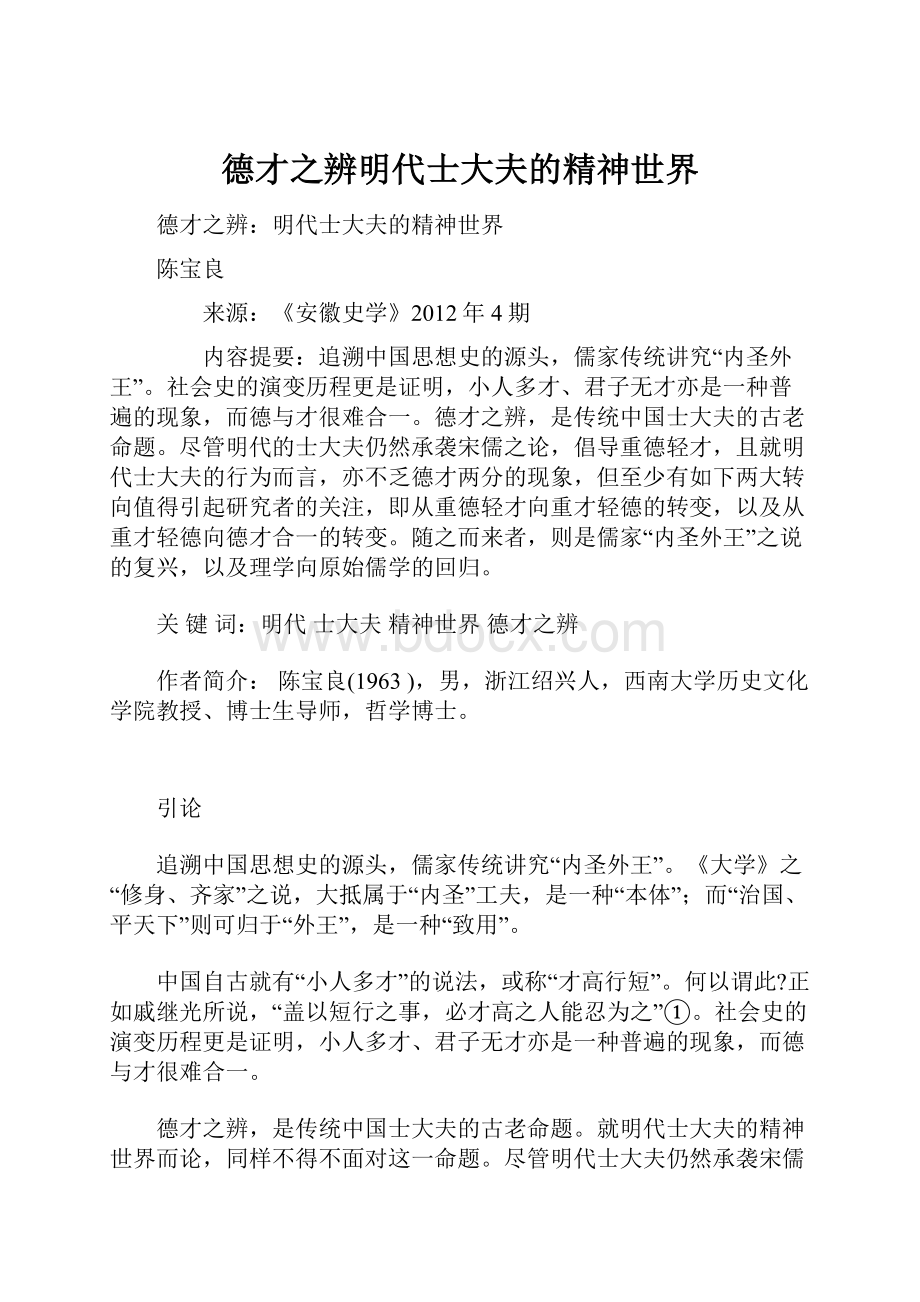
德才之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德才之辨: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陈宝良
来源:
《安徽史学》2012年4期
内容提要: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
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
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
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
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关键词:
明代士大夫精神世界德才之辨
作者简介:
陈宝良(1963),男,浙江绍兴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引论
追溯中国思想史的源头,儒家传统讲究“内圣外王”。
《大学》之“修身、齐家”之说,大抵属于“内圣”工夫,是一种“本体”;而“治国、平天下”则可归于“外王”,是一种“致用”。
中国自古就有“小人多才”的说法,或称“才高行短”。
何以谓此?
正如戚继光所说,“盖以短行之事,必才高之人能忍为之”①。
社会史的演变历程更是证明,小人多才、君子无才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德与才很难合一。
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
就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论,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一命题。
尽管明代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内多而外少”,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
随之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一、德才两分:
从“小人多才”说起
考察明代士大夫的行为史,同样可以印证“小人多才”之说,并足证德与才确实已经两分。
为示明晰,不妨选取严嵩、丰坊、钱谦益、阮大铖四个典型个案,就此问题加以深入的辨析。
严嵩在明代历史上以奸相闻名,其人品为人所不齿已是毋庸置疑。
但就他的文章来说,尤其是早期《钤山堂集》刊刻以后,还是为一些人所称道。
如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在为严嵩集子所作序中,从文章、人品两个方面,对严嵩多有称颂②。
抛开其中阿谀的成分不说,至少说明不能因人废言,这也是一种比较平实的评判标准。
严嵩在钤山读书十载,学业不为不深。
即以他集子中《禹贡直解》五条来看,简洁明畅,不作任何穿凿附会之语,完全撇去了汉、宋诸儒的固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善于说经之人。
但从严嵩其后所行政事来看,最终还是被天下后世视为“佥壬之首”③。
就严嵩之行来说,大抵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通加丑诋,认为严嵩性格中本身具有“狷隘急睚眦”的一面,不免导致残害忠良之举;另一类则多有恕词,对严嵩人格作前后区分,且对其恶行加以父子之别。
就前者来说,在明清两代,为严嵩说恕词者少,而是大多称严嵩为“獠”,甚至深以严嵩得以保全骸骨而终为撼。
明清之际学者周亮工有一则记载,基本表明了当时读书人中间对待严嵩的态度④。
更有甚者,有些记载甚至过意刻画严嵩天性中狷隘且喜欢报复的一面⑤。
尽管如此,在明朝人中尚有人替严嵩所作之恶说了一些恕语,何良俊、张燮堪称其中的代表。
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何良俊、张燮,或称严嵩“怜才下士,亦自可爱”,或称严嵩生平持论,“较多温厚和平之气,犹未见有反覆星辰、摧落一世手段”。
如何良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严嵩早年比较爱才⑥。
张燮则称严嵩早年“雅负朝宁之望”,等到代主制命,才身毁名灭,为后世所笑⑦。
其二,无论是何良俊、张燮,在论及严嵩后来人格变化及其所为恶行时,无不称之为其子严世藩所累。
就严嵩之言来说,对严嵩的文学才艺大多持一种公平之论,即不能因人废言。
如何良俊称颂严嵩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而所作之文,亦“典雅严重”,不可“以人而废之”⑧。
张燮亦称严嵩“文有古意,不类詹詹者”;“诗意兴,所钟者亦多工语”。
即使如王世贞,于严嵩有杀父之恨,并在所作《袁江流》、《钤山冈》中,模拟严嵩父子恶行,备极写照之致。
即使如此,王世贞还是承认,孔雀虽然有毒,却不能掩文章⑨。
这当然算得上是一种确论。
在“小人多才”方面,丰坊堪称是一个特例。
换言之,在众多有才的小人中,尽管其行为人所贬斥,却尚被人多所回护。
即使其行为人所斥,人们亦多持不可因人废言之论。
这是德与才的两分。
而丰坊则不同,尽管很有才,但在很多的记录中,不但诋毁其行,并且对其学问亦颇不认同。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在读《嘉靖实录》时,曾发现了一条记载,并对此发生了兴趣。
记载如下:
“(嘉靖)十七年六月,致仕扬州府通州同知丰坊,奏请上兴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
”正是从这条记载中,才导致黄宗羲鄙视丰坊的为人。
原因很简单,丰坊的父亲丰熙在嘉靖初年这场“大礼议”的争论中,因为不得嘉靖皇帝之意而遭受廷杖之责。
这就是史料记载所谓的丰坊晚节披猖,甚至在替其父丰熙所写的行状中,称丰熙谏大礼,非出本意,负国而叛父,一至于此。
丰坊既然在“大礼”问题的看法上能够背叛他的父亲,其行已是不孝如此,他又何论?
显然,人品可以决定学问。
丰坊的人品可以“怪诞”二字概之,那么学问必然也是怪诞的。
事实证明了这一切。
丰坊的胆子实在太大了,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伪造六经,或是假托出自石经,或是假托得自别传,无不是为了增加自己伪造之经的分量。
不仅如此,他还敢于訾毁“先儒”,放言无忌。
如说朱熹因为“食贫无计”,所以才卖书糊口;杨荣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之类,因为他的妻子姓朱,所以大多采用朱熹之说⑩。
云云。
从这些看法中,不难发现,丰坊希望通过掠取新说,以达到抬高自己声价与地位的目的。
当然,丰坊的五经世学,尽管多悖于大义,应该说还是自能探奇出隐,探研于六艺之旨,亦非近世所易及。
钱谦益不但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久负盛名,号称文坛宗主,且在政坛亦是一个闻人,名列东林君子之党。
然就其行为来说,终因末后一着不慎,沦为无行小人。
在清代学者中,多将其视为“有文无行”之人。
据清人方濬师的记载,入清之后,钱谦益“思欲掌枢要,专史席”,然二者全不如愿,所以郁郁不乐,“终为有文无行之人”。
为此,方氏专门引述了乾隆帝题钱谦益《初学集》诗加以佐证,云: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
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真堪覆酒甕,屡见咏香囊。
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
”(11)此诗固然迎合了清代乾隆时期重竖忠义的时风,所评亦有不公允之处,但终究还是道出了钱谦益大节欠亏的一面。
又如明末温璜,字宝忠,浙江乌程人。
他是大学士温体仁的族弟,反与东林诸公结契,名列复社第一。
温璜与温体仁的关系也就“落落”而已,但他对崇祯朝时的“阁讼”事件,颇不以复社之言为当。
当南都复社诸子以《防乱公揭》驱逐阮大铖之时,温璜就君子与小人之争有过一段公允之论。
他说:
“阮大铖为真小人,钱谦益为伪君子。
真者易知,伪者难测。
斯人得志,即小臣亦当裂麻争之,况同僚乎?
”时人并不以温璜之言为然,但清代史家全祖望相当欣赏“其言之中”(12)。
阮大铖属于“真小人”,此已毋庸置疑。
然其文学才艺,尤其是戏曲创作上的成就,确乎不可轻易加以否定。
明末著名文人王思任,甚至称阮氏在戏曲上的造诣,是继“清远道人”汤显祖而出,并称其人“肺肝锦洞,灵识犀通,奥简遍探,大书独括”。
尽管阮大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諐,渭泾倒置”,仕途并不顺利,最后“放意归田”,然其“顾曲辩挝”的创作历程,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尤其是《春灯谜》,更是被王思任称为“不减击钵之敏矣”(13)。
综上所述,在德与才的关系上,确乎存在着一种德才两分的现象,亦即“文自文”、“人自人”。
换言之,在读士大夫的文学作品时,放言高论,“无之不是古人”;然若细究其“处身居心”,其实“无之不是今人”。
正因为才艺不能出于内心之修德,无怪乎一旦身处大故,就“遑问是何世,是何时,相与安之,不复有所不堪于中心矣。
”(14)可见,德才必须合一,方可成就一个士大夫完美的精神世界。
二、重德轻才:
士大夫精神的偏蔽
从儒学的源头来说,“内圣外王”之说是其根本。
入宋以后,理学崛起,将“内圣”之学发挥到极致,进而导致对“外王”之学的忽视,出现过分“重德轻才”的偏蔽。
这就是说,宋代道学之流,显然存在着一种不通时务之病,亦即缺乏治理国家的干练之才。
他们今日谈“诚意”,明日说“正心”,反而将一切兵戎、财赋紧要之事看成是“缓图”。
毫无疑问,明代士大夫是宋代道学的继承者。
于是,在德才之辨上,他们亦无不遵奉重德轻才之说。
以诸葛亮为例,宋代理学大家程颢就有“孔明有王佐之心而道则未尽”之论。
对此,明人吴廷翰加以适当的发挥,称必须先有“天德”,然后可以谈论“王道”,认为“孔明于天德恐未尽,其于王道自是不纯,益州之取是也。
”孔明虽贤,犹未达到“天德”之纯(15)。
王云凤在论及“大节”(德的层面)与“功业”(才的层面)的关系时,尽管主张“体用”之学,但仍偏向于“大节”之本体。
他认为,诸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为士君子立身之本,可以称为大节。
若是“大节不立”,就会“万事皆颓”,纵使“有功业为世倚赖,不过权谋术数,塞漏补罅于一时者耳。
”(16)
才士与节士各有偏重。
士负才性,大多不羞于小节,反而喜欢功名耀于史册,或者根据时势获取卿相一类的高位,务必使自己达到大富大贵。
而节士则一反于此。
他们一意孤行,喜欢抗论正义,即使空室桑枢,含水蔬食,但内心还是快乐的,而且在当时也获得了很好的荣誉。
如刘绘在任职六科时,曾与当时任职翰林的唐顺之讨论过“才”与“节”的关系问题。
按照唐顺之观点,还是重视节义。
他说:
“节胜于才,犹为得已。
而失节,又奚云才?
”在唐顺之看来,凡是节义之士,尽管才无所见,但必定被人归入“清流”。
因此,士人之廉,犹如女子之洁。
针对此说,刘绘提出了质疑。
刘绘的证据来自文天祥其人。
他认为,像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正气贯日,但从他平日的行为来看,却是喜欢豪奢,并且纵情于声妓。
面对这样的质疑,唐顺之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说:
“古人德业,自有可学与不可学。
如文山,吾当学其正气,其豪奢声妓,吾绝勿学可也。
”唐顺之的看法,得到了罗洪先的附和。
罗氏写信给刘绘,其中有言云:
“士大夫立事,务求本心。
若任才性,而不求之本心,则事虽极奇伟,终归变诈。
”(17)
当然,最为典型的案例还是明末大儒刘宗周与崇祯皇帝关于“功利”的争论。
刘宗周一生最为反对的是“功利”二字。
他曾告诉自己的弟子张履祥说:
“学者最患是计功谋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
”他认为,功利二字,其弊病主要在于“事必欲求可,功必欲求成”。
因此,他主张,“事无求可,功无求成,惟义所在而已矣。
”(18)为此,刘宗周与崇祯帝曾就才能与操守的关系作过讨论。
如在督抚的选拔上,崇祯皇帝认为:
“督抚必才守兼全方可。
”而刘宗周却认为:
“须操守为主。
”对此,崇祯帝反驳道:
“大将另是一段才干,非区区一操守便可胜任。
”(19)明末另一位大儒黄道周将刘宗周之学评为“伊尹之学”,他立论的依据如下:
“伊尹以天下为己任,其原本于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
今但知刘先生一介不取,一介不与,不知其自任天下之重也。
”(20)这固然是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但反映的确实不是刘宗周的实情。
即使刘宗周心中自任以天下,但他决无治天下之才。
黄道周与刘宗周齐名,号称明末两大儒。
从黄道周与崇祯帝关于清、廉问题的讨论,亦已足证道周过分看重士大夫个人所具清、廉一类的道德,而轻视治国之干才。
这又是一个典型案例,不妨详引如下:
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十八日,崇祯皇帝在召见大臣时,有感而言,感叹朝廷腹心耳目之臣,遇事不肯担当,举劾率由情贿,积弊难革。
然而所谓的“清操”之臣,“却又不通方,是古非今,用之恐误事,弃之又可惜”。
当时的少詹事黄道周听后,深不以为然,就官员之德“清”问题上奏,云:
“‘清’之一字,谓惟天清明,人能清则自明。
舜举皋陶,汤举伊尹,便是舜、汤清而明处。
”崇祯皇帝听后,有所反驳,道:
“圣如伯夷才叫做清,若曲谨小廉只叫做廉,不叫做清。
”黄道周还是不服,继续争辩道:
“清、任、和便是智、仁、勇,知人爱人,有体有用。
”崇祯帝驳斥道:
“你说清、任、和便是智、仁、勇,从来未闻。
清、任、和是圣人体段,智、仁、勇是圣人造道工夫,如何扭作一团?
”黄道周答道:
“智即是清,勇即是任,仁即是和。
清、任、和是体,智、仁、勇是用。
然惟天下〔子〕得其全,臣子得其偏。
”崇祯帝随之又反驳道:
“这清是居官之美德。
只有一种人清而无用,自傲逐非的。
朕不是指卿,卿勿得错认。
且天子得其全,何以见得?
”黄道周答:
“《书》云:
宣聪明,作元后。
皋陶言,九德而为天子,六德而为诸侯,三德而为大夫。
这不是天子得其全,臣下得其偏?
”但崇祯帝还是不依不饶,公然说道:
“三德九德,不过是臣不〔下〕强分之目,归美其君之词。
若必有九德而后为天子,自古至今无亡国之君矣!
且孔子具有全德,当初如何不做皇帝?
”(21)说已到此,黄道周确是无言以对,不得不一时语塞。
尽管黄道周抬出大舜、成汤一类的圣人,用来制约崇祯帝过分重才之论,这是其敢于直言之处,然其过分重视儒家道德之论,不但不能应崇祯帝求治之急,就当时的时势而论,确乎亦是一种迂阔之见,无益于治效。
清初人邵廷采在论及明代士大夫时,有云:
“明世士大夫矜负廉节,所绌者才。
然民心士俗,绵延几三百年醇厚者,廉节维之也。
”(22)这一论断的后半部分,即明代民心士俗,能够保持三百年之醇厚,均靠士大夫的“廉节”维系,因无法得到印证,可以置而不论,但说明代士大夫“绌才”,可谓一语中的。
众所周知,明代士大夫绌于才干,甚至庸劣、迂腐可笑,堪称通病。
这有很多例子得以证明。
如史载桐城人给事中孙晋在朝房遇到张凤翼,自言其乡恐怕要遭寇患。
凤翼却说:
“公南人,何忧?
贼起西北,不食南米,贼马不饷江南草。
”闻者粲然而笑。
身为“枢臣”的张凤翼,却说出如此不通世务的可笑话,不免让人对明代士大夫之才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再来看杨嗣昌。
他是代熊文灿出任督师的,前往彝陵“讨贼”,军队驻扎在彝陵,竟然一月不进,只是取《华严经》第四卷诵读,“谓可诅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闻”(23)。
在传统社会中,士君子处世,贵有“特操”。
所谓特操,既是符合儒家一般道德原则的操守,却又不失独立精神。
为了一己之利,舍却操守去徇人,即使幸而有得,也会被世人鄙薄;若是不幸而不得,则不但被世人所鄙,就连自己也会后悔莫及。
然即使是儒家士大夫一贯所持的“特操”,在江盈科看来,在操守与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那些变操以徇人之辈,其实就是一种不知“命”的行为。
换言之,一个人是否官运亨通,按照江盈科的观点,都是命中注定的事。
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他以嘉靖初年“大礼议”时入阁的四人即张璁、桂萼、夏言、严嵩四人为例,进一步加以说明。
此四人,人品不同,事业亦异,但从根本上说都是靠议礼才得以见用。
江盈科认为,这也是四人命中应该拜相。
当时有人见到这四人因议礼而拜相,从而效仿,但终究没有所得。
如丰坊、桂舆、江汝璧三人,虽然也变易自己操守而徇人,却最终一无所得,在江盈科看来,均是一种命(24)。
三、重才轻德:
士大夫精神的转向
在士大夫普遍应和重德轻才之论时,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重才轻德之论,这大抵说明士大夫精神开始出现一些转向。
按照宋代儒家学者的观念,德胜才可以称为“君子”,而才胜德则称为“小人”。
若拿这种评判的标准,来论定明朝的人物,无疑会碰到一些麻烦。
就拿从永乐一直到正统年间很负盛名的“三杨”来说,既有“三杨”之称,可见他们可以齐名,应该不分轩轾。
但如果以宋儒的君子、小人观加以评判,杨士奇尚不脱君子之名,而从杨荣的所作所为来看,倒与“小人”相近。
因为在明朝人当中,就不乏有人称杨士奇“正而不谲”,称杨荣“谲而不正”。
史实已经证明,杨荣在人格上与杨士奇颇有相异之处。
史称他能够“随机应变”,无愧于唐朝的姚崇,但在行为上确实“有所不检”,如在母丧期间,并没有很好地在家守孝服制,而是多次从征。
先是跟随明成祖北巡,又出使甘肃。
回来后不久,又随从北征。
刚回家奔丧,又出使甘肃,从征瓦剌。
在丧礼上,杨荣并不能很好地遵守儒家的孝道与礼教。
毋庸讳言,这当然是因为明成祖武断统世所致,杨荣身为臣子,也不得不尽忠而废孝,但确实也与杨荣本人的为人有所不检有关。
从这一事实来看,是否就可以断定杨荣就是“小人”。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明人廖道南的意见很能说明问题,而且颇合事理。
他说:
“国家多难,羽檄旁午,匪才勿达;上下多违,萧墙交搆,匪才勿定;丑虏窥伺,内猜外疑,匪才勿靖;奸雄僭窃,彼甲此乙,匪才勿协。
”(25)廖道南的辩解是很有道理的。
这从历史上也可以找到例子。
如陈平燕居深念,张良借箸前筹,无不都是有才而且能凭才解决大问题的人。
这样的人,称之为“小人”,可乎?
杨荣的例子足以证明,对于宋儒之论,需要作全面的清理。
随之而来者,则是批评宋儒缺少事功之论的兴起。
凡是有志于事功者,往往不喜欢宋人议论,甚至对宋人之学弃去不顾。
霍韬即是其中一人。
他曾有论,认为宋代的士大夫,“动拥虚名,动多浮议”。
当他们尚未被重用之时,世人多以“大用期之”。
一旦被用,亦只如此而已。
他又说,宋儒的学问,动称“师三代”,然致君图治之效,则不及汉、唐。
汉、唐两代的宰辅虽不知学,尚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
宋儒则“高拱浮谈,屈事戎狄,竭民产一纳岁币,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后已。
”为此,他得出结论,即宋朝士大夫的“浮议”,“甚于战国之横议”,而“流祸之烈,甚于晋之清谈”(26)。
一旦宋儒之罪得到清算,随之而来者,则是士大夫通过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诸如曹操、刘备、贾似道、王安石、岳飞等人的重新评骘,谨慎地确立他们的重才轻德之论。
如何良俊曾与赵贞吉一起讨论过曹操这个人物。
赵贞吉将曹操比喻为狮子一类的“西方之兽”,称狮子“终日跳踯,无一刻暂休”,是因为其“猛烈之气,不得舒耳”。
所以,只要“与之球以消耗其气,遂终日弄球,忘其跳踯”。
曹操之所以“举动轻躁”,亦是因为其“胸中猛烈之气不得舒也”(27)。
历来论三国人物,无不喜欢刘备,而厌恶曹操,孙权次之。
然钱澄之则认为,此“甚非平论”。
为此,他对三人加以重新论定。
他认为,世人将曹操视为“奸雄”、“汉贼”,主要基于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当董卓之后,天下尺寸皆非汉有,曹操之天下,均“取诸强梁之手,非取诸汉也”。
而曹操迎接天子,定都许昌,奉为共主,堪称“存炎灰于既烬,本以为义也”,而并非挟持天子。
换言之,曹操通过“百战以取天下”,未尝“以天子令号召天下而有之也”;即使挟天子以号召天下,当时谁又能奉天子令者?
可见,曹操“使天子拥虚位,不犹愈于天下之弃天子如弁髦”。
基于当时情势,钱澄之进而认为,若说辅佐天子,以兴汉室,不但是孙权所不欲,即使刘备亦无真有此心。
他们三人,目的归趋一致,即“各自欲王耳”。
刘备号称“宽仁忠信”,其实并非“本志”,而是有其目的,即借此“以图反操而济事耳”。
就此而论,孙权称刘备“猾鹵狭诈”,并非虚辞(28)。
基于此,张岱才得出如下之论:
“奸雄”在诗文书画方面的特殊才艺,可以“忏悔恶人”。
他认为,尽管曹操、贾似道属于千古奸雄,且“罪业滔天”,但“诗文中之有曹孟德,书画中之有贾秋壑”,尽可“减却一半”罪业(29)。
由此可见,诗文与人品,有时并不一致。
明人王格替王安石翻案,并非仅仅是一种平情之论,更是与重才轻德之风桴鼓相应。
平心而论,王安石确乎可称旷世逸才,一般的议者只是见到王安石非薄宋制,创立新法,最终导致党同己、排异议,酿成靖康之祸,于是进而加以诋诃,视若寇雠。
揆诸王格之论,大意如下:
一是王安石堪称言行合一之人。
通常世俗之士,学古纂言,“窃仁义道德之腴,以悦泽其辞”,借此而取禄位,自视亦甚高,“虽孔孟无以过之”。
及考其所树立,往往脂韦势利,“视其言百不一酬”。
反观王安石,其学“采摭百家,蹂躏群籍”,多有世儒所未窥者。
变法之端,其实早已见于少作。
一旦官居要津,受知于君主,于是就“尽举而力行之”。
较其言行,亦略相符。
就此而论,确实如古人所谓的幼学壮行,并非“苟为富贵”而已。
二是王安石有言:
人之廉洁而直者,非终然也,规有济耳。
又谓:
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才,虽陷于不义,而犹能自强以列于后世。
这是安石重才轻德之论。
就此而论,王格认为,“宋之末造,群奸并进”,固然可以称为“介甫之所遗”,而宋朝国势所以不竞,究其原因亦在于此。
但王格认为,并不能因此而将宋朝之亡,一概归罪于王安石。
宋至徽宗、钦宗之时,天时人事,已有不得不亡之势。
三是南宋时朱熹将王安石列于“名世”,苏伯衡称道古今之士,自左丘明以下,仅20余人,而王安石名列其中。
可见,唯有如此论定安石,方可称为“得其平”(30)。
岳飞在与金兵接战之时,连接朝廷班师金牌。
那么,面对如此境遇,岳飞应该如何选择。
这在明清的学者群中,同样引起了争论。
争论大体可以概括为文人与理学家两派:
以魏禧为代表的文人,大多主张岳飞不应班师,而是应以国土恢复大业为重,这在传统的观念看来,是“拂乎理之正”。
换言之,文人立论,往往有其好逞偏见的一面。
以应撝谦为代表的理学家,则主张岳飞应该受命班师,以得万世君臣之正(31)。
若换一角度来看,这一争论同样牵涉到才与德的关系。
理学家主张以德统才,他们看重的是一个作为臣子必须服从君命的德,至于恢复山河的功业则在其次。
但文人主张以才统德,在山河破碎的境况下,恢复山河,补金瓯之缺,才是最为重要的头等大事。
至于君命是否服从,尚在其次。
通过对历史上的奸雄以及其他有争议之人与事的重新论定,明代士大夫确立了以才统德之论。
如李贽就认为,真正的“大才”之人,其“小知处必寡”,其“瑕疵处必多”,唯有真“具眼者”才能识得(32)。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主张“使功不如使过”,重视小人之才。
小人有治国干才,在明人中王琼称得上是典型一例,且易引起争议。
史称尚书王琼,奸贪险恶。
早在正德年间,王琼就交结权奸,浊乱海内,罪不容诛。
入嘉靖之后,桂萼等用事,王琼让自己的女婿、家人潜住京师,日夜钻刺,贿赂桂萼等,数至巨万。
于是,桂萼连章力荐,而当时张璁在内阁,亦从中主之,王琼得以起用。
桂萼、张璁起用王琼的依据,就是“使功不如使过”。
换言之,王琼虽有过,但才不可弃(33)。
二是面对有德无才的庸官与有才无德的小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
显然,面对日益多难的国势,明代的士大夫宁可选择有才的小人。
这从明末李清的记载中可以得到印证。
据载,范复粹大拜入阁之后,李清前去拜谒,见其家中庭放置一案,上面供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
而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中,诸如张四知、蔡国用等,均庸碌无才。
为此,李清就对同年申佳胤说:
“若辈纵不能益国,或不至于害人。
”而申佳胤却说:
“不然。
彼无识又无力,闻所票拟或驳,则心手俱战,极力附会,恐庸之害甚于忮也。
”(34)申佳胤“庸之害甚于忮”之说,足以证明代士大夫的德才论出现了新的转向,亦即对有才小人有所宽宥,却对平庸君子多有苛责。
四、从“内圣外王”到“德才合一”
在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但凡遇到如何确立人物的评价标准时,无不引起了才智与操守关系的争论。
照理说来,德是才之所资以发,亦即德为才之本原;而才则为德之所赖以充,亦即才为德的扩充与放大。
两者理应是相辅相成。
然而,中国的很多读书人,也就是“士君子”之流,平常高谈阔论,语细探玄,说得头头是道,却全不切实际,到了紧要关头,并不适用济事。
所以,明代民间称那些拙钝之人为“不中用”,而称那些昏庸之人为“不济事”(35)。
尽管是当时民间谚语或口头语,却一语中了那些读书夸夸其谈者的要害。
这就牵涉到一个如何看待原始之儒以及儒之“用”的问题。
按照明初学者宋濂的观点,儒者原本不但讲究操守,而且其功业也是斐然有成。
根据世俗之见,通常称儒者“少功”,这在宋濂看来,这些人并非真正的“儒者”。
为此,他以商汤以伊尹而兴,周朝以周公而兴为例,借此证明真正的儒者,同样具有“大功”(36)。
当然,儒学史与政治史的演变事实证明,在明代也存在着一些“俗吏”之见,就是认为儒者懦缓偾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