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性》女性形成与处境分析观《灿烂千阳》女性角色特质.docx
《从《第二性》女性形成与处境分析观《灿烂千阳》女性角色特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从《第二性》女性形成与处境分析观《灿烂千阳》女性角色特质.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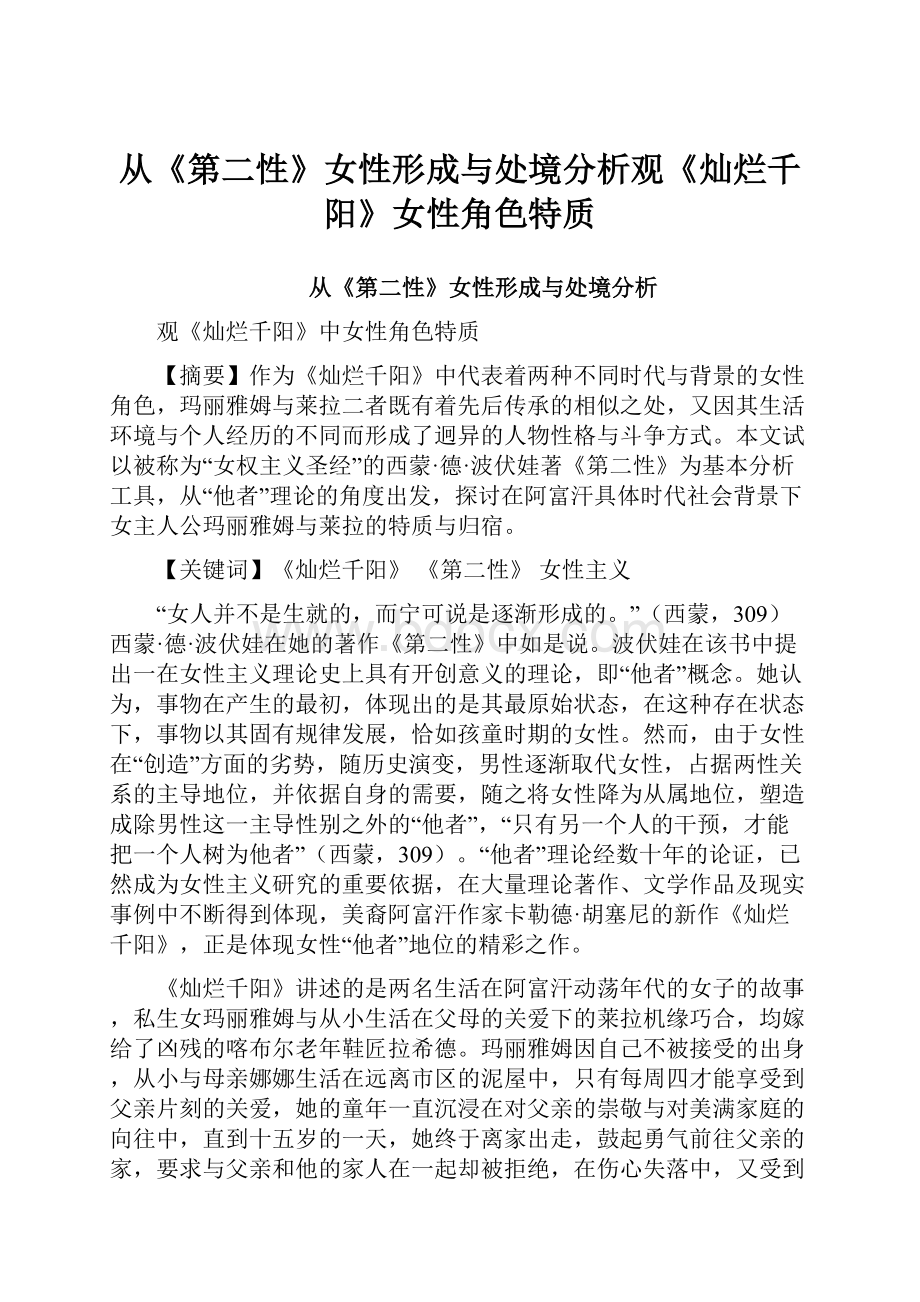
从《第二性》女性形成与处境分析观《灿烂千阳》女性角色特质
从《第二性》女性形成与处境分析
观《灿烂千阳》中女性角色特质
【摘要】作为《灿烂千阳》中代表着两种不同时代与背景的女性角色,玛丽雅姆与莱拉二者既有着先后传承的相似之处,又因其生活环境与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形成了迥异的人物性格与斗争方式。
本文试以被称为“女权主义圣经”的西蒙·德·波伏娃著《第二性》为基本分析工具,从“他者”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在阿富汗具体时代社会背景下女主人公玛丽雅姆与莱拉的特质与归宿。
【关键词】《灿烂千阳》《第二性》女性主义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西蒙,309)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如是说。
波伏娃在该书中提出一在女性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即“他者”概念。
她认为,事物在产生的最初,体现出的是其最原始状态,在这种存在状态下,事物以其固有规律发展,恰如孩童时期的女性。
然而,由于女性在“创造”方面的劣势,随历史演变,男性逐渐取代女性,占据两性关系的主导地位,并依据自身的需要,随之将女性降为从属地位,塑造成除男性这一主导性别之外的“他者”,“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西蒙,309)。
“他者”理论经数十年的论证,已然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依据,在大量理论著作、文学作品及现实事例中不断得到体现,美裔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新作《灿烂千阳》,正是体现女性“他者”地位的精彩之作。
《灿烂千阳》讲述的是两名生活在阿富汗动荡年代的女子的故事,私生女玛丽雅姆与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关爱下的莱拉机缘巧合,均嫁给了凶残的喀布尔老年鞋匠拉希德。
玛丽雅姆因自己不被接受的出身,从小与母亲娜娜生活在远离市区的泥屋中,只有每周四才能享受到父亲片刻的关爱,她的童年一直沉浸在对父亲的崇敬与对美满家庭的向往中,直到十五岁的一天,她终于离家出走,鼓起勇气前往父亲的家,要求与父亲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却被拒绝,在伤心失落中,又受到母亲娜娜离她而去的打击,从此失去了亲人与快乐,被迫远嫁拉希德;与玛丽雅姆相反,幸福开明的家庭和青梅竹马的恋人使莱拉无忧无虑地成长,然而由于战火的来临,她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失去了恋人,失去了家。
此时心怀不轨的拉希德收留了她,使她成为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同在一个屋檐下,玛丽雅姆与莱拉这两个生活背景全然不同的女子在这个战火纷飞的“不可宽恕的时代”,因为政权、男权的压迫与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在摩擦中产生了“不可能的友谊”,以及“不可毁灭的爱”,最终各自坚强地成就了属于她们的勇敢与信念。
“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冲突。
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
”“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她认识、把握和发现周围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自身资源的开发也就越少,因而就越不敢肯定自己是主体”(西蒙,324)纵观《灿烂千阳》中的两名女主人公的生活轨迹,可以发现外界即“人们”对于她们所处性别的定义是两人经历与归宿差异的重要原因,由于玛丽雅姆始终被灌输自身的从属地位,故几十年如一日地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不公与压迫,直到莱拉如同沉沉阴霾中一缕阳光般地到来,使她觉醒,迸发出无穷的勇气;而莱拉所受的教育,父母亲的教导,使她勇于追求幸福生活,勇于同男权与社会的不公作斗争;同时,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她们又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判断力与主体气质,追寻属于自己的方向。
父母等亲属、同龄异性乃至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作用与反作用,最终形成了作品中女性角色个体不同的特质。
一、母权作用
作为女儿的养育者与监护人,父母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往往会直接影响处于成长期的女儿的心理认知。
父母亲将自己所持有的观点态度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这种言传身教,往往会对子女的性格形成、自身定位产生较其他任何一种影响来源更大的效力。
在一个相对传统的社会中,尤其是动荡的伊斯兰国家,大部分的父母倾向于将女儿塑造成具有“女性气质”(西蒙,309)的传统女性,希冀通过这种方式向宗教和传统表示服从,同时也使女儿获得社会普遍意义上的幸福。
在“女性气质”培养模式下成长的女性在成为母亲后,由于多年所受的家庭教育,有较大可能因思维定势而将自己的女儿塑造成同样的模式;而父亲作为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存在,却因自身成长方式的差异,可能在传统与所受教育的影响下,对女儿产生较之母亲更为矛盾的影响。
就母亲方面而言,根据波伏娃的理论,母女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
“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
”(西蒙,325)女儿是母亲的化身,因为同样的性别使她们理论上同属一个体制,归同一种制度管辖,女儿的成长一定程度上是追寻着母亲的足迹,因而母亲可在女儿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有意无意地引导女儿朝自己希望的方向前进,以实现自己或成功或留有遗憾的过去,这时产生的“过分疼爱”也就情有可原。
然而,母亲与女儿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不同于母亲在漫长岁月后屈服的定性,女儿仍有着无穷发展潜力,她们如同一块璞玉,在雕琢后或许可以走向与母亲曾经梦想过却最终未能成行的自由之路,就这种可能性而言,母女之间的隔阂自然产生。
因此,“如果女孩子受到女人的培养,女人就会努力把她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就会表现出交织着傲慢与怨恨的热情。
”“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
这既是在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
”“即使母亲的心胸比较宽阔,真心实意地为女儿谋幸福,通常她也会认为让女儿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是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这样,就会更容易被社会所接受。
”(西蒙,325)正如《灿烂千阳》中娜娜与玛丽雅姆的关系。
大部分的时候,母亲娜娜貌似是怀有敌意地把自己的女儿玛丽雅姆看成是“另外一个人”的,由于过去所受到的欺骗和伤害,她并不希望玛丽雅姆与她的父亲扎里勒有友好的关系。
因此,她无时不刻地告诫玛丽雅姆,不要妄想能够得到父亲的宠爱,因为玛丽雅姆只是一个哈拉米,“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
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卡勒德,4)娜娜由于自身疾病的原因,本已不能从社会正常的途径获得幸福,她进入扎里勒家做仆人,也是迫于生计,并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然而扎里勒的一次冲动,更加毁掉了她仅存的尊严,使她被众人所唾弃,只得居住到远离繁华的郊区。
“他把我们赶出家门。
他把我们赶出他那座豪华的大房子,好像我们对他来说什么也不是。
而且他这么做还很高兴呢。
”(卡勒德,5)从这个层面上说,娜娜将扎里勒看成是一个伪君子,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在玛丽雅姆看来,父亲确实是宠爱着自己的,“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
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卡勒德,4)从小便居住在荒凉的郊区,除了每日共同生活的母亲,只能接触到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就连必须的食物也是由居住在城市中的哥哥们运送,玛丽雅姆的如同被软禁一般的童年显然是寂寞而无生气的。
因此,每周父亲的到来以及父亲带来的“外面的世界”便毫无疑义地成为了玛丽雅姆黑白生活中最绚烂的时光。
只有在父亲来看望她的时候,她才能感到“自己也能拥有生活所能给予的美好与慷慨。
”(卡勒德,6)所以,无论娜娜如何强硬地表现出对扎里勒的怨恨,单纯的玛丽雅姆依然坚持着对父亲的崇敬与爱戴。
母亲对女儿的态度,无论是好意地想将女儿塑造成“真正的女人”,还是怀敌意地将女儿看成“另外一个人”,由于个体的差异,都可能会引起女儿的反抗。
“对生活的强烈自发冲动,对游戏、欢笑和冒险的喜爱,使小女孩认为母性领域是狭窄的、令人窒息的。
她很想避开母亲的权威,避开那种在运用时比男孩子不得不接受的任何权威都更亲切、更平常的权威。
”(西蒙,339)娜娜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女儿,引导女儿不致重复她的悲剧,告诉玛丽雅姆“就像指南针总是指向北方一样,男人怪罪的手指总是指向女人。
”(卡勒德,7)然而,玛丽雅姆并没有理解母亲的好意。
她急切地想要获得和扎里勒其他的子女一样的地位,希望住进渴望了十五年的赫拉特的豪宅里。
她也确实采取了行动,她瞒着娜娜,自己孤身前往赫拉特,希望获得想象中的父亲首肯与接纳。
可是这必然是一条失望之路,父亲的视而不见,旁人同情的眼神,饥寒交迫的一夜使年轻的玛丽雅姆似乎明白了现实的残酷。
然而这并不是终结,更残酷的是,当受伤的她终于回到生活了十五年的泥屋,却发现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守护她的母亲也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强烈的刺激顿时使玛丽雅姆成长,娜娜也最终以一种决然的方式将自己的思想植入自己女儿的内心深处,在玛丽雅姆心中树起关于现实的不可摧毁的壁垒。
二、父权作用
同样是矛盾的态度,父亲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的分化却比母亲要泾渭分明得多。
众星拱月的成长背景,使父亲很难理解女性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内心的不甘与挣扎。
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依据自身经验,或按自己所受的教育模式,不带偏见地培养与在他们心中与儿子同样重要的女儿,或遵循传统观念,忽视甚至损害女儿的生存空间,这种行为对女儿性格形成的影响往往比母亲刻意引导下实现的“女性气质”更为巨大和深刻。
若父亲依照自己的成长经验,使女孩受到与男孩同等的教育和爱护。
那么,当她们在“作主体”这一方面收到鼓励时,“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精神、同样的坚强”,这也正应了波伏娃关于“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的论点。
“值得注意的是,做父亲的更喜欢让女儿受到这种教育。
”(西蒙,324)或者说,基于父亲与女儿血液中天生的纽带,父亲更喜欢培养出具有独立意识的女儿,而不是他在生活中所常见的沉默而没有存在感的女性,只是在某些严格的社会制度下,父亲的这种态度有时并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形成一种父亲希望女儿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亲自引导,女儿逐渐失去主见,父亲失望,对女儿更加冷淡,女儿便更加循规蹈矩的恶性循环中。
幸而莱拉的父亲哈基姆,一个上过大学并担任过高中教师的具有开放思想男性,并没有陷入到这样的恶性循环。
在他的思想中,女性与男性在基础条件、发展潜力、道路选择等方面并没有先天的区别。
因此,“从莱拉小时候起,爸爸就跟她说得很清楚,除了她的安全之外,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教育。
”(卡勒德,118)“让你得到良好的教育,绝对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卡勒德,156)在阿富汗并不十分开明的社会背景下,哈基姆克服阻力,让莱拉得以接受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往往是男性才能享有的教育,并告诉莱拉: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等到战争结束“阿富汗将会像需要它的男人一样需要你,甚至比需要它的男人更加需要你。
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女人没有受过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的可能。
”(卡勒德,118)在父亲的开明栽培下,莱拉很小就懂得了自信与争取。
这使她在受代表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夫权的丈夫拉希德虐待的时刻,能够坚强地反抗,并最终感染了多年来一直甘于忍受的玛丽雅姆,使她勇敢地砸下铁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卡勒德,355)
与哈基姆相反,更多的阿富汗父亲是遵循传统的教导的,他们并不会亲自关注和教育自己的女儿。
同时,由于父亲在传统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即使在日常琐事中没有感到父亲的权威,实际上这种权威也是至高无上的。
只是因为它没有屈尊去处理日常琐事,它才显得更有尊严。
”(西蒙,331)父亲的权威使他的一举一动往往成为金科玉律,左右子女尤其是女儿的行为。
“父亲的生活有着神秘的威望:
他在家里度过的时间、他的工作房间、他周围的东西、他的追求。
他的嗜好,都是神圣的。
他养活着全家人,他是全家人所依靠的一家之主。
他通常在外面工作,所以,家庭是通过他与外部世界沟通的:
他是那广大、艰难和不可思议的冒险世界的化身,是超越的象征,是上帝”(西蒙,331)这样神秘的威望让往往长期守在家中向往外部世界的羸弱的女儿产生近乎信仰的态度。
并且,由于母女既相依又相斥的矛盾关系,以及在女儿潜意识中,自己的未来往往与母亲已有的经历重合,自己迟早可以达到母亲的地位的笃信,使得父亲成为女儿意识中更为强大且无法超越的存在。
在这样的认识下,女儿会尝试着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父亲的关注,并期望得到比她的兄弟们更高的关注,“如果父亲对女儿表示喜爱,她会觉得她的生存得到了极雄辩的证明;她会具有其他女孩子难以具有的所有种种优点;她会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
”“如果女儿没有得到父爱,她可能会以后永远觉得自己是有罪的,该受罚的;或者,她可能会到别的地方去寻求对自己的评价,对父亲采取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西蒙,332)
在莱拉与玛丽雅姆身上,正体现了这两种父亲相反态度的作用。
莱拉由于父亲的宠爱而养成了自信与自立的性格,她敢于同恶势力挑战,当拉希德辱骂、殴打她时,她没有退缩与承受,而是勇敢地反抗。
她敢于追求自己的权利与幸福,无论多少次受挫,还是重新鼓起勇气,来到自己的女儿阿兹莎身边,并最终与青梅竹马的恋人塔里克一起为建设阿富汗而奉献;与之相反,玛丽雅姆因为父亲在她的收留问题以及婚姻对象选择上的懦弱与让步而对父亲万分失望,这种失望持续数十年,在玛丽雅姆已与拉希德生活多年后仍未改变,甚至在扎里勒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希望见到自己的小私生女最后一面时,玛丽雅姆仍未原谅,坚持不与他见面,终成永远的遗憾。
也正由于父亲当年的放弃,使玛丽雅姆长期以来否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否定自己努力的可能,加上母亲去世给她造成的负罪感,玛丽雅姆始终以一种赎罪的心态默默忍受加诸己身的不公,几近失去获得幸福的信念与能力。
三、同龄异性作用
除了父母,女性成长另一重要的影响因素便是与她们有着相同年龄,但往往个性、经历、教育、地位却大不相同的异性。
男孩仿佛就是女孩的对立面,他们从小就被当做是小男子汉,往往在家中受到更高的关注,“有关调查清楚表明,多数父母更愿意要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
人们同男孩子讲话时,态度更认真、更尊重,男孩子享有的权利也更多”(西蒙,330)相对于女孩来说,男孩处于“特权等级”,而双方同样清晰地意识到这种特权与非特权之间的差异。
就男孩这一方而言,由于对自身所处的特权地位的认识,他们自然地区分自己与女孩,将自己看成是比女孩地位更高的存在,“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
在法国,男女合校的男孩子班级,有意欺负和刁难女孩子班级。
如果女孩子想同男孩子斗争,捍卫自己的权利,就会受到非难。
”(西蒙,330)男孩因为从小在家庭在社会中的耳濡目染而以羞辱女孩为乐趣。
但事实上,他们的年龄和经历还不足以使他们理解到特权与非特权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的羞辱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对女孩的歧视上,而是出于一种与社会节奏相协的惯性。
这样的羞辱更类似于一种期望得到回应的游戏,不同的是,由于另一方显然并不接受这种充满伤害的游戏方式,两者之间的隔阂与摩擦随着接触的增加而增大,最初或为善意的游戏成为一种特定的伤害模式。
在这样的伤害模式下,女孩一方面从社会交往层面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从小就产生对男性这一集团的疏离感与恐惧,为今后的家庭生活埋下不安定的种子。
这样的“游戏”即使是处于父母保护下的莱拉也不能避免。
学校里的男孩尤其是以屠夫的儿子卡迪姆为首的一群男孩时常趁莱拉青梅竹马的伙伴塔里克不在、莱拉无人保护的时候欺负她,并以这作为一件乐事,而受到欺辱的莱拉由于力量与势力上的差距,不能有效地反抗或是避免,这使莱拉很小就认识到自己与男孩在各方面的区别,意识到如果没有塔里克的保护,自己的情况会有多糟糕。
“但是事实上,当男孩子平等待她时,她是很高兴的,她想得到他们的赞许。
她很想变成那个特权等级的一员。
(西蒙,341)”因为这种成为特权等级的渴望,莱拉对塔里克的感情并不是单纯青梅竹马间的爱恋,塔里克作为唯一一个平等对她的男孩,当莱拉与他在一起时,能够感受到一种自身被肯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又加深了莱拉对塔里克的感情。
事实上,由于塔里克的存在,卡迪姆等人的欺辱并没有使莱拉像大多数受到欺负的女孩一般自怨自艾,丧失信心,而是在塔里克的肯定下更加顽强,争取完善自己,成为更加自信和强大的女孩。
当女孩结婚后,她所熟悉的以父母为中心的家庭随之改变,丈夫成为了新家庭中的中心人物,妻子成为了丈夫的附庸,“她改用他的姓氏;她属于他的宗教、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结合于他的家庭,成为他的‘一半’。
”“她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果断地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于她丈夫的世界。
”(西蒙,491)如果说在结婚前女性和男性由于生活交集的缺乏,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尊卑之差,然而结婚后,丈夫成为了家庭生活的主宰,在传统制度下,丈夫的工作支撑着整个家庭,此时,妻子要依靠于丈夫才能生存。
作为从小与女孩对立成长起来的男性,丈夫在此时突然完全地战胜了女性,他可以随意支配妻子的行为而从制度上不会受到任何反对。
因此,“他在童年及以后生活积淀下来的所有怨恨,他在别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他要受到横眉冷对和伤害)中间日复一日积淀下来的所有伤害,全都由于他在家对妻子的作威作福而得到清算。
”(西蒙,530)但妻子在此时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社会责任赋予她们掌控家务事的权力,妻子要负责安排丈夫和所有家庭成员的衣食住行,通过自己在家务事上的能力使家庭生活井井有条,此时丈夫与妻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他们各司其职,仿佛相敬如宾。
但这种平衡并不是稳定的,尽管妻子由于在家务事上的主导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并不会直接受到丈夫的完全暴力对待,但极端的情况依然存在,尤其是丈夫的社会地位与财产在外界受到威胁或是挫折时。
拉希德在与玛丽雅姆结婚的初期同样是对她迁就和照顾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拉希德鞋店生意的衰落,以及玛丽雅姆一次次的流产,拉希德逐渐对玛丽雅姆失去了耐心,将自己在外受到的伤害全部发泄到玛丽雅姆身上,就连给他生下了儿子的莱拉也没有受到优待,长期遭受拉希德的随意打骂。
丈夫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此时完全显现出来,妻子作为“他者”因缺乏社会生活中的制度保障,无力自主生存,在遭受长期折磨时仍未思完全颠覆夫权这沉重的压迫,直到长期压抑下的矛盾最终以威胁莱拉生命的方式激烈爆发,玛丽雅姆与莱拉这才迸发了心中一直深藏的愤怒,通过极端的反抗,改变她们的“他者”地位,主宰自己的命运。
两人最后的反抗同样成为全书最高潮之处,展现出在特定背景下,两名成长与教育背景迥异的女子,最终实现殊途同归,完全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实现个体的真正自由而做出最大努力和牺牲。
四、自身作用与反作用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而内因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
女性个性气质的形成固然受到来自社会与家庭各方面作用的影响,然而更为根本的是她们对这些社会信息传达所作出的反应,即她们对内心世界之外事物的感知与理解。
从童年到少年再到婚后,女性所处的阶段与环境不同,经验、知识、责任、目标也大不相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思考的方式会日趋成熟,能够作出更为综合现实与理想的决定,并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些观念指导她们或屈服现实或挑战传统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体现出个性特质,并将对外界产生影响。
童年时代显然是女性最为懵懂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女性对未来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她们所能接触到的是有限的家人与关系者,通过在与周边人群的接触中获得知识,并形成对世界的初步认识。
然而这个时候,她们世界的中心还仅限于自己的父母,在女儿看来,“大人如神仙一般,因为他们有力量赋予他存在。
他感受到他们注视的魔力,这注视,使他一会儿变成小天使,一会儿又变成小怪物。
”(西蒙,311)她通过争取父母亲的注视而获得幸福感,而父母往往也不吝惜这种注视。
同时,由于社会普遍对男孩成为“小男子汉”的期望,女孩往往拥有比男孩更多的向父母索取爱护的自由。
这样,女孩便在父母的宠爱下产生某种特权的骄傲,此时生活中最困扰她们的事情,也仅仅为上文中所提到的男孩对女孩的恶作剧。
然而童年的幸福感又是最具欺骗性的,特权的骄傲有时也会使女孩误解父母的纵容,玛丽雅姆曾坚信自己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于是做出了孤身寻父的决定,这决定很快被证明错的离谱,并对自己的双亲、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这也是玛丽雅姆性格形成的一个最重要转折点,从此她便由活泼开朗转向阴郁沉默,赎罪般屈服于他人的不公正对待。
这是玛丽雅姆的特殊经历,然而在没有意外发生的情况下,女孩童年的骄傲并不会对她的生活轨迹造成太大的影响,而是在岁月的轨迹中与她一同成长。
“虽然整个童年时代,小女孩都在经受欺侮和主动性的剥夺,但她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主的人。
在和家庭及朋友的关系中,在做功课和游戏时,她仿佛仍是一个超越的人:
她的被动未来,只是一个梦。
”(西蒙,378)
然而这个梦很快就显露出其现实的一面。
青年时期的女性处于人生的过渡期,方走出童年期的她们一方面还尚未脱离童年期的稚气,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仍是世界的中心,一方面又意识到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因而形成非常复杂的心态。
“在她看来,男人是他者的化身,就像她对他也是这种化身一样。
但是她觉得,这个他者是处在主要者层次上的,而相对于他,她把自己看成次要者。
她将摆脱儿童教养院式的家庭,摆脱母亲的控制;她将开创自己的未来;但她不是主动地征服,而是举手投降,从而被动地、温顺地受新主人的支配”(西蒙,379)女性认识到自己迟早会与男性结婚的现实,但对于与可能的丈夫相处的方式,她并没有明晰的认识。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被动地接受了自己的臣服地位,并了解到在这段关系中可能得到的利益,但青年时期的女性却未做好直面的准备。
因而,无论是莱拉拒绝塔里克的第一次求婚,还是玛丽雅姆得知父亲要将她远嫁时的绝望,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于婚姻的恐惧感的因素。
这种恐惧感不仅存在于婚前,并持续到婚后与陌生的丈夫相处之时,并反作用于婚姻关系,更使自己成为婚姻中的弱势者。
真正使女性走向成熟的是婚后。
脱离了管教自己多年的父母,女性在婚姻关系中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自主权。
虽然她依然依附于丈夫和孩子,通过主导对社会没有直接用途的家务劳动向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但她同时摇身一变,成为了过去“母亲”的角色,她不再仅对自己负责,而是要考虑到整个家庭的生活,且由于孩子的存在,使她能够在保护幼小孩子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阿兹莎和察尔迈伊便是激发玛丽雅姆与莱拉无穷勇气的重要因素。
当孩子还没有到来之前,拉希德一家三人的关系本是僵化的,尤其是两位妻子,几乎是仇敌一般的关系。
然而自从阿兹莎出世,两名女性的关系也因为心中随之而来的责任感逐渐缓和,并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放下误解,孩子成了联系两人的纽带,更成了两人走向成熟的关键要素。
任何损害孩子利益的行为都会遭到两人的强烈反抗,这种令拉希德倍感陌生的反抗与其说是对孩子的保护,不如说是多年压抑情绪的一种宣泄,通过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并使两人获得无尽的勇气,终于反作用于一直压迫两人的拉希德身上,使故事上升到最精彩之处,玛丽雅姆与莱拉最终化茧成蝶,在对自由的追求中获得完整性格中最后的碎片——果敢与承担,终于完成了属于二人的全部特质。
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生活经历,玛丽雅姆与莱拉的命运却因为残酷的战争联系到了一起。
她们生活在阿富汗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在伊斯兰国家的严厉制度下,但她们并没有屈服于这个系统中千百年来女性的“他者”地位,而是走向了自我救赎与解放,无论是对自己的罪行负责的玛丽雅姆,还是怀着希望重生的莱拉,都展现了超越“他者”的属于女性的独特力量,实现了真正有意义的女性价值。
【参考书目】
1.西蒙·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全译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SimonedeBeauvoir.TheSecondSex.Middlesex:
PenguinBooksLtd,1972.
3.卡勒德·胡赛尼(美)著.李继宏译.灿烂千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张敏.阿富汗文化和社会.昆仑出版社,2007.
5.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M].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