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docx
《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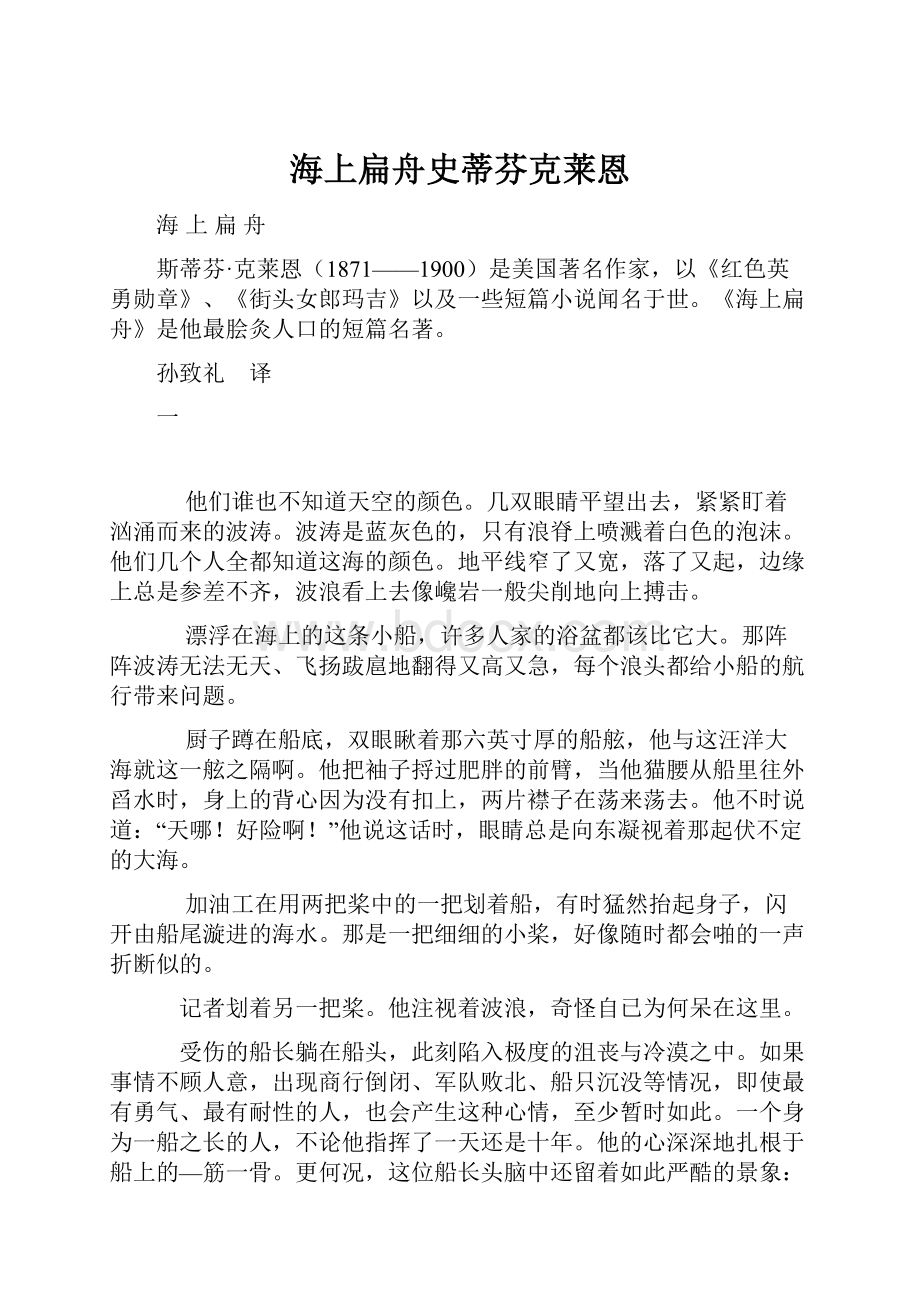
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
海上扁舟
斯蒂芬·克莱恩(1871——1900)是美国著名作家,以《红色英勇勋章》、《街头女郎玛吉》以及一些短篇小说闻名于世。
《海上扁舟》是他最脍灸人口的短篇名著。
孙致礼 译
一
他们谁也不知道天空的颜色。
几双眼睛平望出去,紧紧盯着汹涌而来的波涛。
波涛是蓝灰色的,只有浪脊上喷溅着白色的泡沫。
他们几个人全都知道这海的颜色。
地平线窄了又宽,落了又起,边缘上总是参差不齐,波浪看上去像巉岩一般尖削地向上搏击。
漂浮在海上的这条小船,许多人家的浴盆都该比它大。
那阵阵波涛无法无天、飞扬跋扈地翻得又高又急,每个浪头都给小船的航行带来问题。
厨子蹲在船底,双眼瞅着那六英寸厚的船舷,他与这汪洋大海就这一舷之隔啊。
他把袖子捋过肥胖的前臂,当他猫腰从船里往外舀水时,身上的背心因为没有扣上,两片襟子在荡来荡去。
他不时说道:
“天哪!
好险啊!
”他说这话时,眼睛总是向东凝视着那起伏不定的大海。
加油工在用两把桨中的一把划着船,有时猛然抬起身子,闪开由船尾漩进的海水。
那是一把细细的小桨,好像随时都会啪的一声折断似的。
记者划着另一把桨。
他注视着波浪,奇怪自已为何呆在这里。
受伤的船长躺在船头,此刻陷入极度的沮丧与冷漠之中。
如果事情不顾人意,出现商行倒闭、军队败北、船只沉没等情况,即使最有勇气、最有耐性的人,也会产生这种心情,至少暂时如此。
一个身为一船之长的人,不论他指挥了一天还是十年。
他的心深深地扎根于船上的—筋一骨。
更何况,这位船长头脑中还留着如此严酷的景象:
晨曦蒙胧中,海上漂着七张翻转的面孔,后来又见到一根中桅的断杆,上面还缀着一只白球,在随波冲荡、越来越往下沉,最后沉下去了。
此后,他的声音就变得有点奇怪了,虽说还很镇定,但却带着深沉的哀伤,带着一种口舌和泪水所无法表达的特性。
“比利,把船再向南转—转,”他说。
“是,再向南转一转,”加油工在船尾回道。
坐在这只船上,简宜就像坐在一只狂蹦乱跳的野马上,何况,野马也不比那船小多少。
那船腾跃,竖起,栽下,就和那野马一样。
每逢浪头打来,小船因此而颠起时,它好似一匹烈马向高耸的栅栏扑去。
那船如何攀越过一道道水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况且,到了滔滔的白色浪脊上,通常还存在这样的问题:
浪花每次从浪峰上俯冲下来,小船就必须跟着再跳一次,而且是临空一跳。
接着,小船目空一切地撞上一个浪头之后,便滑下一道长坡,风驰电掣,水花四溅,颠颠晃晃地来到了下一个威胁跟前。
大海上有个特别不利的情况:
当你成功地越过一个浪头之后,你发现后边又有一个浪头接踵而来,一样的气势汹汹,一样的急不可待,非要想方设法把小船吞没不可。
在一条十英尺长的小船上,一个人可以了解大海如何善于兴风作浪;而对于一般从未乘小船漂海的人来说,这是无法了解的。
每逢—垛蓝灰色的水墙涌来,船上的人便给挡得什么也看不见,因而也就不难设想,这个浪头是大海的最后一次爆发,是海水的最后一次逞凶。
波涛的运动极为优雅,静静地荡来,只有浪脊在咆哮。
在惨淡的光线中,那几个人的面孔准是灰白色的。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船尾,眼睛准是在奇怪地闪烁着。
若是从戏院的楼厅上看去,这整个场面无疑是神奇而迷人的。
但是,船上的人却无暇来观赏,即便有这闲暇,他们心里还要想着别的事情。
太阳冉冉地升上天空,他们知道是大白天了,因为海的颜色由蓝灰色变成了碧绿,上面还夹带着琥珀色的光道,而那浪花好似滚滚白雪。
夜去昼来的过程,他们并不知晓。
他们只是从滚滚而来的浪涛的颜色上察觉到这番变化。
厨子和记者在争辩救护站与收容所有何区别,说起话来前言不搭后语。
厨子说:
“就在蚊子湾灯塔的北边,有—个收容所,他们一看到我们,就会乘船来接我们。
”
“谁一看到我们?
”记者问。
“水手们。
”厨子说。
“收容所里没有水手,”记者说。
“据我了解,收容所只是为海上遇难的人准备衣服和干粮的地方。
他们没有水手。
”
“噢,有的,他们有的。
”厨子说。
“没有,他们没有。
”记者说。
“算啦,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没到那儿呢。
”加油工在船尾说。
“嗯,”厨子说,“我看离蚊子湾灯塔不远处,也许不是收容所,说不定是个救护站。
”
“我们还没到那儿呢。
”加油工在船尾说。
二
小船从每一个浪峰栽下的时候,疾风钻透了那几个没戴帽子的人的头发,而船尾扑通一声又颠下去的时候,浪花又溅过他们身旁。
这些波浪,每个浪峰都是一座小山,那些人可以利用呆在峰顶的瞬间,眺望一下浩瀚喧嚣的大海,只见海面熠熠发光,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放荡不羁的大海演出这场游戏。
也许是绚丽多姿的,也许是光彩夺目的,到处闪耀着翠绿色、白色和琥珀色的光芒。
“好极了,风往岸上吹,”厨子说。
“要不然,我们会漂到哪儿去呢?
一点指望也没有。
”
“那倒是。
”记者说。
忙碌的加油工点头表示赞同。
船长在船头闷然一笑,这笑声把诙谐、轻蔑和悲怆融为一体,一股脑儿地全给表露出来了。
“伙计们,你们以为我们现在就有很大指望啦?
”他说。
那三人听了都默默不语,只是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两声。
他们觉得,在这当儿表示任何异常的乐观,那是幼稚而愚矗的,可是,他们心里对情态无疑都感到乐观。
在这种时刻,年轻人的思想是顽固的。
另一方面,从伦理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处境绝对不允许公然表示绝望。
因此,他们只好沉默不语。
“哩,好啦,”船长安慰他的伙计们说,“我们会安全到岸的。
”
不过,他的话音有点不对,引起了三人的深思,于是加油工说:
“是的!
如果风向不变的话。
”
厨子正在舀水。
“是的!
如果我们抢滩时不遇上倒霉的话。
”
棉绒似的海鸥飞来飞去。
有时,它们栖息在海上,附近是一片片褐色的海藻,随波漂荡,宛如暴风中搭在绳子上的毛毯。
鸟儿一群群轻松自在地栖息着,真叫小船上的某些人为之艳羡,因为愤怒的大海对于它们,就如同对于—千英里以外内陆上的一群松鸡一样无所谓。
它们常常飞得很近,用黑溜溜的眼珠子盯着那几个人。
此时,那些鸟儿眼睛一眨不眨地审视着,显得十分神秘,十分阴险,那几个人嗔怒地轰赶它们,叫它们走开。
一只海鸥飞来,显然是要落在船长的脑袋上。
那鸟与小船平行飞着,也不兜圈子,只是像小鸡似地斜着一跳一跳的。
它的一双黑眼睛渴望地盯着船长的脑袋。
“丑八怪,”加油工对那鸟说。
“瞧你那样子,就像用刀子刻成的。
”厨子和记者恶狠狠地咒骂那海鸥。
船长自然很想用粗缆绳的一端把鸟打跑,可他又不敢这么做,因为小船已经满载,任何类似用力的举动都会把它搞翻。
于是,船长用他张开的手,轻微小心地把海鸥挥开了。
海鸥停止追击之后,船长舒了口气,因为他的头发不受骚扰了,其他人也舒了口气,因为他们此刻觉得,那鸟不知怎么那样可怕,那样不吉利。
在那期间,加油工和记者划着船。
现在还在划着。
他们一起坐在同一个座位上,一人划一把桨。
然后,加油工划起双桨;随后,记者划起双桨;接着,是加油工;再接着,又是记者。
他们划着,划着。
这事最棘手的,是轮到靠在船尾的那个人划桨的时候。
说实在话,从母鸡屁股底下偷鸡蛋,也比在那小船上换个座位来得容易。
首先,船尾的人将手顺着座板往前滑动,小心冀翼地挪动身子,犹如他是法国的细瓷一样。
然后,坐在划桨位子上的人将手顺着另—面座板划动。
一举一动都得提心吊胆。
当这两人战战兢兢地擦身而过时,全船的人都警惕地注视着那滚滚而来的波涛,船长大声减道:
“注意!
当心些!
”
不时涌现一簇簇褐色的海藻,好像海岛,好像小块小块的土地。
显然,海藻不在向任何方向移动。
实际上,它们是静止的。
它们告诉船上的人,他们的小船正在朝陆地缓缓前进。
船长在小船被一个巨浪颠起之后,在船头谨慎地抬起身子,说他看到了蚊子湾的灯塔。
厨子马上说他也看到了。
那当儿,记者正划着桨,为了某种原因,他也想看看灯塔,可他背对着远岸,而海浪又气势汹汹,他一时没有机会转过头去。
不过,最后涌来一阵浪头,比别的浪头较为缓和,等他颠到浪顶,他赶忙向西方的地平线瞥了一眼。
“看见了吗?
”船长问。
“没有,”记者慢吞吞地说,“什么也没看见。
”
“再看看,”船长说。
他用手指着。
“就在那个方向。
”
到了另—个浪尖上,记者照船长的吩咐又看了看,这次他的目光在摇摇晃晃的地平线边缘上,偶尔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静止的东西。
它恰似一个针尖。
要找到一个如此微小的灯塔,那得有急切的目光才行。
“船长,你看我们能划到那儿吗?
”
“如果这风持续刮下去,船又不翻掉,我们也只能划到那儿,”船长说。
小船被一个个掀天的巨浪举起,被凶恶的浪峰打得哗哗作响。
它就这么行进着。
这种行进,在周围没有海藻的时候,船上的人是难以觉察的。
那船仿佛只是一件小玩艺儿,颠簸摇晃,奇迹般地没有翻个儿,任凭大洋恣意摆布。
偶尔有一大片海水,好似白色的火焰,涌进船里。
“舀水,厨子,”船长沉着地说。
“是,船长。
”厨子兴致勃勃地答道。
三
在这大海上建立起来的微妙的手足之情,很难用笔墨加以形容。
谁也没说情况如此。
谁也没提起过这种手足之情。
然而,船中确实存在着这种友情,因而使每个人感到温暖。
他们是船长、加油工、厨子和记者,四个人结成了朋友——超乎寻常地、更为奇妙地牢牢联结在一起的朋友。
受伤的船长靠在船头的水罐子上,说起话来总是低声细语,平心静气的,别看他船上的三个人是杂凑在一起的,他决不可能指挥比他们更心甘情愿、更欣然从命的船员了。
他们不只是认识到如何最有利于共同的安全。
这其中的确有一种属于个人的、发自肺腑的特质。
除了对船长的忠诚,还存在着这般的友谊。
就拿记者来说,他—向所受的教育是用冷服看人,此刻甚至认为这种友谊是他平生最美好的经历。
然而,谁也没有说过情况如此。
谁也没有提起过这种友情。
“但愿有个帆就好了,”船长说。
“不妨把我的大衣系在浆头上试试,让你们两个有机会歇一歇。
”于是,厨子和记者撑起桅杆,摊开入衣,加油工掌舵;小船装好了帆,加快了前进速度。
有时,加油工不得不猛地一划,避免一阵海浪冲进船中,但是除此之外,小船一帆风顺。
其间,灯塔在慢慢变大。
现在几乎显出颜色了,看上去犹如天边的一个小小的灰影。
划船的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转过头,真想瞧一眼那小小的灰影。
最后,从每一个浪峰上,那颠簸着的小船上的几个人终于看得见陆地了。
即使灯塔变成天边的一个竖影的时候,那陆地也仅仅像是海上的—条长长的黑影。
当然,这影子比纸还薄。
“我们一定是在新斯麦拿对面一带了。
”厨子说。
原来,他以前常坐帆船沿这一带海岸航行。
“对啦,船长,我想他们大约在一年前就把那个救护站取消了。
”
“是吗?
”船长问。
风渐渐停息了。
厨子和记者现在不必做苦役般地高举着浆。
但是,海浪照旧向小船猛扑过来。
小船停滞不前了,拼命地同海浪搏斗着。
加油工或是记者又接过桨。
本来,船只失事也算不了什么。
只要人们受过专门训练,并在身强力壮的时候遭受船难,那就会有较少的人淹死在海上。
这船上的四个人,在登上小船之前,已有两天两夜没怎么合眼了,而当初在沉船的甲板上到处乱爬的过程中,因为心情紧张,也忘了饱餐一顿。
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加油工和记者此刻都不喜欢划船。
记者天真地想:
既然世人如此神志清醒。
为何还有人把划船视为赏心乐事呢?
划船可不是乐事,而是穷凶极恶的惩罚。
即令神志不清的怪人,也决不会得出别的结论,只能把划船看作是对肌肉的恐怖,对脊背的犯罪。
记者向船上的人概要讲述了他对划船的乐趣的看法,面色疲倦的加油工十分赞同地笑了笑。
顺便插—句,加油工在沉船之前,曾在轮船的机房里值过两次班。
“慢慢划吧,伙计们,”船长说。
“别把劲儿使光了。
假使我们要冲浪抢滩的话,你们还得使出全身的力气,因为我们肯定还得游上岸。
慢慢来吧。
”
陆地惭渐打海上升起。
由—条黑线变成一条黑线和一条白线——原来是树木和沙滩。
后来船长说,他能看出岸上有座房子。
“那一定是收容所,”厨子说。
“他们不久就会看见我们,出来搭救。
”
远处的灯塔高高耸立。
“守塔人要是用望远镜隙望的话,现在应该能看见我们了,”船长说。
“他会通知救护人员的。
”
“其他小船还不可能有到岸报告这次失事的,”加油工低声说,“不然,救生船早就出来救我们了。
”
慢慢地,陆地由海上隐隐浮现了,显得十分优美。
风又来了,由东北风变成东南风。
最后,一个新的声音传进船上人的耳朵。
那是惊涛拍岸发出的低沉隆隆声。
“这下子我们无法抵达灯塔了,”船长说。
“把船头稍许向北转一转,比利。
”
“稍许向北转一转,船长。
”加油工说。
于是,小船把船头再次转到顺风方向,船上的人,除了划手之外,都在望着海岸逐渐变大。
由于陆地在望,疑虑和恐惧从他们心里消逝了。
大家还在全神贯注地驾驭着小船,但却无法压抑心头默默的喜悦之情。
—个钟头之后,他们也许就抵岸了。
他们的脊骨已经完全习惯于在船上保持平衡,现在驾驭起这条烈马似的小船,就像耍马戏的一样熟练自如。
记者以为自己浑身湿透了,可他偶然往大衣上口袋里一摸,竟发现里面有八支雪茄。
其中四支被海水浸湿了,四支安然无恙。
搜了一阵之后,有人找出三根干火柴。
于是,四个漂流者便贸贸然地驾着小船,心想自己即将得救,眼里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他们一面抽着大雪茄,一面评判着世人的善与恶。
每个人都喝了些水。
四
“厨子,”船长说,“在你所说的收容所附近,似乎连个活人的影子都没有。
”
“是的,”厨子答道。
“奇怪,他们没看见我们!
”
一大片低沉的海岸展现在他们眼前。
岸边是些低矮的沙丘,项上长着黑黝黝的草木。
拍岸浪的轰鸣声清晰可闻。
有时,一阵巨浪卷上海滩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那白色的浪尖。
一幢小屋在天边显出黑色的轮廓。
南边,纤细的灯塔将它小小的灰色塔身升高了。
潮水、风和海浪冲着小船向北旋转。
“奇怪,他们没看见我们。
”那几个人说。
拍岸浪的轰鸣变模糊了,可是那声调仍似雷鸣,声势浩大。
当小船在汹涌澎湃的巨浪上颠簸时,那几个人就坐着倾听这轰鸣声。
“我们肯定要翻船。
”每个人都这么说。
事实上,无论哪个方向,二十海里之内是没有救生站的。
然而那几个人并不了解这情况,于是便对国家救护员的视力进行恶毒攻击。
四个人怒眉瞪眼地坐在小船上,编造起形容词来都能创纪录了。
“奇怪,他们没看见我们。
”
先前那股轻松愉快的心情完全消失了。
他们的头脑变敏锐了,很容易想象出无能、盲目以及胆怯的种种表现。
前面就是人烟稠密的陆地的岸边,可是那儿却了无人迹,真叫他们悲怆至极。
“唉,”船长终于说道,“我想我们得自己试试看了。
假若我们在这儿呆得太久,等船沉之后,谁也没有力气游水了。
”
于是,划桨的加油工掉转船头。
径往岸上划去。
猛然间,大家的肌肉绷紧了,心里也思索开了。
“假使我们不能都上岸,”船长说,“假使我们不能都上岸,我想你们几位知道把我完蛋的消息送到什么地方去吧?
”
随即,他们匆匆交换了住址和叮嘱。
至于谈到感想,那可是充满勃然大怒。
这些感想成可归纳如下:
“假使我要淹死——假使我要淹死——假使我要淹死的话,七位疯狂的海神啊,为什么又让我漂泊这么远,眼巴巴地凝视着沙滩和树木呢?
我给带到这儿来,难道仅仅为了在我正要细嚼人生的神圣乳酪时,就把我的鼻子扯掉吗?
简直是荒谬绝伦。
假如命运女神这个老蠢婆子只会来这—套,那就应该夺掉她司掌人类命运的权利。
她是个连白己的意图都搞不清的老太婆。
假使她决定要淹死我,她为何不在一开始就下手,省得我吃这么多苦头呢?
整个事情都是荒谬的。
……但是,不,她不会存心要淹死我的。
她不敢淹死我。
她淹不死我。
搏斗了这么久,不可能。
”随后,那人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对云朵挥挥拳。
“好吧,就淹死我好啦,不过,听我怎么诅咒你吧!
”
此刻涌来的巨浪更可怕了。
它们好像随时都要爆发,把小船打翻在喧腾的浪花之中。
浪涛开始发言之前,总要先发出一阵长长的隆隆声。
凡是不习惯于海上生活的人,都不会断言那小船能及时地攀上那些峻峭的浪峰。
海岸仍然很远。
加油工是个机灵的冲浪船夫。
“各位,”他急促地说,“船维持不了三分钟了,我们离岸太远,没法游水。
船长,我是不是再把船划到海上去?
”
“可以,划吧!
”船长说。
这做加油工,凭着一连串奇迹般的快速动作,以及麻利稳健的驾船技术,终于从那激浪中掉转船头,又安然划回海上。
当小船颠下浪洼向更深的水面冲去时,船上一片沉寂。
接着,有人忧郁地说:
“无论如何,他们现在一定从岸上看见我们了。
”
海鸥顶着风,向着灰茫、凄凉的东方斜飞而去。
从东南方刮来一阵狂风,夹着漆黑的云和砖红色的云,犹如房子失火冒烟似的。
“你们觉得那些救护人员怎么样?
难道他们不是好人?
”
“奇怪,他们还没看见我们。
”
“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在这儿闹着玩呢!
也许他们以为我们在钓鱼。
也许他们以为我们是该死的傻瓜。
”
那是个漫长的下午。
湖水改变了方向,硬把他们往南推,风浪却将他们向北冲。
远在前方,海岸线、大海和天空形成一个巨角,那里有些小点点,似乎表示岸上有个城镇。
“圣奥古斯丁吧?
”
船长摇摇头。
“离蚊子湾太近了。
”
加油工在划船,继而是记者在划,接着又是加油工在划。
这是件累人的差事。
人的脊背所能承受的疼痛,要比医生为—团官兵作通身检查所记载下来的病痛还要多。
脊背是个局部地区,但是却可以成为不计其数的肌肉冲突、缠结、扭拧以及其他舒慰活动的场所。
“你以前喜欢划船吗,比利?
”记者问。
“不,”加油工说。
“见鬼去吧!
”
每当一个人由划船的位子换到船底的位子时,他就感到浑身萎顿不堪,使他什么事情也顾不得了,只知道要把一根手指晃几下。
寒冷的海水在船里荡来荡去,他就躺在水中。
他的头枕在座板上,几乎碰着一个旋转着的浪峰,有时一个狂涛巨浪打进船来,又把他浇个透湿。
然而,这些事并没使他烦恼。
几乎可以肯定,即使小船翻个个儿,他也会舒舒服服地滚到大洋上,好像他确信那是个柔软的大垫子似的。
“瞧!
岸上有个人!
”
“在那儿?
”
“在那儿!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
“看见了,的确看见了!
他走来了。
”
“现在他停住了。
瞧!
他正面对着我们呢!
”
“他在向我们挥手呢!
”
“是在挥手!
真的!
”
“啊,这下我们可好啦!
这下我们可好啦!
再过半个钟头就有船到这儿来救我们了。
”
“他还在走。
他跑起来了。
他是上那座房子那儿。
”
远处的海滩似乎比海低些,必须仔细查看,才能看出那个小小的黑色身影。
船长见水上漂着一根棍子,他们便朝那儿划去。
说来也巧,船上正好有条浴巾。
船长把浴巾绑在棍子上,挥了起来。
划船人不敢抬头,因此只好发问。
“他现在在干什么?
”
“他又站着不动了。
我想他在张望。
……他又走了,向着那座房子。
……现在又停住了。
”
“他在向我们挥手吗?
”
“没有,现在没有!
不过,刚才在挥。
”
“瞧!
又来了一个人人!
”
“他在跑呢。
”
“瞧他跑那样子!
”
“啊,他骑着自行车。
现在他碰上另外那个人了。
他们俩都在向我们挥手。
瞧啊!
”
“有个什么东西来到海滩上。
”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
“啊,看样子像条船。
”
“啊,肯定是条船。
”
“不,是带轱辘的。
”
“是的,是带轱辘的。
嗯,那—定是救生船,他们把它放在车上沿着海岸拖呢。
”
“肯定是救生船。
”
“不,绝对——,那是——那是辆汽车。
”
“我跟你讲,那是条救生艇。
”
“不对!
是辆汽车。
我看得清清楚楚。
懂吗?
是一辆大型
旅馆专车。
”
XX文库-让每个人平等地提升自我 “的确,你说得不错。
是辆汽车,千真万确。
你们看他们用汽车干什么?
说不定正在四处召集救生员吧?
”
“八成是这么回事。
瞧!
那儿有人挥着一面小黑旗。
他站在汽车的踏板上。
那另外两个人也来了。
他们正在一起说活。
瞧那拿旗子的家伙。
也许他不在挥动!
”
“那不是旗子吧?
那是他的大衣。
啊,肯定是他的大衣。
”
“—点不错,是他的大衣。
他脱下了大衣,正绕着头挥动呢。
你们看他挥呀!
”
“啊,我说呀,那里根本没有什么救护站。
那只是一辆避寒胜地的旅馆专车,拉来一些旅客观看我们给活活淹死。
”
“那个拿大衣的白痴是什么意思?
他究竟在打什么信号?
”
“看样子,他想告诉我们向北去。
那边一定有个救护站。
”
“不,他以为我们在打鱼。
只是向我们表示欢迎罢了。
懂吗?
啊,咸利。
”
“唉,我要是能弄懂那些信号是什么意思就好了。
你们认为他是什么意思呢?
”
“他什么意思也没有,只是闹着玩的。
”
“假如他就是示意要我们再次冲浪抢滩,或是划到岸上等候,或是向北,或是向南,或是滚开——那倒多少还有些道理。
可是,你们瞧他。
他只是站在那儿,把他的大衣像车轮子似地转个不停。
这个蠢蛋!
”
“又来了些人。
”
“真是一帮子乌合之众。
瞧!
那不是条船吗?
”
“哪儿?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啦。
不,那不是船。
”
“那家伙还在挥大衣呢。
”
“他一定以为我们喜欢看他那样干呢。
他干吗不住手呢?
真是无聊透了。
”
“我不知道。
我想他是要让我们往北去。
—定是那边什么地方有个救护站。
”
“哎,他还没累呢。
瞧他挥呀挥的。
”
“我怀疑他能坚持多久。
他自打看见我们,就一直在挥大衣。
他是个白痴。
他们为什么不找人放条船出来呢?
一条渔船——一条大渔船——可以安然无恙地驾到这里。
他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
”
“噢,现在没有关系啦。
”
“他们既然发现了我们,马上就会放船来救我们的。
”
低洼陆地的上空,涂上了一抹似隐若现的黄色。
海上的阴影逐渐加深。
风里透着寒冷,那些人索索颤抖起来。
“天呀!
”一个人说,声音里流露出不虔诚的味道,“但愿我们不要总在这儿胡闹!
但愿我们不用成夜地在这儿拼命挣扎!
”
“噢,我们决不会整夜呆在这儿!
你不要担心。
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不久就会来救我们的。
”
海岸蒙胧了。
挥大衣的人渐渐没入暮色之中,那署色也同样吞噬了汽车和人群。
浪花咆哮着冲上船弦时,那几个航海人缩瑟着,咒骂着,就如同在给他们打火印似的。
“我真想抓住挥大衣的那个笨蛋。
为了求求好运,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
”
“为什么”他触犯你什么了?
”
斯蒂芬·克莱恩翻开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新篇章,被人们称为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开拓者。
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人在命运面前、在社会面前和坏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人被剥夺了自由意志,上帝是冷漠的,对人间的苦难熟视无睹,无望得到任何帮助。
”
《海上扁舟》是美国著名自然主义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着重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本文通过大自然的无情与人类的有情、人的希望与失望、大海的浩瀚与船只的渺小、个人的成长以及获救前后岸上的人的不同的对比,论文指出面对大自然对人类困境的漠然处之,友情、坚忍和协作,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希望。
史蒂芬.克莱恩《海上扁舟》的自然主义研究
在《海上扁舟》中,克莱恩刻画了船长、加油工、记者、厨师四人在冰冷的自然界中团结一致,齐心战胜自然的勇气和精神。
四人紧密配合,一个累了另一个接上划桨,谁也没有抱怨,正如船长说的,“他绝不可能指挥比他们更心甘情愿、更欣然从命的船员了”[2](P70)面对冰冷的海洋,人与人的信任和团结才是面对困难的唯一方法,四人的精神像火一样温暖着冷酷的大自然。
小说中克莱恩把人物放置在茫茫大海上,对每一次大海的怒吼,波涛的冲击,船员的行动都做了详细的描写。
这也正是自然小说在创作方面的体现,纵观全文,克莱恩的《海上扁舟》的确是自然主义的经典之作。
四、结语
大自然是冷漠的,它拥有自己的法则。
在现实的环境中不断挑战人类,克莱恩在《海上扁舟》中先给了船员们生的希望,又让他们体会到了死的威胁,揭示了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
成功地表现了自然主义的命题。
不愧为自然主义的经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