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监生.docx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监生.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监生.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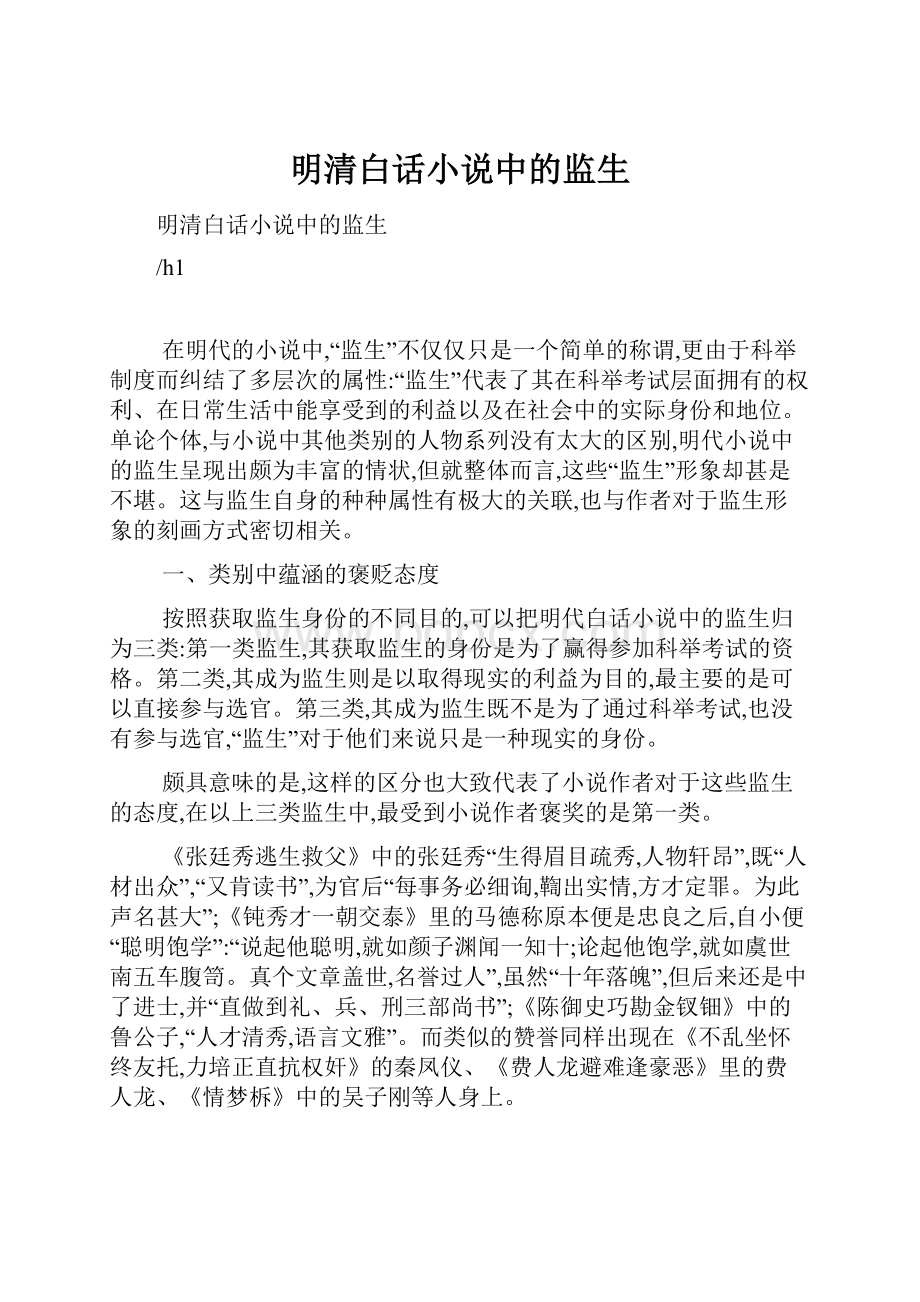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监生
明清白话小说中的监生
/h1
在明代的小说中,“监生”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更由于科举制度而纠结了多层次的属性:
“监生”代表了其在科举考试层面拥有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能享受到的利益以及在社会中的实际身份和地位。
单论个体,与小说中其他类别的人物系列没有太大的区别,明代小说中的监生呈现出颇为丰富的情状,但就整体而言,这些“监生”形象却甚是不堪。
这与监生自身的种种属性有极大的关联,也与作者对于监生形象的刻画方式密切相关。
一、类别中蕴涵的褒贬态度
按照获取监生身份的不同目的,可以把明代白话小说中的监生归为三类:
第一类监生,其获取监生的身份是为了赢得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第二类,其成为监生则是以取得现实的利益为目的,最主要的是可以直接参与选官。
第三类,其成为监生既不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也没有参与选官,“监生”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现实的身份。
颇具意味的是,这样的区分也大致代表了小说作者对于这些监生的态度,在以上三类监生中,最受到小说作者褒奖的是第一类。
《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张廷秀“生得眉目疏秀,人物轩昂”,既“人材出众”,“又肯读书”,为官后“每事务必细询,鞫出实情,方才定罪。
为此声名甚大”;《钝秀才一朝交泰》里的马德称原本便是忠良之后,自小便“聪明饱学”:
“说起他聪明,就如颜子渊闻一知十;论起他饱学,就如虞世南五车腹笥。
真个文章盖世,名誉过人”,虽然“十年落魄”,但后来还是中了进士,并“直做到礼、兵、刑三部尚书”;《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鲁公子,“人才清秀,语言文雅”。
而类似的赞誉同样出现在《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的秦凤仪、《费人龙避难逢豪恶》里的费人龙、《情梦柝》中的吴子刚等人身上。
可以看出,这些因为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入监的监生,作为小说中的正面人物,都得到了作者的褒扬。
并且作者还不惜笔墨,为其安排了较好的人生归宿,他们无一例外都考取了进士,并且大多都能福延子孙。
而这样一致褒扬的情形在第二类中便有所改变。
仍旧作为正面人物被作者表彰的是《济穷途侠士捐金重报施贤绅取义》里的浦肫夫,其自小“爽落多奇”,长大后,不仅“做人会算计灵变”,还“有信行,又慷慨”,是一个侠士。
除此之外,在这些监生里,可以视为小说的主要人物的是《赵春儿重旺曹家庄》里的曹可成,其虽然被称为“曹呆子”,但也不失淳朴忠厚,可是与第一类中的张廷秀、秦凤仪等人比起来,却又远远不及了。
此类中其余的监生多是小说中的配角。
《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徐氏兄弟,在义仆阿寄死后,听信了旁人的谣言,去阿寄房中搜检,看有没有什么私藏;《择郎反错配,获藏信前缘》里的彭一德极是娇惯女儿,其所受的一番困苦都源于对女儿的过分宠爱,亦算是咎由自取。
以上这些监生与第一类中的监生比起来在形象上要逊色得多,但严格说来却也只是各有各的缺点,从“人无完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性格上的缺陷以及所犯的过失都在可以原谅的范围之内。
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缺点并没有对旁人造成多大的伤害,或者说,他们的性格缺陷没有严重到要去主动伤害旁人,而在这一点上与这些监生不同的是《张廷秀逃生救父》里的赵昂。
在小说中,赵昂施出一系列毒计,并险些害死了张氏父子三人的性命。
张廷秀兄弟中进士为官后,赵昂也终于恶有恶报,被处以斩刑,可谓罪有应得。
由以上列举可见,除浦肫夫之外,这一类小说中的监生多不是正面形象,甚至是作者极力贬斥的对象。
而浦肫夫成为监生的经过也颇有些特殊,其原本没有援例入监的念头,但被其资助过的三个进士报恩心切,要替他寻个好前程,执意要替他纳监好让其做官,浦肫夫好意难却,这才不得已去北京做了监生以获取选官的资格。
小说中所叙其做的侠义之事,都在成为监生以前,而更重要的是,成为“监生”以便于选官,只不过是为了解决其不是读书人、不能通过科举为官这一难题的方式,与第一类中的张廷秀等人借监生身份来参加科举以获取官位颇为相似。
从这一角度上看,虽然有参加科举考试与参与选官的不同,就本文的三个类别的划分而言,浦肫夫的“监生”身份在本质上却与第一类中张廷秀、秦凤仪等人的监生身份相一致。
在此之外还有一个特例则是《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
/h1
断狱》里的都司断事林大合,作者称其“吏才敏捷,见事精明”,从他在断案中的表现来看,也确是如此。
而倘若抛开他喜爱男风,并有意周全恃其宠爱,“做件把不法之事”的门子这点缺憾不谈,其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官员。
但需要注意的是,小说在介绍其时,是说:
“虽然太学出身,却是吏才敏捷,见事精明”,从这一句话中的转折关系可以看出,其如此敏捷、精明,并不符合一般的情形,太学出身者本应不敏捷、不精明才是,而这或许才代表了小说作者对于监生出身的官员的真实看法。
总之,与第一类监生所受的一致褒扬相比,第二类监生中既有浦肫夫这样接近“第一类监生”、受到赞赏的正面形象,也有如赵昂般被人唾骂的反面典型,而大多数则是因为其自身的性格缺陷而受到作者的微讽:
既不是绝对的赞扬,也没有一味的斥责,虽然嘲弄、批评之意大于褒奖、肯定,但在涉及他们的笔墨中还是保留了更多的善意。
二、“才疏学浅”与“贪财好色”——以第三类监生为例
相对于通过科举以及选官改变了“监生”身份的第一类和第二类监生来说,第三类监生在科举层面的身份意义从没有发生变化,他们的“监生”身份更为纯粹,就这一意义而言,对于他们的讨论也就更能切中小说中监生形象的实质。
事实上,明初以后,监生的才能已经受到世人的质疑,而在援例入监的制度实行以后,大量没有达到标准的人也进入了太学,监生在学识方面势必更为受人鄙夷,往往“人甚轻之”,正所谓“纳马、纳粟入监者其贤百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
而才疏学浅,正是小说中监生的一个显着特征。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里的汪云生“学问无成”,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得纳了个监生;《真文章从来波折,假面目占尽风骚》里的卜亨是靠银子打通关节才做的秀才,又因为冒充名士在家乡立身不住,只得到南京纳监做监生;《快活翁偏惹忧愁》里的蒙栋被逼无奈,要写一张自己的卖身契。
蒙栋虽是监生,却因为“文理欠通”,竟连这张卖身契都是旁人口授,亦可谓不学无术之至了。
与其学识上的卑下相一致,这些监生在才能上也大有不足,在小说中,受人捉弄、被人欺骗,以至被人嘲笑,便成为了他们的常态。
《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里的潘姓富翁,“受过了好些丹客的骗。
他只是一心不悔”;《杜骗新书》的《道士船中换转金》里的贲监生在回家的船上,将换来的金子拿出来炫耀,终让骗子又将金子换了回去。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里的汪云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自以为人财两得,谁知是落入了旁人的圈套中,所娶寡妇逃走不说,其家财也被“搬一个尽情绝义,并无一物存留”。
由以上诸位监生可以看出,才能与学识上的卑下是他们的共同特征,而这也不仅仅只表现在上面所举的小说里对他们学识以及才能的直接描述中。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本应以读书明理为生活必需的士人,小说中却从不涉及他们读书生涯,这与小说在描写第一类监生时多叙及他们的苦读与勤奋有明显的不同。
在作者的笔下,“书斋”成为第三类监生感知领域之外的另一个天地,与这些太学生至为密切的,是丹房、尼庵、青楼和闺房,而绝不是书斋。
小说的场景从书斋切换成为丹房、青楼等地,本身便代表了作者对他们学识的评价。
而在才能方面,除了潘姓富翁、贲监生、汪监生等因为愚笨而受骗之外,其余各人虽看似还算精明,却也多不能因为这种“精明”而保全身家:
孙富“得病卧床月余,终日见杜十娘在傍诟骂,奄奄而逝”,蒙栋沦为奴才,赫大卿、甄监生都一命呜呼,汪监生的家产被人谋夺,《日宜园九月牡丹开》里的蒋青则更是人财两失,《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赵昂在真相大白后同被处以斩刑。
虽然亦可能一时得利,但却最终不免破家损身,这些监生相似的悲惨结局颠覆了前面情节所提供的“精明”印象,而所隐现的正是作者对于他们才能的贬斥。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才疏学浅”之外,这些监生的还表现出不同的个体特征。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李甲一旦面对千金的诱惑,便忘却海誓山盟抛弃了杜十娘。
杜十娘跳江前,“众人聚观者,无不流涕,都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幸”。
《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赫大卿“为人风流俊美,落拓不羁,专好的是声色二事”;《甄监生浪吞秘药,春花婢误泄风情》中的甄廷诏迷醉于用女色取乐的内丹,
/h1
由于要炼内丹,误食了方士所给的春方,竟为此而一命呜呼。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里的蒋青看上了秀才刘玉的妻子元娘,竟派人将元娘抢到家中,令刘氏夫妇离散了六年;《快活翁偏惹忧愁》里的蒙栋蒙丹秋,是个“色中俄鬼”,因看上了从嫁的媵女小蛮,最终沦为魏国府里的奴才。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里的汪云生则“是个酸涩俚吝之人,故此银子只放进不放出,俗语叫名挟杀鸡,放放恐飞了去”,“人人晓得他是个涩鬼,遂取一个浑名‘皮抓篱’”。
在这里,要特别提出加以讨论的是《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监生赵昂,其与沈洪的妻子勾搭成奸。
皮氏原本想与赵昂一起逃走,赵昂却道:
“只除暗地谋杀了沈洪,做个长久夫妻,岂不尽美。
”并出主意在沈洪面中下砒霜。
毒死沈洪后,赵昂拿着沈家的银子上下打点,欲图嫁祸于玉堂春。
玉堂春屈打成招,赵昂又向禁子、牢头使了银子,“将玉姐百般凌辱。
只等上司详允之后,就递罪状,结果他性命”。
需要注意的是,《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监生赵昂和《张廷秀逃生救父》里的赵昂同名。
两人名字相同,例监的身份相同,性情之毒、手段之辣,以及最后被处斩的结局也无一不同。
事实上,根据小说中的相关情节来看,《张廷秀逃生救父》里的赵昂虽然谋得山西平阳府洪同县县丞得职位,但“在家守得年馀,前官方满”,赵昂正要“择吉起身”,便遇见了中了进士前来复仇的张廷秀,接着就被捕获。
这也便是说,赵昂虽参与选官,却连一天官也没做过,其身份始终是纳粟监生,与第二类确实为官的其他监生尚有不同。
就这一意义而言,无论是身份,还是人物的属性,抑或是作者对其的评价,将其与《玉堂春落难逢夫》里的监生赵昂一同放在第三类监生中显然更为适合。
综合以上列举的第三类监生可见,他们并没有脱离现实中公众对他们的整体观照,在“才疏学浅”这一点上,这些形象呼应了明代社会对于监生的质疑和不屑。
在另一方面,这些小说中的监生又体现出整体观照之外的个性特征:
薄幸、吝啬、贪财、好色、毒辣、虚荣……这些性格特征亦有普遍与特殊的区别:
好色与贪财在绝大多数监生身上都有所体现,而薄幸、吝啬、毒辣、虚荣等则只属于某一、两个特定的个体。
从小说中第三类监生的身上存在的这种整体观照与个体特征的差异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监生的形象中的匠心所在。
首先是其塑造的“监生”要象一个真实的监生。
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并不难满足,基于现实社会中监生在学识与才能方面所受到的恶劣评价,只要通过小说的叙述与情节安排能让读者感受到监生的浅薄和愚笨,就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塑造。
而接下来附加在这些监生身上的其他性格则完全出于人物设置与故事情节的需要,薄幸、吝啬、贪财、好色、毒辣、虚荣等都由此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好色与贪财在个体特征中的普遍存在,其也有超越其他较为特殊的个体特征如薄幸、吝啬等,上升到整体观照中的趋势。
这种趋势随着这种贪财、好色的监生在小说中的大量出现会越发强烈。
倘若将小说在社会中可能的广泛流传与深刻影响考虑进去,则这种趋势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
就这一角度而言,整体观照与个体特征并非固定的存在,整体观照不仅体现了现实中公众的普遍观念,也会因为小说中个体特征的强调和反复而变得更为丰富。
而小说中的某些个体特征在上升为整体观照之后,剩下的特征相对有限,为避免性格的雷同和单一,也迫切需要加入新的性格元素使得人物形象在成功的基础上更为新鲜别致,小说中监生的个体性格也便因此充满了多样化的可能性。
但别具意味的是,尽管有这种多样化的可能,但实际上附加在第三类监生整体观照之外的个体特征却都维度单一:
它们都不是正面的性格,这些监生都成了小说中各种常见的负面性格——薄幸、吝啬、贪财、好色、毒辣、虚荣——的典型。
就此而言,最初的整体观照局限了个体特征的多样性发展,其蕴涵的贬义使得小说中的监生性格成为了一个单向的射线,以“才疏学浅”为原点,向着负极无限扩展。
而也正因为这一原因,与第二类监生所受到的微讽不同,第三类监生多被作者极力贬斥与嘲讽,成为了与第一类监生迥异的形象系列。
三、情节建构与人物设置中的“监生”形象
在以上所讨论的第三类监生中,还有两个比较另类的形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柳遇春和《道士船中换转金》中的邓监生。
柳遇春原先警告李甲不要贪恋烟花之地,后被杜十娘对李甲的真
/h1
情所感动,“自出头各处去借贷”,凑了一百五十两银子让李甲为杜十娘赎身。
李甲与杜十娘能够相聚,实“柳君之力也”。
邓监生则在贲监生要以银换金时,提醒邓监生提防骗术,并在换金过程中,让贲监生拿到金子后不要再过骗子之手。
骗子的骗术一开始没有得逞,都是因为有邓监生从中提醒。
表面看来柳遇春与邓监生的形象似是与此类中的其他监生不符,但需要注意的是,柳遇春与邓监生都不是各自小说中唯一出现的监生,也不是作者欲图着重刻画的人物,在他们之外都另有一个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监生形象存在,即李甲与邓监生。
柳遇春与邓监生的出现不是为了塑造一个新的监生形象,而是为了将作为主要人物的李甲与邓监生的负面性格更为突出的表现出来。
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本事《九龠别集》卷四的《负情侬传》中,原本并没有出现柳遇春,小说中特别设置了这一人物,其用意正是要以柳遇春的慷慨侠义,来衬托李甲的寡情薄幸;而在《道士船中换转金》中,由于有邓监生的精明谨慎,贲监生的愚笨浮露也便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从人物设置与情节建构上说,柳遇春、邓监生两人之所以被写成“监生”,是由于身为监生的李甲和贲监生各自需要有一个与他们关系较近的“同学”,以更为自然地推动情节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监生”身份不是出于自身形象塑造的要求,而是基于情节建构的必需。
因此,虽然由于身份的原因柳遇春与邓监生被归入第三类监生中,但从作者的用意以及实际效果的角度考虑,在讨论此类监生的形象时,可以将此二人放置一边,不予考虑。
虽然在人物形象的方面考虑,这两个监生可以忽略,但如果着眼于小说的人物设置与情节建构,柳遇春和邓监生的特殊价值便显现出来,他们提供了探讨监生形象的一个合适的角度:
所有的形象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只有在放与其他形象的关联以及情节发展的需要中,小说中的人物才有意义。
事实上,这与上面所谈的整体观照与个体特征也有密切的联系:
整体观照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对于人物身份的确定上,倘若根据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的需要,小说要表现一个“才疏学浅”甚至是“不学无术”、“愚蠢痴笨”的士人,“监生”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为适宜的一个选择。
在《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曹可成虽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但在重要性上尚不及他的妻子赵春儿。
幸亏其妻赵春儿能算计,又会持家,曹可成这才凭借监生身份选了官。
做官时,又是“老婆帮他做官”,因此“宦声大振”,并在赵春儿的劝说下,激流勇退,“夫妻衣锦还乡。
三任宦资约有数千金,赎取旧日田产房屋,重在曹家庄兴旺,为宦门巨室”。
在小说中,作者着意表现的不是“曹可成改过之善”,而是“赵春儿赞助之力”。
从人物的关系上说,在曹可成的痴笨和不会算计的对比下,赵春儿的精明能干愈发显现出来。
就这一意义而言,曹可成这一形象性格的形成,是由作者首要表现的人物——赵春儿所决定的,倘或赵春儿不是这般能算计、会持家,曹可成“曹呆子”的特性也不会如此令人印象深刻。
而在人物的身份上,“监生”不仅提供了选官的可能,使得赵春儿的精明能干得以在更为便利的条件下、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得以呈现,更由于其整体观照中蕴藏的本来意义符合曹可成的不会读书、不会算计的基本性格,而成为最适合曹可成的身份标签。
与之相似的还有同在《西湖二集》中的《巧妓佐夫成名》,这篇故事的立意与《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相仿佛,所说的都是原本出身青楼的女子女子助其夫君成名立业之事。
与赵春儿和曹可成这一对人物相对应,《巧妓佐夫成名》中的主角是曹妙哥和吴尔知,曹妙哥也是一个会算计、有谋略的的聪明女子,在故事的每一处情节中,其精明能干都以吴尔知的懵懂无识、缺乏深谋远虑为衬托。
而吴尔知非但才能上远逊曹妙哥,“胸中文学”也“只得平常”,而与曹可成一样,“太学生”的名号其也便无可推脱了①。
不同于整体观照在人物设置方面的预设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物形象的相对单薄,个体特征可以随着小说中人物关系以及情节设置的要求而做出调整,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机动,也因此而提供了更多的可供讨论的性格类型。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因见色起意,遂以钱财拆散杜十娘与李甲的孙富“也是南雍中朋友。
”但在其本事《负情侬传》中,只说其为“有邻舟少年者,积盐维扬,岁暮将归新安,年仅二十左右”,并不曾提到其是监生,由此可见孙富的监生身份应是小说作者所加。
在本事中,“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貌复绹,弄形顾影,微有
/h1
所窥,因叩舷而歌。
生推蓬四顾,雪色森然。
新安人呼生绸缪,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论心。
”而在话本中,孙富借吟诗引起李甲注意一节与本事相似,在两人见面之后,“李公子叙了姓名乡贯,少不得也问那孙富,孙富也叙过了。
又叙了些太学中的闲话,渐渐亲熟”,在此之后才有孙富邀请李甲上岸喝酒的情节。
两相对比,本事中两人从素不相识到“去酒肆论心”之间缺少必要的铺陈,多少显得有些突兀,而在话本中,由于有同为太学生这一共同的身份背景,以“太学中的闲话”作为过渡,本事中的“绸缪”二字便有了着落。
因此,以“监生”形象出现的孙富比身份单纯的邻舟少年要更有利于情节的推进,而孙富进入也便由此进入太学生的行列,丰富了监生作为形象系列存在的个体特征。
可加以特别注意的是《汪监生贪财娶寡妇》里的汪云生,如上所举,其非但学问无成,还因愚笨而为人所骗,并且既贪财,又好色,无论是从初始意义的整体观照的角度来看,还是参照个体特征上升之后的整体观照,都可算是监生中的一个典型。
除此之外,汪云生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吝啬。
在小说中,其遇着几人前来家中避雨,且要求以三百文钱歇宿一夜,“云生想道:
‘有三百文钱便留他歇一夜,落得趁他的。
只恐他这几个人要酒饭吃起来,倒不好了。
’”,不料那几人自己带有酒饭,并邀请汪云生同食,而这对于悭吝的汪云生来说,自然求之不得。
而正是由于同席,汪云生才会愈发为妇人的美色所迷,假伴做妇人之兄王乔的那个后生也才能有合适的契机以财产相诱。
在这一系列情节中,汪云生的“吝啬”成为推动故事进展的重要因素。
巧妙的是,通过作者的塑造,在汪云生的身上,“吝啬”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属性,而是在与其他各种性格的纠缠中呈现出各种复杂的状态。
如同席吃饭一段,以吝啬为主,同时亦汇集了汪云生的好色和贪财。
而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汪云生与那妇人成婚之后的情节,“将五十日,恰遇端午佳节”,由于吝啬,“汪云生只是家常淡饭,并不设酒做节”,那妇人便提议去烟雨楼看龙船,“云生想道:
‘去看未免又要破费几钱船钱。
’只因心爱了,他悭吝不得”,便应允下来,“吩咐王大舅照管家下。
王氏将钥匙都付与王乔收了”,汪云生夫妇二人这才“一船直至烟雨楼前”。
小说中没有明确交待,可还是不难看出,虽然迟至重阳节过后,王乔与王氏方才设计逃走,但正是在端午这天由于“王氏将钥匙都付与王乔收了”,王乔才有机会将汪云生所有的箱笼搬个干净。
原本吝啬成性的汪云生,本应出于节省船钱的考虑回绝王氏的提议,但其性格中的“好色”却又在此时战胜了悭吝,使其答应下来。
而从根本上说,这仍是其根深蒂固的吝啬在作祟:
相对于“几个船钱”而言,在家中“设酒做结”显然要破费更多的钱财,去烟雨楼看龙船,借他人之景装点自己的节日,无疑要经济得多。
事实上,无论汪云生有没有答应去烟雨楼看龙船,其被骗的结局都不会被改变,但由“吝啬”这一性格所引发,却无疑使得情节的进展更为自然,人物的形象也更为鲜明。
尤具讽刺意义的是,王氏逃走后,汪云生后悔不已,但他悔的不是中了旁人的诡计,而是自悔其“惜了钱财”,而王氏“逢时过节,竟不说起”,因此其说道:
“若得依先还我家私,我便朝朝夜夜元宵,我也情愿了。
”在这里,汪云生对其吝啬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但问题在于,这样深刻的反思不是基于洞明事理的理性分析,而是建立在对事情来龙去脉的错误判断上。
在汪云生看来,王氏是因为自己过于吝啬才离他而去,并拿走财产作为报复。
但实际上,王氏与王乔显然都是骗棍,哪怕汪云生真的“朝朝夜夜元宵”,王氏在拿走其财产时仍然不会对其有一丝的留恋。
汪云生之“吝啬”真正应负的责任是促使骗术更为顺利的进行,而不是引发背叛的行为。
就这一意义而言,通过这一番反省,汪云生的吝啬又和其性格中的愚笨产生某种叠加的效应,加重了小说在人物刻画上的力度。
纵观小说的所有描述,吝啬、好色、贪财、愚笨等性格都融合在了汪云生身上,其也便由一个“典型”的监生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形象个体。
类似的形象塑造方式在第三类监生中很为常见,不论是作为主要人物,还是小说中的配角,这些监生在故事中所起的作用都异常关键,他们的性格缺陷和所犯过失:
好色、贪财、愚蠢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行为,是支撑整个小说情节的决定性力量。
而随着情节的渐趋曲折与复杂,这些监生的性格特征也变得更为多样和立体。
因此,小说作者在描写
/h1
他们时,无论是对于他们自身形象的刻画,还是对于涉及他们评价的渲染,都十分着力。
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倘若抛开褒贬的态度,单纯就塑造的力度而言,这些监生的形象甚至比第一类监生还要令人印象深刻。
就此,明代小说中的监生呈现出这样一幅层次分明、次序井然的景象:
最上层是得到褒扬的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入监的监生,中间一层是被微讽的为了获取现实利益主要是参与选官的监生,下层则是受到斥责与嘲讽的只以“监生”的身份出现的监生。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第一类监生在小说中得到褒扬,但从人物的数量上来看,其却远少于被微讽的第二类监生和受到斥责与嘲讽的第三类监生。
这也便是说,哪怕第一类监生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再好,由于数量上的关系,其叠加起来的效果也势必不如后两类。
并且据前所论,由于第三类监生的性格缺陷与行为过失对于各自小说情节的决定性影响,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都极力刻画与渲染,这也使得就作者施加的力度而言,第三类监生也比第一类监生更为深刻。
因此,第一类监生所造成的读者对于监生的良好感受,很容易便会被另两类——特别是三类监生带来的负面感觉所取代。
这不免给人一种直觉:
明代小说中的“监生”并不是蕴涵了正面意义的称谓。
更多的时候,小说中的“监生”是与贪财好色、愚蠢浮露、阴险狠毒等特征联系在一起。
可是事实上,就整体情状而言,明代社会中的监生的状况可能并非如此不堪。
虽然也有邓玉堂这样仗势欺压良善的监生,但在明代的野史笔记中关于监生负面情形的记载并不多见。
台湾学者林丽月曾根据方志和通志中记载的监生统计监生初授官职的情况。
除了那些因为为官而被记载下来的监生之外,还有“不曾除官而名列史册的国子监生九十一人,多见于孝义、忠节、文苑、隐逸等列传”,多为“殊才异德或特立独行之士”。
这些人和第一节所举那些因为科名显赫而被时人津津乐道的监生一样,与当时数量庞大的监生群体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哪怕其再杰出,也不足以代表当时监生的整体状况。
但重要的是,这些入“孝义、忠节、文苑、隐逸等列传”的监生的存在本身便说明当时的监生也有值得大力褒奖的一群,这才符合与任何社会群体都会有善恶之分的基本公理。
在这样的参照下,小说作者对于明代监生负面情状的极力刻画与大力渲染便显得耐人寻味。
与“监生”在现实中的状况相比,其在小说中的总体待遇更为不堪,这既与附着在监生身上的种种属性和作者对他们的刻画方式有关,而从根本上说,又是由科举制度所决定的。
②从一种科举身份到成为某类小说角色,明代“监生”所经历的形象变化要复杂得多,也就更为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