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docx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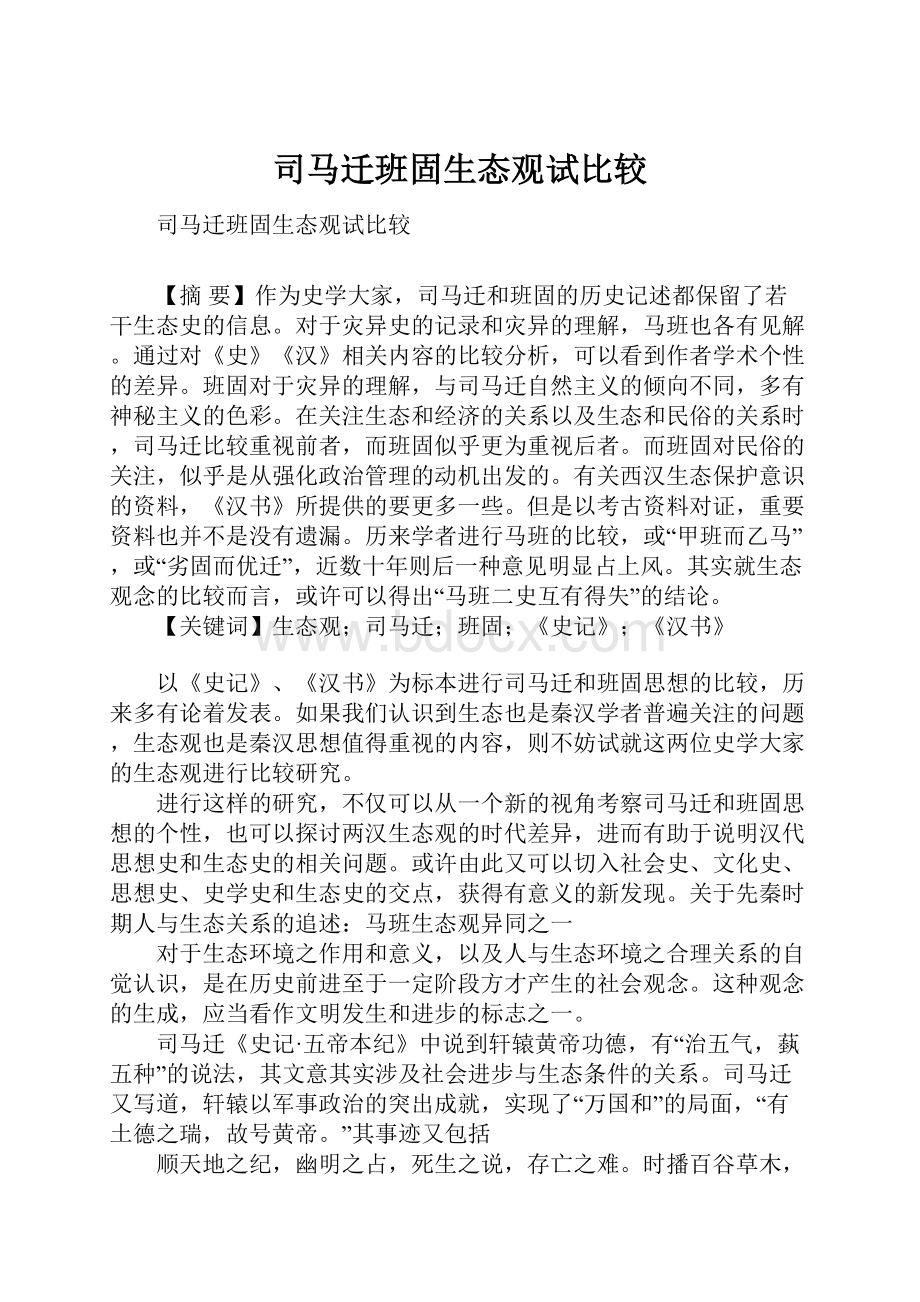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
【摘要】作为史学大家,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记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态史的信息。
对于灾异史的记录和灾异的理解,马班也各有见解。
通过对《史》《汉》相关内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学术个性的差异。
班固对于灾异的理解,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
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
有关西汉生态保护意识的资料,《汉书》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
但是以考古资料对证,重要资料也并不是没有遗漏。
历来学者进行马班的比较,或“甲班而乙马”,或“劣固而优迁”,近数十年则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
其实就生态观念的比较而言,或许可以得出“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结论。
【关键词】生态观;司马迁;班固;《史记》;《汉书》
以《史记》、《汉书》为标本进行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比较,历来多有论着发表。
如果我们认识到生态也是秦汉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生态观也是秦汉思想值得重视的内容,则不妨试就这两位史学大家的生态观进行比较研究。
进行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司马迁和班固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探讨两汉生态观的时代差异,进而有助于说明汉代思想史和生态史的相关问题。
或许由此又可以切入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学史和生态史的交点,获得有意义的新发现。
关于先秦时期人与生态关系的追述: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一
对于生态环境之作用和意义,以及人与生态环境之合理关系的自觉认识,是在历史前进至于一定阶段方才产生的社会观念。
这种观念的生成,应当看作文明发生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到轩辕黄帝功德,有“治五气,蓺五种”的说法,其文意其实涉及社会进步与生态条件的关系。
司马迁又写道,轩辕以军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实现了“万国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其事迹又包括
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有学者指出,这段话,“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
”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段文字之中,还表露了积极的生态意识。
如所谓“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体现出顺应自然的原则。
所谓“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也体现出与自然相亲和的倾向。
关于所谓“节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为孔子所肯定的。
张守节《正义》引《大戴礼》云:
“宰我问于孔子曰:
‘予闻荣荣伊曰黄帝三百年。
请问黄帝者人耶?
何以至三百年?
’孔子曰:
‘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
司马迁所论先古圣王与“节用水火材物”相关事迹,又有
养材以任地。
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又引录范蠡的话:
“节事者以地。
”司马贞《索隐》:
“《国语》‘以’作‘与’,此作‘以’,亦‘与’义也。
言地能财成万物,人主宜节用以法地,故地与之。
”司马贞的解释强调了人与“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提示应当有节制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
这样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司马迁所记述范蠡语的原意。
班固《汉书》作为以汉代历史为主题的断代史,并不直接记录远古时代的传说,因而没有与《史记》“节用水火材物”,“养材以任地”,“取地之财而节用之”一类内容。
《汉书》屡见“节用”一语,但是已经大多并非取与“地”有关的强调节约生态资源的意义,而只是就经济角度言财富。
当然,其中有些作为西汉人言辞,不能完全归结于班固的认识。
不过,我们看到,《汉书》其实也有间接涉及传说时代相关现象的内容。
如《律历志上》:
“五声之本,生于黄钟之律。
”“九六相生,阴阳之应也。
律十有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
”“其传曰,黄帝之所作也。
”“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
”又如:
“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
‘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
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
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
’”也都说到黄帝时代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和谐。
《汉书》中“黄帝”凡134见,出现频率不可谓不高。
但是班固笔下的黄帝及其言行已经神化,对于黄帝事迹的解说也已经神学化,与司马迁所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得自于民间所传诵,因而富于自然气息有明显的不同。
又如《汉书·郊祀志上》写道:
“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说,“夏得木德”,“草木鬯茂。
”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生态之关系的历史记载的片段遗存,但是这样的记载已经为浓重的五行学说的色彩所涂抹,历史的本色已经被掩盖了。
关于灾异史的记录: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二
对于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来说,自然灾异无疑形成对安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
《史记·六国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关灾异的记录,我们现在看到的有22例。
远较周王朝和其它六国密集。
确实可以证实有的学者曾经提出的《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的说法。
其中5例涉及与生态形式相关的灾异,即秦躁公元年“六月雨雪”;秦献公十六年“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河、渭绝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地动,坏城”;秦始皇帝四年“蝗蔽天下”。
对于最后一例,《史记·秦始皇本纪》写作:
“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天下疫。
”
此外,《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以及《十二诸侯年表》中又可见《六国年表》未记载的灾异。
如《秦本纪》记载:
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
《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河鱼大上”;秦始皇帝九年“是月寒冻,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地动”;秦始皇帝十七年“地动,……民大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
所谓秦穆公十四年“秦饥”,《秦本纪》中有相应的记载:
“晋旱,来请粟。
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
缪公问公孙支,支曰:
‘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
’问百里傒,傒曰:
‘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
’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
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
晋君谋之群臣。
虢射曰:
‘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
’晋君从之。
十五年,兴兵将攻秦。
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
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
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驇。
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
晋击缪公,缪公伤。
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
……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
秦妻子圉以宗女。
是时秦地东至河。
”“秦饥”在着名的“泛舟之役”之后,因“晋旱”而“饥”推想,“秦饥”很可能也是因为旱灾所导致。
至于所谓秦献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华”,所记当为一事,年代之异,当有一误。
关于秦史的灾异记录,是《史记》包涵生态史记录因而具有特殊历史文献价值的证明。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司马迁对灾异史的记录是相当重视的。
当然,班固对秦史中的灾异,记载不如司马迁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因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断代史专着《汉书》记述的对象。
此外,我们又应当注意到,班固《汉书》对于秦史灾异其实也并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对于司马迁《史记》记录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写道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
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
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
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
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
京房《易传》曰:
“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
所谓“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见于《史记》,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至于“渭水赤”的情状及原因,我们目前还不能明了。
《汉书·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则有关记录,是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此事也未见于《史记》。
《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
班固《汉书》的“志”,是司马迁《史记》之后的新创史书文体。
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记》“书”的影响。
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则皆为班固新创。
《汉书》的“志”,公认内容“博赡”、“该富”,有学者评论说,“超过了《史记》八书,可谓后来者居上。
”以往以为其“芜累”的指责,或许是将优异看作缺失了。
至于汉初史事记述的比较,“《汉》纪比《史》纪增补了一些史实,是应该肯定的。
”如“《汉》纪比《史》纪增写了一系列诏、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汉书》所立《惠帝纪》,其中有的史家所谓“记惠帝七年间四十三条大小不等的杂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现象与灾异”等。
有学者评论马班优劣,说到《史记》和《汉书》叙事的特点:
“马疏班密,向有定论,然亦论其行文耳,其叙事处互有疏密。
”就灾异史的记录比较《史》《汉》,确实可以说是“互有疏密”。
而以为《史》《汉》“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的意见,从记录灾异史的角度说,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评价。
关于灾异的理解: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三
司马迁对于历史遗存中的灾异现象,是取审慎的态度的。
《史记·天官书》说:
西周晚期以来,星气阴阳之说盛行,“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
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
至天道命,不传。
”《太史公自序》又写道:
“星气之书,多杂禨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
”《儒林列传》中记录了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斥董着《灾异之记》“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惊吓,“不敢复言灾异”的故事,也表明了这种态度。
有的学者说,董仲舒的灾异学说恰与最高权力者汉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为什么《史记》不录《天人三策》,除取裁侧重点与他书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马迁对于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结合,采取轻蔑的态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样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绝对地断定司马迁完全排斥灾异之说。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封禅书》之言祥瑞灾异之说,令人确信司马迁是相信天人对应关系的。
” 《汉书·五行志》中有比较集中的灾异记录。
我们看到,班固对于灾异的分析,与司马迁自然主义的理解不同,大多带有明显的神秘主义的色彩。
如《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史记秦二世元年,天无云而雷。
刘向以为雷当托于云,犹君托于臣,阴阳之合也。
二世不恤天下,万民有怨畔之心。
是岁陈胜起,天下畔,赵高作乱,秦遂以亡。
一曰,易震为雷,为貌不恭也。
史记秦始皇八年,河鱼大上。
刘向以为近鱼孽也。
是岁,始皇弟长安君将兵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迁其民于临洮。
明年有嫪毐之诛。
鱼阴类,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从君令为逆行也。
其在天文,鱼星中河而处,车骑满野。
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终用急亡。
京房《易传》曰:
“众逆同志,厥妖河鱼逆流上。
”
……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
刘向以为近火沴水也。
秦连相坐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横出,残贼邻国,至于变乱五行,气色谬乱。
天戒若曰,勿为刻急,将致败亡。
秦遂不改,至始皇灭六国,二世而亡。
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渭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
京房《易传》曰:
“君湎于酒,淫于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也。
”
天象被看作对人事的警告。
《汉书·叙传下》说:
“《河图》命庖,《洛书》赐禹,八卦成列,九畴逌叙。
世代寔宝,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举。
告往知来,王事之表。
述《五行志》第七。
”可知班固着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务于“王事”,作为“告往知来”的历史鉴诫。
如刘知几所说,“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释休咎,惩恶劝善,以诫将来”,于是有“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徒有解释,无足观采”之处。
其论说,有的学者认为,是运用“阴阳五行说”“将自然灾异、儒家经传、社会政治搅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义的解释”。
于是断言:
“《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观的大暴露。
” 如果人们注意到汉代文化的时代风格,或许会同意这种批判的严厉性应予减缓。
应当看到,这种现象是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
具体的说,是西汉中期以来天人感应学说的盛起和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泛滥,在影响社会文化总体的同时,也消弱了史学的科学性。
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
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
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
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
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
“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
”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
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
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着。
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
《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
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着,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
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
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
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
《史记·货殖列传》说: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
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
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
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
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
《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
班固写道: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
”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
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
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
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
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
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
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
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
司马迁笔下的“大关中”概念,“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
关于巴蜀地方,司马迁写道:
“南则巴蜀。
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
南御滇僰,僰僮。
西近邛笮,笮马、旄牛。
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汉书·地理志下》也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
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
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厄。
”
关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马迁说:
“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
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
”《汉书·地理志下》:
“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
大致看来,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
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
其说从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为了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对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肯定,有学者分析说,“《货殖列传》对我国划分经济地区作了尝试。
地理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被夸大了,……。
” 但是,就对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具体的生态形势而言,班固其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述。
《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准备在盩厔和鄠县、杜陵一带扩建上林苑时,东方朔曾加以谏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
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
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
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
”《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
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
”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
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
“美哉《货殖传》!
美哉《货殖传》!
”
关于生态保护:
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
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
“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
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
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
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
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
《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
《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
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
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
《史记·乐书》: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
”张守节《正义》:
“寒暑,天地之气也。
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
”“风雨,天事也。
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
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
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
“春秋冬夏,或暑或寒。
寒暑不和,贼气相奸。
同岁异节,其时使然。
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或为仁义,或为暴强。
暴强有乡,仁义有时。
万物尽然,不可胜治。
”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
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
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
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
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着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
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祆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
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
所谓“动静上配天,下顺地”,“四时节”,“风雨时”诸语,和上文引录的司马迁“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
而所谓“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中,则体现出生态保护的意识。
特别是将有关措施和“国家大体”、“治国大体”联系起来,应当说在生态保护史上,发表了一种开明的见解。
尽管这是在传统天人关系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还不能说是一种自觉的意识。
这是一段对于讨论生态思想史极有意义的文字,然而《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并未载录。
这或许也可以作为上文引述《史记》“残阙盖多”之说的一条佐证。
据《汉书·文帝纪》,汉文帝元年三月,“诏曰:
‘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
为民父母将何如?
其议所以振贷之。
’”这是一种“顺四时”的举动,而司马迁《史记》也没有记载。
古来有以“四时”为原则的礼俗制度,以调整和确定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秩序。
其规则通常称之为“月令”,《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淮南子·时则》等,都有相应的内容。
《汉书·魏相传》记载,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
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
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