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贰章赋体之渊源及其形式之发展.docx
《第贰章赋体之渊源及其形式之发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贰章赋体之渊源及其形式之发展.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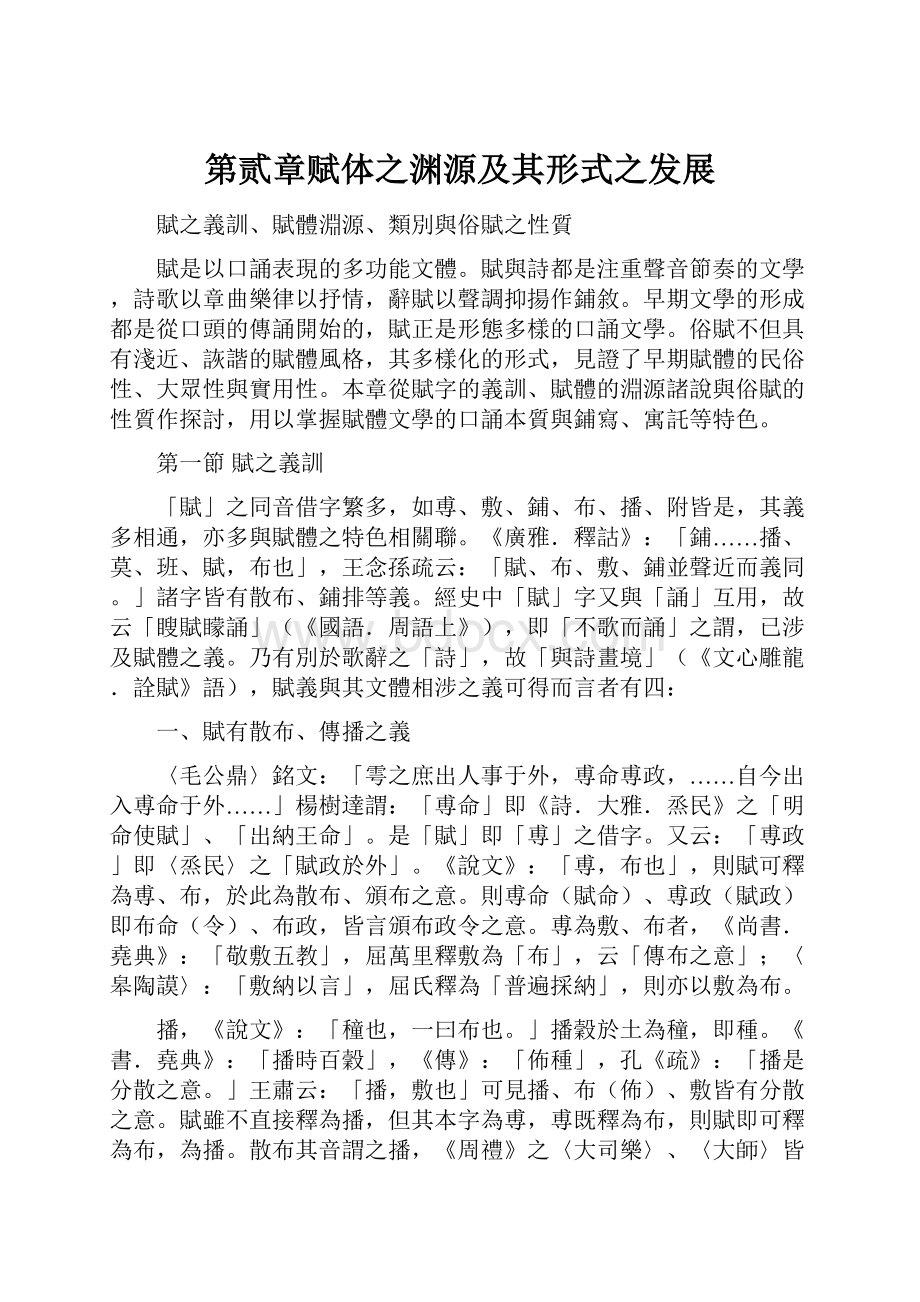
第贰章赋体之渊源及其形式之发展
賦之義訓、賦體淵源、類別與俗賦之性質
賦是以口誦表現的多功能文體。
賦與詩都是注重聲音節奏的文學,詩歌以章曲樂律以抒情,辭賦以聲調抑揚作鋪敘。
早期文學的形成都是從口頭的傳誦開始的,賦正是形態多樣的口誦文學。
俗賦不但具有淺近、詼諧的賦體風格,其多樣化的形式,見證了早期賦體的民俗性、大眾性與實用性。
本章從賦字的義訓、賦體的淵源諸說與俗賦的性質作探討,用以掌握賦體文學的口誦本質與鋪寫、寓託等特色。
第一節賦之義訓
「賦」之同音借字繁多,如尃、敷、鋪、布、播、附皆是,其義多相通,亦多與賦體之特色相關聯。
《廣雅.釋詁》:
「鋪……播、莫、班、賦,布也」,王念孫疏云:
「賦、布、敷、鋪並聲近而義同。
」諸字皆有散布、鋪排等義。
經史中「賦」字又與「誦」互用,故云「瞍賦矇誦」(《國語.周語上》),即「不歌而誦」之謂,已涉及賦體之義。
乃有別於歌辭之「詩」,故「與詩畫境」(《文心雕龍.詮賦》語),賦義與其文體相涉之義可得而言者有四:
一、賦有散布、傳播之義
〈毛公鼎〉銘文:
「雩之庶出人事于外,尃命尃政,……自今出入尃命于外……」楊樹達謂:
「尃命」即《詩.大雅.烝民》之「明命使賦」、「出納王命」。
是「賦」即「尃」之借字。
又云:
「尃政」即〈烝民〉之「賦政於外」。
《說文》:
「尃,布也」,則賦可釋為尃、布,於此為散布、頒布之意。
則尃命(賦命)、尃政(賦政)即布命(令)、布政,皆言頒布政令之意。
尃為敷、布者,《尚書.堯典》:
「敬敷五教」,屈萬里釋敷為「布」,云「傳布之意」;〈皋陶謨〉:
「敷納以言」,屈氏釋為「普遍採納」,則亦以敷為布。
播,《說文》:
「穜也,一曰布也。
」播穀於土為穜,即種。
《書.堯典》:
「播時百穀」,《傳》:
「佈種」,孔《疏》:
「播是分散之意。
」王肅云:
「播,敷也」可見播、布(佈)、敷皆有分散之意。
賦雖不直接釋為播,但其本字為尃,尃既釋為布,則賦即可釋為布,為播。
散布其音謂之播,《周禮》之〈大司樂〉、〈大師〉皆云:
「播之以八音」,鄭《注》一釋「被也」,一釋「揚也」。
〈瞽矇〉云:
「掌播柷梧、簫管、弦歌」,鄭《注》:
「播謂發揚其聲。
」告語亦稱播,《書.盤庚》:
「王播告之」,屈萬里云:
「……《說文》作譒,云:
『敷也』,按:
敷亦布也。
王播告之,言以政令告諸臣(使其傳布於民)也。
」則播有傳布之意。
二、賦有鋪張、鋪排之義
《文心雕龍.詮賦》云: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舒張、舒展曰摛,摛文蓋與鋪采同意。
賦是以形象化的鋪張誇示、排比類聚,並藉以寓託己志。
賦之本字為尃,郭店楚簡甲本《老子》:
「聖人能尃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為」,丙本「尃」作「
」,王弼本作「輔」。
丁原植釋簡本尃字云:
簡文的尃,似當作敷的本字,而解為敷。
將尃解為散布、擴延----聖人的作為,僅在順衍萬物既存的自然事實。
尃、敷、鋪皆為擴延、伸衍之意。
《詩》之六義謂讀《詩》篇的六種功效,而賦即是指鋪張、鋪排。
鄭注《周禮.太師》「六詩」云: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
」案:
六詩與《詩.序》之六義的項目、次序皆相同。
指讀《詩》之六種功用,賦即賦詩。
賦詩又有二解:
一為誦《詩》,即《國語.周語上》的「瞍賦矇誦」,賦與誦為同義之互文。
一為鋪陳《詩》,即鄭注之以《詩》鋪陳政教。
賦借為鋪,為敷,凡文章有所鋪陳、延伸、排比等,皆屬賦體之特色。
至《左傳》之賦某詩,兼含此二義,既謂諷誦《詩》章,又鋪延此《詩》句之義,以施於當時之場合。
尹灣漢簡有〈神烏傅〉,裘錫圭認為傅或賦都是假借字。
「賦比興」的賦,或「詩賦」的賦,本字都是尃,所取的都是陳述、鋪陳一類的意義。
譚學純等認為賦的敷布是有條理的,而漢賦則重空間的表示,也認為賦體的賦、傅皆為假借字,本字為訓布的尃字。
案:
古「傅」字發音同布,亦可旁證傅、尃之訓為布,有音義上之關聯。
三、賦有附加之義
賦又借為附,〈毛公鼎〉銘:
「小大楚賦」,楊樹達謂:
楚賦即《尚書大傳》之「胥賦」,《詩.大雅.緜》之「疏附」。
案:
《尚書大傳.西伯勘黎》:
「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又云:
「孔子曰:
吾有四友焉。
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與?
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與?
……」胥附即親附之意,則賦可借為附。
《詩.大雅:
皇矣》:
「是致是附」,《傳》:
「依倚之義」。
賦亦作傅,尹灣漢墓竹簡的〈君兄繒方緹中物疏〉(墓主師饒字君兄,此指「繒方緹」中的物品目錄)中有〈列女傅〉、〈烏傅〉(應即〈神烏傅〉)之篇名,皆以傅為賦,賦字蓋音近而借用。
傅,《說文》:
「相也」,相有輔助之意,與附加之意類同。
寓言、託諷皆謂附寓其事,屬賦體之所長。
《文心雕龍.詮賦》謂賦可以「體物寫志」,賦的鋪排正是為了顯其志。
鍾嶸《詩品.序》說:
「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
」清.劉熙載引《詩品》所論,也說:
「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
」可見賦以鋪陳、寓物為手段,而終以顯言外之旨。
此皆合於此「附加」之義。
四、賦有諷誦之義
「諷誦」一詞見於《周禮‧大司樂》:
「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
」此三大項或六小項之語詞都與言辭有關。
鄭《注》云:
興者以善物喻善事。
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
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發端曰言,答述曰語。
興就是比興之興,道謂道古鑑今。
諷是背誦,以口腔控制聲調之高低急緩謂之誦。
言、語指發言、對話。
賈《疏》釋「諷誦」云:
云「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云「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
但諷是宜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
諷、誦都是背文,諷是「直言」(《十三經注疏》賈疏「宜言之」,孫詒讓《周禮正義》引作「直言之」),誦則為「吟詠」之背誦,即《注》所云「以聲節之」,此為其區別。
徐養原《周官故書考》:
「諷如小兒背書,無回曲;誦則有抑揚頓挫之致。
」也說誦是吟誦,要抑揚頓挫,不只背讀而已。
「諷誦」二字雖有異訓,習見其合詞通稱,有吟誦、美讀之意。
《荀子‧大略》:
「少不諷,壯不議論,雖可,未成也。
」楊倞《注》:
「諷謂就學諷《詩》《書》也。
」王念孫《讀書雜志》引《大戴記.曾子立事》說:
「『少不諷』當從《大戴記》作『少不諷誦』,諷誦與議論對文。
」「諷誦」也見於《周禮‧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鄭《注》:
「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謂諷、誦的闇讀是「不依詠」,謂不歌(長言為詠,《尚書.堯典》:
「詩言志,歌永言」)。
誦〈世繫〉時,是以琴瑟美其聲,並不是依之而有章曲。
「播其音美之」,言諷誦時以琴瑟伴奏,但實況也難免「以聲節之」,是一種美讀朗誦。
另外近日陳韻竹謂賦應作「獻納」、「徵斂」解(說詳下文「賦體之淵源」),但與賦之文體似無相關,故不列入。
第二節賦體之淵源
賦作為文體,《文心雕龍.詮賦》嘗以荀、宋之作與詩「畫境」。
學者論賦體文學之原始,或以《詩》六義之賦義為追究目標;或以《左傳》君臣因事「賦詩」,隨機口誦詩句作為前例;或以《漢志》「不歌而誦」為賦體之表徵。
除了前節梳理的文字義訓外,有關賦體的起源與流行,大約可以概括學者諸說如下。
本節先辨析各家說法,再作綜述。
一、賦體淵源諸說
(一)出於登高能賦說
《詩.定之方中》毛《傳》云:
「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
」升高能賦,章太炎〈六詩說〉引《韓詩外傳》云:
「孔子遊景山之上,曰:
『君子登高必賦』,子路、子貢、顏淵各為諧語,其句讀參差不齊,……」是謂登高之賦為句讀參差不齊之諧語之賦體。
錢志熙引乃謂:
「賦字在先秦的場合,除了賦詩一義外,還有賦文一體;賦文一體所謂賦也。
」此係假定荀子〈賦篇〉之前已有賦之文體的名稱,升高能賦之「賦」與文中的銘、誓、說、誄一樣都是名詞。
又謂《國語》的「瞍賦」也不是賦詩,而是作賦、誦賦。
此說甚新穎,與舊注不同,而頗與章太炎氏相呼應。
唯所舉證的《韓詩外傳》孔子登景山命子路等賦參差之諧語一事,似為《詩.定之方中》篇中的「升彼虛矣」、「景山與京」文意的延伸,乃臆造之故事耳。
毛《傳》所謂「升高能賦」也許是《論語》:
「揖讓而升」之意,即堂上之賦,非登山而賦。
章太炎〈辨詩〉云:
「登高孰謂?
謂壇堂之上揖讓之時。
」毛《傳》「建邦能命龜,……升高能賦」者,並未說明其時代,若比照《國語》「瞍賦」亦為作賦、誦賦之說,則賦體文學必已發生於春秋之時。
然則歷戰國數百年,此體之名並未重現。
然則是說最多只能提供賦體名稱提早發生之可能,無法確認賦體文學真實之面貌。
蓋賦體即鋪張的口誦之韻文體,其存在形式多樣,並非一脈相承。
登山而賦之賦體,未必即「瞍賦」之賦體。
以賦之淵源而言,此說尚無法提供賦的肇始文體之真實面貌。
(二)出於諸子議對、行人辭令說
清.章學誠認為諸子的文章是賦體發展的重要動力: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
戰國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弘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
又說:
「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客難〉、〈解嘲〉屈原〈漁父〉、〈卜居〉,莊周惠施之問難也。
……」章氏所舉的賦體之特徵:
戰國問對、恢弘聲勢等,可簡化為:
問對、鋪張、排比、諧隱、類聚等賦的要素。
章氏認為此諸要素都可在戰國諸子的文章中找到例證。
說明戰國時百家爭鳴的創作態度,頗能突出自我,「恢弘聲勢」,造成賦體的蓬勃發展。
章太炎則指明「賦之本」是縱橫家或行人之官:
縱橫家者賦之本……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于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
……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
縱橫家靠口才利辯行遍天下,常假設多種情況,以備權衡。
與散體賦的設辭問對的結構與好為誇張之辭最為相近。
趙逵夫舉《戰國策.楚策一》莫敖子華的「對楚威王」,認為是「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龍.詮賦》)的結構方式。
而〈楚人以弋說襄王〉(《史記.楚世家》)、〈說劍〉(《莊子.雜篇》)、〈莊辛謂楚襄王〉(《戰國策.楚策四》)皆與宋玉諸賦之結構與語言風格相接近。
此皆縱橫家、行人之辭,可說是早期賦的形式。
(三)出於瞍矇賦誦說
《國語.周語上》云:
「瞍賦矇誦」,瞽者將史實、箴訓向君王諷誦,以提醒執政者不可怠忽。
趙逵夫認為研究賦的起源問題,應參照賦的實際形式而作探討,認為以對話為主的文賦,即出於瞍矇對行人辭令和議對的改編:
……文賦則主要來自行人辭令和議對。
行人辭令用於國與國之間,議對則是國內的,包括臣子向君主的諷諫和遊士向投奔國的陳說,其中既有事先準備好的書面的陳辭,也有陳辭後追記的文字,也有上書、書信。
……就文賦而言,由行人辭令和議對到賦,必有一個轉變的過程。
……。
矇瞍以其有很強的記憶力和很好的聽覺能力……古代留下的文獻,讓他們卻講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悅耳動聽。
應該說,他們講誦的辭令或議對,其內容和基本框架是有所依據的,但語句變得那樣整飭而有很好的節奏感,是經過了適當的調整、加工和潤飾的。
趙氏並舉《師曠》一書為例,謂是師曠以後的瞍矇收集有關的材料編輯而成,以證成其說。
又說《國語》中很多的精彩鋪陳是左丘明及以後的瞽史及瞍矇,為了講誦而收集加工而傳下來。
案:
雖然無法直接知道瞍矇講誦的內容是否即是辭令或對問,但《國語》說「瞍賦矇誦」的同時,也說「史獻書」、「百工諫」,都是對執政者規戒的分工情況,其中可能即含有議對、辭令等資料的誦辭。
趙氏從各種先秦文本實例,去追蹤推論,頗能梳理出政治上的辭令與議對成為文賦的可能過程。
這些辭令與議對雖然沒有用韻,但其設辭、鋪排的手法幾乎與文賦無異,認為它是賦的上游之一,應屬可能。
若然,瞽瞍無法自行下筆書寫,此種整飭之體應透過「史」的修潤而成為國史的一部分。
這也應是《左傳》、《國語》等史書編纂的過程。
(四)出於俳優辭說
曹明綱依據《史記.屈賈列傳》所說的:
「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
」正是賦名、賦體得以行世之時,論賦之起源應以此先秦賦為準。
荀子、宋玉、唐勒的賦作即具備主客問答、韻散配合的賦體特徵(即別於詩,又別於文)。
而俳優之辭正好合乎此二特徵。
曹氏舉出《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諫葬馬、淳于髡以隱語齊威王和諫長夜之飲為例,說「可以看出問對和韻散配合是始終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淳于髡之諫)觀其整篇結構和體式,與〈漁父〉、〈卜居〉和宋玉的〈風賦〉完全相同。
」
曹氏認為俳優之詞具有民俗性,因為優人地位低下,但他們常有「抑止昏暴」的正義感,以一種隱而不晦,戲而不諛,亦韻亦散,亦莊亦諧的口誦形式與帝王等周旋。
因此詼諧的俳詞具有民間文學的娛樂性與通俗性。
案:
史書上優孟、淳于髡的諧言韻語,都已是整飭的文字,似非當時發生的實錄。
作者有可能即是當事人,而《史記.滑稽列傳》即援引其文入傳。
猶《史記.屈賈傳》之引用屈子〈漁父〉本文當作屈原之生平行事;《漢書.東方朔傳》:
「客難東方朔曰:
……。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即引朔的〈答客難〉為其傳文,且篇中人物皆不避自稱(稱:
屈原或東方先生),與宋玉的諸「對問」自稱其名相同。
淳于髡的諫長夜之飲,全文近三百七十字,若含前文淳于髡講述「道傍禳田」的寓言,將近七百字,已是一篇詼諧諫諍的問對故事賦。
漢初枚皋等人以文學得寵,〈賈鄒枚路傳〉云:
「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
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媟黷貴幸。
」可見地位似俳優的文學侍從,仍然以嫚戲的「賦頌」爭求顧寵。
〈東方朔傳〉中的隱語、射覆辭、對武帝問以古人為諸臣的「封官榜」等,推測也應是東方朔自己的傑作。
趙逵夫提到淳于髡撰述《晏子春秋》及其為通俗之體裁:
《晏子春秋》的篇章或為對話體,或以問對的形式引起議論,……而其中不少篇章又句子齊整,多排比,尤多四言,語言口語化,……雖然不押韻,也不是完全整齊的四言句,但從結構、風格來看,已具俗賦的多種特徵。
如《諫上》的〈景公不恤天災〉、〈景公從畋〉……等。
有的實際上是同一故事的不同傳本,……可見關於晏子故事,講述人很多,因而形成多種傳本,是淳于髡將其收集起來,未作剔除整理,並為一書。
可見俳優對諷諫賦體的蒐集有所用心,這種俗賦對賦體的成長演化有很大的助力。
(五)不同賦體各有淵源說
馬積高認為賦的形成有三種途徑:
(一)由楚歌演變而為騷賦,
(二)由諸子問答體和遊士的說辭演變為文賦,(三)由《詩三百篇》演變而為詩體賦。
又區別辭賦為:
騷賦、詩體賦、文賦、古賦、俗賦等類。
趙逵夫謂各賦體皆源於戰國之前,〈離騷〉、〈九章〉、〈遠遊〉、〈惜誓〉、〈九辯〉皆為騷賦;文賦(散體賦)主要來自行人辭令和議對,(參前文引)〈橘頌〉、〈賦篇〉、〈遺春申君書〉皆詩體賦。
案:
此說不拘單一來源,頗為近實。
馬說以《詩三百》為詩體賦之祖,但《詩》以樂章為結構,雖屬齊言,似與誦體的賦有其差別。
而所區分的文賦與古賦中,俱含漢文賦、駢賦,可見其分體仍有過於形式化之失。
蓋歷代賦體固有所承受,亦不斷受其它文體之影響,如駢文、雜文之類,甚至民間尚存有多樣而活潑的應用體製,皆非少數形式或來源可以規範者。
(六)源於賦詩說
班固云:
「賦者,古詩之流也」,陳韻竹謂賦應作「獻納」、「徵斂」解,賦不是「朗誦」、「創作」或「鋪陳」之義,認為班固之說信而有徵:
論文澄清「賦」不是「朗誦」、「創作」或「鋪陳」之義,「賦」應當作「獻納」與「徵斂」解。
「賦詩」是古代聖王的典制,始初作為周代禮樂制度中的一環,是古代聖王以「知得失,自考正」為目的,「徵斂」諷諫勸正的言語。
「賦《詩》」其所蘊含的政治精神與意義,乃往後「賦」體發展上重要的關鍵,《荀子‧賦篇》所以取「賦」字以命篇,當有追緬王政理想典制的義涵,「古詩」與「賦」在諷諫怨刺的政治功能與意義上,在始初對王政理想追求之宗旨上,是一脈相承的,「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諸人的賦體「詩」源說,是信而有徵的。
陳文說明了「賦詩」的政治制度,卻說賦不是朗誦、創作或鋪陳之義,即否定了文體在演變過程中所釋放的模式概念。
案:
朗誦、鋪陳俱是賦體文有別於其它文體的重要特徵,後人之創作也在此模式上琢磨。
詩與賦都有諷諫作用,在政治上有其貢獻,但民間的應用賦體也各佔領域,在文藝舞台上發揚光大,並非「賦詩」所能解釋。
朗誦(諷誦)與鋪陳正是敘述此一文體特色的交集之處。
二、賦體淵源綜論
上引諸說,除俳優之辭外,大部分都是就文人雅賦而言的。
實則論賦之起源,可就其產生的人類語言原理來探究,即是指口誦的表達方式。
歌、誦都是聲音的美化:
重複歌辭以便謳詠則為「詩」,故有所謂「章曲」;抑揚語言,「以聲節之」,用以諷誦,其體則為「賦」。
詩常全篇用韻,故以齊言為主;賦除韻句外,有散體與駢儷,常為雜言。
探究賦之淵源也可依賦的各種體製,分別上溯。
此涉及民間體裁與文人撰述的交流問題,及演化中俗體的存少佚多的問題。
雅俗之辦,如瞽史的賦誦體,雖屬宮廷中的雅體,但也可能是仿自民俗之體,雅、俗之間並不如後世所見的偌大差異。
當時瞽史諷誦的作品,迄今雖無所見,但師曠(瞽)與周太子對話的《逸周書.太子晉》即可視早期的對問賦或故事賦,可視為雅體,也可視為俗體。
文獻的不足也影響對賦體淵源的判斷。
由於西漢故事賦〈神烏傅〉的出土,得以印證禽鳥賦的來源可以更早,否則曹植的〈鷂雀賦〉或被視為故事賦之祖。
既以「誦」為賦的基本定義,可以認為賦體是多源頭、多型態的。
而同一種形態的賦體,可以雅、俗俱見,如「成相」雜賦(見《漢志》名目)可上溯到《荀子.賦篇》、〈為吏之道〉或淮南王之作;而民間「招魂」之體也可以上溯到屈子。
可見雅、俗文體總是互相影響,共生共榮。
第三節賦體之類別
賦體來源頗雜,故形式非一。
《漢志.詩賦略》區別賦之作品為四類,以作者名領銜者有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共三種,其它作家各連類附之於後,另有無主名的雜賦一種。
其區分條件學者各有推敲,如章太炎云:
「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蓋縱橫之變也。
又認為淳于髡之諫酒,東方朔之隱,管輅郭璞有韻的占辭都是雜賦。
《文選》則以賦之題材作為分卷的依據,另設有七、對問、設論等類。
祝堯《古賦辯體》分辭賦演進為五個階段:
楚辭體、兩漢體、三國六朝體、唐體、宋體;又論辭賦有四體:
古賦、俳賦、律賦、文賦。
明.徐師曾《文體明辨》云:
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為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荀況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若今人之揣謎,於《詩》六義不啻天壤,君子蓋無取焉。
兩漢以下,作者繼起,………故雖詞人之賦而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為古賦之流也。
三國兩晋,以及六朝再變而為俳,唐人又再變而為律,宋人又再變而為文,夫俳賦尚文而失於情,……。
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文賦尚理而失於辭,……至於律賦,其變愈下,……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為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
《文體明辨》之分體今學者多所採認繼承,但其評比之辭亦有可議者。
一為過於崇古,凡屬古賦即謂合乎詩之六義,言俳賦則云重辭而失於情,云文賦指其尚理而失於辭,至律賦則謂情與辭俱失,此恐陷於主觀及過於籠統。
二為尚雅輕俗,謂〈賦篇〉不合六義,君子無取。
案之《漢志》,〈隱語〉十八篇即屬「雜賦」,何以兩漢之作是「古賦之流」,「比興之義未泯」,而《荀子》隱語則不可取?
就比興而論,〈賦篇〉屬客主對話,禮、知、雲、蠶、箴五篇各有深遠之喻旨。
豈以其體於後世未有繼承,又視隱語為文字遊戲,遂忽略其比興風喻?
《荀子》又有〈成相〉,係韻誦體的聯章,為說唱體,〈漢志〉歸在「雜賦」之列。
似不宜視之為民謠。
凡此皆重雅輕俗之弊,亦忽略賦體本為概括多種形態之綜合體裁。
今學者對歷代賦之分類多據格式句法而論,如云有騷體、詩體、散體、律體之類。
此類依形式之區分法,固有簡括、整齊之效,然頗無法突顯賦體特徵。
如騷體與詩體同屬齊言,差別只在語氣詞之有無;散體中兼有對問、俳諧,並無法顯現類名之義涵。
至於其增設俗賦一體,極能概括敦煌俗賦發現以來之各種白話賦、實用賦之體。
然此俗賦係依屬性而命名,與其前依時代、依體式而名者又有不同。
故對賦體之區分標準,似乎頗難「一以貫之」。
其實賦之分類應兼顧形式與內涵,能夠突顯其「屬性」,始為較適當之分類法。
故若兼採形式與內涵特色,作為分類標準,應可將賦體區分為六類,略述如下:
一、自述表志的騷體
屈原的〈離騷〉是抒情述志的吟誦詞,其中多充滿誇張、想像的描寫。
於句中或句尾加以「兮」、「些」、「只」之語助詞。
屈子又有〈大招〉、〈招魂〉、〈九歌〉、〈九章〉等篇,宋玉等及漢以後之作者繼之發揚光大。
《文選》立「騷」體以名之,以別於「賦」體;《文章緣起》亦分立「賦」與「離騷」。
學者對於凡模擬〈離騷〉之體裁語氣者,稱之為騷體賦,以與漢代設辭的散文賦等相區別。
趙逵夫說到宋玉、唐勒、景瑳對屈原〈離騷〉以後騷體的演進:
宋玉、唐勒、景瑳……發展了騷賦鋪排的特徵,而宋玉的騷賦在心理描寫和借助自然現象以抒發感情方面,大大發展、豐富了屈原的抒情手段,使騷賦在心理描寫方面達到很高的水平。
唐勒將屈原浪漫主義創作方法同當時齊、楚一帶流行的神仙家思想結合起來,在原始神話之外引進不少新的意象,使得展示作者思想意識的材料、部件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徵,在遊仙詩、遊仙賦的方面,給後代以很大影響。
景瑳之作比較質直,……接受屈原法制思想,在張揚屈原精神方面有其他任何篇都不能替代的作用。
宋玉、景差、唐勒等雖「祖屈原之從容詞令,終莫敢直諫」,但創造了婉約諷諫的賦體新面貌,成為設問鋪寫大賦的先聲。
漢代的騷體名著有賈誼〈鵩鳥〉、〈弔屈原〉,司馬相如〈長門賦〉,司馬遷〈悲士不遇賦〉等。
三國時禰衡有詠物的〈鸚鵡賦〉,曹植有〈蝙蝠賦〉。
至唐、宋的詼諧短賦仍或採用此體。
似乎「些」、「兮」、「只」之尾音遺響,頗透露出作者對政治的歎息。
雖《史記》將「辭」與「賦」混同看待,但騷體賦與設問賦在形式與內涵上的差異,使二者終於分道揚鑣。
以文學史的進程而論,楚辭體的句法固定,內涵上多用於個人遭遇的咨嗟感慨;賦體則隨著時代建立其特色,不斷創造新的內涵,在口誦文學的基本定義上,作更開闊的發揮。
騷體賦也被文人用來作為雜文,稱為賦體雜文。
它們雖不用淺近的文字,但以騷體寫訴訟之文,充滿著刺謔語氣。
如韓愈〈訟風伯〉、柳宗元〈愬螭〉,都是代表人民對旱災、水怪的控訴,主旨則是「作者希望以王法綱紀來管制權臣的政治訴求」,及針對迷信的破除。
二、設辭說理的問答體
設辭說理賦以問答形式突顯自喻、諷諫之主旨,多為散文、韻文之合構,或純為散文。
對問體實為賦之嚆矢,屈子有〈卜居〉、〈漁父〉,宋玉〈對楚王問〉、〈高唐〉、〈好色〉、〈大言〉、〈小言〉等,漢代的鋪寫大賦,〈漢志〉「雜賦」中的〈客主賦〉,晉.阮籍〈大人先生傳〉等賦體雜文(參本節「諷刺現實的賦體雜文」)皆屬此體。
簡宗梧認為先秦、西漢與東漢以後的「客主」問對體,歷經三次演變:
賦體設辭問對可分三個階段:
先秦宮廷暇豫之賦,大多是朝廷口才便捷的優者暇豫時戲謔逗趣,或迂回諷喻的對話記錄,是真有其人的言語侍從與帝王的對話。
其賦作即使經過整理修飾,仍保留對問體的形式,並以其為大宗。
到了西漢,由于宮廷待詔的賦家眾多,不太有機會與帝王即席對話,其賦都是「受詔」而作,賦家是以先寫劇本式的書面創作方式進行,所以更需要虛擬人物展開對話。
從東漢到六朝,賦不再是日誦耳受的聲音藝術,欣賞者閱讀書面文宇,但賦家仍有采「為主客之分而為對問之體,以曼衍其辭」者,乃借古人代言。
此係從政治生態的改變,說明從俳優的詼諧賦,到待詔賦家的虛擬人物,到完全假託歷史人物的對問賦體的進程。
俳優之賦,見諸《史記.滑稽列傳》優孟、優施之記事。
其對話採滑稽的韻誦體,並表現俳優犯言敢諫的正義態度。
這種韻誦的問答體,也見於民間的故事、論辯賦體。
如《逸周書.大子晉》的機智對話即是用韻,學者多以為是俗賦之體,是民間設問賦的形態。
三、詠物託喻的齊言或雜言體
西漢除了設論的大賦之外,短篇的體詠物賦,多以四言而參以五言、六言。
或稱為「詩體賦」。
四言的屈原〈橘頌〉、荀子〈賦篇〉都有詠物表現及諷諫功能,被視為四言詠物的先聲。
但〈橘頌〉含有「兮」的助詞,可歸入騷體。
〈賦篇〉較接近齊言的詠物鋪寫形式,以君臣對話體的隱語表現,也與西漢詠物賦相似。
西漢四言詠物賦多為應詔即席作賦,文中常見祝賀頌贊或謙卑自稱之語。
如枚乘〈柳賦〉於文末說:
「君王淵穆其度……小臣瞽聵陳詞,……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鄒陽〈酒賦〉說:
「吾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