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纪正我的武术情缘.docx
《阮纪正我的武术情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阮纪正我的武术情缘.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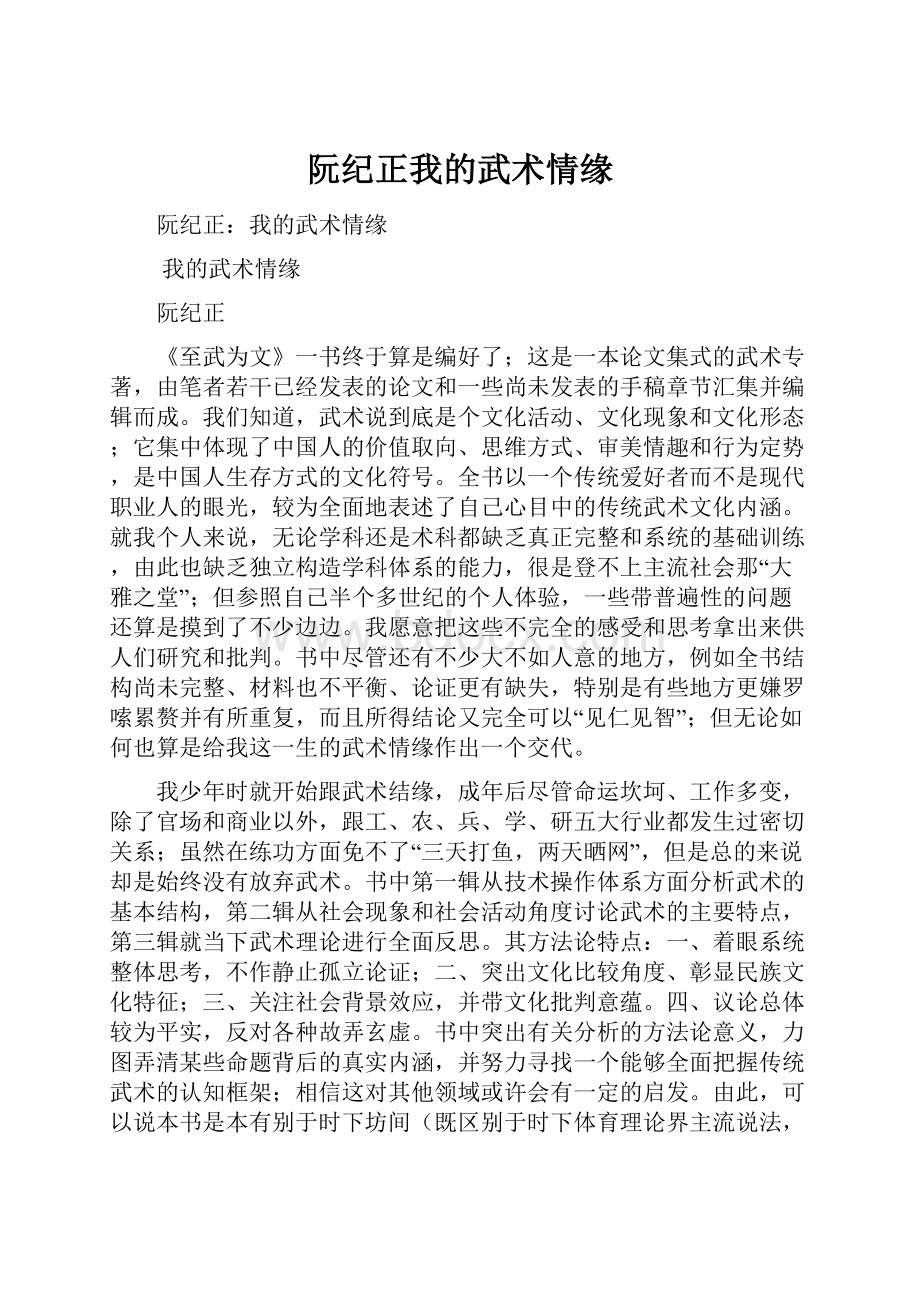
阮纪正我的武术情缘
阮纪正:
我的武术情缘
我的武术情缘
阮纪正
《至武为文》一书终于算是编好了;这是一本论文集式的武术专著,由笔者若干已经发表的论文和一些尚未发表的手稿章节汇集并编辑而成。
我们知道,武术说到底是个文化活动、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行为定势,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文化符号。
全书以一个传统爱好者而不是现代职业人的眼光,较为全面地表述了自己心目中的传统武术文化内涵。
就我个人来说,无论学科还是术科都缺乏真正完整和系统的基础训练,由此也缺乏独立构造学科体系的能力,很是登不上主流社会那“大雅之堂”;但参照自己半个多世纪的个人体验,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还算是摸到了不少边边。
我愿意把这些不完全的感受和思考拿出来供人们研究和批判。
书中尽管还有不少大不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全书结构尚未完整、材料也不平衡、论证更有缺失,特别是有些地方更嫌罗嗦累赘并有所重复,而且所得结论又完全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也算是给我这一生的武术情缘作出一个交代。
我少年时就开始跟武术结缘,成年后尽管命运坎坷、工作多变,除了官场和商业以外,跟工、农、兵、学、研五大行业都发生过密切关系;虽然在练功方面免不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是总的来说却是始终没有放弃武术。
书中第一辑从技术操作体系方面分析武术的基本结构,第二辑从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角度讨论武术的主要特点,第三辑就当下武术理论进行全面反思。
其方法论特点:
一、着眼系统整体思考,不作静止孤立论证;二、突出文化比较角度、彰显民族文化特征;三、关注社会背景效应,并带文化批判意蕴。
四、议论总体较为平实,反对各种故弄玄虚。
书中突出有关分析的方法论意义,力图弄清某些命题背后的真实内涵,并努力寻找一个能够全面把握传统武术的认知框架;相信这对其他领域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
由此,可以说本书是本有别于时下坊间(既区别于时下体育理论界主流说法,也区别于民间若干神秘主义想象)论著,并极具个人特色的武术理论著作。
我出生于抗战时期的“走难”路上,幼儿时还曾经从二楼上跌到并滚下楼梯,个人体质一直以来都极为虚弱,年轻时走路还经常无故晕倒,有次在雨中甚至还跌入水沟差点被淹死;而且学习领悟能力并不高,特别是动手操作能力和考试应对能力则更差,上课时根本搞不清老师在说些什么,小学一年级起就连续两年留级(这里特别显眼的是,我从小学到大学体育课考试从来都是不合格的),青少年时父亲还曾一度把我视作不折不扣的“低能儿”。
加上生母很早去世,长期被寄居在中山县溪角乡龙瑞村的姑妈家里,入读该乡小学。
由于姑妈是嫁到外村(我的祖籍是该县象角乡的的圣狮村)而不在本村,所以当地小孩也就经常把我当作“外村人”经常进行欺负(例如,把我捆在树上并塞生的香蕉要我吃)。
1956年春节后从乡下转到广州盘福路小学读书,结果是到了初中时又被一些较为强悍的同学当作“乡下人”来欺负(例如用所谓“报区”即以木屐的底部打我的头,又以课桌上我的手“过界”为借口,把我的腿也打红了;如此等等),后来还被一些人视之为鲁迅笔下那个胆小怕事和迂腐无能的“孔乙己”,给我起的外号是“阮女人”;于是从小就就萌生了某种练武强身自卫的心理倾向。
最初跟武术明确结缘的动念发愿,起于有次跟小学同班同学区湛生一起到广州青年文化宫观看演出;舞台上有两个小姑娘表演剑术,其点刺拦抹、攻防有序,闪展腾挪、纵横往来、英姿勃勃、潇洒自如,这让我和区湛生两人在精神上都感到一种震撼。
由此便开始到处留心有关武术的事情。
1957年夏天,我考入广州知用中学(入学后不久该校便改称广州28中,改革开放后又恢复了“知用中学”的名称)读初中。
这时学校有个语文老师叫马志斌,曾经参加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比赛得了个武术名次回来(后来还当上了省武术队和市武术馆的总教练),于是在校内搞了很多宣传,要在学校里兴办武术班。
我喜出望外并第一时间跑去报了名。
不料入学测试的结果却被判定为“基础素质极差,根本不是学武的料子”,于是无论怎样苦苦哀求也不予录取。
平心而论,我的身体孱弱、性格内向、反应迟钝、能力低下,确实没有什么培养前途,很难夺取锦标来为老师争光。
不过这次拒教却大大激发个人自尊和自学武术的热情,有道是求人不如求己,于是便花了几毛钱到书店买了些武术书籍,自己偷偷地开始看图识字般的自学,开始了见招拆式那最初的动作形态结构的思考。
最初看的是蔡龙云的《中国武术基础训练》和王子平的《拳术二十法》(后来还陆续看过一些华拳、查拳和新编长拳的著作,比较过马志斌传授的滑拳和花拳、华拳、查拳等特点),书上插图很多,于是就看图识字般“依冬瓜画葫芦”地比划起来。
当时我班上李正、刘文华、陈建国等好几个同学正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跟陈咸民老师学练顾汝章传下的十路“北少林”,每个月要交学费5元。
我交不起这个学费,于是便跟这些同学约好来个互教互学;我把从书上得来的东西教给他们,他们则把师父传授的东西转授给我。
就这样,我跟他们学了四个“北少林拳”的套路(其中的第六路少林拳套路,至今我还全部记得),还有一套“龙行剑”和一套“少林对打”(到现在,我只记得几个典型招式)。
此外,班上的刘照基同学跟他爷爷学过“洪拳”,我也跟他学了一些南派武术的基本手法。
我的同学和拳友大都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并不相信这传说中武术的那些神功异能,所以除了例如《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唐》、《说岳全传》、《小五义》、《三侠五义》等一类较为经典的武侠小说外,一般都不去看清代公案小说和民国新派武侠小说,觉得其中大都其实是些“怪、力、乱、神”的虚幻东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朋友极力推荐下才看了一点金庸小说,尽管故事情节讲得比较引人入胜,但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什么武术理论,而是一种影射现实的政治寓言)。
我所感兴趣的东西,只是新式科学所能解释的现实可能性,而并不是不着边际的那些心理宣泄和审美想象的虚幻满足感,一开始就企图着力去搞清一个客观的为什么。
大约是在1958年,我在书店偶然看到徐致一先生编著的《吴式太极拳》,觉得十分兴奋;书中运用近现代的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对太极拳的操作机理进行分析,其理论支撑较为扎实;特别是其中关于合力、分力、力偶、尖劈、螺旋、重心、平衡等等方面的力学分析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该书引导我的思考着眼于“以弱对强”和“以柔克刚”的客观可能性,提高了我这个弱者的自信。
不久又陆续地看到吴孟侠等编著的《太极拳九诀八十一式注解》和杨澄甫的《太极拳体用全书》,眼界逐步扩大,1959年又请香港的亲戚在香港为我买到吴志青编著的《太极正宗》和王新午编著的《太极拳法实践》等太极拳书寄来,进一步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并由此下决心要改学太极拳。
为了探究有关太极拳的机理,我开始专门找来力学方面的“运动学”、“动力学”,还有综合性的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力学,以及与此相关那社会方面的《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相关著作进行学习,进一步努力从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速决战以及内外线作战、根据地、后勤支撑等一系列不同角度对武术的技击能力进行综合性的思考。
由此看来,我对武术理论的整体性关注,开始得其实并不太晚。
1959年可以说是我的“武术年”。
该年初,我就借助学校体育老师的帮忙,终于挤进了刚刚开办的广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武术班(当时所有的业余班都是免费的),开始正式跟黄啸侠老师(当年是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武术协会主席)学练弹腿,跟赖忠老师学练六路短拳、龙行剑和南派的单头棍。
班上每个学员好像都有一定的武术基础,举手投足都相当像模像样;而我的基础则可以说是全班最差的,操作上无论怎样弄都被指责和挨批评。
每次训练下来,班上除我以外的每个人都说自己收获很多、进步很大,但我的感觉却是每天都在退步,搞不清到底有什么收获,反正一动起来就“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周身动作总“不得劲”,无论怎样做也都觉得“不靠谱”。
不过,大约这也是发现差距,让我笨鸟先飞吧。
在武术班的同学里面,我看来还是属于比较努力的。
回到知用中学,我已经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武术千人操(男生用刀、女生用剑)”集体表演活动,到越秀山体育场的省运会上为群众演出,动作起来好像也颇有点模样。
当时我特别重视下盘功夫的训练,每天弄到两条腿沉重的像灌了铅一样,连上楼梯都想跪下来。
中学同学发现我每天都几乎是第一个到校,在操场上手舞足蹈地反复比划。
到了业余体校学习的后期,我在不少地方便开始赶了上来,居然还被推选为班上两个重点培养对象之一,有人甚至还建议我去报考体育学院。
到了1960—1961年国家经济困难大家饿肚子的时候,上级体委为了保证体校学员的健康,学员们的粮食定量不但一直都维持了每月30斤,而且每次训练还给参加训练的学员供应半斤饼干。
我连续多年每个星期天都坚持去市体育馆进行训练;但到底什么时候离开这个班,则已经记不清楚了。
有道是“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古代练功还特别讲究“财、侣、法、地”四大条件,我学练武术也有几个比较铁的哥们。
武术班中有两个跟我来往很多的拳友,一个叫张煦阳,是知用中学比我高一届的校友,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当了省汽车修配厂的电工;他是个小小的武术家,五岁开始就跟佛山精武会的老师学拳,有专门的太极老师佛山区荣钜,练过鹰爪、太极、六合八法等不少拳种。
当时每个月香港还有武术老师来广州为他辅导。
张煦阳的模仿能力极强,说起武术典故也显得头头是道,由此便自然地成了我的小老师。
另一个叫谭燮尧,是广州十三中的初中学生,很有才气,但后来却竟然一直都没能考上学校,成了没有固定职业的社会青年;他后来跟张煦阳的妹妹结了婚,夫妻一起自学中医并当了社会游医,改革开放后居然还摇身一变成了个“大气功师”。
谭燮尧是个非常活跃的文学青年,真正的博览群书,看过古今大量的武侠小说,并且还极为熟悉中国近现代文学和俄国、苏联文学,也看过一点西欧和北美的近代文学。
他关于“文学与生活”的议论开启了我对“武术与社会”的注意,他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评论则让我对文学了解的重点从古代转到近现代,由此还促使我开始了对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和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关注。
张煦阳这时还介绍他的朋友袁全给我认识(说起来袁全还是我在盘福路小学的前后届校友,受业于同一个班主任),后来也成了我的铁哥们(他在本世纪初借助我加拿大表弟的担保,移居加拿大)。
袁全也是从五岁开始学拳,是广州名拳师傅永辉的入室弟子,腰腿基本功极好,各方面的理解能力也特强,学习成绩相当拔尖,当时在广州市的武术集训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一直都垄断了省、市武术比赛内家拳类青少年组的冠军;八十年代初傅永辉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徒弟中练得最好的就是袁全),1962年成了华南工学院的大学生,1979年还考上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偏微分方程”数学研究生,是个非常高明的电脑专家。
他那数学式缜密思维和对社会信息的高度敏感,后来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的自然科学知识很多都是从他那里听来或受到启发的。
当时我们几个少年人经常聚会,一起讨论武术“学术”问题。
也是1959年的夏天,国家开始正式推广普及简化太极拳。
省、市的武术协会联合在沙面网球场开办简化太极拳的学生暑期普及班,只收5角钱的报名费,不收学费。
于是马上赶去报名,每天早晨从越秀山脚盘福路的家中步行赶到沙面网球场,跟那里主持教学的邓锦涛老师(侠拳名家)学练24式简化太极拳,学完后又赖着不走,继续学练88式杨式太极拳,并悉心比较原先业余体校所学,体会刚柔两种不同武术的主要区别。
这个时期我还跟袁全等拳友相约一起,分别写信向徐致一老师问艺,并获得相当详尽的回信指导。
徐致一老师回信说,袁全的理论基础很好,问题都提到点子上。
我提的问题则大都围绕在步法和腿法上面。
朋友中还有一个叫“老洪”的工人,居然还跟姜容樵老师联系上了(后来老洪还给我弄了一条练习用的长棍子)。
在操作上,我们集中在太极桩功和推胸、推肩、推腹、推胯等基本功练习上,努力体会劲力运行的得力和不得力,追求全身本体感觉的“功夫上身”。
1960年我还尝试写了第一篇武术学习论文《谈谈太极拳的步法训练》,并以“广州28中太极拳学习小组”的名义,大胆地投给了《羊城晚报》副刊;结果则是很快地作退稿处理。
我这时确实还是很不成熟,达不到全面和准确分析问题的能力;不过,这篇早期论文也体现了我对武术训练重点的理解和把握。
大约是1959年的秋冬,经济困难开始在全国蔓延,人们普遍感到吃不饱。
为了减少人们的活动强度,太极拳于是被政府推荐为主要的课外活动方式。
知用中学的前校长张瑞权先生(这时已经当了广州市副市长)特意为知用中学的老师请到广东省文史馆的岭南派古琴名家杨新伦老先生(直到30年后的1990年,我才知道,杨新伦老先生的背景身份原来是20年代上海精武体育会派来协助成立广州精武体育会的技击部部长),为老师们传授传统正宗的杨式太极拳(杨老师原先跟李瑞东侄子李子廉学李式太极拳,后来到上海精武会跟傅钟文亦师亦友、用太极五星锤与之换艺,互教互学又学练了杨式太极拳)。
我也乘机跟在老师们后面一起比划。
杨新伦老师见我很努力,于是便叫我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单独辅导我练单推手。
当时常去老师家练拳的还有钟锦章和孙德輝两个同学,他们两人主要练套路,我则主要练推手。
杨老师当时很少给我们談理论,更多的则是辅导我们进行操作。
他带我练推手时进退的幅度纵深很大,而且只能跟着画圈,不允许硬推硬拨;就这样,我的腰腿功便初步地练了出来。
这种简单的反复单推“打轮”从1959年秋到1963年9月持续了四年,直到考取了北大离开广州时才告一段落。
1963年底,经北大生物系一个原是广州知用比我高一届校友的引荐,我开始进入北京大学武术队太极拳组,跟随教练李秉慈老师进一步学练国家套路和太极剑。
但由于我自学的拳风太杂,动作并不规范好看,不能参加比赛拿成绩(1964年的一次北京高校武术比赛,我搞了个自编的套路,裁判们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经会商后给了个7分多点,根本不能入围),所以只能呆在预备队里跟着比划。
1964年底学校搞“四清”,借口没有钱要辞退李秉慈老师。
同学们便对李老师说,老师要走了,但我们还不知道太极推手是怎么一回事,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李老师便利用临走前的一个星期介绍太极推手。
由于我有单推手的基础,对劲路的运行和变换多少有点体会,于是便利用这个星期的训练时间速成学会了简单的双推手和活步推手。
老师离开北大以后,我还居然成了队友们的“小老师”,不但指导太极拳队的同学练拳,而且还兼过学校病号保健班的简化太极拳课。
1964年底和1965年初,我还借助“校际学术交流”的名义,到清华大学武术队学过形意拳。
1965年我们北京的大学生都要下乡搞四清,1966和1967年文革运动更是席卷全国,人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给卷了进去,但我仍然经常到学校武术队经常活动的小树林里去练拳,跟我一起练的还有生物系的几个女同学和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几个男同学(其规模确实要比文革运动前小多了),并不见有什么人走来干预。
1968年初为躲避北大的校园武斗,我住到清华大学一个同乡的宿舍里,还跟一位浙江籍的老师学过太极棍。
同年底临离开北大前夕;经人民大学一个学生的推荐,更到北京中山公园向一个老拳师(当时没有询问姓名,据分析可能是杨禹廷)问过拳和推过手,体会太极功夫怎样可以达到的虚空粉碎和空灵神妙;与此同时还到北京紫竹院公园跟一些练大成拳的拳友交流过拳艺,吸取攻守进退、走位取势的武术意识。
这期间回广州休假时,也广泛到各个公园练拳人群中去观察“偷师”。
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广州中央公园教“无极桩”的蔡松芳老师;我在他那里借鉴了“气遍身躯”的“掤劲”。
就这样,我在文革初期的“大混乱”时期竟然可以到处去“偷拳”,从不同方面吸取可以为我所用的养料。
在我的经历中,文革期间无论在广州还是北京,尽管并没有什么公开的宣传发动,甚至也看不到什么“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一类说法,可公园里仍有不少人公开而且相当认真地在练拳。
这个时期我还几乎每年都回中山县沙溪公社龙瑞大队姑妈家探亲,在村子里经常跟自己的小学同学胡大白切磋交流拳艺(他所学的是南派“洪拳”),而且还教了刘保康、刘康元等几个同龄乡亲学简化太极拳,也始终未见有什么社会的干扰。
这跟当下虽然有着大量的公开宣传广告,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扶持基金,但事实上却没有多少人去认真练拳恰成对照。
1968年底大学毕业时离校时,曾经觉得个体性的拳打脚踢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决意要告别武术,于是把个人所有武术藏书全都送人。
毕业后到了湖南洞庭湖6939(后来又改组为0634)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机会练拳。
但多年的习惯无法一下子根绝,居然还利用为抬水泥管的同学当“扶手拐棍”而体会“听劲”和“跟劲”,研究不同力量的关系。
1970年再分配到了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休息时也喜欢私下里跟农民一起切磋各种动作的劲力方法和路线。
我让农民随意用拳打我,我并不还手,在练排打功的同时,看看到底怎样才能把这打来的力化去。
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北京武术队访问美国,全国各地体委开始集训武术骨干(广州也在这时成立了“工人武术队”和一大批“太极拳辅导站”,这时张煦阳的弟弟还介绍他的一个在辅导站练拳和教拳的同学萧琨来正式跟我学拳)武术活动于是逐步地又活跃了起来。
我所在的城步县也有几个中学毕业生被抽到地区体委学习武术,回来后便在一些公社里“依冬瓜画葫芦”地办了一些培训班。
我到清溪公社的武术班看了一下,乘机把我当年练的“第六路少林拳”拿出来跟他们交流,还给身边的几个知识青年公开教了点太极拳,我曾给这些县城知青展示太极桩功,被他们称之为“推不动的土机器”(其中跟我学得颇为像样的是时任县委书记边俊业的儿子边疆,当时未见上级对此有任何干预,但可惜边疆的这个学习后来却有点“浅尝辄止”)。
这时我的武术体验,已经开始扬弃招式动作,进入夺位取势、劲力发挥的阶段。
80年代初特别是在电影《少林寺》放映后的武术热中,我还利用探亲的机会应邀在湖南邵阳办过两期简化太极拳班,编有“七星关节操”一套配合太极桩功、步法,训练颇有名声,竟然折服了当地号称最能打的一批习武青年,由此武术名声大振。
1980年12月底我从湖南调回广州工作以后,又在拳友推动下依托广州市太极拳研究会(现已经升格为太极拳协会)研习太极功夫,并在辅导站指导过一些太极拳教练和爱好者的拳艺,还跟太虚拳、咏春拳和其它一些拳种的拳友相互交流过拳艺,比较过其不同技击特点,并得以跟若干外来的武林各派高手名家交流切磋。
1982—1985年间,借助广州太极拳研究会向顾留謦、杨振铎、马岳梁、吴英华、孙剑云、李天冀、陈小旺等多位前辈名家学练各式传统太极拳和太极枪,还特别关注有关推手技术,还跟这些名家高手推手摸过劲,同时还以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武术知识为海内外拳友提供理论和技术的咨询服务。
这个阶段我在技术上体会较深的要领主要有:
分出两点、明辨三节、脚踩涌泉、重心入地、松腰落胯、命门饱满、尾闾中正、开胯护裆、以意导气、以气运身。
1984年正式受命组建广州太极推手研究组,自任组长,参与组织广州市第一届太极推手表演赛(后来组建太极推手会,我则由于不善交往而在挂了一“顾问”的虚衔后,事实上则退出该会活动)。
1985年则到广州武术馆任兼职教练,正式面向社会公开招生教授太极推手。
在这不久后,甚至还被聘为广州精武体育会的太极拳总教练,后来又被推举为中国武术学会第二届委员,受聘为粤港多个武术团体的顾问等等,居然成了远近知名的武术拳师(在民间颇有名声,1989年拜访成都武术名人林墨根时,他居然在酒店摆了六席为我接风,四席为我饯行;当时路过重庆,当地武林前辈吕紫剑先生也托人传话希望跟我见面。
在官方层面则除多次获得全国性和号称世界的传统武术优秀论文奖外,2007年还获得广州武术协会五十周年武术成就奖),海内外均有不少爱好者前来咨询就教(据说,在美国居然还有人打着“阮纪正徒弟”的招牌开班教拳)。
虽然武术并不是我自己所学的专业;但后来我得以“专业归口”的机会,却神奇地来自这个跟自己大学哲学专业完全无关的武术。
1983年日本福岗太极拳代表团访问广州,由市太极拳研究会接待。
该会拥有一批所谓“国际金牌教练”,其录像带还占领了香港市场;但却是花拳绣腿完全没有功夫,害怕真的“以武会友”,于是便在市内征集“打手”。
基于我的武术名气,年轻时的拳友便把我推荐到该会,并受命牵头组建广州太极推手研究组,训练推手人才和参与组织市第一届太极推手表演赛;我的工作魄力不大而且办法也不多,但却相当的认真和执着,七拼八凑起来的工作居然还算可以交差。
接着组建广州市武术馆时,馆长李卓儒便指名要把我调入;但我的武术基本上可谓是自学出身、票友下海、业余练拳、杂学旁收,属于没有正式拜师不是门内嫡传、没有正规体育院校学历缺乏相关理论知识、没有任何比赛名次得不到社会正式承认的“三无人员”,由此不好评定职称。
我表示很愿意为该馆工作,但为自己前途考虑,关系和档案则要另找可以解决职称问题的单位挂靠。
李卓儒馆长解放前是中大地下党的,他的入党介绍人胡大钧恰好曾经在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所担任过领导,而且跟时任的院党组书记还是潮汕籍小同乡,于是便请胡大钧为我做疏通工作。
就这样我于1984年底在院党组否决后,竟然还可以“重新研究”被调入该院哲学所;并几乎同时成为市武术馆的兼职教练,打破原先门内个别秘传的惯例,开办广州历史上第一个面向社会公开传授太极推手的训练班,还长期免费为各种爱好者提供武术咨询,不久又成了广州精武体育会的太极拳总教练,在武术界开始混出一些小名气。
我效法孔夫子的有教无类,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由此从学的人员不但有社会青年、在校学生、下岗工人、退休人员、家庭妇女、少年儿童,而且还有领导干部、公安干警、私人老板、外国专家,甚至还有专业的武术教练。
1984年10月底,我正式调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对中国武术的思考重点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从“术科”转向“学科”。
在改革开放的总体背景下,我的研究思路主要沿“变革中的哲学文化思考”方向展开:
宏观是当前中国社会变革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微观则转向武术文化研究;我力图把武术作为一个“人体文化符号”,从中去挖掘其跟整个社会背景的对应关系,并以此破释什么是“中国人”。
在武术研究起步时,我的很多观点还是比较简单和朴实的。
其中术科观点,是认为武术之道在于练,其妙只在熟能生巧而已。
跟讲究一味求快那手上力量的西洋拳击不同,中国武术突出腰腿“下盘功夫”,提倡步法、身法协调的“功夫上身”和敌我双方关系的就势借力技术。
太极拳的虚灵神妙,是建立在整体性的松静沉稳基础上的。
其中学科观点,则开始以“人体文化符号”角度去探求太极拳跟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探究太极拳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发展可能性。
我觉得,武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是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妖魔化的;其基本性质和演变可能,应放在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当代社会前进要求上面,作为一种客观性的群众社会文化活动加以考察,而不应从官方意愿或个人想象的角度对其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
中国武术本是“综合实用技术”而不是单一的“体育竞技运动”,但这追求实用目的之途径,往往又是相当艺术化的;由此其推广应主要走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多元路子。
为了使自己的研究得以深入下去,我特地作了一些知识上和方法上的这样几个方面的准备:
(1)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系统思维。
作为一种应对冲突的肢体操作(狭义武术),武术本身是个极为庞大的复杂技术系统。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我就从拳友袁全那里听说清华大学有人组织起来搞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研究,也听说上海交通大学有人组织起来搞人体科学的研究。
对此我颇有兴趣,但限于深山苗寨的农村条件而难以接触。
80年代初我已经回到了广州,马上便以广东省建材技工学校教研室的名义向清华大学邮购了一批他们内部讨论的油印材料,由此如饥似渴地研读起来。
我这时还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广东省系统工程学会的组建,协助联系和参加接待美国系统哲学家拉兹络等活动,希望扩大视野和得到帮助。
后来随着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学术原著不断翻译出版,我又进一步关注和跟踪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论、突变论、混沌论与分形论等整个非线性复杂科学的历史进展,同时还把这些思路跟中国古代以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