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docx
《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docx(4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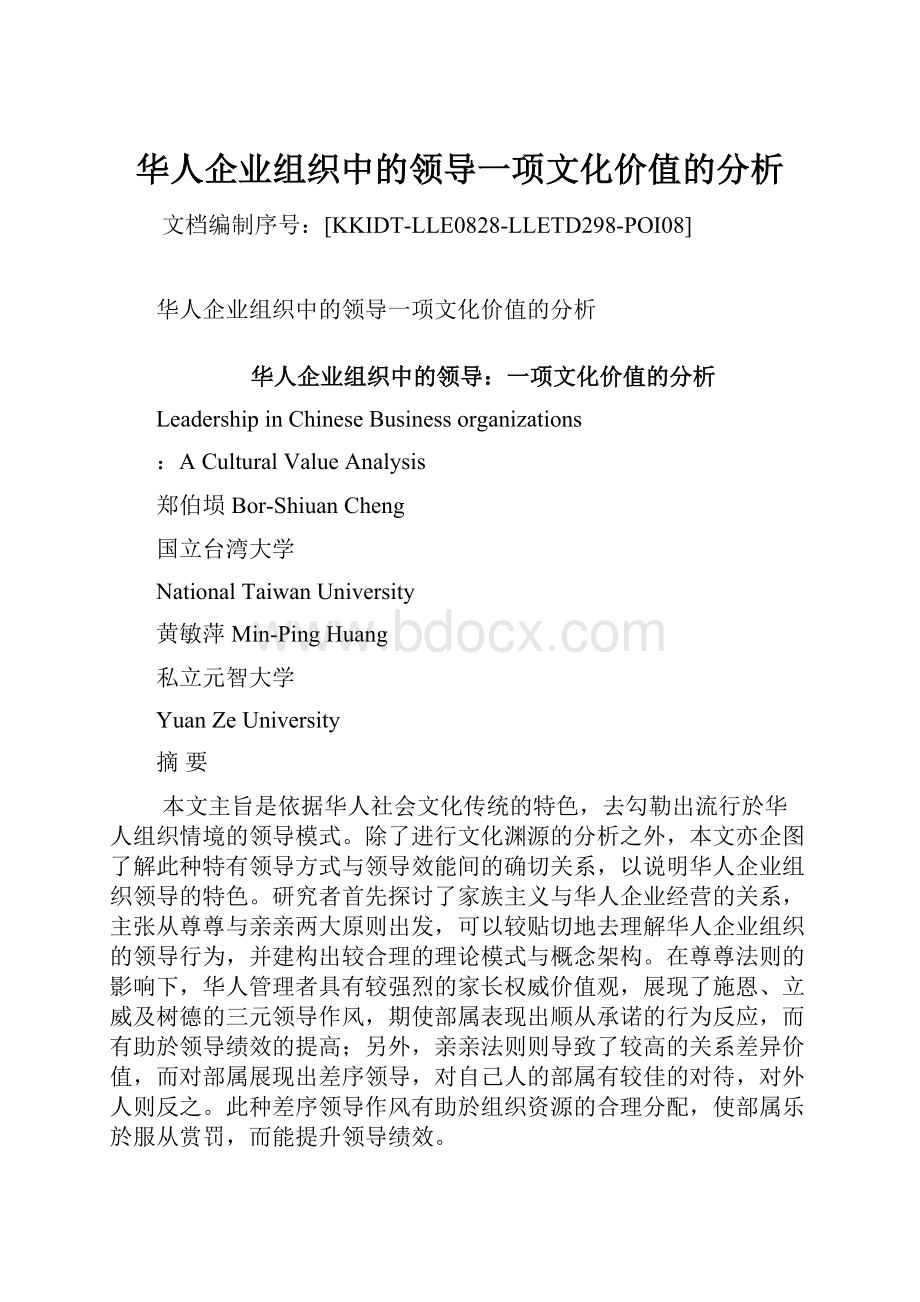
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
文档编制序号:
[KKIDT-LLE0828-LLETD298-POI08]
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
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
一项文化价值的分析
LeadershipinChineseBusinessorganizations
:
ACulturalValueAnalysis
郑伯埙Bor-ShiuanCheng
国立台湾大学
NationalTaiwanUniversity
黄敏萍Min-PingHuang
私立元智大学
YuanZeUniversity
摘要
本文主旨是依据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特色,去勾勒出流行於华人组织情境的领导模式。
除了进行文化渊源的分析之外,本文亦企图了解此种特有领导方式与领导效能间的确切关系,以说明华人企业组织领导的特色。
研究者首先探讨了家族主义与华人企业经营的关系,主张从尊尊与亲亲两大原则出发,可以较贴切地去理解华人企业组织的领导行为,并建构出较合理的理论模式与概念架构。
在尊尊法则的影响下,华人管理者具有较强烈的家长权威价值观,展现了施恩、立威及树德的三元领导作风,期使部属表现出顺从承诺的行为反应,而有助於领导绩效的提高;另外,亲亲法则则导致了较高的关系差异价值,而对部属展现出差序领导,对自己人的部属有较佳的对待,对外人则反之。
此种差序领导作风有助於组织资源的合理分配,使部属乐於服从赏罚,而能提升领导绩效。
依此理论架构,本文总结了过去对华人领导的研究结果,除了强调此种领导方式与西方迥然不同,是镶嵌在华人特有的文化价值基础上外,亦指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及其在管理实务上的涵意。
Abstract
BasingontheculturaltraditioninChinesecontext,thisstudytriestooutlinetheleadershipstyleprevalentinChineseorganizations.Afterexplor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familismandChinesemanagement,webelievetheconceptsofzun-zun(respecttotheelders)andqin-qin(closetotheclansmen)havesignificantinfluencesonChineseleadership.Underthepaternalisticanddifferentialleadership,anapplicationofzun-zunandqin-qin,employeesaresupposedtobehaveobedientlyandtheresourcesoforganizationscanbeallottedreasonably.Leaderslifttheeffectivenessasaresult.WeconcludeChineseleadershipisinlaidwiththespecificvaluesinChinesecontext,andthusistotallydifferentfromthewesternone.Finally,weidentifykeyresearchissuesforfuturestudiesandtheimplicationinmanagementpracticesinChineseorganizations.
前言
古今中外,领导现象都是一个令人重视的课题,理由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往往能够力挽狂澜,缔造丰功伟业,甚至改写人类的历史。
例如,由於政治领袖的领导,而建立了新个国家;由於企业家的努力,而有了跨国的公司;由於宗教领袖的诞生,而使群众的灵魂有了寄托之所。
凡此种种,均说明了领导现象的普遍性。
因此,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哲学家就常常对领导现象加以说明与诠释,试图揭开领导的神秘面纱。
甚至着名的君臣对话录、名人的演说也就成了许多人学习的对象,以便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
然而,由於领导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现象,要透过这种琐碎与片断的臆测来掌握领导的现实,实属不足。
因而,在二十世纪以後,终於有了科学性的领导研究与探讨。
从领导研究的历史轨迹来看,这种科学性的探讨,在1980年以前的西方,几乎都是采取准则式的研究途径(nomotheticapproach),坚持领导现象与领导内容应该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不太应该受到文化、地域、国家的影响,甚至宣称有全球化、普遍性的领导作风存在(House,Wright,andAditya,1997)。
然而,在1980年以後,许多研究者在透过理论整合的反省以及跨文化的研究之後,承认领导内涵颇受文化的影响。
他们强调:
虽然领导也许是全球共有的现象,但领导的内容却是镶嵌在文化之下的,随着文化的不同,领导的内涵与及其与效能的关系是有差异的(如Chemers,1993;Hofstede,1980)。
究竟领导是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规范抑是一种镶嵌在文化底下的特定表现目前学界对这种争论虽然未有一致的共识,但对实务工作者而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文化歧异(culturaldiversity)的管理却变得日益重要。
派驻海外的管理者是不能光靠一套由西方或母国发展出来的管理与领导规范,就可在异国发挥经营绩效;甚至母国的管理的良药,在异国具有负面作用。
对实务工作者而言,这种看法早就是一种常识(如Cox,1993)。
在学术研究上,虽然争论仍然存在,但有许多研究与个案已经证实了领导应该是镶嵌在文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如Hofstede,1980;HofstedeandBond,1988)。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Hofstede(1980)针对IBM全球四十几个国家的员工所进行的文化价值观研究。
他从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的规避、及男性化等四个层面,来剖析各国的文化价值,结果发现:
(1)接受研究的四十几个国家,在四个构面上,可以形成数个清晰可辨、迥然不同的文化群;
(2)相对於英美等西方国家,海外华人的国家或地区,如香港、新加坡、及台湾,在文化价值是十分相似、而群聚在一起的,但与西方国家则大异其趣。
其中,与领导行为具有密切关连的上下权力距离,华人社会与西方的差异颇大:
华人社会的权力距离较大,而西方较小。
Hofstede与Bond(1988)也因此质疑美式管理的文化普同性,认为领导放在不同的文化场域,能展现其原有效果的假定是不对的;「橘逾淮为枳」反而是合理的观察。
进一步来说,做为一种社会影响历程,领导也许是全球普同的现象,并不受国界或文化的阻隔。
然而,领导的内涵、领导作风、及实务作法却颇受文化的影响。
领导者选择何种领导作风,在大多数状况下,会反映其文化价值,而不见得完全是个人意志的决定;同时,究竟何种领导作风有效,也会受限於社会脉络的影响(FarhandCheng,1999)。
以华人社会而言,从现有的研究证据来看,西方,如英美诸国所强调的个人主义,以及上下之间的权力差距较小,彼此较为平等的倾向,是与华人社会所强调的集体主义与上下权力差距大十分不同的。
这种不同不唯在东亚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三小龙中发现,针对中国大陆的研究亦肯定了上述差异(如BirnbaumandWong,1985;Chong、CraginandScherling,1983;LaiandLam,1986)。
诚如许多研究者所言(如Hsu,1953),华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西方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因此西方所发展出来的领导模式,硬是套用在文化十分不同的华人社群中,就可能发生「削足适履」的情形,不但无法捕捉华人领导原有的风貌,甚至可能发生歪曲事实的情况(SmithandWang,1996)。
而且过分强调彼此间的相似性,就会忽略了华人社会更显着而重要的独特领导现象。
这种作法往往不能帮助研究者仔细而全面地去了解一个文化,从而找出,并发觉更贴切而完整的比较架构。
最近,已有一些研究者(如郑伯埙,1991;Redding,1990;Whitley,1992;Wong,1985)采用主位研究途径(emicapproach)的方式,来探讨华人企业组织的特性以及管理作风等诸般问题。
这些华人企业组织散布在台湾、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中,结果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即华人企业组织大多是由家族控制的,与家族主义具有密切的关系;华人企业的高阶领导拥有清晰、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展现出上尊下卑的家长式领导,一方面又具有偏私自己人的差序作风。
这种领导作风,在非家族企业的企业组织(例如,大陆与台湾的国营事业)与政府机构(例如,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中也十分常见(Pye,1981;Walder,1986)。
本文的目的,即承袭过去对华人企业组织领导的研究,检讨华人企业组织所处的环境脉络;家族主义与领导行为、领导效能间的关系,以对华人企业组织中的领导有较深入的了解。
华人企业组织的特徵
对台湾、香港、或东南亚诸国的许多华人支配的经济体系而言,都具有外销导向、企业规模偏小、企业由家族控制、以及工作外包的特色(如郑伯埙与林家五,1999;Levy,1988;Tam,1990)。
的确,由华人主导的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华人经济的主体。
以香港来说,在1980年,雇用人数在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占所有制造业的﹪,雇用了﹪的劳动力,产值则占﹪。
台湾何尝不然,在1998年,中小企业家数占%,雇用了%的劳动力,出口总值占%(中小企业白皮书,1998)。
虽然台湾有些企业组织的规模较大,但比起日本与韩国,仍然是小巫见大巫(HamiltonandKao,1990;Levy,1988);何况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大多是公营事业,目的是在提供中小企业外销所需的原、物料。
一般而言,这些企业多是由家族控制的,讲求的是创业家族主义(entrepreneurialfamilism),强调公司是家产的一部份(如Wong,1985)。
企业体通常由第一代企业家创办的,再把公司财产与权威传续给下一代,外人很少有染指的余地。
以台湾民营企业的主要经营阶层而言,具有亲戚关系者占了90﹪以上,而且董事长与总经理常具有父子关系的特徵(彭怀真,1989)。
虽然华人企业组织的规模偏小,但是其在外销市场的竞争力仍然很大,理由是华人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严密的网络关系。
透过人际与关系网络,华人企业组织能将制程的一部份外包,而且充分运用产能、资金、讯息等各项资源(郑伯埙,1995b;Greenhalgh,1988;Numazaki,1986;Tam,1990),来提高生产力。
底下将针对家族控制与组织网络两种重要特色做更进一步地说明。
家族控制。
华人的家族企业通常被视为是家产的一部份,而非一个独立的生财或生产单位(Wong,1988)。
这说明了在家族企业里面,重要的决策权与资源,所有权都掌握在家族手里,尤其是家族中的大家长。
因此,企业做为一种经济组织远不如家族组织重要。
这种现象可以从企业主持人通常由家族成员担任,产权、所有权、及经营权合一,专业经理人不负经营责任等看出来。
另外,在创办新事业体时,也由家族成员主导或寻找家族信任的伙伴来创立,而非授权给专业的外人来经营(Redding,1990;Wong,1988)。
正因为讲究家族的直接控制,华人家族企业不但规模有限,而且通常只专注在单项具体的经济活动上,专精的程度很高。
换句话说,如果从生产链来看,华人家族企业通常只负责一项生产制程,尤其是中间的制程,至於上游的原、物料供应与下游的外销或行销则由其他公司负责(Stites,1982)。
即使是高科技,如半导体产业,仍具有所谓的垂直整合分工(disintegration)的特色,许多公司只专精於产业链中的某一制程,而非上下通吃(吴思华与沈荣钦,1999)。
虽然台湾目前的一些电子公司,像宏碁(Acer)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品牌,而且展现部分的垂直整合特色,但毕竟是少数的例外。
同时,严格来说,这种垂直整合的概念也是以集团,分散为多家公司的作法来遂行,而非采单一公司的作法(Levy,1988)。
香港的情形也是大同小异,以纺织业而言,虽然也有不少企业主介入房地产的买卖,但其主要的经营重心与根基仍然独锺与专精於纺织。
在创办新事业方面,家族也具有最大的主导力量,通常采用机会式的多角化策略(opportunisticdiversificationstrategy),扩大经营层面(HamiltonandKao,1990)。
其作法通常是由家族成员主其事,或委托信得过的至亲好友或亲信,采用人脉关系,透过结盟的方式设立新的事业单位,发展为所谓的集团企业,涉入不同的产业领域(Hamiltonetal.,1990;Orruetal.,1988)。
虽然如此,集团企业在华人社会的主导力量还不是太大,根据Hamilton与Kao(1990)的分析,台湾96家最大的集团企业只雇用﹪的劳动力,而且多角化的程度也远不及日本的会社(Kaisha)及韩国的财霸(Chaebol)来得高。
由於家族对企业具有最大的控制力量,因此,其决策速度通常是很有效率、很快速的,而能符合弹性与即时反应的市场要求,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当环境改变时,华人家族企业通常能比竞争对手更快速地调降价格、消化库存、降低成本(HicksandRedding,1982),对所有资源做更有效的运用(Redding,1990),以快速攫取市场机会。
当然,这种快速转变的背後,与产业网络内各结点公司的紧密配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网络关系。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家族企业的规模偏小,专精於某一种特殊领域,应该是不容易存活的(Perrow,1992)。
然而,由於华人家族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互相依赖、互通有无的组织间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network),而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具有十分强大的竞争力。
更具体来说,每个公司都是网络中的一个结点,透过人情义务、人际连带、共同活动、及商业利益交织出紧密相依的复杂关系,而与其他许多公司互相连结。
在连结的背後,信任当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如郑伯埙等人,1997;郑伯埙与刘怡君,1995;Abegglen,1994;Wong,1988),并展现出消费者导向与外销导向的特色。
更准确地说,从消费者到生产者之间的路线已经细分化,由消费者→零售商→进口商→制造厂→外包厂→外包点→家庭加工间,必须以上游单位的需要为依归。
例如,零售商必要考虑消费者的需求,供应价廉物美的商品;进口商则需进口零售商所要求之规格、品质、式样、及价格的产品。
依照产销体系逐一下授的外包原则,最後产品的加工可能落入家庭工厂或家庭包工点手里。
家庭加工厂的利润虽然微薄,但因纯靠劳力获取加工报酬,而且做多少就赚多少,使得闲置的劳动力得以加入(郑伯埙,刘怡君,1995)。
另外,由於利润完全归诸个人,为了提高报酬,加工点的负责人就会想办法来提高工作效率与效能(如谢国雄,1992;夏林清、郑村棋,1990)。
一般而言,需要上生产线组合的成品会由规模较大的工厂负责;而半成品、零件加工则由家庭工厂或包工点负责;至於原、物料则由大型企业供应或直接进口。
这种细分为各式各样单位的产销组合,最适合多样、生命周期短、变化大、创新快速之商品的市场需求。
一但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下降,透过此一产销体系链锁,逐层加以吸收後,就可依照原来价格供应市场,以达到维持市场占有率的目标。
由於此种链锁十分有弹性,不但可以吸收管理成本,而且可以随时扩大或缩减产量,在客户要求的条件下达成工作目标。
另外,当产品生命周期短或创新产品上市时,又可做机动调整,随时上线因应。
因此,在组织设计上,这是一种备受推崇的网络型生产模式(Powell,1990)。
每个单位或企业体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或业务留在公司内,而将较不熟悉或不精通的业务,分散到外部去。
如此一来,各企业体不但可以简化其规模,节省人事费用,降低管理成本,而且可将省下之经费,再度投入主业中,增加自己的专业优势。
在面临改革需要时,也会因为组织小、周边协力厂商多的弹性优势,而能迅速因应环境变化,化解危机。
从本质上来看,网络关系无非是私人关系的放大(Deglopper,1978)。
人际关系、私人信誉、交货速度、及成本低下与是否获得外包订单有关,但并不必然建立长期的交换关系,除非彼此拥有十分良好、类似家人的情感关系(陈介玄,1995;郑伯埙,1996;郑伯埙与刘怡君,1995)。
换言之,华人企业是由家族拥有的,而外包点则是由外人构成的,因此,对外包点或合作厂商的承诺较为有限,而且较为短暂(Redding,1990)。
只要环境改变或条件改变,家族企业就会另外寻找夥伴,而展现出弹性与即时反应的特色。
这种特色很容易在港、台的成衣、电子、制鞋、塑胶制品、及高科技的半导体等外销产业中发现(吴思华与沈钦荣,1999;郑伯埙,1995b;Myers,1986;Tam,1990)。
港、台如此,东南亚的华人企业何尝不然,诚如Abegglen(1994)的观察,华侨企业的扩张,常是一种网络关系的复制。
透过网络,而能涉足各种不同的产业。
总之,从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华人企业组织的观察当中,可以明显看出华人企业组织的特色,包括规模偏小、结构简单、专精单一行业、由家族控制、透过组织间网络展现弹性与速度等。
其中,家族控制实为最根本的基础,此特色会透过家族主义,而表现在企业内部的管理与领导行为上面(周丁浦生,1995;Whitley,1992)。
最近几年来,虽然华人企业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不少家族企业虽然进一步蜕变成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而展现出专业管理的特色(许士军,1998)。
然而,其管理本质仍脱离不了具信任格局、群党主义(clientalism)的色彩(彭怀真,1989;Walder,1986;郑伯埙、黄国隆,2000)。
例如,以台湾高科技半导体的龙头之一,联华电子,是由四位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所的研究人员胝手胼足创业成功的,其经营方式具有十分浓厚的群党主义之夥伴关系的色彩(Cheng,TsaiandChou,1999)。
至於,中国大陆乡村企业的崛起,与群党主义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不管是信任格局、群党主义、或夥伴关系,对华人企业而言,都是源自於家族主义的进一步转化。
因此,虽然也许家族控制的成份降低了,但转化之家族主义的精神仍然存在。
家族主义与企业经营
既然家族主义或转化之家族主义是华人企业经营的重要准则之一,则家的概念自然会展现在华人企业组织的经营与管理上。
为什麽家的运作原则与华人的企业经营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基於两大理由:
第一、企业组织是家的放大:
从华人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企业组织是家的逐渐扩大,由家户、家族、雇用外人、建立制度、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一直演变到所有权、经营权、及执行权三权分立的较大型企业(黄光国,1984;郭建志,1999)。
在演变的历程中,虽然规模有变、制度有异、外人加入,家的运作原则在企业经营中,虽然有所修正,但却持续保留着,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郑伯埙,1995a)。
换言之,虽然企业逐渐发展、茁壮,但家族主义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却依然存在(郭建志,1999)。
第二、家是组织生活的起点:
家属於一种原级团体,团体生活时所发展出来的规范或型塑行为的法则,会迁移到其他团体或组织生活上。
因此,具有团体或组织特性的企业组织自不可免於其影响。
这种迁移作用,可称之为泛家族主义或拟似家族主义(杨国枢,1992)。
已有证据指出,当企业规模扩大、科层化程度提高、组织规章确立时,家族主义的直接作用可能降低,但泛家族主义的影响却仍然极大(陈千玉,1995)。
扼要而言,家族主义所强调的角色规范,含盖了两类重要的人际法则,一为尊尊原则,一为亲亲原则。
前者涉及的是尊卑,指的是根据双方地位的尊卑上下,尊其所当尊;後者涉及的是亲疏,指的是根据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亲其所当亲。
事实上,尊卑与亲疏的人际法则是人类社会关系很重要的基本形式(庄耀嘉,1996;Leary,1957),而华人社会则更彰显出尊尊与亲亲的重要特色。
尊尊原则。
想要了解家族主义与企业经营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传统中国家庭的本质,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Bellah,1970)。
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家庭是中国社会三千年来最主要的与基本的建制单位。
儒家的五伦当中(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有三伦是属於家庭中的关系(即父子、夫妇、及兄弟)。
在父权的传统下,父子轴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远超过夫妇轴等其他社会关系。
父亲的权威要远高於子女及其他的家庭成员,权力可说是绝对的。
瞿同祖(1961)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LawandsocietyintraditionalChina)一书中,就特别强调:
中国的家族是家父长制的,父祖是统治的首脑,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手中,家族中所有人口─包括他的妻妾、未婚的女儿、孙女、同居的旁系亲属、以及家族中的奴婢,都臣服在他的权力下,经济权(法律权、宗教权)也在他手里。
经济权的掌握对家长权的支持力量极为重大。
中国的家族是注重祖先崇拜的,家族的绵延,团结的伦理,都以祖先崇拜为中心。
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疑地,家长权因家族祭司(主祭人)的身份而更加神圣化,更加强大坚韧。
同时,也由於法律对其统治权的承认与支持,使他的权力更是不可摇撼。
(瞿同祖,1961;
表面看来,这种家父长权威颇类似古代地中海文化,诸如以色列、罗马、及希腊中的家长。
然而,就像Bellah(1970)所指出的,中国与古代地中海文明对父权的看法,仍有基本差异存在。
这种差异主要来自於家父长的权力来源不同,而非谁拥有家户治理权。
在西方,家父长的权力是来自神的赋予。
当家父长与神的关系慢慢地变为隐晦不明之後,家父长的权力就逐渐受到削弱。
尤其是在政府权力壮大之後,家父长对家户的权力必须形诸法典,纳入政府的法律系统当中。
一旦父权法典化了之後,统治者、菁英份子、及富豪的权力,就剥夺与限制了家父长的权限(Hamilton,1990)。
因此,父权制在西方是逐渐衰落的。
相反地,在中国并没有一位全真全能的上帝,赋予家父长权力的来源。
父权是来自於儒家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其本质是孝道,是指屈从父亲的旨意。
对儒家而言,在许多方面,家庭都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情境。
个人与上天的关系,是透过父母亲做为媒介的,每个人的神圣义务即是孝顺父母。
因此,孝顺不只是完人的美德、家庭团结和乐的基石,更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础。
在实际运作中,人子尽孝与孝道在生活中,都是强制性的义务,是传统社会中,支配原则的核心。
当然,传统中国社会重视孝道,有其生态与经济上的理由(杨国枢,1985)。
时至今日,孝道的内容与意涵可能有所转变,但孝道概念仍然受到相当的重视,也是华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行为准则与德行之一(叶光辉,杨国枢,1991)。
从孝道的主轴出发,Hamilton(1990)采社会比较的观点讨论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社会结构的不同。
他强调:
西方家父长制强调「个人」的最终优位;反之,中国的家父长制则强调「角色」的最终优位。
因此,这个不同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上的差异。
对於任何一个社会而言,这个差异隐含着两套不同的意义及建构社会秩序的方式。
西方是把人的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系统化,中国则把角色的意义系统化。
西方家父长制强调的是身份地位优於个人的权力,并给他命令权及一个可以正当行使命令权的领域(如:
家户)。
相对的,中国家父长制强调下属顺从的责任,赋予他们象徵着顺从的角色义务,并且依据一套角色关系(如:
父子、君臣、夫妇)限定其权力及服从关系。
西方以超验的神只赋予父权,而中国则待之以内在的正当性。
西方以「爱」规范家族成员相互关连的情感,中国规范情感乃在於「敬」。
Hamilton这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