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柏林《面皮》水墨画展研讨会文章.docx
《画家柏林《面皮》水墨画展研讨会文章.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画家柏林《面皮》水墨画展研讨会文章.docx(1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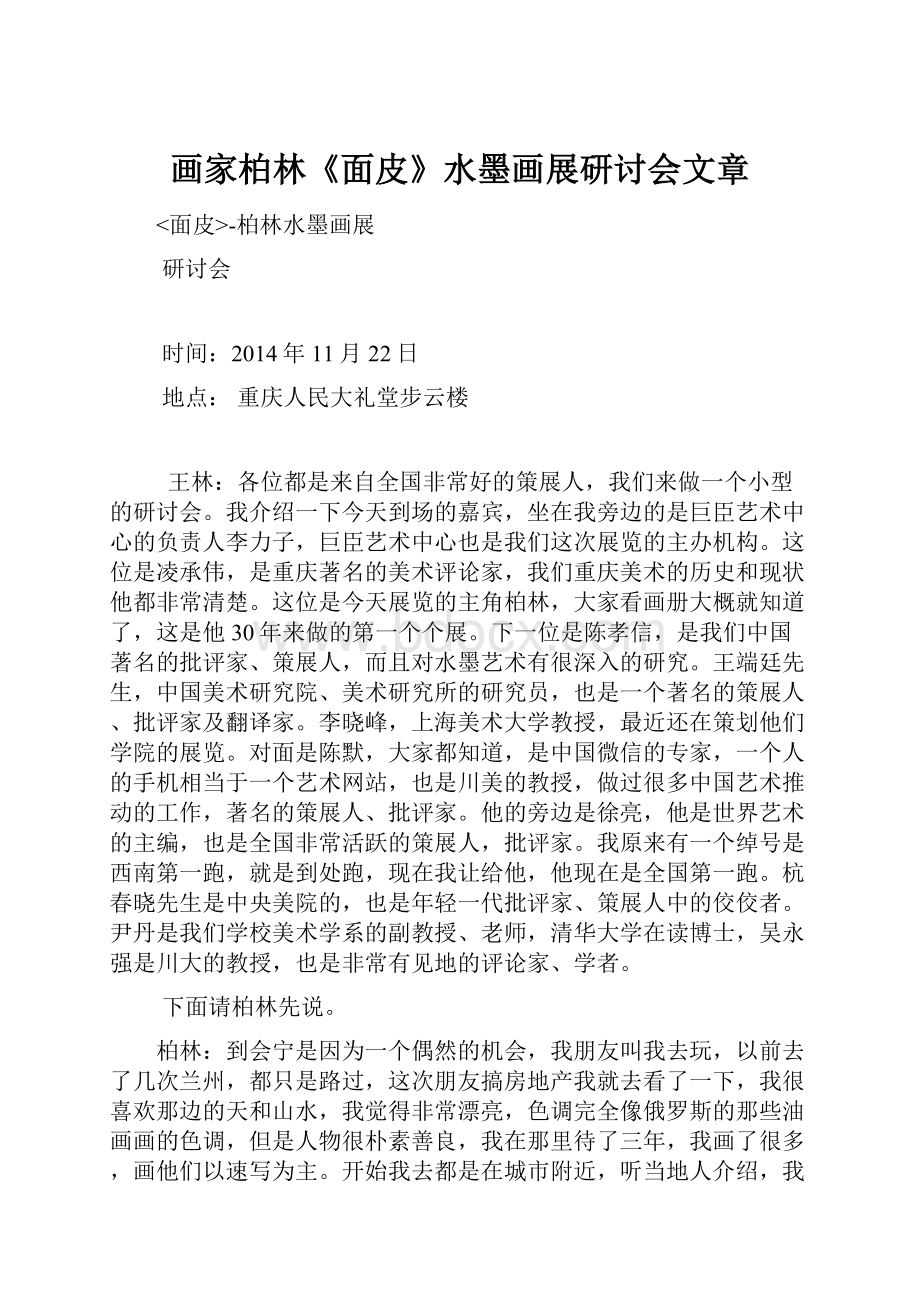
画家柏林《面皮》水墨画展研讨会文章
<面皮>-柏林水墨画展
研讨会
时间:
2014年11月22日
地点:
重庆人民大礼堂步云楼
王林:
各位都是来自全国非常好的策展人,我们来做一个小型的研讨会。
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巨臣艺术中心的负责人李力子,巨臣艺术中心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办机构。
这位是凌承伟,是重庆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我们重庆美术的历史和现状他都非常清楚。
这位是今天展览的主角柏林,大家看画册大概就知道了,这是他30年来做的第一个个展。
下一位是陈孝信,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批评家、策展人,而且对水墨艺术有很深入的研究。
王端廷先生,中国美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一个著名的策展人、批评家及翻译家。
李晓峰,上海美术大学教授,最近还在策划他们学院的展览。
对面是陈默,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微信的专家,一个人的手机相当于一个艺术网站,也是川美的教授,做过很多中国艺术推动的工作,著名的策展人、批评家。
他的旁边是徐亮,他是世界艺术的主编,也是全国非常活跃的策展人,批评家。
我原来有一个绰号是西南第一跑,就是到处跑,现在我让给他,他现在是全国第一跑。
杭春晓先生是中央美院的,也是年轻一代批评家、策展人中的佼佼者。
尹丹是我们学校美术学系的副教授、老师,清华大学在读博士,吴永强是川大的教授,也是非常有见地的评论家、学者。
下面请柏林先说。
柏林:
到会宁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朋友叫我去玩,以前去了几次兰州,都只是路过,这次朋友搞房地产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很喜欢那边的天和山水,我觉得非常漂亮,色调完全像俄罗斯的那些油画画的色调,但是人物很朴素善良,我在那里待了三年,我画了很多,画他们以速写为主。
开始我去都是在城市附近,听当地人介绍,我就去了这个地方,会宁县中川乡马沟村,住在一个老乡家里。
那里没有水,一年四季靠吃雪,每年下雪的时候,把雪水存放起来,他们修了一个窖池,水都变绿长毛了,但还在吃。
当地人用他们自己的一种茶叶,一小杯喝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喝水了。
我们去了以后,主要是洗脸和洗澡的问题不好解决,我刚去的时候住老乡家里,他们给我拿了一床被子,晚上把炕烧的非常烫,以前没有睡过炕。
炕的檐口有1尺5左右宽,中间烫的睡不下去我就睡在炕的边缘,但是又冷,翻过去又烫,一晚上都在反复。
这床被子大概十四五斤,非常重,平常城里盖的都是几斤重的。
而且被子上面有很大的味道,我看白色的布都变成了灰色的了,我说你换个新点的给我,他说这已经算是新的了,才盖了14年。
我就把它拿到沙土里面去,拿棍子打一下,就算洗了,洗澡、洗脸也是这样,到沙土里面弄一下,讲究一点的就是拿一个毛巾蘸一点点水。
我前后待了三年把他们文化也了解了一些。
两百年前,他们那儿是原始森林,全部是参天大树,到了70年代他们那儿有井水,到了90年代还有点水,到现在一点水都没有了,而且生存条件比较恼火,但是人很幸福愉快。
他们在一起,一见面都非常好,那个地方到镇上,坐2块钱的拖拉机就可以到,镇上到县上要坐8块钱的车,当地村里面的人很多人没有到过县城,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他们说去县城要十几块钱,而且去了以后还要吃饭,还不一定赶得回来,所以他们都不去。
那些老人都很辛苦,每天都在做事,特别是女人,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盐碱地,生小孩生不出女儿来,全部生的儿子。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我问他几个小孩,他说我不行只生了8个儿子,他们说那个地方没有人去过,连县里人都没有去过,他说我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外地人。
我很早就有一个想法,面皮怎么让大家记得住,我用腊猪脸来做后用油画画下来,但是画下来感觉很恐怖,因为没有美感。
做的过程中,我也想看它的变化,就是面皮腐化的过程。
我用了一些手法,我觉得水墨来表现最好,表现过程中我用了传统的原始符号。
这次面皮共画了一百多幅,李力子先生他在承办这个事情,策划就是王林先生在做,这一套的绘画过程基本就是这样的。
王林:
孝信先生可能算年龄最大的,您就先说吧。
陈孝信:
柏林先生是我的一个盲点,我以前从未接触过柏林先生,也未接触过他的艺术。
所以昨天到了以后,我就把他的画册认真翻看了一遍。
下面,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他的创作态度,体现了一种纯粹性。
他画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就是对这群人有感情,有想法,在内心里想把“他们”表达出来,充分地流露了一种真情实感。
由于主观上相当投入,所以,这批作品的主观性很强(我后面还要讲到)。
画法虽然是比较地具象、写实,出来的效果也比较真实,但主观性还是很强烈。
只有坚持用眼去观察,用感情去体会,用心去领悟,才能画得出这样的作品。
创作上的纯粹性的态度,是这一批作品成功的关键。
现在我们艺术圈变得很浮躁,人们的欲望很旺盛,所以,很难有人能以这种纯粹性的态度来对待艺术。
第二,这批“人物”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生气勃勃。
他虽然是学院毕业的,但是,这批作品却像是“原生态”的创作,而且有着很明显的纪实性特点,属于一种纪实性人物肖像。
尽管艺术家在创作它们的过程中,撇开了环境的因素,把重点聚焦在了五官上面,但是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习性、心性甚至他们的爱好都能从肖像当中体现出来。
所以这一批客观而真实的肖像,具有了人文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可以说是对会宁这个地方人文现状的一次当代意义上的“考古挖掘”,也可以说是献给会宁地区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第三,创作思路。
我仔细看了,因为他是学院毕业的,所以,在创作思路上,我的基本看法——它们是“新中国人物画”、“新写实人物画”、“新浙派人物画”的继承和发展。
这一类人物画,我们可以想到徐悲鸿、蒋兆和、方增先等等,实际上他也受了这些人的影响。
他目前所在的泸州就曾是蒋兆和的老家。
所以,在创作思路上有一个“双向性”的结合问题。
也就是说,他既是在用素描和写实的手法来进行造型,同时又掺进了传统的意笔手法。
每一张“面皮”的造型都很准确,几乎和人物原型一模一样。
如果没有结构素描基本功的话,这些“人物”画不出来。
人物很逼真,结构很准确。
这里又有两个重点:
首先是人的五官、脸部用传统山水和花鸟画的办法,先以淡墨边晕染,边铺开,显示出五官和脸部的结构,然后再用小写意和或大写意加以强化。
中、西并用,浓淡相间,这是双向的,也可以说是“左右开工”的创作思路。
再仔细看笔墨语言,我们又会发现,竟然是那么地单纯!
柏林的笔法、墨法,我个人认为是有板有眼,有章法,有节奏。
正是借助了这种水墨语言的有效性,才最终达到了人物性格刻划的深刻性。
如果说要有所不足的话,我提一点,因为同样是人物的肖像画,严培明在上海美术馆展出的人物肖像给我感觉很震撼,那种震撼的感觉和柏林先生的肖像画给我感觉是不同的。
他也是单纯人物肖像,但是给人以很整体的视觉力量感。
柏林先生的一百多件作品是故意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的。
但在实际上,每一个人物肖像表达的角度不同,视角不同,手法也不同,所以它们很难被“集合”到一起,从而产生出一种视觉上的力量。
柏林的作品,只能是一幅一幅地单独欣赏。
但在整体把握上,观念性比较弱。
这是柏林先生的这批“群像”比较吃亏的地方。
因为单个地去深入,一个一个地去把握,就没有办法把它们“并置”在一起,产生出一种整体上的视觉冲击力。
王林:
谢谢陈孝信先生,他说到最重要的几点,一个是从柏林的创作和构思,谈到了水墨人物画在笔墨上的变化和推进。
其实中国人物画,水墨的人物画,大致有两种,一是勾线的造型,用线把人基本造型勾出来,然后加以适当的匀染。
二是大写意。
刚才陈孝信谈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柏林的画,结构和笔墨都是一笔成型,这样的结合是有难度的。
水墨,一笔上去它要浸润,浸润的边界要和结构保持一致性,取决于你对宣纸、墨质、水份、笔力的把控,宣纸的润燥程度不一样,浸润的程度都会不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其实柏林画这个画,他受制于一个对美的把握。
其实艺术有很多地方是突破美的,是超越了美的。
可能表达不局限在美的范筹,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很赞成陈孝信说的这一点。
因为一个展览,做了以后画了一个圈,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已经跳出了创作者的角度,重新看待一批作品的时候,我想今天大家的讨论,对以后创作的点非常有启发意义,所以大家可以非常坦率的谈论。
下面请凌承伟谈一谈。
凌承伟:
看这个画展非常感动。
在时下艺术圈内华美、光鲜盛行的时候,柏林的展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难能可贵的体验。
我多年做美术史研究,尤其关注重庆本土美术和美术家。
今天能够认识你,非常高兴。
我刚才听你的讲话,几乎没有谈艺术,没有谈你是怎么画这些画的,而是谈你去的那个地方和那里的人,以及你对那个地方的认识和感受。
甘肃白银会宁,我特别留意你说那里的人非常快乐、幸福,然而他们却是非常非常的贫穷。
那里的人不愿意进城,不是不愿意去而是他们没有钱。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得非常自在,惬意。
这让我想到很多,我想,这正是我们画家、艺术家需要思考的。
今天上午我在展览上看您的画的时候,我就在揣摩您的作画时的心绪。
你创造了如此鲜活、感人的一群人物画像。
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但是不多。
人像中有神情木讷的、活跃的、专注的、漫不经心的,等等。
也有时髦的,一个青年带个墨镜,一笔浓墨画出的头发搭在前额,印象很深。
然而“面皮”整个展览更多传递出的是一种苍凉、洪荒的气息。
您在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一呆就是三年,执着地认识人的本质,寻找人类生活的意义。
你画了那么多当地人,使我猛然想起了梵高,你刚才说会宁的土是黄的,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我想起了梵高向往的法国南部小镇阿尔,他在那里画了一大批充满阳光的作品。
我不知道这种比喻是不是恰当,但是我却是产生了这种联想。
另外,我发现您的展览有几个独特之处:
第一,全是水墨画,一点色彩都没有,很单纯;第二,都是人物面部特写,所以称之为“面皮”,你想从中发现或寻找什么;第三,画的是一个地方的人,西北某个地方的,而不是四川的。
这样一个从形像、画法到取材都非常独特的展览显得非常真实,非常有特点,感觉非常好。
据策展人讲,这是你从事绘画30年以来办的第一次展览。
这实际上标明了你的艺术态度,一种远离世俗、利欲的人生态度。
这对当下艺术圈中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的现象,是一次提醒和昭示。
你执着艺术多年,在丰厚的积淀和深沉的认知之下,寻找人生最真实、最本能的东西。
这是让我很受触动的地方。
艺术的心态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现在的一些艺术家,今天画这个,明天画那个,总在想不断的创新。
说实在话,我不太愿意用“创新”这个的词语。
因为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旧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不好的。
我比较喜欢用“发展”的说法。
柏林在四川美院受过很严格的基础训练,笔墨上是没有问题的,你把传统笔墨用于对现在生活的发现和表现,真实的发现,真诚的表现。
让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真实的人。
人物塑造的成功不仅是造型上,而且在精神层面。
无论是俏皮的、忠厚的、幽默的、狡黠的、木讷的老人面像,或是眉宇间透发着些许时尚气息的青年、姑娘神态,我们看到是一个真实的、可信的、没有矫饰的、让人感到亲近的世界。
另外,从重庆美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无论是版画、雕塑、油画领域,我以为重庆的画家似乎有这样的一种共性,那就是比较执着、专注、认真,有秉性。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无论是人或是事,不胜枚举。
如果说这也是重庆美术的一种传统,我认为柏林和他的作品体现了这种传统。
重庆地处内地,比较闭塞,不像沿海城市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很多,这促使我们的艺术家立足脚下的这方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和发生的事来进行创作。
另外,如果要提一些建议的话,你现在的这些画都是头像,有些还是面部的局部,略显单调了一点。
我想能不能稍微视域再扩大一点,从肖像的角度来表现人物。
肖像不仅仅是头像,无论从技术或艺术上来说这对你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次展览受“面皮”命题的界定,仅有人物的面部是可以的。
我们看人总是先看脸,看脸首先是看眼睛,这是我们的视觉习惯,也是这次展览着眼之处。
我在想如果人物表现从肖像的角度,可能表现的内容会更丰富一些,更能有特点的表现一个地方、一群人,无论是从精神、内涵到外在、形态。
王端廷:
在我国大致可分为三类人,城市人、农民和农民工。
在当代艺术里面对城市人和农民工画的多,这些年画真正地道农民还是少。
所以,柏林的这一批作品从题材上看是很特殊的。
他画的大部分是老人,年轻人也有,但是很少,这些老人的脸上都有岁月的痕迹,这样的面孔是非常生动的,非常有内涵的。
看得出来,柏林的这个系列,一百多幅作品,超越了城市艺术家到乡村采风的那样一种层面,他真正的走到了这些人的生活甚至这些人的内心。
跟他对话的这些人,都是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呈现出了他们非常本真的面貌和表情。
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平常人要想很放松,要想没有戒备是很难的。
你只有完全取得人家的信任,或者你也完全接受他们,只有在双方彼此接受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这样的一种状态。
柏林的绘画都有照片作范本,而且都是特写的镜头,这种镜头其实带有一种逼迫性,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一种考验。
如果有一些陌生人来照相,我们的心里是会紧张的,超过三秒脸部肌肉就会紧张。
所以,首先我觉得他跟他们是完全没有距离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的这些肖像没有丑化,也没有美化。
我们当代艺术丑化的现象是比较显著的,而主流就是美化,所以这是一种中间状态。
他追求的是人物真正的本真状态,这在中国艺术中是非常稀缺的。
中国人是害怕真实,恐惧真实,拒绝真实。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这样一种人物画是非常可贵的。
而且,他并不是现场写生的,没有写生的那种草率。
王林:
对,他有基础。
王端廷:
从创作手法来说,柏林这批作品有素描的影子,但是结合了水墨的语言,还有一种摄影的结构。
所以我觉得他的绘画是素描、水墨和摄影的结合。
他的创作手法感觉上是以水墨为主,在人的面部上勾线比较少,几乎可以说是“没骨晕染法”,就是通过水墨的晕染就把一个肖像的结构、块面、体积和量感都呈现出来了。
能够用水墨获得素描和油画那种效果,这种创作方法我看的不太多。
我觉得这样一种独特的创作手法,还是具有个性和新颖性的。
传统中国画家画人像是要画完整的,柏林画的这些头像,额头上面都剪掉了,耳朵也没有了,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图像视觉现象,摄影和电视都是这样的。
体现人像特征最重要的部分是眼睛、鼻子和嘴,所以现代摄影、影视和绘画在表现人像时也只突出呈现这些部分,而将其他部分省略了。
柏林的这批水墨肖像也是这种现代图像和视觉经验的反映。
柏林的绘画跟其他当代画家的比较,也许在艺术语言上不是特别当代,我倒是觉得,他这样一种考察生活,或者说考察人生的态度,恰恰是有独特性和当代性的。
他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是技法和手段层面,更重要的是对待农民的立场和态度。
我觉得当代艺术贵在独特,也就是你不要追求潮流,不要跟别人一样。
王林:
我看到柏林绘画的时候,第一个反映,我觉得这是需要胆量的,因为写实的画在我们这被赋于了太多的历史形态,第二个反映是乡土绘画的传统,我们的乡土绘画经常停留于人文关怀,这种关怀是居高临下的。
柏林作品恰恰没有这个因素,他和村民是平等的。
从外人来看,这些人简直就是在受苦受难,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并不这么样想。
底层人群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生存价值,不是艺术家可以去定义和指点的。
其生存价值的真实性,恰恰是艺术最应该追求的。
对他们好坏优劣,艺术无法去做评价。
在所谓真善美之中,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更多的去追求真的东西,因为不管是政府功利、国家功利,还是江湖功利、个人功利,都在掩饰和忽略真实性的价值。
柏林的作品有一种还原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画家放弃过度的主观情绪,不让自己的情绪性去影响底层人群本身的呈现。
这种主动退出是对真实的尊重,是对真实性艺术价值的尊重。
陈孝信:
我不同意王端廷的一句话,把柏林先生的肖像讲成具有当代性,我认为柏林先生的人物肖像,具有早期现代主义的特征,如果要比的话,就类似于梵高这一类的创作,就是早期现代主义的特征,不具有当代性。
第二点,面部淡墨的应用,既单纯又丰富。
李晓峰:
我补充,我觉得既不要是否当代,也不要是否不当代,这毫无意义,因为他是一个个案,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这个特殊,我们先不要急于把他往当代、现代去定义。
第二,肖像的概念,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前几天在上海参加了一个狗肖像展览,那个研讨会其实也谈论了关于肖像的问题。
今天我们通俗的讲众生相,但是众生相如何去看待,聚焦在哪个点上。
过去是领袖像后来是英雄,后来是名人肖像,再后来我们所关注的聚焦的是明星像。
在这样一种肖像聚焦的牵引和变化中,其实背后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和评估。
我们研讨也是为了解读,为什么柏林先生会关注这样一个群体的形象,对于他本人来说,他本身是科班出生,本身与西北没有太大关系,他的经历也许是天意召唤他到会宁那个地方,我今天还说,现代的艺术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吃得起这份苦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肯定是有一个东西在召唤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百件肖像。
我今天问了一个同事,就说是不是只画这样跟我们尺度几乎是等大的的肖像,这个等大的肖像,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呢,我听说他也有大的,只是这一次展览选择了等大的。
说明他很明确,所以这一次展览非常成功。
这些肖像的等大性和选材的具体性,意味着什么呢,我同意陈老师提到的纪实性,他有一个高度纪实。
你在纪实中解读出什么东西呢,被我们忽略的,但是仍然有巨大感人价值的人文精神。
具体来说,这种人文精神是什么呢,不是美化也不是丑化,是非常朴实的方式。
陈孝信:
还原。
李晓峰:
就是非常素朴的,没有一个是动了手脚的,是天然的,而城市人的脸,很难说有一个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我不定义你的作品是否当代性,也许闯入了当代的情境,这个时候,这些脸显然是发生作用的,这些作品是朴实、真实、平和。
不是那种过度去诠释这些人,是非常平和的去描述,这个是很明确的。
你自己也讲到,你是最终选择了中国画的方法,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些脸,或者你想呈现的面孔,用中国画好象是最贴切的。
这种贴切给我的感觉,是可控性和不可控性的一个结合,你在这时候呈现的这些点,是否也给了我们一种暗示,就是它是一种天然,是天的规律和个体人的命运的结合。
这是原生态的、自然的生命状态是一种契合,所以我觉得你所表达的脸不只是纯然的写实或者复制,其实是刻意的要表达一个艺术家所能够呈现的一种生存观、生命观或者叫自然观。
你为我们今天的人文精神,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不应该遗忘的一个侧面。
在今天,它是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来呈现的。
王林:
刚才谈到一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比较一下,它可能是一种描述性,描述性往往带着画家主观的情绪化的东西,我觉得大家谈到的这几个想法,其实柏林的作品,也有一种还原的性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成份是,放弃了画家这种过度的主观的情绪性,不要让过度的情绪性去影响底层的人群本身的呈现,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陈默:
刚才前面几位老师说得比较全面,几乎将我想说的都涵盖了。
当然,我们会有不同的看问题的侧重点,在这里谈几点看法。
柏林从美院毕业三十年,埋头积累三十年,三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的艺术功底和人生经历窖藏,集中释放到这个展览上,令人刮目相看。
从作品中可以看到,学院扎实的训练功底是非常需要的。
好的想法、好的动机、好的情感、好的表达,缺一不可。
现实中不少艺术家有这种毛病,眼低手低,加上心境紊乱,精神颓废,怎么走得出来?
虽然人们常说学院培养不出艺术家,但是好的艺术家却大部分有学院学习的经历,他们有着优质天赋,毕业后经过个人修炼沉淀和积累,坚持以恒,储备了足够力量,往往能走得很远。
我注意到本次展览的前言和艺术家介绍,柏林先生向外界透露,这是他毕业30年来第一个个展,这让我很意外。
因为在现实中,艺术院校毕业后能坚持画画的,三十年不做展览有些天方夜谭。
另外,他的简历简单至及,只有寥寥几字,十分罕见。
按一般规律,他30年的积累,简历应该有好几大篇了。
由此可见,这个艺术家的个案不一般,甚至很极端。
可以设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陈孝信:
他看不起那些拉扬篇的简历。
陈默:
看得起看不起,各有各的立场、方式、活法,而柏林选择了应该是一种最别扭、最不舒服的立场和活法——对他而言,可能也是最舒服最有价值的选择。
另外,他似乎没有征兆地到了会宁,那里是革命圣地,当年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地方,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当然,如果没有那次会师,红军将可能继续被围剿,历史也会改写。
大家敬仰的革命圣地,却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可能比另一个革命圣地延安还要落后几十年。
延安离北京比较近,关注点高,国家以及一些企业不断投资建设,面貌改观不少。
但是看看会宁,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几乎被世人遗忘。
说到柏林比较选择的极端生活方式,在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简陋的村庄,常年不洗脸不洗澡,盖着几十年不拆洗的被子,每天是土豆和一杯苦茶。
他说喝了苦茶,一天口味就没了。
我们知道,甘肃有个“三西”,严重缺水无法种粮,是国家确定的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上世纪90年代政府把这里的人迁移往河西走廊,而会宁的情况可能比之更差。
作为革命圣地,今天情况如此糟糕,情何以堪?
一个极端的艺术个案,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极端的环境、极端的选择、极端的隐忍,各种极端的“融合”,逼着人们要极端地关注。
再一个是关于他的艺术表达。
刚才陈孝信、王端廷老师争议他是现代性还是当代性,没有定论。
我比较同意李晓峰的说法,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扯得有点远了。
今天在针对柏林个案的时候,“主义”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呈现的面貌,形式、技法、语言、结构适不适宜他。
技法到什么程度为佳呢?
对他而言够用就好,顺手就好。
顺手的人用铅笔也能画好画,不顺手的人,给他再高级的工具也不行。
另外关于柏林所使用的技术手法,让我想起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刘秉江和新疆画院的龚建新,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用过没骨写意手法画肖像,后来已不大常见。
这种作品方式可能与我们今天的艺术市场、艺术现实不相符合,或者说是落伍了。
今天早饭时,我们开杭春晓的玩笑,他孪生兄弟的绘画作品一幅若干万,画一天的收入可能比春晓忙活一年的收入还高。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柏林先生选择了艰难苦涩的方式,不能不令人刮目先看。
研究艺术个案,重要的是关注最后呈现,呈现出什么样的作品面貌。
就这个展览而言,我认为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没法复制的奇异个案,他的精神境界、艺术表达、生活经历等等,都是值得艺术界关注的。
面对一个积累了30年的唯一个展,为这位可敬的艺术家开这个也是唯一的学术研讨会,意义不一般,着实令人感动,必须给他点赞!
徐亮:
各位好,各位其实都是资深的评论家,我本人是媒体人十多年,走的多,看的多,跑的多,想法也多。
刚才各位都说了很多,我就从我本人和媒体的角度,谈谈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第一,从柏林看当代艺术的底片。
其实柏林先生的艺术重要,但他对生活的态度更重要。
他本人完全可以像他的其他同学一样,滋润一点,市场一点,吃的好一点过的好一点,但他没有,他30多年来一直像苦行僧一样生活在农村,像古代的文人雅士一样吟诗作画,在都市化、现代化强烈飞速发展的当下生活语境下坚守文人的操守,回归人的本性生活和艺术的状态。
这一点是让我本人非常钦佩也向往的状态。
我们目下的中国画创作的队伍中基本都是在都市生活,享受着西方化、都市化的现代生活,而在许多的画面里表现出来的确实古代的生活,其实那都是古人的生活和状态,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境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我们社会上的大批画家画一些无聊的古代山水。
而柏林的生活和创作状态和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例。
他的艺术底片是真实的透明的。
其片基是坚实的文化理想和人文情节。
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就是需要这样真实,而不是虚伪。
造假的“伪文人”。
其实对艺术来说生活态度是非常重要,这是我非常钦佩柏林的地方。
第二,从柏林的艺术看艺术的地域性表征,现在我们总在说当代艺术,这个派那个派的,分门归类,这个代那个代。
在我以为艺术其实能真正的反应社会最真实的生活和态度是最重要的。
我前一段在重庆做了一个联展,两个人作品各异,一个是传统的,一个是古典抽象的东西,各有特色,如果非要用当代艺术的概念来套用归类我以为他们就是峨眉派的。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