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生火》杰克伦敦之欧阳总创编.docx
《译文《生火》杰克伦敦之欧阳总创编.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译文《生火》杰克伦敦之欧阳总创编.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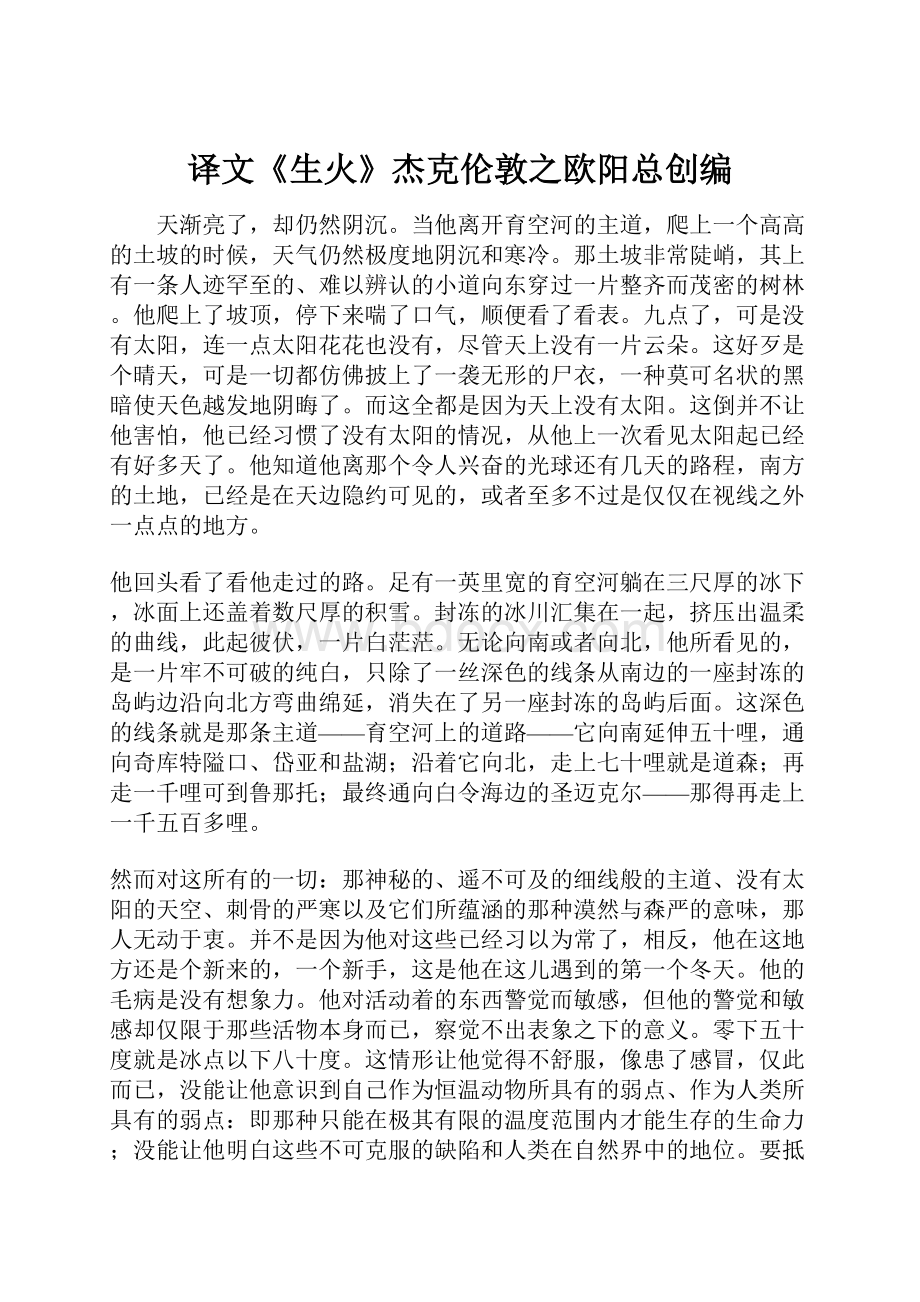
译文《生火》杰克伦敦之欧阳总创编
天渐亮了,却仍然阴沉。
当他离开育空河的主道,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的时候,天气仍然极度地阴沉和寒冷。
那土坡非常陡峭,其上有一条人迹罕至的、难以辨认的小道向东穿过一片整齐而茂密的树林。
他爬上了坡顶,停下来喘了口气,顺便看了看表。
九点了,可是没有太阳,连一点太阳花花也没有,尽管天上没有一片云朵。
这好歹是个晴天,可是一切都仿佛披上了一袭无形的尸衣,一种莫可名状的黑暗使天色越发地阴晦了。
而这全都是因为天上没有太阳。
这倒并不让他害怕,他已经习惯了没有太阳的情况,从他上一次看见太阳起已经有好多天了。
他知道他离那个令人兴奋的光球还有几天的路程,南方的土地,已经是在天边隐约可见的,或者至多不过是仅仅在视线之外一点点的地方。
他回头看了看他走过的路。
足有一英里宽的育空河躺在三尺厚的冰下,冰面上还盖着数尺厚的积雪。
封冻的冰川汇集在一起,挤压出温柔的曲线,此起彼伏,一片白茫茫。
无论向南或者向北,他所看见的,是一片牢不可破的纯白,只除了一丝深色的线条从南边的一座封冻的岛屿边沿向北方弯曲绵延,消失在了另一座封冻的岛屿后面。
这深色的线条就是那条主道——育空河上的道路——它向南延伸五十哩,通向奇库特隘口、岱亚和盐湖;沿着它向北,走上七十哩就是道森;再走一千哩可到鲁那托;最终通向白令海边的圣迈克尔——那得再走上一千五百多哩。
然而对这所有的一切:
那神秘的、遥不可及的细线般的主道、没有太阳的天空、刺骨的严寒以及它们所蕴涵的那种漠然与森严的意味,那人无动于衷。
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相反,他在这地方还是个新来的,一个新手,这是他在这儿遇到的第一个冬天。
他的毛病是没有想象力。
他对活动着的东西警觉而敏感,但他的警觉和敏感却仅限于那些活物本身而已,察觉不出表象之下的意义。
零下五十度就是冰点以下八十度。
这情形让他觉得不舒服,像患了感冒,仅此而已,没能让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恒温动物所具有的弱点、作为人类所具有的弱点:
即那种只能在极其有限的温度范围内才能生存的生命力;没能让他明白这些不可克服的缺陷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要抵御持续的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和针扎般的霜冻必须有手套、耳套、温暖的鹿皮靴和厚厚的长袜。
零下五十度对他来说就是零下五十度,至于其它还意味着什么则根本没有进过他的大脑。
他继续前进,随意朝地上吐了口痰,但一种尖利、响亮的爆裂声惊动了他。
他又吐了一口,他发现痰还没有落到雪地上,还在半空中就爆开了。
他知道零下五十度的气温能使口痰立即冻结,着地即碎,但这痰还没有着地就碎开了。
毫无疑问,气温已经低于零下五十度,但低了多少他不知道。
不过气温不是问题。
为了那一种古老的需求,他一心想去到哈德逊湾分岔口的左岸人们聚集的地方。
当他兜了个圈子去看能不能将木料从溪流里运出育空河中的小岛时,那些人越过了以印地安人湾为准的分界线。
六点种,也就是天黑下来以后不久,他应该在帐篷里了,真的,那些人全在那儿,会升好一大堆火,准备好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
他把手伸进大衣里面的一个鼓鼓的包裹中,那是他的午饭。
那包裹在他的衬衣里面,用围巾包好紧贴着他的皮肤,这是防止那些饼干冻结的唯一办法。
他想到这些饼干、这些一层层包起来肥满的腌肉、这些腌肉的裂纹和里面滋润的油脂,惬意地笑了。
他投身钻入那片整齐的丛林。
道路难以分辨。
雪橇经过后的雪地已凹下去有一英尺深。
他为自己没有雪橇而庆幸——这样可以轻装前进。
事实上,除了那顿包在围巾里的午餐以外,他什么都没带。
他还是多少对这寒冷觉得有些奇怪。
他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擦了擦麻木的鼻子和脸:
的确是冷啊,他觉得。
他一脸大胡子,但这一脸的毛没法保护他高耸的颧骨和那只挑衅一般地伸进寒风的鼻子。
有一条狗小跑着紧跟着他。
那是一条很大的野狗,一条真正的狼狗。
那狗一身灰毛,无论外形或脾气都与它的野狼兄弟没有两样。
极度的严寒也将那野兽弄得极度虚弱。
它知道自己没时间闲逛,它的本能给了它一条比任何人类的约束都远为真切的教导。
事实上,气温并不是只比零下五十度低一点,而是比零下六十度、零下七十度还要低,低到了零下七十五度。
零上三十二度就是冰点,也就是说天气冷到了冰点以下一百零七度。
狗不懂什么是温度,可能也不像人类那样脑子里有着对严寒的环境的清楚的意识,但野兽有的是它的直觉。
这种直觉焕发出一种模糊的威胁,控制了它并迫使它一路上鬼鬼祟祟地跟在那人后面;让它盼着那人钻进一个帐篷或者找到一个容身之所然后升起一堆火,而且让它对那人的每一个意料之外的行动感到纳闷。
那狗已认识了火,它想要一堆火,要不就只好在雪地上刨个洞然后蜷在里面好保持暖和。
它呼出的湿气已在它的毛皮上结了一层霜,特别是它的下颚、鼻子和眼皮,已经被水晶般的冰粒变成了白色。
那人的红胡子也同样冻上了,而且冻得更牢固。
他不断呼出的温暖而潮湿的空气已慢慢冻结、积聚成了冰块。
他正嚼着烟草,脸上的冰块把他的嘴唇都冻结了,以至于他吐掉汁水的时候没法把下巴弄干净。
最后,弄得他胡子上冻结的水晶和琥珀般的硬块越积越多,越来越长。
如果他跌倒的话,那东西就会像玻璃一样碎成片片。
不过他对这个附在他身上的东西并不在意。
这是每一个在那个地方嚼烟的家伙都躲不过的惩罚,他早在前两次寒潮袭击时便已经领教过了。
从一个叫“六十哩”的地方的公用温度计上他读到了一次是零下五十度,另一次是零下五十五度。
但那两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冷,这一点他知道。
他在那片广阔的林地中前进了几哩,穿过了一片平坦的黑土地,然后下到一条已经封冻的河床上。
这儿就是哈德逊湾,他知道他离那河流的分岔口还有十哩。
他看了看表,现在十点。
一小时走了四哩,他算了算,自己在十二点半应该可以赶到那岔口。
他打算在那儿吃午饭算是庆祝这一成绩。
在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冻结的河床上时,那狗也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尾巴跟着他下到了河床上。
这条老路上的辙印仍然清晰可辨,尽管已经有十英寸厚的积雪盖在了最后一对雪橇的压痕上。
这寂静的河床已有一个月没人经过了。
他坚定不移地继续走着,什么也不多想。
除了该在岔口边吃午饭和晚上六点钟钻进帐篷和同伴们在一起以外,他也的确没什么可多想的。
旁边也没有人可以说话,就算是有,他嘴上的冰甲也让他没法开口。
所以他只好一个劲儿地继续嚼他的烟草和继续加长他的琥珀胡子。
有一段时间他总觉得冷,从来没有这么冷过。
他一边走着,一边不停地用手套擦着颧骨和鼻子,不自觉地双手交替地擦着。
但尽管他擦个不停,他的脸颊还是很快就麻木了,然后鼻尖也立即失去了感觉。
他知道他的脸冻僵了,他明白。
他责怪自己没想到在寒冷来临的时候应该有一条鼻带。
这种带子可以横着把脸裹起来,这样就能保护好鼻子和脸。
不过这也没关系。
冻僵了是怎么回事情呢?
一点儿疼痛,仅此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虽然他的脑袋里一片空白,但他仍然十分清醒。
他注意到了这条河的变化,那些弯道、拐角,以及那些灌木丛的变化,他专注于自己的每一个下脚处。
有时,遇到一个凹处,他会突然跳开,像一匹受惊的马。
然后绕过他刚才走过的地方,沿着河道回走一段。
他知道这条河已经冻得透了底了——在这极地的寒冬里,河里是绝不会还有活水的——他也知道会有从山里冒出来的泉水在封冻的冰河和其上的积雪之间流着。
他知道就是最冷的寒潮也冻结不了这些泉水,他同样也明白这些水所包含的危险。
这些水就是陷阱,会在雪下形成小水洼,大约三英寸深,有的则深达三英尺。
在这些水洼表面会结成约半英寸厚的冰壳,冰壳上覆着积雪。
有时多个冰壳和夹杂其间的水层相互交叠着,人一踏上去就会陷下去一直没到腰部。
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小心翼翼地躲闪着。
他能感觉到他脚下积雪的松动;听到雪下的薄冰碎裂的声音。
在这样的气温下弄湿了脚是麻烦甚至危险的,至少也要耽误些时间。
因为那样的话,他必须停下来生一堆火,在火堆光着脚烤干袜子和鹿皮靴。
他站定了,辨认了一下河床和河岸,确认水流来自右边。
他思考了片刻,一边又擦了擦鼻子和脸。
然后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掂量着每一次落脚的分量,朝左边绕过去。
一旦躲开了一个危险,他就狠嚼一口烟草,然后继续蹒跚着向一小时四英里的目标迈进。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他总是遇到相同的陷阱。
覆盖在水洼上的积雪通常是凹陷而且稀松的,这样就容易识别。
不过还是有一次,他差一点就踏了上去;又有一次,他觉得前面的雪地不可靠,就命令那狗走在前面,那狗不干,一个劲儿向后缩着。
最后他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向前挪过去。
那狗紧跟着他跑过了那白色的、看似牢固的雪地。
突然,雪壳穿了,那狗掉了下去。
它挣扎到水洼边,爬上了一处结实些的地方。
它的前肢全湿了,上面的水很快结了冰。
它立即咬掉了它腿上的冰块,接着有躺在雪地上咬爪子上的。
是它的直觉让它这样干的。
如果听任冰块留在那儿会让腿脚剧痛,它并不知道这一层,它只不过遵循着那种从它自身的最深处升起的无名的冲动。
那人却明白这一点,他权衡了一下情况,摘下了右手的连指手套好让右手去擦拭眼角,防止眼泪冻结。
让他吃惊的是,他的指头敞在外面还不到一分钟,那迅捷的麻木感就已经侵袭了它们。
的确很冷啊!
他赶紧拉上手套,然后用右手使劲地捶着胸口。
十二点是一天中最亮的时候,但太阳仍然在地平线以下遥远的南方作她冬日的徜徉。
大地上凸起的山峦将她同哈德逊湾隔开,在这儿,那人在正午的晴空下走着,连做伴的影子也没有。
十二点半,他按时到达了那岔口。
他对自己行进的速度很满意,若能保持的话,就一定能在六点钟赶到同伴们中间。
他解开大衣和衬衫,取出他的午餐来。
整个动作不过十几秒钟,可就在这样短的一段时间里,麻木又一次抓住了他裸露的指头。
他没有马上戴上手套,而是狠狠地用手拍着大腿。
片刻之后,他在一根被雪盖住的圆木上坐下打算开始吃东西。
可是手指在腿上猛拍所产生的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却让他大吃一惊。
他不停地拍打着手,终于只好又把手套戴上;然后脱出另一只手来好吃饭。
可是这样却弄得他连吃到一块饼干的机会也没有。
他试着满满地咬上一口,可封冻的嘴唇却张不开。
他忘了该升一堆火来熔化嘴上的冰块。
为这个失误他吃吃地笑了,可要笑的时候,他感到麻木已经钻到他裸露的指头里去了。
而且,他还发现行走时总是最先觉得疼的脚尖在他坐下以后也不疼了。
他想弄明白脚步指是否也麻木了,将脚在靴子里擦搓着,然后他明白脚趾也冻僵了。
他开始感到有些害怕,赶紧戴上手套站了起来,一个劲儿地跺脚直到脚又有了剌痛感。
的确是冷啊,他想。
有一个从硫磺湾回来的人曾提到过在野外有时会冷到什么程度。
那个人说得没错!
而他那时候却在嘲笑那人,这说明他没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明摆着的,冷极了!
他把脚高高地抬起来,跺下去;同时不停地拍打着手,直到确认它们又暖和起来了为止。
然后他拿出火柴着手生一堆火。
他在灌木丛中找到了木柴,那是在过去的春天发大水时生长起来的。
经过一会儿小心细致的努力,他升起了一堆旺火。
他在火旁烤化了脸上的冰块,在火焰的庇护下吃掉了饼干。
那狗满意地躺在火旁,它在合适的距离上舒展开身体,这样既十分暖和又不会被烧到。
一时间,四周的寒冷仿佛退却开了。
吃过午饭,他装上烟斗惬意地抽起来。
然后他戴好了手套,拉下两侧的帽沿牢牢地护住耳朵,沿着冰河的支流继续前进。
那狗恋恋不舍地朝着火堆嚎叫着,可那人却不知道冷。
可能,他祖上十八代的先人都对寒冷一无所知,都对真正的,冰点以下一百零七度的寒冷一无所知。
那狗却知道;它所有的祖先都知道;它从它们那儿知道这一点。
它还知道在这样冷得可怕的天气里到处走是很坏的。
现在应当蜷缩在雪下的一个洞里等着大片大片的云层覆盖这阴冷的天空。
不过,那狗和人之间没有什么亲密的感情,一个是帮另一个干活儿的奴隶,狗所能得到的爱抚是呼啸的皮鞭和粗声粗气的嗓门里发出的关于呼啸的皮鞭的威胁。
所以那狗并不会想方设法将自己的忧虑告诉那人。
它才不关心那人的死活呢。
它是为了它自己的缘故才对着火堆嚎叫的。
但那人却冲着它吹口哨,并用呼啸的皮鞭的嗓门儿冲它大喊大叫,它只好转过身来跟着那人走开。
那人嚼了一口烟叶,又开始给自己打造一副新的琥珀胡子。
他呼出的湿气很快就在他的胡子、眉毛和睫毛上打了一层霜。
在这哈德逊湾的支流上似乎没有那么多暗沟,在半小时里他还没有发现有一处存在的迹象。
可倒楣的事却发生了:
在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特别,柔软而紧密的雪地看上去牢靠而实在。
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他踏穿了,陷了下去。
水洼不算深,冰水淹没了他膝盖以下的半条小腿,他赶紧挣扎着上到坚实的地方。
他很恼火,一个劲儿咒骂这倒楣的运气。
他原计划六点钟到达营地与同伴们会合,而现在他得因为生火烤干鞋袜而耽误一个钟头。
在低温的环境里这是极其紧迫的,他对此很清楚,于是转身爬到土坡上。
在坡顶的灌木丛中、低矮树木的枝干上,纠缠接着的枝条就是春天的遗留物——干燥的木柴;而更重要的是有大片的碎木片和干燥的去年的草类。
他将许多大片的木片铺在雪地上,这样可以防止烧旺了的火烤化的雪水将火浸灭。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片白桦皮,用火柴在上面一擦,打着了火。
这东西比纸还易燃,他立即将这片白桦皮放在铺好的木片上,再抓着小把小把的干草和最小最细的树枝往这一团小火里送。
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干这些事时显得十分缓慢而小心。
渐渐地火大了起来,他也增大了柴禾的块头。
他蹲在雪里,从灌木丛纠缠不清的枝杈里不断地扯下些枝丫经直送进火里。
绝对不能出一个错!
他知道,当一个人弄湿了脚呆在零下七十五度的天气里时,他要生的第一堆火是绝不能失败的。
如果他的脚是干的,火没人升起来的话,他可以沿着雪路跑上半里来恢复血液的循环。
但一双冻僵的湿脚上的血液在零下七十五度的气温里是没法通过跑步来恢复流动的;不论他得多快,脚都只会冻得越来越死。
这一切他都明白。
秋天,那个硫磺湾的归来者曾经警告过他,现在他认真地思考那些警告了,而此时双脚已经毫无知觉了。
为了生火,他不得不又脱下连指手套,手指又很快地麻木了。
他每小时四哩的进度支持着他搏动的心脏将血液送到他身体的表面和每一只指尖,但自从他停下来的那一刻起,那种搏动便减缓了下来。
寒潮侵袭着这个星球的这个荒僻的角落,而他,正在这个荒僻的角落里承受着寒潮全部的冲击。
他的血液早已退缩了,血是活的,就像狗,也想藏起来,把自己埋起来好避开这可怕的寒冷。
当他以每小时四哩的速度行进时,他强迫着,挤压着他的血液流到身体的边缘去;但现在,血液退却了,收缩到了他身体的深处。
他已开始感觉不到自己指头的存在了。
他的湿脚越来越僵,手指也越来越麻木,尽管它们还没有完全僵死;鼻子和脸已经僵了,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冷得好像没了血液。
不过他仍是安全的,脚趾、鼻子和颧骨只是让寒潮舔了一下,这时火旺旺的烧起来了。
他用有他手指那么粗的枝条去喂它,过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将手腕那么粗的树枝塞进去了。
到那时,他就可以脱下鞋袜去烘干它们,把裸露的脚也烤暖和——当然,先得用雪搓上一阵。
火就是胜利,他得救了!
他想起了那个硫磺湾的归来者的警告,他笑了。
那个人一口咬定没人能在冬天的克朗代克单独旅行,但现在他做到了!
他干了这件事并且活了下来。
“嘿,看来那些老手们不过全都是些娘们儿!
至少他们中有的人是”他想着。
一个男人该做的就是保持颜面,而他就是赢家!
是男人的话就单独前进!
不过他没料到的是自己的鼻子和脸会冻僵得如此之快;他没料到的是自己的手指这么一会儿就僵死了。
指头是那样地不听使唤,他想合拢它们好抓起一根小枝桠都不行,好象它们已经不在他身上了,已经离开他了一样。
当他想抓起一根小枝的时候,不得不看看自己是否抓住了。
那根树枝在他面前径直的从他指间落了下去。
不管那么多了!
火焰在燃烧着、跳动着、噼啪响着,用它的每一个火苗跳着生命之舞。
他开始解开他的鹿皮靴。
鹿皮靴已经让冰包住了;厚厚的德国产长统袜硬得像铁皮打的刀鞘死死地箍着他的小腿肚子;而鹿皮靴的鞋带如同是火灾过后扭曲、交织成一团的钢条。
他用麻木的手指使劲地拽着,不久他明白这是白费力气,于是拔出了砍刀。
不过还没等他割断鞋带,坏事却发生了。
这是他自己的错,一个大错:
他不该在树下生火,应该在开阔地才对,虽然在树下可以方便地从树丛中扯下枝条直接送进火里。
在他生火的地方的那颗树上已经积起了厚厚的一层雪。
有一个星期没吹风了,树杈上的雪已经积满,摇摇欲坠。
每一次他从树上扯下一根树枝时都感到一丝轻微的不安和颤动,一丝他自己难以察觉的不安和一丝足以导致灾难的颤动。
在树梢处的一根树枝上的积雪给抖落了,落在下面的树枝上,使那些树枝上的积雪也掉落下去,就像滚雪球似的,这一动作向外扩展着它的影响直到整棵树都卷入了这场纷争。
没有警告,像雪崩一样,大片的积雪径直砸在那人和火堆上面。
火灭了!
给盖住了。
原先的火堆变成了一摊碎雪。
他惊呆了,仿佛听见了死神的召唤。
有片刻他呆坐在那儿凝视着火堆的残骸。
然后他平静了下来。
假如他听从了那个硫磺湾的归来者的劝告;假如他有一个同伴,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弄湿了脚,他的同伴会帮他生火的。
没办法,必须再升起一堆火来,而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有一点差池的。
就算成功了,他也多半会失去几个脚趾。
他那冻僵的脚现在一定糟透了,而离第二堆火升起来却还有一段时间。
这是他的念头,他根本没细想,在他一个劲儿忙活的时候这些念头一一在他的头脑里闪过。
他为火堆铺起了一层新的地毯,这一次是在开阔地,没有捣乱的树会跑来扑灭它。
然后,他又从那些春天的残骸中收集起了一堆干草和树枝。
他不能用手指捏住它们扯下来,但可以一次一把地握住。
这样他只弄到一些腐烂的枝桠和一点儿苔藓,远不够用,但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
他有条不紊地干着,甚至还收集起了一抱粗大的树枝以备火焰烧旺之后使用。
整个过程中那狗在一旁蹲者注视着他,眼中充满了急切的渴望。
在那畜生眼里他是一个可以提供火的人,一堆火正慢慢地被创造出来。
万事俱备,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另一片白桦皮。
他知道它在那儿,虽然他没法用手指感觉到它,却能听见手指和它摩擦时发出的那种清脆的沙沙声。
可是他尝试过了最大的努力,却抓不住那片白桦皮。
他知道在这整段时间里的每时每刻他的脚都在挨冻。
这一意识让他觉得恐慌,不过他仍努力克服着并保持冷静。
他用牙咬着拉上了连指手套,用力前后甩着手臂,用手狠狠地砸自己的胸口;他原先是坐着的,又赶紧站起来不停地砸着。
整个过程中那狗蹲在雪地里,狼一样的大尾巴暖和地盘着,盖住了前爪;狼一样的尖耳朵一动不动地向前探着,仿佛盯着那人一般。
而那人,在他敲拳头、甩胳膊时,却对那畜生有着天生的用以抵御寒冷和保全性命的毛皮感到了一种剧烈的羡慕。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那正敲击着的指头开始有了一种遥远的感觉,那微弱的疼痛逐渐强烈起来,直到演变为一种明显的刺痛。
他觉得这样足够了。
于是从右手上摘下了连指手套去摸那片白桦皮。
裸露的指头很快又麻木了。
接着他拿出一把硫磺头的火柴。
但那可怕的寒冷已经从他的指头上夺走了生气,他本想从那一把火柴里抽出一支来,火柴却全都掉到了雪地上。
他试图把它们从雪地里抠出来,却无法做到,僵死的手指抓不住也摸不到了。
由此他想到了自己冻僵的脚、鼻子和脸颊,全都感觉不到了。
他小心翼翼,整个心思想要抓起那些火柴。
他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想用视觉来弥补麻木的触觉。
他看着他的指头罩住了它们,然后合拢,或者,想要合拢,但他手上的线路已经断了,手指不听使唤。
他给右手又戴上了手套,在膝盖上猛烈地拍着。
最后,他不敢再摘掉手套,双手并用将那些火柴连同一把碎雪一起捧了起来放到了衣兜上。
他只能做到这样了。
经过一番细致的努力,他将那些火柴挑了出来夹在两个手掌间。
用这样的姿势他把火柴捧到了嘴边。
他强行把嘴张开,嘴上的冰甲发出断裂的噼啪声。
他用下唇包起下牙,上唇翘起,伸出上颌想要用门牙在那一把火柴里挖出一根来。
他做到了,他从那把火柴里挖出了一根落在了他的衣兜上。
他只能做到这样。
他无法将那根火柴拈起来,不过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用牙齿咬着,将火柴在大腿上摩擦。
然后他就这样衔着那根燃着的火柴去点那块白桦皮。
可火焰的边沿却窜上了他的鼻孔并钻进了他的肺里,呛得他立即不住地咳起来。
那根火柴栽进雪地里,熄灭了。
那个从硫磺湾回来的家伙是对的!
他在接踵而来的绝望中想到:
在零下五十度的天气里应该结伴而行。
他敲打着双手,但再也没有一点儿感觉了。
突然,他用牙扯掉手套,露出双手。
然后用双掌夹起所有的火柴——他臂上的肌肉还没有冻僵,这使得他还可以用双掌紧紧地夹着——他就这样将那一把火柴在自己腿上摩擦。
火柴头闪出了火花,七十支硫磺头一下子全都点着了!
没有风来吹灭它们。
他把脑袋偏向一边好避开令人窒息的烟雾,将那一把火柴夹到那片白桦皮上。
他这样夹着的时候,感到手上又有了一点知觉。
他的手掌烧着了,他闻到了焦味,也能隐约感觉到。
那感觉逐渐清晰起来,变成了灼痛。
他忍着痛,笨拙地夹着燃烧的火柴将火焰凑到那片白桦皮上去,可白桦皮却难以点燃——他的手在碍事,挡住了大部分的火焰。
剧痛让他受不了了,他的手猛地抽搐了一下,火柴扎进了雪里,咝咝响着。
但白桦皮总算是点燃了。
他开始把干草和细小的枝桠向火里送。
他没法挑选,因为他只能用手掌去夹起那些燃料。
有小片的朽木或者绿色的苔藓夹杂在那些枝桠里,他尽量用牙齿将它们咬出来。
他小心翼翼但笨手笨脚地呵护这一团小火——火就是生命,一定不能熄灭!
体表的失血现在让他哆嗦起来,也让他更加笨拙了。
有一片苔藓直直地砸在了那一堆小火上。
他打算用手指把那片苔藓拨开去,可颤抖的手却拨得太狠了,连同那一堆小火也给拨散了,燃烧着的干草和枝桠分散开来。
于是他赶紧试图将它们重新聚拢起来,虽然他付出了极为紧张而顽强的努力,但颤抖不止的身体却出卖了他,那些枝桠仍然令人绝望地四散着,接着纷纷冒出一缕缕青烟,熄了。
提供火的人失败了。
他默然地四下里看了看,看到了那条狗,坐在那由他造成的火堆的残骸中间,在雪地里焦躁不安地蠕动着,前肢不停地轻轻蹬着,身子急切地前后耸动着。
对狗的注视唤起了他的一个残忍的念头。
他想起有一个人,被困在了暴风雪里,结果那人杀死了一头牛然后钻进剖开的尸体里去,这样救了他自己一命。
他得杀死那条狗,把手插进它温暖的尸体里去直到不再麻木了为止。
这样,他才能再升起一堆火。
他叫那狗,唤它到他这儿来。
但他的嗓门里所有的一种奇怪的恐怖情绪却吓住了那畜生——它以前从没听见过什么人用这样的嗓音来叫它。
有什么不对劲儿?
那畜生多疑的天性嗅到了危险,什么样的危险它不清楚,但那危险就在某处,以某种方式窥视着,它对那人产生了警惕。
它垂下了耳朵好不去听那人的声音,它的焦躁不安的蠕动、耸动和蹬脚的动作更加剧烈了一些,但它并不打算到那人那儿去。
那人跪下,双手双膝并用向那狗爬去。
这个不寻常的动作更加可疑,狗侧身跑开了。
他坐在雪地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然后他用牙齿戴上连指手套,试着双脚直立起来。
双脚的知觉全无使他失去了同大地的联系,他向下注视着自己的动作,慢慢站了起来。
他直立的姿势开始打消了那狗的疑虑。
他用惯常的音调,也就是呼啸的皮鞭的嗓门冲那狗喊着。
狗表现出了那种惯常的顺从向他走来。
当那畜生刚刚进入他够得着的距离,他立刻暴跳起来,张开双臂向那狗扑了出去。
那一刹那间他忘了自己的双手已经冻僵了,而且一直在冻着。
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那狗还来不及跳开那人就死死地箍住了它。
他着实大吃一惊,他的手全无知觉,手指一点也无法弯曲,根本不能抓住什么东西。
那人跌坐在雪地上,以这样的姿势紧紧地搂着那条狗。
那狗咆哮着、呜咽着、猛烈地挣扎着。
但他只能做到这样,这样搂着那狗坐在那儿。
他明白了自己没法儿弄死它,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双毫无知觉的手既不能拔出砍刀也握不住,更不可能掐死那畜生。
他松了手,那狗猛然窜了出去。
咆哮着,夹着尾巴跑到离他约四英尺的地方停下来。
它尖尖的耳朵向前探着,疑惑不解地打量着那人。
那人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好确定它们的位置。
两手无力地挂在臂膀的末端。
一个人得靠眼睛来弄明白自己的手在哪儿,这让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惊奇。
他又开始使劲地前后甩着双手,将手在肋骨上敲着、狠狠地敲着。
这样干了五分钟,他的心脏的搏动剧烈起来,将血液压到了他身体的表面,这让他暂时停止了颤抖。
但双手仍然毫无知觉,仍然像重物一样悬挂在他臂膀的末端。
这情形使他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他力图驱散这个印象,却做不到。
他感受到了死亡,一种模糊而压抑的威胁。
这威胁越发地痛彻起来,他意识到了这不再仅仅是冻掉几个手指或脚趾的事情,也不单是失去手或者脚的事情,而是生死攸关、胜负难料的严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