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docx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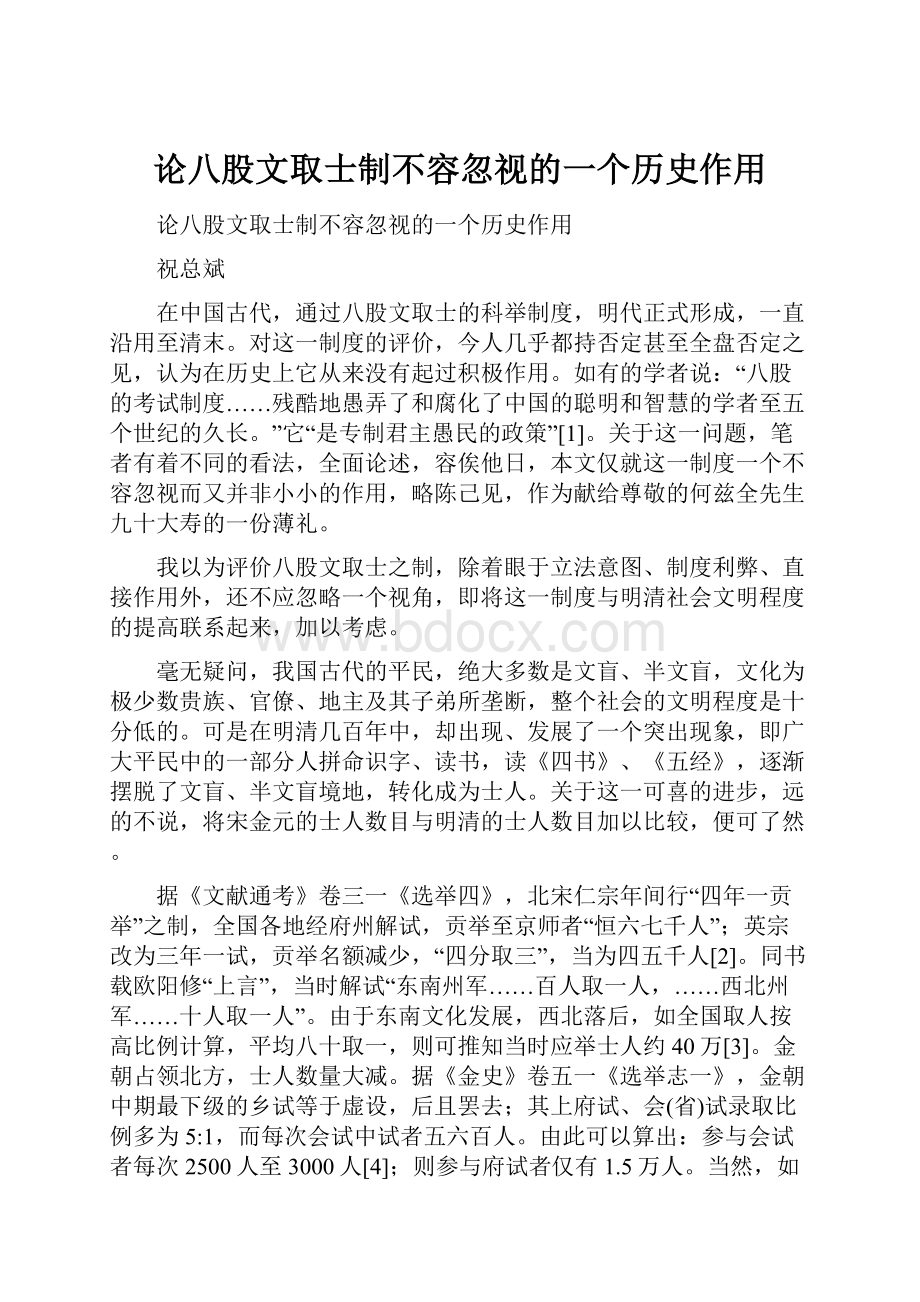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祝总斌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
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如有的学者说:
“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
”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
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
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
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
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
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
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
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
由此可以算出:
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
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情况则不同。
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
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
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
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
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
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
再看学校。
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
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
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
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
如据一史料记载:
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
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
学校已为虚设[9]。
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
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
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
顾炎武曾估计:
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
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
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
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
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
梁启超也估计:
“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
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
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
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
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
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
原因何在?
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
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
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
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
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
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
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
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
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
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
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
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
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
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
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
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
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
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
……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
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
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
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
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
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
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
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
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
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
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
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
下面略作阐释。
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
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
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
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
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
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
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
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
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
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
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
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
乾隆自己也说:
“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
”[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
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
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
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
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
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
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
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
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
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
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
故清初杨宁曰:
“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
”[46]
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
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
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
‘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
’遂罢其议。
”[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
试举二例: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
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
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
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
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
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
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
‘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
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
’”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
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
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
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
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
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
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
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
钱基博先生便说:
“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
”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
他说:
“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
斯不愧知言之士已!
”[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
--------------------------------------------------------------------------------
[1]容肇祖《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载《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
又参见何忠礼《二十世纪的中国科举制度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八“省试取人额”条:
黄庭坚于哲宗元祐三年为贡院参详官,“试礼部进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可证。
[3]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称宋哲宗时,“天下应举者无虑数十万人”;卷四《官冗议》又称“今科举之士……十数万人”。
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67页以为,由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到宣和二年的20年中,共进行了7次考试,“每次参与考试的人数大约在十万人到四十万人”。
[4]《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载金末御史中丞把胡鲁言:
“(世宗)大定间赴(会)试者或至三千”。
[5]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附录三《南宋贡举登科表》共49榜,录取正奏名进士2.3万余人。
由此计算得出。
[6]葛绍欧《宋代府州的贡院》,载《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305页。
文中列有南宋21篇府州军“贡院记”表,其中记有投考人数者10篇,由“数百人”至万人不等。
经粗略计算,平均为3900余人。
按南宋府州军监共204(见顾颉刚等《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2—165页),则可知投考人数亦为80万,与上一数字吻合。
[7]参见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第三章第七节,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又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下册第2编第22章第570页,便说这两万多学校“盖合社学而言”。
[8]见《庙学典礼》卷五“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式”条。
又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说极受推崇的元代书院,“规模都比较小……有些书院只有二三十名学生”。
同书第124页引近人学术成果称元朝共有书院296所。
如果平均收学生按40名计,一共也只有1.2万人,远不足与80万之数相比。
[9]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养士》,见《元代奏议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下编第93页。
[10]关于“重吏轻儒政策”,参见拙文《试论我国古代吏胥制度的发展阶段及其形成的原因》,载《燕京学报》第9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1]陶安《陶学士集》卷一五《送马师鲁引》。
[12]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四《新城县庙学记》。
[13]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
[14]张仲礼《中国绅士》第二章第二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人数,不是每次童试录取之数,依张先生算法,它是21次童试中试秀才,又终生未考上举人者所积累之数。
具体算法,请参见该书。
顾炎武所估计明末秀才数,亦大体当如此理解。
又明清都有武举,张仲礼上书以为太平天国前武秀才有21万多,因非八股文取士,本文从略。
[15]同上书,第90页。
[16]《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7]《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见同上书,第79页。
[18]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二《学校一》称明末江南各县“县试童子(即童生)不下二三千人”。
江南文化发达,如全国每县童生平均低估为1000余人,据《明史·地理志一》,明代府州县共1471个,则全国童生总数也近200万。
[19]士人中还有高中级士人,即进士、举人,各级官府之幕友,以及隐士等,但因数量都很少,这个数字已可包容,不再另计。
[20]这是考虑到明清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如印刷术普及、书籍大增等),人口增加等因素。
但人口增加与士人增加,比例并不一致。
据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6页,元代全国人口突破1亿,“较宋金户数之和增14.7%”,但如上所考,士人总数减少;第459页,明万历时人口1.5亿,但秀才加童生即士人总数却有200余万,增加好几倍;第510页,清道光三十年,即太平天国起义前,人口猛增至4.3亿,但秀才数52万余,仅比明末50万略多。
可证士人总数变化当主要决定于其他因素。
[21]如元代是“选秀民充弟子员”,“选民俊秀入学”等,见《续文献通考》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
[22]《明(万历)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选补生员》。
同条记载后来又规定:
生员缺,“许本处官员军民之家……选补”,“官员”在首位。
[23]《明(万历)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选补生员》。
[24]据《续文献通考》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皇明》“风宪官提督”条:
明万历敕谕“童生必择三场俱通者,始收入学。
大府不过二十人,大州县不得过十五人”。
如录取人数平均按十三四人计,《明史·地理志一》记明代府州县共1471个,则全国每次童试录取约2万人。
清太平天国起义前每次童试录取总数为2.5万人,见前引《中国绅士》第86页。
[25]同上引“风宪官提督”条:
万历十一年题准,已有三年内“岁考”及“科举之年”再考的规定。
《阅世编》卷二《学校一》载明末“三年两试”,称“科入”、“岁入”新生云云。
清三年两试,参《中国绅士》第71页。
[26]分别见《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及《明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廪馔》。
[27]《明会典》卷七八《礼部三十六·学校·儒学·风宪官提督》。
[28]《清(光绪)会典》卷三二《礼部》“简学政……敦其士习”条。
[29]《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上》。
又《清会典》卷三二“敦其士习”条:
对秀才“各衙门官以礼相待”;秀才违法,“地方官不得擅自扑责”。
如“笞杖轻罪,照律纳赎”,见《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任彭年重辑)卷四赎刑条例。
[30]参见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载《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见前引《中国绅士》第一章第三节。
[31]《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
谓之八股。
”参见拙文《略论中国封建政权的运行机制》第五节“人事机制”,见马克尧主编《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研究》第十章,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317页。
[32]《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33]《清史稿》卷一一五《选举志三》。
[34]此钱大昕语,见《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科场”条。
直到清末依然是科举“唯重《四书》文”,见徐勤《中国除害议》,载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6页。
[35]《清史稿》卷一一三《选举志一》。
《小学》,朱熹所作,内容浅显,“意取启蒙,本无深奥”,参《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二《子部儒家类二·小学集注》提要。
[36]《钦定学政全书》(嘉庆十五年)卷六“厘正文体”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五经”,此处不具论。
[37]参《明史》卷七○《选举志二》、《清史稿》卷一一五《选举志三》、《续文献通考》卷四五《选举考·举士三》。
[38]参见拙文《〈四书〉传播、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9]虽然实际上士人只选考一经,仍甚烦重。
如清礼部便曾评价郑玄等注疏《礼记》“卷帙繁多,学者难以诵习”,见光绪增修《钦定科场条例》卷一七“乡会试艺”门,乾隆五十八年。
[40]参拙文《〈四书〉传播。
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如《论语》在唐代为“小儿”学习之书,是“易习”之书。
等。
[41]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一《答敬夫〈孟子〉说疑义》。
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页。
[42]参见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载《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43]《四书》、《五经》,作者均被认定是先秦时人,如代其中圣贤立言,自不能涉及秦汉以下事。
如乾隆年间一次会试,题出《诗经》,某考生用“肠一日而九回”句,“上(乾隆)以言孔孟言,不应袭用《汉书》语”,下令“严重磨勘”,查禁类似现象。
见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
[44]就统治集团主观意图言,只是为了逼使士人认真读经书,阐述经义,不要胡乱联系后代史事。
早在北宋已有“经义禁引史传”之例,见《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
[45]清初大儒陆陇其《示子帖》便说:
学八股文体,“只当择数十篇时文,看其规矩格式足矣”,只有“读经”等,才是“根本功夫”,“根本有得,则时文亦自然长进矣!
”见《制义丛话》卷二。
顾炎武《日知录》多处只就经义内容被剽窃,尖锐批评八股文后来的弊端,虽介绍八股文体、格式,无一字批评语,原因亦在于此。
[46]《日知录集释》卷一七“生员额数”条集释引。
何炳棣统计1371—1904年1.2万多进士,1804—1910年2.2万多举人、贡生履历,发现超过49%的“绅士”,均出身“布衣”家庭,转引自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第29页。
生员中“布衣”比例当更高。
[47]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五“议考试废制义”条。
此证行八股文取士制主观上是为了宣扬“义理”,即程朱理学,前文已提及;但客观上却促成人们读“四子书”。
[48]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一回:
陕西朝邑县一村庄“祖上世代为农”。
后因赵姓人家有人中了秀才,十分风光,方姓“瞧着眼热”,也出钱办一学堂,请一“举人老夫子”“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
同样反映秀才的诱惑力。
[49]当时童试需经县试、府试和院试(由学政主持),方能入学,成秀才。
此彭鹤皋虽在府县试“屡居前列”,当因未通过院试,故仍不得入学。
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一章,三联书店1958年版。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