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性哲学详解.docx
《《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性哲学详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性哲学详解.docx(2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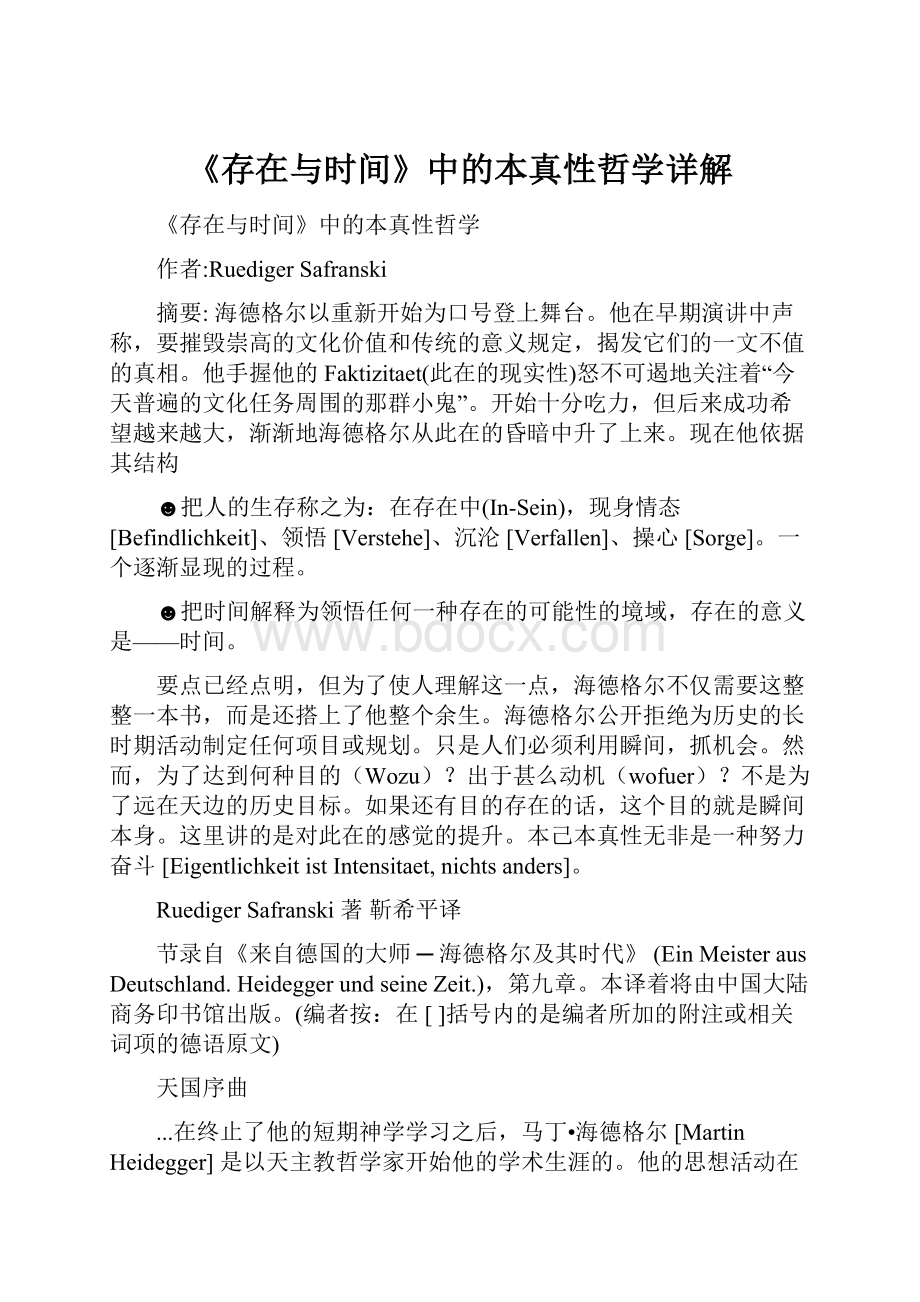
《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性哲学详解
《存在与时间》中的本真性哲学
作者:
RuedigerSafranski
摘要:
海德格尔以重新开始为口号登上舞台。
他在早期演讲中声称,要摧毁崇高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意义规定,揭发它们的一文不值的真相。
他手握他的Faktizitaet(此在的现实性)怒不可遏地关注着“今天普遍的文化任务周围的那群小鬼”。
开始十分吃力,但后来成功希望越来越大,渐渐地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昏暗中升了上来。
现在他依据其结构
☻把人的生存称之为:
在存在中(In-Sein),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领悟[Verstehe]、沉沦[Verfallen]、操心[Sorge]。
一个逐渐显现的过程。
☻把时间解释为领悟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的境域,存在的意义是——时间。
要点已经点明,但为了使人理解这一点,海德格尔不仅需要这整整一本书,而是还搭上了他整个余生。
海德格尔公开拒绝为历史的长时期活动制定任何项目或规划。
只是人们必须利用瞬间,抓机会。
然而,为了达到何种目的(Wozu)?
出于甚么动机(wofuer)?
不是为了远在天边的历史目标。
如果还有目的存在的话,这个目的就是瞬间本身。
这里讲的是对此在的感觉的提升。
本己本真性无非是一种努力奋斗[EigentlichkeitistIntensitaet,nichtsanders]。
RuedigerSafranski著靳希平译
节录自《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及其时代》(EinMeisterausDeutschland.HeideggerundseineZeit.),第九章。
本译着将由中国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
(编者按:
在[]括号内的是编者所加的附注或相关词项的德语原文)
天国序曲
...在终止了他的短期神学学习之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是以天主教哲学家开始他的学术生涯的。
他的思想活动在对上帝进行研究的领域:
在这里,上帝是我们的世界性知识和自我认识的终结和保证。
面对神已经失去意义的现代(文化)的挑战,海德格尔出身的那个传统仅能力求自保而矣。
为了要保卫麦氏教堂镇[Messkirch镇位于德国巴登邦,乃海德格尔的出生地]的这一片天,海德格尔也曾启用现代的武器,比如
☻胡塞尔[Husserl]关于逻辑的有效性是超时间超主体的观点。
在中世纪形而上学的哲学中他发现了这个观点的雏形。
在这里他还发现了
☻理性的唯名论式的自我怀疑:
它确切认识的,理性不仅不能把握上帝,而且也无力把握"haecceitas",即在此的这个东西,唯一性的个体。
Individuumestineffabile(个体是不可言传的)。
但是,关于历史性的观念才真正向他揭示了整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所在。
尽管形而上学并不认为人是固定不变的,但却都坚持,最后的意义联系是固定不变的。
通过对狄尔泰的学习,海德格尔认识到,☻真理本身也有它的历史。
在他的大学教职论文接近完成之际,他的基本观点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他开始从较远的距离上观察同他如此亲近的中世纪思想,发现尽管它楚楚动人,但那是一个精神沉没的时代。
按照狄尔泰的看法,☻「只有在人和他的历史中意义和意思才得以产生。
」狄尔泰的这个观点成了他的最高原则。
对历史性观念的彻底把握摧毁了那种无所不包的普遍有效性的要求。
在欧洲历史上这种观念在对人本身的自我把握中造成了可能最巨大的裂隙。
它意味着海德格尔天主教哲学思考的结束...
历史性的生活成为哲学思考的基础。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只要「生存」这个概念尚未得到澄清,那么这个看法就不会产生甚么具体成果。
在现象学的「学校」里,他才渐渐意识到,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他以杰出的现象学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采取甚么样的立场才可以使人的生存「显示」出它的特征性属性。
这个问题的回答奠定了他自己哲学的基础:
☻对对象化的批判。
主客二分
他告诫我们,当我们企图在对象化过程中从理论上对人的生存进行把握时,生存就会从我们面前滑过去。
在我们尝试对简单的「讲台经历」加以有意识的把握时,我们就已经注意到这类情况。
☻在客观化的思考中,生存的世界性关联这种丰富内容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客观的立场会使生存经历失去生存[entlebt],使与我们相遇的世界失去了世界[entweltet]。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转向人们所经历的瞬间的昏暗。
但这里并不涉及甚么神秘的深刻,也不涉及下意识的地下世界,或者神灵的天界。
这里涉及的是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生存实施过程中的自身的透明性[SelbstdurchsichtigkeitderLebensvollzuege]。
在海德格尔这里,
☻哲学成为一种此在使自己觉悟的艺术[编者按:
「此在」于本文是Dasein之翻译]。
转向日常生活还有一种挑战的味道:
☻它是对那种总以为可以认识人生的规定性的哲学的挑战。
海德格尔以重新开始为口号登上舞台。
在他早期演讲录中,有明显的达达主义的狂热,要摧毁崇高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意义规定,揭发它们的一文不值的真相。
他手握他的Faktizitaet(此在的现实性)怒不可遏地关注着「今天普遍的文化任务周围的那群小鬼」(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给列维特[Loewith]的信中这样写道)。
开始十分吃力,但后来成功希望越来越大,渐渐地海德格尔从此在的昏暗中升了上来。
现在他依据其结构
☻把人的生存称之为:
在存在中(In-Sein),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领悟[Verstehe]、沉沦[Verfallen]、操心[Sorge]。
这些就是《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生存性概念」[Existenzialien]。
他找到了「关涉其本己本真的存在之可能性的此在的表达形式」。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想通过他的工作从哲学上证明,
☻此在[menschlichesDasein]除了他在那里存在的此(da,场或情景)之外一无所有。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工作是尼采工作的继续。
尼采思考上帝的死亡,批判「最后的人」,因为,人们用神的代用品来勉强应付塞责,以逃避对上帝消失的惊恐。
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惊恐能力的表达方式是:
「有勇气去畏惧」。
《存在与时间》这个题目告诉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整体的问题。
该书戏剧性的布局十分成功。
书以「天国序曲」开篇:
柏拉图首先登场。
从柏拉图的《智者篇》[Sophistes]中引的一段话:
「因为,显然当你们使用『存在』这个字的时候,你们早已对你们本来所想的内容了如指掌。
但是我们则以为,我们尽管已经对它有所领悟,可是现在我们却陷入了尴尬的困境」。
海德格尔认为,这个「尴尬困境」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不肯承认它。
当我们说,某种东西存在(是)时候,我们一直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说甚么。
这个序曲控告了对存在的双重遗忘:
☻我们忘记了,存在是甚么;☻同时也忘记了我们这种忘记。
因此现在应该重新对存在的意义进行发问。
但是由于我们已忘记了我们的这种忘记,所以,「首先应该重新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的领悟」。
这个序曲为甚么而作,在书开始已有明示,把时间解释为领悟任何一种存在的可能性的境域。
存在的意义是——时间。
要点已经点明,但为了使人理解这一点,海德格尔不仅需要这整整一本书,而是还搭上了他整个余生。
甚么存在﹖甚么意义﹖从何开始﹖
存在问题。
严格的讲,海德格尔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seiend)时,我们到底想的是甚么﹖这里被问及的是表达的意义。
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和关于存在本身的意义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领悟这个问题在意义上的双重性,海德格尔居然声称,对这个问题意义的领悟根本就不曾有过。
一个令人惊异的断言。
我们可以说,
☻关于存在的意义(不是关于表达的意义)的问题,是一个自历史之初直到今天,一直不间断地困扰着人类思考的问题。
☻这是对人类生存的意义、目的、含义以及自然的意义、目的、含义的发问。
☻这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取向的发问,是对世界、天界和宇宙为何原因和为何目的的发问。
☻实践上的道德生存使人对此发问。
在物理学、形而上学和神学尚且没有分离的过去的年代,科学也曾试图解答关于意义的问题。
但是康德发现,我们人作为道德的实体,肯定会对意义发问,可是人作为科学家却不能对此给予任何回答。
从此以后,严密的科学对意义问题退避三舍。
但在人的实践中的道德生存却继续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在广告中、在诗歌中、在道德的反思中、在宗教里均是如此。
海德格尔怎么能声称,人们已经对这个问题根本无所领悟了呢﹖只有当他认为,所有这类意义的存在(Sinngebungen)以及与其相应的对意义的追问都仅止于与存在的意义擦身而过,他才可以作这类断言。
这个大胆断言使他自己获益匪浅,因为他是以柏拉图以来的遗忘性和遮蔽性的重新发现者的身份登场的。
首先海德格尔把关于对存在意义的发问(我把这个发问称之为「加强性问题」[emphatischeFrage])放在一边,而从另外一个问题,即语义问题开始他的追问。
当我们在表达中使用「是」(seiend)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说的意思是甚么﹖我们在甚么「意义」上在谈论「存在(Sein)」﹖这是一个和现代科学有关的问题。
任何一门科学,物理学、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是对各自确定的领域的实存([Bezirkdes]Seienden)的处理研究,或者它们在同一领域中工作,但使用着不同方法,关心的是不同的问题。
所有对方法的思考,即对以何种方式才适合于接近其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思考,都隐含了一种区域本体论[reginonaleOntologie],尽管人们并不如此称呼它。
正因为如此,开始人们并不理解海德格尔的下述断言:
人们并不想搞清楚,他们在各自领域中,于甚么意义上获取了「存在」。
因为,由新康德主义发展起来的恰恰是方法论意识的特殊重视。
李凯尔特[Richkert]和文德尔班[Windelband]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作出了细腻的区别。
还有狄尔泰的解释学、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解社会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下意识的心理分析解释学等等。
上述所有这些科学在方法上都不是天真幼稚的。
它们均有自己的本体论问题意识,都对它们自己在现实研究的相互联系中的位置进行了考察。
所以,无论在语义-方法问题上还是在存在意义的加强性问题上,情况都是一样的。
海德格尔都声称根本不存在对意义问题的理解--可是实际上这类问题到处被提出:
在实践的道德生活中常常提出的加强性问题,而在科学中常常提出的则是方法论-语义性问题[methodisch-semantischeFrage]。
海德格尔一定是想达到甚么特别的目的。
但他具体想要甚么,人们还不清楚。
他很成功地制造了一种紧张空气,然后才提出他的论题。
恰恰在关于人的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科学自身并不清楚,在甚么意义上让人作为实存(seiend)而存在。
从做法上看,似乎可以像对待世界中的其它现成在手的对象那样来对待人,可以以此获得关于人的整体概观。
在这个过程中,
☻科学实是循着此在的一种自发倾向:
此有倾向从实存出发去理解它自己的存在,此有本质上是不停地并且首先地与此实存之发生联系的;也就是说,此有倾向从「世界」出发理解它自己的存在。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一五页)。
但是
☻这实际上是此在的自我蒙蔽。
只要此在一息尚存,他就不会象一个对象那样成为一个做完了的、完整的、结束了的东西,而是永远向未来开放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的东西。
「可能-是」[Moeglich-sein]是属于此在的。
☻与其它的实存不同,人同自己本身的存在有着一种关系。
海德格尔把这种关系称之为「生存」(Existenz)...,生存(Existenz)具有「及物性」意义[transitiverSinn]。
而此在的不及物性[dasIntransitiveamDasein]被海德格尔称之为「被抛性」[Geworfenheit]:
「...难道此在自己为愿意或不愿意进入此在自由地作出了决断吗﹖」(《存在与时间》二二八页)但是当我们不及物地存在在那里时,我们所能作的就只是:
及物地成为我们不及物地存在的那东西。
我们不及物地已经所是的,我们就能够且必须及物地是。
后来萨特[Satre]为此发现了表达方式:
「从人为何故而被构成的那个『何故』处,人须再行创造」。
我们是一种同自身的关系,并因此是存在的关系。
「此在实存性的最显著的特征恰恰在于,它是懂存在的。
」(《存在与时间》一二页)
「实存的」(ontisch)这个表达指称任何存在的东西。
而「懂存在的(ontologisch)」是用于指称那种关于实存之好奇的、惊诧的、恐惧的思想活动,对于有我、和居然有某某内容存在的思考。
譬如格拉比(Grabbe)无法模仿的名句「只来世上一次,而且恰恰是Detmold的白铁工」,就是存在之论[ontologisch]。
☻此在或者生存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存在着),而且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着)。
☻我们从来不会象现成在手的东西那样成为一个成品。
☻我们不会走出去围着我们自己看来看去。
☻在任何一点上,我们都是向未来开放着。
☻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生活。
☻我们把我们交给了自己。
☻我们是我们的未来之生成。
如何谈论此在才是合适的﹖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就已经瞄准了时间。
我们象深入瞭望开放的地平线一样洞视着时间,此时我们便注意到,我们面对着某些不确定的、没把握的东西。
但有一个东西是确定的:
一个巨大的「过去了」[Vorbei过去。
消逝。
从……旁边经过。
],即那个死亡。
我们对它十分熟悉。
并不是因为他人的死亡我们才熟悉它,而是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会经历这个「过去了」:
☻时间的流逝--无数小的告别,无数小的死亡。
☻时间性就是对现在、将来以及死亡性的「过去了」的经验。
时间性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它的结束,一个是它的开放的维度,即向死亡的存在和向可能的存在--都是对此在的严重挑战。
正是囿于此,此在倾向于把自己看成如手头现成存在类似的东西,以至在它尚未完成之际便自以为,它是可以完成的,并因此使生命之圈结束,而我们则又处于开始的那个地方。
在海德格尔看来,
☻以科学的方式对人加以客观化,是在回避此在的躁动不安的时间性。
☻各种科学只不过是日常此在的人们熟知的顽固倾向的继续,即从世界出发,来理解自己;
☻即把自己理解成处于诸物中的一物。
海德格尔要触动的就是这颗铁石心。
海德格尔把加强性的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同「存在」这一表达的意义这个方法性语义性问题结合在一个讨论题中:
此在把自己抛到诸物之中的这种倾向,业已贯彻在关于存在意义的加强性问题的提问之中。
人们寻求的这个「意义」,就像在世界里或某种想象中寻找彼岸天国中存在的某种手头现存的东西一样,人们以为可以把它们当作依靠,或者作为生活的取向。
这类手头现存之物包括上帝、普遍适用的规律、千古不变的道德规范等等。
像寻找手头现存的东西那样去询问意义,也是此在逃避它的时间性和可能存在的一种方式。
从手头现存物的形而上学这个方向上去对存在意义进行发问和寻求答案是完全错误的。
今天这个魔鬼又在庆祝它的复活:
在这里「制作了一个意义」,那里又有了一个创造意义的项目,还有人谈论甚么意义贮备的紧缺,说甚么必须让它发挥经济效益等等。
这完全是特别愚蠢的手头现存性的形而上学。
这里涉及的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不正确态度。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存在意义的发问,已经不再属于高度发达的精密科学所研究的问题。
因为在那里这个发问已经作为不良行为被戒掉了。
当然实践-道德的日常意识还在提意义问题。
但是人们又是如何理解这种意识态度的呢﹖
畏惧直到该书中部海德格尔才让对存在意义的发问的主体登场。
这是《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戏剧技巧之一。
这个从事发问的「谁」,这个发问的主体是一种情绪(Stimmung),而其中的畏惧(Angst)是这种情绪的基础情态。
此在于恐惧中向存在的意义发问,向它存在的意义发问。
《存在与时间》著名的第四十节专门谈论畏惧问题,尽管身边有汉纳?
阿伦特[HannahArendt],但《存在与时间》中没有关于狂欢、关于爱情的章节。
其实从这些确定的情绪性出发也可以激发出对存在意义的发问。
这不仅是由于从他的哲学开拓力出发,只有通过这种确定的情绪,才可以在哲学上有根有据地勾划生存此在﹔而且主要与作者本人有关、和他的实际情绪、他对某种情绪的偏爱有关。
现在来谈畏惧(Angst)。
畏是处在情绪的阴影中的女王。
首先必须把它同害怕区别开。
害怕总是针对某种具体东西的,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
畏惧则不同,它针对的是不确定的无边无际的东西,如世界一样。
畏惧所面对的是作为世界的世界。
在这种畏惧面前,所有的一切都赤裸裸地降到地上,暴露了它们的意谓。
畏惧是最高统治者,它能够无缘无故地就在我们内部发挥强力的作用。
它真正的对手不过是虚无而已,所以它无需甚么诱因便发挥作用。
谁要是畏惧,世界对他「便无所提供,与其共在的他人亦是如此。
」畏惧不容忍其它神灵在它身旁存在。
它的具体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它撕裂了同邻人的纽带及使个人从同世界的信赖关联中脱落出来。
它用世界的赤裸裸的Dass(那具体内容)和本己本真的自己同此在相对质。
问题是,当此在经过冷酷的畏惧之火的焚烧之后,并不是一无所获。
被畏惧从它身上烧掉的东西,在此在的红炭火中显示出来:
「向自身的自我选择和自我把握的自由开放(Freisein)。
」
在畏惧中,此在经历了世界的阴森可怕(Unheimlichkeit)和本己本真的自由。
所以畏惧可以同时是对两者的畏惧:
对世界的畏惧和对自由的畏惧。
上述这种分析是受到基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启发。
在基尔凯郭尔那里,面对自由的畏惧就是面对自己的过犯的畏惧。
他企图通过向信仰的跳跃,越过这个深涧,来克服这种畏惧。
但是海德格尔的畏惧不是为跳跃而做的准备工作。
他已经失去他出身的信仰。
在海德格尔这里是跳跃之后的畏惧,即还在不断下落过程中的畏惧。
当然海德格尔的畏惧哲学的来源,是二十年代到处流行的危机情绪。
文化中的没情绪--弗洛伊德[Freud]曾在一九二九年以此为题发表过论文--到处蔓延。
...
《存在与时间》也是这股危机情绪中的一员。
但是它以自己的独特的样式而与众不同。
这里没有提供治疗的良方。
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发表的论文《文化中的没情绪》[DasUnbehageninderKultur]在开场白中说:
「于是,我失去了在我的共在同人面前妄称先知的勇气,我躬身接受他们的谴责,我竟没有为他们提供安慰。
从根本上讲,他们都有这个要求。
」1弗洛伊德的话也适用于海德格尔的工作。
他的思想也来自对「没情绪」的经验,但拒绝扮演先知的角色,拒绝为他人「提供安慰」。
当然,海德格尔关于存在意义的强调性发问恰恰可以唤起那种对安慰的期望。
它也的确唤起了不少人的期望,只是这种希望并没有得到满足。
这种希望必然落空恰恰是《存在与时间》带给人们的消息:
☻背后一无所有﹔
☻存在的意义就是时间﹔
☻而时间并不是充满赠品的仙岛,它不向我们提供任何东西,也不给我们指引方向。
☻意义就是时间,但是时间没「给予」任何意义。
作为海藻殖民地的此在
在海德格尔此在分析中,畏惧是转折点:
它从「一直紧紧生活于其中」的关系网上堕落下来。
在分析畏惧以之前的诸章节中,分析的主题是此在早已完全习惯的那个世界。
这种分析表明,因为畏惧让世界背离常规,而且仅就他是一种造成同世界的距离的现象而言,对畏惧的描述是较为容易的。
相反,具体地紧紧生活「在-世界-中-存在」之中的日常生活,因为它与世界毫无距离,所以想要对它加以描述就相当困难。
如果真想澄清它的话,就不允许你处于外在的旁观者的立场,你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这种无距离的此在运动之中去。
这恰恰是现象学的基本原则。
你不应该「对」该现象进行谈论,而是必须选择一种立场使得你可以经历到现象的自身显现。
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考察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它们均有过犯。
它们不是描述意识怎样从世界中产生(自然主义),就是描述世界如何由意识来构成的(唯心主义)。
海德格尔寻求的是第三条道路。
他的原初的,而且也是不得不采取的立场是,必须从「在-存在-中」[In-Sein]开始。
因为,
☻在「现象上」我既不是先经验我自己,然后再经验世界,也不是相反地先经验到世界,再经验到我自己。
在经验中,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同时给出的。
在现象学中这种经验被称为「意向性」[Intentionalitaet],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现象学的最重要的观点。
海德格尔不像胡塞尔那样将此理解为意识的结构,而是把这种经验把握为此在的世界联系。
在海德格尔对「在-存在-中」的分析中,术语与术语之间,丝丝入扣,关系异乎寻常的紧密。
因为任何一个概念性表达句都必须避免重新落入近在咫尺的主体-客体分裂的老套,避免在主体(内在)的立场和客体(外在的)立场之间进行抉择。
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由连字符构成的妖物。
它们应该指称那种不可分割破坏的结构联系。
我们举几个例子:
☻「在-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意思是:
此在不可能从世界中走出来同世界面面相对,它总是已经处于这个世界之中的。
☻「与-他人-一起-存在」[Mit-sein-mit-anderen]的意思是:
此在总是已经和他人一起处于一个共同的处境之中。
☻「自己-在到-前面去」[Sich-vorweg-sein]的意思是,此在并非偶或从现在这一点出发去瞭望一下将来,而是在操心过程中不间断地盯着未来。
连续状态
这些表达方式显示了整个工作的进退维谷的特性。
分析本身就意味着将其分解支离。
但是海德格尔企图把分析的效果(即分解离析为部分和原素),重新加以消除。
海德格尔把握此在就象人们去把握海藻团一样:
不管你抓到它的甚么部位,你都必须把它整体拖出来。
把握某种个体,为的是同时把与此相关的整体连带着加以称谓。
这种努力使海德格尔陷入一种「滑稽戏」中对自己的模仿性讽刺。
比如把操心[Sorge]规定为:
「作为存在-于-在世界内-相遇的-实存-之旁的自身-已经-预先-在到-(某个世界)之中的自身-已经-在到-前面去。
」[Sich-vor-weg-schon-seinin(einerWelt)alsSein-bei(innerweltlichbegegnendemSeienden)](《存在与时间》德文版三二七页)
语言的这种复杂性应该正好与日常生活的此在的综合性相适应。
在一九二五年夏季的讲课稿《时间概念史导论》[ProlegomenazurGeschichtedesZeitbegriffs]中海德格尔说:
「我们这里不得不引入一些离奇的也许并不美观的表达方式,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出于我杜撰个人术语的怪僻或者特殊偏好,而是出于现象本身的强求...当这类表达方式频频出现时,希望大家不要反感。
」(《海德格尔全集》第二十卷,二○四页)海德格尔这类独特术语--与布莱希特的手法相对应--实际上是一种异化技术。
因为这里待研究的东西「并不是陌生的、根本不认识的东西;相反,它是与我们最切近的,因此使它们看走了眼的东西」。
(同上,二十卷二○五页)特别是当所涉及的语言具有计算性的时候更是如此。
这种语言讲述着某种显而易见的自明之事,它使哲学家对此也这样把握。
这样,在对日常生活的侦察中,语言表明,自己需要哲学家的心血。
但一般的情况下,它们却被置之不顾。
「实存的切近和熟知就是存在论上的遥远、无知...和被忽视。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四三页)。
对此在的分析,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生存论分析」[Existenzialanalyse],而此在的基本规定叫做「生存性概念」[Existnezialien]。
这个概念引起过许多误解。
它实际上构成了传统的范畴概念[BegriffderKategorie]的对应。
在一般情况下传统哲学将其研究对象的规定称之为范畴,比如空间、时间、广延等等。
但由于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不是手头现存的所谓「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