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docx
《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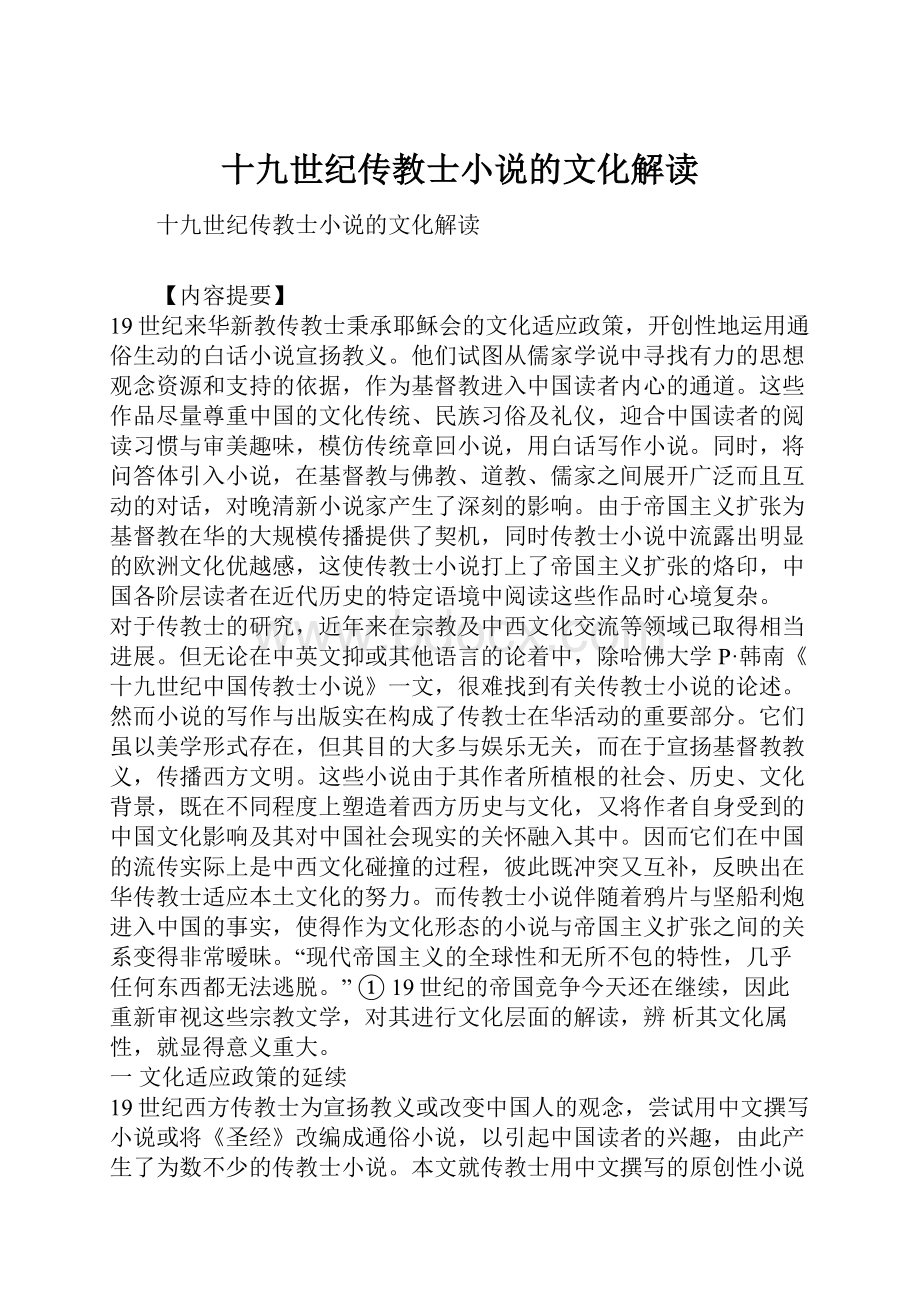
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
十九世纪传教士小说的文化解读
【内容提要】
19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秉承耶稣会的文化适应政策,开创性地运用通俗生动的白话小说宣扬教义。
他们试图从儒家学说中寻找有力的思想观念资源和支持的依据,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读者内心的通道。
这些作品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模仿传统章回小说,用白话写作小说。
同时,将问答体引入小说,在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儒家之间展开广泛而且互动的对话,对晚清新小说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扩张为基督教在华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契机,同时传教士小说中流露出明显的欧洲文化优越感,这使传教士小说打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烙印,中国各阶层读者在近代历史的特定语境中阅读这些作品时心境复杂。
对于传教士的研究,近年来在宗教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已取得相当进展。
但无论在中英文抑或其他语言的论着中,除哈佛大学P·韩南《十九世纪中国传教士小说》一文,很难找到有关传教士小说的论述。
然而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实在构成了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重要部分。
它们虽以美学形式存在,但其目的大多与娱乐无关,而在于宣扬基督教教义,传播西方文明。
这些小说由于其作者所植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既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西方历史与文化,又将作者自身受到的中国文化影响及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怀融入其中。
因而它们在中国的流传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碰撞的过程,彼此既冲突又互补,反映出在华传教士适应本土文化的努力。
而传教士小说伴随着鸦片与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事实,使得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与帝国主义扩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暧昧。
“现代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和无所不包的特性,几乎任何东西都无法逃脱。
”①19世纪的帝国竞争今天还在继续,因此重新审视这些宗教文学,对其进行文化层面的解读,辨析其文化属性,就显得意义重大。
一文化适应政策的延续
19世纪西方传教士为宣扬教义或改变中国人的观念,尝试用中文撰写小说或将《圣经》改编成通俗小说,以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由此产生了为数不少的传教士小说。
本文就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原创性小说展开讨论,它们主要出自基督教新教教士之手。
尽管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教事业远远晚于天主教,要迟至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之后才得以成功开创。
但当其与中国文化在不同层面相遇时,仍然无法避免耶稣会士曾经历过的困境,即如果不在礼仪问题上妥协,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就会导致“士大夫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或基督徒不可能进入士林,这就破坏了耶稣会士和平进入中国的基础——同情关系。
禁止祭祖礼仪则使中国人断定教会敌视中国社会,于是基督教仍然是中国社会文化机体上的一个外来体。
”②特别是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当在华耶稣会士之间及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发生中国礼仪之争,最终由康熙在1717年谕礼部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后,传教事业更加举步维艰。
在这种情形下,新教教士秉承为耶稣会弃之不用的文化适应政策实在是明智之举,并很快在传教事业上超过了耶稣会。
一个有趣的例证是,光绪皇帝延请的帝师并非清廷一贯聘用的耶稣会士,而选择了在学问与资历上稍逊一筹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
运用通俗生动的白话小说宣扬教义,正是这一背景下新教教士们独创的传教方式。
从1819年第一部传教士小说——伦敦差会米怜所着的《张远两友相论》到1882年杨格非《引家当道》,短短数十年间,传教士们对于小说创作可谓乐此不疲③。
耶稣会富有创造力的文化交流与创新随着那场着名的“中国礼仪之争”嘎然而止,而新教教士们却将这场交流与争论继续了下去,并充分反映在其小说创作中。
首先,传教士试图从被最大多数中国人认同的儒家学说中寻找有力的思想观念资源和支持的依据,作为基督教进入中国读者内心的通道。
因此,传教士小说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释耶,而且常常采取简单而醒目的方式,即将儒家论点直接与《圣经》教义并列,表明二者持论相同。
如《诲谟训道》第一回写基督徒陈委用《论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劝喻贪财而吝啬的商人勤跨:
他[指陈委]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犹弃敝矣。
若留心于富贵,如春梦浮云。
况生不携一缕,死不能带半缕,就有财也,化阵清风而去矣。
”耶稣曰:
“谨慎勿贪财,盖本业盛余者,非真生命也。
遂以比喻言。
”④
《赎罪之道传》第一回,吴御史与林翰林首先探讨了《书经》所说的世界本源:
小弟读《书经》曰:
“天地万物之父母。
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亦《易》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
是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万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有四端之灵,备万善知觉,独异于物。
”小弟再三看不尽其义,“天地万物之父母”何谓哉?
⑤二人讨论不出结果,不得不向学识渊博的陈老爷请教。
陈公是基督徒,于是对儒家的这一观点做了一番基督教的阐释,结论是上帝是万物的主宰:
陈公道:
“天地无君,犹身无首,则身不立;无长则家不齐;无君则国不治;无源则川不流;无根则木不登;无帝则天地万物不生。
今有主焉,天地于是乎成,而万物化醇,于是乎行矣。
惟一大主,为群生本源,无形而形形;无象而象象;非天而天天;非地而地地;无始无终,全知全能,全智全善全义。
此之谓天地万物之元也。
”⑥
他又进一步将这一观点与忠孝观念结合起来,把中国人对养育之恩、对天地君亲师的恭敬和爱戴引申为对万物之主宰——上帝的信仰:
陈公喟然叹曰:
“甚哉谬矣!
孝者天之经,地之义,百行之源,众善之宗,仁义之实,人之行也。
孝父母,爱子之心,及恭敬天地万物之元者,乃众人之心,庶民之所当为也。
饿而不能自哺,寒而不能自衣,以养以教不止。
疾痛则寝食俱废,惟上帝万物之主宰之慈爱,太过之也。
生我养我,无旦不保,无夜不佑。
自生之日至于死后,莫不泽恩及我也。
天以覆之,地以载之,而万物之主宰,生育超乎天地矣。
君以治之,而万物之主宰,临更切乎君矣。
亲以怀之,而万物之主宰,爱厚乎亲矣。
师以诲之,而万物之主宰,训笃于师矣。
是故导之者,不止于君焉;服之者,不止于师焉;感之者,不止于恩焉;望之者,不止于福焉。
钦崇万物之主宰,信焉,爱焉,望焉,且尊之与万物之上,此之谓也。
”⑦
作者常常不顾及小说这一文体本身的特征,在书中连篇累牍地引用、解读儒家经典。
这些引文的出处很可能是传教士在学习中文过程中使用的经学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尤以《论语》、《孟子》居多。
目的性很强,即寻找基督教与儒家之间的联系,附儒合儒,至少使二者相互接近的思想观点与经验可以并存。
由于儒家与基督教共同关心的都是人的道德发展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同时在神学与宇宙论的范畴上有许多并行不悖之处,为传教士以儒家学说附会基督教教义,以儒家的仁、道、德等概念来解释基督教伦理提供了可能。
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和阐释,是带着先验的目的与假设的。
这些阐释或许合乎逻辑和字面意思,却只是西方式的解释,服从传教利益的解释,是对本义未能完全参透或有意稍加歪曲的解释⑧。
文化适应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新教教士尽量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及礼仪。
即便是不肯循规蹈矩的郭实腊,在他的小说中,也竭力迁就中国读者的习惯,依据中国历史编年叙述西方历史事件,便于其理解。
他在《圣书注疏》中明确地表明了这种意图,并以此证明《圣经》内容的历史真实性:
[泰成]对福有道:
“尔通得圣书之史,而知本国的史乎?
只恐对人说,终未容易。
”福有道:
“小弟自愧菲才,才薄智浅,然颇读史,殚心竭力说一遍。
至于尧帝前,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与圣书之史合,毫无异矣。
尧纪儿童歌曰:
‘立我蒸民,莫匪尔极。
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有老人击壤而歌于路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
’舜继禹接,国民大兴。
亚伯拉罕于夏帝扃年间旺盛焉,约色弗为宰相,积五谷,保国民之命。
于商成汤年纪,当是之时,中国凶年饥岁,大旱七年。
汤以身祷于桑林,祝曰:
‘无以子一人之不敏伤民之命!
’以六事自责曰:
‘政不节欤?
民失职欤?
宫室崇欤?
女谒盛欤?
苞苴行欤?
谗夫人昌欤?
’言未已大雨方数十里。
且摩西商祖辛沃甲年间兴焉。
据说来约书亚于商南康之纪崩也。
由此观之,圣书之史确实有凭据,毫无疑矣。
”⑨又如《赎罪之道传》第九回中写道:
忽然罗马民服普天下,犹太人进贡,罗马总督操权。
西汉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有犹太祭司飒加利亚夙夜只畏上帝,凛遵上帝之律例,妻石胎,年迈未生子也。
忽一日,飒加利亚仍久在上帝殿焚香献祭,率然天使显焉。
⑩
焚香献祭以示敬意,原是中国的社会习俗,此处居然被基督教徒用于向上帝的祈祷仪式中。
而将教堂称为“上帝殿”的不伦不类的称呼,正显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而且该书中的主人公往往身兼教徒与儒生的双重角色,对科举考试的描写也是正面的:
“却说苏连幸,固依靠上帝之宠佑,不徒费精神。
捱过残冬,到了新年,转眼乃春闱。
仍旧入场,真是文齐福齐,又高中了第十六名进士。
及至殿试,又是四甲第三。
选了官职,广东推官。
”11实际的情形与此相同,很多教会学校一面开设宗教与西学课,一面授国学,鼓励学生遵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参加科举考试。
直到19世纪末,科举的弊端日益显现才受到教会抵制。
此外,文化适应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传教士在翻译宗教术语时,往往从儒家典籍中寻找对应的词语。
如《张远两友相论》中,将“上帝”译为“真神”、“神天”、“神”、“主”、“神主”、“天地之大主”,“圣灵”译为“圣神风”,《新约全书》译为《新遗诏书》等。
《赎罪之道传》“上帝”作“皇上帝”、“圣神”,“圣父”作“大父”、“神父”,“圣子”作“神子”等。
事实上,上帝、皇上帝、神天、神主、神风、圣父、神父、神子这些概念全部源于儒家经典,有关创造并维护万物的造物主思想在儒家典籍中随处可见。
《书经》及其他儒家典籍差不多每页都在昭示上帝的性格与属性:
是万物之本,力量无边,纯洁、神圣与公正,严惩罪恶,哪怕是身居皇位之人;善良、仁慈并充满同情,公共灾难和四季失序仅是善意的忠告,用以暗示他们悔过与改正12。
但小说中术语的使用显然相当混乱,它们未经统一与小心界定,很容易令一般的晚清读者产生困惑。
儒家典籍中既大量使用“上帝”,同时道教神灵世界中许多高等级的神祉也称为“上帝”13。
19世纪末,多产的传教士学者花之安在上海着名传教士出版社广学会发表文章,对运用不同中文词语指涉“GOD”这一基本问题,认为要谨慎,并最终确立借用儒家术语“上帝”指涉“GOD”,但他仍然担心这会令中国读者感到迷惑:
我侪所称上帝,与道家之称上帝不同,与儒家之称皇祖父为上帝亦异,中文上帝二字,无一定称谓,我侪专指大主宰而言,故圣经不泛称天而必称天父,所以示区别焉。
14
此后术语的混乱状况有所改观。
如《张远两友相论》第三回写“真神止一,但在其体有三位,曰父曰子曰圣神风。
此三位非三个神,乃止一全能神。
”这段话到1906年上海美华书馆排印本中就改为近代标准的译法:
“上帝止是一个,但一体之中,分为三位,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这三位并不是三位上帝,止是一个上帝。
”然而传教士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已经过去。
二章回小说中的问答体与中西文化的对话
与文化适应政策相应,传教士小说尽力迎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特征,模仿传统章回小说,用白话写作小说。
首先,学习添加回目,熟练地使用说书人的套语,如“且说”、“却说”、“话说”、“不知林翰林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
其次,注意骈散结合的特点。
如《正邪比较》每一回结束都有回末诗。
《赎罪之道传》第十一回《论约翰铎德》,将大量的赞美诗改编成中国的长篇歌行。
《大英国统志》卷三则用一首长诗描绘英国的风土人情,抒发胸臆。
第三,使用楔子。
如《大英国统志》共五卷,卷一即相当于楔子,没有标题,叙述了主人公叶椟花与林德豪的身世经历,二人如何去伦敦谋生,又如何荣归故里。
由此引出本书的正题:
与乡亲聚谈,分几方面介绍英国的情况。
卷二“文武民人”,卷三“民之规矩风俗经营”,卷四“城邑乡殿庙房屋”,卷五“大英藩属国”。
此外,传教士作者甚至仿照章回小说的评点间或采用眉批出注,为读者提供阅读线索获取更多信息。
如《张远两友相论》第五回,张谈到阅读《圣经》中耶稣降世以救罪人的感受时,有眉批“见弟摩氏第一书第一章十五节”15。
运用生动通俗的小说宣扬教义并非始于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开创之功只是在于模仿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
由于小说容量较大,篇幅可长可短,便于充分、灵活地解析教义。
同时因其叙事性和语言特色,更易于也更乐于为普通读者所接受,对传播福音颇为奏效,所以广为传教士采用。
但作者的命意显然在于宣教,是以个人叙事来传授教义。
这种创作意图与小说文体结合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就是采用问答体,“假设问答以着书”16。
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着作的特点之一就是运用问答体,这一体例在中国也古已有之。
“问答”又称“答问”、“对问”、“问对”、“设论”,其代表作如桓宽《盐铁论》、东方朔《答客难》、班固《答宾戏》等。
早期耶稣会士利玛窦和艾儒略也使用过问答体17。
米怜将问答体引入章回小说,并被其他传教士效仿。
除了《引家当道》等极少数作品,传教士小说大多运用了问答体,由懵懂无知的非教徒发问,而睿智正义的教徒的回答往往是长篇演讲与辩论。
涉及的问题则非常广泛,围绕教义与宗教史展开,如《张远两友相论》中张与远二人就基督徒的行为特征与准则、原罪与忏悔、耶稣的品质与忠贞、灵魂永生与死后入天堂或地狱、复活之身与现在之身的不同、有罪之人是否能得到上帝的赦免展开了一系列问答,逐步揭示教义内容。
《赎罪之道传》共十八回,两卷,每回的回目即其中心论题。
卷一分八个主题讨论:
第一回论贤士教人遵万物之主宰;第二回看山玩水赞美上帝;第三回论人之善与人之恶明白;第四回论老年人听赎罪之道;第五回论善人之死;第六回论祭祀之大义;第七回论赎罪之道安慰心;第八回论人尽心竭力得意。
卷二分十回讨论《圣经》中的历史内容。
小说人物在问答之间实际上显示了基督教与佛教、道教、儒家之间广泛而且互动的对话,是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锋。
作者非常注意强调基督教的不同之处,如《赎罪之道传》将儒、释、道的人生态度与基督徒相比较:
吴公道:
“老先生说来最有理,进教解闷舒怀。
但愚见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在海东’,惟有孔孟崇现事,眼前无日不春风。
莫若今日饮酒食肉,明日诸事罢了。
”且说林公听此言,甚怒道:
“吉凶祸福由于天,非人所能主也。
但放肆淫邪,招皇上帝之怒。
轻圣教,纵邪欲,莫不惹万祸。
上帝鉴万人,连心之私思可知也。
相公若弃其实且随影,一定遭难无尽矣。
”18
与儒家学说相比,佛教和道教具有宗教突出的神圣性与排它性,与基督教存在更为明显的冲突。
故传教士小说在主张基督教的理性一神论方面态度十分坚决,对佛教与道教中广泛流传的多神论、偶像崇拜等传统不断提出挑战,同时触及了深入人心的佛教轮回转世的观念、道教所追求的长生不死与基督教的复活思想之间的比较,民间流行的道教偶像崇拜则被视为低劣的迷信行为受到批驳。
《张远两友相论》第一回比较信耶稣与其他偶像崇拜的不同,强调真神只有一个耶稣:
远曰:
“我看世人多亦敬神,则何说信者比世人不同呢?
”张对曰:
“世人所敬的各神类,不过系自己手所作、无用无能的偶像而已,这是假神,不是真神。
又这假神系无数的,惟其真神止一,可见信者比世人不同。
”19小说第六回,由远追悼哀思父亲引出了佛教轮回观念与基督教复活思想的讨论,批评前者荒谬:
远想久而曰:
“……前四年,父亲眼看我,耳听我,口教我,手助我。
而今其眼安在,却独留虚眶;其耳已坏,只留耳孔;其口舌唇皆成泥土,只留牙骨,起手足筋络已无,只留骨节而已。
……夜梦见父亲转出世,变山羊形,食草在山野。
从那时以来,我心不安乐,常想着轮回。
今尊驾讲死者复活,我甚愿听。
”张曰:
“死人转出世成禽兽之形,皆虚话哄骗愚人。
相公不可信之。
今所言复活大不同。
”远问曰:
“死者复活过若何?
”张答曰:
“你看这苍天、明月、光星,今晚虽美之至,而无可比,然后来皆必致尽而完。
于彼时万死者将复活。
其葬在地冢与其没在海内者皆然。
自天地开辟,至天地穷尽,所有万万人,大小贵贱贤愚,无一不复活,而各人得其本身。
”20
《庙祝问答》中代表佛教立场的庙祝与基督教代表人物传道者之间也展开了跨越宗教的对话。
如二人就点烛烧香拜菩萨的佛教仪式展开争论:
传道者就庙祝而问曰:
“点烛烧香是何意耶?
”答曰:
“是表诚敬之心而已。
”曰:
“诚敬枯木何益乎?
”曰:
“非敬此木所雕之像,乃敬此像所附之神。
凡拜之者,蒙其佑也。
”曰:
“果有神附此像乎?
”庙祝曰:
“然。
”曰:
“既有神附此像,何以鼯鼠穿之,蝼蚁蛀之,而不能自保。
菩萨自身难保,安能保万民耶?
以生活之身躯,崇拜可坏之土木,比拜龟蛇者更愚焉。
”21
但这显然是一种力量失衡的交锋,双方的话语权并不平等。
庙祝与传道者的争论总是以失败告终,恼怒不已:
“速去速去,勿在此忤触神明!
”“问者必浅,而答者必深;问者有非,而答者必是”22几乎已成了一种定式。
发问的非教徒懵懂无知,处于劣势,提出的问题肤浅幼稚;而作答的基督徒则睿智正义,博学善辩,大多以将对方说服入教结束。
人物刻画上也出现定型化的通病,其原因并非由于写作技巧,而在于作者总是赋予基督徒以强势话语权。
小说文体的特性也由此大为削弱,对话的目的不是为刻画人物,而在于宣扬教义。
长篇大论解构了小说的故事性与娱乐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传教士小说在体例上其实相当驳杂,它们远远不是来自单一的、统一的、自成一体的章回小说传统,它们实际上包含的“异物”及与章回小说的差距比传教士们力图克服的要多。
《大英国统志》中甚至连篇累牍地开列英国对外贸易的清单,介绍其殖民地,使其小说特性大打折扣。
只有少数作品如《悔罪之大略》、《诲谟训道》、《小信小福》,更多地顾及到小说的文体特征,使议论与故事情节叙述更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更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立体感,表现其变化的轨迹与内心的矛盾。
传教士的问答体小说对晚清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刘鹗《老残游记》、吴趼人《上海游骖录》、钱锡宝《杌萃编》、彭俞《闺中剑》、壮者《扫迷帚》等小说中都可以看到问答体的特点。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将此归因于传统文体对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影响23。
但联系西风正炽的晚清社会状况与许多新小说家深受西学影响的个人经验,特别是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者与代表作家梁启超甚至有为李提摩太担任秘书的经历,本文更倾向于将新小说家们热衷于问答体的运用视为是受到传教士小说影响的结果。
三传教士小说的文化属性及其在近代历史语境中的阅读
毋庸置疑,对传教士小说进行美学与叙事学层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但由于小说的世俗性,它与所包含的真实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探究传教士小说在历史叙事与文化版图中的位置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
它的位置似乎是游移不定的,既可以归入19世纪帝国主义开拓殖民地的大背景下,又有着宗教的超乎时代、地域与民族的特性,既有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关切及对中国信众的真诚呼唤,又传达出对基督教在中国遭遇敌意的不满。
然而,尽管传教士趋附中国本土文化的努力显而易见,但对其小说的文化属性做出判断并不困难:
传教士小说是与19世纪帝国主义的扩张紧密相连的。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鸦片战争强行打开禁教,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更大规模的传播提供了便利,这使得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难脱干系。
1842年以前,基督教传教士不能以传教名义进入中国内地,1842年《南京条约》后,特别是1843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传教的权利,传教活动从地下转入公开。
1860年英、法、美、俄强迫中国政府批准和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几乎全部开放了西方传教士的宗教特权24。
尽管传教士也谴责鸦片,如小说《诲谟训道》通过苏州商人勤跨两个不成器的儿子万行、门咨因吸食鸦片家破人亡,下场悲惨,揭示了鸦片的危害。
1895年傅兰雅的小说征文,将鸦片作为中国社会一大流弊,予以抨击。
但是其中的“戏剧性和悲剧性成分,是传教士的同胞们把它带进来而用枪逼我们接受”25,传教士小说普遍印证了它与帝国主义之间无法隔绝的联系。
原创性传教士小说的高峰期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
它们的作者此时对中国的看法和立场已发生转变。
大约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利玛窦时代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理想主义的报道被遗忘,莱布尼兹、伏尔泰式的对中国宽容、羡慕、崇敬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替代。
19世纪,随着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工业革命的拓展,欧洲人的“自大感”发展到极端。
德国历史学家郎克认为中国是静止的,对英国以强权打开中国报以喝彩:
“英国人用他们的商业统治整个世界,他们曾为欧洲打开东印度,打开中国,使所有这些帝国同时屈服于欧洲的精神。
”26而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则变得怪诞愚昧,滑稽可笑,溺婴、狎妓、吸鸦片、赌博、贪污等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被放大27。
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郭实腊。
这位能言善辩的教会代言人出生于普鲁士,受荷兰教会资助来华,但他极力推崇的却是19世纪处于强势的英国文化。
他在1830—1833年间曾三次搭乘鸦片商船沿中国海旅行,强行进入中国内地,这种举动本身就带有帝国主义扩张的性质。
郭实腊从1835年开始为英国政府服务,并在《南京条约》谈判中担任英方翻译,1843年以后担任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
所以他的小说大多将英国作为理想的国度,代表着先进与文明。
中国虽因情节需要和阅读对象的缘故也在书中得到描写,但没有正面的、全局性的评价与描述,而主要在叙事学层面上起作用,作为叙事场景存在,以博取读者的亲切感。
他的历史小说《大英国统志》叙述了儒士叶椟花随朋友林德豪搭船去英国,旅居异国二十余年回到家乡,向家乡人介绍英国的宗教、政治、军事、教育、贸易、外交等。
作品传达了一种不满情绪。
这位朝圣者与布道者在中国处处遭逢着急剧的失落感,他对所来到的这个地方没有政治上的控制权,没有自由贸易的权力,没有布道的机会,甚至被视为蛮夷得不到尊重极为不满。
《诚崇拜类函》发表于1834年初,由福州某户人家的长子在英国旅行期间写给家人的一系列书信组成。
小说《是非略论》发表于1835年。
此书模仿米怜的小说,由一系列的对谈构成。
一个来自广州的名叫陈择善的人,自幼就是孤儿,后设法去伦敦,在那里开了店,生意兴隆。
二十五年后他回到家乡,与一个姓李的仇视外国人并充满偏见的朋友展开了一连串辩论。
题目中的“是非”不是指向道德命题,而是指海外对华关系的事实真相,尤其是中英关系。
这部小说简直就是中国应加入互惠贸易关系的长篇咨文。
书中宣称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既不是“红毛番鬼”也不是“夷人”,而是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文化。
作者提供的证据之一是——大英帝国每年出版不少于一万册图书。
根据文化或军事实力,英国不应被作为进贡国来对待。
书中咏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在使读者认识到外商的合理性,他们的富有和实力,好的政府以及外国的先进与文明。
该书最后一章谈到了英国的基督教、教育、语言与撰文、婚姻习俗并且强调了英国妇女的地位28。
这种英国文化优越论乃至欧洲文化优越论,使布道之举和意在宣扬教义的传教士小说都打上了帝国主义扩张的烙印,在近代历史的特定语境中,遭遇了来自中国各阶层的种种复杂态度。
总体上,传教士小说在晚清的阅读和接受大体可分上层文士与下层民众两个层面考察。
与晚明不同,晚清的士大夫很少有人与传教士建立良好的私交,对传教士小说也基本持抵触、排斥的态度。
一方面,随着帝国主义的扩张,民族情绪日益高涨。
国仇家恨都使稍有良知的文人难以再接近教会。
署名“天下第一伤心人撰”的《辟邪纪实》,卷中收录《阅〈甲乙二友论述〉》,指斥这部小说荒谬不经,将矛头直指基督教:
第四章内谓耶稣降世,特救罪人。
试问耶稣既特救罪人,然则从彼教者不必须罪人耶?
第五章内,谓人死复生之身,不病不老不死不坏,且谓恶者之身,精力必强。
盖上帝将坚其体以膺多难。
试问人既不病不老不死不坏,且精力必强,更何为难耶?
29
这种驳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义理的辩驳,而更多的是在宣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在当时文人中较为普遍。
另一方面,作品内容多为宣教,异乎当时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关怀,即富国强兵,为国家发展寻找理想的出路。
所以与西学书籍大行其道相反,传教士小说备受冷落。
而李提摩太的翻译小说《回头看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