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docx
《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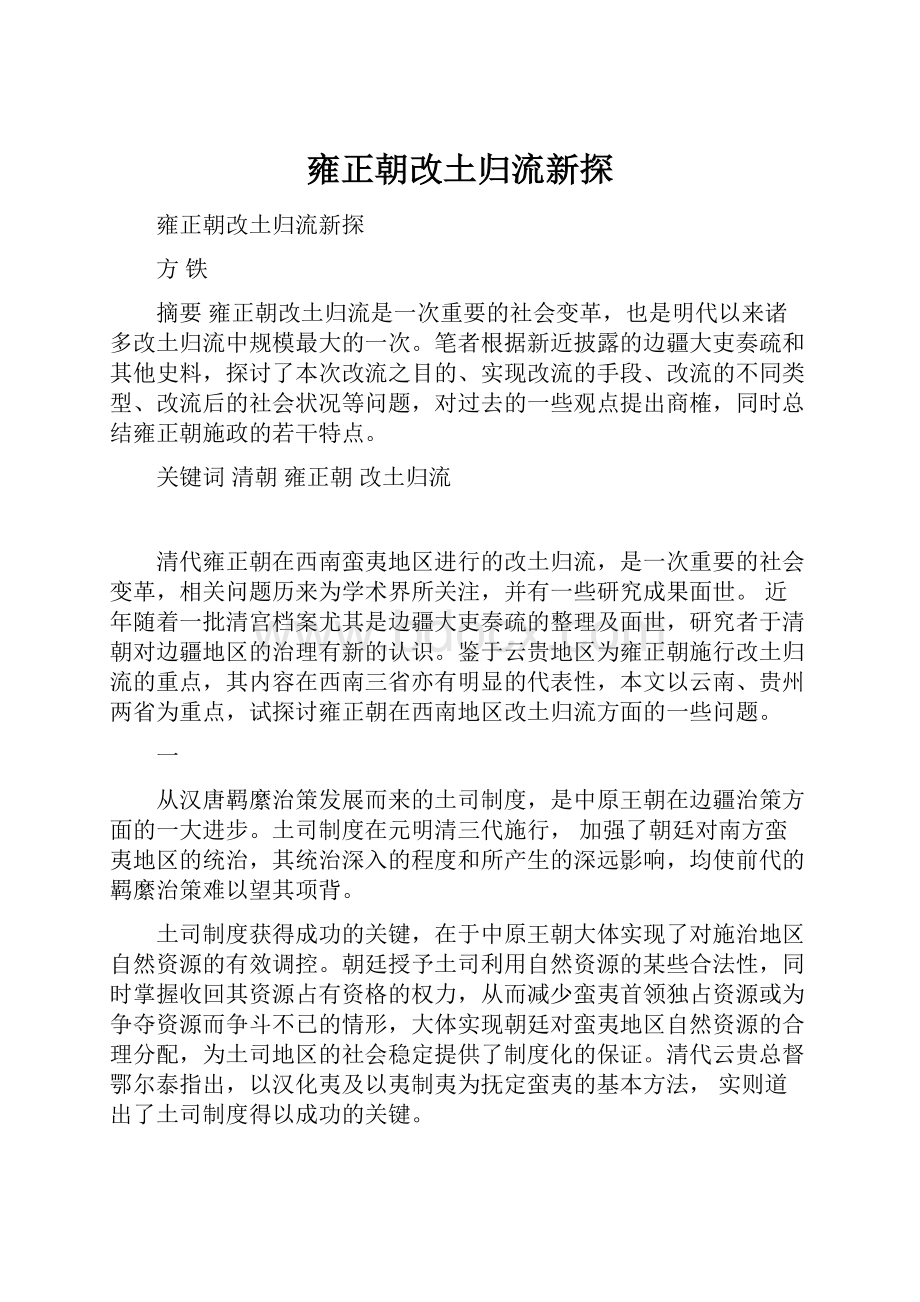
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
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
方铁
摘要雍正朝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笔者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了本次改流之目的、实现改流的手段、改流的不同类型、改流后的社会状况等问题,对过去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同时总结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关键词清朝雍正朝改土归流
清代雍正朝在西南蛮夷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相关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
近年随着一批清宫档案尤其是边疆大吏奏疏的整理及面世,研究者于清朝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有新的认识。
鉴于云贵地区为雍正朝施行改土归流的重点,其内容在西南三省亦有明显的代表性,本文以云南、贵州两省为重点,试探讨雍正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方面的一些问题。
一
从汉唐羁縻治策发展而来的土司制度,是中原王朝在边疆治策方面的一大进步。
土司制度在元明清三代施行,加强了朝廷对南方蛮夷地区的统治,其统治深入的程度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均使前代的羁縻治策难以望其项背。
土司制度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原王朝大体实现了对施治地区自然资源的有效调控。
朝廷授予土司利用自然资源的某些合法性,同时掌握收回其资源占有资格的权力,从而减少蛮夷首领独占资源或为争夺资源而争斗不已的情形,大体实现朝廷对蛮夷地区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为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提供了制度化的保证。
清代云贵总督鄂尔泰指出,以汉化夷及以夷制夷为抚定蛮夷的基本方法,实则道出了土司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
土司制度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要是土司获得朝廷的保护,而朝廷对其行为或鞭长莫及;土司亦逐渐掌握与朝廷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以自肥,条件具备时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
朝廷允许土司沿用传统的管理方式,客观上也保护了落后社会及其旧俗,并使土司辖下的夷民难以得到国家法制的保护。
随着边疆地区的进步,土司制度保守、落后的一面逐渐明显,土司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对驿路开通和移民进入等肆行阻挠,也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
清军平定云南后,吴三桂盘踞其地10余年,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全面治理西南边疆。
吴三桂在云南滥封土司,并煽动部分土司参加叛乱,使明末以来云南土司难以管控的局面更趋严重。
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疏,从十个方面提出筹滇的善后事宜。
其内容丰富且切中时弊,康熙帝以所奏各款有合时务,令九卿、詹事、科道议行。
蔡毓荣上疏与土司有关者计三条,一为治土人。
他指出吴三桂叛乱时滥征土兵,狂任伪总兵或副将,伪署之参游都守等遍及诸蛮。
吴乱既平,各地土司虽先后归诚,但“骄纵既久,驯服为难”。
二是收军器。
吴三桂叛乱遍征土兵,发与军器及火器甚多;土兵溃败各自带归,并无一件缴至军前者。
三为弭野盗。
上疏指出反叛、掳掠常为滇患,时以滇南鲁魁山土司的危害最大。
筹滇计者多不主抚而主剿,认为抚仅得一时之安,而剿可一劳永逸。
蔡毓荣认为因形势所限暂不宜剿,数年后再视情形酌取对策。
由此可见云南违法土司之猖獗。
经40余年康熙朝的悉心治理,雍正初云贵地区发生很大变化,原先疮痍满目、百业衰堕的景象明显改变,云贵地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乃成为雍正朝治理追求的目标。
此时土司长期积累的严重问题日渐突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亦已成熟。
雍正帝乃以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主持在三省蛮夷地区进行改土归流。
细阅相关奏疏,其中有改土归流之目的、实现改流的手段、改流的不同类型、改流后的社会状况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关于改土归流之目的。
过去研究者或认为雍正朝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由于改流地区地主经济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上层建筑包括土司制度必相应改变。
从迄今已知的记载来看,上述看法有待商榷。
鄂尔泰分析了前代实行土司制度的原因。
他说土司地区既属边徼,王朝统治未久,亦为蛮烟瘴雾、穷岭绝壑之区,倮俗、苗情实难调习,因此朝廷令土官为之管制,以流官为之弹压,“势不得不然。
”自明初以来数百年来情况发生改变,若仍以夷待夷,无异于“以盗治盗”。
况且土司挟官府之势残虐群苗,“横征苛敛,贡之朝廷者百不一二。
”又烧杀劫掳,骚扰百姓十常八九。
须行改流,“军民相得以安”。
以上所言,道明土司制度已难以适应清初社会变化的事实。
在相关奏疏中,鄂尔泰详细列举违法土司的以下罪状:
肆虐违法、危害百姓,致使夷情无法控制。
云贵土司多年豪强,所属苗众悉听其指使,残暴横肆无所不为。
若土官懦弱,则凶恶把目危害更甚,不但目无府州,心中亦无督抚。
及至事发,上级官府因难以处置多隐忍了事。
贵州土司单弱不能管辖,“故苗患更大。
”仅杀几个祸首,不过是急则治标,本病仍未根除。
一些地区苗倮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
由此得出“滇黔大患,莫甚于苗猓,苗猓大患,实由于土司”的结论。
霸占膏腴土地与矿山等资源,使官府、商贾与百姓无法进入,国家的贡赋难增。
雍正四年(1726)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奏:
四川乌蒙土司纵恣不法,若不惩戒治理,将来益无忌惮。
若进行改土归流,“于地方大有裨益。
”他还说:
四川东川与云南之寻甸、禄劝、沾益三州接壤,“方隅广阔,地土肥饶。
”因“土人凶悍、专事劫掠”,致使川民不肯赴远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
建议将东川划给云南,并将附近营汛移驻其地,以巩固康熙三十一年(1692)献土改流的成果,可使“茂草皆变为膏腴,民受福利,国增钱粮”。
十一月,鄂尔泰在奏疏中进一步指出:
云贵两省荒地甚多,而“荒地多近苗界、虑苗众之抢割”而无法开垦的情形十分普遍;若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将不招而来者自众。
”因此“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制苗为急务”。
次年,鄂尔泰又报告乌蒙土司不务农业的情况,说乌蒙土司所辖之地,仅大关屯等处夷人知耕种,“独土府附近地方从不务农,惟以劫掠为事,”所需盐米皆取资于镇雄、大关屯等处。
鄂尔泰还断言:
“若不尽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擒拿,懦弱昏庸者渐次改置,纵使田赋、兵制尽心料理,大端终无头绪”。
因此,谋划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
他还试采东川汤丹厂之矿,认为“矿苗甚旺,就目前核算,岁课将及万金”。
除汤丹厂以外,东川尚有革树等厂10余处,改土归流后若积极开采,“虽或衰旺不一,皆不无小补”。
滇南之十二版纳、思茅、六大茶山等地,亦有土司、奸商插手或垄断茶叶交易,以至发生“夷民情急操戈”之事。
鄂尔泰建议将思茅、六大茶山及橄榄坝六版纳划归流官管辖,其余江外六版纳仍隶宣慰司;在产茶之地择址设总店主持茶叶交易,令通判管理,不许奸商等外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
”六大茶山每年产茶约六七千驮,客商买茶每驮纳茶税银三钱,对朝廷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至于云南南部之威远、新平、哀牢等处土司,“种类不齐,顽悍则一,”而六大茶山尤系久叛之区,从无数年宁帖。
“目前虽无大害,日久将为隐忧。
”因此鄂尔泰建议尽早改流。
雍正帝亦批:
“此等事推诿不得的,随出随办,一劳永逸之举,不可少惮烦劳也。
”雍正四年(1726),云南镇沅之者乐甸土司因“民夷怨恨”,向清廷投献印信和号纸,“情愿归流”。
六年鄂尔泰上奏,谓云南澜沧江内外之车里、茶山、孟养、老挝、缅甸等处土司,“争相雄长,以强凌弱,”地方官府置之不问,“以致凶夷肆恶,渐及内地。
”建议亦行改流,在江内诸地分设营防,“以图一劳永逸”。
由此可见,雍正朝在云贵等省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部分土司或苗酋纵恣不法、危害社会,以及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驿路开通与外来移民进入等问题,另外,对一些“目前虽无大害,日久将为隐忧”的边疆土司,雍正朝也决定尽早改流,以绝后患。
以上所说雍正朝进行改土归流之目的,与土司地区之地主经济是否发展大体无关。
二
关于雍正朝实现改土归流的手段。
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属草率从事且准备不足,并以对夷民肆意杀戮为施行的主要手段。
就迄今所见的史料观之,以上观点亦失之偏颇。
首先,雍正帝与受重托主持改流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就施行改流必谋划细致、准备充分及务必成功达成共识。
鄂尔回顾为平定麓川土司思任发之乱,明朝三次征讨而终未能定的教训,指出明朝未能筹画万全、设法剿抚,动辄提师数万支饷数省,但敌手旋服旋叛,“究不能为久长计”。
他推崇诸葛亮之“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为至言,谓承平之世用兵,关键在于乘机握要,“即可制胜,并无庸多兵。
”极盛之时尤当思患预防,“则力半功倍,可谋久远。
”其言得雍正帝赞同,并特谕鄂尔泰“一切机宜务出万全、慎密,勿少轻易致生事端”。
清廷慎重对待改土归流,还表现在“得人方可行”的态度方面。
雍正帝强调施行大事,“以用人为要,以得人为难。
”认为尚若如此,“小试之则小效,大试之则大效”。
雍正四年(1726),新任云南总督鄂尔泰上疏建议改土归流,所言详细得体。
雍正帝阅后认定鄂尔泰“必能办寇”,乃下决心改流,随即诏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由四川改隶云南,六年复铸云贵桂三省总督印给鄂尔泰,令其兼治广西。
十二年台拱苗叛,鄂尔泰以此前筹划未周请罪朝廷。
雍正帝追述改流的缘起,谓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提出改流必行并恳切陈奏,“朕以鄂尔泰居心诚直,识见明达,况亲在地方,悉心筹画,必有成算,始允所请,命其慎重办理”。
其朱批还说:
“凡卿所办之事,朕实无一言可论矣。
在廷诸臣皆与观之,人人心悦诚服,贺朕之福庆,国家得人,朕亦惟以手加额,感上苍、圣祖赐朕之贤良辅佐耳。
”雍正在朱批中亦如此敲打鄂尔泰:
阅所上疏“必欲将六茶山千余里地尽行查勘,安设营防”之言,“好趁此一番振作,务为一劳永逸之举。
”“但善后事宜,全在文武员弁委用得人。
若不得其人,宁缓事以待,必预备有人,方可举行。
不然,好事亦被酿成妄举矣。
料卿委用者,不得错误也”。
雍正帝所言“委用得人”,既明谕受命查勘之人,又暗指鄂尔泰不得误事。
鄂尔泰既担重任,亦时有皇帝提醒,必呕心沥血笃行之。
由此看来,雍正间进行的改土归流,大致以谋划细致、准备充分、策略灵活和务期成功为其特色。
其次,雍正帝与鄂尔泰均认为,“欲靖地方须先安苗猓,欲安苗猓须先制土司,欲制土司须先令贫弱。
”即彻底解决违法土司,为治理蛮夷乃至云贵地区的关键。
至于惩办违法土司,亦须讲究策略,雍正帝提出对纵恣不法的乌蒙土司,宜先行详加戒谕,令其毋虐土民,毋扰邻境,使之痛改前非,恪守法度。
若敢怙恶不悛,再经悉心策划以部署改流。
鄂尔泰亦认为乌蒙土司虽一贯凶恶似难感化,但仍可先施之以恩,在其归滇管辖后晓以国法,渐离其心腹,徐减其党羽,待可乘之机再设法招抚。
若效果不佳方可用兵,“然威止可一举”。
进而提出“改归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的改流策略。
雍正帝还以朱批提醒:
改土归流固系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能使夷民有避溺投火之想,方可保永安长治。
如一意以兵威慑,视夷民如禽兽,任意凌虐苛求,难免令其追思故主,所关甚巨。
一般而言,清廷在改流中较注意区分驯良与凶顽。
对东川各寨驯良之苗子与干倮倮,认为“不应惊扰”;黑倮虽然凶顽,但仍与首恶有别。
鄂尔泰提出除酋长、头人务严剿穷搜、或诛灭或遣送外地,其余胁从若来归顺,“概予安插。
”但对改流后屡有反覆如乌蒙土司者,则认为“屠灭有名”,“若复少事姑息,贻害何底?
”而予以残酷镇压,不仅对土司族姓尽行杀戮、逆目恶党予以根除,胁从之人若有证据,“俱未可宽纵。
”或将其家口俱徙北方之宁古塔,或剁去右手、割去脚筋乃复其故居。
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的残酷性。
其三,重视改流以后的善后处理,即鄂尔泰所言之“改土归流实无难事,但善后之图尤不可不慎重”。
对改流土司的善后之法,一是将“汉奸”、犯法之土司或土目依法惩治,将相关土府移置内地,以终其后患。
二是在改流地区部署绿营兵以为弹压。
雍正帝朱批:
“不可惜此小费,当谋一劳永逸,万不可将就从事”,待归化日久再议减撤,“未为不可”。
滇南之车里、普洱等地因邻近缅甸,改流后的部署尤为严密。
清廷将普洱改府,普威营改普镇协移驻普洱,与知府同城。
并分营防相通关哨,“俾左右兼顾,可以举重驭轻。
”思茅一带居民稠密、土地宽阔,为九龙江、橄榄坝与六茶山之咽喉,清廷遂将普洱通判移驻思茅,“以联声势。
”橄榄坝为全郡门户,“最关紧要,”朝廷乃立州治,并设率兵之安都司与知州同城。
因部署变动,清廷减裁元江协仅留把总三员,就近拨入临元镇标。
经过军事上的增设与调整,清廷对车里、普洱等地的控制明显增强,雍正帝朱批:
以上部署“是当之极”。
在实施改流之前,鄂尔泰重视先行调研,以弄清改流地区的基本情况。
在上奏拟解决东川府土司后,他秘密遣人至东川一带细访确勘,了解的内容包括地方疆界、形势险要、山川城池、衙署营汛、兵丁户口、粮饷赋役、蛮夷风俗与矿厂经营等,“俱得悉大概。
”俟奏疏获准,又亲往其地细勘,与部属商议改流的具体步骤,鄂尔泰如此慎重的原因,是“事在初定每易简略,始之不慎终成弊端,不可不熟虑”。
在车里等地部署绿营兵之前,鄂尔泰担心烟瘴所聚难以布兵。
后了解到思茅、六大茶山、橄榄坝、九龙江各处仅有微瘴,“现在汉民商客往来贸易,并不以为害,”方放心于其地设官驻兵。
雍正十二年(1734),贵州之台拱苗改流后复叛,鄂尔泰以此前筹划未周请罪。
雍正帝诏:
“是从前经理之时,本无定见,布置未协所致。
”可见改流时清廷的策略相当灵活并允许随机改变,方有“本无定见,布置未协”之说。
由于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清廷在云贵等地的改土归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东川、乌蒙、镇雄类型。
鄂尔泰认为乌蒙、镇雄等地土司“积恶累世,荼毒边疆”,鄂尔泰在当地改流“原以计取,并未大加惩创”,以后土司又背叛反复,因此“屠灭有名”,“非以兵威不能伏制”,乃兵出多路大开杀戒,令官军“登高涉险,攻关搜箐,凡贼巢无不深入”。
元生、成贞率军自威宁攻乌蒙,连破80余寨,击败其众数万。
提督张耀祖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群苗战栗。
”以后雍正帝奖励鄂尔泰及诸将,以元生、成贞等为首功,又发帑犒劳其师。
可见清军对乌蒙、镇雄等地夷众的残酷镇压,是得到朝廷首肯的。
鄂尔泰解决上述土司的策略,由先前的“先施以恩”、未果方可用兵,骤然改变为大开杀戒,固然缘于相关土司屡降屡叛,但亦有蓄意造成恐怖氛围,逼迫乌蒙、镇雄等地的土司逃离本地的考量。
乌蒙土司禄万钟败逃后,鄂尔泰在奏疏中说:
“臣料两土府智穷势迫,非投川无路,屡经密檄川员,兼致手札,详道情事,并嘱以在滇务应严逼,在川不妨宽收,总期成事。
”可见在滇以严厉镇压相逼,威迫反叛土司北逃入川,“在川不妨宽收”是鄂尔泰内定的策略。
事态发展果如其所料,乌蒙、镇雄等地的反叛土司,率众分别逃入金沙江以北的大凉山南部和乌蒙、镇雄等地的高山瘠地,空出坝子及丘陵地带大面积的肥腴土地,为以后外来移民进入垦荒种植创造了条件。
新辟苗疆类型。
贵州古州一带是雍正朝改土归流的重点之一。
从雍正六年(1728)至十一年,经多次经营,清朝在以古州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先后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都江和台拱六厅,时称“新辟苗疆”。
早在雍正四年呈《改土归流疏》时,鄂尔泰便指出贵州土司与云南不同,凶顽之举大都出自基层的寨主土目,因此改流其地宜“因地制宜,更须别有调度”。
鄂尔泰向贵州镇远知府方显询问拓开苗疆之法,方显称生苗不隶有司,亦无土司管辖。
苗疆为内地入云南、湖南与广西必经之地,但因生苗盘踞萌乱,往来官民皆绕道远行。
生苗又时出界外剽掠,“内地商旅尤以为苦。
”而苗疆泉甘土沃,盛产桐油、白蜡、棉花、毛竹与木材等物。
若改流苗疆使舟楫无阻、财货流通,不仅汉民颂德,苗民亦受其福,“此黔省大利也。
”因此力主改流,并说宜剿抚并施,可先抚后剿,既剿仍归于抚。
方显所言深得鄂尔泰赞同。
鉴于改流的对象主要是寨主与土目,改流之目是惩办劫掳地方的苗霸、夺回被生苗割据的土地及其他资源,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提出在苗疆改流的策略,是先择其最顽、最强者首先擒治,就其素良素弱者明示安抚,如此可“慑其胆而服其心”。
雍正则提醒“今既用兵威抚取,则善后事宜更当谨慎为之。
”并说凡新定之地万不可计较“利”,亦万不可惜之钱粮,“勿因小误大”。
九年,皇帝朱批又说治理苗疆“全在文武官弁抚驭得法,不可丝毫致涉欺凌。
”必实心教化调养,务令苗汉相安,“数年后方可言成效也”。
缘由于此,鄂尔泰认为苗疆的改流应视具体情况斟酌变通,亦应区分缓急,基本原则是“审时度势,顺情得理”。
强调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既不足以服人,亦恐无以善后。
并举例说“欲靖黎平,必以都匀为先声;欲靖镇远,必以黎平为前导”,如此可举重驭轻,“施秉不劳而自靖”。
由于制定“剿抚并施”、各个击破的方略和“审时度势,顺情得理”的原则,清廷在苗疆的改流进行较为顺利,产生的社会震动及破坏也相对较小。
新辟苗疆占地二三千里,“几当贵州全省之半。
”清廷在苗疆各地增营设汛以加强控制。
自清水江、丹江一带改流设营,官府雇苗船100余艘赴湖南购取盐布粮货,通过水路往返,“民夷大忭,估客云集。
”官府又开拓连通都江与清水江的河道,楚粤商船籍此可直抵镇远城外,“古州大定”。
鄂尔泰还注意在苗疆恢复和发展生产。
雍正七年(1729),鄂尔泰奏准在贵州威宁一带开采铜矿,命主办官吏劝本地苗民参与开采,“不必多招闲人,一则使之有利,可以资生;二则各有所事,自必渐为良懦”。
用心可谓良苦。
雍正帝对苗疆的改流亦予肯定。
十年鄂尔泰奉调入京就任保和殿大学士,皇帝颁谕:
古州等处生苗自古未归管辖,鄂尔泰运筹调度、剿抚兼施,使苗人怀德畏威,抒诚内属,致使“疆域开拓、边境辑宁”。
猛缅、者乐甸类型。
云南顺宁府所属猛缅长官司,为澜沧江以北之靠内土司。
因土司为承袭行贿被查实,其又苛虐派扰夷民,猛缅五十村寨夷民数百人赴迤西道官府,请求在其地改土归流,以“立救夷命”。
经清廷派人密查,合猛夷民俱称:
“群愿改流,早出水火。
”为避免夷民继续被土司鱼肉,杜绝沿边各土司效尤玩法,清廷同意在猛缅改设流官。
镇沅所属者乐甸土长官司,“江形山势尤为险阻。
”该长官司土司刀联斗昏庸乖戾,为害地方致民夷怨恨。
鄂尔泰遣将带兵至者乐甸质问,刀联斗自知罪无可逃,乃出迎并献印信与号纸,“但求免死,情愿归流。
”鄂尔泰奏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授以职衔,准予养赡。
该类型的主要特点,是清廷顺应夷民企望改流之请,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改流,并对提出改流的土司适当照顾予以安置,“以示鼓励。
”但此类改流的情形不多,且改流土司的级别较低。
澜沧江地区类型。
为解除日后隐忧,“以图一劳永逸,”雍正六年(1728),在用兵威远、新平诸倮土司的基础上,鄂尔泰遣军进剿云南澜沧江以内之孟养、茶山土夷。
先令车里土兵截诸江外,远征清军各持斧锹开路,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攻据六大茶山40余寨,并以降夷为向导继续深入,“无险不搜。
”随后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又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置兵,“以扼缅甸、老挝门户。
”清朝在澜沧江地区的用兵及改流,在边疆地区产生极大震动,广南土府、富州土知州各愿增岁粮二三千石,并捐建府州城垣;孟连土司献银厂,怒江野夷输皮币;老挝、景迈皆来贡象,“缅甸震焉”。
该类型突出的特点,是清廷为巩固边疆及防务而改流,清军远行数千里深入边地搜查,随后在各地设置营防,大致实现了鄂尔泰“将六茶山千余里地尽行查勘,安设营防”、“凡应安营设汛、并可建立州县之处一一斟酌妥确,以为一劳永逸之举”的设想。
改流后清廷仍保留一些土司,彻底改流之地仅限澜沧江以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则沿用土司。
三
雍正间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施行地区土司纵恣违法、危害社会的情形明显改变,当地社会秩序亦趋安定。
云南镇沅土府改流八个月后,据鄂尔泰调查,当地“夷民帖服,并无异议”。
乌蒙地区土司原颇凶悍,自改流设镇三年,鄂尔泰遣人不时查访,均“汉夷相安,颇称宁帖”。
雍正十年(1732),云南巡抚张允随在奏疏中说:
自鄂尔泰总制三省主持改土归流,“数百年未通声教之地尽入版图,”过去一些夷人“专以烧杀抢劫为事、捆掳索保营生”的情形大有改变。
若守土各官善为化导,夷人畏威怀德渐化淳良,“地方得以永远宁谧”。
十二年,据云南官吏尹继善奏疏报告,云南的普茅、思洱、元江与临安等地,自改流撤师以来,“地方宁谧,民乐耕耘,其招抚夷人俱已各安故业,现在禾苗遍野,妇子恬熙,迥非从前景象”。
改土归流解除了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在官府的积极招徕下,各地移民大量进入改流地区垦殖,情形以乌蒙地区最为突出。
雍正九年(1731),云南巡抚张允随奏准除镇雄、永善等地招抚复业外,由云南官府遍行晓谕,积极招徕百姓至“荒地甚多”的乌蒙地区垦种。
规定本省若有愿往乌蒙开垦住家者,不仅分给土地永为世业,而且官府借给工本,“按年扣还,照例升科。
”张允随还建议朝廷晓谕四川官府,有外省携眷入川尚未得安业者,由官府量给盘费置送来滇,“安插乌蒙垦种,”官府按照人口多寡拨给土地,“并借给工本,给照升科。
”预计一二年间乌蒙地区“尽换良民,生聚日繁,开垦日广”,千年荒芜之地可为“万年宁一之区”。
雍正帝朱批:
由川入滇应听其自愿,可由张允随移言川府,推动此事实现。
十二年,昭通府奏准朝廷拨银54800余两,修建滋泥、利济、拉擦等三河水利,不仅恩安、鲁甸已垦之地可资灌溉,还在附近地区增加水田万亩。
次年张允随上奏,昭通府自改流后,“土著夷民安居乐业,招徕垦户月益岁增。
”去年昭通秋收丰稔倍常,恩安、鲁甸、大关等处荞价甚平。
“恐荞价过贱,汉夷民人不知爱惜,”建议由官府照市价平买收藏,以增积贮。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土归流产生的深远影响逐渐显现。
乾隆十三年(1748),云贵总督张允随上奏,谓亲见从前苗倮之变,多由兵役欺凌、“汉奸”教诱,遂致夷民挺而走险。
自实行改流加强管理,惩办“汉奸”及严禁兵役滋扰苗寨,“现今内地苗夷咸皆宁谧。
”唯未改流之徼外尚“屡肆不法,杀掳公行”,经以兵征剿业已平息,现正处理善后事宜。
二十二年,云南巡抚臣刘藻奏云南省治安的情形,谓全省夷情与边境的情形大致相同,即诸族“沐浴圣化历年,已多畏法敬官,极为恭顺”;近年来边境虽有外夷内讧,多自相攻击,但因沿边要隘增拨土练,加强防范,“边民安堵,中外肃清”。
四十七年,云贵总督富纲、云南巡抚刘秉恬的奏疏称:
云南省土夷错处,涵濡教化百数十年,从前由土司管辖者大半改属流官,现今夷民“奉公畏法,最为醇谨”。
永昌、顺宁、普洱等沿边地区为世袭土司,界连外夷,过去或有因承袭、分产等事争执到官,经调查,“(现今)云南省土司并无彼此仇控、经年不结之案”。
其言或有粉饰,但云南社会基本安定、各族百姓奉公畏法应属事实。
贵州的情形与云南大体相同。
五十一年皇帝上谕说:
贵州古州苗民,雍正间经鄂尔泰戡定;“今承平日久,边境极为宁谧。
”次年,云贵总督富纲奏:
云贵两省地方辽阔,所在非苗即倮;云南普洱之思茅、贵州之古州,尤为极边紧要之地。
自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初时或尚有野性未训、致有煽惑蠢动之事,”教化至今50余年,夷人多有薙发衣冠、读书入泮者,“其语言、服食,与内地人民无异,”且改变从前专以射猎打牲为事的习俗,男子尽皆务农。
以上所说的情形,在改流以后的西南诸省较为普遍。
综上所述,明清两朝在西南蛮夷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原由虽复杂多样,但雍正朝施行较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却较为清楚,即主要是为解决一些土司或苗酋纵恣不法、危害社会,以及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资源,阻挠驿路开通及外来移民进入等问题。
另一方面,清廷注意到土司或生苗控制的地区夷汉百姓遭受欺压十分痛苦的情形,则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民生的关心,以及将这些百姓纳入国家的规范管理及法治保护下的企望,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为以较小的代价完成改土归流,雍正朝臣较注意调查研究,通常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施行改流的过程中讲究方式与方法,并由此形成若干种不同的类型。
这也反映出雍正朝臣之勤政以及吏治之清明。
雍正朝进行的改土归流,实质上是对土司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非彻底废除土司制度。
改流基本上获得预期效果,促进了改流地区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改流地区调整社会关系与民族关系。
同时应指出,雍正朝进行的改土归流,毕竟是封建剥削制度下政府主导的行为,因此具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
雍正朝在改流中虽强调“剿抚兼施”,但在一些地区仍肆意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