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悌 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docx
《李孝悌 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李孝悌 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docx(2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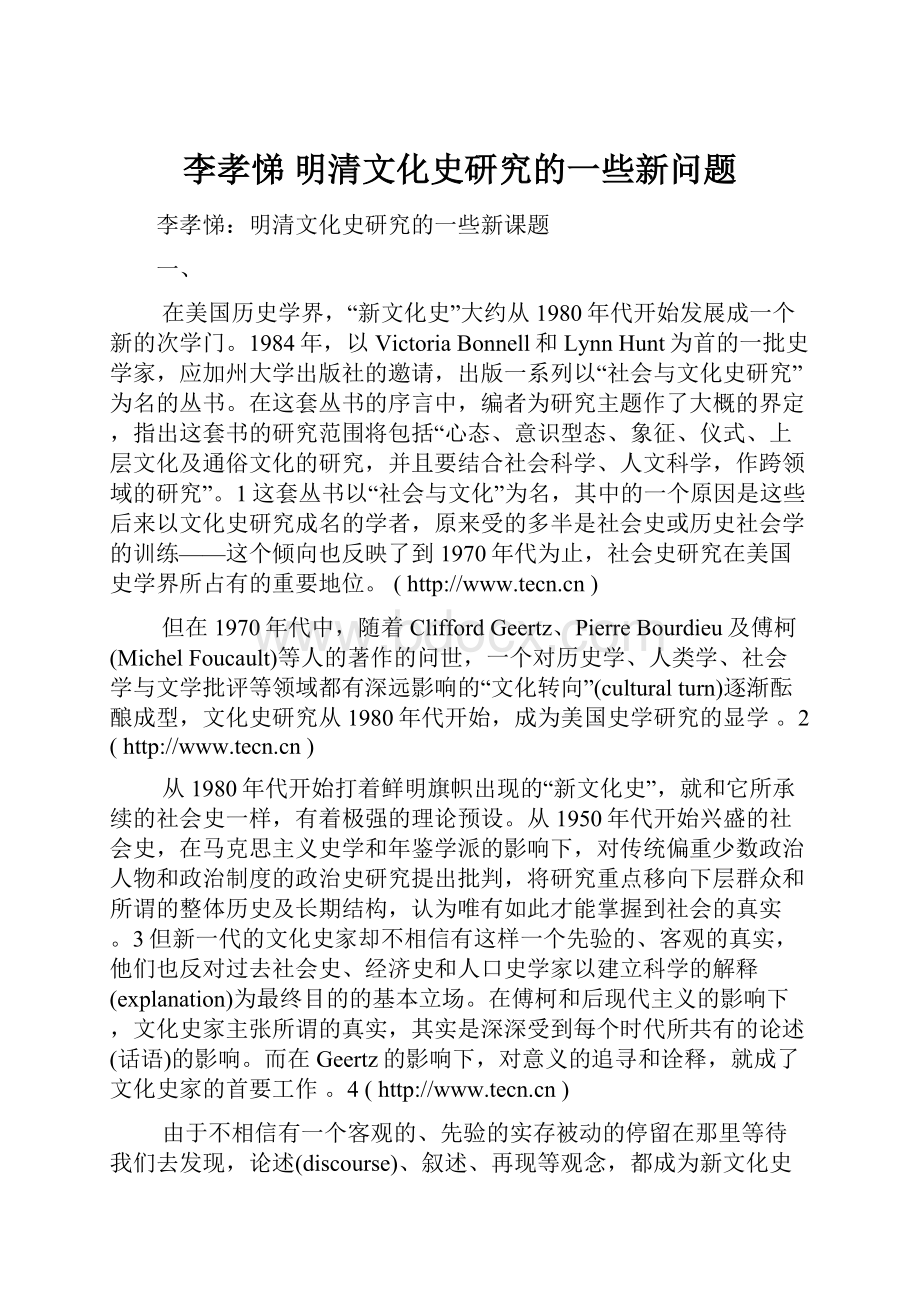
李孝悌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
李孝悌:
明清文化史研究的一些新课题
一、
在美国历史学界,“新文化史”大约从1980年代开始发展成一个新的次学门。
1984年,以VictoriaBonnell和LynnHunt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应加州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出版一系列以“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为名的丛书。
在这套丛书的序言中,编者为研究主题作了大概的界定,指出这套书的研究范围将包括“心态、意识型态、象征、仪式、上层文化及通俗文化的研究,并且要结合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作跨领域的研究”。
1这套丛书以“社会与文化”为名,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后来以文化史研究成名的学者,原来受的多半是社会史或历史社会学的训练——这个倾向也反映了到1970年代为止,社会史研究在美国史学界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
但在1970年代中,随着CliffordGeertz、PierreBourdieu及傅柯(MichelFoucault)等人的著作的问世,一个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学批评等领域都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逐渐酝酿成型,文化史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成为美国史学研究的显学。
2()
从1980年代开始打着鲜明旗帜出现的“新文化史”,就和它所承续的社会史一样,有着极强的理论预设。
从1950年代开始兴盛的社会史,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对传统偏重少数政治人物和政治制度的政治史研究提出批判,将研究重点移向下层群众和所谓的整体历史及长期结构,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掌握到社会的真实。
3但新一代的文化史家却不相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客观的真实,他们也反对过去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学家以建立科学的解释(explanation)为最终目的的基本立场。
在傅柯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化史家主张所谓的真实,其实是深深受到每个时代所共有的论述(话语)的影响。
而在Geertz的影响下,对意义的追寻和诠释,就成了文化史家的首要工作。
4()
由于不相信有一个客观的、先验的实存被动的停留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发现,论述(discourse)、叙述、再现等观念,都成为新文化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论上的问题。
此外,由于不相信我们可以经由科学的律则和普遍性的范畴来发现历史的真理,文化史家转而对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或独特性付出更多的关注。
不少知名的史学家放弃了过去对长期趋势或宏大的历史图像的研究,而开始对个别的区域、小的村落或独特的个人历史进行细微的描述,EmmanuelLeRoyLadurie和NatalieDavis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5()
文化史家虽然对科学的规则或普遍的范畴感到不满,并对一些受后现代主义和文学批评所启发的理论有细致深刻的思辨,但在从事实证研究时,却常常在课题的选择上招致批评。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权威学者FrancoisFuret就曾指责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缺乏明晰的焦点,同时由于没有清楚的定义,研究者只能跟随流行,不断地寻找新课题。
即使像RobertDarnton这么知名的文化史家,也批评法国的文化史家无法为心态史这个研究领域建立一套首尾一贯的观念。
6不管这样的批评是否公允,文化史研究的目的何在,似乎成了各地学者都要面临的问题。
()
二、
台湾的文化史研究,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萌芽。
其中虽然可以看到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在最初的阶段,对再现、叙述等观念的理论意涵,并不像前述西方史学家那样有深刻的省思,和历史社会学的关系也不紧密。
此外,由于台湾的文化史家不像西方的同行那样,对社会史的理论预设,因为有清楚的掌握从而产生强烈的批判,所以从来不曾把社会史研究作为一个对立的领域,并进而推衍、建立新文化史的理论框架和课题。
我们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新文化史研究其实是从社会史的研究延伸而出。
()
这个新的文化史研究方向,最早是从研究通俗/大众文化出发,然后有专门的团队以“物质文化”为题进行研究。
最近三年由中研院支持的主题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聚集了一批海内外的历史学者、艺术史家和文学史研究者,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为题,持续地进行团队研究,累积了相当的成果。
文化史的研究至此可以说是蔚为风气,一个新的研究次领域也大体成形。
()
在通俗文化的研究中,民间宗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社会史研究的影响在此清晰可见。
葬礼和三姑六婆等不入流的下阶层人物,也因此跻身为学院研究的对象。
接着学者开始从戏曲、画报、广告等资料去探讨城市民众的生活、心态和娱乐等课题,文化史的色彩日益凸显。
我自己和其它几位学者又进一步利用戏曲、流行歌曲、文学作品、通俗读物、色情小说等数据,对士大夫、一般民众以及妇女的感情、情欲、情色等感官的领域,作了一些踰越过去研究尺度的探索。
与此同时,和通俗读物有密切关系的明清出版市场,以及图像在通俗读物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等课题,也吸引了艺术史学者和历史学者的重视。
()
物质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已经被提上议程,却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在这一方面,对中古时期的椅子、茶/汤,以及明清时期的流行服饰、轿子等细微之物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这其中关于服饰和交通工具的研究,其实和海峡两岸学者对十六世纪初叶之后,商品经济的勃兴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及物质生活的改变所作的大量研究,有极密切的关系。
()
“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的主题计划在提出时,有一部分受到Braudel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及所谓的“totalhistory”的观念的影响,觉得我们过去对明清社会的研究,还有不少需要补白的地方。
但我们对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其它理论背景并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完全不知道LynnHunt等人也以“社会与文化史研究”为名,进行了十几年的集体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
()
虽然在计划提出时,我们都希望针对一些过去不会被拿来当作严肃学术研究对象的课题进行研究,但却不曾对探讨的课题作太多的限制或给予一个非常紧密、集中的理论框架。
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必须尊重研究团队各个成员自己的专长和兴趣,一方面也因为我们觉得生活或城市的历史自身就非常丰富、歧异,在对细节有更多的了解前,似乎不必用过分聚焦、狭隘的视野限制了可能的发展。
()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在过去三年中,对食、衣、住、行、娱乐、旅游、节庆、欲望、品味、文物、街道、建筑等课题进行广泛的探索,这些实证性的研究,除了提供许多新鲜有趣的视野,使我们对明清文化的了解有更丰富、多元的理解,也让我们建立了一些解释框架,再转过来协助我们去重新看待史料。
()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对这些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课题,作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这些课题包括:
逸乐作为一种价值、宗教与士人生活、士庶文化的再检讨、城市生活的再现、商人的文化与生活、微观/微物的历史以及传统与现代等。
()
三、
1.逸乐作为一种价值
我在《士大夫的逸乐:
王士祯在扬州》一文中,曾经对以逸乐作为学术研究的课题有下述的论辨:
“在习惯了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的角度,来探讨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后,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些人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在形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严肃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层文化。
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7()
这样的看法,并不是我一个人偶发的异见,而是我们长期浸淫在台湾的史学研究环境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省思和反映。
事实上,我们这个计划团队的成员,纷纷从不同的课题切入,指出在官方的政治社会秩序或儒家的价值规范之外,中国社会其实还存在着许多异质的元素,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这个文化传统的理解。
()
陈熙远在《中国夜未眠:
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一文中,利用巴赫汀(MikhailBakhtin)狂欢节的观念,对中国元宵节的历史与意涵作了深入的剖析。
8官方对这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节庆日,虽然原有一套规范的理念与准则,但在实践过程中,民众却踰越了种种规范,使得元宵节不仅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娱乐节庆,更成为颠覆日常秩序的狂欢盛会。
()
百姓在“不夜城”里以“点灯”为名,或在“观灯”之余,逾越各种“礼典”与“法度”,并颠覆日常生活所预设规律的、惯性的时空秩序──从日夜之差、城乡之隔,男女之防到贵贱之别。
对礼教规范与法律秩序挑衅与嘲弄,正是元宵民俗各类活动游戏规则的主轴。
……而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型的“走百病”论述,妇女因而得以进城入乡,游街逛庙,甚至群集文庙、造访官署,从而突破时间的、空间的,以及性别的界域,成为元宵狂欢庆典中最显眼的主角。
9()
元宵节固然为民众──特别是妇女──带来了欢愉和解放,却并不是唯一的例子。
庙会、节庆同样也能让民众从日常的作息和劳役中得到暂时的解脱。
巫仁恕对江南东岳神信仰的研究,显示在明清之际,江南各地不论是城市还是市镇,都会隆重的庆祝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东岳神诞会”:
“金陵城市春则有东岳、都天诸会”“诸皆遨游四城,早出夜归,旗伞鲜明,箫鼓杂沓。
”“无锡乡村男女多赉瓣香走东岳庙,名曰‘坐夜’。
江阴迎神赛会,举国若狂。
”“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为东岳天齐圣帝生辰,邑中行宫,凡八处,而在震泽镇者最盛。
清明前后十余日,士女捻香,阗塞塘路,楼船野舫,充满溪河,又有买卖赶趁茶果梨,……以诱悦童曹,所在成市。
”10()
这样的庙会节庆,和元宵节一样,发挥了重要的娱乐功能,但另一方面也同样潜在着颠覆既存秩序的危险。
一旦遇到政治、社会状况不稳定时,节庆的仪式活动很可能为民众的叛乱与抗争活动,提供象征性的资源。
11()
除了这些定期的节日和庙会庆典,明中叶以后流传的民众旅游,也提供了更多娱乐的机会。
这些旅游活动很多是和民间信仰中的庙会、进香有关,也有一部分是受到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晚明士大夫旅游风气盛行的影响。
根据巫仁恕的研究,晚明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城市附近的风景区都变成民众聚集旅游的胜地,北京、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附近的名胜都有“都人士女”聚游与“举国若狂”的景象。
在岁时节庆时,旅游活动的规模更加扩大。
12逸乐已经很明显的成为士大夫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环。
()
王鸿泰对游侠的讨论,更精辟地指出不事生产、纵情逸乐的游侠之风,如何在明清之际的士人文化中,成为“经世济民”“内圣外王”和科举考试等主流的儒家价值观之外,另一种重要的人生选项和价值标准。
这些士人由于在举业上受到挫折,逐渐放弃了儒家基本的价值观──齐家、治国、治世,并发展出一套全新的人生哲学和生活实践。
任侠、不事生产、不理家、轻财好客,纵情于游乐、诗酒活动成为这些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而城市则提供了实践这种游侠生活最好的舞台。
13()
在经济、宗教因素之外,价值观的改变,则为侠游或广义的逸乐活动带来了更正面的意义:
侠游活动,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新的人生观、生命意义的建构工作,而对整体社会文化而言,则可以说是种新的社会价值、生活意义的创造过程。
或者,更精确地讲:
侠游活动是个人透过特定的社会活动,以及相应的意义诠释,而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进行意义与价值创造的工作。
14()
我在这里以“逸乐作为一种价值”为标题,有两层意义:
一是用来呈现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明清文化的一种重要面相;一是要提醒研究者自身正视“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一种分析工具、一种视野以及一个研究课题的重要性。
而这两者又相互为用。
前面介绍的几项研究,都显示在明清士大夫、民众及妇女的生活中,逸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甚至衍生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
研究者如果囿于传统学术的成见或自身的信念,不愿意在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或感时忧国等大论述之外,正视逸乐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及切入史料的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整个明清历史或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势必是残缺不全的。
()
知名的思想史家StuartHughes在1958年出版的ConsciousnessandSociety:
theOrientationofEuropeanSocialThought,1890-1930一书中15,一开头就提到:
“自来历史学家便在不知所以然的情况下,一直在撰述‘高层次’的事物。
他们的性质气质投合于过去的伟大行为与崇高的思想。
社会科学的新自觉,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这种倾向。
”这句几乎是半个世纪前有感而发的议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特别是当我们要为逸乐这个软性、轻浮的,具有负面道德意涵的观念在学术史上争取一席之地时。
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型态,明清的儒家思想和欧洲中古的基督教、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或十九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在各个文明的实际进程和研究者的论述中所占有的主导性地位,是不需要有什么怀疑的。
但在主流之外,如何发掘出非主流、暗流、潜流、逆流乃至重建更多的主流论述,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这样的脉络下,Bakhtin对森严的中古基督教世界内的嘉年华会的研究16;PeterGay对启蒙运动中,哲学家对“激情与理性”等议题的辨析;17以及StuartHughes对十九、二十世纪初,实证主义之外的无意识作用和“世纪末”思想风气的论述18,无疑地都对我们在理学之外,彰显逸乐的价值,有极大的启发性。
()
2.宗教与士人生活
在我们从2001年到2003年所执行的三年主题计划中,宗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
西方汉学界过去二、三十年内,对民间宗教以及宗教与民众叛乱间的关系,已经作过大量的研究,有不少也成为典范性的作品。
巫仁恕对江南东岳神信仰的研究,除了指出庙会节庆活动幽默、滑稽与竞赛的娱乐功能外,并就民间信仰与城市群众的抗议活动间的关系,作了相当细致的阐述。
过去关于宗教的研究,多半将焦点集中在农村,对城市民变的研究,则侧重在经济社会面,而忽视了宗教所扮演的功能。
就此而言,巫仁恕对东岳神信仰和城隍信仰的研究,无疑是有许多新意。
()
相对于巫仁恕从城市群众与暴力的观点切入,我则特别想理解宗教在明清士大夫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之所以选择士大夫作为研究的重点,有一部分的理由和前述的逸乐观类似。
我的基本前提是:
作为意识型态的儒家思想或理学,虽然是形塑明清士大夫价值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因素。
过去的研究太侧重在作为主流意识型态的儒家思想在道德及理性层面所发挥的制约、规范力量。
在这样一个道德的、理性的儒学论述之后,那些被视为不道德的、非理性的、神秘的面相──如逸乐、宗教,在我们讨论明清士大夫文化、思想时,往往隐而不彰,甚至被刻意消解掉。
()
在我所处理的几个个案中,王士祯对风水、算命等宗教活动和各种奇怪可异议之论,表现出极高的兴趣。
袁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虽然不像王士祯那么清晰明确,但《子不语》和《续子不语》中,数十卷虚实相间的神怪故事,却构筑出一个丰富、驳杂的魔幻写实世界。
在十八世纪南京城的一隅,从儒家仕宦生活中退隐的袁枚,在自己的后花园中,发挥了无比的想象力,营造出一片神秘的宗教乐园。
19()
比袁枚早一个世纪的冒襄(1611-1693),虽然因为不同的原因中断了儒生的志业,却和袁枚一样,精心营造出一片园林,并在园林中充分享受了明清士大夫文化中的各种美好事物。
和袁枚一样,冒襄也在幽旷的园林中,留下了鬼魅魍魉的记述。
但不同于袁枚各项记述的虚实相间,冒襄却以惊人的细节,描绘了自己和亲人在死生之际的种种神秘历程。
更重要的是,冒襄因为赈济疾厉、灾荒而致病濒危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忠实地履践儒生经世济民的志业和地方士绅周济乡党的职责。
而他之所以能死而复生,则是因为在执行这些儒生的志业时所累积的功德。
另一方面,冒襄几次倾其所有的赈济灾民,背后的一个重大驱力,则是出于至孝之忱,希望以此累积功德,为母亲阴骘延寿。
()
CynthiaBrokaw的研究,指出功过格在明末清初士大夫阶层中普遍流传,有极大的影响力。
20冒襄的夫子自道,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极佳的例证。
但我特别感到有趣的是,在这个例子中,儒生的价值观和神秘的宗教信仰是如何紧密的纠结在一起。
21我们在研究明清士大夫的生活与文化时,如果只从一个特定的范畴──如儒生/文人,或学术的专门领域──如经学/理学/文学──着手,势必无法窥其全豹。
这些既有的学术传承常常让我们忽略了研究的对象并非都是“扁平型”的人物,而往往有着复杂、丰润的面貌。
文化史和生活史的研究,在此可以扮演极大的补白功能。
()
3.士庶文化的再检讨
我在1989年,首次对大/小传统或上/下层文化这套观念的由来,及其在中国史研究上的应用,作了简要的介绍22。
接着,我又在1993年,从“对民间文化的禁抑与压制”、“士绅与教化”、“上下文化的互动”三个角度出发,对十七世纪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与民间文化的关系,作了一次研究回顾。
23在此期间,台湾学界对民间文化的研究日益增长,但对上/下层文化这个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效力的质疑,也不断出现。
()
尽管有各种质疑,从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所作的研究中,却可以发现士庶文化这个课题仍有极大的探索空间。
王鸿泰、巫仁恕等人的研究,也让我们对明清的雅/俗、士/庶文化,有了耳目一新的看法。
()
根据巫仁恕的研究,一直到明代中叶,旅游还不被当成正经的活动,知名的理学家湛若水就对士大夫的山水旅游抱持轻蔑的态度。
不过就像许多其它现象一样,士大夫对旅游的观念也从明中叶以后渐渐有所改变。
旅游不仅被视为一种“名高”的活动,更成为士大夫中普遍流行的风气。
在士大夫笃好旅游之风的影响下,游记大量出现,旅馆日趋普及,甚至还有了为游客提供各项服务的代理人(牙家)。
士大夫出外旅游,除了呼朋引伴、奴仆相随外,也不时劳动僧道作为导游。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旅游并不是士绅官僚的专利,大城市附近的风景区往往也成为一般民众聚集旅游的胜地。
士大夫优越的身分意识,在这种情境中毫不遮掩地显露出来。
对他们来说,嘈杂的民众总是将美景名胜变成庸俗之地:
“使丘壑化为酒场,秽杂可恨”。
所以在游旅的地点和时间上,士大夫往往作刻意的区分,不是选择一般民众不常聚集的郊外山水,就是选择人踪稀少的季节或时辰。
同时,为了彰显自己独特的品味,他们也常常发展出独特的旅游观──所谓的“游道”。
对游具、画舫的讲求,就是士大夫展示其精致品味的具体表征。
24()
巫仁恕的研究,不但丰富了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内容,也为雅俗之辨找到一个有趣的切入点。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的流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模仿、复制士大夫文化,在晚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些庸俗化的模仿、复制,不但让自命风雅的文人名士感到不屑、厌憎,也往往引发他们对身分认同的自觉和危机感。
所以,区分雅俗,经营出特有的生活品味和风格,就成为明清文人士大夫的重要课题。
王鸿泰在《闲情雅致──明清间文人的生活经营与品赏文化》一文中,就对文人文化的特色作了全面而具有理论意涵的分析。
()
在王鸿泰看来,明清文人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建基于一套将世俗价值扫落于后的“闲隐理念”。
但重要的是,要实践这一套闲隐的理念,文人士大夫不但不能无为地坐任文化自动开展,反而要孜孜矻矻地努力建构。
王鸿泰在此提出生活经营的概念,可说是切中问题的核心。
我对袁枚随园和冒辟疆水绘园的研究,可以作为“经营”这一概念的脚注。
()
明清士人从闲隐的理念入手,在科举、仕进的价值观之外,开展出一套极为繁复的生活方式:
“在具体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明中期以后,为士人所强调,且为之别辟意涵的闲隐生活,并非循着山林隐逸的传统,也并未简单地以‘朴素’对抗‘繁华’(或者以‘原始’对抗‘文明’),事实上,它是在发展一种‘闲’而‘雅’的生活模式,它开展出极为繁复、丰富的生活形式及相关论述。
它在建立一套新的生活美学──一种优‘雅’的生活文化,且以此自我标榜,以此对抗世‘俗’的世界,进而试图以此新的生活美学来参与社会文化的竞争,……这就是明清文人文化发展契机与内涵。
”25()
巫仁恕提到士大夫在旅游地点和季节、时辰的选择上的讲求,与王鸿泰此处所说的雅俗对抗,可以前后互应。
除了山川旅游、诗酒酬唱、歌舞笙箫外,对玩物的耽溺,也是士大夫雅文化的要素:
“明后期士人‘闲隐’理念的具体落实乃开展出一套‘雅’的生活,而所谓雅的生活可以说就是在生活领域内,放置新的生活内容,这些生活内容如上所言:
无非‘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也就是说将诸如书画、茶香、琴石等各种无关生产的‘长物’(或玩物)纳入生活范围中,同时在主观态度上耽溺其中,对之爱恋成癖,以致使之成为生活重心,进而以此来营造生活情境,作为个人生命的寄托,如此构成一套文人式的闲赏文化。
”26()
这种对雅文化的追求,自明中叶以后逐渐形成,在不断的充实与渲染之后,渐渐成为士人/文人特有的文化类型,这个文人文化一旦发展成优势的文化类型,就引起社会上不同阶层,特别是商人阶层的仿效。
文人为了划清与这种附庸风雅的复制、赝品间的界限,乃格外重视雅俗之间的辩证。
()
4.城市生活的再现
在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中,邱仲麟是真正从一般民众切身的生活琐事着手,讨论明清北京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
他在这几年内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内,分别讨论了民众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燃料、用水,以及如何用冰来维持食物的新鲜,并缓解酷热的气候所造成的不适。
27()
煤炭、用水与冰,看起来和闲雅的士大夫耽溺其中的书、画、茗、香、琴、石一样,都是琐细之物,但所具有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由于邱仲麟能将这些琐细之物,放在更广大的生态史和制度史的脉络下来考察,不但使原来看似干涩的典章制度和单调、没有生命的结构、物质,因为和生活紧密相连,而产生新的意涵;也同时让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细琐之物,能承载更严肃的使命。
()
北京居民原来是靠附近森林所提供的木柴,作为主要的燃料。
但随着人口的增长,饮食炊爨、居室建材等需求加大,山林滥伐的问题日益严重,柴薪的供应也日趋枯竭,从十五世纪后半叶开始,煤炭的使用日益普遍,渐渐取代柴薪。
成为主要的燃料。
煤炭固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