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知识.docx
《古典文学知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典文学知识.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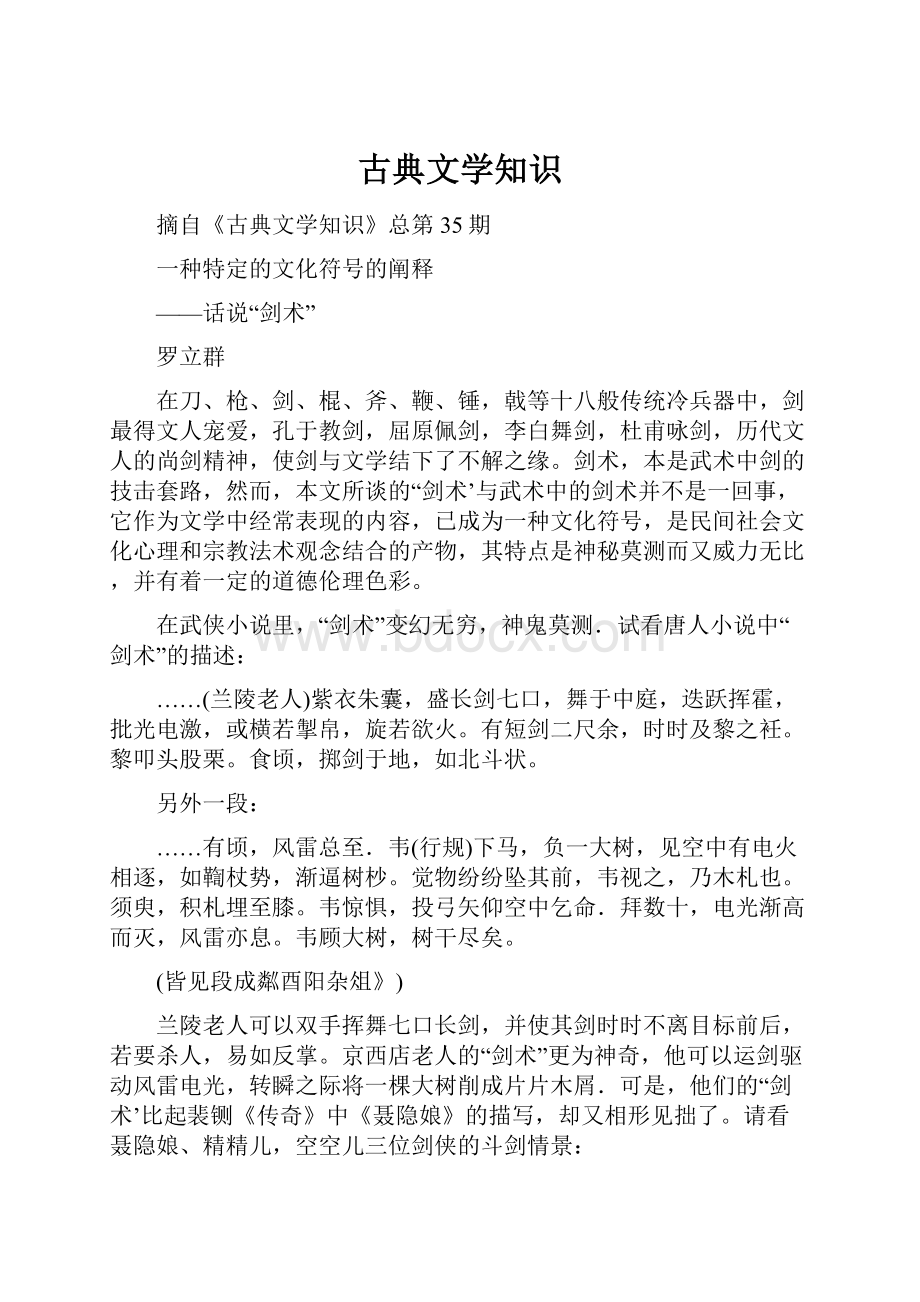
古典文学知识
摘自《古典文学知识》总第35期
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的阐释
——话说“剑术”
罗立群
在刀、枪、剑、棍、斧、鞭、锤,戟等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最得文人宠爱,孔于教剑,屈原佩剑,李白舞剑,杜甫咏剑,历代文人的尚剑精神,使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剑术,本是武术中剑的技击套路,然而,本文所谈的“剑术’与武术中的剑术并不是一回事,它作为文学中经常表现的内容,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民间社会文化心理和宗教法术观念结合的产物,其特点是神秘莫测而又威力无比,并有着一定的道德伦理色彩。
在武侠小说里,“剑术”变幻无穷,神鬼莫测.试看唐人小说中“剑术”的描述:
……(兰陵老人)紫衣朱囊,盛长剑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批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欲火。
有短剑二尺余,时时及黎之衽。
黎叩头股栗。
食顷,掷剑于地,如北斗状。
另外一段:
……有顷,风雷总至.韦(行规)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火相逐,如鞫杖势,渐逼树杪。
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
须臾,积札埋至膝。
韦惊惧,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数十,电光渐高而灭,风雷亦息。
韦顾大树,树干尽矣。
(皆见段成粼酉阳杂俎》)
兰陵老人可以双手挥舞七口长剑,并使其剑时时不离目标前后,若要杀人,易如反掌。
京西店老人的“剑术”更为神奇,他可以运剑驱动风雷电光,转瞬之际将一棵大树削成片片木屑.可是,他们的“剑术’比起裴铡《传奇》中《聂隐娘》的描写,却又相形见拙了。
请看聂隐娘、精精儿,空空儿三位剑侠的斗剑情景:
……是夜明烛,半宵之后,果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良久,见一人自空而踣,身首异处.隐娘亦出曰:
“精精几已毙。
”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
隐娘曰;“后夜当使妙手空空儿继至。
空空儿之神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能从空虚入冥,善无形而灭影。
隐娘之艺,故不能造其境。
此即系仆射之福耳.但以于阗玉周其颈,拥以衾,隐娘当化为蠛蠓,潜入仆射肠中听伺,其余无逃避处。
”刘如言。
至三更,瞑目未熟,果闻项上铿然,声甚厉。
隐娘自刘口中跃出,贺曰:
“仆射无患矣1此人如俊鹘,一抟不中,即翩然远逝,耻其不中耳.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
”后视其玉,果有匕首划处,痕逾数分。
能飘然于空中相斗,能钻入活人腹中,来无影去无踪,眨眼功夫飞行千里,“剑术’之高、之奇,令人不可思议。
这类“剑术”描写,在以后的武侠小说中一直延绵不绝,且越变越奇,至民国年间《蜀山剑侠传》问世,终于达到了奇幻绝伦的顶峰。
古人对于这种神奇的“剑术”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
司马迁在《史记》里慨叹荆轲刺秦王的失败是在于“惜哉,疏于剑术”;楚霸王项羽力能扛鼎,勇敌万夫,武艺超群,“去学剑’竟“不成”,无法领悟“剑术”的精妙旨意。
司马迁所说的“剑术”恐怕不是武术中的剑术技击,而是传说中的神奇‘剑术”了。
唐代小说中凡写剑侠施展“剑术”,或曰亲眼目睹,或曰听某人自述亲身经历,言之确凿,不容置疑。
明人王世贞在《<剑侠传>小序》中认为专诸、聂政那样力敌众人、不畏生死的刺客之流,其剑术“反其粗耳”,难入正宗。
凌潆初在其话本小说《初刻拍案惊奇》里更明确指出;“专诸、聂政诸人,不过义气所使,是个有血性好汉,原非有术。
若这等都叫做剑术,世间拼死杀人,自身不保者,尽是术了?
”凌氏认为世间确有“剑术”,但不是专诸、聂政那样的血性、武功,相比之下,“剑术”要神奇得多。
古人如此迷信“剑术”,那么,这神奇而又虚幻的“剑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追根溯源的探讨。
剑,身窄而两面有刃,轻便灵活,素有“百器之君”之称。
据史籍记载及出土文物的印证,剑作为传统的冷兵器,几乎是与青铜器的使用同时产生的.春秋时代就已大量使用青铜剑,至战国时期,铁剑登上历史舞台.稍后,韧而又刚,坚而不脆的钢剑一跃而起,统治剑坛。
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剑越铸越精,越来越利,人们对剑的崇拜心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普遍.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诸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极力寻找和聘请精于冶炼技术的工匠,为自己铸造神兵利器。
据史书记载,先秦时期著名的铸剑大师就有薛烛,风胡子、欧冶于、干将,莫邪等人,而著名的剑器则有莫耶、鱼肠,吴鹊,扈稽、湛卢、钝钩、胜邪、巨阙、龙渊(也作龙泉)、泰阿(也作太阿)、工布等。
先秦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着严重的威胁。
随着剑器在战争中的普遍使用和产生功效,人们为摆脱内心的恐惧和寻求安定,便幻想三尺青锋在手,就能制敌全身,由此而产生对剑器的寄托和崇拜。
这种寄托和崇拜在民间巫祝风气盛行,宗教鬼神思想的传播指引下,很自然地升级为一种超自然的幻想,剑器被神秘化和人格化了。
剑器在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首先是在剑型、剑纹和剑饰上涂以神幻色彩,配以威灵之物,增益其超自然的功能。
欧冶于师徒被风胡子请至楚国,为楚王造了三把宝剑:
一日龙渊,二日泰阿,三曰工布。
铸成后,楚王问风胡子,“何谓龙渊、泰阿,工布?
”风胡子答道:
“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泰阿,其弧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弧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
”《古今刀剑录》一书是记载古代刀剑的专著,为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所著,书中著录了夏禹、太康、孔甲,殷太甲、武丁、周昭王、秦昭王,秦始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等君王所铸和所佩带的宝剑,都有一定程度的神幻色彩。
如记“夏属于帝启,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铜剑,长三尺九寸,后藏之泰望山腹上。
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为星辰,背记山川月日。
”其次,是优美动人而又神奇的铸剑传说和剑器的拟人化。
汉赵晔《吴越春秋》记载,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其妻莫邪自投于炉中,铁汁乃出。
遂铸成雄雌二剑,取名干将、莫邪(人名、剑名合一)。
干将进雄剑于吴王,自藏雌剑。
雌剑思念雄剑,常悲鸣。
《晋书·张华传》中则记载剑气以及剑的变化,飞腾和消失,带有一定的神秘气氛和人化色彩。
再次,剑器被神化为能祛除妖魔,压邪避祸,遇难呈祥的法宝。
晋人王嘉在笔记小说集《拾遗记》中写道:
“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
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赴,指其方则克。
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吟。
”
剑器被神化为“剑术”的过程中,除了上述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之外,还有文学自身的继承和发展因素。
最早对“剑术”予以文字描述的是庄周。
《庄子·说剑>>篇中描述了战国时期的击剑风气,并具体细微地阐述了运剑之道。
庄子认为;“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
”并指出用剑时,要“忘己虚心,开通利物,感而后应,机照物先”,如此这般,方能达到‘其剑十步杀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的绝高境界。
《吴越春秋》也描述了一位精通“剑术”的越国处女论剑之道:
越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
“臣闻越有处女,国人称之。
愿王请问手战之道也。
”于是王乃请女。
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
问女曰:
“闻子善为剑,得一观乎?
”处女曰:
“妾不敢有所隐也。
惟公所试。
”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槁,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应节入之三女。
因举杖击之,袁公飞上树,化为白猿。
打败袁公后,越女见到了越王。
越王请教“剑之道”,答曰:
其道甚微而易,其意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
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皮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先若仿佛,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
越女说完后,当场表演,其“剑术”果能“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天下无敌。
,庄子与越女的“剑术理论叶分相似,异曲同工,这极为深奥而又充满辨证哲理的“剑论”,对后世武侠小说中神奇剑术的形成,无疑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古书中不仅论及“剑道”,而且将其具象化,用形象生动的故事来叙述剑器的神幻。
《列子·汤问》中有一则关于邱邴章之子来丹借剑为父报仇的故事。
来丹之父被黑卵所杀,黑卵力大无穷,骨硬皮坚,刀枪不入,来丹只有依靠“剑术’来复仇。
他听说孔周藏有殷帝之宝剑,能“却三军之众”,便往求之。
“孔周曰:
‘吾有三剑,唯子所择,皆不能杀人。
且先言其状,一日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有,其所触也,泯然无际,经物而物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所触也,窃窃然有声,轻物而物不疾也。
三日宵练,方昼则见影而不见光,方夜则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也,[]然而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焉。
此三宝者,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于事。
匣而藏之,未尝启封。
”来丹借了“宵练”剑去杀黑卵,乘黑卵醉卧之时,“自颈至腰三斩之”,黑卵却毫无动静,仍然沉睡.来丹知道“宵练”剑果然不能杀人,叹而归去。
书中写来丹寻觅神剑,蓄意报仇,虽然不曾杀死黑卵,但“含光”,“承影’、‘宵练”三剑的神奇之处依然可见,为后世武侠小说中描写神乎其神的“剑术”提供了借鉴。
在剑器衍化为‘剑术”的发展过程中,佛教与道教的贡献最大。
佛教的传播使剑器的神化得以加强和完善,并直接推动了唐代剑侠小说的创作。
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妙吉祥最胜根本大教王经》有成就剑法,云:
“持明者用华铁作剑,长三十二指,巧妙利刃。
持明者执此剑往山顶上,持诵大明,至剑出光明,行人得持明天剑有烟焰,得隐身法。
剑若暖热,得降龙法,寿命一百岁。
若法得成,能杀魔冤,能破军阵,能杀千人。
于法生疑,定不成就。
”又有圣剑成就法。
”又云,“若欲成就剑法,及入阿苏罗窟,当作众宝像,身高八指’云云。
按唐小说记剑侠诸事,大抵在肃、代,德,宪之世,其时密宗方昌,颇疑是其支别。
如此经剑法,及他诸神通,以摄彼小说奇迹,固无不尽也。
这段记载详细叙述了佛家修行“剑术”之法,“剑术”的威力,修练者的心诚以及对唐代剑侠小说的影响。
相比之下,道教对剑器的神化和崇拜更加狂热。
道教徒一向把剑视为设道场、显神通、驱邪镇魔的法物,并且十分重视“炼”剑.道教是讲究丹鼎之术的,认为凭此能炼出长生不老之药,吞服可助修仙,所以,剑也只有被拿来冶炼(已不完全是科技中的冶炼技术了,而是含有宗教情绪的修炼宝物)后,才能成为神器.明代钱希官在《狯园》中有一篇《青丘子》就是专讲炼剑之事。
青丘于隐于武当山炼剑,属下有青童玉女守炉看火,有专备炼剑的净室:
……室中有药鼎,高数尺,周遭封固,紫焰光腾,照耀林壑,第教生以守炉看光,添缩薪炭,不得擅离妄视而已。
每昼则有玉女持稠膏一筒,投鼎中,搅和之,鼎中声类霹雳.夜半则有青童复持稠膏,依前沃入,其声[][]如旧。
此室之中,玉女二人,青童二人,更番直应,
日以为常。
生偶问及鼎中何物,皆笑而不对。
先生已具知之,愠怒诟责,便欲驱逐出门,众相跪请乃止,后遂不敢发问。
久之,丹鼎成矣,出其金液,计可六百余斤,分而为二,又折之至七八斤而止。
移置大磐石上,捣之,昼作夜息,渐渐而薄,因成铁片。
择甲午、丙午诸日,铸成六剑,悬于绝壁之下,以飞瀑溅激其上,日月之光华烛之,历经旬朔,剑质始柔。
类似这样的描述,在明清以后的文言短篇和长篇白话小说中经常出现.剑即炼成,就是神器宝物,它可以纳于口中,也可以藏于脑后,或藏于指甲间,用剑时,只须放出一道剑光便可制敌于死地.高手之间斗剑,仅有神剑还不行,还需用剑者有神通,这些佛道都能办到。
葛洪在《抱朴子·对俗篇》中列举了道教修行可掌握的诸种神术异能,如’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召致虫蛇,合聚鱼鳖,三十六石,立化为水,消至为饴,溃金为浆,入渊不沾,蹴刃不伤,幻化之事,九百有余。
”剑侠具备了这些神通,更加出神入化,来去自如,神鬼莫测了。
由于佛道思想的浸透,身怀“剑术’神通的剑侠,其行为举止总有着一股出家人的气味,他们或来无影去无踪,事成拂衣去,不图利和名,或隐居深山大泽,专事修行,不管凡尘人事.他们是超脱世俗红尘之外的高人,是怀着慈悲心肠来拯救世人出苦海的术士,是披着宗教服装的侠客,或是手握利剑的僧家道士。
剑使神通广大,行侠人间,颇类似于西方当代科幻化了的“超人”,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剑侠与“超人”有本质的不同,“剑术”与科幻本领也大相径庭。
“剑术”是中华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产物,是中华民族渲泄情感的一种“有意味”的表现形式。
它有着中华大地泥土的芳香,有着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情感,也带有中国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色彩。
具备‘剑术’神通的剑侠,必需有着佛家的‘慈悲’襟怀,道教的‘隐逸”思想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
正如《七剑十三侠小引》所说;“所谓‘剑仙大侠’似乎都在世乱之时才出现人间:
其实这也是必然之理!
因为盛治之时,文教昌明,民心耻格,事实上也不须有‘剑侠’的白刃,到了纲常弛废,道义沦亡时,奸邪当道,强梁横行,居上位的只管淫侈骄恣,在下位的也单知阿谀囊括,土豪劣绅棍徒恶霸辈便益发肆行无忌!
良善的人们只能遭摧残,被冤抑,受压迫,忍哀怨,于是一般剑侠便要来代天伸诛了。
”剑侠出自乱世,“剑术”是行侠人间的手段,若有人用“剑术’行不义之事,就会带来杀身之祸,其“剑术”甚至会失去灵验。
我们在小说经常看到剑侠艺成出山,其师必再三叮嘱,不得持“剑术”为非做歹,否则必遭天遣。
非但如此,宝剑作为一种神器,有德者才配得到,无德之人纵拿到它,也必定会失去,所以,武侠小说中众多的神兵利器总是归正派侠士所拥有。
至于要练成无所不能的“剑术”神通,更须是一位心无杂念的具有传统美德的正人君子才行。
《七剑十三侠》里海殴子说:
“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练气,采取五金之精,炼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方才有用。
”(第一回)飞云子曰:
“谈道术者,第一要戒淫。
”(六十四回)玄贞子云;“古来剑仙侠客,那一个不从忠孝节义四字上做起?
”(七十回)可见,不具备传统伦理道德的人是练不了“剑术”的。
综上所述,‘剑术”的形成有一个剑器神幻化、人格化、具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社会宗教,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所以说,武侠小说中的“剑术”描写,并非是一味胡编乱造、不着边际的空想,而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有着明确意义、道德情感和宗教情绪的文化符号,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充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心理和精神内蕴的情感特征。
(作者:
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
《古典文学知识》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宝玉挨打的分析
【作者】吴世昌
《红楼梦》是一部大家熟悉的小说,但不一定每一个读者都熟悉其中每一个故事。
我常把这部书比作一个中国的大园林,譬如颐和园。
它整个是一座大花园,但它包含一个个各自成趣的、独立的小花园或院子。
风格各不相同。
例如颐和园里的仁寿宮不同于谐趣园,但各有妙处,而且一处处互相沟通,却又别有天地。
《红楼梦》全书象座大花园,里面每一回或二、三回的故事是一个独立的小花园。
这些小花园又有曲径、回廊、小桥、清溪互相通幽,互相映带,由一回发展到另一回,就像从一个院子转到别一个暗中相通的院子。
作者对于整个小说的布局也是如此。
一个读者随意浏览此书,往往可以得其大意,而忽略了他精雕细琢、颇费匠心的部分。
我们现在提出书中一个故事来讨论学习。
这个故事读者可能早已看过,也许还不止一次,正如某一名园以前早已游览过,但也不妨对比一下,以前旧游之地,这次重游,有没有发现以前所未注意的地方?
有没有“温故而知新”?
我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
作者写书中任何一个故事,都有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两个方面。
我们选读“宝玉挨打”这一故事,也许读者早已痛恨贾政性子暴躁,心狠手辣;其实贾政的这种行为自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
他对贾母说:
他这样打宝玉是为了“光宗耀祖”换句话说,他是在执行封建教育,他自己也成为这一万恶传统的牺牲者而不自知。
原来,为了维护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国有国法,家有家法。
贾政自以为他在执行家法。
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即使在内部,也要用国法或家法来压制不顺从的分子。
当时的国法还有条文可循,不触犯条文的可免惩罚。
家法则随各封建家庭自立自制,并无明文规定,有时可以比国法更不讲理,更不通人情,即更为野蛮。
一个封建家庭的少数“主子”可以压制多数奴仆,即是凭“主子”们随意订立的“家法”的作用。
家法听起来好象是一本法律,实际上是一套刑具。
所谓“伸家法”就是用刑敲打。
《红楼梦》二十三回宝玉挨贾政的毒打,就是封建家族中对其自己成员“伸家法”以压制异端思想的形象说明。
当然,宝玉挨打的原因并非那样简单,只是贾政为了压制异端思想。
而且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这种思想也不容易看出来。
至于挨打的结果,也并非表明贾政的胜利,倒是被袭人转化利用为她的胜利(下面要说到),宝玉脑子里的异端思想,贾政也不可能用大板子从他的屁股上打下去。
贾政也不是凭抽象的思想问题就动火打儿子。
如果只是那样的写法,就不是大文豪笔底下的作品了。
曹雪芹写贾政打宝玉,在贾政的立场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是非打不可的;故事本身使读者觉得:
如果他处在贾政的地位,见儿子窝藏供应王府的优伶——与王爷争夺男宠,使他遭到王爷的忿怒,认为他教子无方,在官场贵族中大丟其脸,何况家中又出了人命案子,原因是宝玉要“强奸母婢”,使她含羞自杀,这两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可以使封建家族的为父者怒打儿子,何况宝玉一人犯此两件罪过,同时并发。
曹雪芹写贾政之恶,不在于他怒打儿子,而在于他偏听妄信,对重大事情没有调查清楚,就粗暴发怒,动手用刑。
他不但做了自己野蛮性子的俘虏,而且还做了他的劣子贾环的俘虏,他被贾环调唆得昏头昏脑,对他被贾环利用来作为打击宝玉的工具而不自知。
如果宝玉真被打死了,则是贾环成功地假贾政之手以杀宝玉。
而被作为凶具用的贾政却仍不自知,还以为他替封建社会整顿了歪风邪气,有功于世道人心。
分析宝玉挨打的原因,若仅就贾政所得的“报告”而论,两事都有该受惩罚的理由。
但仔细推究,都不是宝玉之罪。
琪官在外面买房子,躲开忠顺王的召唤,宝玉有何罪?
宝玉是琪官的好友,知有此事,被忠顺王府长史作为“外调”对象,他本来想替琪官隐瞒,后来被点出证据,只好照实说了,这又有什么大罪?
至多受几声呵责,或小打警戒.反正忠顺王府找着了琪官,也不会责怪宝玉隐藏。
琪官自己不愿再在忠顺王府被王爷当男妾玩弄,他是演员,要自立门户,单独在社会上谋生,又有何罪?
所以,如果没有“强奸母婢不遂,逼得她羞恨自杀”这一条事关人命的重大案件,如果没有这一假造的报告,也不至于两罪俱发,使宝玉受此重打。
所以这一顿打,是贾环的大成功、大胜利。
这一打对贾环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读者在未读到第三十四回时,决不会想到:
这一打对袭人也有利,对宝钗也有利;只有对两人不利:
一个是直接受皮肉之苦的宝玉自己,一个是受袭人在王夫人之前的“浸润之谮”的林黛玉。
——这一点下面还要分析,现在且按下不表。
贾政打宝玉,除了偏听妄信之外,还有为自己泄愤的成分。
例如他听见王夫人提起“老太太一时不自在了,岂不事大?
”便冷笑道:
倒休提这话。
我养了这不肖的孽障,已不孝;教训他一番,又有众人护持,不如趁今日一发勒死了,以绝将来之患!
“说着便要绳索来勒死”。
这虽是气话,也显得他已无教子成材之意,徒存为己丢丑之恨。
他这几句话,使他这一顿打完全失去了他所谓“光宗耀祖”的教育意义,只有泄忿的作用而已。
在这之前,作者写贾政只要用刑,并不问罪。
他一见宝玉,“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
”作者写他不问罪行,而只要“着实打死”,这种封建官吏对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一旦出来做地方官,对老百姓的虐待不言可知。
因他“不问”,使宝玉无从为自己辩白。
作者对于记在宝玉账上的罪状,究竟是谁犯的,其实写得一清二楚。
金钏儿怎么死的?
正是那位“阿弥陀佛”、宽厚仁慈的王夫人一个嘴巴打了还不够,立刻要把她撵出去,原因是:
金钏儿对宝玉说:
“你到东小院子里拿环哥儿同彩云去。
”就因为说了这句话,王夫人认为“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
即使跪下哭求:
“我跟了太太十来年了”,也不中用,还得滚。
(三十回)金钏儿觉得从此无脸见人,只好跳井。
但这条人命的账,却被贾环写在宝玉的名下,而贾政深信不疑。
为了金钏儿的死,宝玉所付的代价是被打得皮绽肉破,而王夫人所付的代价是三十两银子、两套旧衣服(是宝钗捐出来的)、“几件簪环”,又请几个僧人为她念经超度。
这在当时社会风尚看来,似乎已经很优待死者了——因为她不过是一个婢女。
有此赏脸,已经使她母亲白老媳妇“磕头谢了出去”。
即使那个聋婆子,把“要紧”听做“跳井”,也认为“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
”死个把个人“有什么不了的事?
……太太又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的!
”婆子看人命如此不关重要,可见封建教育中毒之深。
这个婆子应该是与金钏儿同一个阶级的女奴出身吧!
然而她对于自己阶级的一条人命,其代价也只要两套衣服、几两银子而已。
作者这样叙述,恐怕比满纸是什么“阶级斗争”、“奴隶造反”等口号更为真实些。
至于王夫人为此事有些内疚,也不失为实事求是,题中应有之笔。
但作者也并不因此就肯定这个刚愎而愚昧的贵夫人。
下面,我们还要论到:
她怎样变成了袭人的俘虏,正如她丈夫变成了贾环的俘虏。
“宝玉挨打”作为一个高度戏剧性的场面,作者是精心布置的。
宝玉正因为听说金钏儿自杀,才在路上低头感叹,“五内摧伤”,一到厅上,仍是神魂出舍,一头撞在贾政身上,被他带住。
又因为方才见贾雨村时对答不利,已招父怒,此时又垂头丧气,自不免被贾政看出来,他有“思欲愁闷气色”,读者已先替宝玉捏一把汗,知道凶多吉少,已经铺排好了悲剧的气氛。
正在这时,突然来了忠顺王府里的长史官要见贾政.要他帮忙,代索琪官(蒋玉菡)回府。
及至问到宝玉,他还推说不知,王府的长史只好点出琪官送他红汗巾的事(事见二十八回);宝玉才说出琪官在郊外紫檀堡买了房子的事。
长史官何以知有“红汗巾”的事,其中必另有曲折,作者故意不说,要把它留作下文故事的线索。
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未了,宝玉出家后,袭人嫁与蒋玉菡(琪官)。
结婚后,蒋发现袭人有此“红汗巾”,即当年他与宝玉交换的礼物。
但三十三回长史官来调查琪官下落时已知有此红汗巾事,他何从知道,确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且按下不表。
但这一发展,更富于戏剧性,宝玉之终于要挨打,至此已无可避免,火上加油的是贾环的谎报陷害:
我母亲(赵姨娘)告诉我说:
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大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那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
如果只听听这样的报告,当然谁都要生气的。
但贾政却不问情由,不分皂白,不辨真伪,一顿乱打。
直到王夫人出来抱住板子哭“珠儿”,他才停止。
这些戏剧性的发展,都是入情入理。
写在纸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似乎已经达到高潮。
但更高的高潮却要等贾母出来才来到:
贾母说:
“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
”贾政还强辨说,他教训儿子,也是为“光宗耀祖”,贾母便问:
“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
”贾政不是正途出身,可见他青年时并未好好读书,所以一辈子不学无术,连大观园中作对子都不如自己儿子,顶嘴也顶不过贾母。
贾母问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
”可谓直刺其心。
这里也流露贾母对他的不满:
没有正途科举出身,只靠祖宗的余荫做闲散的京官,终于不免坐吃山空!
宝玉挨打以后,大家利用他这次的不幸,纷纷奉承,以求见情。
最善于这类人情世故的当然是宝钗,即刻送药来敷伤治疗。
袭人则忙于打听挨打原因,自作准备。
她们二人都想利用这一顿打来改造宝玉的思想,以符合封建道德传统的标准。
宝钗说:
“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
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
”这话也许是真情,但“早听人一句”什么“话”呢?
因为说到她不成材的哥哥薛蟠,她到底要为他辩护,不免要批评宝玉:
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
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
老爷才生气……
真正为宝玉挨打而伤心的,恐怕只有林黛玉。
她的无声之泣、“满面泪光”,“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不敢让来问病的凤姐看见,怕她取笑,只好从宝玉床背后的后门溜走了。
王夫人的心疼也是真的,因为金饥儿毕竟是她逼死的,宝玉却因此而挨大板子。
逼死金钏的内疚与痛子受刑同时进发,不如平时刚愎自用,比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袭人看准了这一点,乘机进谗。
袭人向焙茗调查清楚了真实原因。
她找了焙茗来细问:
“方才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
”焙茗说是为琪官和金钏儿的事,“那金钏儿的事是三爷(贾环)说的。
我也是听见老爷的人说的。
”“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景,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