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docx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docx(2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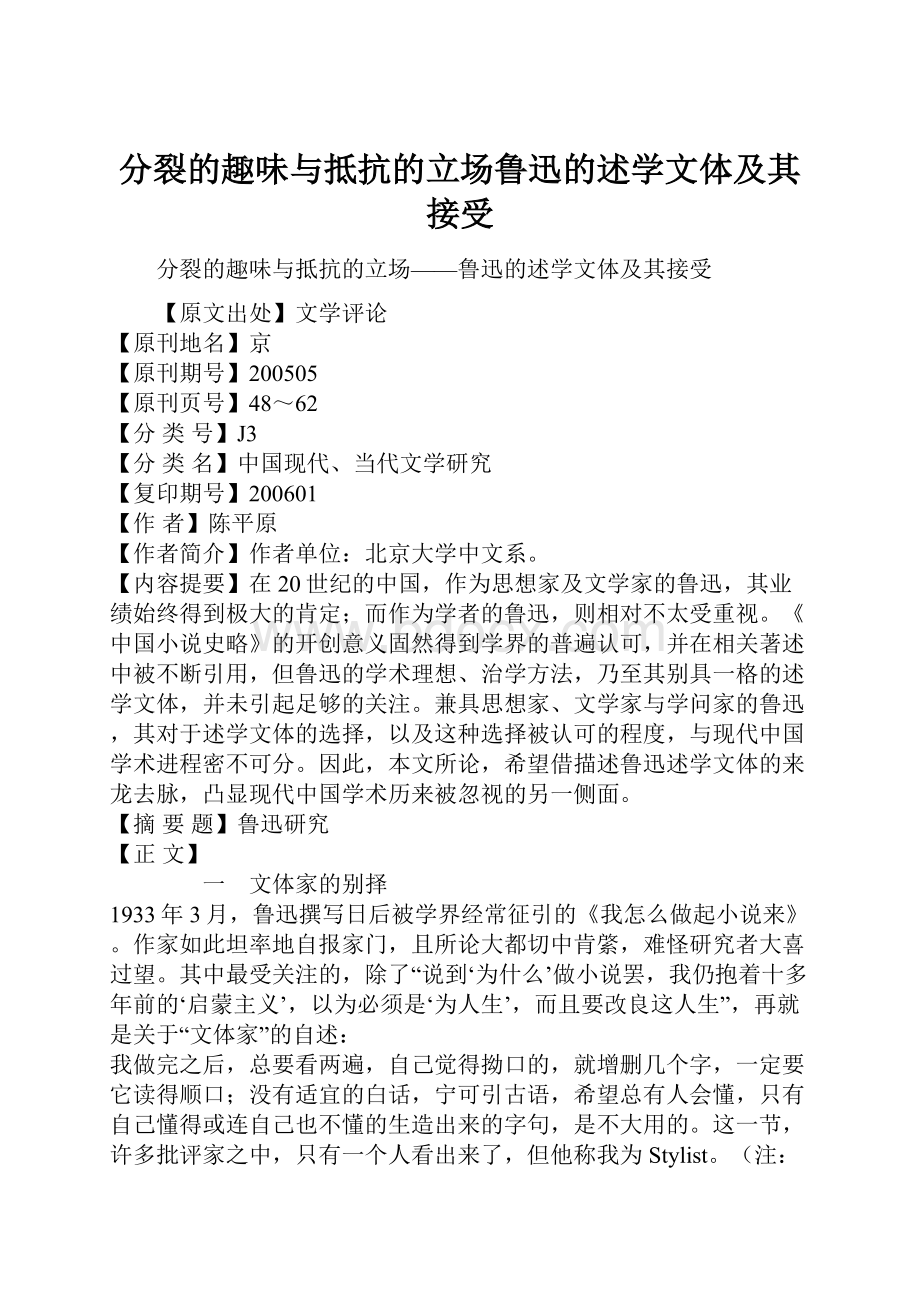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
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505
【原刊页号】48~62
【分类号】J3
【分类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200601
【作者】陈平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中国,作为思想家及文学家的鲁迅,其业绩始终得到极大的肯定;而作为学者的鲁迅,则相对不太受重视。
《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意义固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在相关著述中被不断引用,但鲁迅的学术理想、治学方法,乃至其别具一格的述学文体,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兼具思想家、文学家与学问家的鲁迅,其对于述学文体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被认可的程度,与现代中国学术进程密不可分。
因此,本文所论,希望借描述鲁迅述学文体的来龙去脉,凸显现代中国学术历来被忽视的另一侧面。
【摘要题】鲁迅研究
【正文】
一 文体家的别择
1933年3月,鲁迅撰写日后被学界经常征引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作家如此坦率地自报家门,且所论大都切中肯綮,难怪研究者大喜过望。
其中最受关注的,除了“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再就是关于“文体家”的自述: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适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注: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512—513页,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最早将鲁迅作为文体家(Stylist)来表彰的,当属黎锦明的《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
可黎氏此文将Stylist译为体裁家,将“体裁的修养”与“描写的能力”分开论述,强调好的体裁必须配合好的描写,并进而从描写的角度批评伤感与溢恶,夸张与变形等(注:
黎锦明《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文学周报》5卷2期,1927年8月)称:
“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Stylist)者。
……我们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所谓体裁这名词,到现在还是没有。
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
后者所涉及的,本是文体学所要解决的难题,如今都划归了“描写”,那么,所谓的“体裁”,已经不是Style,而是Gener——这从黎氏关于章回小说《儒林外史》的辨析中,也不难看出。
倒是鲁迅关于Stylist的解读,接近英文本身的含义(注:
韦勒克和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
三联书店,1984年)第十四章“文体和文体学”称:
“文体学研究一切能够获得某种特别表达力的语言手段,因此,比文学甚至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广大。
所有能够使语言获得强调和清晰的手段均可置于文体学的研究范畴内:
一切语言中,甚至最原始的语言中充满的隐喻;一切修辞手段;一切句法结构模式。
”(191页))。
黎氏对Stylist的误读,其实很有代表性,因古代中国作为文章体式的“文体”,与西学东渐后引进的探究语言表达力的“文体”(Style),二者之间名同实异,但又不无相通处。
直到今天,中国学界谈论文体,仍很少仅局限于语言表达,而往往兼及文类(注:
30年代修辞学家陈望道撰《修辞学发凡》,论及文体时称,有八种分类方法:
民族的分类、时代的分类、对象或方式上的分类、目的任务上的分类、语言的成色特征上的分类、语言的排列声律上的分类、表现上的分类,依写说者个人的分类等。
而作者最为关注的是第七种,即“表现上的分类”,包括“简约和繁丰”、“刚健和柔婉”、“平淡和绚烂”、“谨严和疏放”这四组八种体性(《修辞学发凡》26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90年代,申丹撰《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区分文学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等。
论及狭义的文体即文学文体时,作者称:
“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如果局限在文学文体学,论者一般都会兼及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而不仅仅是语言分析。
)。
如此半中不西——或者说中西兼顾——的批评术语,使我们得以将“Stylis”的命名,与“新形式”的论述相钩连。
就在黎氏撰文的前几年,沈雁冰发表《读〈呐喊〉》,赞扬鲁迅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
(注:
雁冰:
《读〈呐喊〉》,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
鲁迅没有直接回应茅盾关于其小说“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评述,但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称此书“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注:
《〈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2卷342页。
),除顺手回敬成仿吾的批评,也隐约可见其挑战常识,不以“文学概论”为写作圭臬的一贯思路。
你可以说沈从文、张天翼是文体家,那是指其小说体式的讲究;你也可以说茅盾的《子夜》、《白杨礼赞》和《中国神话研究》各具特色,可那是体裁决定的。
明显的文体意识,使得鲁迅所撰,即便同是小说、诗歌、散文、杂文,表达方式也都很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这一“文体感”背后,有明显的文化关怀。
汉魏以降,中国人喜欢讲文章体式(注:
最典型的,莫过于曹丕的《典论·论文》: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
合体式而又能创新,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创造。
可几乎所有的“文章辨体”,都侧重历史溯源,而非逻辑分析,故显得灵活有余,精确不足。
这里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重视具体经验,而不太擅长抽象思辨;但很可能还隐含着一种重要思路——任何大作家的出现,都可能打破常规,重建文类边界。
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七《文辨》中有一妙语,大致表明了“文章辨体”的意义及边界:
“或问文章有体乎?
曰:
无。
又问无体乎?
曰:
有。
然则果何如?
曰:
定体则无,大体则有”。
认定“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的鲁迅(注: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6卷3页。
),关注的是那些不太守规矩、着力于另辟蹊径的作品。
比如,表彰俄国的《十二个》以及日本的《伊凡和马理》强调的都是其“体式”的“异样”,或“格式很特别”(注:
参见《〈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7卷301页;《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3卷342页。
)。
鲁迅本人的写作,同样以体式的特别著称,比如作为小说的《故事新编》,以及散文诗《野草》。
《野草》最初连载于《语丝》时,是被视为散文的(虽然其中《我的失恋》标明“拟古的新打油诗”,《过客》则是剧本形式,可以直接转化为舞台演出)。
等到鲁迅自己说: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注: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4卷456页。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异口同声地谈论起散文诗来。
鲁迅曾自嘲《朝花夕拾》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文体大概很杂乱”(注:
《〈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2卷230页。
)。
其实,该书首尾贯通,一气呵成,无论体裁、语体还是风格,并不芜杂。
要说文体上“很杂乱”的,应该是指此前此后出版的杂感集。
《且介亭杂文》中的《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阿金》等,乃道地的散文,可入《朝花夕拾》;《准风月谈》中的《夜颂》、《秋夜纪游》则是很好的散文诗,可入《野草》。
至于《门外文谈》,笔调是杂文的,结构上却近乎著作(注: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这样的开篇,确实不像学术论文。
可这十二则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系列短文,有完整的理论构思,非寻常杂感可比。
第二年,此系列短文加上其他关于语文改革的四篇文章,合为《门外文谈》一书,由上海天马书店单独刊行。
)。
文章体式不够统一,或者说不太理会时人所设定的各种文类及文体边界,此乃鲁迅著述的一大特征。
轮到鲁迅为自家文章做鉴定,你会发现,他在“命名”时颇为踌躇。
翻阅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四卷的《鲁迅著译书目》、第七卷的《自传》、第八卷的《鲁迅自传》和《自传》,其中提及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纂辑以及译作、著述等,态度都很坚决;但在如何区分“论文”和“短评”的问题上,则始终拿不定主意。
称《坟》为“论文集”,以便与《热风》以降的“短评”相区别,其实有些勉强。
原刊《河南》的《人之历史》等四文,确系一般人想象中的“论文”;可《看镜有感》、《春末闲谈》、《灯下漫笔》以及《杂忆》等,从题目到笔法,均类似日后声名显赫的“杂感”。
将《坟》的前言后记对照阅读,会觉得很有意思。
后者称,“在听到我的杂文已经印成一半的消息的时候”——显然当初鲁迅是将此书作为“杂文”看待,而不像日后那样将其断为“论文集”;前者则干脆直面此书体例上的不统一: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结集,并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注:
参阅《写在〈坟〉后面》和《〈坟〉题记》见《鲁迅全集》1卷282页、3页。
)。
反过来,日后鲁迅出版众多“杂感集”,其中不难找到“违规者”。
在《二心集》的序言中,鲁迅称:
“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于是百无禁忌,在这回“杂文的结集”里,连朋友间的通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注:
参见《〈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4卷189—192页。
)。
其实,不只是朋友间的通信,《二心集》里,除作为主体的杂感外,既有论文(如《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演讲(如《上海文艺之一瞥》)、传记(如《柔石小传》),也有译文(如《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答问(如《答北斗杂志问》)、序跋(如《〈艺术论〉译本序》)等,几乎无所不包。
同样以说理而不是叙事、抒情为主要目标,“论文”与“杂文”的边界,其实并非不可逾越。
鲁迅不愿把这一可以约略感知但又很难准确描述的“边界”绝对化,于是采用“编年文集”的办法,避免因过分清晰的分类而割裂思想或文章。
对于像鲁迅这样因追求体式新颖而经常跨越文类边界的作家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创举。
在《〈且介亭杂文〉序言》里,鲁迅进一步阐释“分类”与“编年”两种结集方式各自的利弊,强调“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
“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注:
《〈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6卷3页。
)——如此纵论“古已有之”的“杂文”,恰好与《〈坟〉题记》的立意相通。
也就是说,鲁迅谈“杂文”,有时指的是“不管文体”的文章结集方式,有时讲的又是日渐“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独立文类(注: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卷291页、293页。
)。
学界在谈论鲁迅的杂文观时,一般关注的是后者,即作为文类的“杂文”或“杂感”。
像“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注:
《〈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5卷4页。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
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
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6卷291页、293页。
);以及“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
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注:
《做“杂文”也不易》,《鲁迅全集》8卷376页。
)等,这些都是常被鲁迅研究者引用的“绝妙好辞”。
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作为文章结集方式的“杂文”,即“不管文体”导致的不同文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渗透。
在《〈华盖集〉题记》、《〈华盖集续编〉小引》、《〈三闲集〉·序言》、《〈伪自由书〉前记》等文中,鲁迅明明将自家写作命名为“杂感”、“杂文”,可为何在各类自述文字中,却又改用面目模糊的“短评”?
是否因意识到《华盖集》等其实是以“杂文”为主体的“编年文集”,而不是文章分类意义上的“杂文集”,并因此做了区分,目下不得而知。
但鲁迅的“短评”集之兼及杂文、散文、论文、书信、日记等文类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鲁迅文章的丰富性,以及鲁迅“文体”的多样性。
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很早就提及这一点:
“把鲁迅的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放在一起研究,就能特别明显地看出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以及体裁的多样化”(注:
谢曼诺夫著、李明滨译:
《鲁迅和他的前驱》102页,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
如只是涉及鲁迅短篇小说、散文诗、回忆记、杂文、散文等文类的成就,以及各文类内部的革新与变异,自茅盾以降,已有无数论述。
我关心的是鲁迅的“论文”与“杂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希望将这一关注贯穿到语言层面。
二 论著、杂文与演讲
同样是文章名家,周氏兄弟的“文体感”以及写作策略却明显有别:
周作人是以不变应万变,同一时期内的所有撰述,不管是翻译还是创作,是散文还是专著,笔调基本一致。
鲁迅则很不一样,不要说翻译和创作不同,小说与散文不同,即便同是议论,杂文与论文的笔调,也都可能迥异。
换句话说,读周作人的文章,可以采用统一的视点,而且不难做到“融会贯通”;读鲁迅的作品,则必须不断变换视点,否则,用读杂文的眼光和趣味来读论文,或者反之,都可能不得要领。
后世关于鲁迅的不少无谓的争论,恰好起因于忽略了作为“文体家”的鲁迅,其写作既源于文类,而又超越文类。
只读杂文,你会觉得鲁迅非常尖刻;但反过来,只读论文和专著,你又会认定鲁迅其实很平正通达。
很长时间里,我们习惯于将鲁迅杂文里的判断,直接挪用来作为历史现象或人物的结论,而忽略了杂文本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特征。
在尊崇鲁迅的同时,违背了鲁迅顾及全人与全文的初衷(注:
在《“题未定”草(六)》中,鲁迅这样谈论陶渊明:
“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全集》6卷422页)。
)。
“文化大革命”期间编纂的三种鲁迅言论集,即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选的《鲁迅论外国文学》(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中山大学中文系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论中国现代文学》(广州:
中山大学,1978)和厦门大学中文系所编的《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在给学界提供很大便利的同时,也留下了若干后遗症。
除了“选本”和“语录”的盛行,必定缩小读者的眼光;更因其将论文、杂文以及私人通信等混编,很容易让人忽略论者依据文类所设定的拟想读者与论述策略,导致众多无心的误读或“过度阐释”。
这三种言论集目前使用者不多,但《鲁迅全集》电子版的出现,使得检索更为便利。
于是,寻章摘句以及跨文类阅读,使得上述问题更为严重。
除了专门著述,鲁迅杂文中确实包含了大量关于古代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论述。
这些论述,常为后世的研究者所引用。
必须正视将鲁迅杂文中的只言片语奉为金科玉律的负面效果;但如果反过来完全否认蕴涵在鲁迅杂文中的睿智的目光及精湛的见解,无疑也是一大损失。
如何超越这一两难境地,除了前面所说的顾及全人与全文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将鲁迅论敌的眼光包括在内——杂文作为一种文类,其补阙求弊的宗旨以及单刀直入的笔法,使得其自身必定是“深刻的片面”。
所谓“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注:
《〈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4卷191页。
),鲁迅的抱怨,主要针对的是读者之缺乏通观全局的目光和思路,而过于纠缠在个别字句或论断上。
杂文的主要责任在破天下妄念,故常常有的放矢;而论文追求“立一家之言”,起码要求自圆其说。
二者的目标与手段不同,难怪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
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后,鲁迅还在很多杂文中谈论唐宋传奇以及明清小说。
单看结论,你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缝隙,但鲁迅并没有修订旧作的意图——《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本序提及马廉和郑振铎的贡献,也只是偏于资料订正。
假如你一定要把鲁迅众多杂文中对于林黛玉的讥讽(注:
参见《坟·论照相之类》、《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二心集·宣传与做戏》、《花边文学·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花边文学·看书琐记》和《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
),作为鲁迅对于中国小说的“新见解”来接纳,而不是将其与梁实秋论战的背景,以及对梅兰芳自始至终的讨厌考虑在内,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那里,“文类意识”与“文体感”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马上日记之二》评说《伊凡和马理》,兼及其“文法”与“体式”的“欧化”;《答KS君》批评《甲寅》,也是将“文言文的气绝”与“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相钩连(注:
参见《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3卷342页;《答KS君》,《鲁迅全集》3卷112页。
)。
至于《坟》的前言后记,更是兼及“体式”(论文、杂文)与“文体”(文言、白话)的辨析。
并非混用概念而不自觉,而是有意识地将“体式”与“文体”挂钩——鲁迅这方面的思考,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
《〈坟〉题记》中关于《摩罗诗力说》写作过程的叙述,似乎只是个人经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河南》杂志的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愈长稿费愈多;再加上受《民报》文风的影响,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注:
《(坟)题记》,《鲁迅全集》1卷3页。
)。
这一叙述,得到钱玄同、周作人回忆文章的证实。
鲁迅刚逝世,钱、周分别发表文章或答记者问。
前者称周氏兄弟跑到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目的是文字修养:
“他们的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注:
钱玄同:
《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1936年10月26日《世界日报》(北平)。
)。
后者也提及当初“每星期日亦请太炎先生在东京民报社内讲学”,紧接着补充道:
“彼时先兄尚有出版杂志之计划,目的侧重改变国人思想,已定名为《新生》,并已收集稿件”(注:
参见《周作人谈往事》1936年10月20日《世界日报》(北平)。
)。
周氏兄弟早年的思想及文章受章太炎影响很深,这点学界早有定论。
我想证明的是,这种影响,并非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周氏兄弟的崛起于文坛而自动终结。
尤其是对于“述学文体”的探索,章太炎的影响十分深远(注:
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以及拙文《作为“文章”的“著述”》(见《掬水集》,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
古代中国,不乏兼及文学与学术者,现代学者则很少这方面的追求。
鲁迅及其尊师太炎先生,应该说是少有的将“著述”作为“文章”来经营的。
换句话说,鲁迅之无愧于“文体家”称号,应该包括其学术著述——除了学术见解,也牵涉文章的美感,以及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调适。
后人撰小说史著时,喜欢引鲁迅的“只言片语”,因其文辞优美,言简意赅,编织进自家文章,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其他人的论述(如胡适、郑振铎等),也有很精彩的,但引征者大都取其观点,而不看中其审美功能。
晚清以降,随着新教育的迅速扩张,学者们的撰述,包括了专著、演讲、教科书等;而这三者之间的边界,表面上壁垒森严,实际上很容易自由滑动。
按理说,不同的拟想读者和传播途径,必定影响作者的述学文体。
可在实际操作中,好的系列演讲,略加整理就可成书(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教科书若认真经营,摇身一变,又都成了专著(如《中国小说史略》)。
专著需要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鲁迅很清楚这其间的缝隙。
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注:
在《〈集外集〉序言》中,鲁迅称:
“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
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
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
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鲁迅全集》7卷5页)),或因与相关文章略有重复(注:
参见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
只要入集的,即便是演讲,也都大致体现了鲁迅思考及表达的一贯风格。
但是,作为演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主要是案头之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二者虽都有学术深度,可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后者严守史家立场,前者则多有引申发挥,现场感很强。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六讲,乃鲁迅1924年7月在西安讲学时的记录稿,经本人修订后,收入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印行的《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
(二)》中。
开头与结尾,确系讲演口吻;中间部分则颇多书面化的表述(注:
如“敬梓多所见闻,又工于表现,故凡所有叙述,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为独多而独详”云云,就不能说是口语实录。
)。
不过,即便如此,对比其专门著述,还是大有区别。
其中谈过了《官场现形记》后,接下来便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部书也很盛行,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常常张大其词,又不能穿入隐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
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
(注: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鲁迅全集》9卷335页。
)
这段话,根基于《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如下表述:
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注: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鲁迅全集》9卷282页。
)
两相比较,前者之接近口语,与后者的简约典雅,形成鲜明对照。
演讲与著述之间,如果只是文体差异,一通俗,一深邃,那问题还不是很大。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允不允许借题发挥。
根据演讲整理而成的《从帮忙到扯淡》,将屈原的《离骚》概括为“不得帮忙的不平”,宋玉则是“纯粹的清客”,好在还有文采,故文学史上还是重要作家云云(注:
《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6卷344页。
以上。
),与《汉文学史纲要》关于“屈原及宋玉”的论述,便有天壤之别。
《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论及屈原作《离骚》,毫不吝惜褒奖之辞:
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注:
《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鲁迅全集》9卷370页、375页。
)
至于宋玉所撰《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注:
《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鲁迅全集》9卷370页、375页。
)。
如此赞誉,哪有日后“清客”之类讥讽的影子。
如此“前言”不搭“后语”,与其说是思想演进,不如考虑文体的差异。
谈及鲁迅的“偏激”,研究者有褒有贬,但多将其作为个人气质,还有思维方式以及论述策略(注:
要说鲁迅的“偏激”有策略性的考虑,最合适的例